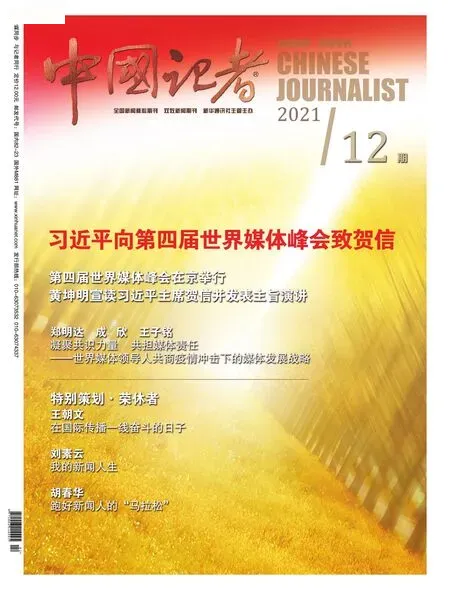我的新聞人生
□ 劉素云
2021年6月11日,我面戴N95口罩、身著防護服,登上了開羅飛往中國的航班,告別了我新聞生涯的最后一站——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開羅記者站,并在回國后辦理了退休手續,我的新聞人生由此畫上了句號。
年紀稍長的人,都會記得一部老電影《李雙雙》,里面男女主人公有這樣一句臺詞:“先結婚,后戀愛。”這些年來,我常常借用這句臺詞來形容我與新聞持續38年的緣分。我當年進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是大學畢業時學校分配的。那時,中文系畢業的我還懷揣著一個文學夢,從未想過與新聞相隨相伴。但是慢慢地,我開始喜歡上新聞,后來又發自內心地愛上了這份工作,直至把它當成我生命的一部分。由此我也相信,一個人只有熱愛工作,才會有熱情投身其中,才會不斷涌現激情,迸發靈感,最終有所創造、有所成就。
國際部:我新聞生涯的引路人
至今仍記得,1983年8月25日,剛剛大學畢業的我,怯生生地走進了有武警把守的廣播電視部的大門。威嚴的武警戰士,宏偉的蘇式建筑,高高的迷宮般的回廊,還有書桌上或排列整齊或隨意堆放的報刊、剪報,以及式樣典雅的臺燈,都給人一種神秘感和神圣感。我的新聞生涯就從這里開始了。
在干部司辦完報到手續,我被告知分到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當時,我只知道廣電部下屬有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臺的名字還是第一次聽說。隨后,我被安排在國際部,擔任國際新聞編輯。
國際部是國際臺的國際新聞發稿部門,每天編發近百條國際新聞稿件,供全臺各語種選用。
為了提高國際報道的時效和質量,國際部同事們為此付出了很多辛苦。先是每天早、中、晚三班輪值,到后來實行每周7天、全天候24小時值班發稿制度。前方記者寫稿爭分奪秒,后方編輯部也是分秒必爭,跟新華社比快慢,跟國際主流媒體比時效,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作品。
國際部是我在國際臺工作的第一個部門,也是我新聞生涯的起點,在老一輩新聞人身邊耳濡目染,他們不僅教會我如何做新聞,更讓我看到新聞人的執著追求與不懈堅守,引領我樹立正確的新聞觀,培養了我作為新聞人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時政采訪:風光背后的辛苦與歷練
從1991年到2000年,我作了9年的時政記者。在這一特殊的工作崗位上,我自覺地要求自己、歷練自己,在新聞職業道路上得到新的升華。
時政記者,看似風光,實際是一個辛苦、責任重大的職業。首先要有強烈的政治意識,事關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大活動,不得有絲毫閃失。還要有很強的保密觀念。
說起吃苦,最苦的莫過于沒有時間睡覺。那樣的經歷,現在想起來,還讓人心有余悸。記得有一次在莫斯科,晚上困得頂不住了,手似乎還在鍵盤上敲,但屏幕上出來的都是亂碼。最后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就決定上床躺10分鐘,然后再起來寫。結果,一倒在床上,就睡得人事不省,直到有人敲門。
迷迷糊糊地打開門,一個服務員問:“你房間什么東西燒著了嗎?”
我一下驚醒了:“沒有呀!”
她伸著鼻子聞了聞,眼睛掃到了床頭柜上的電熱杯。
想起來了,那是我躺下之前燒上的。電熱杯里的水已經燒干,電源還通著,結果把實木的床頭柜烤糊了,發出一股焦糊味。她就是尋著這股糊味找過來的。
當時,國際臺時政組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國家主席一年一度對海外聽眾的新年講話。
大國元首發表新年講話是國際慣例。邀請中國國家主席通過國家對外廣播電臺發表新年講話的設想,最早是國際臺提出的,得到了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主席辦公室的首肯。
中國國家主席第一次通過國際臺發表新年講話是1990年。當年12月31日,中國國家主席的新年講話《我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通過國際廣播電臺的43種語言,傳送到了世界各國。
自此之后,國家主席通過國際臺發表新年講話成為慣例。我本人則幾次參與新年講話稿的錄制等工作。隨后,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相繼加入進來,現在隨著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的成立,國家主席新年講話也改為通過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和互聯網發表。
幾年的時政記者生涯,培養了我的責任心、敬業精神、吃苦精神、合作精神,使我養成了細心、嚴謹、守時的工作作風,多年來受益匪淺。
耶路撒冷:激情燃燒的新聞歲月
2000年7月15日,我告別北京,告別親人,登上飛往以色列的飛機,從此開始在耶路撒冷4年零3個月駐站生涯。這期間,正好趕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爆發新一輪武力沖突,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應該說,能到這樣一個世界熱點地區做記者,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非常值得珍惜的機會,同時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和挑戰。在此期間,我多次前往以軍封鎖下的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區采訪,前往發生在以色列的自殺爆炸現場采訪,寫出了一系列鮮活生動的報道,并獲得中國新聞獎等國家級獎項。我本人也因為這幾年的出色表現,于2009年榮獲第十屆長江韜奮獎(韜奮系列)。
直面危險。說起耶路撒冷,許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爆炸。我駐站4年期間,以色列共發生了100多起自殺性爆炸,其中一多半都在耶路撒冷。餐廳、咖啡廳、超市、公共汽車……都是爆炸的目標。多少次,我們與爆炸擦身而過;在記者站所在的公寓,時常清楚地聽到爆炸聲、炮擊聲;武裝直升機、戰斗機馬達的轟鳴成為伴隨我們入眠的戰爭交響。
2000年月10月,我與同事前去巴以沖突中心地區加沙地帶實地采訪,成為沖突爆發后最早到現場采訪的中外記者之一。直到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次采訪中這樣一個細節。在加沙中部的尼茨薩利姆猶太人定居點附近,以軍士兵與巴勒斯坦人發生了沖突。一群巴勒斯坦青年不停地向以軍崗樓投擲石塊,躲在崗樓里的以軍士兵則不時地向人群開槍射擊。隨著槍聲,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倒下了,就在離我十幾米遠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沖突,第一次面對真槍實彈。
記者永遠在現場。要完成一篇好的新聞作品,經常要付出許多辛苦。至今我還記得當初采寫錄音報道《巴以兒童的節日期盼》時的情景。
2000年9月爆發的巴以流血沖突,給巴、以雙方的孩子們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因此,在2001年“六一”兒童節前夕,我們決定就此采寫一篇報道,通過孩子們的生活與遭遇,來反映巴以沖突給雙方造成的傷害,以及這一地區人們對和平的長久期待。首先,我們通過當地記者聯系到加沙的一個巴勒斯坦家庭。這是一個很具典型意義的家庭。家中共有6個孩子,排行老二的12歲男孩杜拉,在巴以沖突爆發不久的一次交火中被以軍槍炮擊中身亡。當時,這一場景被正在現場的法國電視二臺記者拍攝下來,并在世界各大媒體反復播放。小杜拉由此成了在沖突中受害的巴勒斯坦兒童的象征。一時間,加沙街頭到處張貼著小杜拉遇害時的圖片,為他創作的歌曲《杜拉之歌》廣為傳唱。
5月的一天,我們驅車來到以色列與加沙交界處的埃雷茲檢查站,隨后又在一名巴勒斯坦司機兼翻譯的陪同下,走訪了小杜拉在加沙南部難民營的家,采訪了他的父母和哥哥。
對以色列孩子的采訪則選擇了幾個不同的場景,其中一個是位于耶路撒冷南郊的吉魯猶太人定居點。由于吉魯緊鄰阿拉伯村鎮,沖突爆發以來一直是巴武裝人員的襲擊目標,因此,這里的學校、民宅大部分都裝上了防彈玻璃窗。在一個家庭幼兒園,我們還看到了用大約3公分厚的鋼板制成的一段“圍墻”。在采訪中我們獲悉,一些猶太定居者當天要在總理府舉行示威。我們于是又迅速趕往總理府,采訪了參加示威活動的兒童,錄制了不少生動的現場音響。幾天后,我們又采訪了耶路撒冷的一所公立小學校,并將學生們演唱的著名的《和平之歌》作為文章的結尾。
曾讀到一篇新聞理論文章,文中引用一位老前輩的話說:新聞是用腳板寫出來的,意即記者一定要多跑,多到事件發生現場去。據此,又有人引申說:新聞是用眼睛寫出來的。其實,不管是用腳還是用眼,講的都是一個道理,即記者要腿腳勤快,多外出采訪。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提倡的新聞記者的“四力”,即腳力、眼力、腦力、筆力。
與阿拉法特“零距離”。2001年12月,以色列為報復巴勒斯坦激進分子連續制造3起自殺爆炸,先后出動坦克、裝甲車將巴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圍困在約旦河西岸拉姆安拉總統府中。阿拉法特的命運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當時由于以軍的圍困,阿拉法特失去了行動自由,這位“國際旅行家”甚至不能離開拉姆安拉半步。在這種情況下,阿拉法特也希望借助媒體向國際社會傳達他的聲音。于是,我們與新華社駐耶路撒冷的記者一起多方聯系,對阿拉法特進行了專訪,時間是2002年2月6日。
那天一早,我們從耶路撒冷出發,途中經過以軍的三個檢查站,中午時分進入拉姆安拉,被獲準進入總統府已是晚上。在經過長時間等待后,我們幾名中國記者和另外幾名巴勒斯坦聲援者意外被邀請與阿拉法特一起共進晚餐,采訪安排在晚餐之后。
記得餐廳就在辦公室旁邊,里面有一個小廚房。正對門的墻上懸掛著一幅熟悉的照片:東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薩清真寺和金頂巖石清真寺——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是阿拉法特一生的追求和夢想。餐桌上鋪著白色桌布,上面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盤子,都是阿拉伯傳統家常食品,蔬菜、雞蛋、面包、奶酪等。整個晚餐過程中,阿拉法特沒有說太多的話,但看得出來,他的胃口不錯。阿拉法特還不斷招呼大家用餐,并將面包蘸上果醬一塊塊送到大家手中。他還指著工作人員端上的一盤甜點介紹說,這種點心是用芝麻和蜂蜜做成的,對心臟非常好,你們每個人都嘗一塊兒,就像一位慈愛的老頭兒。
晚上11點鐘,采訪才開始。對我們準備的十幾個問題,阿拉法特耐心地一一回答。他特別談到巴勒斯坦與中國的情誼,說他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63年。他說,巴勒斯坦不會忘記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提供的各種幫助和支持。
采訪結束時,阿拉法特同我們每個人合影留念。我問他能否為我們辦的一份國際新聞報紙《世界新聞報》寫幾句話,他爽快地答應了,并隨手拿起辦公桌上的鋼筆,我則迅速將事先準備好的紙張鋪在他面前。阿拉法特很認真地在白紙上一筆一劃地用阿拉伯文寫起來,這幾句題詞翻譯過來就是:“中國英明的領導人在各種條件下都給予了巴勒斯坦人民全方位的支持。在此,我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并以我個人的名義,向中國人民和領導人表示衷心的感謝。——阿拉法特。”
隨后,我又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個景泰藍花瓶,作為禮物送給他。我指著花瓶向他介紹說,這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工藝品。阿拉法特高興地接過去,緊緊握著我的手表示感謝。后來幾次去阿拉法特辦公室采訪,我注意到那個花瓶一直放在他身后的書架上。
現在,阿拉法特已成歷史,但他的故事將永遠被人們銘記。

□ 劉素云在日內瓦萬國宮。
由于時間久遠,當時的采訪錄音都沒能保存下來,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遺憾。
首席國際新聞編輯:努力做一名學者型新聞人
應該說,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我積累了一定的報道經驗,在國際新聞和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努力做一名學者型的新聞人。
這一年,我在當時國際臺主辦的《世界新聞報》上開辟個人專欄“素云看世界”,主要就國際局勢中的熱點問題進行分析和點評。寫專欄,對作者有著更高的要求。新聞報道只是客觀地記錄一個新聞事件,最多加一、兩段分析,專欄則是比較個性化的一種報道形式,個人見解、分析能力甚至個人寫作風格都要體現出來。所以,專欄作者內心要豐富,思想要深邃,要有感受力、洞察力、判斷力;除了要跟蹤問題、熟悉問題,還要考慮怎么把專欄寫得生動,甚至有趣。這個專欄開了一年左右,寫了幾十篇,如《戰爭之痛與人性之惡》《錯誤考驗政治家的智慧》《“六重奏”與“二人傳”》等。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堪稱是一個人才高地,集中了大批優秀的編輯記者和外語人才。2007年,國際臺首次推出了“首席”制度,第一批共評出了9位首席,我被榮幸地被評選為“首席國際新聞編輯”。這對于我的新聞職業生涯來說,是一個新的臺階。我重新給自己定位:盡快完成從普通記者向學者型記者的轉變,將多年的新聞經驗與積累更好地釋放出來。
在隨后幾年中,我組織一些有經驗有潛力的年輕編輯們撰寫出版了國際人物傳記:《貝·布托——血雨腥風中墜落的鐵蝴蝶》《奧巴馬畫傳》《從總理到囚徒——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她可當總統——奧巴馬夫人米歇爾》《法國第一夫人卡拉·布魯尼》等。我們這是一個寫作團隊,每次都根據選題臨時搭班子。參與寫作的共有七、八個人,圖書選題緊跟最新國際形勢,時效快,內容權威。
另外,我還代表國際臺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策劃編輯出版了“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系列叢書”共計13冊,這也是國內第一套有關國際傳播研究的系列圖書。
2008年2月,我受命組建國際臺時事專題部,承擔起完善國際臺新聞策劃機制和評論性報道機制的重任,提高國際臺引導國際輿論的能力,加強在世界舞臺上的“中國聲音”。
在國際臺大廳入口處,樹立著一塊牌子:“中國立場,世界眼光,人類胸懷”。這既是國際臺的辦臺理念,也是中國的對外傳播理念。在時事專題部期間,我帶領部門人員邊摸索邊實踐,初步建立起新聞中心的重大事件策劃機制,并圍繞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改革開放30周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等重大新聞事件,組織策劃評論文章,在加強外宣言論性報道、闡述中國立場、樹立中國國家形象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
在日內瓦報道世界故事
我2011年被派往國際臺駐日內瓦記者站擔任首席記者,開始了一段新的駐外記者生涯。
日內瓦是聯合國歐洲總部所在地,除此之外,這里還有4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和機構,200多個非政府組織,每年上萬次的國際會議……所以,這里被稱為“世界多邊外交中心”。在日內瓦之所以會發生各種“世界故事”,正是因為日內瓦所代表的國際性。
在日內瓦共有600多名外國記者,世界各大媒體都在日內瓦設有常駐機構,在萬國宮內有專門的媒體辦公室。聯合國新聞局每周在萬國宮舉行兩場新聞吹風會,不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我們的采訪報道范圍涵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難民署、聯合國人道主義協調辦公室、國際電信聯盟、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移民組織等。
另外,鑒于日內瓦獨特的外交地位,以及瑞士的中立國地位,許多國際爭端的談判也都選擇在日內瓦舉行。我本人就曾參與報道了在日內瓦舉行的伊朗核問題談判、敘利亞和談、利比亞和談、也門和談等。
瑞士還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足聯等體育組織所在地,而每年年初在瑞士山城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更是吸引了全球各大媒體競相前往。我本人曾前后七次采訪報道達沃斯論壇年會。
特別值得一提的,日內瓦還是新中國多邊外交的發祥地。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新中國從這里走上國際舞臺。當時代表團下榻在日內瓦郊區小鎮的一幢別墅“花山別墅”,這里由此也成為新中國的一個紅色印跡。直到今天,還時常有中國人前來拜訪。
在埃及見證中國故事
2018年,我結束在日內瓦的任期,在7月份這個最炎熱的月份,來到了地處中東沙漠的埃及。
埃及記者站創立于1986年12月26日,是國際臺第9個海外記者站。30多年來,在中東熱點問題的報道中,埃及記者站歷任記者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我特別想說的是,這次在埃及常駐,我感受最大的是見證了中國巨大的影響力。而這也是我們采訪報道的核心主題。
金字塔無疑是埃及最著名的地標。今天的埃及人也喜歡用“金字塔”來形容一些里程碑式的工程。目前,在埃及首都開羅東部正在建設中的新行政首都,其核心項目中央商務區是由中國建筑集團埃及分公司承建的,其中包括非洲第一高樓“標志塔”,而它同時也被埃及人驕傲地稱為“新時期的金字塔”。這一合作項目是2016年1月21日,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埃及總統塞西的共同見證下簽署的,是目前中國企業在埃及簽訂的最大金額的項目合同,也是“一帶一路”沿線的一項重要國家工程。
中國在埃及以及非洲,有許多這樣的建設項目,解決了當地的就業,也促進了當地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提升了現代化水平。比如,在埃及新首都項目工地的3000多名工人中,有一半都是埃及人。埃及人對于能在中國企業謀得一份工作,也感到非常高興。中國與非洲的關系之所以被描述成兄弟情誼,就是因為中國給非洲人民送上了實實在在的幫助。
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處處可見。比如,走在開羅的大街上,當地的人們都會用中文跟你打招呼“你好”“謝謝”“再見”。在埃及,學習中文的年輕人越來越多。這既是源于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更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與非洲日益廣泛的合作,讓埃及年輕人意識到,學習中文將來能夠謀得一份好工作。2019年12月,在開羅舉行的第十屆埃及大學生中國詩詞朗誦大賽上,來自開羅大學的一名學生朗誦了他的原創詩歌《一個埃及人唱給長江的歌》,深情地表達了中埃兩個文明古國之間的濃厚情誼。
感謝大家
與新聞事業38年的牽手,讓我收獲了成長和有價值的人生。這些年來,我的采訪報道曾先后獲得中國新聞獎、中國國際新聞獎等全國性獎項,我本人也在2009年榮獲中國新聞界最高獎項長江韜奮獎,以及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
每每想起這些,都讓我頓升萬般感慨:意外,欣喜,還有感激。
說意外,是因為我在做事的時候,只是想著要把它做好,從沒想過要通過做事獲取什么身外之物,不管是利益,還是名譽。做事情,就一定要認真做好,這一直是我心中的樸素思想。
說欣喜,是因為得到領導的肯定,得到同事們的認可,心里總之還是很高興的。
說感激,是因為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結果得到了這么多的榮譽。在這里,我想真誠地說一聲,謝謝大家,謝謝每一位給我關心和鼓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