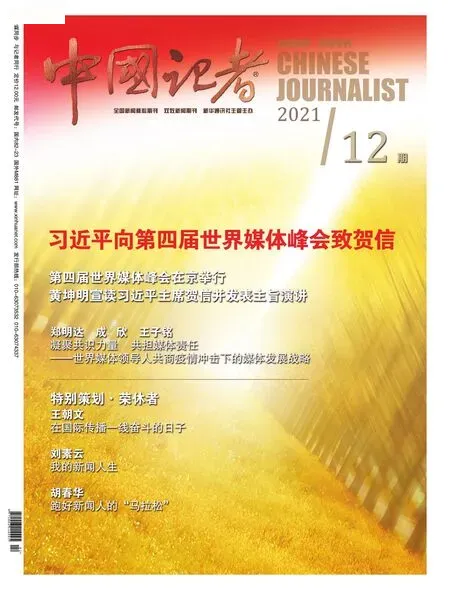不變的初心
□ 龔曉潔
1985年填高考志愿的時候,一個基于未知的判斷,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
當時,我始終在選擇讀經濟與新聞之間猶豫:喜歡新聞,但數學是我的強項。
猶豫再三,我首志愿填了復旦新聞系,第二志愿是世界經濟系。而就在這一年,世界經濟系的錄取分首次超過了新聞系,我就此與經濟無緣。不料,這次的“失手”,讓我未來的職業生涯,變得一波三折。
要講真話
畢業那年,對新聞系學生來說,是“畢業即失業”的一年。拿著復旦優秀畢業生榮譽的我,去了一張機關小報。
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宣傳部。拿到報到單的時候,我有點失落,在大學畢業紀念冊上,甚至寫錯了單位的名字:上海中國民主同盟宣傳部。(我至今非常感激,在彷徨不定的時候,他們接收了我們這批大學生)
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有一張小小的報紙:《上海盟訊》,而且有公開發行刊號。不過,它的“發行”對象,是上海的民盟成員,主要報道民盟市委的動態、盟員的事跡等。從采訪、編輯、排版、付印甚至郵寄,宣傳部一肩挑。
上班之后,為這張報紙采稿,成為我主要的工作。我,是機關第一個新聞專業畢業生,而且單位絕大多數都是老前輩,大家都對我寵愛有加。
然而,我快樂不起來。
清楚地記得,第一篇稿子寫完,我就遇到了職業生涯中第一次的沮喪。
這篇新聞稿報道的是上海盟員去貧困山區,幫助當地村民脫貧。我覺得當盟員拿到報紙后,這事兒已經不是新聞。于是,我沒有寫導語,用一位大山里的母親,幾十年來守著薄地艱難度日的故事開頭,然后引出上海民盟扶貧志愿者,如何利用專業知識幫助貧困村民改種經濟作物,讓山珍走出深閨,讓村民勤勞致富。
可是,等報紙排印出來,這篇稿件被編輯刪掉了例子,成了短消息。
那個年代,站在世界新聞舞臺中央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是新聞系學生的偶像。我困惑的是:在這張一個月一期的內部動態報紙,如何能實現我的新聞理想?
轉折,來自于我開始跑基層。
在民主黨派機關工作,還需要了解成員的思想動態,與他們交朋友,甚至包括生活中的急難愁事,盡力幫助解決。
當時上海民盟的大學支部、新聞支部,有一大批新聞界的前輩。
王中,是復旦新聞系的老系主任。我第一次走進他的家,他正在看電視。聊天到一半,他叫來保姆,掐準了分秒,將頻道換到了動畫片的開頭。他笑著解釋:“緊張一輩子,返老還童也蠻好。”
那天,我走出老系主任的家,心里掠過一陣失望:那個在1949年上海解放時,走進校長室,宣布復旦大學從此被接收的上海軍管會新聞室軍代表去哪兒了?那個曾經寫下《新聞學原理大綱》,告誡學生為人治學是首要的教授、那個被打成右派掃了二十二年廁所也不屈服的人,去哪兒了?也許,新聞真的是讓人生不堪重負的一條路,就連王中這樣的硬漢,最終也回到了看一部動畫片的人生起點。
然而這種失望,在新聞系60周年大慶時,被一票否決。
記得那天的最后一項活動,是在會堂聽老系主任王中講話,系友們將中間的桌子團團圍住。輪椅推進來,一頭白發的王中,身穿中式布衫,精神矍鑠,與之前我看見的完全是兩個模樣。
簡短講話的最后,老人突然提高了聲音,眼神犀利,言語鏗鏘:“新聞系的學生們,一句話,你們記住,要講真話,一定要講真話!”
話音剛落,掌聲如潮。
這一瞬間,我看到:那個鐵骨錚錚的新聞人,回來了!他眼里很久未見的光,是心中不滅的新聞理想。
之后再去王老家,我第一句話就說:“您在系慶時候說得真好,真的好!”
他很認真地回我:“你也要記牢!”
很多年過去了,王中主任的叮囑,一直刻在我心底。講真話,用事實說話,是新聞的第一要義。在漫長的新聞工作生涯中,無論是寫稿還是改稿,我們可能會遇到身不由己的時刻,但不歪曲事實、不欺騙受眾,是必須堅守的底線,哪怕最終廢稿、廢選題。
大概在我上班半年后,《上海盟訊》開了個人物專欄,專門介紹有成就的盟員。有一期定了一個采訪對象:趙超構。
作為一名老報人,趙超構的《延安一月》在學校里就作為新聞史的范例。筆名林放的他,主筆犀利的雜文專欄《未晚談》,是上海《新民晚報》最受歡迎的欄目之一。
我的領導找到我的時候,是用了激將法:趙老出了名的,從來不接收記者采訪,要看你的本領了!
天生牛犢不怕虎。我,敲開了趙老家的大門。
開篇是拉家常,繞了半天試探著問:“趙老能不能被采訪一次呢?”
他果然回答:“不行不行,沒什么好訪,從來不的。”那就繼續聊天。從他最喜歡的魯迅,到舊日往事,再聽聽報海軼聞,一個下午,很快過去。
年紀輕,記性好。回辦公室,我將對話寫下來,整理一下,一篇人物采訪就出爐了,還在發稿前寫了個按語:“也許,一輩子采訪別人的趙老,已經不習慣被別人采訪。于是我憑著記憶,記錄下我們的對話。”
稿子見報,我帶著報紙再次敲開趙老家門,心里,是有點忐忑的。
遞上報紙,說:“趙老我先斬后奏了怎么辦?”
“哦,已經看過了。”
“那您生不生氣?”
“沒什么生氣的,只要寫的是事實,就好。”
我心里,一塊石頭落地。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這只是一位老報人對后輩的寬容而已。采訪對象,尤其是專訪,應該征得被采訪者同意后才能發表。而我當年,確實是無知者無畏,腦子里只有采訪寫作課上“翻墻”也要采到新聞的概念。實際上,排除萬難搶新聞與尊重采訪對象的意愿,是兩碼事。
走動多了,我也會和趙老嘆苦經,說總覺得自己不像是在做新聞。他也贊同:如果喜歡新聞工作,將來一定要去正規新聞單位。他勸我,現在不妨把它當成一段經歷,多接觸人,多讀點東西(順便推薦魯迅),甚至可以試試出國讀書。做新聞,積累很重要。
趙老的稿子發表后,上海市政協主辦的《聯合時報》,開始向我約稿。他們說,能夠“‘不擇手段’讓趙老開口的人,蠻厲害的!”
之后,我寫的人物專訪就一稿兩投。幾年里,我先后采訪了滬劇團團長馬莉莉、雕塑家章永浩、中國書裝設計界“北張南陶”的陶雪華、漫畫家丁聰,等等。
民盟有許多德高望眾的知識分子,所以在《上海盟訊》這份小報工作的日子里,在與這些老一輩知識分子、老報人們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一群篤學不倦、追求真理、百折不撓的人。他們的指點,也對我的為人處世,產生了深的影響。回想起來,雖然那些年我失去了一段“搶”新聞的經歷,但是,我“搶”到了一段人生最寶貴的經歷。
重起爐灶
小報的工作,畢竟比較空。利用業余時間,我考了托福,還報名上了日語課。扔出幾份出國留學申請,填的專業也不外乎Communication或者Journalism,也許這就是新聞夢始終讓我欲罷不能的緣故吧。
就在我努力為“轉型”而起步的時候,一個機會,來了。在我工作后的第五年。
那天,初夏陽光,梧桐碧綠。我走進石門一路郵局,寄出一份文件。
突然聽到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回頭,是新聞系的老系主任林帆教授。他依然心懷歉疚,因為我們這屆的分配不盡人意。問了問我的近況,然后給了一個推薦。
就這樣,我迎來第二段職業生涯:上海電視臺新聞部,整整二十六年。
盡管我是新聞系學生,但專業是報紙采編,我等于是重起爐灶,從頭學起。
記得第一次跟著電視臺新聞采訪部主任走進編輯機房,他順手一指唯一一個正在編片子的年輕記者,說:“跟他學吧,編片子。”

2001年作者在上海APEC會議結束后的留影。
這位年輕的帶教老師,在編輯機上一邊手指翻飛,一邊告訴我,找到畫面、打進點、放圖像、拍轉盤;快進、再找、再打進點……在我眼花繚亂之際,他已結束戰斗:“我去交片子,你再自己琢磨琢磨。”
機房里,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編輯機前,我既忐忑,又興奮。怕的是,自己一點兒不懂,把機器弄壞,興奮的是:時隔五年,我終于進入了新聞行業的“暴風眼”。
有意思的是,大概在二十多年后,我從事電視行業的第一個帶教老師,那個編畫面手速快得像“外星人”一樣的記者,當上了上海廣播電視臺臺長。
我進入上海電視臺的初期,是中國電視行業高速發展的年代。改革、創新、競爭,是電視行業的常態,我在這波浪潮中,充分感受著作為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緊張、辛苦、樂趣和自豪。
最初的外拍采訪,有老記者(其實年紀并不大)帶著出去。那天,采訪對象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我彎下身子,遞上話筒錄實況。收線之后,老記者悄悄對我說:“你應該蹲下來遞話筒。”
當時我還有點納悶:彎腰為什么不可以?回到臺里一看素材,我才恍然大悟:盡管我彎了腰,但我是站著的,仍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而如果我蹲下采訪,我和輪椅上的老人就處于同一視覺水平線。尊重采訪對象,一定要顧及每一個細節。
細節,決定成敗。
記得那時候我們的直播間在9樓,編輯機房在12樓。有一次,樓下已經開始播出,剛剛從現場趕回來的記者,畫面還在編輯中。審片間的電話不斷打上來,不斷發出“警報”提示還有幾分鐘輪到這條新聞播放。當最后一個畫面落定,記者退出編輯帶的瞬間,只見早已等在邊上的采訪部主任一把搶過播出帶,從樓梯間飛奔至樓下,在最后一分鐘,把播出帶塞進了播出機。跑樓梯的時候,采訪部主任還崴了腳,后來打了幾個月的石膏,被大家嘲笑“劉阿太”。事后我不解:為什么不事先按個電梯鍵,比跑樓梯快啊?
主任說:“萬一電梯壞了怎么辦?”
在電視臺,也就是這無數個需要堵住的萬一,確保了新聞播出的安全。而我,也在不斷觀察前輩們對每一個細節的苛求中,逐漸成長為一名職業的新聞人。
初心不變
兜兜轉轉二十多年,隨著時代的發展,上海電視臺新聞部變成了新聞中心,又升級為融媒體中心。而我,也把崗位幾乎輪了個遍:記者、編輯、通聯、甚至還學過導播和放像。早新聞、午新聞、晚新聞、夜新聞、新聞快報、專題新聞,各個欄目都蹲過。就如同大學老師所說:記者是百搭。我則是電視臺的崗位百搭。
與年輕時不一樣的是,在即將告別職業生涯的時候,我已經記不清,也不在意究竟搶出多少新聞,得了多少新聞獎、先進榮譽。但是,卻記得每當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在哪里,做了什么?

□ 在北京報道全國兩會時,作者(后排左三)與同事們在京西賓館合影。
我記得,1997年香港回歸之夜。已經懷孕5個月的我,在四川北路的上海郵電大樓,采訪通宵排隊等候買郵票的市民。
千禧年到來的第一分鐘,我守在上海電視臺收錄機房,錄下譚盾音樂會的實況。第一縷陽光升起的時候,我又來到外灘,加入迎新直播團隊。
2001年,APEC會議在上海舉辦。我抱著一大包素材帶,獨自穿過空曠的東方明珠廣場到國際會議中心會場。放我過警戒線的武警低聲提醒:“不要回頭,不要彎腰撿東西,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
同年9月11日晚上,我在家接到央視地方部的一個電話:“快!打開電視機,紐約世貿大廈倒塌了!”。遠在千里之外、震驚全球的恐怖襲擊,催促我動身回臺,因為緊急報道任務來了。
2007年上海長江大橋通車。我們的直播就在橋上。一陣大風,幾乎要把我吹落到橋下。
很多年來,每當全國兩會開幕的時候,我都在當時中央電視臺的機房里,用直傳干凈畫面編輯成片,趕到大塔傳回上海。
我最終的崗位,是在上海電視臺新聞報道欄目,做一名責任編輯。這個欄目,剛剛獲得了中國新聞獎。
走出校門時的我,一心想成為法拉奇這樣的記者,哪里有大事件,哪里就有我,認為這才是新聞人的榮耀。
而現在的我,變了。
也許有很多同行和我一樣,并不奔跑在一線,甚至沒有人認識你、知道你。但是,我是新聞傳播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齒輪。現在的我,在電腦前、在直播間,把新聞傳播到每一個角落。我努力在做的,就是在第一時間告訴大眾:發生了什么?這才是新聞的本源,是一個新聞人的初心。
有哪一份工作,能讓我們與事實的真相、與瞬息萬變的世界距離那么近?
作為一個新聞人,我沒有理由不為當初的選擇感到慶幸,并為自己感到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