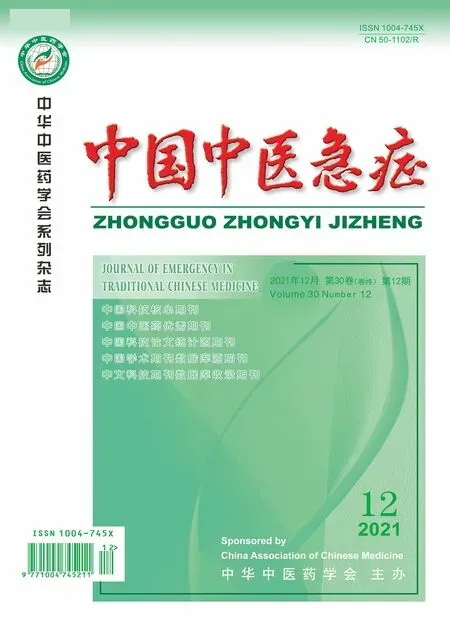通腎祛邪散聯合左氧氟沙星治療急性腎盂腎炎(膀胱濕熱證)的療效觀察
李海燕 張惠迎 王慶云 趙旭濤
(山東省濟南市中醫醫院,山東 濟南 250002)
急性腎盂腎炎是由細菌經上行性或血行性感染腎盂、腎盞、腎實質所引起的急性化膿性炎癥,病情發展迅速,若治療不當或不及時,極有可能演變成慢性腎盂腎炎,甚者出現腎功能衰竭[1]。西醫治療以抗生素為主,療效有限[2]。中醫學對急性腎炎腎炎進行辨證論治,尤其是聯合敏感抗生素治療該病,可明顯縮短病程,減少并發癥,進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3]。腎盂腎炎屬于中醫學的“淋證”范疇,急性期多為濕熱蘊結于膀胱所致[4]。通腎祛邪散出自《辨證錄》,具有清熱利濕通淋的作用。筆者在臨床實踐中對急性腎盂腎炎(膀胱濕熱證)患者給予通腎祛邪散,發現其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特別是在西醫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通腎祛邪散能明顯提高治療效果。因此,本研究旨在觀察在左氧氟沙星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通腎祛邪散對急性腎盂腎炎患者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診斷標準:急性腎盂腎炎參照《腎臟病學》[5]中相關診斷標準;中醫診斷根據《中醫內科常見病診療指南·西醫疾病部分》[6]中膀胱濕熱證擬定。納入標準:符合急性腎盂腎炎診斷標準,且中醫辨證為膀胱濕熱證;年齡18~60歲;入組前3 d無抗菌藥物使用史;簽署知情協議。排除標準:妊娠、哺乳期婦女;酒精、藥物濫用史;對本治療方案用藥過敏;合并心、肺、肝等嚴重功能障礙;精神病者;合并尿路引流不暢、梗阻以及結石等泌尿系統其他類型疾病;有泌尿系統手術史者。
1.2 臨床資料 選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在本院就診的急性腎盂腎炎(膀胱濕熱證)患者62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兩組各31例。對照組男性11例,女性20例;年齡27~59歲,平均(43.73±6.11)歲;病程13~44 h,平均(25.40±3.94)h。觀察組男性10例,女性21例;年齡29~60歲,平均(44.01±6.03)歲;病程12~46 h,平均(25.22±3.99)h。兩組臨床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在第1~7天患者接受鹽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揚子江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9990324),每次0.2 g兌入0.9%氯化鈉注射液250 mL中靜脈滴注,每日2次;在第8天改口服乳酸左氧氟沙星片(上海中西三維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00416),每次0.2 g,每天2次,連續7 d。觀察組加予通腎祛邪散,藥物組成:白術15 g,茯苓12 g,瞿麥12 g,薏苡仁12 g,萹蓄10 g,肉桂4 g,車前子12 g。每日1劑,水煎取150 mL,分2次服。兩組共治療14 d。
1.4 觀察指標 1)記錄兩組患者的主要癥狀如腰痛、發熱以及尿路刺激征的消失時間。根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7]評價膀胱濕熱證癥狀改善情況,按4級(正常、輕度、中度、重度)評價患者的納呆、腰痛、咽痛、尿頻尿急、尿后灼熱澀痛,對應計分為0、1、2、4分。2)在治療前及治療后7、14 d,空腹抽取靜脈血3 mL,3 000 r∕min離心10 min后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清C反應蛋白(CRP)和降鈣素原(PCT)水平。
1.5 療效標準 參照文獻[8]擬定。有效:尿沉渣鏡檢與細菌學檢查結果為陰性,或尿白細胞小于5個∕HP。無效:尿菌仍呈現陽性,或尿白細胞大于5個∕HP。有效率=有效病例數∕總病例數×100%。
1.6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20.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s)表示,比較均行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均行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癥狀及陽性體征消失時間比較 見表1。觀察組的腰痛、發熱以及尿路刺激征的消失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P<0.01)。
表1 兩組癥狀消失時間比較(d,±s)

表1 兩組癥狀消失時間比較(d,±s)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P<0.01。下同。
組 別n 腰痛 發熱 尿路刺激征觀察組對照組31 31 10.18±1.73△△12.49±2.11 3.14±0.40△△4.13±0.51 5.37±0.63△△7.83±0.91
2.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2。觀察組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

表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2.3 兩組治療前后膀胱濕熱證證候評分比較 見表3。治療后,兩組患者的膀胱濕熱證證候評分明顯降低(P<0.01),觀察組治療后各項證候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P<0.01)。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膀胱濕熱證證候評分比較(分,±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膀胱濕熱證證候評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1;與對照組治療后同時點比較,△P<0.01。下同。
組別尿后灼熱澀痛時 間 納呆 腰痛 咽痛 尿頻尿急觀察組(n=31)對照組(n=31)3.39±0.343 1.09±0.16*△0.40±0.06*△3.36±0.41 1.55±0.21*0.96±0.17*治療前治療后7 d治療后14 d治療前治療后7 d治療后14 d 3.16±0.39 1.03±0.15*△0.43±0.05*△3.13±0.37 1.44±0.18*0.94±0.14*3.14±0.41 1.09±0.16*△0.47±0.06*△3.19±0.40 1.52±0.19*0.93±0.15*2.98±0.33 1.01±0.14*△0.37±0.04*△3.01±0.34 1.49±0.19*0.91±0.14*3.34±0.39 1.06±0.14*△0.34±0.04*△3.30±0.40 1.46±0.19*0.90±0.14*
2.4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CRP和PCT含量比較 見表4。治療后,兩組CRP和PCT在血清含量均顯著下降(P<0.01),且觀察組血清CRP和PCT含量顯著低于對照組(P<0.01)。
表4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CRP和PCT含量比較(±s)

表4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CRP和PCT含量比較(±s)
組別觀察組(n=31)對照組(n=31)時間治療前治療后7 d治療后14 d治療前治療后7 d治療后14 d CRP(mg∕L)63.09±7.51 21.04±3.04*△6.37±0.73*△63.18±7.33 30.09±4.03*10.14±1.46*PCT(ng∕mL)3.39±0.43 1.13±0.15*△0.40±0.05*△3.44±0.41 1.93±0.25*0.57±0.07*
3 討論
急性腎盂腎炎是由多種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炎癥性疾病,如大腸埃希菌、變形桿菌等。左氧氟沙星為第3代喹諾酮類抗生素,其能夠抑制細菌的DNA內旋轉酶成分,阻止細菌DNA的合成,從而起到強效抗菌作用[9]。近年來隨著抗生素類藥物廣泛用于治療急性腎盂腎炎,使耐藥細菌逐漸增加,導致急性腎盂腎炎的治療困難系數不斷提高[10-11]。
中醫學認為腎盂腎炎的病位在腎,多因腎氣虧虛、濕熱之邪留戀下焦,使膀胱氣化失司[12]。《諸病源候論·諸淋候》指出“諸淋,由腎虛而膀胱熱也……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澀,數而且澀則淋瀝不宣,故謂之淋”。但在腎盂腎炎的急性期病機以膀胱濕熱為主,多由于患者飲食不節或嗜酒過度釀成濕熱,或者情志失調濕熱內生,或者外感濕熱等,濕熱蘊結下焦,傷及腎與膀胱,導致膀胱氣化失司,水道不利,而致此病[2]。因此,在治療上中醫主張清熱利濕通淋。通腎祛邪散方以白術、茯苓補脾益氣、燥濕利水;瞿麥、扁蓄利尿通淋;薏苡仁健脾益氣、清熱滲濕;車前子清熱利尿、滲濕通淋;然膀胱之濕熱雖去,而腎氣弱,終不能通氣于膀胱治愈淋證,故于清熱利濕之中更益腎氣,加肉桂補元陽,此解濕熱又不損腎氣,故腎氣反通轉,分解濕熱。
本組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腰痛、發熱以及尿路刺激征的消失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治療后,觀察組患者的膀胱濕熱證癥狀(納呆、腰痛、咽痛、尿頻尿急、尿后灼熱澀痛)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觀察組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表明通腎祛邪散聯合左氧氟沙星治療急性腎盂腎炎(膀胱濕熱證)的療效較單純使用左氧氟沙星更佳,且可促進患者的癥狀體征以及中醫證候好轉。急性腎盂腎炎是一種急性化膿性炎癥疾病,抑制患者體內的炎癥反應是評價其臨床治療效果的重要指標之一[13]。CRP、PCT均是臨床上常用的感染性評價指標,目前已廣泛用于急性腎盂腎炎患病情嚴重程度的有效預測指標[14-15]。本研究治療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血清CRP和PCT含量顯著低于對照組,表明通腎祛邪散聯合左氧氟沙星治療急性腎盂腎炎較單純使用左氧氟沙星,可進一步抑制患者體內的炎癥反應。
綜上,熱淋清顆粒聯合左氧氟沙星治療膀胱濕熱證之急性腎盂腎炎能提高臨床治療效果,能促進癥狀體征和中醫證候的改善,有效抑制炎癥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