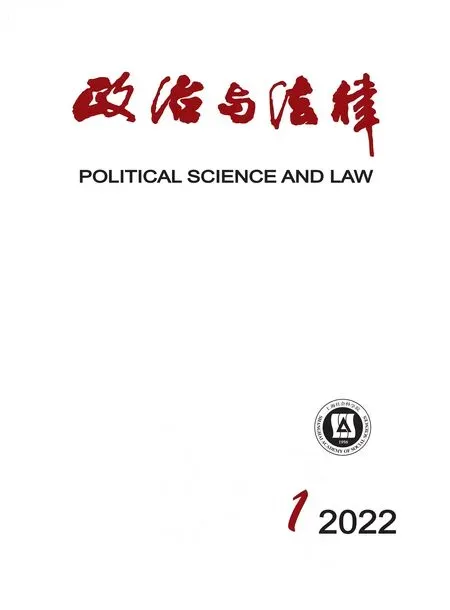輕罪時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盧建平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5)
法網如同漁網,治罪的數量不僅取決于水中魚的數量,也取決于漁網以及網眼的大小。大網、大網眼抓大魚,小網、小網眼抓小魚。相對于外國的大法網,我國的刑法是小法網,而相比于外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小網眼,我國立法定性又定量的入罪門檻就是大網眼,結果是我國的犯罪率低而外國的犯罪率高。當然,要考慮統計標準或口徑的差異,在我國的刑事法網之外還有一張更大的治安法網,外國的犯罪率應等同于我國的犯罪率加治安違法率。也須明白,再大的漁網也抓不盡水中的魚,違法犯罪的黑數也是客觀存在的,進入違法犯罪統計的僅是明數。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中國刑法正在告別重罪重刑的小刑法,逐步走向犯罪圈不斷擴大而刑事制裁日漸輕緩與多樣的大刑法。從1979 年刑法到1997 年刑法,再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刑事法網不斷增大,而網眼愈加細密。由此不僅導致犯罪數量先升后降的顯著變化,而且導致犯罪現象內部結構的變化:嚴重暴力犯罪數量與重刑率下降、輕微犯罪數量與輕刑率上升、呈現“雙降雙升”,輕罪新罪成為犯罪治理的主要對象,與既有犯罪治理體系如規范體系、組織體系和思想觀念形成沖突,為此須相應調整犯罪治理的戰略策略、體制機制和手段方法。
一、輕罪時代已經來臨
現代社會的犯罪形態變化快而大,不僅進入到了法定犯時代〔1〕參見儲槐植:《要正視法定犯時代的到來》,載《檢察日報》2007 年6 月1 日,第3 版。、逐步告別自然犯時代,而且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運用,網絡犯罪迅速蔓延,數量和占比上升,網絡犯罪的時代已然來臨。近年的犯罪統計也表明,中國已經進入輕罪時代,正在慢慢告別重罪時代。
在用統計數據揭示輕罪時代的到來之前,需先說明,何為重罪?何為輕罪?根據犯罪的性質、情節及其刑罰輕重分出重罪、輕罪、微罪甚至更多層次是世界多數國家的通例〔2〕參見盧建平:《犯罪分層及其意義》,載《法學研究》2008 年第3 期。。借助犯罪分層和犯罪分類(根據犯罪主體、客體等不同標準劃分)理論,結合我國公安統計和司法統計深入分析后發現,我國的犯罪現象在內部結構上正呈現“雙降”與“雙升”的趨勢。
“雙降”是指兩類指標下降:一是近年來八類嚴重暴力犯罪的犯罪率逐年下降,其在全部犯罪總量中的占比也在下降。截至2016 年1 月,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量連續11 年持續下降,2015 年的降幅達到12.5%。〔3〕參見周斌:《找出問題直面問題解決問題 防控五大風險全力維護公共安全》,載《法制日報》2016 年1 月25 日,第1 版。2016 年,全國嚴重暴力犯罪案件量比2012 年下降43%。〔4〕參見張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訪中央政法委秘書長汪永清》,載《人民日報》2017 年9 月13 日,第8 版。表1 顯示,2010 年至2019 年,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案件中,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與強奸等危害性大的嚴重暴力犯罪比例總體呈下降趨勢(強奸罪略有回升)。

表1 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與強奸三類犯罪立案數量和所占比例〔5〕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相應年份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案件數,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o1,2021 年11 月22日訪問。
二是重刑率下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慣例,判決有罪的罪犯中,被判處5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乃至死刑的罪犯稱為重刑犯,重刑犯在所有罪犯中的比率即為重刑率。“嚴打”時期的重刑率最高,達到47%,1995 年為45%,1996 年是44%,到了2002 年、2003 年下降到22%左右。〔6〕參見盧建平:《我國犯罪治理的大數據與大趨勢》,載《人民檢察》2016 年第9 期。近年來,我國的重刑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2015 年是9.37%,2016 年下降到了8.01%〔7〕數據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歷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見圖1)。

圖1 五年以上重刑犯比例(%)
“雙升”指輕微犯罪大幅度上升和輕刑率穩步提升。輕微犯罪上升的典型是危險駕駛罪。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危險駕駛罪,2011 年5 月1 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生效之日至2011 年12月31 日,全國危險駕駛犯罪案件即達5 萬余件,2012 年為8 萬余件,2013 年9.1 萬件,2014 年11.1萬件,2015 年13.5 萬件,2016 年145461 件,2017 年170473 件,2018 年209965 件〔8〕鑒于我國犯罪統計數據的發布不夠規范,目前關于危險駕駛罪的數據來源不一,主要來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國裁判文書網,但2016、2017、2018 年的數據源自非官方的北大法意數據庫,其信度有待驗證。,2019 年32.2 萬件。以“危險駕駛罪”為關鍵詞在“12309 中國檢察網”上對全國檢察機關公開的法律文書進行檢索,檢索到2019 年、2020 年的起訴書與不起訴決定書總量分別為359565 和383094,分別是盜竊罪的1.38 倍和1.57 倍。危險駕駛罪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的占比也在逐年上升:自2014 年以來,危險駕駛罪的占比已經超過10%,在一些地方甚至超過了20%〔9〕參見2017 年10 月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數據研究院、案例研究院發布的《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之危險駕駛罪》,該報告顯示2015 年的危險駕駛罪總量超過13.5 萬。關于各地危險駕駛罪在刑事案件總量中的占比,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人民法院2016 年1月18 發布《2015 年度司法統計分析》顯示,全年新收刑事案件721 件,其中危險駕駛案件148 件,占比20.5%。。而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不完全數據,2019 年危險駕駛罪已占法院網上公布刑事判決的26.45%〔10〕中國裁判文書網自2014 年1 月1 日起運行,自此上網公布的危險駕駛罪數量明顯上升,但因為上網的判決文書并非全部,因而由此得出的案件數量也不完全準確,只能作為參考。(見表2)。

表2 危險駕駛罪占法院上網公布刑事案件的數量與占比
2020 年5 月25 日,張軍檢察長在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時指出,從1999 年至2019 年,“醉駕”已經取代盜竊成為刑事追訴第一犯罪。〔11〕參見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0 年5 月25 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載《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報》2020 年第3 期。以2019 年全國檢察機關的主要辦案數據為例,逮捕人數排在前五位的罪名是:盜竊罪188408 人,占17.3%;詐騙罪113454 人,占10.4%;尋釁滋事罪93834 人,占8.6%;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70763 人,占6.5%;故意傷害罪67846 人,占6.2%。而起訴人數排在前五位的罪名是:危險駕駛罪322041 人,占17.7%;盜竊罪249301 人,占13.7%;詐騙罪119383 人,占6.6%;尋釁滋事罪113850 人,占6.3%;故意傷害罪111509人,占6.1%。〔12〕參見孫風娟:《最高檢發布2019 年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載《檢察日報》2020 年6 月3 日,第4 版。2021 年4 月23 日,最高檢發布2021 年1 月至3 月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從起訴罪名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危險駕駛罪74713 人,同比上升1.1 倍;盜竊罪45662 人,同比上升12.6%;詐騙罪24173 人,同比上升6.7%;故意傷害罪18749 人,同比上升5.2%;開設賭場罪17897人,同比上升49.2%。〔13〕參見孫風娟:《最高檢發布第一季度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載《檢察日報》2021 年4 月24 日,第2 版。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據也表明,“醉駕”已經取代盜竊成為刑事審判的第一犯罪。2019 年7 月31 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2019 年上半年審判執行工作數據,危險駕駛罪成為全國法院上半年審結數量最多、占比最大的刑事案件〔14〕孫航:《最高法發布二〇一九上半年審判執行工作數據:新收案件數持續增長 結案數同比大幅增加 整體運行態勢穩中向好》,載《人民法院報》2019 年8 月1 日,第1 版。。
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時間周期看,犯罪輕重趨勢變化更為顯著。1999 年至2019 年,檢察機關起訴的嚴重暴力犯罪從16.2 萬人降至6 萬人,年均下降4.8%;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占比從45.4%降至21.3%。與此同時,新類型犯罪增多(尤其以輕微罪居多),危險駕駛罪增加最為明顯,擾亂市場秩序犯罪增長19.4 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增長34.6 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增長56.6 倍。嚴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的下降,反映了社會治安形勢持續好轉,人民群眾收獲了實實在在的安全感;而輕微犯罪及輕刑率的上升也反映出新時代犯罪形態的顯著變化,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上升,重罪輕罪微罪各層次的占比發生變化,表明社會治理進入新階段,人民群眾對社會發展內涵有新期待。〔15〕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0 年5 月25 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載《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報》2020 年第3 期。
重刑起點為5 年有期徒刑,這在理論上頗有爭議,也與立法規定的緩刑適用條件和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實踐不符。依據我國刑法,以3 年為界應該更為合理。2020 年10 月15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情況時,使用了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確定輕罪案件的標準,這無疑是一大進步。因為5 年標準的信號效用降低,靈敏度不高,所以必須換成更低的3 年。
若以3 年為輕罪重罪的分界,則數據如表3〔16〕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http://gongbao.court.gov.cn/Articlelist.html?Serial_no=sftj,2021 年11 月22 日訪問。:

表3 以3 年為界的重罪輕微罪比例
大體而言,可以將5 年以下刑罰占比超過90%,或3 年以下刑罰占比超過80%的2013 年稱為輕罪時代的元年,自此,中國進入輕罪時代。
輕罪時代也可以說是一個新罪的時代。動態而論,在我國犯罪總量的上升過程中,輕罪微罪的貢獻是主要的;相比于傳統犯罪(也可稱舊罪),立法新增的輕罪微罪(或稱新罪,以危險駕駛罪為典型)在犯罪增量中的占比也是絕對的。靜態地看,新罪、輕罪的數量及其在犯罪總量中的占比在上升,而傳統犯罪、嚴重暴力犯罪或重罪的比重在下降。從新罪名的司法適用看,據最高檢公布的2021 年第一季度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17 個罪名中,已提起公訴258 人,其中人數較多的罪名有:襲警罪101 人、催收非法債務罪91 人、妨害安全駕駛罪30 人、高空拋物罪21 人、危險作業罪14 人。〔17〕《2021 年1 至3 月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載《檢察日報》2021 年4 月24 日,第2 版。
二、輕罪時代輕罪為主的原因分析
“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43 頁。,因此,在反社會或背離社會規范的行為體系內,犯罪行為處于最高級,位居越軌行為、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階梯的頂端。但即便如此,犯罪仍然是一個龐大的行為群,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既非簡單抽象的法律概念,也非平板一塊。平面地看,犯罪圈由核心、中間和外圍組成;立體地看,犯罪應該是塔狀結構,塔尖是最嚴重犯罪,數量最少但危害最大;塔身由嚴重犯罪組成,數量較大,危害也較大;塔基由輕微犯罪組成,數量最大但危害較輕,如何處置,選項較多,從而引發很多爭議。
犯罪分重、輕、微,是犯罪事實客觀狀態的自然分布。而中國犯罪治理進入輕罪時代,更是積極治理的成果體現。積極治理,首先體現為積極立法〔19〕參見周光權:《積極刑法立法觀在中國的確立》,載《法學研究》2016 年第4 期。,即通過修正刑法增加新罪,以法定犯或輕罪微罪為主〔20〕參見周光權;《論通過增設輕罪實現妥當的處罰—積極刑法立法觀的再闡釋》,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6 期。。從1997 年刑法全面修訂至今,立法機關共頒布了1 部單行刑法和11 個修正案,刑法分則條文從350 條增加到387 條,罪名從412 個增加到483 個。近年刑法修正過程中增加的新罪多為輕罪微罪,其中,危險駕駛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設的罪名,是典型微罪。微罪是指最高法定刑僅為拘役、管制的犯罪,或可判處拘役或以下之刑的罪。〔21〕參見儲槐植、李夢:《論說“微罪”》,載趙秉志主編:《當代中國刑法立法新探索——97 刑法典頒行20 周年紀念文集》,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24 頁。《刑法修正案(九)》又增設了兩個微罪罪名,即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第280 條之一)、代替考試罪(第284 條之一第4 款)。微罪出現以后,我國的犯罪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基本形成了重罪(即可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輕罪(可處拘役以上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與微罪(最高刑為拘役的犯罪)的三層次結構。《刑法修正案(十一)》又增加了新的輕罪,即第133 條之二的妨害安全駕駛罪和第291 條之二的高空拋物罪。因此,在犯罪論部分,刑法的犯罪門檻下降、犯罪圈擴張,不斷侵蝕行政法甚至民法的調控范圍,出現大量的輕微犯罪(主要為法定犯、行政犯或秩序犯),犯罪的質的規定性漸趨軟化(幾乎與行政違法混同)。
積極治理,其次體現為積極司法。統計數據已經表明,我國的犯罪治理,從車過彎道、水過險灘時期的嚴打斗爭,已經進入水流平緩、江面開闊的寬嚴相濟新時代,我國的犯罪總量在2015 年達到頂點以后開始回落,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輕微犯罪成為主體,暴力犯罪淪為次要且其總量和占比不斷下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推行的成效顯著,犯罪現象雙降雙升的態勢得以鞏固,社會治安形勢趨穩,社會治安或犯罪治理的整體效應明顯。
若犯罪總量減少(連同治安案件總量的減少,見表4),而其中的重罪和暴力犯罪也減少,說明犯罪治理的整體成效是顯著的,至少說明對于重罪的治理是有效的。當然為此付出的代價也不小,公檢法司成本支出與刑事犯罪案件數之比(也即案均成本),從1978 年的4032 元/起,猛增到2010 年的146703 元/起,漲了38 倍。〔22〕參見盧建平主編:《中國犯罪治理研究報告》,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9-178 頁。當然,過往的成績來之不易,應該肯定并繼承。重罪治理好了,社會治安程度提高,人民群眾對于社會治安、司法公平正義的滿意度也在上升。國家體改委社會調查系統曾經通過對全國公眾的抽樣調查,了解公眾對社會治安的滿意度,結果1993 年為14.5%,1994 年18.3%,1996 年26.7%。〔23〕參見曹鳳:《第五次高峰——當代中國的犯罪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頁。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民眾對于犯罪治理的績效、對于社會治安的滿意度呈上升趨勢。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2020 年全國群眾安全感為98.4%,對當前主要民生領域現狀的滿意度調查中,群眾對社會治安的滿意度位列第一,達83.6%。〔24〕參見張天培:《久久為功,推動掃黑除惡常態化》,載《人民日報》2021 年4 月13 日,第5 版。犯罪治理的績效提升了犯罪治理的自信。與此同時,我國犯罪治理能力與水平也顯著提高,立法從粗疏到精細,司法從嚴打到寬嚴相濟,犯罪治理現代化程度不斷提升。

表4 2012-2019 全國治安案件與刑事案件分類統計
積極治理旨在滿足人民群眾對于公平正義的新期待。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和法治國家建設的不斷推進,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長,需要刑法加以保護的新法益不斷涌現,犯罪治理法治化的需求,特別是程序正義的需求不斷提高。以往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無論是應對犯罪還是違法,都強調效率為先而相對忽視公平,常常采用運動式執法或嚴打專項斗爭等非常態治理手段。如今人民群眾對良善司法的期望值上升,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成為群眾的新期待,常態治理、依法治理成為首選。習近平總書記2012 年12 月4 日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 周年大會上提出:“要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2018 年8 月24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2019 年5 月7 日,總書記在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中再次強調:“公平正義是執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線,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辦理、每一件事情處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當然,積極治理更是為宏觀的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出的努力,也為犯罪治理的現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礎。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平穩期,國家治理體系日趨完善,治理能力不斷增強,治理資源更為豐富,治理制度持續優化,治理效能顯著提高。這一變化同樣體現在犯罪治理領域。
三、輕罪時代的主要挑戰
(一)輕罪時代犯罪類型的數量增減
按照菲利的犯罪飽和律(law of criminal saturation),只要社會上存在一定量的引起犯罪的個人、物理和社會因素,就必然引起一定量的犯罪。〔25〕該定律由意大利犯罪學家菲利在所著的《犯罪社會學》(Criminal Sociology)提出。參見[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會學》,郭建安譯,商務印書館2018 年版,第66-67 頁。也即一定規模或一定量的社會關系,對應一定量的犯罪。犯罪現象不僅具有周期性增長,也有周期性變動。隨著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犯罪表現出下列波動模式:每年的財產犯罪和人身犯罪交替變化,當一類犯罪上升時,另一類犯罪下降。
中國進入新時代之后的犯罪現象演化,基本驗證了菲利的犯罪周期性增長理論,也即犯罪順應社會發展而相應增長。但統計研究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犯罪數量的增長趨勢與犯罪治理法治化程度提高、行政法或警察權收縮等因素密切關聯。那么,輕微犯罪的增加,能否驗證菲利的犯罪周期性波動呢?也即,輕微犯罪總量和占比的上升,是否意味著重罪的數量和份額在減少?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文所述,近二十年來,我國嚴重暴力犯罪絕對數量的下降及其在犯罪總量中占比的下降均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犯罪統計數據也不是絕對客觀的,它既是對客觀犯罪現象的真實反映,也是犯罪治理結果或成效的體現。那么,輕微犯罪或新罪增加,是否意味著少辦了重罪而多辦了輕微犯罪,因為輕微罪好辦?或者受到了GDP 思維的影響,單純追求辦案的數量?確實,輕微罪相對好辦,因為多數是從行政犯、治安犯升格而來的法定犯,易于認定。客觀地看,輕微罪相對好辦也是事實,例如醉駕類危險駕駛罪的查辦猶如張網捕魚,只要交通警察出警率高,設卡堵截,醉駕行為人就很容易被查獲,查獲現行犯罪的幾率大,而且人證俱獲,證明起來也相對容易。
犯罪統計數據分析表明,輕微犯罪增加的同時,危害公共安全、社會管理秩序、侵犯財產罪的數量也增加了;危險犯或舉動犯增加了,而實害犯或結果犯減少了;網絡或線上犯罪增加了,而線下犯罪減少了。這些現象在驗證犯罪周期性變動的同時,也折射出現行犯罪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極限問題,也即特定資源約束條件下特定治理體系的治理上限。
(二)輕微犯罪的治理成為關鍵問題
以現行的犯罪治理體系(主要為刑事法體系),能夠有效應對輕罪時代的挑戰嗎?罪刑均衡,不僅是立法順應罪刑階梯,體現整體均衡;而且司法也要考慮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體現個案的罪刑均衡。輕罪時代既要治重罪,更要治輕罪。而面對以輕微犯罪為主的犯罪態勢,我國的刑法體系表現出整體罪刑不均衡、實體和程序不匹配、過程與結果不相符等缺陷。現行刑法小而重的特點,刑罰體系的傳統、單一,刑事程序的嚴苛(審前羈押率高,即逮捕刑拘的多,變更強制措施難),刑罰執行的嚴格(實刑多而緩刑少,長刑執行的機械、減刑假釋的嚴格掌控)等等,幾乎都是為重罪配置的,與輕罪時代犯罪治理的要求相去甚遠。總結起來就是輕罪重刑,刑法和刑訴法的不斷修正即說明現行治理體系的不適。
以刑罰體系的單調、嚴苛為例,危險駕駛罪為典型微罪,其法定刑最高為6 個月拘役,因立法并未設定情節嚴重的要求,也未配置管制刑,因而執行起來顯得極為剛性。醉駕入刑以后,案件數量及其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急劇攀升。而從實體法與程序法協調適用的角度看,對于危險駕駛類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適用逮捕這一措施,也曾經引發爭議,因為逮捕的法定條件之一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近年的犯罪統計中,檢察機關批捕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數量相對較少,但提起公訴的此類案件數量卻是前者的好幾倍,原因即在于危險駕駛類犯罪欠缺逮捕的法定條件。盡管危險駕駛罪等輕微犯罪的辦案流程快,醉駕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普遍適用速裁程序,案件流轉速度快,平均結案周期僅為7 天,但考慮到醉駕畢竟是犯罪,其審前羈押性強制措施適用率較高。以北京市某區為例,2016-2019 年間,危險駕駛涉案人員在判決前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比率高達89.7%。而審前羈押的比例和長短往往又決定了刑罰的輕重,關多久與判多久的關聯度極高。在北京,針對醉駕案件,起訴率即實刑判處率高,但刑期普遍較低。某區約97.4%的醉駕案件被起訴,換言之,醉駕案件的不起訴率不足3%。凡公訴的醉駕案件均獲得有罪判決,近五年來緩刑適用的案件總數僅為個位數。
醉駕案件持續高發固然與我國汽車保有量、機動化程度不斷提高,酒文化長盛不衰等因素有關,更與司法機關持續嚴格、嚴厲打擊有關,是厲而不嚴傳統刑事政策的反映。單調的拘役與罰金刑,加之實際更為嚴厲的犯罪附隨后果(黨紀政紀處罰、社會征信體系約束,不僅制裁行為人,甚至殃及家人親屬),導致明顯的罪刑不適應,刑大于罪。從宏觀意義上看,如此司法也嚴重消耗了寶貴的司法資源,增加了犯罪治理的成本,降低了犯罪治理的效能。三個一律(即一律立案、一律起訴、一律判刑)機械司法的背后隱藏的是嚴打思維,是陳舊的辦案理念、落后或僵化的辦案機制,是報應懲罰觀念,也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在起作用,說明商鞅“嚴刑重罰”“輕罪重刑”的思想影響深遠,至今不絕。〔26〕《商君書·靳令》即強調:“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這與和諧社會建設,與教育改造、幫助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的刑罰目的背道而馳,更與輕罪時代的犯罪治理要求格格不入。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我國刑法體系都呈現出整體的罪刑不均衡:立法上,刑罰偏重,不適應犯罪整體趨輕的態勢;在寬嚴相濟政策作用下,司法不斷降低刑罰嚴厲程度,導致立法偏重與司法趨輕的不均衡;諸多的典型個案(如許霆案、于歡案、王鵬鸚鵡案、天津趙春華槍支案、河南蘭草案、掏鳥窩案等)顯示,立法上的重刑配置、傳統重刑依賴思想導致司法機關的機械司法,一些判決畸重,不被社會大眾認可,具備合法性但欠缺正當性、合理性,程序嚴厲且機械。究其根源,主要源于刑事立法及實際效力等于立法的司法解釋的嚴苛,最終又受制于思想觀念的滯后。
四、輕罪時代犯罪治理方略的調整
刑罰世輕世重;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當今世界,不能奢望無罪無刑的理想主義,更不能固守重刑主義,而應該直面輕罪時代,迎接輕罪時代的挑戰。
(一)重構刑事政策,創立犯罪治理學
既然犯罪有重、輕、微之分,犯罪治理就應該在共性基礎上有所區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中央政法會議的講話中要求,“深化訴訟制度改革,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27〕張洋:《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全面深入做好新時代政法各項工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保障人民安居樂業》,載《人民日報》2019 年1 月17 日,第1 版。。總書記的講話中體現了犯罪實體分層、程序分流的思想,這是未來犯罪治理的正道。受此啟發,筆者主張在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的新語境下,推行新的犯罪治理體系,以犯罪分層為核心,以輕微罪治理為主體,全面改革立法、司法和執法體系。在寬嚴相濟、嚴而不厲政策指導下,實現刑法上犯罪分層,輕重分離,輕重兼顧,并借鑒預防醫學治未病、治末病的原理,主攻輕罪,以寬為主,以寬為先,刑罰整體趨輕,制裁多元,刑事程序多樣。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語境下,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構建犯罪治理的大學問,并推動犯罪治理領域的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革。
(二)重新定位刑法
刑法是典型硬法(hard law),然而在此硬法體系內部,晚近也出現了如下變化:一是刑法的犯罪門檻下降、犯罪圈擴張,不斷侵蝕行政法或民法的調控范圍(出現大量輕微犯罪、法定犯、行政犯),犯罪的質的規定性(罪質)漸趨軟化,罪量降低,與違法混同。二是增加了越來越多的難以歸屬于刑罰的處遇措施,如社區矯正、禁止令或職業禁止,與傳統刑罰相比,這些措施(保安處分)要柔軟很多。換言之,刑法體系犯罪論部分的擴張導致其制裁體系的不適應(制度短缺),因而必須向其他部門法借力。三是從刑法功能來說,從原先的懲罰、報應已然之罪,轉向現在的預防或管控風險,防治未然之罪,必然要求刑罰或制裁措施具有必要的彈性。這些變化對于刑法的最后法、保障法地位,對于罪刑法定、刑法謙抑(審慎、善意)等提出挑戰。刑法功能的現代轉換,即從懲罰、報應已然之罪,轉向預防或管控未然之罪,轉向治理風險(governance of risk),必然要求刑法體系整體而全方位的變革,即犯罪論、刑罰或制裁論、程序論的變革;應對手段從單一到多元,結構從簡單到復雜;性質由硬變軟,由確定到彈性,軟硬結合,寬嚴相濟;最終刑法的地位從最后法、保障法向干預法、預防法、治理法轉化。新的觀念孕育新的功能,新的功能產生新的結構,導致整個體系的聯動變化。
在刑法范圍擴大的同時,其制裁的強度是否也要稀釋?也即,刑罰或制裁也應以輕緩為主?筆者傾向于這樣的政策導向。即便不能總體確立,至少應該用于治理輕罪。由此使得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刑法(刑罰)上得到軟硬結合的響應。用軟法(soft law)概念來指代刑法不科學,整體推行軟法的思路也不合適,因為它挑戰了罪刑法定、刑法謙抑,以及審慎、善意(善治)的刑法理念,但至少在行刑銜接、刑民交叉的連接地帶,在刑罰手段和制裁方法上,刑法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軟化。特別是在輕微犯罪領域,軟性制裁是可行的,這就類似密封圈的原理,在兩個硬部件之間,只有橡膠等柔軟性、彈性好的材料才能擔此重任。
(三)犯罪論的改造
在擴大刑法干預范圍、擴大犯罪圈后,應該實行輕重分離的策略,立法上區分重罪、輕罪、微罪,以刑罰輕重為標準——或以法定刑或以宣告刑,以拘役或徒刑以下刑罰處罰的為微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至拘役的為輕罪,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的為重罪。
如何在立法和司法統一的意義上實現罪刑整體均衡?理想的方案是立法定性不定量,去除數額化,以實現零容忍,使刑法干預提前,由小而重變成大而輕,由二元漸趨一元,變成全控刑法(total control by criminal law),然后再內部分層。較為現實可行的方案是降低犯罪門檻,增設新罪(以輕罪微罪為主),繼續擴大犯罪化,將刑法干預的重心下沉,彌補立法空白,填充中間地帶,進而實行犯罪分層。
擴大犯罪化會招致過度犯罪化、刑法依賴主義或者以刑治國、違背刑法謙抑的質疑。然而我國刑法本就是小刑法,嚴格意義上的犯罪率極低,加之有行政違法的前置或基礎,犯罪化效應在民權保障的角度并不直接,且從統計數據看并不過度,其負效應可控。從司法負荷來看,輕罪微罪的辦理若經科學分流,也是司法系統可以承受的;同時推行刑罰輕緩化與制裁多元化,在擴大入罪與擴大出刑兩端發力,實現“入口”與“出口”的動態平衡,也可大大緩解監獄壓力。
在擴大入罪的同時,司法機關也應積極擴大出罪和出刑。出罪與出刑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出罪是前提,出刑是目的;出罪一定出刑,而出刑不一定出罪。當前全國檢察機關正在力推少捕慎訴慎押,針對輕罪案件等強化羈押必要性、社會危險性審查,破除“構罪即捕”的傳統觀念。如杭州市檢察機關受“健康碼”啟發,針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管,運用數字賦能研發“非羈碼”〔28〕參見謝添、李洋:《刑事訴訟非羈押人員數字監控的實踐與探索——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非羈碼” 使用為視角》,載《中國檢察官》2021 年第7 期。,不僅能夠有效降低審前羈押率,創新保釋制度,而且可望推廣運用到刑罰執行階段的非監禁刑之中,可以降低監禁率,減少司法成本,有助于最終實現輕刑化、緩刑化。
寬嚴相濟、嚴而不厲的政策需要程序機制甚至行刑機制的配套,需要訴訟程序或執行的輕緩化。而當務之急是實現輕罪輕罰,并且更多考慮輕罪免罰、不罰。例如,2017 年5 月1 日實施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規定,“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準確定罪量刑。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此后,浙江、上海江蘇等地司法機關紛紛跟進,作出更為具體和可操作的出罪出刑的細則。〔29〕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關于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浙高法〔2019〕151 號,2019 年10 月8 日發布。這一出罪免刑的舉措也在“兩高”最新量刑指導意見中得到延續,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定罪免刑或出罪出刑,也必須與非刑罰處遇有效銜接。德國1975 年《刑事訴訟法典》修訂增加的第153 條a 規定,在處理輕罪案件時,在征得管轄法院同意的前提下,檢察院在作出不起訴決定時,可以對被不起訴人處以懲罰性措施,包括繳納罰款、提供社區服務、賠償被害人的損失、遵守贍養令或撫養令。〔30〕參見《德國刑事訴訟法典》,李昌珂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73 頁。要實現刑法體系構造從“厲而不嚴”轉向“嚴而不厲”,必須為輕微罪配備“非刑罰化”的處罰方法。一些地方正在試行的針對醉駕案件的社會公益服務評價機制是值得關注和推廣的制度創新〔31〕王柏洪、魏干:《“醉駕”案件社會公益服務評價機制研究》,載《浙江檢察》2021 年第2 期。。
在肯定立法擴大犯罪圈、將醉駕行為作為危險駕駛罪予以刑事處罰的同時,司法更應該本著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充分認識微罪輕罪內部的復雜結構,適度加大對該類犯罪從寬從輕、定罪免刑甚至不作為犯罪處理的力度,而摒棄一律從嚴或一律從寬的片面思維。同時也要根據法律實施的績效,適時考慮危險駕駛罪的立法改造,如確立初次醉駕行政處罰,二次醉駕刑事處罰;刑罰配置上與妨害安全駕駛罪看齊,即由“處拘役,并處罰金”改為“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增加管制刑,為推行社區矯正、罰金刑等監禁刑替代措施留出通道。
如此改造之后,犯罪治理的相對優勢將會更加明顯,既可解決“要么無罪要么重罪”的尷尬(如高空拋物、危險駕駛、妨害安全駕駛、催討非法債務),避免行政處罰重于刑罰的局面,也可抑制行政權尤其是警察權從而推進輕微犯罪治理的司法化,整體提升犯罪治理的法治化。其實,增設新罪輕罪也并不必然就擴張了刑法的調整范圍、危及公民自由,反而是在傳統或原屬刑法范圍內的改革,可更加徹底地貫徹罪刑法定原則,更好地保障公民自由和權利。如對故意殺人罪的立法改造方案(如增設安樂死、幫助自殺、見危不救等規定),即可有效規制安樂死、幫助自殺、見危不救等現象,不致于一律按故意殺人罪這一重罪予以定罪處刑。
在刑法立法擴大犯罪圈、降低犯罪門檻,主要面向輕微犯罪的時候,也要輕重兼顧。但此時究竟是以重罪為主還是以輕罪為主,值得探討。輕重不同而治理策略不同,治理資源的配置也應該不同。就全國或宏觀而言,重罪當然是犯罪治理的重點,因而需要配置足夠的資源,但主要體現為審級和審理的專業力量配備、程序的嚴格。對于地方或基層來說,顯然是以輕微犯罪的治理為主,不要籠統套用“二八定律”(即所謂的用80%的資源去治20%的重罪,以20%的資源去治80%的輕罪)。
(四)刑罰論的重構
儲槐植教授著眼于世界范圍內刑罰結構的嬗變,認為從過去到未來,刑罰結構可能有五種類型:死刑在諸刑罰中占主導地位;死刑和監禁刑共同在諸刑罰方法中為主導;監禁刑在諸刑罰方法中占主導地位;監禁刑和罰金刑共同在諸刑罰方法中為主導;監禁刑替代措施占主導地位。第一種已成歷史,第五種尚未到來,中間三種在當今世界中存在。死刑和監禁刑占主導的可稱重刑刑罰結構,監禁刑和罰金刑占主導的可稱輕刑刑罰結構。〔32〕參見儲槐植:《論刑法學若干重大問題》,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3 期。中國的刑罰結構屬于何種類型尚不清晰,既保留并適用死刑,監禁刑尚處中心地位,而替代監禁刑也已成為改革方向,可稱為混合形態,但屬重刑刑罰結構,應是確定無疑的。為此需推行刑罰輕緩化的改革,推動從刑罰體系走向刑事制裁體系,以輕刑化為導向,以死刑改革為龍頭,刑罰整體趨輕,方法多元,力推輕刑、非監禁刑和非刑罰制裁,增加微罪處分和保安處分;增加網絡信息化制裁手段,如網絡禁止令、電子監控等,并注意控制犯罪的附隨后果。
晚近刑法修正,在刑罰論或制裁論部分,增加了越來越多的非刑罰措施,以求實現罪刑均衡或罪罰相適應。與傳統刑罰相比,這些措施如《刑法》第36 條、第 37 條、第37 條之一、《刑法》第17 條第5 款所援用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 條、第44 條、第45 條等等,規定的均為非刑罰處罰,但其收效和監禁刑一樣,甚至更好,足以有效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應在刑法總則部分有顯著的位置〔33〕將“非刑罰措施”置于“刑罰”一章或“刑罰的種類”一節之下顯然不合邏輯,應單列“非刑罰措施”一節。。
面對輕罪時代,亟待深入反思的是,刑罰的目的是什么?單純刑罰體系是否足以應對?是否應該增加保安處分(security measures),推行處罰體系的二元化?刑罰或保安處分的本質又是什么?是報應報復、懲罰,還是剝奪其危害社會的能力(也即預防、治理)、重新社會化?若是后者,則網絡數據時代的非物理消滅、非物理剝奪的權利刑、數字刑等手段完全可以實現以上功能。傳統社會對人的管控手段有限,須人與時空對應,或者將人的生命剝奪,或者將其拘禁在特定的場所,與世隔絕,看似剝奪或限制自由,實質上仍然是物理消滅或隔絕的理念。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監視打破了時空的限制而變得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處于網絡中的個體彼此連接,不可分離。數字化時代每個人均是數字化的存在,每個人均處在一定的數字監控之下,只是被監控的程度不同而已。數字化時代監視的方式已不同于福柯所處的時代,可以實現人與時空的分離(所謂非接觸時代),更有效地控制人的行為(遙控,remote control)。為此,可借鑒“健康碼”“行程碼”等數字化監控手段,探索數字化的監管(如非羈碼)或數字監獄,推動刑罰體系從生命刑、身體刑向權利刑、資格刑轉化的同時,豐富和發展保安處分制度,使制裁手段從物理消滅、身體拘束、財產剝奪向權利限制、資格剝奪、行為或過程監控的方向發展。應借鑒“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推動有形的懲罰向無形的懲罰轉變。
數字化保安處分目前尚不具普遍適用的可行性,但可以先行先試,適用于輕微犯罪,尤其是初犯、偶犯、過失犯、法定犯,或者非暴力犯罪,或者未成年人、老年人、懷孕或哺乳期的婦女等等。對于假性犯罪人格的行為人以監視規訓為主,而對真實犯罪人格的行為人則主要以自由刑等傳統刑罰加以應對。
在后現代語境中,數據庫的權力技術統治模式消解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限,實現了對人全面的、無時無刻的監視和規訓。據此,波斯特將福柯的全景監獄理論與數據庫聯系起來,提出了“超級全景監獄”理論。這是推行數字監控或數字刑罰過程中必須高度警惕的,要避免整體控制或全面控制(total control),防止數字監控淪為互聯網全景監獄。〔34〕參見呂安心:《波斯特超級全景監獄與福柯全景監獄比較研究》,載《學理論》2017 年第7 期。基于保障人權、維護人格尊嚴的底線原則,應對數字化保安處分予以特別限制。
(五)行刑機制的創新
輕罪時代意味著五分之四的罪犯或將經受機構矯正(3 年以下短期自由刑)而很快重返社會,或將通過社區矯正等行刑方式而受到規訓懲罰教育。因此行刑社會化以克服短期自由刑之弊、如何更好地運用社區矯正等非拘禁措施就變得至關重要。隨著刑事政策的進一步人道化和科學化,當今世界范圍內出現了非自由刑化或非監禁措施為中心的趨勢,聯合國大會1990 年12 月24 日通過了《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東京規則》),自由刑的適用受到嚴格限制。相比于一般而言的非監禁刑,《東京規則》的非拘禁措施(又譯非剝奪自由的措施)涵義更廣,適用于所有受到起訴、審判或執行判決的人,覆蓋從審前至判決后處置的各個階段。〔35〕聯合國大會1990 年12 月24 日通過的《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東京規則)中,使用了“非監禁措施”(non-custodial measures)這個術語,在聯合國的文件中又被翻譯為“非拘禁措施”。具體包括審前處置(如撤銷訴訟;對輕微犯罪案件,檢察官可酌情處以適當的非拘禁措施)、避免審前拘留(應將審前拘留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最后手段加以使用);在審訊和判決階段的非拘禁措施有社會調查報告;口頭制裁,如告誡、申訴和警告;條件撤銷;身份處罰;經濟處分和罰款,如罰錢和按日計算的罰金;沒收或征用令;對被害者追復原物或賠償令;中止或推遲判決;緩刑和司法監督;社區服務令;送管教中心;軟禁;以及任何其他非監禁方式,或上述辦法的某種結合;判決后階段的處置辦法包括:準假和中途管教所;工作或學習假;各種形式的假釋;寬恕;赦免。《東京規則》同時鼓勵制定和密切監督新的非拘禁措施,并對其使用情況進行有系統的評價;要求根據法律保障措施和法制,考慮在社區內對罪犯加以處理,避免訴諸正規的訴訟或法院審判;強調采用非拘禁措施應成為向非刑罰化和非犯罪化方向努力的一部分,而不得干預或延誤為此目的進行的努力。相形之下,我國對于非拘禁措施的理解是狹隘的,基本限于非監禁刑,〔36〕如2011 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國家安全廳、司法廳聯合出臺《關于依法正確使用和執行非監禁刑的指導意見(試行)》(2011 年6 月1 日施行)。而在審前階段和行刑階段基本忽略。隨著社會治安的好轉、犯罪治理能力的提高,為科學應對輕罪時代的新形勢,應在刑事案件辦理的全流程努力貫徹《東京規則》的各種非拘禁措施。目前檢察機關正在推行的少捕慎押理念值得公安機關、審判機關和刑罰執行機關學習。為了進一步擴大非拘禁措施的適用,立法司法應學習借鑒對于失信被執行人或“老賴”的約束機制,以行為禁止、資格剝奪或從業禁止等為核心,〔37〕參見2016 年9 月25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具體包括禁止出入境,上高速,禁止某些駕駛行為,凍結駕駛證,限制駕駛證年檢;限制高消費,從事特殊行業或項目限制包括設立金融類公司限制、發行債券限制、股權激勵限制、合格投資者額度限制、股票發行或掛牌轉讓限制、設立社會組織限制、參與政府投資項目或主要使用財政性資金項目限制等;政府支持或補貼限制;任職資格限制如擔任國企高管、事業單位法定代表人、金融機構高管、社會組織負責人、招錄為公務員、入黨、擔任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入伍資格;又如特殊行業準入資格,如海關、食品藥品行業;特殊市場交易限制,如不得從事不動產交易,不得使用國有林地、草原;限制支付寶、芝麻信用等網絡支付工具;以及通信限制、執行中手機定位、“老賴”可被強制解除勞動合同、App 標注“老賴”號碼等等。積極推動相關立法。
(六)程序的多元化
在推動實體法變革的同時,刑事程序也要嚴而不厲,力推繁簡分流、快慢分道,構建普通、簡易、速裁和認罪認罰等多層次訴訟程序,訴訟、調解、仲裁、線上線下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多元多層,靈活快速,以有效治理輕微犯罪。實體程序和刑罰執行等全過程均要一體推行“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思想。
1979 年刑訴法制定后,經歷了1996 年、2012 年與2018 年的多次修正,一個主要的方向是追求程序的多元化,雖有積極成效,但仍需改進以適應新形勢需要。以2012 年刑訴法修改為例,雖然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但仍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于是通過立法機關特別授權的方式進行輕罪速裁程序的改革(2014-2016 年)和認罪認罰制度的改革(2016-2018 年)等等,待改革成效得到驗證后再通過立法修改加以確認。
在擴大犯罪圈的同時,立法司法機關也在探索繁簡分流、快慢分道和輕重分離的程序制度改革,推進科學治理。如將刑事和解、調解機制與簡易程序、速裁機制(如針對輕微案件的48 小時速裁機制)、認罪認罰制度有機結合;根據刑事案件刑罰輕重與難易程度確定級別管轄,在貫徹二審終審制原則的前提下探索特殊的第三審制度(如死刑復核程序事實上正在向第三審的方向發展)等(見表5)。

表5 犯罪分層
輕罪時代的犯罪治理也須高度重視社會環境建設。從自然犯為主過渡到法定犯為主,意味著犯罪的道德非難程度降低,報應、復仇等基于自然犯罪的刑罰根據退居第二位,而恢復法秩序、強化法權威的根據上升。輕罪微罪為主的時代,對犯罪的法律制裁相應降低,其社會容忍度相應提高,這是輕罪時代犯罪治理的社會條件。為此必須改變罪不可赦、十惡不赦等傳統的重罪觀念,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分層次配置犯罪的附隨后果,破除一刀切的機械做法。最重要的是轉變社會觀念,要順應時代的變化,順應犯罪現象量與質的變化,學會寬容、容忍,守法公民要接受并適應與犯罪人共同生活的現實,學會和平共處。如此,則立法、司法、執行、預防等等改革才能進行。要更加重視犯罪治理的多元參與,更加注重信息網絡時代的犯罪治理信息溝通與共享。犯罪治理相關數據尤其是犯罪統計數據,既是犯罪治理的成果展現,是觀察測量犯罪現象的重要工具方法,又是評判犯罪治理績效的基本依據,更是大數據時代犯罪治理的寶貴資源和社會公共財富。以統計數據來展示犯罪治理的成就,可以更好地宣傳犯罪治理業績,樹立犯罪治理的自信,凝聚犯罪治理的合力,取得更優的犯罪治理績效,鞏固并彰顯制度優勢。
五、結 語
在新時代,我國社會治安形勢總體平穩,但也面臨諸多挑戰。犯罪圈擴大后,由重罪為主轉向輕微罪為主,要求刑罰或制裁相應輕緩,并與非刑罰處遇更好銜接;同時,刑事程序也須相應變革,與審級管轄、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等等相配套。
輕微罪治理與重罪治理相比更為復雜:重罪治理關乎生死,社會關注度高,而輕微罪治理基本都在犬牙交錯地帶,關乎罪與非罪,既要防止刑法過度干預社會生活,又涉及刑行銜接、刑民交叉,關涉自由財產,因而更加考驗治理者的政策水平、理論功底和專業能力。未來在犯罪外部邊界清晰、內部層次結構分明之后,還將面臨“層移”,也即不同層次之間的位移或升級(如違法升級為犯罪,或微罪升級為輕罪,輕罪升級為重罪)、或降級(如重罪降級為輕罪、輕罪降級為微罪,微罪變成無罪)〔38〕如法國刑法理論和實務中就細致地區分重罪化(criminalisation)、輕罪化(correctionnalisation)與微罪化(contraventionnalisation)。,因而輕罪的治理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犯罪化、輕罪化甚至輕刑化的主張,也會招致反對,如立法擁擠(倉促)、頻繁修法,過罪化,象征性立法,違反刑法謙抑性,增大犯罪效應,引發社會恐慌等等,不一而足。但事實證明,很多恐慌都是臆想,而很多問題,如立法倉促、修法頻繁等可通過科學立法、優化頂層設計加以解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犯罪治理首先需要依法,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亟待提高,治理績效或治理效能也有賴于法治化的保障。法治意味著權力受到限制,所有公權力均須謙抑。作為最后法的刑法自當謙抑,而作為前置法的行政法、警察法更須謙抑。目前單純強調刑法謙抑,而忽視行政權特別是警察權的擴張,有違法治精神。罪刑法定、程序正當,即是謙抑之道。
從重罪時代進入輕罪時代,刑法法網從小而大、網眼從疏而密,法條或罪名從少而多,刑罰從嚴厲到輕緩,制裁從單一到多元,程序從剛性到柔性、靈活,刑法治理從重罪向輕微犯罪板塊的整體位移和層次下移,從自然犯向法定犯、經濟犯,從線下犯罪向網絡犯罪,從實害犯、結果犯向危險犯、秩序犯位移,犯罪治理向違法越軌行為的源頭位移,刑法功能從懲罰打擊為主向預防治理、教化規訓為主,宗旨都是為了實現輕罪時代犯罪治理的科學化。
輕罪時代犯罪治理方略的變革有賴于刑事科學方法論的革命。宏觀地看,改革開放不僅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也使我國的犯罪治理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對于犯罪現象的認識已經從想象的時代進入觀察、計量的時代,統計、量化分析、實證研究成為刑事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方法。借助犯罪統計、公布裁判文書、各種民調或田野研究的數據資料,對犯罪現象的認識已經進入數字時代,犯罪治理也從感性時代進入理性時代。這不僅實踐了法國哲學家孔德提出的“觀察優于想象”的實證主義理念,也符合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本立場,即以經驗事實為依據,以唯物辯證法為分析手段,在具體的社會過程和社會聯系中探求歷史發展規律。理性的基礎特征即算計,主要是成本與收益的比較。理性的犯罪治理是在資源稀缺的總約束之下以盡可能少的治理資源投入,產生盡可能好的治理效益,追求最佳治理效能,這是經濟理性主義的要求。而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語境下,又須實行嚴格的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和適用刑法一律平等,這是法治主義的基本要求。在引入實證研究方法之后,理性同樣要求根據犯罪現象的內在復雜結構和外部關聯關系,引入橫向的犯罪分類與縱向的犯罪分層等方法,更加精準地把握犯罪現象發展演化的規律和趨勢,科學評判犯罪現象的危害與影響,及時調整犯罪治理的戰略戰術,從而實現更加精準、科學高效的治理。
借助犯罪統計和犯罪分層等科學方法,可以認定我國犯罪治理已經進入輕罪時代,這是一個客觀社會現實,也是一種發展趨勢。但是輕罪時代,或更加確切地說是輕微犯罪為主的時代,并不否認其中嚴重犯罪的存在(如暴恐犯罪、黑惡勢力犯罪、毒品犯罪、黃賭毒犯罪、新型網絡犯罪、跨國犯罪、盜搶騙犯罪、食藥環境等影響民生的犯罪等等),不否認某些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人、殘害群眾的惡性案件的發生,甚至也不排除在個別或極端的情況下,輕罪時代也可能逆轉,重罪輕罪的比例會發生逆變化。人民群眾對于社會治安的滿意度、對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認同度,對于犯罪治理的自信心會因此發生搖擺。為了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個奇跡,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當前的犯罪治理既要摒棄重刑主義或嚴打思維,立足輕重分離,科學治理輕罪,預防重罪;也要居安思危,嚴格依法辦案,防止“有案不立、壓案不查、有罪不究”等敷衍塞責甚至粉飾太平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