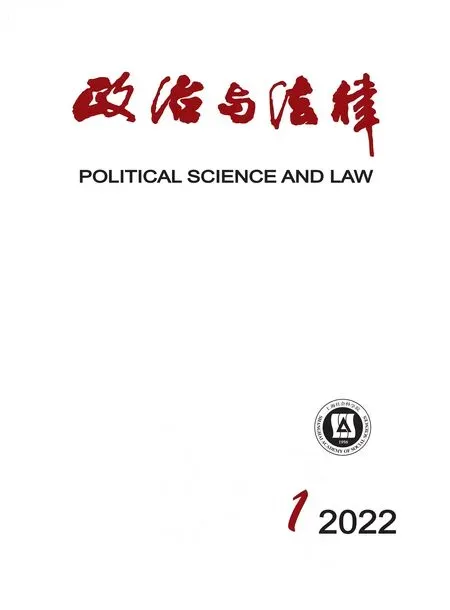走私犯罪既未遂形態認定研究*
金澤剛
(同濟大學法學院,上海 200092)
有數據表明,自 2015 年起,在每年公安的刑事立案數量中走私犯罪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如 2017年立案數甚至超過 2015 年的 40%。〔1〕參見中國犯罪學學會組織編撰:《中國犯罪治理藍皮書 犯罪態勢與研究報告(2019)》,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1 頁。同時,隨著法學研究的精細化,在審理走私案件時,一些理論爭議如既未遂的區分標準等問題越來越突出。盡管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曾出臺《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2002 年《意見》),2014 年兩高也發布了《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4 年《解釋》),對走私犯罪既未遂的問題作了部分規定,但囿于走私案件類型的復雜性,司法實踐中對各類走私行為既未遂認定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和時間差別。因此,有必要對近年來我國走私犯罪的裁判情況進行梳理,總結審判規律,發掘裁量矛盾,依據刑法理論,提出一套相對科學、完善的走私犯罪既未遂形態的界定標準。
一、我國走私案件未遂判決的現狀
截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筆者以“走私”“犯罪未遂”為條件檢索裁判文書網,得出裁判文書共計5968 篇(最早的為 2008 年),占全部走私類裁判文書(244813)的 2.44%。
但是,其中絕大部分案由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而這一類犯罪(選擇性罪名)實踐中又以販賣毒品罪為主,即裁判文書網中絕大部分“走私未遂”的判決實際為販賣毒品未遂的判決。剔除此類及其他類似無效判決后,〔2〕即行為人所犯的并不是走私犯罪,但由于曾經有過走私經歷等原因在判決書中出現了“走私”字眼而被檢索出來。我們對這部分判決也進行了剔除。篩選出全部“辯護意見認為屬于走私未遂”的判決共 229 份〔3〕當行為人明顯屬于走私既遂,也未提出未遂的辯護意見時,即不存在未遂的認定問題。同時,從司法實踐來看,也不存在辯護意見認為既遂、法院認定為未遂的案件。因此,我們的樣本選取目標除全部法院最后認定走私未遂的案件外(當然這部分案件也均提出了未遂的辯護意見),還加入了辯護意見認為屬于走私未遂,但法院最后認定既遂的案件,以對比得出法院在走私犯罪既未遂認定問題上的標準與差異,這兩類案件在裁判文書網中合計 229 起。,整理其中法院判決未遂的情況,以分析司法機關在走私犯罪未遂方面的認定標準,具體如下。
(一)走私未遂裁判的總體情況
在全部 229 份裁判文書樣本中,走私毒品類犯罪為 81 起,占比 35.4%;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為 47 起,占比 20.5%;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犯罪為 32 起,占比 14.0%;走私廢物犯罪為 23起,占比 10.0%;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犯罪為 22 起,占比 9.6%;走私貴重金屬犯罪為 13起,占比5.7%;走私武器、彈藥犯罪為 9 起,占比 4.0%;走私淫穢物品犯罪為 2 起,占比 0.9%(見圖1)。

圖1 涉走私未遂判決中的各罪占比
最終,各地法院認定為走私既遂的為 142 起,認定為走私未遂的為 87 起,未遂的認定率為38.0%。其中,由于走私淫穢物品罪的樣本量過小,故其 50%的未遂認定率參考意義不大。除此以外,其他各走私類型中未遂認定率最高的為走私普通貨物罪(44.7%,21/47),此后未遂認定率從高到低分別是走私毒品罪(44.4%,36/81)、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40.9%,9/22)、走私珍貴動物、動物制品罪(31.3%,10/32)、走私廢物罪(30.4%,7/23)、走私貴重金屬罪(15.4%,2/13)、走私武器、彈藥罪(11.1%,1/9)(見圖2)。

圖2 不同走私罪名的未遂認定情況
從裁判時間上看,目前上網文書中第一例走私未遂的案件為 2009 年的“徐克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案。”〔4〕參見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浙溫刑初字第 274 號刑事判決書。此后至 2013 年間未遂認定均較少。隨著2014 年“兩高”和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出臺,走私犯罪既未遂的認定有了較為明晰的標準,此后的一年(2015 年)走私未遂判決開始顯著增加,但在 2016 年又回歸穩定。隨著近年來刑法謙抑精神的認同和刑罰適用輕緩化趨勢的再提倡,我國司法機關對犯罪未遂的認定也更加積極,作為經濟犯罪的走私未遂的認定數量也從 2018 年開始迎來高峰〔5〕因2021 年的裁判還未全部上網,故 2021 年整體判決書數量及走私未遂判決數量均較少。(見圖3)。

圖5 不同年份的走私未遂判決數量
從走私的行為類型上看,87 起走私未遂的案件全部由通關走私、繞關走私和間接走私三種形式構成。〔6〕事實上,后續走私等其他走私類型在司法實踐中也有不少,但暫時未在裁判文書網中檢索出未遂的判決。即行為人主要采取的是偽報、藏匿、蒙混和闖關,或使用私人船舶、車輛等繞過海關設關地,或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國家禁止進口物品這三種行為方式。其中,通關走私數量最多,為 51 起,占比 58.6%;其次為繞關走私,為 31 起,占比 35.6%;間接走私僅 5 起,占比 5.8%。值得一提的是,這三種走私行為類型又分別是由不同的罪名構成。例如,51 起通關走私未遂中,有 29 起均為走私毒品案件;〔7〕其中,走私毒品 29 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 6 起,走私珍貴動物制品 6 起,走私廢物 7 起,走私貴重金屬 1 起,走私武器、彈藥 1 起,走私淫穢物品 1 起,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 0 起,合計 51 起。31 起繞關走私未遂中,有近半數(15 起)均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8〕其中,走私毒品 7 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 15 起,走私珍貴動物制品 0 起,走私廢物 0 起,走私貴重金屬 1 起,走私武器、彈藥 0 起,走私淫穢物品 0 起,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 8 起,合計 31 起。5 起間接走私未遂中,絕大部分(4 起)屬于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件。〔9〕其中,走私毒品 0 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 0 起,走私珍貴動物制品 4 起,走私廢物 0 起,走私貴重金屬 0 起,走私武器、彈藥 0 起,走私淫穢物品 0 起,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 1 起,合計 5 起。這主要是因為,毒品體積較小,容易藏匿于體內或其他物品之中以逃避海關查驗,故行為人較多選取通關的方式。而普通貨物、物品通常為服裝、原材料、冷凍食品或其他大宗貨物,體積較大、數量較多,故行為人更青睞繞關走私的方式。最后,象牙、犀牛角、虎皮等珍貴動物制品的需求者一般為具有一定經濟實力或特殊癖好的企業管理者,他們自己不會參與走私,而是向其他走私人直接購買此類動物制品,從而成為了間接走私的主體(見表1)。

表1 不同走私形式未遂判決中的罪名差異
(二)法院認定走私未遂的主要原因
我國《刑法》第23 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但具體到司法實踐中,如何統一認定既未遂形態始終是個難題。
就走私犯罪而言,2014 年《解釋》曾對走私犯罪既未遂問題作出規定,但其是從“負面清單”即哪幾種情況為既遂的角度來嘗試劃分既未遂的界限,如2014 年《解釋》第23 條規定:“實施走私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犯罪既遂:(一)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的;(二)以虛假申報方式走私,申報行為實施完畢的;(三)以保稅貨物或者特定減稅、免稅進口的貨物、物品為對象走私,在境內銷售的,或者申請核銷行為實施完畢的。”換言之,如果未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虛假申報行為未實施完畢、減免稅貨物核銷行為未實施完畢的,就應當以走私未遂論處。但從司法裁判的現狀來看,各地法院對走私犯罪未遂的認定標準并不統一,甚至相互矛盾,大體可涵蓋以下幾類。
一是以藏匿等手段入境,接受海關檢驗時被當場查獲,主要發生在各類通關走私案件中。〔10〕此類行為應當以走私既遂論處,但實踐中認定為未遂的仍然存在。如許榮國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參見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 04 刑初 43 號刑事判決書。二是在走私過程中交通工具出現故障導致出入境失敗,主要發生在各類繞關走私案件中。〔11〕如屠桂善、章開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參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浙 02 刑初 88 號刑事裁定書。三是在走私物分批入境時,后續部分貨物尚未入境,主要發生在各類通關走私案件中。〔12〕如林保佳、泉州極尊貿易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參見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閩02 刑初 45 號刑事判決書。四是走私物尚未進(出)入我國國境時即被緝私人員(或他國海警)查獲,主要發生在各類繞關走私案件中。〔13〕如劉志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參見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遼 02 刑初 115 號刑事判決書。五是以郵寄等形式走私時,包裹在郵寄途中丟失或被快遞人員發現,主要發生在以毒品為對象的通關走私案件中。〔14〕如徐克走私毒品案,參見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浙溫刑初字第 274 號刑事判決書。六是在向其他走私人購買走私物時,因其他走私人被抓獲而未購買成功,主要發生在以象牙、犀牛角等珍貴動物制品為對象的間接走私案件中。〔15〕如李道宇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案,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粵高法刑二終字第 19 號刑事裁定書。七是在走私出境前裝載貨物或倉儲時被警方查獲,主要發生在各類繞關走私案件中。〔16〕如馬國強等人走私普通貨物案,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20)桂刑終 178 號刑事判決書。八是在入境申報時,部分走私物還未進行申報并未入境,主要發生在各類通關走私案件中。〔17〕如廣東順德潤槿貿易有限公司走私廢物案,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粵刑終 809 號刑事裁定書。這些案件在適用上述解釋時,亟待統一適用標準。
(三)走私犯罪未遂判決的具體矛盾與認定難點
首先,走私物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的,認定未遂與既遂結果不一。盡管2014 年《解釋》明確規定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犯罪既遂,但 2014 年后仍有部分判決無視該司法解釋的存在,僅根據我國《刑法》第23 條,認為被海關查獲屬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從而認定為未遂。例如,在前述許榮國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中,法院認為,許榮國已經著手實行銷售珍貴動物制品的行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海關現場查獲——筆者注,結合判決書前文得出),根據我國《刑法》第23 條,應認定為犯罪未遂。另有大部分判決援引了 2014 年《解釋》,將該類行為認定為既遂。如在劉曉昀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中,法院指出,依據《解釋》第23 條第1 項之規定,“實施走私犯罪,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的,應認定為犯罪既遂;本案被告人劉曉昀 2018 年 3 月11 日走私的鯨牙被海關現場查獲,應認定為犯罪既遂。”〔18〕參見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湘 01 刑初 113 號刑事判決書。
其次,在以虛假申報為形式的走私行為中,申報行為完成后被海關查獲的,認定既遂與未遂也不一致。根據 2014 年《解釋》,申報行為實施完畢的應當認定為既遂。換言之,只有未進行申報或申報行為未完成的才構成未遂。例如,在顏海曉走私廢物案中,〔19〕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粵刑終 808 號刑事判決書。顏海曉得知前兩批貨物被海關查獲后,其第三批貨物到達南沙港碼頭進入海關監管區但未申報進口,法院即認為“顏海曉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將第三批貨物申報入境,是犯罪未遂”。但在文一東走私廢物案中,〔20〕參見山東省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威刑二初字第 5 號刑事判決書。文一東以偽報品名的方式走私進口牛皮邊角料,準備了核銷單等所有報關材料,并向威海海關進行了申報進境,后在檢驗過程中被查獲,法院仍將文一東的走私行為認定為走私未遂。
再次,在間接走私中,走私物入境后被海關查獲的,購買者既未遂的認定不一致。這類案件中,由于其他上游走私人已經攜帶走私物入境,故其被查獲后顯然應認定為既遂。但是,購買者并未實際接收到走私物,其應認定既遂還是未遂存在爭議。如在陳澤斌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案〔21〕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9)桂刑終 446 號刑事裁定書。中,陳澤斌通過微信向他人訂購從越南走私入境的象牙制品,他人通過快遞發貨給陳澤斌途中被查獲,法院仍將陳澤斌認定為犯罪既遂。相反,在李道宇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案〔22〕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粵高法刑二終字第 19 號刑事裁定書。中,針對同樣的行為,法院則認為“李道宇案發當天攜帶贓款準備向走私分子直接購買走私的象牙,其行為應按走私論,構成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因自己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賣家被抓獲——筆者注),屬于犯罪未遂。”
此外,在走私共同犯罪中,共犯的既未遂認定存在差異。我國《刑法》第156 條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在共同走私中,對于部分共犯的停止形態問題是否會直接影響其他共犯,實踐中做法不一。根據理論通說,當具體實施走私行為者犯罪既遂時,其他共犯一般也應認定既遂;〔23〕例如曹中斌走私武器、彈藥案,參見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皖 01 刑初 44 號刑事判決書。當具體實施走私行為者犯罪未遂時,其他共犯一般也以未遂論處。〔24〕例如利宇駿等三人走私毒品案,參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閩刑終 283 號刑事裁定書。但是實踐中,具體實施走私行為的犯罪人被查獲后認定既遂,其他負責聯絡、資金管理的共犯認定未遂的案例也不在少數。〔25〕例如在俄沙、才讓旦真、澤爾登等走私貴重金屬案中,俄沙、才讓旦真、澤爾登、彭曲、奪爾科等分別負責聯絡買家、資金管理、走私行為等工作。2018 年 3 月 12 日俄沙、澤爾登、奪爾科在走私過程中被查獲,三人均被認定為走私既遂。后才讓旦真、彭曲在聞訊逃匿時被抓獲,被當地法院認定為走私未遂。參見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川 01 刑初 245 號刑事判決書。
出現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對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本身存在認識偏差,而實際上則要歸咎于既未遂的判斷在法理上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加上走私犯罪的復雜多樣性,其既未遂的認定爭議更大,亟待提出一套科學、實用的理論標準,以指導司法實踐。
二、從法益侵害的本質探索走私犯罪的既未遂標準
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或對法益產生危險),而犯罪的本質也應該貫徹于犯罪認定的整個過程之中。作為犯罪過程中的停止形態,既未遂的判斷,也應回歸到對犯罪本質特征的考察中來。
(一)法益侵害與犯罪既未遂的關系
法益這一概念起源于比恩鮑姆(Birnbaum)的財(益)侵害說。比恩鮑姆認為,抽象的權利本身不可能受到侵害或減損,受到侵害的只能是權利的內容或者說對象或客體,即“法律上歸屬于我們的財(益)”。犯罪行為正是因為侵犯了他人的“財(益)”而應當受到相應的刑事處罰。〔26〕轉引自王鋼:《法益與社會危害性之關系辯證》,載《浙江社會科學》2020 年第 4 期。后來,法益在德國經歷了形式法益說和實質法益說的嬗變,形式法益說以賓丁(Binding)為代表,其認為法益的定義全部基于刑法本身而來,法益是刑法行為規范被遵守的一種狀態。實質法益說以李斯特(Liszt)為代表,其認為法益實質上是國家共同體的生活條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個人的生活條件,不是法秩序產生法益,而是生活產生利益。即法益并不是源于刑法,而是源于刑法之外。后來法益說經由日本學者的改造傳入我國。我國傳統刑法是基于“社會危害性”這一核心概念來把握犯罪的本質特征。20 世紀90 年代,經楊春洗、張明楷等學者研究,法益的概念逐步納入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論中。在此基礎上,有學者認為,犯罪既遂同未遂在宏觀上的根本區別在于行為在人們的經驗層面上足以引發的“客觀實害”是否出現。簡言之,犯罪的本質為侵犯合法權益,刑法的目的則是保護合法權益。因此,犯罪既遂理應以“犯罪行為給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造成實害”為根本標準。〔27〕參見馮亞東、胡東飛:《犯罪既遂標準新論——以刑法目的為視角的剖析》,載《法學》2002 年第 9 期。所以,“從與法益的關系來看,區分未遂與既遂的基本標準應當是,行為是否發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法益侵害結果。”〔28〕參見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3 頁。這可以稱為“法益侵害結果說”。
不過,也有學者反對將法益的概念引入既未遂的判斷中。“首先,法益侵害主要解決的是定罪問題,沒有法益侵害的行為不論是立法上還是司法上均不宜納入刑事打擊的范圍。其次,將法益侵害作為既未遂的認定標準,對于判斷是否著手實施犯罪行為具有一定意義,但對于犯罪實行完畢的認定沒有任何意義。一定程度上,任何犯罪行為的著手實施都將對法益構成威脅,而不論該行為是否實施完畢。再次,賦予法益侵害的既未遂認定意義,必將導致法益侵害理解的擴大化和抽象化,對于不要求犯罪結果的行為犯,將抽象的法益侵害作為既未遂認定標準,也不具有實踐可操作性。”〔29〕參見南英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0 頁。
筆者認為,從法益侵害的視角來研究既未遂問題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強調的是:其一,法益侵害是犯罪的本質特征,只要行為構成犯罪就必然存在法益侵害,故是否存在法益侵害解決的只是罪與非罪問題。即便存在法益侵害,也并不必然意味著犯罪已然既遂。由于刑法的規定以既遂犯為模式,一般案例實踐中處理的大都是既遂犯,所以就習慣性地認為侵犯了法益,構成了犯罪,也就既遂了。但現在要研究的卻是既未遂的區分問題,未遂犯無疑也是侵害法益的,只是二者侵害法益的性質或者程度有所不同。〔30〕研究的前提當然是有可能也有必要區分既未遂的犯罪。不排除一些輕罪無處罰未遂的必要,也可能有的犯罪著手實行即為既遂。不能把對構成要件的判斷與既未遂的判斷相混淆。其二,如果僅將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結果作為既未遂的標準并不科學。按照“法益侵害結果說”的觀點,犯罪行為造成法益侵害結果的屬于既遂,反之屬于未遂。但這只是針對那些能夠判斷將結果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即結果犯)而言,而大多數犯罪是否存在這樣的結果,或者這個結果的評價標準是什么,本身存在很大爭議。對于那些只是實施一定危害行為,難以區分是行為實施到某個階段了,還是發生了某種犯罪結果的犯罪(如行為犯),更無法尋找這個法益侵害的“結果”。同時,法益侵害結果說與傳統既遂理論中的“結果說”并無本質差異,只是將結果進一步聚焦在了“法益侵害結果”。
所以,我們承認法益侵害在犯罪既未遂認定中的重要性,但判斷的重心不在“有無”侵害,而應在侵害的性質或者程度上,既遂犯侵害法益的程度可能是某種危害結果的發生,也可能不必等到發生實害結果。是否存在法益侵害只是既未遂判斷的前提而非歸宿,只有存在法益侵害即可能構成犯罪時才存在既未遂判斷的問題。對于大多數故意犯罪而言,隨著實行行為的向前推進,法益遭受侵害的程度會越來越嚴重,未遂犯較既遂犯的法益侵害程度低,但較無罪或預備犯的法益侵害程度要高。而究竟將既未遂的臨界點確定在什么地方,不僅取決于被侵犯法益的性質,更取決于該犯罪停止形態的常見形式,還與民眾的基本認知有關。例如,法益越重要,既遂認定會越靠前;既遂犯常常是該犯罪常見的典型形態,某種犯罪很少呈現出來的表現形式不能作為既遂的標準,如殺人罪以致人死亡為既遂標準,但放火罪顯然不能認為燒光了財產才是既遂。
而當具體犯罪侵犯多種法益時,則要考察主要法益遭受侵害的性質和程度,以認定是既遂還是未遂。以搶劫罪為例,搶劫罪侵犯財產權益和人身權益,一般搶劫罪以侵犯財產法益為主,未劫取財物為未遂,但當致人輕傷以上時,根據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即使未劫得財物,也構成既遂。〔31〕該意見之十規定:搶劫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后果的,屬搶劫未遂。據此,《刑法》第263 條規定的八種處罰情節中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這一結果加重情節之外,其余七種處罰情節同樣存在既遂、未遂問題,其中屬搶劫未遂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加重情節的法定刑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因為在搶劫致人輕傷或者重傷、死亡的情況下,其侵犯的主要法益是人身法益而非財產法益。對主要法益的判斷,取決于行為對象、犯罪目的、實際危害等因素,下文將結合走私犯罪做進一步探討。
(二)走私犯罪侵犯的法益與著手的認定
走私犯罪屬于大類罪名,刑法分則根據走私犯罪的對象劃分出十個具體的走私罪名。對于類罪侵犯的法益,傳統刑法理論稱之為“同類客體”,對類罪之下的個罪的法益,則稱為“直接客體”。但對同類客體與直接客體的關系鮮有論證,比如說,我國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的同類客體與各章項下具體個罪的直接客體似乎并無差異,然而,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項下的具體罪名的直接客體與這兩大類罪的同類客體則可能不同。比如,生產、銷售、提供假藥罪,不僅侵犯市場經濟秩序,也危害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權益;集資詐騙罪不僅侵犯市場經濟秩序(金融秩序),還侵犯他人的財產權益;尋釁滋事罪不僅侵犯社會管理秩序,還危害他人身體健康或財產權益,等等。走私類犯罪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
自從走私類犯罪被分為十個不同的走私罪名之后,對于它們侵犯同類法益的研究甚少,研究者著重關注的是個罪的客體或者對象。不同走私個罪的直接客體有的是單一客體,有的是復雜客體。如有觀點認為,走私武器、彈藥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文物罪以及走私貴重金屬罪屬于單一客體,侵犯的是國家對外貿易管制制度或者進出口管理制度。而其他如走私假幣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淫穢物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等六個罪名,侵犯的是復雜客體,除了國家對外貿易管制制度或者進出口管理制度外,還有國家貨幣管理制度、野生動物保護制度、海關監管秩序、社會管理秩序、環境保護制度,以及稅收制度等。〔32〕參見謝望原等著:《刑法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2-100 頁。從這些個罪的客體來看,其侵犯的法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共同侵犯的同類法益,即國家外貿管制制度或者進出口管理制度,另一類是由犯罪對象決定的特殊法益,這種特殊法益可以稱為該罪的間接性法益。而同類法益則是我國學界的主流觀點,盡管表述不同,但本質上并無太大差異。如有學者認為,走私犯罪侵犯的是國家的外貿管理制度。〔33〕參見馬克昌主編:《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0 頁。有學者認為是國家的海關監管制度。〔34〕參見王作富主編:《經濟活動中的罪與非罪的界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4 頁。此外,還有學者表述為國家進出口貿易制度、國家稅收制度等。〔35〕另外,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七節還專門規制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走私毒品罪所侵犯的法益應當是國家對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益。筆者認為,走私犯罪的主要客體或者法益是國家外貿管制和海關監管制度,外貿管制和海關監管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前者反映的是國家對貨物進出口的法律規制,后者是對前者的查驗執行。正是基于犯罪對象和法益的緊密聯系,不同的走私對象反映出法益侵害的特殊性。如對于應稅貨物,我國采取的管理方式是繳納關稅和代征稅的制度,只要繳納了關稅和代征稅,行為人就可自由進出境,因此走私應稅貨物侵犯的法益主要為我國的稅收制度。而對于某些限制進出口的貨物,我國采取的管理方式是采用配額管理和許可證管理,即對某種貨物、物品的進出口配置相應的額度予以進出口和發放許可證予以進出口兩種方式,因此走私這類限制進出口貨物侵犯的法益主要為我國的外貿管理制度。而對于禁止進出口(包括只禁止出口)的貨物,我國完全禁止申報,不得進口與出口,此時走私行為侵犯的主要為我國的海關監管制度。但不同走私犯罪針對的對象不同,同時還會侵犯其他法益,即使這種侵犯具有間接性,但這仍然是刑法應當保護的利益,如環境資源法益、國家稅收法益等。而衡量社會危害性,主要依據侵犯的主要法益進行判斷,間接性法益起次要的輔助作用。同樣地,走私犯罪的既未遂也要依據侵害主要法益的程度進行判斷。
厘清了走私犯罪侵犯的法益及其差異,隨之而來的則是如何判斷走私行為的著手,因為只有著手了,才可能產生既未遂。
著手是實行行為的起點,而何為著手,理論界同樣存在爭議。目前,關于著手及其認定,主要存在主觀說、客觀說、折中說等觀點。其中,客觀說內部又分為形式客觀說和實質客觀說,而實質客觀說又可再細分為行為說和結果說等。具體而言,主觀說認為,犯罪是行為人危險性格的外化,因此當行為人犯意彰顯時即為著手。〔36〕參見[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刑法總論教科書》,蔡桂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7 頁。形式的客觀說認為,當行為人開始實施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時即為著手。形式的客觀說是我國的通說。實質客觀說中的行為說認為,當行為人開始實施具有現實危險性的行為時是著手,而結果說認為,只有當行為發生了作為未遂犯的結果(或至少為緊迫危險)時才是著手。〔37〕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2 頁。折中說認為,當行為人以表現于外的客觀行為明確顯示其犯罪意圖,并以明顯顯示其犯罪危險性的方式實施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時為著手。〔38〕參見謝望原:《保險詐騙罪的三個爭議問題》,載《中外法學》2020 年第 4 期。
其實,上述觀點適用于大部分案件所得結論一般大同小異。只不過在具體的認定過程中,主觀說與折中說中的“犯罪意圖”如何把握可能是難點。形式客觀說中什么才是“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行為”仍有待明晰;實質客觀說中的行為說和結果說對著手的認定似乎又一個過早一個過遲。同時,在隔地犯、復雜行為犯等領域,上述觀點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在郵寄毒物等形式的隔地犯中,根據不同的著手認定標準可能會得出寄送主義(即當行為人交付郵寄物之時就已著手)、到達主義(即當被害人收到郵寄物之時為著手)、被利用主義(即只有當被害人開始使用或服用毒物之時才可認定為著手)等不同的結論。又如,在以保險詐騙罪為代表的復雜行為犯中,實質客觀說中的結果說認為只有當行為人向保險公司索賠時,才能認為保險秩序和保險公司的財產受侵害的危險性達到了緊迫程度,此時才構成著手;〔39〕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第五版,第 342 頁;參見黎宏:《刑法學》,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85 頁。而形式客觀說、行為說、折中說等其他學說則認為當行為人故意造成保險事故時就已經著手。〔40〕參見謝望原:《保險詐騙罪的三個爭議問題》,載《中外法學》2020 年第 4 期。二者的爭議還是非常明顯的。
筆者認為,著手作為未遂犯處罰的時間起點,意味著自此產生了侵害法益的現實危險。這種現實危險既不能離犯罪的實害結果或者危害行為的最后階段太近,也不能太遠,甚至無以到達。在此,筆者在某種程度上贊同“只有當行為產生了侵害法益的具體危險狀態時,才是著手”的觀點〔41〕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第五版,第 342 頁。,但并不同意評價是否得逞的“侵害結果發生說”〔42〕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第五版,第 345 頁。。因此,著手的認定應當秉持“侵害的現實危險說”。具體而言,當法益沒有受到侵害的危險時不是著手。例如,購買意圖走私的珍貴動物制品,尚未對法益產生侵害危險,此時只是犯罪預備,而非著手。同時,法益還要瀕臨侵害的現實危險,是比較接近的危險。譬如,隨身攜帶貴重金屬出門開車去機場,此時法益雖然受到侵害,但尚未發生現實的危險,不宜認定為著手走私。但一旦到達機場海關監管區域,就是犯罪的著手。對于走私進口的既遂,日本的判例一直采取“上岸說”,對打算通過扔入海中然后回收這種方式走私進口興奮劑的案件,日本判例就否定存在實行著手。〔43〕參見[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王昭武等譯,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第二版,第 273 頁。
盡管不同的走私方式也會在實行的手段上體現出一定差異,但總體上,認定著手應當秉持的原則是,當主要法益有遭受侵害的現實危險時,才屬于犯罪的著手。例如,在通關走私中,當行為人收購走私物、購買機票、租賃集裝箱時,我國的外貿制度、海關監管秩序等法益尚未受到現實的侵害危險,此時只是犯罪預備。而當行為人攜帶走私物登機或集裝箱起運時,走私行為開始直接指向我國外貿管制和海關監管制度,法益受到了現實危險,此時就是犯罪著手。又如,行為人采取郵寄走私的,收購走私物、在家打包等行為仍屬犯罪預備,只有當行為人寄出走私物時,〔44〕值得注意的是,郵寄走私與前文郵寄毒物傷害或殺害他人犯罪存在差異。走私罪侵犯的法益為我國外貿制度、海關監管秩序等法益,因此當走私物寄出時法益就已經受到侵害危險,故采取“寄出主義”。而郵寄毒品傷害或殺害他人的,侵犯的法益為他人的身體健康或生命安全,因此“到達主義”或“被利用主義” 更為合適。我國外貿制度、海關監管秩序等法益才會受到現實侵害,此時才有著手和未遂認定的空間。如在張智勇、李慶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中〔45〕參見云南省臨滄市臨翔區人民法院(2019)云 0902 刑初 271 號刑事判決書。,李慶按照張智勇的吩咐,將獅子頭骨打包后從廣西省東興市某快遞站點寄出,快遞在經過廣西省臨滄市某分揀站時,被工作人員查驗出獅子頭骨并報警,后法院認定張智勇、李慶已經將走私物打包好寄出,屬于“已經著手實行犯罪”。
三、走私犯罪既未遂形態的具體認定
總的說來,當走私行為侵犯主要法益,并產生緊迫的危險時,就是犯罪既遂,而緊迫的危險可能出現在走私行為實行中的某個節點,無須走私行為全部實施完畢,更無需發生某個特定的結果。實踐中走私犯罪往往存在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在確定了主要法益和著手之后,判斷既未遂時,關注點還是要回到行為本身。〔46〕換言之,行為主體的身份、監管主體的差異性等不應成為影響既未遂認定的要素。例如,不可簡單地因查獲走私的主體不是海關而是公安機關(白所有卜走私貴重金屬案,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藏 02 刑初 4 號)、邊檢部門(齊一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5)二中刑初字第 7 號)等就認定為走私未遂。走私行為往往有一個將走私對象運(帶)進(出)海關的過程,全部行為實行完畢當然是既遂,中途被抓因而未完成全部行為未必就是未遂,但也并非只要在著手實行后被查獲的就是既遂。對于經濟犯罪沒有必要設置這么嚴苛的“超前” 既遂標準,而讓未遂幾乎沒有余地。走私行為必須要以國家外貿管制和海關監管制度已遭受緊迫的危險為犯罪完成的標志。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走私形式中,法益侵害程度的判斷也不盡相同。走私行為一般可區分為通關走私、后續走私、間接走私和繞關走私四種。〔47〕綜合我國《海關法》第82 條、第83 條的規定,走私行為包括:(一)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或者限制進出境貨物、物品或者依法應當繳納稅款的貨物、物品進出境的;(二)未經海關許可并且未繳納應納稅款、交驗有關許可證件,擅自將保稅貨物、特定減免稅貨物以及其他海關監管貨物、物品、進境的境外運輸工具,在境內銷售的;(三)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走私進口的貨物、物品的;(四)在內海、領海、界河、界湖,船舶及所載人員運輸、收購、販賣國家禁止或者限制進出境的貨物、物品,或者運輸、收購、販賣依法應當繳納稅款的貨物,沒有合法證明的;(五)有逃避海關監管,構成走私的其他行為的。現根據不同走私行為,分析其既未遂形態的判斷。
(一)通關走私
通關走私主要以藏匿、瞞報、偽報和闖關等為形式。在通關走私中,當行為人采取藏匿、瞞報手段企圖躲避海關檢查時,其犯罪行為就已經著手。例如,行為人將禁止或限制攜運的物品隱藏在某一允許進出境物件的部位之中,隨該物件一起進出境。實踐中,象牙、虎皮等珍貴動物制品一般藏匿于行李箱夾層中,〔48〕如許榮國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參見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 04 刑初 43 號刑事判決書;姜院華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山東省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威刑二初字第 3 號刑事判決書等。而體內藏匿則更多發生在毒品走私等案件中。〔49〕如李永能、趙慶龍走私毒品案,云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云 04 刑初 46 號刑事判決書;谷某走私毒品案,云南省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2017)云 29 刑初 116 號刑事判決書等。此時,需要根據其行為停止的節點判斷法益受侵害程度。如果行為人已經入境,在海關監管區接受檢驗時被查獲,那么其行為就已經對刑法設立走私罪保護的法益產生了緊迫危險。在此意義上,上述許榮國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姜院華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的未遂認定有待商榷,而其他大部分此類案件的既遂認定值得肯定。同樣地,在段某某走私毒品案中〔50〕參見云南省普洱市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6)云 0827 刑初 12 號刑事判決書。,被告人段某某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到緬甸國邦康收取錢款,后在當地某男子處購買了 3 包毒品卡苦(共計 38 克)準備帶到中國孟連縣。當晚 20 時許,被告人段某某將買來的 2 包毒品卡苦藏匿于自己衣物內,卻在入境前被邊檢執勤民警查獲。雖然段某某并未實際將毒品帶入我國境內,但法院認定段某某走私毒品既遂。
當行為人采取隱瞞貨品真實性〔51〕實踐中主要以偽報貨品品類、數量、價格、規格等為主要形式。例如,在趙某甲、陳某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中,陳某制作了虛假的合同、發票、質檢單等報關材料,通過唐山市豐南區華盛物資經銷處申報,將 40 噸硅鐵申報為硅塊。參見河北省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唐刑初字第 73 號刑事判決書。而向海關作虛假申報時,仍要將判斷的重心放在虛假申報行為本身,而非所謂的“偷逃應繳稅款數額”上。這是因為,走私行為人自入境后,會分別經歷入境、海關申報、接受檢查、征稅和放行等多個環節。在行為人向海關申報以前,其始終占據主動,既可以選擇申報,也可以選擇不申報;可以選擇真實申報,也可以做虛假申報。而一旦行為人申報完畢,在后面的接受檢查、征稅和放行三個環節中,行為人缺乏任何主導力,其不可能左右海關是否查驗到走私物、是否對其征稅和放行。但行為人是否真實申報,則完全由其自己決定。所以,在偽報類走私中,我們應當僅考察行為人的申報行為及其真實性。當行為人完成虛假申報時,就已對外貿監管制度和海關監管秩序實施了實際侵害,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這也是 2014 年《解釋》 第23 條第2 項的法理依據。相反,如果行為人在數批走私物中,僅對部分批次貨品進行了虛假申報,部分貨品真實申報或未申報的,那么對未申報的貨品則應認定為未遂。例如,在王某某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中〔52〕參見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閩 02 刑初 31 號刑事判決書。,王某某與王志強、洪清固商議,將一批化妝品、電腦配件、紅參等偽裝成王某某正常申報進口的塑料顆粒走私入境。在走私物入境后還未來得及申報時,洪清固因涉嫌其他走私行為被抓獲,故而王某某未對該批走私物進行申報,后法院認定為走私未遂。
而當行為人采取郵寄等形式進行走私時,走私行為包括“寄”和“收”兩個環節,且“寄”和“收”之間一般存在較長的時間間隔。例如,“刷單”是最常見的跨境電商郵寄走私形式,行為人通過搭建虛假跨境電商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購買或獲取網絡用戶的身份信息,以此為基礎制作虛假訂單,生成虛假快遞單和支付單,進而偽裝成其他物品或享受稅收優惠的物品進行郵寄。〔53〕參見馮曉鵬、馬聰:《跨境電商走私犯罪法律分析及其合規不起訴的實現進路》,載《法治日報》2021 年 7 月 14 日,第9 版。此時,不能簡單地認為行為人(或域外賣家)寄出走私物時犯罪行為就已結束,而至少應當以走私物進(出)國境時為標準。當走私物剛被寄出時,其雖然對我國的外貿監管制度產生了威脅,但因為運輸的長期性,這種威脅并不緊迫。郵寄物在運輸途中,行為人仍可以修改地址或申請退回,即存在犯罪停止的可能。因此,在郵寄的走私物尚未進出國境即被查獲的,宜認定為走私未遂。只有當走私物已經進入我國境內(監管現場)的,應認定為既遂。因此,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關于對海關監管現場查獲的走私犯罪案件認定既遂、未遂問題的函》中提到,“行為人采取在境內郵寄貨物、物品方式進行走私的,只要行為人在郵政部門辦理完畢郵寄手續的”,均應認定為走私既遂,筆者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在前文蔡開走私毒品案中,被告人蔡開在加拿大某網站聯系賣家購買了 400 克大麻,賣家將大麻藏匿在魚油膠囊瓶中通過快遞的方式郵寄至蔡開提供的國內收貨地址。該包裹由加拿大快遞門店攬收,經加拿大多倫多機場空運至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入境,最后發往湖南長沙,并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到達蔡開所在小區的菜鳥驛站中。后蔡開妻子劉某在取件時被公安抓獲,當地法院認定蔡開系犯罪未遂。根據法益侵害程度論,筆者認為蔡開應認定為走私毒品既遂。
(二)繞關走私
所謂繞關走私,即未經國務院或其授權機關批準,從未設立海關的地點或者故意不經海關而運輸、攜帶國家限制、禁止進出境的貨物、物品,以及應當依法繳納稅款的貨物、物品進出境的行為。在通關走私中,行為人入境后就像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其必定要經歷申報、接受檢查、征稅(如有)、放行等環節。如前所述,在這條“流水線”后端,行為人缺乏自主選擇權,所以對行為停止的節點需要仔細辨認。但在繞關走私中,行為人入境的地點、時間和方式均有較大自主選擇權。當走私行為著手后,只要行為人還未攜帶走私物進出國邊境,就不可直接斷定行為人“馬上就要進出國邊境”,進而預判性地認為法益已經遭受到緊迫的危險。所以,在繞關走私中,當行為人尚未進出國邊境〔54〕也有觀點認為應當以是否進出“關境”作為繞關走私既未遂的標準,即只要進入(離開)關境,或者貨物、物品脫離海關的監管范圍,被查獲的,即為既遂。筆者認為,進入(離開)關境、接受海關查驗,本質上即屬于通關。且實踐中大部分繞關走私均為偷偷從人跡稀少的國境線進入(離開),故而“國邊境說” 較“關境說”更為合理。時即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未遂。
以國境為例,如果攜帶走私物的行為人尚未出(入)我國陸地邊界即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未遂。例如,在李明相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一案中〔55〕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人民法院(2019)桂 1481 刑初 142 號刑事判決書。,李明相安排馬海月(另案處理)等面包車司機去低價收購豬腳等凍品準備走私至境外出售,自己駕駛貨車到憑祥市公路局養護站旁邊的一個停車場內等待過駁。2018 年 10 月 31 日晚,所有凍品被過駁至李明相貨車內。當李明相駕駛貨車準備駛離時,被公安機關依法查獲,后法院認定李明相屬犯罪未遂。
而在以海運為手段的繞關走私中,則出現了水路邊界的內海說、領海說、毗連區說、專屬經濟區等不同觀點。筆者主張應當以進出領海為既遂的標準。這是因為,在領海內,沿海國不僅享有主權管轄,還有權行使司法管轄。至于領海的范圍,根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每一個國家有權確定其領海的寬度,直至從按照本公約確定的基線量起不超過 12 海里的界限為止。” 我國也應當以 12 海里為基準。當攜帶走私物的行為人駕駛船舶駛入(出)我國領海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而對于犯罪未遂,則不應將標準放得過寬,在專屬經濟區(176 海里)甚至公海行駛時,不能簡單推定我國海關監管秩序等法益已經受到威脅,只有當船舶至少駛入我國毗連區(24 海里)時才存在未遂的空間。這是因為,雖然毗連區沒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但沿海國可在毗連區行使一定的管制權,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的“沿海國在毗連區行使下列管制:防止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法律和規章;懲治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定的行為。”〔56〕參見聯合國官網: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UNCLOS-1982.shtml#2,2021 年 7 月 7 日訪問。
有觀點認為,在繞關走私中還存在空運繞關的形式。其以嚴光仁走私普通貨物案為例〔57〕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滬 03 刑初 31 號刑事判決書。,認為這就是典型的空運繞關。〔58〕參見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公眾號:《如何認定繞關走私犯罪從犯》,https://mp.weixin.qq.com/s/ehTCZ1RD-JRU4mtZXZpRuQ,2021年 6 月 7 日訪問。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6 月,被告人嚴光仁多次從日本國內商店或日本免稅店購買香煙后,乘坐飛機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在該機場的日上免稅店購買香煙,然后走無申報通道攜帶上述香煙闖關入境,以及雇傭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術公司駕駛員被告人周某、嚴某使用機場內部工作車輛將從日本免稅店購買的香煙以“繞關”方式帶出海關監管區,從而偷逃應繳稅款。筆者認為,嚴光仁的行為并非空運繞關,其仍屬于通關走私的范疇。之所以將其理解為繞關,是因為對“關”即海關監管區的范圍作了過于狹義的理解。根據《海關法》第100 條的規定,海關監管區即“設立海關的港口、車站、機場、國界孔道、國際郵件互換局(交換站)和其他有海關監管業務的場所。”其包含港口、車站、機場的大片范圍,而非單單的檢查通道。同時,即便走所謂的無申報通道入關,其最后還是要接受海關檢查,與通關走私無異。故此類行為仍屬于常規的通關走私。此時被海關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解釋》將“海關監管區”擴大至“海關監管現場”,〔59〕《海關法》第六條規定,海關在海關監管區、海關附近沿海沿邊規定地區以及海關監管區和海關附近沿海沿邊規定地區以外的其他地區均可以行使相關調查權力。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但是,“海關監管現場”亦不可作過于寬泛的理解。有學者認為,對于監管現場要針對個案作動態的理解,所有海關行使監管權力的現場均應視為“海關監管現場”。不論是通關走私還是繞關走私,只要海關人員現場查獲,統一按犯罪既遂處理,可以避免標準多元所可能導致的理解和執行上的混亂。〔60〕參見南英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2-353 頁。筆者認為,所謂“繞關”繞的就是海關監管,不能因為查獲現場有海關人員就簡單將其理解為“海關監管現場”,進而依據2014 年《解釋》第23 條第1 項認定為走私既遂。否則的話,會直接造成該條第1 項同第2 項、第3 項的矛盾,導致走私未遂幾乎沒有了認定的空間。且無論是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還是寬嚴相濟等刑事政策,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都不合適。因此,在具體個案中認定既未遂仍需要遵循法益侵害程度的判斷標準。
(三)間接走私
間接走私,是指行為人并不直接實施走私行為,而是向其他走私人收購走私物。我國《刑法》第155 條規定了兩類間接走私行為。(1)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國家禁止進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走私進口的其他貨物、物品,數額較大的;(2)在內海、領海、界河、界湖運輸、收購、販賣國家禁止進出口物品的,或者運輸、收購、販賣國家限制進出口貨物、物品,數額較大,沒有合法證明的。
在間接走私中,行為人從頭到尾沒有實施過跨越國邊境的行為,其行為從提出購買意愿到收到走私物期間,對法益的侵害始終處于一種較為模糊和游離的狀態。具體言之,當行為人與其他走私人達成購買的意思表示或相應協議的時候,間接走私行為就已經著手,這個相對來說容易認定。但隨后,行為人可能出于諸多原因而收購失敗,如其他走私人被抓獲、走私物運輸過慢、走私物價格上漲等。其中,有部分原因屬于主觀原因,行為人可以選擇繼續收購也可以選擇放棄收購,而此時放棄的,應當認定為犯罪中止。還有部分原因屬于客觀原因如具體走私人被抓,此時,行為人已經不具有繼續收購走私物的可能性,不可能再對法益產生實害或緊迫的危險,故應認定為走私未遂。例如,在李魁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案中〔61〕參見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陜刑終第 192 號刑事裁定書。,李魁系白某甲等人走私犀牛角的收購者,在白某甲走私犀牛角入境后,李魁親自前往西安機場附近等待接貨購買,但因白某甲被現場查獲而未購買成功,法院認為李魁屬犯罪未遂。
在間接走私中,需要注意間接走私者與教唆犯和普通共犯的區別。如果其他走私人本無走私意圖,但行為人不停勸說、授意和利誘,讓他人產生走私犯意,并承諾走私完成后進行高價收購。此時行為人就已脫離了間接走私的范疇,而屬于教唆犯,其既未遂形態和被教唆之人相同。如被教唆者走私入境被海關現場查獲,即便行為人沒有真正“收購”到走私物,同樣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
另外,間接走私還應區別于走私共犯。《刑法》第156 條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其中,關于“通謀”,2002 年《意見》認為,通謀是指犯罪行為人之間事先或者事中形成的共同的走私故意,包括:(1)對明知他人從事走私活動而同意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海關單證,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2)多次為同一走私犯罪分子的走私行為提供前項幫助的。如經查,行為人并非真正收購,而只是為走私人提供貸款或資金便利的,則應以走私共犯論處。此時,可以秉持共同犯罪中一人既遂全部既遂的原則,如其他走私人被海關現場查獲的,作為共犯的行為人同樣應當認定為既遂。〔62〕例如,在曹中斌走私武器、彈藥案中,2014 年 6 月,曹中斌與網名叫“皇后姐姐”的人(另案處理)通過網絡認識,二人約定由曹中斌幫“皇后姐姐” 代收代發氣槍槍管及其他氣槍零部件并代收貨款,“皇后姐姐”按照發一支槍管 500 元,發一整套槍支配件 800 元的標準支付傭金給曹中斌。后“皇后姐姐”從我國臺灣地區走私槍支配件入境時被查獲,當地法院認定曹中斌同樣屬于犯罪既遂。參見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皖 01 刑初 44 號刑事判決書。
(四)后續走私
后續走私又稱變相走私,主要指違反《海關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未經海關許可并且未補繳稅款,擅自將海關監管的保稅貨物、特定減免稅貨物、物品在境內銷售的行為。〔63〕參見趙秉志:《海峽兩岸刑法各論比較研究(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6 頁。《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的兩類行為屬于后續走私。(1)未經海關許可并且未補繳應繳稅額,擅自將批準進口的來料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設備等保稅貨物,在境內銷售牟利的;(2)未經海關許可并且未補繳應繳稅額,擅自將特定減稅、免稅進口的貨物、物品,在境內銷售牟利的。從司法實踐看,后續走私暫時未出現未遂認定的案例,但既遂認定并不鮮見。〔64〕如孫某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參見廣東省汕頭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 05 刑初 26 號刑事判決書。這是因為,后續走私在行為模式上與其他走私類型體現出較大的差異。
后續走私主要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某些在我國境內享有保稅貨物經營權或特定減免稅待遇的企業需要申領或進口相應的保稅、減免稅貨物;其次,這些企業擅自銷售貨物或違規申請核銷(假核銷或假轉廠)。以來料加工為例,行為人先要經歷備案、申領手冊等環節才能拿到買賣指標,憑借指標進口相應的原材料貨物。但是,保稅加工貨物進境是為了加工出口產品,原則上出口前不可進入國內市場。而行為人在獲取來料后卻與他人簽訂內銷合同并實施了銷售行為。可以發現,后續走私中的犯罪行為主要發生在后一環節,即犯罪行為并不發生在進出境現場,而發生在對特定保稅、減免稅貨物的后續監管環節。
在前一環節即申領、進口相應保稅、減免稅貨物時,不產生任何法益侵害(危險)。這是因為,行為人本就具備保稅貨物經營權或減免稅待遇,他們是通過合法的申領程序才獲得的進口指標,因此其進口保稅、減免稅貨品的行為合法合規。然而,保稅加工等只具有臨時進口性質,其目的是為了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這些保稅加工貨品主要為了其他跨國企業進一步深加工使用,有著特殊的工業加工需求和貿易需要,在我國的境內加工只是產品線上的某一環節,貨品本身在國際分工的背景下會再一次進入到國際貿易程序之中。因此,在貨品決定最終去向之前,我國海關會采取暫停對其征收關稅的措施。此時,如果行為人加工完畢后正常申請轉廠、出口和核銷,同樣不會產生法益侵害,不可能構成犯罪。但是,一旦行為人擅自在境內銷售牟利,或采取假轉廠、假核銷的形式平衡《加工貿易登記手冊》的,〔65〕所有從事對外加工貿易的企業,按照加工合同規定的內容,保稅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時,都會在海關處領取《加工貿易登記手冊》作為原始登記憑證,這是海關監管加工貿易企業的依據。加工合同執行完畢后,不論剩余料件是轉入下一本手冊,還是料件全部進口,合同執行完畢,《登記手冊》必須進出平衡。則會對法益產生現實危險。基于前期行為的可控性,若銷售行為或核銷行為未實施完畢即被查處,則構成走私犯罪的未遂;如銷售行為或核銷行為已經實施完畢,乃犯罪既遂。
四、結 語
近年來,走私案件仍呈現不斷增多的趨勢,盡管 2002 年和 2014 年我國相繼出臺具體的規范性文件,但“負面清單”式的規定還是難以滿足實踐需要,科學裁判尤其是既未遂的認定問題始終是個難點。究其原因,刑法理論的指導作用不夠是值得反省的。我們不能只是在構成要件的層面判斷走私犯罪是否成立,而是要基于對走私犯罪的常見形態的考察,分析走私行為侵害法益的程度,以判斷走私犯罪的實施是否充分和完成。事實上,根據本文對法益侵害程度的判斷標準,約 70%左右的結論與案例判決書的結論相同,也有部分判決結果值得商榷。在此意義上,期待今后司法實踐能夠在走私犯罪既未遂的認定上更加科學和精準,也期待本文的觀點能對其他經濟類犯罪既未遂形態的研究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