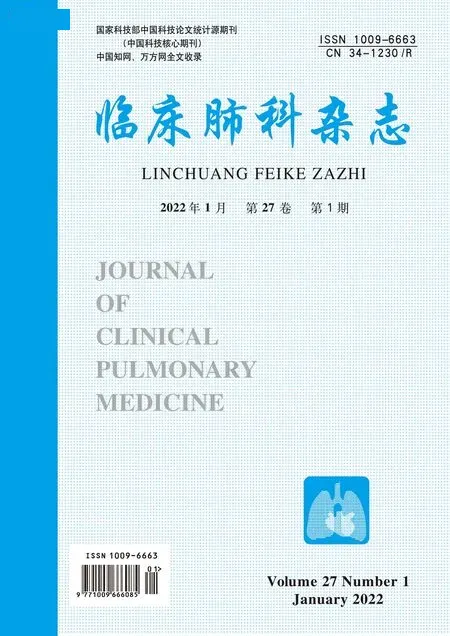兒童支氣管哮喘抗炎治療的新展望—ω-3長鏈多不飽和脂肪酸
郭子瑞 王敏
如今,由于全球支氣管哮喘(以下簡稱哮喘)防治工作的積極開展,部分地區哮喘患病率逐漸趨于平穩[1],但在一些欠發達以及空氣質量較差地區的發病率仍相對較高[2],哮喘患者尤其是兒童患者的生活質量及身心健康受到較大影響[3]。哮喘長期治療中,吸入糖皮質激素為一線用藥[4-5],部分患者對激素不敏感[6],還存在擔心副作用,治療依從性差等問題[7]。為此研究者們致力于找到潛在非藥物治療的方式,輔助甚至替代哮喘傳統治療,提高哮喘患者尤其是兒童患者治療的依從性。ω-3長鏈多不飽和脂肪酸(ω-3 long-chain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ω-3PUFA)在促進健康和降低疾病風險方面發揮多種益處[8-10]。近年來,研究者們逐步證實ω-3PUFA在減輕哮喘炎癥,促進炎癥消退方面發揮一定作用[11-12],這引起了研究者們對ω-3PUFA的極大興趣,并找到了ω-3PUFA的新來源[13-14]。現就國內外ω-3PUFA在哮喘中發揮的抗炎作用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ω-3PUFA的合成及來源
ω-3PUFA是ω-3脂肪酸中的甲基末端第三個和第四個碳原子之間具有兩個或多個雙鍵的長鏈多不飽和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均為ω-3PUFA的主要形式[15]。人體能夠以堅果,植物油等膳食中的α-亞麻酸(alpha-linolenic acid,ALA)為前體,在Δ-5去飽和酶、Δ-6去飽和酶等作用下合成ω-3PUFA[16],另一來源主要是鮭魚、金槍魚和沙丁魚等這樣富含脂肪的海洋油性魚類[15],以及其制成的補充制劑[16]。然而ALA轉化為EPA和DHA十分有限[17],且不同種類的魚含有不同數量的ω-3PUFA,某些類型的魚類可能受到環境的污染,含有較高的甲基汞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18-19]。為彌補傳統來源的不足,研究者們尋找到新的替代來源——外源性合成的二十碳五烯酸單甘酯(Eicosapentaenoic acid monoglyceride,MAG-ω3)以及可合成大量ω-3PUFA的轉基因淡水鯉魚[13-14],MAG-ω3不需要脂肪酶,胰腺脂肪酶的作用,可直接被人體吸收而提高生物利用率[20]。同時轉基因淡水鯉魚可產生大量EPA和DHA,其體內的ω-3PUFA總量比非轉基因鯉魚提高了78%[13],這一發現有望讓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從日常食用的淡水魚中就獲取更多ω-3PUFA。
哮喘的炎癥過程
Th1和Th2細胞亞群比例和功能失衡是哮喘的主要發病機制,主要表現為Th2細胞占優勢[21],Th17細胞也參與了哮喘的炎癥過程[22]。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巨噬細胞(Macrophages,M?)等免疫細胞,以及其介導的各種細胞因子的表達,可調節Th0細胞分化方向[23]。患者受到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等過敏原刺激時,DC等抗原呈遞細胞將過敏原呈遞給Th0細胞,促使Th0細胞分化為Th2細胞,其衍生的細胞因子IL-4、IL-5、IL-17等可以誘導嗜酸性粒細胞(Eosinophils,EOS)活化和局部浸潤,并刺激B細胞的激活,產生大量的特異性IgE[24],IgE黏附于氣道黏膜下的肥大細胞(Mast cells,MC)或血中的EOS上,當機體再次接觸過敏原時,IgE與MC等表面結合可導致高親和力IgE受體(FcεRI)交聯[25],引起細胞膜磷脂代謝發生變化,細胞脫顆粒產生組胺、白三烯(Leukotriene,LTs),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s)等炎性介質,這些炎性介質作用于各種效應細胞,引起支氣管收縮,黏液分泌增多和氣道纖毛破壞等,此為速發型哮喘反應。IL-4,IL-5和IL-13等細胞因子也參與遲發性哮喘反應,介導氣道慢性炎癥,損傷氣道上皮,反復異常的修復可導致氣道重塑,最終引起可逆性氣流受限[24, 26]。ω-3PUFA正是在上述炎癥過程中發揮其抗炎作用的。
ω-3PUFA在BA中的主要抗炎作用機制(如表1)
一、ω-3PUFA與免疫細胞
DC細胞被變應原激活后,上調共刺激分子(Co-stimulatory molecules,CDs)如CD80、趨化因子以及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表達,具有Th2細胞趨化效應[27]。Teague H等證明,ω-3PUFA可顯著下調DC誘導的CD80、Th2細胞趨化因子CCL17及 TNF-α的表達,減少Th2細胞極化[28]。Uchi S H等則表明,ω-3PUFA喂養小鼠的DC可減少Th17細胞及其細胞因子IL-17的產生[29],而Th17細胞以及IL-17與哮喘的發生及嚴重程度相關[30-32]。細胞因子IL-23通過Th17細胞的增殖表現出促炎特性,而ω-3PUFA產生的衍生物如促溶解素(resolvins,RV)具有減少DC分泌的IL-23等炎性因子的能力[33]。此外ω-3PUFA還可增加DC分泌的具有抗炎作用的細胞因子IL-10[34]。
MC脫粒產生組胺、LTs、PGs等促炎介質,在啟動和維持炎癥中起著關鍵作用[35],其分泌的組胺、LTs、PGs等炎癥介質主要受細胞內活性氧(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信號通路等調節的影響[36-37],ω-3PUFA可呈劑量依賴性的減少MC細胞內ROS的活化,并顯著降低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的激活[38],調節炎癥介質的產生。Wang X等發現在產生內源性ω-3PUFA的轉基因小鼠體內,MC產生的TNF-α和趨化因子配體顯著減少,而外源性補充ω-3PUFA也可以減少MC脫顆粒[39],此作用可能是通過破壞FcεRI脂質筏分配,并隨后抑制小鼠體內MC的FcεRI信號傳導來抑制MC的功能,并與MC表達的G蛋白偶聯受體(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GPR120)的連接有關[40]。Park 等人還發現ω-3PUFA可呈劑量依賴性降低MC產生的IL-4,IL-13等細胞因子及其mRNA的表達[41]。
M?存在兩種表型,分別為表達高水平炎癥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M1型,表達較低水平促炎介質和高水平抗炎介質如IL-10的M2型,M2型在炎癥末期可促進炎癥的消退[42]。Song等發現ω-3PUFA發揮抗炎作用的效應可能與M?遷移能力降低,以及M?從促炎的M1表型轉變為抗炎的M2表型有關[43],Montserrat-de等也同樣發現ω-3PUFA可增強單核細胞分化為M2型的能力[44]。Danyelle等人表明,M?相關炎癥因子(IL-6、TNF-α)及趨化因子(CCL-2、CCL-7等)mRNA的表達在ω-3PUFA的作用下顯著下調,M1極化標志物如iNOS等也明顯降低,這一作用可能與ω-3PUFA減輕了TNF-α信號傳導過程有關[38]。Tian等人也發現LPS刺激的小鼠M?中,ω-3PUFA可顯著下調M?中IL-6等促炎因子的mRNA表達[45]。

表1 ω-3PUFA的主要抗炎作用途徑
二、ω-3PUFA調節細胞膜脂質代謝
上述提到,MC及EOS細胞膜磷脂代謝發生變化后,導致細胞脫顆粒產生組胺、LTs,PGs等炎性介質[26],產生這些介質的主要為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RA)[15]。變應原刺激后,磷脂酶A2催化ARA從細胞膜上游離出來,代謝衍生為LTB4,PGE2等促炎介質[46],ω-6/ω-3PUFA的比例升高與促炎因子升高平行[47]。ω-3PUFA在細胞膜上的比例增高時,與ARA競爭性的結合磷脂酶A2,迅速從細胞膜上分離出來,減少游離ARA的濃度,減少促炎介質的產生[48],即使ω-3PUFA也可產生LTB5,PGE3等介質,但其炎癥趨化性顯著低于LTB4,且LTB5有助于增加M2型M?表面CD14和CD163等標志物,增加抗炎型M?的極化[49]。
三、ω-3PUFA衍生的特殊促分界介質(Special demarcation media,SPMs)的抗炎作用
隨著氣道炎癥的發展,組織炎癥逐漸進入緩解修復期,組織中的ω-3PUFA可快速轉化為促成炎癥修復過程的內源性脂質——SPMs,如DHA來源的RvDs、EPA來源的RvEs、保護蛋白(Protective protein,PD)、Maresins蛋白以及脂氧素A4(Lipoxins,LXA4)等[50]。SPMs的作用包括抑制粒細胞的募集,減少Th2及Th17細胞產生的TNF-α等炎性細胞因子[51],在恢復肺組織穩態,減少肺損傷以及炎性細胞浸潤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52]。例如EPA衍生的RvE在小鼠哮喘模型中對嗜酸性氣道炎癥具有抗炎和促分解作用,減少局部組織中如IL-4、以及IL-13等mRNA的表達,同時顯著下調DC細胞和M?中IL-17的mRNA表達[33],Maresins蛋白可在急性炎癥早期選擇性調節與肺部炎癥相關的促炎介質如TNF-α等,恢復肺穩態,減少炎性細胞浸潤[52]。哮喘的癥狀加重以及不受控制可能與SPMs的表達水平較低有關,嚴重哮喘患者的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檢測到的SPMs水平顯著低于正常人和輕癥哮喘患者中的水平[53]。
四、ω-3PUFA與受體的識別及炎癥信號轉導
GPR120是唯一高表達于促炎性M?的ω-3PUFA受體,也稱為脂肪酸受體(Fatty acid receptor,FFRA)[54],為ω-3PUFA發揮作用的靶點,ω-3PUFA將FFAR激活后可將M?極化為具有抗炎作用的M2型,減少IL-6、TNF-α等M1型炎癥因子的表達,并通過FFAR誘導支氣管上皮細胞的增殖,促進氣道損傷的快速修復[55],MC上表達的GPR120還介導了ω-3PUFA減少MC脫顆粒的過程[39]。
NFκB參與炎癥相關蛋白編碼基因上調,炎癥信號激活非活性的NFκB后,游離出NFκB二聚體誘導炎性基因的表達[56],而ω-3PUFA可顯著減少炎性因子及其轉錄水平,減少對NFκB通路的激活,抑制細胞內炎癥因子的轉錄[57]。ω-3PUFA影響NFκB活化的機制,還與抗炎轉錄因子——過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體-γ(Peroxidas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相關,在ω-3PUFA的作用下PPAR-γ顯著上調[57],物理上干擾了NFκB向細胞核的移位,抑制其炎癥信號的轉導[57]。LPS等刺激與細胞上Toll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TLR4)的結合介導了NFκB的激活,并可通過TLR4信號誘導Th2細胞的優勢應答[58],Wang 等人發現ω-3PUFA可下調細胞膜上TLR4的表達,減弱TLR4介導的NFκB炎癥信號轉導等作用,從而降低哮喘炎癥反應[58]。Sun等人研究發現即使是ω-3PUFA的衍生物如RvD1等同樣具有抑制NFκB的激活,減少炎癥信號的轉導的作用[59]。
ω-3PUFA對哮喘的防治作用
一、 ω-3PUFA對哮喘的預防
攝入富含ω-3PUFA的魚油或補充劑可能與哮喘發病呈負相關[60-61],Muley 等表明ω-3PUFA降低哮喘的發病這一潛在有益影響可能在兒童中更為顯著,可能是因為兒童對ω-3PUFA更敏感[62]。我國兒童哮喘的發病年齡多集中在3~5歲以下[63],因此早期預防是極為重要的,Foiles 等發現,母親有過敏性疾病的嬰兒給予含DHA的配方奶粉喂養,可使其出生后前4年哮喘的發生率降低74%(P=0.02)[64],Best等研究表明,不區分孕母是否有過敏性疾病的情況下,孕期開始補充富含ω-3PUFA的魚油,使子代對屋塵螨的敏感率整體下降7%(P=0.049)[65],子代持續性喘息或哮喘的風險降低了6.8%(P=0.035)[66]。
二、ω-3PUFA改善氣道反應及炎癥
Brigham等發現ω-3PUFA攝入量增加可改善哮喘的嚴重程度和對PM2.5等空氣污染的反應(P<0.01)[67],Williams等還發現ω-3PUFA可減少運動誘發的支氣管收縮,6.2g/d和3.1g/d的ω-3PUFA分別使呼出FeNO基線分數降低了24%(P=0.020)和31%(P=0.018)[68]。另一研究發現輕度哮喘兒童連續6個月每周食用2次150g富含ω-3PUFA的魚油,FeNO較基線值降低了18.5%(P<0.001)[69]。Farjadian表明,人體服用含ω-3PUFA的魚油后,血清TNF-α、IL-17等炎性細胞因子水平下降了15%~20%(P<0.05)[70]。
三、ω-3PUFA改善哮喘患者肺功能、控制情況及減少激素使用劑量
Farjadian等發現,哮喘患者連續3個月服用含180mgEPA和120mgDHA的魚油后,89%患者肺功能FEV1/FVC變化高于臨界值(P=0.044)[70]。Barros R等人的研究中,哮喘未控制組患者的ω-6/ω-3PUFA比控制組高37%,而攝入0.73~0.94g/d及以上的ω-3PUFA與未控制哮喘的發生成負相關(OR:0.18,95%CI:0.05)[71]。Stoodley等發現ω-3PUFA指數[紅細胞膜EPA(mg)+紅細胞膜DHA(mg))/總紅細胞脂肪酸(mg))×100]大于8%時,哮喘患者糖皮質激素最大使用劑量下降了50%(P=0.019)[72]。
然而,關于ω-3PUFA的作用還存在一些爭議,一些研究并未發現ω-3PUFA在哮喘患者中有明顯的益處[73-74],Hamazaki 等甚至認為魚油和ω-3PUFA的攝入與某些過敏性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19],這可能與ω-3PUFA的來源、劑量、攝入時間、吸收和利用率,去飽和酶基因的多態性以及脂肪酸受體的敏感性等因素相關[75-76]。研究者們發現的ω-3PUFA新型來源可能有望彌補上述不足。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ω-3PUFA可通過多種途徑在哮喘的炎癥過程中發揮抗炎作用,但這些研究尚處在實驗階段,其在哮喘患者中的治療作用還有些爭議,并且ω-3PUFA新的來源是否能直接用于人體,以及其能夠在哮喘疾病過程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仍是我們需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但這可能是一種潛在的治療策略,可能作為緩解哮喘氣道炎癥的輔助甚至替代藥物,豐富哮喘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