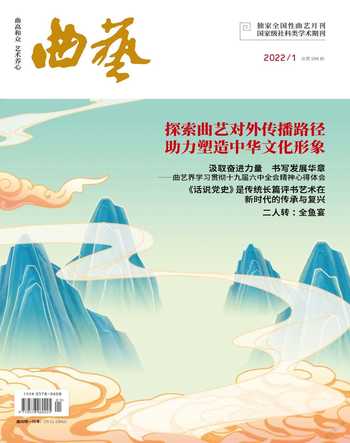《話說黨史》是傳統長篇評書藝術在新時代的傳承與復興
楊魯平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助推黨史學習教育活動的深入開展,田連元先生創作了現代長篇章回體評書《話說黨史》。該節目已經錄制40集,在“學習強國”網絡平臺和中央廣播電臺正式播出。
《話說黨史》根據黨史資料中的大事記,甄選出100件史實,編撰成百集系列故事,通過廣電傳媒平臺,變換說、演、評、博不同的藝術手法,將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傳播于社會大眾。這個以藝術化講述中國共產黨黨史開先河的創舉,無論從政治的高度,歷史的深度,還是從藝術的審美角度審視,都有其特殊的現實、深遠意義。《話說黨史》是代表我們曲藝界同人向建黨100周年的獻禮,同時,它是評書藝術與政治歷史融合創編的首篇之作,將對我們新時代的曲藝作品創作,有直接的引領、指導作用,為評書、評話、故事及其他曲種打造主旋律題材新的經典,推出新的扛鼎之作,提供了一部學習借鑒的教科書式的范本。
歷來,涉及重大政治歷史題材的曲藝作品創作,業內有些人是有畏難情緒的。有人認為:曲藝,是接地氣的民間傳統藝術形式,生存于普通百姓之中,專注于表現蕓蕓眾生的生活百態。家長里短,嬉笑怒罵,針砭時弊,以小見大是其典型的藝術特征。黨史,則承載我們黨的滄桑歲月,見證我們黨苦難輝煌的發展歷程,涉及多方面重要歷史人物及重大歷史事件,史料真實、嚴謹不茍,具有權威定論性,禁忌隨意編造發揮。所以,在舞臺上單人表演為主,形式單一的曲藝,擬創作黨史如此厚重的作品,從構架、容量到深度都難以駕馭完成。結論是:民間藝術小、快、靈,重大題材繞道行,更為穩妥。以至多年來,沒有任何曲藝形式能將黨史完整、系統地創演成作品,呈現于舞臺。直到2019年,田連元先生首先成為林子外面的那棵樹,勇于起步探索,以傳統評書章回體形式,選擇新時代的視角,創作出《話說黨史》。
以辯證的觀點審視,《話說黨史》的問世,絕非偶然。它是作者個人經歷、思想、藝術從量變到質變的行為過程。田連元出生于評書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苦練語言、身段基本功。年少,正式拜師學藝傳統書目《隋唐演義》《楊家將》《水滸傳》等,在三尺書臺上打下了評書表演扎實的功底。成年后,被招入國家體制文藝團體,專業從事評書的創作表演。在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入了黨,被任命為業務副團長。他堅持認真學習、踐行黨的文藝理論、方針、政策,在演出業務中自覺規范自己的言行。他緊跟時代發展需要,敏銳地關注社會政治導向,體察百姓文化需求,在繼承傳統書目基礎之上,配合黨在不同時期的宣傳文化工作,不斷創作革命歷史題材,謳歌時代英雄、模范人物的新書,如《虎穴鋤奸》《追車回電》《歐陽海之歌》《梁上君子》等。進入新世紀,在全國道德模范基層巡演近16年的創作演出過程中,他每部作品如《英雄無悔》《英雄三兄弟》《好漢金漢》《明星采訪記》等的創作思路、結構方式迥然各異,不斷在藝術上挑戰自己,突破創新。正因為田連元先生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對黨和人民有一顆赤子之心,內心具備強大的文化自信心和深厚的藝術功力,所以他創作評書《話說黨史》,是偶然產生于必然之中。
田連元選定以傳統章回體評書形式詮釋黨史,獨具匠心。傳統章回體評書形式,是由宋、元朝代講史的“話本”發展而來,到明代中期趨于成熟,問世了四大通俗奇書《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金瓶梅》。明末至清初,章回體例正式形成,引發了文學雙高峰經典《儒林外史》《紅樓夢》。章回體長篇大書的特點是將全書分為若干章節,稱之為“回”。每回開端以工整的偶句或單句作文字回目,概括本回故事內容一目了然,繼后敘述一個較完整的故事。故事段落整齊,敘事清楚,首尾相接,符合大眾欣賞習慣,也便于讀者、聽眾間歇欣賞。《話說黨史》選擇章回體形式,是對古代藝人講史“話本”的歷史傳承,在表現形式上突出了華夏傳統文化特色,這是對祖先文化的敬畏和尊重。
《話說黨史》與傳統評書講史比較,有諸多不同點。傳統評書講史是演義,故為三分實,七分虛。故事歷史背景是實,整體綱目構架中的故事情節、人物、場景描述則以虛構為主。因為傳統書目是以商業娛樂演出為目的,藝人要在講史“話本”演義中,加入大量宮廷爭斗、兇殺篡位、嬪妃紛爭、閨樓脂粉等獵奇情節,招攬吸引觀眾聽書。
評書《話說黨史》是七分實,三分虛。歷史背景、事件、人物均以真實史料為準繩,因為這些史料是幾代共產黨人追求信仰、主義,舍生忘死挽救民族危亡,建設新的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歷史見證。所以,在原則限制中,作為載體的評書敘述故事,既要保證故事中詮釋的黨史內容真實、不走樣,又要保證故事引人入勝、高質量的藝術化,這對藝術家的政治、藝術綜合素質,思想把控、甄別能力,要求甚高,也與傳統講史“話本”有質的區別。
作為一名有思想的評書表演藝術家,田先生對藝術有著自己嚴肅的審美追求。他選擇黨史素材,總是緊緊圍繞黨內思想路線斗爭激烈交鋒的危難時刻,或是敵我雙方殊死拼殺生死攸關的戰場,在真理與謬誤,堅守與背叛,勝利與失敗,人物情感交織的高潮迭起中構思情節,設置“扣子”(即懸念),沿著故事的脈絡線條,合理地發展到極致,形成強烈的戲劇沖突,扣人心弦。
綜上所述,田先生《話說黨史》審美追求的嚴肅性,集中體現在其中每段故事的情節線,都是精心安排“扣子”的組合編排層層推進,而每一個“扣子”的設置,語言、動作的鋪墊,絕不允許使用與情節發展、人物性格毫無相關的外插花式、插科打諢式、嘩眾取寵式的噱頭取悅觀眾,游離主題,貶低作品的藝術價值。
田連元創作《話說黨史》強調的審美邏輯是“真實即美”。說事、寫人,不以作者的意志為轉移,注重了解還原事件的真實過程,挖掘人物的真情實感。強調生活素材提煉出的藝術的真實再現。他的《話說黨史》沒有純理論化的、宣講式的政治論談,聽來不沉重不晦澀,作品通篇富有輕松友善的人文色彩,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人物性格、矛盾的展開,說書人娓娓道來,引導觀眾被故事情節吸引,在或悲或喜的情緒氛圍中,逐步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對共產黨人的信仰、追求,人格精神的表現,產生內心的自我判斷,悟出作者的寓意、傳遞的思想意識。在這里,沒有概念灌輸,沒有說教宣講,只有自我聆聽,自我感受,自我判斷。
虛構是藝術的本質,是轉變生活真實為藝術真實的重要手段,正因為虛構挖掘的是生活素材的本質,所以具有更高的真實性。田先生在《話說黨史》中,根據真實的史料,充分運用自身的閱歷、想象力、表現力,為聽眾、觀眾營造出藝術想象的空間。
在已經播出的40回中,例如:第一次黨代會召開,突遇法國巡捕搜查,文件險被發現的細節;代表們轉移至嘉興租船打麻將做掩護,繼續開會機智周旋的場景;毛主席秋收起義去安源途中遇敵,臨危不懼,化險為夷的冷靜對話;井岡山反圍剿戰役,朱德、陳毅等紅軍將領指揮若定,指戰員們英勇殺敵的群雕形象;說書人在演播敘述中,刻畫的人物血肉豐滿,生動真實,場景渲染讓人身臨其境,懸念叢生,觀眾在不知不覺中被帶入到說書人規定的場景之中,這就是藝術虛構之魅力。
在主要人物刻畫方面,田先生塑造幾位偉人的語言,采用了各地不同的方言飾音。摹仿方言的同時,并不追求原汁原味,而是傳意不傳真,分寸拿捏、點到為止,這也是業內一句古訓——學者生,是者死。模仿歷史人物像斯而非斯,人物就會有靈魂有神韻,避免表演的刻板程式化。田先生刻畫塑造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等眾多偉人,性格各異,既有胸懷有智慧,又平實而普通,有常人的七情六欲,沒有生硬標榜人物高大上的光環,在觀眾心目中留下了真實可信的形象記憶。其他眾多當事人物出現,均采用普通話音飾,根據情節需要,賦予他們喜怒哀樂的情緒變化,讓眾生相活靈活現、栩栩如生,人物之間形成鮮明對比,不斷推動情節向前發展。
一部長篇評書作品完成文本創作后,根據文學臺本進行演出臺本的二度創作(指排練過程)是極為重要的,要進行口語化調整、文字改動、聲音技巧的設置運用、形體造型編排等。《話說黨史》人物眾多,情節曲折。人物喜怒哀樂的情緒變化,節奏遲急頓挫的處理,說表扣人心弦的懸念,排練起來難度很大,熬精力,耗體力。田先生年近耄耋,心理、體能承受了超負荷的壓力和考驗,這種壓力和考驗,真正體現出田老在二度創作中的嚴謹態度和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
從評書表演的角度賞析,田先生在《話說黨史》中,說、演、評、博的專業技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在演播中,他的表演沒有沿用傳統評書開臉兒、贊賦、撥口兒、現掛等程式化的表演套路,淡化了臺詞的戲劇腔調,語言表達松弛自然,平實、生活化,讓觀眾與演員之間消除了舞臺距離感,就像面對面坐那聽他聊天兒。這種藝術思想的突破到表演風格的轉變,打破了長期形成的思維定式和習慣,以多元素的表演模式展現,揮灑自如不露痕跡。
田先生融合其他姊妹藝術的表演多元素,集中體現在根據不同劇情需要,說表、刻畫人物,借鑒了影視臺詞、形體的表述方式。例如:何長工在長沙飯店里與叛徒周旋,以一盤兒紅油肚絲兒為由,騙過叛徒走出包間兒,回身兒拿筷子別住門鎖脫身,這段通過描述人物行為細節,推動情節向前發展的過程,就有很強的鏡頭感。
又如:故事講述遵義會議召開的經過,對會議背景、會議代表抓重點介紹,“說”與“評”,穿插進行,為“演”做渲染鋪墊。“演”,則突出刻畫毛澤東發言,這個中心人物形象,將遵義會議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確立毛澤東在紅軍、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重要意義,形象藝術地“演”了出來,讓聽眾有如身臨其境,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會議、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銘記在心。
評書表演,“說”“演”固然很重要,而評,則能畫龍點睛,是評書的精神亮點。《話說黨史》書中的點評、論評、引評,觀點準確深刻,趣味高雅健康。
“說”“演”“評”又與“博”緊密相關,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為什么同樣一部書,有人說得引人入勝,有人說得味同嚼蠟?這是說書人“博”的修養決定的。說書,除了先天語言、表演的天賦異稟,后天專業技巧的舞臺實踐,更多的是“功夫在書外”,學習專業之外的知識,豐富自己。正如田先生所言:“博,是指社會知識、歷史知識、文學知識、雜學知識淵博。博覽群書才能信手拈來,出言成趣,長期積累,厚積薄發。”這是一名演員從藝終身修煉之目標。《話說黨史》是典型的人保活的作品(業內行話,“活”即作品),要有深厚的藝術修養,有滿滿的文化自信,才能端得動這塊活。《話說黨史》播出后,受到全國廣大聽眾一致好評,很多單位學習黨史,就聽田連元的《話說黨史》,足見田先生深厚的“博”的藝術造詣,《話說黨史》獲得贊譽非一日之功。
縱觀當前,全國曲藝作品的創作,主旋律、歌頌體的有深度的精品節目少,整體水平有待提高。出現的瓶頸和難題主要集中在處理不好素材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就是如何將這些歷史的、新時代的優秀共產黨員、國家英雄、道德模范的原型人物和事跡,藝術化地表現出來,讓他們光環籠罩的高大上的人物形象,還原為有血有肉、普普通通人的本色,讓他們的境界、思想、言行,都在平淡的生活細節之中折射出來,真實感人地再現于舞臺,這是最重要的關鍵所在。素材的真實是為藝術的真實服務的,宣傳歌頌的最終目的是完美塑造、流芳千古。《話說黨史》,追求的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完美統一,所以,令人可信,征服了觀眾和青年朋友。
田連元先生是從藝人到演員,從演員到藝術家,再從藝術家到藝術大家,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他的藝術理念、藝術才華經歷了由量變到質變的蛻變過程。我以為最根本的,是因為指導思想的成熟自信而改變了行為和形象,評書《話說黨史》標志著“德”“藝”產生了質變和升華。田連元現象值得我們思考和研討,特別是中青年曲藝作者和演員們,都會從田先生的評書創作、表演藝術經歷中獲得啟示和借鑒。我們的曲藝創作表演需要傳承,繼承傳統的藝術精華,我們更需要復興,即發展創新。讓評書藝術在青年朋友們的簇擁下,走向明天。
習近平總書記說,文藝工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田連元先生以習總書記講話為指引,在藝術之路上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學習榜樣會形成群體,群體會凝聚成力量,我們期待中青年演員們學習田連元先生堅定文化自信,敢于接受挑戰,敢于探索創新中的不可知性,在評書藝術的復興之路上,創作出新的精品力作,涌現出新的田連元式的藝術人才。
(作者:中國曲協評書藝委會主任)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