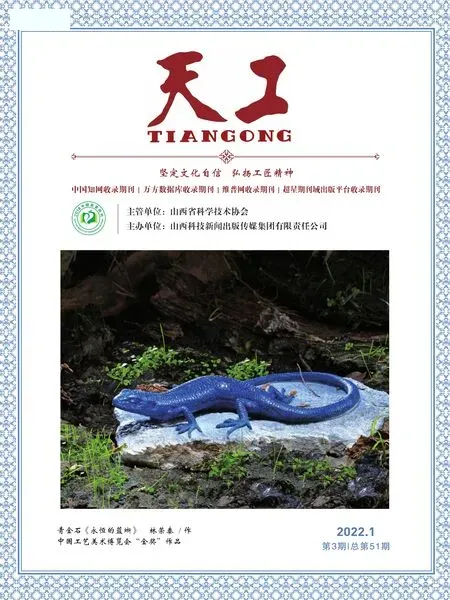淺析當代公共藝術中視覺表現的發展方向
——以弗洛倫泰因·霍夫曼的“大黃鴨”藝術為例
楊子媛 北京語言大學
一、“大黃鴨”視覺符號的產生與發展
公共藝術既是一種開放、公開與公眾密切互動的藝術形式,又是城市文化再傳播和發展的表現。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如果要向大眾傳達抽象的信息,就需要將抽象但具有明確意義的信息內容進行符號化的處理與轉換。就公共藝術層面來說,更多的是以視覺圖像作為表現手法,視覺在如今的信息傳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更是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黃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圖1),這門藝術由擅長在公共空間創作巨大造型物的當代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于2007年發起,“大黃鴨”藝術作為全球巡游創作項目,始發于荷蘭阿姆斯特丹,途經法國、日本、新西蘭等地,中國香港則是第14站。香港“大黃鴨”凈高16.5米,其視覺原型是隨著工業生產而走進千家萬戶的橡皮小鴨,多數國家嬰幼兒洗澡時常見的浴盆玩具。橡皮鴨隨著大眾文化的發展變幻出不同的造型與裝飾,而霍夫曼的設計則是將一切回歸本真,回到最初橡皮小鴨走進家庭時的形象。

圖1
霍夫曼拒絕將“大黃鴨”放置在博物館永久收藏,因此“大黃鴨”作為旅行者,它不屬于任何一個地方。這樣“大黃鴨”就成為一種具有“活態”的藝術景觀,通過在全球不同城市的水域展出,使水域在符號層面成為“大黃鴨”的浴盆,形成一種裝置空間,既保證了項目的可持續性和完整性,又喚起了人們對童年“浴盆小黃鴨”的記憶。直觀化的視覺符號間接營造出一種形態上的童年經驗,讓觀者通過“大黃鴨”看到自己的童年經歷,感受到親切的公共藝術進而產生移情,達到情感共鳴。這種動物題材的選取本質上是對人類童年經驗的提煉,由視覺圖像引起的童年記憶聯想可以更好地調動公共參與。“明代思想家李贄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同樣在西方,童年的看法自19世紀以來大致就有兩派:洛克派支持規訓可以將兒童改造成為文明的成人;而盧梭派則認為兒童天性可貴,他們的生長應該保證有機與自然。”“大黃鴨”利用了“童心”這一社會概念,讓海灣成為澡堂,讓街道成為畫布,讓城市里的成人找回童心,提升了公眾對藝術的認知感。
二、“大黃鴨”視覺表現的意蘊與影響
現代公共藝術的發展存在內外兩支,內省的一支由形式到觀念,在不斷地自我批評中成長;外向的一支尋求作品的公共途徑與公共價值,在印刷、電視、電影乃至網絡時代重建藝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大黃鴨”作為后者,發展和外向世界的交流與互動成為霍夫曼公共藝術的主題。“當代藝術家通過做減法的方式把文化符號減到最少,進而使這個符號逃過永無止境的變化,成為永恒的藝術。”這類“弱符號”的代表以現代藝術之父杜尚的代表作品《泉》為例,杜尚利用現成品進行藝術創作,其作品的命名讓人不禁聯想到主張唯美主義的學院派畫家安格爾的同名作品《泉》,杜尚把同樣的命名賦予了“不堪入目”的小便器,從而徹底粉碎了傳統意義上的“美”,正是這種簡單到極致的新藝術形式使得杜尚的《泉》成為當之無愧的當代藝術鼻祖。“‘大黃鴨’就屬于‘弱符號’的一種,它刪掉了橡皮小鴨(如圖2)原本富有裝飾性的造型樣式,讓其以極簡的本生造型來進行巡游展示。”

圖2
但“大黃鴨”藝術品本身的空間占據以及引起的觀看潮又將其本質指定為一種“強圖像”。它的出現帶來了萬人空巷的場景,是一種群體性的對于童年記憶的消費。因此,“大黃鴨”藝術是一件“弱符號”和“強圖像”的矛盾結合體。批評家孫振華說過:“公共藝術不是一種藝術形式,也不是一種統一的流派、風格,它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間的藝術能夠在當代文化的意義上與社會公眾發生聯系的一種思想方式,是體現公共空間民主、開放、交流、共享的一種精神與態度。”“大黃鴨”的出現帶來了全新的人際互動關系,體現了社會對公共空間的需求。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認為:“冷熱媒介隨時間、地點、空間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其屬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冷媒介的優勢在于可以實現多種感官的思考,受眾參與自由度高,而熱媒介的優點則是使受眾直觀理解且具有高清晰度的特點。無論“大黃鴨”的視覺圖像傳播屬于冷媒介還是熱媒介,其歸根結底都是在向受眾進行信息傳播,冷熱媒介雖然相對但并不絕對,重要的是信息在傳播時的內容表達。人們對童年快樂記憶的回憶與渴求,恰好被“大黃鴨”所迎合。
三、“大黃鴨”的視覺表現對當代公共藝術的啟示
霍夫曼的“大黃鴨”從展覽之初就一直強調公共空間藝術的公立性,這也是“大黃鴨”藝術能夠在多元文化下被廣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它體現了藝術品與城市、藝術本身及展出空間的關系創新。愛德華·霍爾曾經說:文化就是交流,交流就是文化。“大黃鴨”作為公共藝術符號,之所以能夠在不同文化之間快速地傳播與發展,所依靠的正是視覺表現與公共文化的相互結合。當代社會是一個讀圖的時代,公共藝術的視覺表現既是公共精神與意志的重要體現,也是引發觀者情感共鳴的重要延伸。因此,公共藝術創作者要善于入世,注重視覺表現的研究。“唯有打開公共藝術視野,公共空間的能量才能得以擴張,公共空間的品質才能不斷提升。”
綜上所述,“大黃鴨”所引起的萬人觀看潮,再一次印證了視覺表現在公共藝術傳播中的重要作用。霍夫曼的“大黃鴨”體現了藝術的邊界與公共的尺度,值得國內當代公共藝術的借鑒。藝術創作者應該重視將外在的視覺表現與精神、公眾認知相連接,使藝術與文化進行交流與互動,讓公共裝飾引領人們思想交流、升華情感,從而成為公共環境中有效的存在要素,得到大眾的認可與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