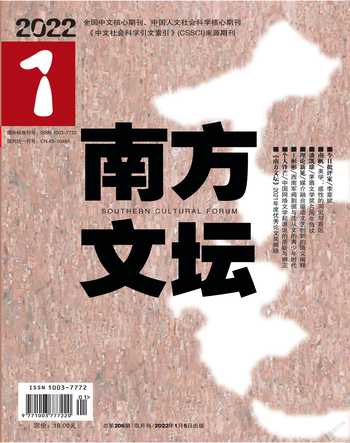中國登山文學:一座高峰,又一座高峰
作家黃怒波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珠峰海螺》正在引發讀者的強烈反響,也得到文學評論家們的高度關注。這部作品講述了一個登山家英甫被困在“珠峰”第三臺階8750米處3天,感悟人生的故事,描寫了一個人的生命在生命禁區頑強斗爭,在不可能生存的難以想象的嚴酷環境中,創造生命輝煌奇跡過程,表現出人身上迸發出來的那種超然的巨大的力量,從而折射出一個偉大時代創造者們堅強的意志和樂觀向上的精神。中國的小說也許并不是第一次講述“珠峰”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由攀登“珠峰”的親歷者用小說的方式講述的“珠峰”的故事。作者黃怒波是中國著名的登山家。直到現在,他已經3次成功地站到珠穆朗瑪峰頂上。《珠峰海螺》就是他與世界最高峰較量搏斗經歷生死考驗的真實寫照。從這個意義上說,《珠峰海螺》最真實反映“珠峰”登山探險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如果我們找不出世界上還有另一個小說家也攀登過“珠峰”的話,那么《珠峰海螺》可能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最真實描寫“珠峰”探險的長篇小說。僅這一點,這部長篇小說就應該令人稱奇,就應該得到高度評價。
十年前,中國詩人駱英就以一部長詩《7+2登山日記》開辟了中國詩歌一個新的創作領域,掀開中國詩歌新的一頁,立起了一座中國登山文學的新高峰。詩人站在世界上7座最高峰的峰頂、2個極地的中心寫詩放歌,表達人類對自然的敬畏熱愛和贊美,表達了詩人那種勝利者的驕傲與豪情,更表達一個中國人面對世界的特有的家國情懷。其中,《珠峰頌》等幾首詩,就是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頂上構思創作完成的。在時時受到腦水腫嚴重威脅,人的正常思維狀態混亂面臨崩潰的條件下捕捉到詩的感覺,追求到詩的意境,堪稱詩歌創作的“奇跡”。作為一個登山探險家,詩人駱英艱難而出色地攀登世界7座最高峰,走完2個極地——南極北極。在當時,整個世界,只有十幾個人能夠完成這個極難的運動項目,而駱英就是他們當中唯一一個詩人,也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詩人。直到今天,他創造的這個紀錄,還沒有哪一個詩人打破。幸運的是,詩人駱英和小說家黃怒波恰好同一個人。十年前,他以“在場”的姿態,創作了詩歌《7+2登山日記》,十年后當他第三次從“珠峰”走下來的時候,創作了小說《珠峰海螺》。兩部作品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構成了中國登山文學相當長時期里,還無人逾越的兩座高峰。一座是詩歌創作的高峰,一座是小說創作的高峰。
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也是站得住腳的。世界文學史上登高之作、探險之作并不鮮見。許許多多優秀作品都與登山和探險相關。中國探險文學并不發達,但中國文學史上的登高之作卻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部同類題材作品相媲美。從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經驗看,一個優秀的詩人,一生中都必須一次或數次遠行大川,登臨名山,旅行探險,方有作品流芳百世。不過,我們很容易就會注意到,世界上所有文學家都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像中國當代詩人駱英、中國當代小說家黃怒波那樣,登的是挑戰人類體能極限和生命極限的峰頂。這種感受,幾乎沒有哪一個詩人作家能夠企及,能夠體味。這就意味著,這種體驗、這種感悟、這種想象無法復制,沒有經驗可參照,所以這種體驗和經驗是一個詩人、一個作家所獨有的。世界上只有一個詩人作家占有這種感受、這種體驗、這種想象,也就形成作品獨一無二之處,獨一無二的文學的生命體驗價值。我們這些山底下的人,可以試圖去分享詩人作家在沒有生命跡象的高峰上傳遞給我們的情感和精神的信息,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詩人作家的情感和精神,是怎樣感悟和抵達彼岸的。世界上也許只有兩種人能夠體悟彼岸的存在。一種人是宗教修行者,一種應該就是能夠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詩人作家。修行者有很多,一直都有。詩人/作家現在只有一個。
僅從中國登山文學發展這個層面上,就可以認定《7+2登山日記》《珠峰海螺》兩部作品作為世界探險文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讀世界文學史我們得知,探險文學的興起與發展,從來都不能完全看作是詩人/作家個人的行為,而更多地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興盛或衰弱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和一個國家面對世界、走向世界、作用于世界的大勢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以及精神狀態通過文學和詩歌,也就是通過詩人/作家個人的創作和作品得以表現和張揚的。一般說來,文學發展與經濟實力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強大的民族、強大的國家不一定能夠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弱小民族、弱小國家也可能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但是,探險文學發展不一樣。一定要有強大的國家實力支撐,一定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的上升時期的精神文化產物。沒有國家的“開疆拓土”意識,就沒有繁榮的探險文學。很難想象,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國家,哪里能夠有開疆拓土的沖動,哪里有征服世界的雄心。沒有這種沖動雄心,就沒有自己民族的探險文化和文學。從這個思想層面上說,世界探險文學的上一個輝煌時代,正是呼應了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的強勢發展,由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歷史創造的。也是從這個思想層面說,中國探險文學的良好勢頭,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激活的。中國時代,正在產生自己偉大的探險文學作品,中國的登山文學走到了前列,引領了中國探險文學的走向。新的世界探險文學的發展,一定會有中國文學的重大貢獻。
事實證明,民族復興、國家強盛、社會進步、人民振奮的時代,為中國登山文學的發展積累了豐厚的歷史和現實資源,創造了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優越的條件,不斷把中國的登山文學推向時代精神的高峰。然而,我們的文學仍然在相當的時間里,苦苦等待著與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相稱的優秀作品。直到詩人駱英的《7+2登山日記》的問世,我們這種等待才算有了令人振奮的回報。之前,盡管詩人駱英不斷用優秀詩作試圖把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在詩人上,但整個社會仍然把他當作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人們普遍認為,他得益于這個時代的資本運作的成功遠遠高于詩歌方面的成就。《7+2登山日記》證明,他內心的文學力量要遠遠大于他所承擔的資本的力量。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是一個超越自我的登山探險者,更是一個深得時代精氣神灌注的思想者,這些文化因素碰撞在一起,創造出了一部向著人類精神“珠峰”的沖頂之作。
詩人駱英在完成了這部堪稱劃時代的詩歌作品后,并沒有停止他登山探險的腳步。第三次攀登“珠峰”,沖頂成功之后,他的文學創作“野心”像“珠峰”上的狂雪一樣,鋪天蓋地狂卷而來。他居然在把五星紅旗展開在世界最高峰上那一剎那間,神力一般地激活了一個小說的“靈感”并產生強烈的創作沖動。為了這個產生于“珠峰”的靈感,他心甘情愿地花費了10年的時間去讀大量的書,去做大量的案頭,然后,投入幾近瘋狂的創作中。幾易其稿,終于推出了一部與《7+2登山日記》同樣不可思議的近40萬字的長篇小說《珠峰海螺》。應該說,這部作品,以充滿時代精氣神的品質,再次打開了中國登山文學廣闊的空間,再度把中國探險文學推向時代精神的“峰頂”,也是一部將在相當長時期里不可逾越的“珠峰”題材的大作品。
如果說,《7+2登山日記》第一次把中國詩歌“場”擴大到世界五大洲,折射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走向世界的豪邁感和樂觀精神的話,那么,《珠峰海螺》則把目光聚焦在世界第一高峰,反映這座高峰對人類世界的極端重要性。同樣有一種豪邁感和樂觀精神。由此,我們會注意到,作家黃怒波已經完成了由詩人向小說家的轉換,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向故事敘述者的轉換。盡管作品主題內涵仍然有我們山底下人不可企及的成分,但小說故事的虛構性、現實性和故事性,多少稀釋了詩歌中的不可知的神秘感,多少把他所獨占的“珠峰”題材從彼岸拉回了此岸,拉回了世俗的人間。他的一座“高峰”立在彼岸,他的另一座“高峰”立在此岸。
被困在“珠峰”上的登山家英甫也是全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他生死拼搏的三天,也是他的企業生與死的三天。他人在峰頂,卻在山腳下引發了社會風暴。大本營正在動員所有的力量全力搶救。事實上,在當時的條件下,大本營不僅救生資源匱乏,本身也處在極度危險當中,要救人談何容易。與此同時,一個想害死英甫的陰謀也在實施。有一種力量有意阻撓對英甫的求助,企圖粉碎救人的最后努力。而遠離“珠峰”的北京,英甫的企業正面臨著重大的危機。他的對手認定英甫下不了山了,便開始動用各種非法手段,肢解公司,轉移股份,傾吞財產,鬧得烏煙瘴氣,人心惶惶。一場深刻的社會較量正在醞釀,不可避免地爆發。這一切,困在山上的英甫自然一無所知,他已經開始腦水腫了,體溫也越來越低了。他現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沒有活下去可能的地方創造可能性,堅定地活下去。
小說試圖從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來揭示生存斗爭的復雜性和嚴酷性。作為一個登山者,他經歷了千難萬險、生生死死,在征服自然中認識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認識到人類的表面自大、內心渺小,有了對大自然的深度敬畏,升華出現代應有的思想境界。作為企業家和社會精英,他在殘酷的商戰搏殺中看清了人性的復雜性,深刻認識了資本財富的本質,也深刻認識了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強者,其實非常軟弱脆弱,從而也深刻感悟了生活的意義,認識了人的本質。兩種關系有機交織在一起,托起小說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相互依存、和諧共處的主題,令人深思。
也許,小說主題內涵盡管豐富深刻,讀者卻不難提煉。當代小說,描寫和表現當代人關于“現代性”的困惑與矛盾已經很普遍,思想理論也很完備。因為,主題的“現代性”思想可能還不是作品《珠峰海螺》最重要的貢獻。對一部小說來說,人物形象才是最重要的。作品所有的思想精神信息,都將從人物形象身上透露出來。人物形象的獨特性,決定了作品的獨特性,人物形象的新意,決定了作品的品質。值得高度重視的是,《珠峰海螺》主人公英甫的形象正在顯露出獨特性和不可代替性。小說有意把故事濃縮在三天里,而這三天,正是英甫困在“珠峰”的三天。坦率地說,能在“珠峰”堅持三天等待援救的人,本身就是生命堅硬如石的“超人”,而能把“超人”寫出來,只有《珠峰海螺》做得到。所有的小說家都沒有可能體驗,沒有任何經驗。只有黃怒波有這個體驗,有這個經驗。只有他知道“英甫”這三天是怎樣活過來的,只有他體驗過一個被冰雪和腦水腫反復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狀態,因此,英甫這個形象,天生就有不可重復性與不可超越性。
小說所有觸目驚心的“珠峰”細節,都在支持著英甫形象的“唯一性”。其中,英甫一個人面對多年前就死在那里的山友和死者對話細節,更是難以想象的。也許,在這座神圣的高峰頂上,死亡并不意外,也不恐怖了。事實上,主人公只有利用清醒的一瞬間,閃過他的那些“商戰”,才有恐怖感。而在這高山上,在風暴中,內心卻也一片平靜、從容與神圣。這種感覺,與《7+2登山日記》的彼岸哲理一脈相承,都是對人生新的格局和境界的再發現。英甫的性格正是有這種先進思想打底,就能透過現實撲朔迷離的世俗,把握住自己的命運。有了這一點,英甫的人物形象就有了思想的靈魂,就突現了性格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質。整座“珠峰”就像命運的靈魂一樣,牽動著整個世界。而英甫形象融入了這座高峰里,身上也閃耀著“靈魂”的光芒。“三天”的描寫,托出中國登山文學的一個新的文學形象。
英甫這個形象的深刻塑造,使小說也超越出登山探險文學的格局,有了社會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作品直接間接觸及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民生”許多問題。如應對百年未有大變局問題,深化改革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價值觀、道德觀、財富觀問題,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生態問題以及更深層的文化問題。小說中,英甫不僅是探險家、企業家,還是一個自覺的生態保護主義者。他在“珠峰”探險,也在努力保護著“珠峰”的生態。他把保護的重點放在“狼”的方向上。小說細膩地描寫了藏區的風土人情和老百姓的生存狀況,與已經國際化的一支支登山隊的現代登山運動對生態環境的挑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也描寫了在這樣的矛盾生態下,物種面臨的生存危機,例如狼的物種,如果沒有人類自覺的保護,很快就會消失。狼這種動物,在商業社會中常常被描述為狠角色,是“強者”的象征。可是,這種個性仍然強悍的動物,現在已經是生態鏈中的弱者,一個瀕臨滅絕者。這讓人很自然引申到英甫這個形象上。看似時代寵兒,時代弄潮兒,資本精英,成功人士,生活的強者,其實,“三天”就足以產生風險和危機,也是很脆弱的。也許,也是時代的脆弱與危機。小說的新意也許就在引發我們在體悟人生命運的同時,思考社會、現實和時代。雖為登山文學,卻也有豐厚的社會文化含量,是中國登山探險文學需要堅持探索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7+2登山日記》的題記寫的是:山,本來不在那里,是我們找來了它。而《珠峰海螺》有題記寫的是:獻給珠峰新高度。前者具有豪邁的氣勢,后者則更帶著虔誠的膜拜。前者浪漫,后者寫實,異曲同工,共同把中國登山文學這座“山”推向“新高度”。■
(張陵,作家岀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