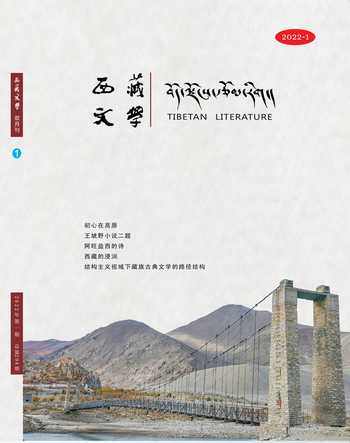抓著馬尾爬山的那個(gè)女孩
旺珍
像往常一樣,午餐后收拾完廚房,瑪吉熬起甜茶,上好的斯里蘭卡紅茶在鍋中與牦牛奶翻滾在一起,整個(gè)廚房彌漫著淡淡的茶香……拉薩夏日午后的艷陽(yáng)很容易讓人慵懶,此時(shí)來(lái)一杯甜茶是不錯(cuò)的選擇。
滴鈴鈴……一陣鈴聲響起,瑪吉拿起放在餐桌上的手機(jī),電話(huà)里傳出一個(gè)花季少女的聲音,是她遠(yuǎn)在英國(guó)留學(xué)的女兒吾瑪。
“阿媽啦,您在干嗎?”吾瑪邊收拾東西邊問(wèn)道。瑪吉說(shuō):“在做甜茶。”吾瑪說(shuō):“我剛起床準(zhǔn)備去上課。”
這時(shí)剛睡完午覺(jué)的拉姆掀開(kāi)白底藍(lán)紋的門(mén)簾踏了進(jìn)來(lái),瑪吉趕緊湊近拉姆,給她看手機(jī)視頻,電話(huà)那頭的吾瑪在喊:“嬤啦嬤啦!”拉姆雙眼笑得瞇成一條細(xì)縫,這時(shí)吾瑪說(shuō):“哦,再不走我要遲到了,嬤啦拜拜。”拉姆正準(zhǔn)備說(shuō)點(diǎn)什么,視頻已經(jīng)掛斷了。
“這孩子,我還沒(méi)說(shuō)一句就掛斷了。”
瑪吉放下電話(huà),款款地拿出兩個(gè)精致的瓷杯,一邊斟著甜茶一邊說(shuō):“她那邊著急上課呢!晚上我再給她撥過(guò)去,您再跟她聊,現(xiàn)在很方便的。”
“現(xiàn)在的科技真是太厲害了,隔著千山萬(wàn)水卻可以隨時(shí)相見(jiàn)。”
“是啊,智能時(shí)代的科技把人類(lèi)的好多幻想都變成了現(xiàn)實(shí)。”瑪吉說(shuō)。
點(diǎn)著頭,拉姆伸出那雙微微發(fā)顫寫(xiě)滿(mǎn)歲月滄桑的手,小心地從餐桌上端起斟滿(mǎn)甜茶的青花瓷杯,意味深長(zhǎng)地說(shuō):“是啊,就像這杯甜茶!”拉姆不由得感慨起來(lái)……
“拉姆,還不快點(diǎn)跟上!”管家吼道。“隆司。”拉姆弓著腰吐了一下舌頭說(shuō)道。天蒙蒙亮就出發(fā)了,這會(huì)兒已經(jīng)走了八個(gè)多小時(shí),穿著那雙露了腳趾頭的松巴靴,小拉姆走在彎彎曲曲的野石榴叢的小道,望著眼前即將要翻越的這座山脊,小拉姆已經(jīng)有些體力不支腿腳發(fā)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