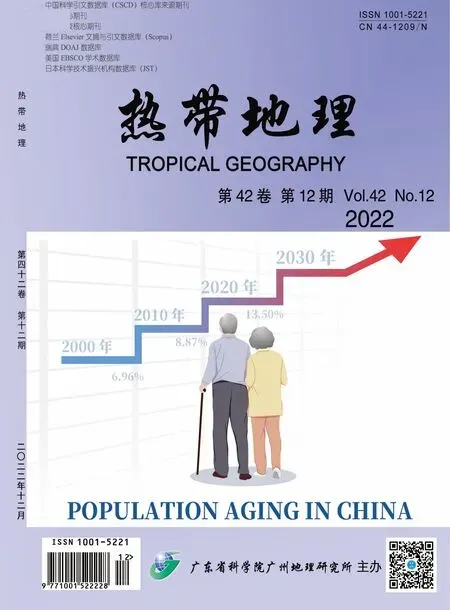社區分異視角下建成環境對老年人日常休閑行為的影響
——以合肥市為例
程淑賢,韓會然,楊成鳳
(安徽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安徽蕪湖 241000)
人口老齡化是當前全球面臨的嚴峻問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到2021年末,中國≥60周歲人口比例為18.9%,其中≥65 周歲人口比例達到14.2%,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國家統計局,2022)。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由于未能充分考慮老年人的活動需求,老年人的日常活動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約。最新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指出要繼續完善養老服務體系,加快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和社區建設,提高社區宜老性水平(新華社,2021)。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各項身體機能開始退化,活動空間會相應地有所縮小,住所和社區成為其主要活動場所(Hanson et al., 2012;趙俊,2016);與其他人群相比,老年人的日常活動更容易受社區建成環境的影響。建成環境通過作用于體力活動這一中介變量,對居民健康產生積極或消極影響(Lee et al.,2004;于一凡,2020)。因此,營造有利于老年人活動出行的建成環境,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實現健康老齡化的有效途徑。
休閑行為具有預防退化性疾病,緩解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提高身體素質等作用,是老年人群主要的日常活動之一(Juarbe et al.,2002;周潔等,2013),通過參與休閑活動獲得的健康效應會隨老年人年齡的增長而日益增強(Nmrod et al.,2016)。地理學中有關老年人休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休閑行為的時空特征、休閑空間的適宜性評價以及休閑行為的影響因素等方面(Robert et al.,1997;劉珺等,2017)。受健康狀況和出行能力的影響,多數老年人的基本休閑圈在社區及社區1 km范圍內,不同社會經濟屬性老年人的休閑空間存在差異(孫櫻等,2001;柴彥威,2010)。從時間上看,清晨和午后是老年人休閑活動的高峰期,在晚間休閑活動中,女性老年人的參與率更高(徐怡珊等,2019;崔洪軍等,2020)。優質的休閑空間是吸引老年人主動開展休閑活動的重要前提,散步是老年人主要的日常休閑活動之一;因此,多數研究關注老年人休閑性步行空間的適宜性,人行道、綠化景觀、休憩設施等微觀環境要素是常用的評價指標(Borst et al.,2008;劉珺等,2017;黃泰等,2022)。休閑行為的影響要素大致可分為個人因素、人際因素及結構性因素3類(林嵐等,2012)。個人因素中,性別、年齡、收入、健康狀況、行為偏好等與休閑行為密切相關(陳梓烽 等,2014;王心蕊 等,2019;Roy et al.,2021);人際因素中,休閑同伴以及來自家庭和親友的社會支持對休閑參與有重要影響,家庭成員數量較多的居民有更多的休閑活動(Liu et al.,2019;Mouratidis et al.,2019);結構性因素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制度政策等方面(Liu et al.,2020)。建成環境作為影響休閑行為的結構性因素之一,是近年來城市地理學和城市規劃學界的研究熱點。已有研究對建成環境的測度多從密度(density)、多樣性(diversity)、目的地可達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到交通設施的距離(distance to transit)和設計(design)5 個維度展開(Handy et al.,2002;Ewing et al.,2010)。其中,前四者可歸為空間要素,主要通過增加通達度即減少居住地與目的地間的距離影響居民行為(魯斐棟等,2015)。具體而言,公園廣場等休閑場所和康體設施的密度高、可達性好,有利于促進居民主動出行,從而提高其休閑活動水平(Lin,2018;陳菲等,2019;馬明等,2019)。而建成環境多樣性通常以土地混合利用度表征,土地混合利用度高,表明多種功能用地相互臨近,能有效地縮短出行距離,促進出行行為;但土地混合利用度過高時,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Ma et al.,2015;Hou et al.,2021)。到交通設施的距離與目的地可達性關系密切,通常被認為能有效促進交通性出行活動,但對休閑行為的影響有待進一步論證(黃曉燕等,2020)。建成環境設計則主要表現在場所要素上,高品質的休閑場所如綠地、公園等戶外開放空間對老年人有較強的吸引力,是老年人進行休閑活動及鄰里交往活動的主要場所(王小月 等,2020;Ottoni et al., 2021)。此外,除了客觀建成環境要素,個體所感知到的主觀建成環境要素也會顯著影響休閑活動,老年人的休閑行為與他們對安全性和可達性等特征的感知密切相關(Barnett et al.,2017;姜玉培等,2020)。
綜上,建成環境與休閑行為關系密切,且已經得到驗證,但基于社區分異背景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國外關于建成環境與老年人出行行為的研究多以城市街區為尺度,按照人口普查區域定義社區(Barnett et al., 2017),但對于轉型期的中國城市,由于歷史原因和住房市場化改革,城市中的社區類型多樣。其中,單位房社區和公租房社區是2種較為特殊的社區類型,居住在其中的老年人的休閑行為也表現出明顯差異,因此有必要開展相關研究。近年來,國內也有部分文獻探討建成環境與老年人休閑行為的關系(馮建喜等,2017;李康康等,2021),但較少考慮社區類型的影響,多是將研究區域作為一個整體。社區類型分化在某種意義上可看作是居住空間分異的外在表現,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同時,城市空間與居民行為互動的過程存在尺度效應,人的行為受到不同尺度空間的制約;因此,有必要從社區出發,研究“不同類型社區中的人”如何與其所在社區的建成環境進行互動。在住房體制改革過程中,受時期效應和世代效應影響,具有某些共同屬性或特征的人群在住房產權獲得上具有顯著優勢(吳開澤,2017);而不同類型的社區在城市化進程中受到的影響程度不同,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中不同社區的人口構成存在顯著差異(周春山等,2021)。從社區分異的視角探討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能有效控制居住自選擇效應所帶來的偏誤(Wang et al., 2017;韓會然 等,2019)。因此,選取合肥市單位房、商品房和公租房3類典型社區作為案例,探討以下問題:老年人的休閑行為是否存在社區差異?社區建成環境如何影響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這種影響是否存在社區分異?產生差異的原因是什么?以期為推進健康老齡化和宜老社區建設提供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范圍為合肥市主城區,包括包河區、蜀山區、廬陽區和瑤海區4個轄區,具體社區分布見圖1 所示。作為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合肥市近年來在宜老社區及智慧社區建設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初步成就。但目前針對合肥市區不同類型社區的建成環境對老年人日常休閑行為的影響研究較少。因此,選擇合肥市作為研究區域具有一定代表性。

圖1 樣本社區的地理區位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sample community
數據來自2020 年7—8 月在合肥市開展的“社區建成環境對老年人身體活動影響”問卷調查。采用分層抽樣調查法,選擇合肥市主城區4個行政區,按照合肥市商品房、公租房和單位房3類住房產權數量比例確定各類社區抽樣數量,最終選取單位房社區3個(省糧食局機關大院、市委大院、杏花小區),商品房社區6個(琥珀山莊、御湖觀邸、祥源城、琥珀名城、美生濱江花月、利港銀河新城),公租房社區2個(民康百合園、濱湖惠園);社區內部采用隨機抽樣調查,被訪者為年滿55周歲的女性和年滿60周歲的男性。選取內部環境和居民構成存在較大差異的11 個社區,如市委大院等單位房社區,由于建成年代較早,配套設施老舊,缺少針對老年人的公共服務設施,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可達性高,主要居民為單位職工;琥珀名城等商品房社區建成時間較近,社區內設施、綠化景觀較好,但居住人口構成較復雜;而以民康百合園和濱湖惠園為代表的最早一批公租房社區,也存在設施老化、配套設施不完善等問題,且社區內的居民多為中低收入者。調研過程中,共發放問卷800份,回收有效問卷702份,有效率為87.75%。其中單位房社區211份,商品房社區319份,公租房社區172份,分別占有效問卷總數的30.06%、45.44%、24.50%。問卷獲取到的相關信息包括:居民個人社會經濟屬性、居民對所在社區建成環境的主觀感知評價和居民日常休閑活動的類型、頻率及時間。
1.2 變量選擇與測度
1.2.1 休閑活動水平評估 休閑行為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多種類型的活動。對老年人而言,年齡的增長會將他們的休閑行為空間限制在住所及社區周邊,休閑活動類型也會趨于一致,如看電視、接待訪客、在社區內散步等(周潔等,2013)。基于此,本研究的休閑行為主要指老年人在社區內及周邊進行的日常行為,如散步、打牌、跳廣場舞、設施健身等,因變量為每周休閑行為的頻率,通過詢問被訪者“您一周之內有幾天會進行以上這些休閑活動”獲取數據。本文休閑行為頻率由4個等級的有序變量(1、2、3、4)構成(表1),等級越高,說明其休閑活動水平越高。

表1 老年人個人屬性及社區建成環境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2020年)Table 1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ividual attributes of elderly people and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2020)
1.2.2 社區建成環境測度 社區建成環境分為主觀感知建成環境與客觀建成環境兩類,分別使用不同方法測度。其中,感知建成環境變量來自調查問卷中受訪者對社區環境的評價,包括“社區治安”“社區綠化環境”“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社區交通便捷度”和“休閑娛樂場所”5個指標,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進行賦分,“1”為“非常不滿意”,“5”為“非常滿意”,得分越高表明老年人對感知建成環境的評價越好。
客觀建成環境是社區的基本屬性,直接影響到居民對社區環境的感知和評價(申悅等,2019)。按照15 min生活圈的概念,以被訪者居住社區的幾何中心為圓心,建立半徑為1 000 m 的緩沖區作為客觀建成環境變量的測量范圍,通過百度地圖遙感影像和ArcGIS10.2進行空間計算。具體指標包括土地混合利用度、交叉口密度、公交站點數、到最近公交站的距離和休閑娛樂場所數量。
自變量除了上述的主客觀建成環境變量,還包括居民的社會經濟屬性,主要有性別、年齡、戶籍、個人月收入和居住組合方式(見表1)。
1.3 研究方法
1.3.1 研究框架 哈格斯特朗認為人的行為活動存在于特定的時空中,受到能力制約、組合制約和權威制約,能力制約與個體特征密切相關,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個體所能達到的空間范圍;建成環境被包含在組合制約內(Torsten,1970),同休閑制約理論相似,基于此,構建本研究框架(圖2)。根據已有研究及所選定的變量(馮建喜等,2017;黃曉燕等,2020),提出6點假設:

圖2 社區建成環境影響老年人日常休閑行為的分析框架Fig.2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daily leisure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people
H1:個體特征變量對老年人的日常休閑行為影響顯著,尤其是年齡和個人月收入,年齡的增長在客觀上限制老年人的日常休閑活動,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老年人休閑機會。
H2:對感知建成環境變量的評價越高,老年人的日常休閑活動頻率越高。
H3:土地混合利用度對老年人的日常休閑行為具有顯著影響。
H4:交叉口密度越高,表明社區通達性越好,能有效促進老年人的日常休閑活動。
H5:公交站點數、休閑娛樂場所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休閑空間的可達性,與老年人的日常休閑活動呈正相關關系。
H6:距離最近公交站的距離與老年人的日常休閑行為間存在負向關系。
1.3.2 模型設定 為探討不同類型社區中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因素,將老年人的休閑活動水平劃分為4個等級,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探究個人社會經濟屬性及社區的主客觀建成環境與老年人休閑行為之間的關系。為了修正使用有序Logistic 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時可能出現的多重共線性問題,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篩選并剔除引起多重共線性的變量,從而建立最優回歸模型(石磊等,2020)。有序Logistic模型的表達式為:

式中:xi代表第i個變量;α為截距;β是一組與自變量x對應的系數;y為老年人休閑活動水平,給各等級y賦值j(j=1,2,3,4),由于本文的因變量有4 個等級,相應地建立3 個累積的Logistic 回歸模型:

式中:Pj代表老年人休閑活動水平為j等級的概率,j=1,2,3,4;αj為截距;β表示與之對應的自變量x的回歸系數,有序Logistic 模型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參數估計,計算出αj和β后,y=j等級發生的概率即可通過公式(3)計算得出:

有序Logistic 模型估計出的結果以概率累積比的形式呈現,從系數的方向和顯著性2個角度解釋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從而對二者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
2 老年人休閑行為與社區建成環境特征
為非本地戶口;約有60%的老年人個人月收入≥2 000 元。在居住組合方式上,52.42%的老年人與子孫一起居住,其次為與配偶同居(35.61%),10.68%的老年人為獨居。而住在社區內養老服務機構的老年人較少,這一方面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及經濟條件的影響,部分老年人對此類機構存在抵觸心理(李玉玲,2016);另一方面由于調研正處于疫情防控期間,社區的養老服務機構采取封閉管理措施,因此該類別的老年人樣本較少。
從休閑活動頻率看,有70%左右的老年人的日常休閑行為頻率為每周≥3 d,大約18%的老年人每天都會進行日常休閑活動。不同類型社區中的老年人休閑頻率有所差異,居住在單位房社區老年人的休閑活動頻率最高(均值為2.45),其次為商品房社區的老年人(2.23),公租房社區的老年人休閑頻率最低(1.87)。從休閑活動類型看,老年人日常參與率最高的休閑活動為散步(占70%),其次為跳廣場舞(11.63%)、打牌(9.75%) 和設施健身(6.47%)。總體上,多數老年人的休閑活動以低強度活動為主,這主要是受老年人身體狀況及家庭因素的影響,約有50%的老年人需要照顧孫輩,這些低強度的休閑活動既可以提高身體素質,又可以照料家庭。
表2 和圖3 顯示,在社區感知建成環境方面,各變量的均值都>3,表明多數老年人對社區建成環境評價較高。老年人對社區治安、社區綠化及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的感知差異較小,比較滿意及非常滿意的累計占比為55%左右。社區交通便捷度的比較滿意及非常滿意的比率明顯高于其他變量,說明老年人對該變量的評價最高。休閑娛樂場所得分最低,選擇一般及比較不滿意的累計占比高于其他變量。為探究不同社區中老年人的建成環境感知是否存在差異,分別以各感知建成環境變量為因變量,社區類型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老年人只在社區綠化感知上表現出顯著的社區差異,其中,商品房社區的老年人對社區綠化的評價相對高于其他兩類社區,社區治安、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社區交通便捷度及休閑娛樂場所的評價得分雖存在社區差異,但在統計學上不顯著。

圖3 老年人社區感知建成環境評價Fig.3 Evaluation of the perceived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f the elderly

表2 不同類型社區樣本的感知建成環境評價Table 2 Perceptual built environment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samples
由表3 可以看出,3 類社區的客觀建成環境存在明顯差異。單位房社區的土地混合利用度及休閑場所數量明顯高于其他2類社區,表明在單位房社區中居住用地所占比例較高,居民的休閑活動場所較多。社區的連通性與交叉口的數量緊密相關,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單位房社區的通達度高于其他2類社區。公租房和商品房社區周邊的公交站點數明顯少于單位房社區,且與最近公交站的距離遠于單位房社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對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但單位房社區的老年人對社區交通便捷度的評價沒有顯著高于其他2類社區(見表2)。這可能是由于本文所調研的單位房社區都位于老城區,建成年代較久,社區內及周邊道路設計缺乏整體規劃且交叉路口多,人流量、車流量較大,不利于老年人出行,同時也會使老年人缺乏安全感,從而導致他們對交通便捷的感知評價較低。

表3 不同類型社區客觀建成環境特征Table 3 Objective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3 社區建成環境對老年人日常休閑行為的影響
利用調查數據,首先對全樣本、單位房社區、商品房社區、公租房社區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建立4 個回歸模型,分別探討在不同類型社區中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是否存在社區差異。并在回歸模型的基礎上構建邊際效應模型,探討具有顯著作用的影響因素對于老年人休閑行為的作用程度。
3.1 老年人日常休閑行為的影響因素
全樣本的回歸結果顯示,老年人的休閑活動水平與其社會經濟屬性沒有顯著相關性,假設1不成立。老年人對社區交通便捷度的滿意度與其休閑行為間具有正向關聯,這可能是因為對交通便捷度的滿意度越高,表明社區周邊休閑場所的可達性越高,能夠提高老年人休閑行為的頻率。土地混合利用度對老年人的休閑行為有積極作用,這是由于高土地混合利用度意味著土地利用的多樣化,各種設施、場所匯集,一方面給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休閑機會,另一方面能有效減少老年人的出行距離,促使其更多地選擇步行作為主要出行方式(Ma et al.,2015;齊蘭蘭等,2018),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頻率。交叉路口密度與老年人休閑行為頻率呈負相關性;雖然交叉路口密度越大,社區的通達度越高,但過多的交叉路口可能會導致社區內交通狀況混亂無序,出于對安全性的考慮,老年人的外出意愿會降低,從而導致休閑行為減少。此外,到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對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頻率也產生顯著的消極作用;有研究表明,在交通優惠政策的作用下,公交車是老年人出行方式中成本較低的一種,僅次于步行,乘坐公交車出行是老年人中長距離出行中首選的出行方式(Zhang et al., 2019);隨著社區到最近公交車站距離的增加,老年人可能會選擇放棄乘車前往附近的休閑場所,導致其休閑活動頻率下降。
居住在單位房社區老年人的休閑行為受到性別、戶籍、社區治安、社區整體步行環境、土地混合利用度和交叉路口密度的影響,假設1、2、3成立。其中,社區治安的回歸系數為正,表明老年人對社區治安的滿意度越高,其休閑活動頻率也越高。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的回歸系數為正,說明良好的步行環境能有效增加老年人的休閑散步等行為。與全樣本的回歸結果一致,土地混合利用度對老年人的休閑行為具有積極的作用,且顯著性水平更高;交叉路口的密度對老年人的休閑行為產生負向影響,但其顯著性水平明顯低于全樣本,即相對于全樣本,在單位房社區中交叉路口的密度與老年人休閑行為的相關性有所降低。性別與老年人休閑行為頻率的相關系數為負,表明老年女性的出行頻率要明顯高于老年男性。從戶籍看,本地老年居民的休閑行為頻率比外地老年居民高,相對于外地居民,本地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更強,更愿意在社區及周邊進行休閑活動。
在商品房社區中,年齡、性別、居住組合方式、社區整體步行環境以及到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對老年人的休閑行為有顯著影響,假設1、2、6 成立。其中,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的回歸系數為正,和單位房的回歸結果一致。客觀建成環境變量中,只有到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這一變量與老年人的休閑行為有顯著的相關性,距離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越近,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頻率越高,反之越低,與全樣本的回歸結果一致。年齡表現為負向影響,說明隨著年齡的增長,健康狀況及活動能力下降,老年人的休閑活動頻率也會降低。與單位房社區不同,在商品房社區中,老年男性的休閑活動頻率顯著高于老年女性,這可能是由于在單位房社區中與子孫同居的老年人的比例僅為35.55%,而商品房為67.40%,這部分老年人在家庭中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如接送孫輩上下學,而女性相對來說更容易受到這些家務性活動的制約,因此老年女性的休閑機會和頻率會低于老年男性。居住組合方式的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家庭成員越多,老年人的休閑活動水平越高,這可能是因為相比于獨居或與配偶同居的老年人,與子孫同居的老年人能得到更多的代際支持,且他們的休閑觀念更容易受年輕一輩的影響,其休閑活動水平會相應更高。
在公租房社區中,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個人月收入、居住組合方式、社區綠化、社區交通便捷度、土地混合利用度、到最近公交站的距離,假設1、3、6成立。其中,社區綠化的滿意度與老年人休閑行為呈負相關關系,這與以往的認知存在不一致,有待進一步驗證。社區交通便捷度為正向影響,到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為負向影響,說明對交通便捷度的評價越高,到最近公交站的距離越近,老年人的休閑行為越頻繁。土地混合利用度的回歸系數為負,與單位房的結果相反,這可能是由于土地混合利用度存在閾值,新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土地混合利用度在0.4~0.7之間,老年人的休閑步行時間最長,因為過低的土地混合利用度意味著各種服務設施分散且相互距離較遠,可達性較差;過高的土地混合利用度則可能會由于設施的過度集中造成混亂無序的狀態,易使老年人受到傷害,二者都會對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造成消極影響(Cheng et al.,2020)。個人月收入表現為正向影響,即老年人休閑行為頻率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提高,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高的老年群體,休閑機會和時間越多,他們在休閑活動中的消費能力更強。居住組合方式的回歸結果與商品房社區正相反,表明在公租房社區,家庭中同居的人數越少,老年人休閑行為的頻率越高,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公租房社區中與子孫同居的老年人的比例(45.03%)低于商品房社區(67.40%),這部分老年人要分擔子女的生活壓力,而獨居或僅與配偶同居的老年人只需要承擔1~2人的家庭責任,他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和精力進行休閑活動。
3.2 邊際效應分析
表4中有序Logistic模型估計出的系數含義不直觀,只能從方向和顯著性兩方面得到有限的信息,所以在此基礎上計算各自變量對老年人休閑行為的邊際效應,由于篇幅的限制,表5只列出具有顯著影響的變量。

表5 老年人休閑行為影響要素的邊際效應Table 5 Marginal effect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isure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people
從全樣本的邊際效應模型看,當所有解釋變量都處于均值時,對交通便捷度的滿意度每增加1個單位,老年人休閑行為頻率為“每周1~2 d”的概率下降0.031,為“每周5~6 d”的概率上升0.010,為“每天”的概率上升0.023,土地混合利用度的影響與之類似。交叉路口密度在Y=1時邊際效應為正,表明隨著交叉路口密度的增加,老年人休閑頻率為“每周1~2 d”的可能性增加;但當Y>2時邊際效應為負,說明交叉路口密度越高,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頻率為每周≥5次的概率會降低,總體上,與表4的結果一致。

表4 不同類型社區回歸結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在感知建成環境變量中,單位房社區的老年人對社區治安的評價每提高1個單位,其休閑行為頻率為每天的概率上升0.053,每周1~2、3~4、5~6 d的概率分別下降0.049、0.018、0.013。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的滿意度對單位房和商品房的老年人的邊際效應相似。在公租房社區中,對社區交通便捷度的滿意度每增加1 個單位,老年人休閑行為頻率為“每周1~2 d”的概率下降0.120,“每周3~4 d”“每周5~6 d”及“每天”的概率分別增加0.058、0.031、0.032。
從客觀建成環境變量看,土地混合利用度的邊際效應在單位房社區和公租房社區呈明顯差異。在單位房社區中,土地混合利用度每增加1 個單位,老年人的休閑頻率為“每周1~2 d”和“每周3~4 d”的概率分別下降0.889、0.329,“每周5~6 d”和“每天”的概率分別上升0.242、0.975;而在公租房社區中,土地混合利用度增加1個單位,老年人的休閑頻率為“每周1~2 d”的可能性增加0.264,“每周3~4 d”的概率下降0.127,這可能是由調查的公租房社區土地混合利用度過低引起。交叉路口密度是單位房社區中邊際效應最小的顯著解釋變量,到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在商品房社區中的邊際效應大于公租房社區。
在個人社會經濟屬性中,性別對單位房和商品房社區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都產生顯著影響,且兩類社區的結果相反,與回歸模型中的結果完全一致。戶籍只對單位房社區的老年人產生顯著影響,相比戶籍為本市的老年人,外地戶口的老年人休閑行為頻率為每周1~4 d 的可能性較大,而本地戶口的老年人休閑頻率在每周4 d以上的概率更大,總體上,仍然是本地老年居民的休閑活動水平更高。對于商品房社區而言,75歲以上的老年人其休閑活動頻率為每周1~2 d的可能性更高,55~74歲的老年人休閑活動頻率為每周≥5 d的概率更高。居住組合方式對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在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區中存在明顯的差異,具體地,在商品房社區中,居住在社區養老服務機構的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頻率傾向于每周1~2 d,與子孫同居的老年人的休閑頻率在2 d以上的可能性較大;而在公租房社區中,前者的休閑頻率為每周≥5 d的概率較大,后者的休閑頻率為每周≤4 d的可能性更大。個人月收入的邊際效應與回歸模型的結論一致,不再贅述。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基于對合肥市3類社區的老年居民問卷調查數據,運用有序Logistic 回歸分析,探究不同類型社區中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得出的主要結論為:
1)不同類型社區中,老年人的休閑活動有顯著差異,居住在單位房社區的老年人休閑頻率最高,公租房社區最低。整體上,多數老年人的休閑活動頻率為每周≥3 d 且每天的休閑活動時間較長,休閑活動類型以散步、跳廣場舞、打牌等低強度活動為主。老年人的休閑行為雖然是個人偏好選擇,但家庭和社區因素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社區差異。在感知建成環境變量中,全樣本的回歸結果顯示,僅社區交通便捷度與老年人休閑行為有明顯的相關性,與公租房社區的回歸結果一致,對社區治安的感知評價僅在單位房社區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的評價則在單位房和商品房社區都表現出積極作用。
3)從客觀建成環境變量看,在全樣本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交叉口密度、到最近公交站的距離3 個變量與老年人的休閑行為密切相關,但從不同類型社區的回歸結果看,這3類社區都沒有得到與全樣本完全一致的結論。土地混合利用度盡管在單位房和公租房社區都表現出顯著的影響,但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交叉口的密度僅與單位房社區老年人的休閑行為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到最近公交站的距離在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區中均產生負向影響。
4)建成環境對于不同休閑頻率的老年人也表現出差異化的影響。單位房社區中,社區治安、社區整體步行環境、土地混合利用度與中低休閑頻率的老年人之間呈負向關聯,與高休閑頻率的老年人之間呈正向關聯,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區中,低休閑頻率的老年人受到社區整體步行環境的負向影響、到最近公交車站距離的正向影響,但二者對于高休閑頻率老年人的影響方向正好相反;公租房社區中,低休閑頻率的老年人與社區交通便捷度之間呈負相關關系,與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車站的距離呈正相關關系,而中等休閑頻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閑頻率的老年人僅受到社區交通便捷度的積極影響。
4.2 討論
本研究顯示,在單位房、商品房和公租房3類社區中,影響老年人休閑行為的主客觀建成環境要素有所不同,這種基于社區分異背景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在國外的一些研究中,老年人的休閑活動與密度、多樣性等建成環境要素未表現出顯著相關性(Chaudhury et al., 2016;Cleland et al.,2019),但在本研究中,密度、土地混合利用度等要素與老年人的休閑行為有明顯關聯,表明由于中國的社會狀況和城市空間結構與國外存在差異,老年人的休閑行為與建成環境間的互動關系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盡管國內部分研究論證了建成環境與老年人休閑行為間的關聯(馮建喜等,2017),但忽略了社區之間的差異,可能會造成結果的偏差。以土地混合利用度為例,在本文中,當不區分社區類型時,其與老年人的休閑行為呈正相關,但分社區的結果表明,在公租房社區中,二者間的關系與全樣本的回歸結果相反,說明社區形態、設施配置等方面的差異可能會改變建成環境與老年人休閑行為間的關系。此外,邊際效應模型的結果表明,即使是在同一類社區中,對于具有不同休閑頻率的老年人來說,建成環境所帶來的邊際效用也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對于休閑頻率較低或較高的老年人來說,他們的休閑活動可能更多受到態度偏好及身體機能的影響。
建成環境與居民行為活動間的關系是復雜的,社區環境影響居民的行為活動,而居民的行為也塑造、改變社區建成環境。本文通過對合肥市3類社區的實證研究,從社區類型和老年人個體需求的視角出發,探討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休閑行為的影響,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深化老年人行為活動與城市空間結構的互動研究;另一方面,也能為社區建設與改造、老年友好型城市社區構建提供針對性的建議。例如,對于單位房社區應該重點關注社區治安及社區內部交通狀況,可以增加一些安全設施及照明設備;對于公租房社區應增加康體設施密度及休閑場所數量,提高可達性;商品房社區設施設備相對完善,但在社區步行環境方面還有較大改善空間。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休閑行為數據來源于老年人的自我報告,可能存在記憶偏差,且僅進行橫向研究,難以判別建成環境與老年人休閑行為間的因果關系,未來可考慮對老年人群進行追蹤調查,獲取長時間序列數據,以分析二者間的因果聯系;另一方面,只針對合肥市進行研究,相關結論是否適用于其他城市或地區還有待驗證,未來將進一步擴大研究范圍,選擇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驗證本文結論,同時探討城市尺度建成環境與老年人行為間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