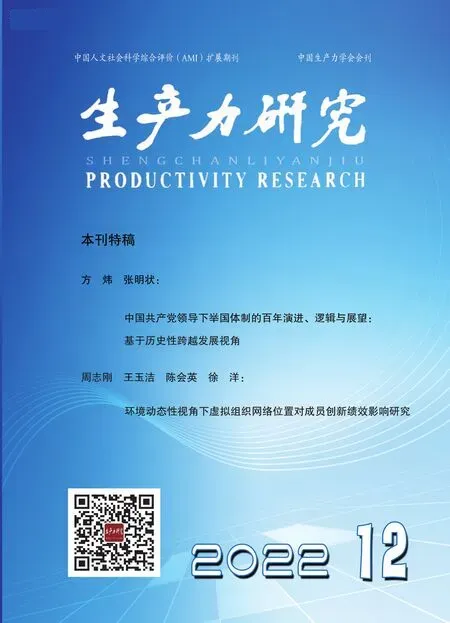環境動態性視角下虛擬組織網絡位置對成員創新績效影響研究
周志剛,王玉潔,陳會英,徐 洋
(山東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590)
全球化競爭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市場影響,使企業面臨諸多挑戰,面對動態變化的組織內外部環境,企業僅僅依靠自身能力往往無法應對市場需求的迅速變化。而虛擬組織是以不同企業間的市場需求為導向,充分利用在線信息技術,通過不同成員企業的知識資源整合,促進合作創新的動態網絡組織。虛擬組織為企業提供了豐富的外部資源,使企業能夠滿足顧客多樣化、個性化的現實需求,進而在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相比于傳統企業組織,虛擬組織作為一種特殊組織形態,具有人才聚集優勢、信息占有優勢和效率提升優勢,可以幫助企業形成核心競爭力。
企業在各種網絡中的位置是企業獲得創新性和異質性知識資源的入口,網絡位置通過影響知識獲取效率間接影響企業創新能力。Collins 和Clark(2003)[1]基于結構嵌入視角,指出處于網絡中心位置的企業可能獲得更多的創新成果;梁娟和陳國宏(2019)[2]證實了在多重網絡嵌入下,集群企業可以獲取豐富的、異質性的知識,實現知識的共享與整合;劉思萌和呂揚(2019)[3]基于企業網絡理論和知識資源理論,分析得出創業企業的網絡嵌入有利于企業進行知識整合與提升創新績效;張保倉和任浩(2018)[4]基于知識獲取視角,論證了虛擬組織知識資源獲取對持續創新能力有積極影響。
通過梳理文獻發現,現有研究對虛擬組織的資源合作特征有較為深刻的分析,但對虛擬組織運作過程中網絡位置如何影響成員創新績效仍不夠明確。因此,厘清網絡位置通過知識耦合影響創新績效的作用路徑,提高企業在動態環境下新知識的獲取和吸收能力,對促進企業創新具有重要意義。而動態能力視角已成為戰略管理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視角之一,因此將環境動態性納入虛擬組織創新研究模型,探討環境動態性對虛擬組織網絡位置-知識耦合-創新績效路徑的調節作用,為解決如何在動態環境下提高企業可持續創新能力提供借鑒。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網絡位置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網絡位置作為企業與組織內其他主體互動關系建立的結果,是指企業在網絡中的位置,反映了企業嵌入網絡獲取額外資源和控制信息傳輸的能力[5]。處于網絡中心地位的企業更容易有效地獲取高質量的創新資源,以期抓住創新機遇,實現卓越的創新績效。相關文獻表明,度數中心度和結構洞是衡量企業網絡位置的重要維度,分別用來表征網絡中的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6]。
度數中心度權衡企業在網絡中充當中心樞紐的程度和對知識獲取與應用的程度[7]。位于網絡中心位置的企業擁有多種多樣的知識來源和知識渠道,有更多機會接觸創新來源、獲取和生成能夠促進企業創新的知識信息[8]。而結構洞就是組織內兩個主體間的非冗余聯結[9]。如果網絡成員表現為連接互不關聯的結構洞的橋梁,便能以較低的成本和風險獲取更為多元化、差異化的知識[10]。組織內企業間的非冗余聯結促進了新穎知識的產生,也使得擁有較多結構洞數目的企業能與多種多樣的擁有不同背景、知識、技能的企業聯結,從而有益于企業進行創新活動。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1a:高水平的度數中心度對創新績效有正向作用效應;
H1b:占據豐富的結構洞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正向作用效應。
(二)網絡位置對知識耦合的影響
知識基礎觀指出,企業創造、積累和應用知識優勢的能力對于獲得競爭優勢至關重要。Chen 等(2021)[11]將知識耦合定義為企業與其合作伙伴之間在知識要素層面協同工作的程度。Yayavaram 首先使用知識耦合來描述不同知識元素相互耦合或隔離的結構,并根據知識元素的關系屬性,將知識耦合劃分為兩個維度:互補性知識耦合和替代性知識耦合[12]。
中心度高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合作伙伴的知識溢出,因為它們能更容易識別多樣性合作伙伴的潛在優勢,能夠更好地獲取組織效應、打破組織慣性、控制認知距離[13],控制虛擬組織中成員的知識和經驗的差異程度,促進知識資源在企業間的交互和共享,進而有利于虛擬組織間知識耦合行為的產生。而占據較多結構洞的企業更容易控制和影響其他網絡節點,利用其構建的非冗余聯結,進入差異化信息領域,獲得相應的異質性知識,有助于其更高效地整理和歸類創新過程中所面臨的多種信息和知識[14],進而產生更好的創意方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2a:度數中心度對互補性知識耦合有正向作用效應;
H2b:度數中心度對替代性知識耦合有正向作用效應;
H2c:占據豐富的結構洞對互補性知識耦合有正向作用效應;
H2d:占據豐富的結構洞對替代性知識耦合有正向作用效應。
(三)知識耦合與成員企業創新績效
進行產品研發等創新活動的企業需要開展廣泛的知識獲取,以儲備必要的有形技術知識和無形能力知識。知識耦合通過聚集知識要素,對現有知識和新知識進行反復利用和整合,從而提高知識的利用效率,促進企業知識基礎的調整或重構[15]。在一定程度上,知識耦合會推動企業在生產、制造流程的改進,從而提高創新績效水平。
成員企業通過外部搜尋從合作伙伴處獲取互補性知識,通過對新知識的學習、消化和吸收,能夠突破現有的思維慣例。此外,企業將搜尋到的新知識與舊知識不斷重構與連接,淘汰舊的或落后的知識元素,構成企業快速轉型升級的內核[16],從而實現快速轉型升級。而當異質性知識無法直接被企業吸收利用時,企業依據現有知識基礎對相似知識元素的搜索可加快知識耦合速度,聚焦關鍵知識領域,快速形成新產品或新服務,提升企業研發效率[17],從而強化企業的核心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3a:互補性知識耦合對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作用效應;
H3b:替代性知識耦合對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作用效應。
(四)知識耦合的中介作用
根據SECI 模型,企業可以通過組織培訓、經驗積累和知識共享等方式獲取知識。同時,企業還需要將這些經驗、知識等進行耦合,形成全面的知識體系和動態的知識架構,才能進一步形成可持續的創新動能。根據知識基礎理論,基于內部知識的封閉式創新模式已不足以支撐企業尋求高性能創新,因此企業迫切需要進行廣泛的知識搜索,探索進入新知識領域,尋找外部知識資源來實現其創新目標[18]。通過與合作伙伴之間的互動,企業能夠獲取新知識以促進知識更替,存儲和吸收合作伙伴的相似性知識資源,實現知識價值增值。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4a:互補性知識耦合在網絡位置對虛擬組織成員創新績效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H4b:替代性知識耦合在網絡位置對虛擬組織成員創新績效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五)環境動態性的調節作用
由組織復雜性理論可知,在知識信息時代,企業面臨著多樣的組織環境和日趨復雜的外部市場環境。環境動態性是企業必須重視的影響因素,其主要強調環境的變化,表現為企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當環境變化迅速且不易被預測時,則具有高動態性[19]。為應對環境動態性的挑戰,團隊更有可能搜索外部知識,不斷獲取新的資源來促進創新的可持續性,而不是依賴于內部資源[20]。相反,當企業處于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時,行業技術發展較慢,企業預測發展趨勢相對容易,多方獲取知識信息的需求較低[21]。此時,企業通常會注重對現有資源的持續開發,對現有知識進行重構和再分配,提高對現有知識的有效利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5a:環境動態性正向調節互補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
H5b:環境動態性負向調節替代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構建以下理論模型:

圖1 結構模型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收集
針對共享經濟下參與虛擬組織中的企業,選擇的樣本企業滿足以下條件:近幾年擁有比較明確的創新合作伙伴;進行產品研發和創新活動;進行產品制造或業務外包活動。問卷主要通過微信、經管之家論壇、問卷星網站和電子郵件等渠道發放。通過問卷星調研網站共發放195 份問卷;以微信、經管之家論壇、電子郵件等信息渠道向企業共發放問卷210 份;此外,向企業發放紙質問卷203 份。問卷發放合計608 份,回收383 份,回收率62.99%,在回收的問卷中,剔除75 份信息填寫不全的無效問卷,總計得到有效問卷30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50.66%。
(二)變量測量
變量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進行測量,從1~5,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網絡位置中心度的測量主要借鑒張保倉(2020)[22]設計的量表,如“本企業比競爭對手更容易獲取關鍵性資源”“本企業在網絡中的地位驅動了其他組織成員的合作意愿”等,共3 個題項。結構洞測量主要借鑒王海花和謝富紀(2012)[23]設計的量表。如“本企業能夠識別與合作伙伴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本企業能夠辨識各個合作伙伴之間的關系的緊密程度”等,共3個題項。知識耦合的測量主要是借鑒梁娟和陳國宏(2019)[2]的成熟量表,其中互補性知識耦合主要包括“本企業與合作企業擁有相似的新知識”“相似的新知識能在虛擬組織中廣泛傳播”等共5 個題項,替代性知識耦合主要包括“本企業能夠通過虛擬組織獲取不同的新知識”“獲得的不同的新知識能及時替代相應的老知識”等共5 個題項。環境動態性測量主要是借鑒陳國權和王曉輝(2012)[24]設計的量表,如“本企業的合作伙伴的行為變化快”“本企業所在的市場和客戶的需求變化快”等,共5 個題項。創新績效測量主要是借鑒Wenpin(2001)[25]設計的量表,如“本企業新產品開發速度較快”“本企業的資源整合及再創造能力有顯著提升”等,共5個題項。
三、數據分析與結果
(一)信度與效度檢驗
信度檢驗采用Cronbach's α 系數來評價量表可靠性和一致性。由表2 可知,所有變量的Cronbach's α 值均在0.7 以上,最小值為0.708,表明量表測度擁有較高的內部穩定性和內部一致性。
收斂效度采用A VE 和CR 來測量各題項之間的關聯程度。如表3 所示,所有變量AVE 值均大于0.5,最低值為0.512;CR 值均在0.6 以上,最小值為0.760,收斂效度良好。區分效度通過AVE 平方根來測定,由表4 可知,各潛變量A VE 的平方根大于其所在行與所在列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因此,各測度項間的區分效度較為理想。

表3 收斂效度檢驗

表4 區分效度檢驗
(二)路徑檢驗
本文主要采用結構方程模型(AMOS 6.0)分兩步來考察網絡位置、知識耦合以及創新績效的假設關系。首先,不考慮知識耦合,檢驗網絡位置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卡方統計量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1.744)小于2,RMSEA=0.049(P 值在0.001 水平上顯著),GFI、AGFI 以 及CFI(GFI=0.939、AGFI=0.916、GFI=0.967)基本都大于0.9,表明此模型的擬合效果整體很好。從關系模型的分析結果(見表5)不難發現,假設H1a、H1b 得到支持。
其次,引入知識耦合,檢驗網絡位置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其中卡方統計量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1.484)小于3,RMSEA=0.040(P 值在0.001 水平上顯著),GFI、AGFI 以及CFI(GFI=0.906、AGFI=0.886、GFI=0.960)基本都在0.9 左右,表明模型總的擬合效果很好。從路徑檢驗的結果(見表5)可以看出,度數中心度、結構洞對知識耦合均有直接顯著正向影響,知識耦合對創新績效也有直接顯著影響。其中,度數中心度對知識耦合的影響路徑系數為0.151(P<0.05)、0.137(P<0.05),假設H2a、H2b 成立;結構洞對知識耦合影響效應的路徑系數為0.360(P<0.001)、0.417(P<0.001),假設H2c、H2d 成立;知識耦合對創新績效影響效應的路徑系數為0.275(P<0.001)、0.384(P<0.001),假設H3a、H3b 成立。為了進一步探究企業網絡位置對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以及檢驗知識耦合是否對創新績效具有間接作用,本研究將在4.3 對知識耦合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

表5 路徑檢驗
(三)中介效應檢驗
運用SPSS 24 的process 置信區間宏程序,進行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分析來驗證知識耦合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6 所示。首先,檢驗互補性知識耦合的中介效應。度數中心度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為0.117 5,間接效應為0.067 0,95%置信區間為[0.0142,0.1498],不包含0,結構洞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為0.141 8,間接效應為0.101 3,95%的置信區間為[0.0382,0.1952],不包含0,這說明互補性知識耦合的中介效應顯著并且為部分中介,假設H4a成立。其次,檢驗替代性知識耦合的中介效應。度數中心度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為0.094 2,間接效應為0.090 3,95%的置信區間為[0.027,0.1764],不包含0,結構洞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為0.103 9,間接效應為0.139 3,95%的置信區間為[0.0666,0.2452],不包含0,這說明替代性知識耦合的中介效應顯著并且為部分中介,假設H4b 成立。

表6 中介效應檢驗
(四)調節效應檢驗
此次研究利用SPSS 24 進行Process 檢驗,驗證環境動態性在互補性知識耦合、替代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之間的調節作用。首先,通過Processv 3.3 插件得出調節系數及顯著性,如表7 所示,環境動態性對互補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關系的調節顯著為正(β=0.100,p<0.1),對替代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關系的調節顯著為負(β=-0.085,p<0.1),因此假設H5a、H5b 得到驗證。然后,根據Jaccard 等人的分類將習慣均值正負一個標準差(±1SD)定義為高低兩個類別,通過繪制調節效應示意圖,以更直觀的方式觀察習慣的調節作用。

表7 環境動態性的調節效應檢驗
圖2 表明,當環境動態性水平較低時,企業互補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之間為正向關系;當環境動態性水平較高時,企業互補性知識耦合對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明顯增強。因此,環境動態性在兩者之間的關系中起到顯著正向調節作用。如圖3 所示,當環境動態性水平較低時,企業替代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之間呈現較強正向關系;當環境動態性水平較高時,企業替代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之間呈現較強負向關系。因此,環境動態性在兩者之間的關系中起到顯著負向調節作用。

圖2 環境動態性在互補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中的調節效應

圖3 環境動態性在替代性知識耦合與創新績效中的調節效應
四、總結與啟示
(一)總結
新時期面對動態環境的不確定影響,虛擬組織形態下的創新合作網絡對成員企業的創新活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鑒于此,本研究聚焦于虛擬組織,研究環境動態性視角下虛擬組織網絡位置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并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虛擬組織網絡位置對成員創新績效存在正向影響;第二,度數中心度對互補性知識耦合和替代性知識耦合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占據豐富的結構洞對互補性知識耦合和替代性知識耦合均有顯著正向影響,但結構洞比度數中心度對知識耦合的作用更強;第三,知識耦合在企業網絡位置與成員創新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第四,環境動態性對互補性知識耦合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而對替代性知識耦合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具有顯著負向調節作用。
(二)啟示
上述結論有以下啟示:
第一,互聯網+新經濟的動態環境下,企業要提升創新能力,關鍵在于嵌入網絡的建設。企業要加強與虛擬組織內成員的聯系,逐步占據虛擬組織網絡中的中心地位,以獲取和支配更多的知識資源,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同時,企業要盡可能地聯結多個不相關的企業即占據豐富的結構洞,通過整合知識鏈上下游企業、競爭對手、科研院所、投融資機構等相關參與方的資源,形成可持續創新能力。
第二,占據虛擬組織網絡中心位置,聯結豐富結構洞是提升企業間知識耦合的效率和質量的關鍵。首先,在虛擬組織網絡框架范圍內,企業可同其他成員企業分享知識與技術,增加獲取其他成員企業相似知識和新知識的機會,提高知識交互和耦合的頻率,精準獲取并內化各種替代性知識。其次,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中,企業要不斷獲取新穎的異質的知識,通過查找學習、理解意會、吸收轉化,將所獲互補性知識與自身知識匹配與整合。
第三,虛擬組織成員通過知識耦合提升創新能力受動態環境的影響。當虛擬組織處于相對平穩、競爭性不強的環境時,企業應積極搜尋與自身具有知識相似的知識,及時替換或更新現有知識,從而促進替代性知識耦合。當企業處于動蕩變化的市場環境時,應在原有知識利用的基礎上,將目光集中于異質性知識的探索,以應對外部環境的動蕩性和不穩定性,實現企業的探索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