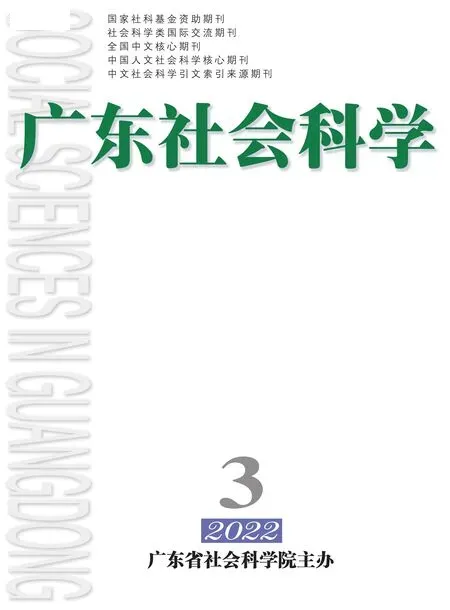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定作人的侵權責任
任九岱
承攬關系作為一種工作完成型的基礎性用工關系,可以與其他形式的用工關系進行嵌套或者組合,形成復合型用工關系,常見的形式如承攬+承攬(即再承攬)、承攬+勞務(雇傭),甚至是更多層級的復合用工關系。(1)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用工關系”是一種廣義的用工關系概念,包括所有涉及到勞務提供的用工關系,包括承攬關系、勞務關系、勞動關系等。此外,考慮到“雇傭”與“勞務”在中國法語境下區分的復雜性,本文對此不進行精細區分,將個人勞務關系視為雇傭關系的一種類型。此種復合型用工關系契合專業分工的時代特征,可以滿足用工者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工作成果專業化水平的現實需要。但此種用工形式在壓縮實際用工成本的同時,也會使得用于保障勞動者安全生產的相應成本被壓縮,這在轉包、分包甚至是多次分包的情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無疑會增加實際勞動者致害的風險,也使得用工主體所獲得的利益與所承受的風險不匹配,致使用工風險被不當轉移和外部化,由此導致相關的侵權損害賠償案件糾紛持續高發。此外,就規范層面而言,《民法典》在繼承原《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0條的基礎上,對定作人侵權制度作出了專門規定,但該制度是以單一承攬關系為原型進行的規則設計,對于復合型用工關系中定作人應否承擔侵權責任,以及承擔何種侵權責任,并未明確。
立足于這兩方面現實因素,下文將通過對司法案例的梳理、學理歧見的辨析,以及在參酌比較法經驗的基礎上,對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定作人的侵權責任予以探究。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所探究的復合型承攬關系,限定于初始用工關系為承攬關系,再嵌套其他的用工關系的類型,如再承攬、先承攬后雇傭等形式,而所指稱的定作人侵權責任,也僅限定于初始承攬關系中定作人所應承擔的侵權責任。
一、裁判案例的梳理:兩種侵權責任承擔模式的角力
在司法實踐中,裁判者關于定作人在復合型承攬關系中所承擔的侵權責任,存在嚴重的裁判分歧。這不僅體現在不同審級的人民法院在審理同一案件的情形,也體現在類案的情形。
在時虎、劉軍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2)參閱(2019)皖民再15號再審判決。,一審法院認定利達公司(定作人)明知雇主沒有消防工程承包資質和相應的安全生產條件,仍然進行發包,適用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要求定作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二審法院則以案涉的事故現場不屬于包工頭所承包的工作場所為由,認定在從事案涉工程活動時受害人與包工頭均受雇于利達公司,應由利達公司單獨承擔90%的責任。再審法院則認為,在從事案涉承攬活動時,包工頭與受害人存在雇傭關系,包工頭與利達公司存在承攬關系,定作人存在選任過錯,且提供錯誤的水壓信息,定作人與雇主分別承擔40%和50%的侵權責任。而在“汪成祥、林永憲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3)參閱(2017)粵民再514號民事判決。中,一審法院適用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要求定作人與雇主承擔連帶責任;二審法院認為定作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雇主(承攬人)沒有相應資質或安全生產條件而將案涉工程交由其二人施工,存在選任過失,依據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0條的規定,定作人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具體為雇主所承擔侵權責任的30%。再審法院則認為,由于定作人將本案工程發包給沒有相應施工資質的雇主進行施工,應當適用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對受害人的人身損害依法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通過對這兩個較為典型再審案件的梳理,不難窺知在審理此類案件糾紛時,不同審級法院在法律適用方面所存在的嚴重分歧。
而在類案的情形下,裁判觀點大體而言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定作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另一種則是定作人承擔按份過錯責任。在“戴祖芬、湖南宇內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4)參閱(2019)湘01民終10655號民事判決。中,二審法院認為,定作人明知分包人易達明,將涉案工程再分包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戴祖芬,且在施工管理過程中未盡到安全監管責任,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另有其他法院也持有持同樣的裁判觀點,即以發包人將工程發包、分包給沒有資質、不具有安全生產條件的承包人為由,要求定作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5)參閱(2021)遼01民終7947號民事判決,(2020)魯14民終1677號民事判決。而在“謝偉峰、朱沈華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6)參閱(2020)浙04民終1224號民事判決,(2020)鄂06民終1494號民事判決。,二審法院認為,定作人明知承攬人不具備相應資質,且要求護欄安裝在平臺外側導致需高處搭架作業,存在選任和指示上的過失,應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類似的案例可參見“楊代偉與江朝祿、重慶愛莎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7)參閱(2020)渝01民終4559號民事判決。“馮永輝、馮中成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8)參閱(2020)川16民終752號民事判決。等。
這些案件基本上均為“工程分包或者轉包+雇傭”的用工模式。關于此處的發包或者分包關系,依據《民法典》第808條的規定(9)“本章(建設工程合同章)沒有規定的,適用承攬合同的有關規定”,“適用”這一立法技術即表明立法者對建設工程合同與承攬合同的關系定位,即“建設工程合同為承攬合同的一種,屬于承攬完成不動產工程項目的合同”。參閱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中)》,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1490頁。,本文將其統一界定為承攬關系,因而可將其統一簡化為“承攬+雇傭”的模式。雖然此類先承攬后雇傭的復合用工關系,不能涵蓋復合型承攬關系的所有類型,但卻是實踐中應用相對廣泛、較易滋生糾紛的類型,通過對該類型的剖析,無疑可以獲得對整個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定作人侵權責任承擔的有益法制經驗。
此種復合型用工模式再附加“定作人明知或者應知接受發包或者分包的主體不具備相應的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這一要件事實,正好滿足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所對應的構成要件,因而在此情形下,應否適用該條規范要求定作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往往成為裁判者必須要回應的問題。與此同時,該案件事實亦可為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0 條(《民法典》第1193條的前身)規定的構成要件所涵攝,進而要求定作人承擔與選任過錯相適應的侵權責任。從規范分析的視角進一步來看,該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構成要件要素中包含了“選任過錯”的內容,而該司法解釋第10條的適用并不限于單一承攬關系,亦包括復合型承攬關系的情形,這使得兩條規范的適用范圍存在重疊與交叉,而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于由此所帶來的規范沖突問題,未予明確,這也是導致司法實踐中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存在嚴重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引申出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連帶賠償責任與按份過錯責任在法律適用上區分的關鍵何在,以及這兩個法律規范的適用范圍應如何廓清;其次是這兩種侵權責任承擔模式的比較,何者是目前制度環境下更優的制度選擇。應該說,這兩個層面的問題是相互對照的,侵權責任的具體承擔模式是法律規范適用的法效果,而侵權責任的承擔模式的優劣也會反過來影響侵權法規范的適用,因而下文將對此分別予以探究。
二、兩種侵權責任承擔模式的適用分歧:“共同過錯”的認定
依據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只要證明定作人“明知或者應知接受發包或者分包的主體不具備相應的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即認為其違反了《安全生產法》第16條、第86條,以及《建筑法》第22條、第29條等所規定的法定義務,與造成實際損害后果的雇主具有共同過錯,(10)參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171頁。應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無疑構成侵權法中“共同過錯”認定的特別規則,而且是一種較為寬松的認定標準。而依據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0條(現在的《民法典》第1193 條)的規定,如果定作人存在前述選任過錯,通常不會被認為存在“共同過錯”,承擔的也是與過錯相適應的按份責任(11)參閱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2309頁。鄒海林、朱廣新:《民法典評注侵權責任編1》,北京: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39頁。。由此,不難發現這兩條法律規范適用分歧聚焦于,此種關系結構中“共同過錯”的認定問題。
共同侵權行為中的共同過錯既包括共同故意,也包括共同過失。(12)參閱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01頁。在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形下,因為存在共同的意思聯絡,由定作人承擔連帶侵權責任,是顯而易見的,無需展開。而在復合型承攬關系中,是否存在共同過失,進而要求定作人承擔連帶責任,則是較為復雜的問題。因而關于復合型承攬關系結構中“共同過錯”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共同過失”的認定問題。
關于認定“共同過失”的標準,存在明顯的理論分歧。有觀點認為,數個行為人共同從事某種行為,基于共同的疏忽,造成他人損害,且數個加害人的過錯內容相同或者相似,即構成共同過失。(13)參閱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下)》,第2245頁。另有觀點認為,共同過失是指各加害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具有共同的預見性,而且是基于對各加害人共同的注意義務的違反。(14)參閱曹險峰:《數人侵權的體系構成——對侵權責任法第8條至第12條的解釋》,《法學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頁。楊麗珍:《論定作人之責任》,《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第144頁。還有學者認為,當行為人基于一致的意思而行為時,能夠預見共同作出的行為會導致他人損害,并且可以避免這樣的損害發生卻并未避免時,便表現為共同過失。(15)參閱葉金強:《共同侵權的類型要素及法律效果》,《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第68—69頁。另有觀點指出,共同過失則是指在協同行為中對相同注意義務之違反,對損害結果無意思聯絡,但對行為的發生存在意思聯絡。(16)參閱鄒海林、朱廣新:《民法典評注侵權責任編1》,第39頁。有法院則認為,共同過失實施的行為同樣構成共同侵權,而共同侵權行為的認定不以意思聯絡為必要,當事人行為具有共同關聯性時即可認定。(17)參閱(2021)京02民終4261號民事判決書。
前述就“共同過失”標準的討論,實際上是為了解決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的理論基礎問題,即是否存在共同過錯,使得各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一個整體,對外承擔連帶責任。(18)參閱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研究上卷》(第二版),第529頁。這些標準要么強調的是“一致行動的意思”,強調的是行為的共同性或者協同性,要么突出的是共同預見性,但對共同預見的內容究竟系侵權行為的發生抑或損害結果的發生存在分歧,還有就是強調的是對相同或相似注意義務的違反,即過錯內容存在相同或相似性。這些標準實質上都服務于證成數個侵權行為的共同性、整體性,以解決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的基礎問題,而這些“共同過失”的認定標準,能否妥當適用于復合型承攬關系中不無檢視的余地。
承攬合同是以交付特定工作成果為標的的勞務之債,承攬人對承攬活動的進行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而定作人的定作、選任、指示通常具有事前性,由此定作人對承攬活動的介入或者控制較弱。由于存在明顯的時空間隔,在侵權行為發生之時,定作人通常不在現場,甚至可能與實際從事承攬活動的雇主相互陌生,此時就很難認定定作人與雇主對侵權行為的發生存在協同性或者存在共同行為,尤其是在多次分包的情形下。此外,定作人與雇主在承攬活動中所應盡到的注意義務顯然不同,前者主要是與定作、指示或者選任相對應的注意義務,主要存在于承攬活動開始之前的階段,而后者的注意義務則更廣,包括對勞動者的安全保障義務、采取相應的安全保護措施等,存在于整個承攬活動中,可以說兩者的注意義務的時間階段、場景性均有較大差異,難謂其一概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過錯內容。(19)關于兩者注意義務具體內容的差異,參閱程嘯:《侵權責任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432—433,438—439頁。至于共同預見性,在定作人通常與實際施工者互不隸屬、相互陌生的情形下,對于侵權行為的發生抑或損害結果的發生是否存在可預見性,同樣不無質疑的余地,在司法實踐中定作人常常以自己與受害人既不認識,也不存在控制或者支配關系為由提出抗辯,因此僅憑欠缺相應的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就由此推論出存在對侵權行為或者侵權結果的共同預見性,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而且亦有觀點認為,定作人此時不應承擔連帶責任,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定作人和承攬人對第三人損害的發生通常不存在共同的加害目的,通常也不存在共同的意思聯絡,而且對此也難以舉證證明。(20)參閱姬新江、王燕軍:《論定作人的指示過失責任》,《當代法學》2007年第1期,第107頁。
在此種復合型承攬關系中,關于“共同過失”的認定存在復數解釋方案,各個解釋方案寬嚴尺度不一,但每一種解釋方案均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究竟以何者為當,顯然不是單純通過概念界定和邏輯演繹即可完成,此系法政策問題,應考慮特定解釋方案的社會效果的預期或者作目的性考量。(21)參閱楊仁壽:《法學方法論》(第二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80頁。而這就需要回到一個原初問題,即連帶責任模式與按份過錯模式的功能區別問題。二者重要的功能區別在于對部分行為人喪失清償能力的風險的分配,連帶責任制度是將該清償不能的風險由每一個具有清償能力的行為人來承擔,而按份責任則是由受害人承擔部分行為人清償不能的風險。(22)參閱葉金強:《共同侵權的類型要素及法律效果》,第69頁。由此,不難發現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背后的法政策考量是,通過將部分行為人清償不能的風險分配給其他具有清償能力的侵權人來強化受害人的救濟。那么此種連帶責任模式是否會損及其他價值目標的實現,又會對侵權行為的預防發生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其本身是否構成一種有效的受害人的救濟方式,均需要進一步辨明。
但目前存在一個特殊情況值得關注,在2020年新修正的《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未被保留,而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并未作出專門說明,這是否就意味著定作人未來在此種情形不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實際上構成多數人侵權規則的具體化,因而縱使新的《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不再保留該條規定,通過適用《民法典》第1168條的“共同侵權”條款,亦可產生連帶賠償責任的法律適用效果。而且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僅是囊括了復合型承攬關系結構中“共同侵權”的部分情形,因而該規則是否保留,對于該問題的探究均不產生實質性影響。與此同時,對于該問題的探究還存在兩重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是因為該規則廢止所帶來的溯及力問題,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相關的法律爭議(23)承認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效力的判決,參閱(2021)皖17民終452號民事判決書。不承認適用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效力的判決,參閱(2021)粵13民終310號民事判決書。;其次未來制定的《民法典侵權責任編司法解釋》是否會重新規定該規則,也未可知。綜合前述因素,在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被廢止的背景下,討論在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定作人是否存在共同過錯,應否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仍有重要價值。
三、行為激勵視角下的兩種侵權責任承擔模式的比較
法律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它通過責任的配置和賠償責任的實施,內部化個人行為的外部成本,誘導個人選擇社會最優的行為,(24)張維迎:《法律、信任與責任》,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63頁。在侵權法中就表現為激勵侵權行為人和被侵權人各自盡到最優注意義務,使社會總成本最低(25)參閱汪華良:《基于合同關系的替代責任——一個法律經濟學視角》,《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第63頁。。這兩種侵權責任承擔模式顯然會對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各方主體的行為產生不同的激勵效應,因而有必要對此進行分析。
就雇員(受害人)而言,無論是按份賠償責任還是連帶賠償責任,均不會對其自身風險的防免產生實質性影響,因為其作為自身安全的直接負責者,發生人身損害違背正常人的理性,其對自身損害的發生持厭惡的態度。換言之,無論是按份賠償責任還是連帶賠償責任均不會對其風險防范產生實質性的激勵作用。
就定作人(發包人或者分包人)而言,無論是承擔按份過錯責任還是連帶賠償責任都是建立在其對損害的發生存在過錯的基礎上,而且兩種模式下的過錯內容及其認定大體相同。按照過錯責任對行為人的激勵效應,只要定作人盡到應盡的注意義務,即可免于承擔最終的損害賠償責任,當然連帶賠償責任模式可能會導致定作人支出過度的預防成本,進而產生“預防剩余”問題。但是這兩種侵權責任模式對定作人盡到注意義務的激勵效應可能只是程度之別,并無本質差異,對于提升實際勞動者的勞動安全狀況,以及避免損害的發生并無實質改善。
而就雇主(承攬人)而言,承擔按份責任抑或連帶賠償責任會對雇主(承攬人)的注意義務的履行產生顯著不同的激勵效應。如果是采取連帶賠償責任的模式,只要定作人明知或者應知雇主不具備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此時就需要對此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種連帶的方式將使得原本由雇主直接應當承擔的侵權責任部分或者完全轉移給定作人承擔,這種預期會助長雇主(承攬人)的僥幸心理,不利于激勵其積極履行其應盡的注意義務。相反如果采取按照按份過錯責任模式,即按照過錯的程度和原因力大小,來具體分配應承擔的侵權責任,由于在復合型承攬關系的情形下,雇主相較于定作人對雇員的控制力度更強,對危險的發生具有更強的預防能力,雇主應盡的法定注意義務的范圍更廣、程度更高,雇主若沒有盡到此種注意義務,對最終損害發生的過錯程度更高、原因力更大,最終承擔侵權責任也更重,這會促使其采取必要的措施,積極履行應盡的注意義務,以避免或者減少損害的發生。美國法的經驗也表明,連帶責任的分攤模式,即受害人必須向那些財力有限的加害人要求賠償,而非全部由經濟實力最強的加害人承擔,使得美國的事故死亡率下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其加強了對財力有限的加害人的激勵,從而降低了事故的發生率。(26)[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六版),史晉川、董學兵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7頁。而且通常而言,在復合型承攬結構中,與損害發生距離最近的加害人,往往是加害人一方中經濟實力最弱的一方,同時也是僥幸心理更強、風險意識更弱的一方,因而強化其侵權責任的承擔對于最終降低風險和損害程度是大有裨益的。
由此觀之,在“承攬+雇傭”復合型承攬關系背景下,由定作人對雇員的損害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模式,雖然出發點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和督促定作人審慎選任適格的承攬人,但此種模式卻可能損害其他價值目標的實現,降低了對雇主(承攬人)履行應盡注意義務的行為激勵。而此類糾紛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受害人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所遭受的后果常常是非死即殘,這對其家庭、對社會穩定都會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如果說在此情形下,事后的救濟是重要的價值目標,那么事前的對侵權行為的預防可能更為重要。因而,從強化侵權行為預防、提升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勞動者的安全保障水平等角度出發,顯然按份過錯責任模式是在當下的現實國情和制度約束條件的更優的選擇。
四、比較法視野中的定作人連帶責任模式分析
關于復合型承攬關系結構中主要定作人所應承擔的侵權責任,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不僅設置專門的法律條文,而且也積累了相當的裁判案例,對其制度模式進行梳理,亦可提供有益的鏡鑒。
(一)相關法律規范的梳理:職業災害連帶補償模式
我國臺灣地區“民法”除了設有專門條文規定定作人責任外,還在“勞動基準法”第62條、第63條,以及“職業衛生法”第25條、第26條等法律中規定了事業單位招人承攬以及再承攬情形下,對因從事承攬活動而遭受職業災害的勞工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該法中的“事業單位”專門是指各業雇用勞工從事工作的機構,其在交付承攬或者再承攬用工關系中,承擔的是定作人的身份。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兩種情形:(1)依據“勞動基準法”第62條、“職業安全法”第25條第1款,以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31條的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承攬人或者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的勞工,均應與最后承攬人,連帶承擔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該規定實質上是,只要是交付他人處理就需要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無論交付承攬的層級如何,均應視為雇主而受拘束,其制度目的在于在職業災害發生時,使得勞工或其家屬多一層補償保障,避免因轉包再轉包后的雇主無力補償,而失去保障。(27)參閱林豐賓:《勞動基準法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287—288頁。(2)依據“勞動基準法”第63條第2款、“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第2款的規定,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對于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例如事業單位的安全督促義務、危險情況的事前告知義務、采取有關勞動安全衛生的必要措施的義務等,致承攬人或者再承攬人所雇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由此不難發現,我國臺灣地區法律在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或者再承攬時,對勞工的職業災害采納的是連帶職業災害補償模式,以此強化對受害者的救濟。不過需要指明的是,職業災害補償不同于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是兩種不同的責任形態,前者主要是通過職業災害保險來解決,可通過職業災害保險抵充雇主所應承擔的職業災害給付,不以過錯為構成要件,存在法定限額,而后者則是通過民法的損害賠償責任制度來實現,但以過錯為要件,奉行填平原則,賠償范圍更廣。(28)參閱王澤鑒:《侵權行為》(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4—25頁。
(二)學理以及司法實踐中對職業災害連帶補償模式的反思
在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實踐中,已經出現對事業單位在承攬或者再承攬情形承擔連帶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的反思。有學者就明確指出,此種制度模式的不妥之處在于,事業單位支付的價金已經包含責任風險在內,而且職業災害的發生是由于承攬人疏于防范所致,應由承攬人承擔,不應再轉嫁給事業單位,事業單位不應對無從掌握或者監督事項所生之職業災害負責,這也會不當免去依法本應對該職業災害負責者的警惕,對社會整體利益也是一種損害。(29)參閱林豐賓:《勞動基準法論》,第289頁。
同時,在臺灣地區的裁判實踐中,部分裁判者對事業單位在交付承攬或再承攬情形下承擔連帶補償責任已經采取限縮適用的立場。一種裁判觀點是通過對承攬事項的類型區分來限制定作人的責任承擔。如果是將其經營內容交付承攬,則應承擔連帶補償責任;但如果事業單位是將所經營的事業之外工作的交付他人承攬,即屬于與該機構經營內容無關的事務,對于此種類型的承攬,原則上作為定作人的事業單位不應承擔連帶職業災害補償責任,(30)參閱鄭津津:《承攬關系中“原事業單位”之連帶職災補償責任》,《月旦法學教室》2019年10月,第31—32頁。另外一種裁判觀點則提出了事業單位對風險的防范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標準(31)參閱我國臺灣地區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107年度勞上字第16號判決。,具體而言,只有當事業單位對其事業、營業具有專業知識,具備期待可能性時,才應當其承擔防止職業災害的責任。如果并非事業單位所熟悉的活動交付承攬,那么對于該承攬活動的危險性,并非該事業單位所預先理解或控制,不能僅以該項危險活動與該事業單位有所關聯,即強求該事業單位負擔此等危險責任。事業單位將所經營事項以外的工作交付承攬,往往就表明其對從事該活動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一般也無法期待事業單位具有預防此種職業風險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觀察,這兩種裁判立場實質并無本質區分,皆是為了緩和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或者再承攬情形下承擔的連帶補償責任的制度剛性,避免過分加重其責任承擔。
(三)兩種邊帶責任模式的比較
職業災害連帶補償模式弱化了依賴個人責任財產承擔民事侵權責任所可能導致的清償不能的風險,確實有利于受害人救濟的實現,但此種責任模式也在某些情形,不當加重了事業單位(定作人)的責任負擔,因而司法實踐中也呈現出對該模式限制適用的趨勢。不過總體而言,該責任承擔模式仍是一個運轉良好、發揮積極作用的制度模式。可以說,正是因為已經建立起較為成熟的勞工保險體系和勞工職業災害救濟體系,在此基礎上,由事業單位連帶承擔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的制度模式才不會過分加重事業單位的責任負擔,因為其得借助職業災害保險來事先分散風險和轉移損失。
而從我們自身的制度現實出發,雖然目前已經形成了多元侵權責任救濟體系,但此種侵權責任救濟體系屬于一種倒金字塔的賠償補償模式(32)參閱王澤鑒:《侵權行為》(第三版),第37頁。,主要由侵權行為法承擔分配損害的功能。在社會保障制度覆蓋范圍較窄、承保力度不夠、民眾購買商業保險的意識不強,全社會損害風險分擔機制不夠健全的條件下(33)參閱王竹:《侵權公平責任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1頁。,要求定作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可能會過分加重定作人的負擔,影響到承攬用工活動的健康發展,而且可能對造成對定作人的不公平,因為其對損害發生的過錯與原因力通常弱于其他用工主體。此外,司法實踐經驗也表明,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所確立的連帶賠償責任模式,裁判分歧嚴重,二審、再審的案件數量多,直接影響到受害人獲得及時、有效的救濟。因此,從現實的制度條件出發,連帶責任模式并非更優制度選擇。
五、《民法典》法律規范的適用
通過前述分析不難得出結論,按份過錯模式是在當下制度實踐約束條件下,更優的制度選擇方案。這也為確定“共同過失”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外部論證依據。由此,在復合型承攬關系的情形下,應當從嚴把握“共同過失”的認定標準,在定作人的過錯程度、內容,與雇主或者再承攬人的過錯不處于同一個層次,不應當認定存在“共同過失”,而應適用《民法典》第1193條和第1172條的規定要求定作人承擔與過錯相適應的按份責任。具體而言,如果定作人僅是存在定作、選任、指示過錯,該過失行為與最終損害發生距離較遠,原因力較弱,那么此時不應當將其納入“共同過失”的范疇。當然,如果受害人一方能夠舉證證明,定作人與雇主或再承攬人對損害發生的過錯大體相當,處于相同的層次,例如定作人施工現場發出有過失的指示,并因此造成損害的發生或者明知承攬事項存有重大危險仍強令承攬人予以執行,此時承攬人對承攬事務的違法性或重大危險性主觀上也是明知的,這自然滿足“共同過失”的認定要件(34)參閱姬新江、王燕軍:《論定作人的指示過失責任》,第109頁。,此時仍應當適用《民法典》第1168條的規定,要求定作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關于溯及力問題,根據前文的分析,無論是否廢止該條規范實質上并不影響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定作人侵權責任的認定與承擔,因而前述論證結論亦應適用,即應當嚴格限制連帶賠償責任的適用。而針對未來制定的《侵權責任編司法解釋》,則不宜再重新規定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的內容,應當通過適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關于多數人侵權的相關規則以及定作人侵權責任的規則來處理此類糾紛,同時在認定存在“共同過失”適用《民法典》第1168條時,要強化裁判者的論證說理義務。
當然需要承認的是,按份過錯賠償模式并非解決復合型承攬關系結構中受害人救濟最優的模式,這只是在當前制度約束條件相對更優的選擇。就受害人的賠償而言,完善保險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對于受害人一方的救濟而言是更為高效的,這就在呼喚建立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強化民眾購買商業風險來進行損害的社會分擔(35)參閱王竹:《侵權公平責任論》,第12頁。。為了解決復合型承攬關系中勞動者保護和救濟問題,單純依靠末端的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是不足夠的,這就需要一種多維度、綜合治理的思維,需要其他制度相配套,例如擴充定作人的注意義務的范圍、加強勞動安全生產的行政監管力度,以及推動建立和完善承攬型用工關系的保險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