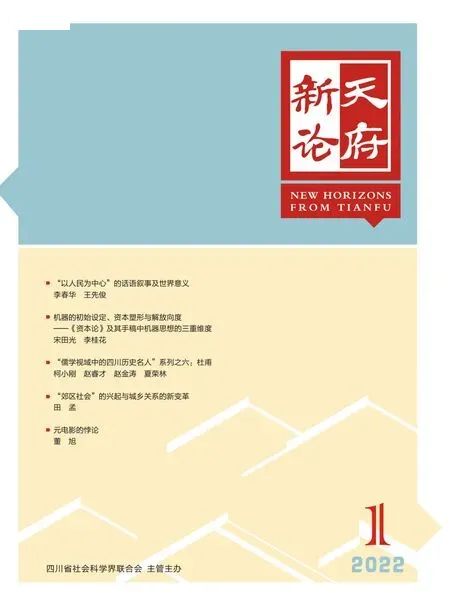論《資本論》的定性與讀法
盧斌典
《資本論》自問世以來,關于這部著作的定性和讀法一直爭論不休,成為一樁難解的學術公案。有人認為這是一部純粹經濟學著作,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哲學著作,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歷史學、人類學或文學著作。基于不同的立場,對《資本論》的解讀也不同。近來,張旭和常慶欣教授重審這樁學術公案,主要成果有《〈資本論〉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駁〈資本論〉哲學化》(1)張旭、常慶欣: 《〈資本論〉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駁〈資本論〉哲學化》,《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1期。(簡稱“張文1”)、《〈資本論〉哲學化解讀再研究》(2)常慶欣、張旭: 《〈資本論〉哲學化解讀再研究》,《天府新論》2020年第1期。(簡稱“常文”)、《再論〈資本論〉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兼答雪婷“論〈資本論〉的哲學根基”中的困惑》(3)張旭: 《再論〈資本論〉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兼答雪婷“論〈資本論〉的哲學根基”中的困惑》,《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簡稱“張文2”)。他們堅稱《資本論》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駁斥對《資本論》的哲學化或存在論解讀,激發了學界的思考。不容置疑,嚴謹的、客觀的、公正的學術探討有助于深化對《資本論》的理解,促進學科間的對話,推動對《資本論》的研究。但是,這兩位作者在批判他人的觀點時存在誤解,在論證時邏輯混亂甚至自相矛盾,在理解《資本論》時存在偏差。筆者不揣冒昧,撰文與兩位教授商榷。
一、《資本論》的定性:是政治經濟學著作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
在以往的研究中(包括張旭和常慶欣教授的研究中)存在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即《資本論》究竟是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這個問題困擾著研究和對話的深入發展。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明確寫著“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不是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也明確指出,他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交換關系,而不僅僅是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些學者罔顧經典文本中的闡述,僅僅依據自身學科或自己的理解(4)據筆者的了解,在政治經濟學界也有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爭議,主要有“生產方式論”“生產關系論”“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論”等。不能漠視這些爭論而將《資本論》簡單理解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去建構《資本論》的性質問題,顯然失之偏頗。關于什么是“批判”,張文2中做了闡發。常慶欣和張旭教授認為,批判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評論者做出實事求是或客觀的評價和評論;第二層含義是對一個人或一件事不同意,認為他們不符合規范和標準,用尖銳的詞句表達。(5)張旭:《再論〈資本論〉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兼答雪婷“論〈資本論〉的哲學根基”中的困惑》,《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他們認為,馬克思是在第一層面上使用“批判”的含義的。也就是說,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做了實事求是或客觀的評價,吸收了其合理的成分,揚棄了不合理的成分。于是,否定性的批判變成了肯定性的批判,非連續性的關系變成了連續性的關系,歷史科學變成了一門實證科學,批判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工具或手段。如果我們按此邏輯回溯哲學史或批判史,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馬克思對黑格爾、費爾巴哈、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批判,似乎都變成了一種繼承性的和缺乏革命性的批判,整個批判史都帶上了折衷主義的色彩。顯然,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康德和黑格爾的批判絕不是妥協的,馬克思的批判也不是妥協的。馬克思的批判充滿了戰斗性,他從現實歷史和現實的人出發,對一切權威進行無情的批判,追求“此岸的真理”。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其實有兩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批判,第二重意思是對整個政治經濟學或者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有關的學問所做的批判。正如孫正聿教授所說:“‘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資本論》的副標題,馬克思極為醒目地提示我們:《資本論》的出發點是不贊同‘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理解和闡釋,是把‘政治經濟學’作為‘靶子’而構成其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揭露‘政治經濟學’的‘病根’才會產生馬克思的《資本論》;認清‘政治經濟學的病根’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正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構建了以《資本論》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6)孫正聿:《〈資本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1期。
按照常慶欣和張旭教授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對《資本論》的理解,“《資本論》以商品作為出發點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社會性、物質性,并說明新社會形態的萌芽是如何在資本主義這種暫時性的社會形態中萌發的,以及在何種前提條件下,這些萌芽會真正成長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形態。《資本論》的研究,是抽象分析和經驗研究完美結合的典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和充實,是辯證方法的具體化和實例化”(7)常慶欣、張旭:《〈資本論〉哲學化解讀再研究》,《天府新論》2020年第1期。。通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得知:《資本論》是以商品為基點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多種性質,《資本論》要揭示新的社會形態的萌芽和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研究是抽象與經驗的統一、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和辯證方法的具體化。我認為,這種理解是完全實證化的理解,與曾經的蘇聯式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有驚人的相似。他們認為馬克思對價值和價格關系的分析是一般制衡的特例,而不懂得價值形式的辯證法。他們忽略了馬克思對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關注,也忽略了《資本論》與前期著作的區別,事實上將《資本論》理解為一部實證科學著作,抽離了馬克思的批判性和人文關懷。他們對《資本論》的方法的理解也是教條的,而非辯證的,大大削減了馬克思文本的理論深度。他們只把馬克思視作一位經濟學家,而馬克思的方法論也因此淪為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按照他們的理解,馬克思似乎并不比他所批判過的政治經濟學家高明多少。張旭和常慶欣教授躬耕于或致力于論證《資本論》是一部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我們可以反問幾句:難道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嗎?難道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不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嗎?雪婷博士明確指出,他們混淆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的方法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前提進行批判,解蔽了商品、貨幣、資本等經濟范疇所表征的現代社會人的存在方式。因而,無論從研究對象還是從研究方法,《資本論》都不應該僅僅被視為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8)雪婷:《論〈資本論〉的哲學根基——兼與張旭、常慶欣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12期。。
張旭和常慶欣教授在張文1中用較多筆墨介紹了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分析,然而,他們卻忽視了阿爾都塞對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剖析。基于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援引阿爾都塞的理解來重新審視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區別。
要理解阿爾都塞的觀點,必須理解他所提出的科學與意識形態斷裂、總問題和本質切割等觀點。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偉大發現之一是剩余價值理論。而剩余價值并不是馬克思的獨創發明,它隱藏在先前政治經濟學的論述中。然而,先前的政治經濟學只是在分配、地租和利潤上察覺到了剩余價值所在,卻未能科學、完整地揭示剩余價值的來源和性質。正如阿爾都塞所說,古典經濟學生產了一個新問題,卻沒有看到自己變換了場所,仍停留在舊的問題領域,局限于舊的視野。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看不到自己在做的東西,它的回答是圍繞著舊的問題展開的,就如同福柯所說的“認知型”,存在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可能性。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不一樣,它提出了新的總問題和對象,將政治經濟學本身作為一個對象去考察,提煉出了剩余價值理論。阿爾都塞指出:“‘批判政治經濟學’意味著提出一個同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的新的總問題和新的對象,也就是把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本身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但是,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是通過它的對象獲得規定的,因此,從一個與舊的對象相對立的新的對象出發的批判,可以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存在本身的批判。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只有對政治經濟學本身提出問題,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立的理論要求以及它為了發展成為理論而在社會現實中進行的‘切割’提出問題,才能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提出問題。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徹底的:它不僅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提出問題,而且對政治經濟學本身提出問題,作為自己的批判對象。”(9)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176頁。阿爾都塞認為,將馬克思簡單界定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是錯誤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是一種同質空間,它的思想基礎是有關經濟人的意識形態人本學。 《資本論》作為一種科學,是與意識形態相斷裂的,是反歷史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阿爾都塞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之前的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本質切割”,認為,政治經濟學是在平面空間中通過機械因果性來理解經濟現象和經濟范疇的,是一種經驗主義的總問題,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完成了一場理論革命,驅散了政治經濟學的誤解與迷霧,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性徹底決裂,在特定領域中揭示經濟現象。同時,這種理論革命的背后恰恰存在著哲學的革命。
二、《資本論》的讀法:是政治經濟學解讀還是其他?
《資本論》是一部開放性的著作,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文學、法學等思想,它不會因為某一學科的解讀而封閉。一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通過“不越界”的政治經濟學解讀而抹殺其他解讀的可能性和當代價值,這是失當的。《資本論》所涵蓋的內容不會因為宣示它是“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而減少其豐富性和解讀的多元性,也不會因為對哲學化解讀的批判而消解了對《資本論》的哲學解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馬克思去世之后,一些經濟決定論和機械決定論的解讀給馬克思的《資本論》帶來了“太多的侮辱”。恩格斯和列寧對這些觀點進行了積極的批判。我們可以通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及恩格斯晚年的歷史唯物主義書信和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著作發現他們的反思和澄清。普列漢諾夫也在《資本論》中發現了馬克思的哲學觀和歷史觀。而斯大林推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則恰恰是以政治經濟學解讀為手段、以實證化和機械化的方法來理解和應用《資本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乃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們致力于批駁這種模式并開辟新的解讀空間。其中,阿爾都塞對反思政治經濟學解讀和深化哲學解讀作出了突出貢獻。
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讀法做了認真細致的思考,他主要借助精神分析的一些方法發明了“癥候閱讀法”并主張“哲學與科學的循環閱讀”。阿爾都塞認為,作為經濟學家,閱讀《資本論》,只是提出經濟學的分析和圖示問題,把《資本論》與其他政治經濟學加以比較,但是,假如不涉及《資本論》的對象問題,也就不會知曉《資本論》的對象、思想和方法已經完成了認識論的革命。阿爾都塞指出,斯賓諾莎是歷史上第一位提出讀和寫問題的哲學家,通過想象與真實的區別類比閱讀的本質和歷史的本質。他指出,自己是作為一個哲學家來閱讀《資本論》的,是在探討《資本論》及它的對象的關系以及它的對象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在阿爾都塞看來,《資本論》的對象既區別于古典和現代經濟學,又區別于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當然,阿爾都塞也承認,從單一的哲學視角出發是“有罪的閱讀”。但這不妨礙對真理的探究。他指出,在對《資本論》進行哲學閱讀時容易發生一種錯誤,那就是按照馬克思閱讀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來閱讀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讀法是一種回顧式的閱讀,是通過直接閱讀法來閱讀斯密和李嘉圖等,揭示斯密、李嘉圖等人的發現與空缺、貢獻與不足。而這種讀法讀不出馬克思關注的問題和基于此問題的哲學革命。阿爾都塞指出,還有一種深刻而有用的讀法,那就是“癥候閱讀法”,即基于看到忽視的聯系發現沉默與空白,把文本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建立與別的文本的聯系,思考問題本身而不是更改對問題的回答。這樣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馬克思能看到斯密和李嘉圖等政治經濟學家看不到的東西,因為馬克思占領了新的場所。阿爾都塞用這種讀法來閱讀馬克思的著作,發現《資本論》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阿爾都塞指出:“馬列主義理論包括一種科學(歷史唯物主義)和一種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因此,馬列主義的哲學是無產階級斗爭所必不可少的兩種理論武器當中的一種。共產主義戰士們必須吸收和運用這種理論(科學和哲學)的原則。無產階級革命需要既是科學家(歷史唯物主義)又是哲學家(辯證唯物主義)的戰士們來幫助捍衛和發展理論。”(10)阿圖賽:《列寧和哲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21頁。阿圖賽通譯為阿爾都賽。阿爾都塞意圖通過研究和解讀《資本論》來理解早已被實踐過的文本,洞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性。同時,阿爾都塞在《哲學的改造》中揭示了理解《資本論》的“難題性”,那就是馬克思沒有使用與客體形式和直觀形式相對的哲學概念,而是直接對資本主義的結構以及其他社會形態的結構進行研究,進而探討階級斗爭。馬克思的話語是一種非傳統哲學話語的經濟學話語。阿爾都塞指出:“他建立的是一種具有存在的特殊的現實,這種存在的特殊性同時既要用所有的傳統哲學話語來預設,卻又天生地被排斥在這些話語之外。”(11)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0-191頁。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資本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呢?一些政治經濟學家和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觀點的基本看法是,《資本論》是一門新的科學,而非一門新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資本論》以前的著作(比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德意志意識形態》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哲學的貧困》)中已經成熟,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運用了這種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些學者對這種觀點進行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建構論”(孫正聿)、“雙向建構論”(張一兵)、“內在貫通論”(卜祥記)、“應用和建構論”(白剛)。阿爾都塞認為,《資本論》與馬克思此前的著作,特別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存在“距離和間距”,這種“距離和間距”體現在“結構”中,而不是體現在馬克思對拜物教的批判中。這也是對盧卡奇理論思考的一種反思。阿爾都塞認為:“在哲學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的是意識形態的戰斗,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在同一場所出現是為了戰斗。僅僅堅持斷裂的著作或者僅僅堅持后來的意識形態斗爭的論據,這實際上就是陷入了‘忽視’。這種忽視就在于看不到我們可以讀到馬克思真正哲學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12)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3-24頁,第76頁。于是,我們不禁思考,《資本論》蘊含的真正哲學是什么?這需要回顧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劃分和他所堅持的“哲學與科學的循環閱讀”。阿爾都塞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劃分為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科學,主要負責科學的認識論,而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哲學,主要負責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斗爭。在阿爾都塞那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催生出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落后于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發展有待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化,而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化必須要通過對《資本論》的批判研究。只有理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更好地理解《資本論》,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闡釋和捍衛是一種迫切的歷史任務。在此基礎上,阿爾都塞主張一種循環閱讀:“在《資本論》中鑒別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對象要以鑒別和認識《資本論》本身的對象的特點為前提,而后一種鑒別和認識又要依賴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并要求它不斷發展。不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能真正閱讀《資本論》,而我們同時也應該在《資本論》中讀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這種雙重的閱讀,也就是不斷從科學的閱讀回復到哲學的閱讀,再從哲學的閱讀回復到科學的閱讀是有必要和有成效的,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在這種閱讀中認識到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所包含的這一哲學革命的本質:一次開創了全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革命。”(13)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3-24頁,第76頁。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于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對《資本論》進行哲學閱讀,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我們的重要研究對象。這形成了一個閉環。在閱讀《資本論》時,我們也要找尋馬克思主義哲學,用這種哲學從事對《資本論》的研究,揭示掩蓋科學的意識形態因素。
三、曲解與澄清:對批判所做的批判
張旭和常慶欣教授的批判矛頭名義上指向哲學化解讀,實際上指向存在論解讀。張文1中做了交代,張旭和常慶欣教授贊同三種形式的哲學化解讀(對《資本論》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挖掘、對經濟現象和范疇的哲學解讀、哲學與經濟學的跨學科研究)。但在常文中,卻直接批駁整個哲學化解讀:“對《資本論》所做的哲學化解讀只有使馬克思退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水平上才能成立,它不會為我們理解《資本論》中的核心思想提供應有的幫助”。(14)常慶欣、張旭:《〈資本論〉哲學化解讀再研究》,《天府新論》2020年第1期。這其實反映了兩位作者思想之間的內在差異,或者是兩者在標題、摘要或措辭上的馬虎。兩人認為,《資本論》的哲學化解讀是將《資本論》看作一部哲學著作,認定《資本論》建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用哲學革命闡釋《資本論》的哲學思想,將《資本論》對經濟范疇的分析上升到哲學或存在論層面等。這種界定的問題在于,它混淆了定性與讀法,窄化了其批判對象的思想;同時,它批判的對象也是復雜多元的,這容易使讀者產生困惑和不解。《資本論》是一部哲學著作還是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是一個定性問題,而《資本論》的哲學解讀或政治經濟學解讀是一個讀法問題。將兩者混同起來思考容易引發混亂。在張旭和常慶欣教授所批駁的哲學化解讀中,很大一部分學者并沒有把《資本論》當作一本純粹的哲學著作,他們尋求的是一種哲學化解讀,試圖開辟《資本論》乃至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的哲學空間。鑒于張旭和常慶欣教授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們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資本論》哲學化解讀的困惑和誤解,我們認為,有必要追根溯源,澄清《資本論》哲學化解讀的理論背景、哲學傳統和研究譜系。
首先,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強調《資本論》建構了哲學而不是應用了哲學?這其實是基于對蘇聯式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的反思以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阿爾都塞等思想家的理論成果的借鑒。傳統的蘇聯式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僅僅承認《資本論》應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忽視了《資本論》這一文本所蘊含的哲學體系,容易陷入經濟決定論或以早期馬克思思想解讀成熟時期馬克思思想的理論困境。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反思教科書體系的弊端,批判借鑒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遺產,指出《資本論》建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反思第二國際的失誤,基于特定的歷史條件背景,從哲學層面思考了《資本論》的內涵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可能。盧卡奇認為,從青年馬克思到晚年馬克思,“哲學味”并沒有變少,而是深化了其哲學,達到了哲學的制高點,這一點體現在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克服上。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將《資本論》界定為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論。他根據《資本論》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并結合韋伯的理性化思想推出物化理論,通過總體性辯證法來理解馬克思的哲學,晚期則關注以勞動為主體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他指出:“任何一個馬克思著作的公正讀者都必然會覺察到,如果對馬克思所有具體的論述都給予正確的理解,而不帶通常那種偏見的話,他的這些論述在最終的意義上都是直接關于存在的論述,即它們都純粹是本體論的。”(15)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上)》,白錫堃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637頁。科爾施則反思《資本論》的對象,認為《資本論》是關于社會勞動以及通過無產階級斗爭對束縛這種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破壞的科學。葛蘭西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實踐哲學,主張反《資本論》的革命,認為革命不是依靠一本書的力量,而是靠人類自覺自愿的活動。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通過癥候閱讀法以及哲學和科學的循環閱讀,讀出了《資本論》的對象和方法,讀出了馬克思的術語革命乃至哲學革命,讀出了《資本論》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批判借鑒(而非全盤吸收)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遺產,反思蘇聯式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重新審視《資本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聯系。這也就是說, “建構論”本身就是一種批判、是另辟蹊徑。
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為什么將《資本論》解讀為一種關于“現實的歷史”的存在論?這是基于哲學傳統,受海德格爾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啟發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結果。這種存在論解讀不同于希臘羅馬哲學的本體論、近代西方哲學的認識論以及存在主義的生存論,而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揭示馬克思對存在秘密的破解。古希臘羅馬哲學家追問世界何以存在,他們探討世界的本原,在本體論層面提出了水、火、土、無定、數等假說;經院哲學家們探索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近代西方哲學家們從認識論層面通過思維把握現實存在。哲學家關注的中心一直是“解釋世界”,而馬克思則更多地關注“改變世界”。馬克思在兩條戰線上努力:一方面,在哲學領域清理迷霧,批判繼承黑格爾的頭足倒置和神秘的辯證法,批判費爾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義,批判鮑威爾、蒲魯東、施蒂納等人思想上的漏洞;另一方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戰斗,馬克思反思了斯密、李嘉圖、穆勒等政治經濟學家們思想體系的迷失和錯亂,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提出了商品和勞動二重性以及剩余價值理論,解開了政治經濟學的秘密,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交換關系的運行機制,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局,主張通過階級斗爭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對“現實的歷史”存在的一種質問和解答,是馬克思對時代精神的正確把握,是馬克思拷問世界的新方式。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馬克思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懂得資本主義世界的雙重現實,也就是經濟發展和這種發展需要的架構。海德格爾認為,馬克思從異化深入歷史的本質,通過經濟學話語說明了現代人的生存方式。馬克思不僅關注人的現實存在,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重視人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認為這是人之存在的根基,還關注人的生存狀態,揭露人的異化和物化的現實,主張通過階級斗爭破除無產階級身上的鎖鏈,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這既是“改變世界”的邏輯,也是人的政治存在的應有之義。在馬克思之前,古希臘羅馬哲學家乃至黑格爾都曾涉及存在論。在馬克思之后,雅斯貝斯、海德格爾等人也提出了一套生存論。那么,馬克思是否也存在一套存在論,他的存在論又是怎么樣的呢?他的存在論與他的《資本論》有何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們關心的問題和正在解決的難題。關于《資本論》的“存在論”解讀還可以參見徐赟和莊忠正等學者的論著。徐赟認為,哲學批判是經濟的生存論蘊含的前揭示,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經濟的生存論蘊含的現實揭示,勞動價值論是經濟的生存論意義的內在揭示。(16)徐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存在論基礎》,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莊忠正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揭露物與物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揭露資本主義中人的生存境遇以及個人受抽象統治的邏輯,是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存在論批判。(17)莊忠正:《政治經濟學的存在論批判》,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當然,也有學者從哲學層面反思了存在論解讀,將存在論解讀理解為一種道德批判。王南湜反思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根據《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將《資本論》理解為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發展的存在論,認為這種存在論既是一種客觀揭示,又是一種道德批判。(18)王南湜:《〈資本論〉與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河北學刊》2017年第6期。如果非要明確揭示《資本論》中的存在論的話,筆者認為,《資本論》研究的是一種對象性存在和關系性存在,馬克思既解開了哲學史中存在的秘密,又揭示了人的社會存在和歷史存在。對象性存在繼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思想精華,而關系性存在是《資本論》中的新見。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關系,是一種神秘存在和形而上的怪誕。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要揭示資本邏輯導致的物與物的關系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進而主張揚棄私有制,通過階級斗爭實現人與人關系的解放。一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不對這些哲學傳統深入研究,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關心的問題,不清楚國內外學者對《資本論》所做的哲學化解讀,還妄圖得到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或者僅僅站在自己學科的立場上,抱一種不理解或不懂別人的理解的態度去質疑和批判,這是不恰當的。
最后,哲學化解讀究竟意味著什么?國內外學者是如何進行哲學化解讀的?張旭和常慶欣教授簡單地將“《資本論》是一部哲學著作”這種觀點看作哲學化解讀的重要標志之一。其實,重要的不是將《資本論》視為一部什么樣的著作,而是國內外學者是怎樣進行哲學化解讀的。國外學者對《資本論》的哲學解讀按基本的流派大致可以分為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的解讀、第二國際的解讀、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文本文獻學解讀。恩格斯認為《資本論》是馬克思最成熟的作品,他們的“新世界觀”在《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在《資本論》中成熟。《資本論》的兩大特點是嚴格的科學性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的批判”則蘊涵哲學意味,這種批判是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統一。列寧曾指出,要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必須要弄懂黑格爾的邏輯學。他堅持辯證法、認識論與邏輯學的統一,指出,馬克思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狄慈根在讀完《資本論》第1卷后寫信給馬克思說,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深邃的哲學。伯恩斯坦曾意圖用康德的思想來補充馬克思主義。他將《資本論》界定為一本倫理學著作。斯大林推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則直接將《資本論》理解為歷史唯物主義在政治經濟學中的應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反思第二國際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的弊端,主張從哲學層面審視《資本論》。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論》的解讀是一個復雜的“星叢”,主要包括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晚期馬克思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東歐馬克思主義、日本馬克思主義等各式各樣的解讀。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總體性辯證法來理解《資本論》。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都是在哲學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中理解《資本論》的,他們開辟了一種不同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理論。新實證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分析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流派從價值形式、認知科學和分析學等維度闡發《資本論》的科學性。晚期馬克思主義學者如詹姆遜和大衛·哈維重讀《資本論》,從現代勞動結構和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維度解析金融危機后《資本論》的當代價值。福斯特、齋藤幸平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者從物質變換斷裂角度探析《資本論》中的思想。東歐的科西克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統一和具體辯證法去理解《資本論》。日本的廣松涉則從物象化入手解析《資本論》中的哲學。美國的奧爾曼從內在關系哲學探究《資本論》中的思想。此外,還有一批文本文獻研究者通過文獻梳理和文本比對鉆研《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與《資本論》哲學思想的異同。國內學者主要從純粹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等角度闡發《資本論》的哲學思想。白剛從純粹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三重維度系統梳理《資本論》哲學解讀模式的演變和貢獻,重新闡釋了《資本論》哲學化解讀的當代路徑。純粹哲學是邏輯基礎,指的是大寫字母的邏輯學;經濟哲學是現實內容,指的是批判的實證主義;政治哲學是價值規范,指的是關于拜物教的革命性。(19)白剛:《〈資本論〉哲學的三大解讀》,《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比如,孫正聿、鄒詩鵬、白剛、王慶豐、孫樂強等學者是從純粹哲學或存在論去解讀《資本論》的,張雄、魯品越、宮敬才、張一兵、唐正東等教授是從經濟哲學去解讀《資本論》的,而段忠橋、李佃來、程廣云等學者是從政治哲學去解讀《資本論》的。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維度闡釋《資本論》的哲學思想。比如,王東認為,《資本論》不僅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代表作,而且是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制高點;(20)王東:《〈資本論〉的哲學底蘊及其現代意義》,《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8期。孫承叔、卜祥記和陸云等學者認為,《資本論》的哲學內核是現代史觀或唯物史觀;李德順等人從價值哲學出發研究《資本論》;任平從交往實踐觀出發認為,馬克思創立的新哲學是在經濟學語境中批判地考察資本全球化問題;鮑金從實踐哲學維度出發認為,《資本論》哲學是在一個具體的社會生活層面上將實踐哲學革命化的典型;(21)鮑金:《“使現存世界革命化”:〈資本論〉的哲學性質探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郗戈認為《資本論》的哲學線索是資本邏輯及其自我揚棄,“在當代視域中重新研究《資本論》,應該打破學科壁壘,開啟“哲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視野,重新彰顯《資本論》原著本身的有機總體性。”(22)郗戈:《〈資本論〉的哲學主線:資本邏輯及其揚棄》,《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這才是國內外學者對《資本論》的哲學化解讀。
四、結 語
張旭和常慶欣教授窄化了對《資本論》哲學化解讀的理解,曲解了他們所批判的對象的理論旨趣。實際上,他們所批判的對象并沒有將《資本論》看成一部哲學著作或者囿于單一的哲學視野去理解《資本論》。比如孫正聿教授指出:“跳出我們現行的體制化、職業化、學院化、科層化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跳出現在通行的關于學科分類的思考方式,不再用‘哲學’、‘經濟學’或各種學科分類的視域去閱讀和研究馬克思這個‘最偉大的人物的思想’,我們才能更深切地理解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理解馬克思關于人類解放的學說。”(23)孫正聿:《怎樣理解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3期。孫正聿教授認為,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既不是純粹的哲學批判,也不是獨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者孤立的空想社會主義批判,而是三大批判的統一。《資本論》是一種理論自覺把握現實歷史,縮短和減輕社會發展中的痛苦。我們可以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張旭和常慶欣教授誤解和窄化了他們所批判的思想。與此同時,他們的批判方式也有待進步。他們通過擬定權威(所謂的學界的共識)來反對權威,通過擺明立場(政治經濟學立場)來反對立場。但是,他們旨在客觀、公正的研究卻陷入了一種“視域之差”。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哲學界為什么鮮有人回應張旭和常慶欣教授的“商榷”和“反駁”,因為《資本論》本身就是開放性的。 《資本論》的定性和讀法之爭歷來不絕如縷。重提這樁學術公案是好的,可是意圖一下子解決這個難題,給學界一個滿意的答案卻是不現實的。況且,他們的反駁并無實質的建構,只是在政治經濟學范圍內擺明自己的方法和立場,沒有對《資本論》的哲學化解讀給予應有的同情的理解。這也啟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任務緊要而迫切,同時又任重而道遠。我們既要在學科內做大做好,又要在學科之間交流對話、尊重差異、和平共處,還要在學科外生成一種具有凝聚力和創造力的學術和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