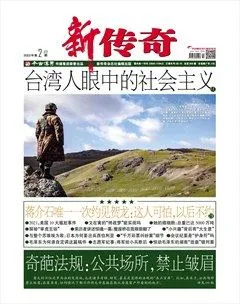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十個孩子
2022-02-03 22:29:20
新傳奇
2022年2期
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很喜歡孩子,和孩子們在一起時,他們也天真得像個孩子。有一次,得知某個孩子和他們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時,周恩來頗有感慨地對鄧穎超說:“我如果不離開廣州,我們的孩子可能就活下來了。”在這種時候,鄧穎超總是內疚地說:“我不該背著你打掉第一胎。那時我才21歲,年紀輕,看著廣州革命形勢好,你忙我也忙,就開了一點兒中藥打了胎。”但這種父母思兒之情一下子就過去了,隨后,他們繼續以父母慈愛之心,去關心和愛護革命的后代。
所以,當周恩來的表姐龔志茹遺憾地說“美中不足的是你們沒有一個孩子”時,周恩來反駁道:“誰說沒有?我們有10個!他們的父母是為革命而犧牲的,我們就要擔當起父母的責任。”這10個孩子或許只是一種泛指,可以不必考證,但他們撫養革命后代的故事卻早在革命隊伍中流傳。
1937年,16歲的孫維世和大哥一起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不認識她,又覺得她年齡太小,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門口不肯離去,剛好被周恩來遇見。周恩來看她哭得傷心,立即詢問原因,才知道她是老戰友孫炳文的女兒,于是馬上把她帶進辦事處。
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延安,并寫信給她的母親任銳,表示愿把這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女兒。此后,他們給予了孫維世無限的關懷。
參加南昌起義的25師黨代表李碩勛是在1931年被捕遇難的,他的夫人趙君陶(革命家趙世炎的胞妹)那時帶著孩子李鵬東躲西藏。……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