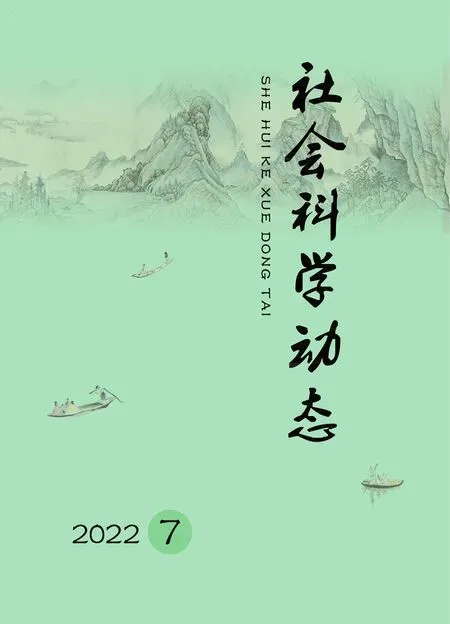《民法典》視域下遺產管理人制度實務問題研究
羅 師
隨著《民法典》于2021 年1 月1 日起正式生效,實施了近四十年之久的《繼承法》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民法典》繼承編。較之于《繼承法》,《民法典》繼承編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確立了遺產管理人制度,填補了法律制度的空白,其積極意義自不待言。但《民法典》繼承編關于遺產管理人的規定只有5 個條文,不僅結構略顯單薄,其規定也較為籠統。自《民法典》公布實施一年多以來,上述規定在司法實務中已經出現捉襟見肘之窘狀,難以應對復雜多元的現實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秩序的混亂。針對這一現狀,筆者以司法實務中的相關案例為考察對象,結合學界研究和比較法的經驗做法,對《民法典》遺產管理人制度的若干實務問題進行分析和梳理,并提出相關解決方案,以求教方家。
一、遺產管理人的產生和去職
《民法典》第1145 條、第1146 條(若無特指,以下均為《民法典》相關條款) 對遺產管理人的產生作了規定。將此二條文聯系有關遺囑繼承的規定可知,被繼承人可通過訂立遺囑選定遺產管理人;遺囑未選定的,由繼承人推選或共同擔任遺產管理人;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放棄繼承的,由有關部門擔任。但這些規定考慮的情形過于片面,不足以解決司法實務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一) 遺產管理人的產生
根據第1145 條和第1146 條之規定,遺產管理人可以通過被繼承人自行選定、繼承人推選和法院指定這三種方式產生。
1.被繼承人自行選定
遺產管理行為須符合被繼承人的意愿和利益,而對于何人能夠勝任遺產管理事務,被繼承人往往知之最詳,故由被繼承人自行選定遺產管理人通常是最為理想的狀態,也更不容易引發糾紛。但司法實務中的問題是,被繼承人訂立遺囑時,尚未確定管理遺產的合適人選,或者希望由其他個人或機構代為確定,特別是遺產數額較大或繼承人眾多時,以及存在涉外因素等情形。這就涉及到被繼承人能否在遺囑之外選定,以及能否委托他人代為選定遺產管理人的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學界通說認為,被繼承人只能通過遺囑選定遺產管理人;通過其他方式“選定”的,不產生繼承法上的效力。其理由在于,被繼承人對遺產管理事務的安排,應以其生前最后的意愿為準,而只有遺囑能夠達到這一效果。司法實務界也多采此觀點。比如,在“潘某和楊某1、楊某2 繼承糾紛”案中,被繼承人楊某文生前在《結婚協議書》中對遺產管理事務所作的安排就未被法院所認可。①但對于第二個問題,學界和實務界則存在分歧,比較法上亦有不同做法。比如,德國、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均規定被繼承人可以委托第三人選定遺產管理人,而瑞士、法國等則不允許被繼承人這么做。②有觀點認為,我國采取的是后一種立法模式,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從字義上看,第1145 條并無排除被繼承人委托他人代為選定遺產管理人的意思。其次,我國的遺產管理人制度并非只限于遺囑繼承的場合,對法定繼承也同樣適用,這實際上為以委托方式確定遺產管理人提供了可能。考察司法實務可知,被繼承人對遺產管理人的選定與對其他遺產繼承事務的安排,特別是對繼承人和繼承份額的確定,往往持不同心態。如果一味堅持上述思路,則可能會影響被繼承人意思自治和多元表達的實現。因此,對被繼承人委托他人代為選定遺產管理人的,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法院就應當認可。
2.繼承人推選
根據第1145 條第2 分句之規定,遺產管理人可以由被繼承人推選產生。但這一規定過于簡略,難以有效地指導司法實務。
首先,推選主體不明確。顯然,只有在有數名繼承人的場合才可能存在推選產生遺產管理人的情況。但是由全體繼承人推選,還是部分繼承人推選,《民法典》未予明確。不少法院傾向于前者,但這極容易導致遺產陷于虛懸狀態,而使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蒙受不利益。因為在實際生活中繼承人相繼出現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有的在遺產分割完畢若干年之后才出現。倘若只要求部分繼承人推選,那么可參加推選的繼承人應滿足什么條件,所推選的結果是否應通知,以及如何通知其他繼承人?《民法典》同樣沒有明確。筆者認為,針對上述一系列問題,可以借鑒臺灣地區的“親屬會議制度”③,即由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繼承人組成“繼承人會議”,當其人數滿足特定要求,便可召開繼承人會議,對推選遺產管理人事宜作出決議并通知其他繼承人;只要不存在侵害其他繼承人和利害關系人合法權益的情況,繼承人會議推選遺產管理人的決議對所有繼承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其次,推選期限不明確。第1145 條第2 分句要求對遺產管理人的推選應當“及時”進行,但未明確推選的期限。考慮到可能存在繼承人怠于推選或其他導致遺產陷于虛懸狀態的情形,不僅會對被繼承人的債權人的權益造成影響,還可能影響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故應當對推選設置一定的期限。設置此期限的意義除了督促繼承人盡快推選外,還包括允許任一繼承人或利害關系人可以“超出期限”為由直接要求法院進行指定,而無需達到第1146條“確有爭議”的要求,從而大大提高遺產管理和分配的效率。臺灣地區“民法”第1177 條規定,“親屬會議”應于繼承開始后的一個月內推選出遺產管理人。④這一做法可為司法實務所借鑒。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期限并非程序法上的不變期間,亦非實體法上的除斥期間,即便已逾期限,但只要繼承人對所推選的遺產管理人均無異議,法院就應予認可,而不能因推選超出期限就否定其效力。
3.法院指定
在司法實務中,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無法就確定遺產管理人的問題達成一致,故要求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的情況較為普遍。第1146 條規定了法院指定的情形,但法院應根據何種要求進行指定,以及應在什么范圍內指定,仍需要進一步予以明確。
關于第一個問題,根據第1146 條之規定,法院啟動指定程序,需以利害關系人的“申請”為必要。實踐中,利害關系人一般會直接“申請”法院指定其“意有所屬”的某特定個人或組織。⑤倘若法院一味順其“申請”,對其他利害關系人而言難謂公平。在比較法上,“申請”只是啟動法院制定程序的必要前提,法院需要根據被繼承人的遺囑、繼承人的實際情況以及“親屬會議”的意見等作出指定裁決。⑥這說明雖然法院是“依申請”進行指定,但指定程序一經啟動,利害關系人的意志就不屬于法院考察的范圍。因此,法院在面對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時,除了“依申請指定”和“駁回申請”的處理以外,還可以根據其他客觀情況另行指定法院認為適合的個人或單位作為遺產管理人。⑦
關于第二個問題,《民法典》并未明確法院應在何種范圍內指定遺產管理人,學界亦存在爭議。司法實務的做法則差異較大,包括繼承人、繼承人以外的近親屬、被繼承人身前的工作單位、律師事務所和被繼承人身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門或村委會等。筆者認為,對法院指定的范圍不宜限制得過窄。在市場環境不斷變化的今天,如何盡可能地避免遺產的價值和效用在分割前受到市場波動以及其他客觀因素的不利影響,已經成為一個亟需破解的難題,需要借助于那些具備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專業設備的個人或單位。某些具有法律咨詢和金融服務職能的第三方機構可能會比繼承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更適合擔任遺產管理人的工作。在比較法上,法院指定律師事務所、信托公司、理財機構等作為遺產管理人的情形已經非常普遍,目前我國也已經有多家律師事務所掛牌了遺產管理人業務。
(二) 遺產管理人的去職
一般認為,遺產管理人的職務因繼承結束、遺產管理人死亡以及自身喪失民事行為能力而終了。但對于遺產管理人能否辭任,以及繼承人能否解任遺產管理人的問題,《民法典》并未明確,學界亦存在爭議。現就這兩個問題分述如下:
1.遺產管理人的辭任
在比較法上,一般允許遺產管理人辭任,但辭任的條件不盡相同。比如,德國民法規定遺產管理人“得隨時終止其職務”,日本和韓國民法則要求遺產管理人須有“正當理由”方可辭任。⑧在我國,有主張應以“正當理由”為必要者,也有主張“可隨時辭任”者,還有主張區分產生情況區別對待的,即由繼承人推選產生的遺產管理人可以隨時辭任,而由遺囑選定和法院指定的遺產管理人則須提供“正當理由”方可辭任。筆者認為,遺產管理人的工作雖然需要兼顧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但其本質上屬于私人事務的問題,要求遺產管理人必須有“正當理由”方可辭任的做法有欠妥當。但因遺產管理人的辭任導致繼承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遭受損害的,除不可歸責于遺產管理人的情形外,遺產管理人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還有觀點認為,法院指定的遺產管理人“應當立即就任,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且不允許辭任。⑨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民法典》對遺產管理人的規定可知,遺產管理人絕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遺產保管人或看護人,其負有不使遺產散失、處理被繼承人債務及分割遺產等重要職責,并伴隨著相應的法律責任。對一般人而言,若不是對被繼承人、繼承人或者遺產有著較為強烈的感情和期待的,恐怕并不愿意承受如此重任,特別是可能會使自身遭受不利益的情況下。法諺有言,“法律不強人所難”。當被指定人堅持不愿意擔任或具有不能擔任的正當理由時,應允許其拒絕接受指定,而法院則應另行指定。⑩因此,為了避免造成當事人精力和時間及司法資源的浪費,法院在指定遺產管理人前,“應聽取被指定人之意見而就愿就任者指定之”。?
2.遺產管理人的解任
有學者提出,對遺產管理人的解任須以“怠于履行職責和其他正當理由”為限。?但筆者認為,對遺產管理人的解任,應區分具體情況而定:第一,對于繼承人推選產生的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有權隨時解任。這是因為,繼承人與遺產管理人之間屬于委任關系,是以雙方的相互信任為基礎;一旦信任不復存在,這種委任關系便難以為繼,應當允許繼承人隨時解任。這亦符合權利產生和運行的規則。?第二,對于被繼承人選定或法院指定的情形,繼承人仍有權解任,但須以遺產管理人怠于執行職務或其他重大事由為必要。比如,遺產管理人因嚴重疾病、下落不明或長期不在當地等原因導致管理遺產有困難的,繼承人可以對其解任,具體情形可參照關于解任破產管理人的相關規定。比較法上亦有因遺產管理人與繼承人之間、數名遺產管理人之間存在“激烈對立”而允許繼承人解任遺產管理人的做法?,可資借鑒。當然,繼承人對是否解任或對新選定遺產管理人產生爭議的,可依第1146 條之規定要求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被解任后仍可依第1149 條之規定要求獲取必要的報酬,因為即便是無償之委托,仍不能因此增加受托人的任何經濟負擔,也不能令其蒙受損失。?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民法典》未對遺產管理人的行為能力作規定,但一般認為其應當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比如,臺灣地區“民法”規定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不得作為遺產管理人。?日本民法則在禁止未成年人和禁治產人擔任遺產管理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排除了破產人擔任遺產管理人的資格。筆者認為,遺產管理人應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否則難以確保其勝任遺產管理工作。若被繼承人在遺囑中選定的遺產管理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該遺囑部分無效,需另由繼承人推選或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就職之后被宣告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其立即喪失遺產管理人資格,應由繼承人另行推選或由法院另行指定。對于已經作出的遺產管理行為,鑒于遺產管理人的地位類似于破產管理人,可作為無權代理處理,但若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均無異議的,則仍為有效。
二、遺產管理人的職責
關于遺產管理人的職責,第1147 條作了列舉式規定,大致可概括為清理遺產并制作遺產清單、管理遺產、管理遺產之必要行為和清償遺產債務。關于遺產管理人職責的具體內容,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存在一定的爭議,需加以厘清。
(一) 清理遺產并制作遺產清單
1.清理遺產
遺產管理人應妥善管理并依照遺囑或法律規定分割遺產,因此有必要對遺產進行清理以明確其內容和狀態,這也是遺產管理人就任之后的首要任務。所謂清理,就是對遺產的名稱、數量、地點、價值等情況進行全面的清查,并準確地將那些不屬于遺產的財產(如被繼承人的夫妻共同財產、家庭共同財產等) 剔除出去,以避免被繼承人的配偶、家庭成員等人的財產權益受到影響。遺產管理人應清理的遺產范圍,既包括被繼承人生前留下的積極財產,也包括其消極財產(即債務)。需要注意的是,消極財產不應包括專屬于被繼承人的債務,這部分債務隨著被繼承人的死亡而消滅。
在清理過程中,遺產管理人應善良、忠實地對遺產進行搜索、收集和整理,并采取適當方式予以保存,以便進行管理和日后的移交。清理遺產除了需要對遺產的范圍進行框定以外,還應對遺產施以適度的保全措施,否則就難以實現遺產管理制度的目的。清理遺產的意義在于:一方面使遺產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得到保障,為其他遺產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則使遺產管理人的職責范圍被確定下來,一切管理活動都應以此為限。
2.制作遺產清單
關于制作遺產清單存在的問題和相關解決方案,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制作遺產清單的時間和期限不明。制作遺產清單,須“不遲滯地盡速為之”?,否則將影響接下來所有遺產事務的順利展開,但《民法典》并未對此作任何規定。根據比較法的經驗,要求遺產繼承人于其就任后立即清理遺產并制作遺產清單是較為妥當的。對于制作清單的期限,則應視遺產的具體情況而定,一般不得超過三個月;需要延長期限的,應得到繼承人或法院的準許。?相關司法解釋的制定應對此予以考慮。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因遺產管理人的不當拖延,對繼承人、被繼承人的債權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產生不利益。
第二,制作遺產清單的方式不明。一般認為,遺產管理人應全面如實地記載遺產的種類、數量、狀況等,并注明入冊的日期,確保沒有遺漏。?但這并不是要求遺產管理人必須對所有財產都極盡其詳,對具體財物的價值價格、品類材質,以及日常用品、家具什物等,應允許作概括的記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對積極財產記載其所管理者,對消極財產則記載其所已知者為已足,縱有脫漏,亦無特別之制裁。”?
第三,制作遺產清單的職責可否免除。有觀點認為,制作遺產清單是遺產管理人的法定職責,其可能對其他利害關系人產生影響,故不得依被繼承人及繼承人的意思而免除。?但筆者認為,對此問題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論。對于遺產較少或利害關系人明確的情況下,若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均認為確無制作遺產清單之必要,應當允許免予制作。畢竟,因制作遺產清單而產生的費用須由遺產支付,由此造成的遺產減少可能并不是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所愿意承受的。但在遺產債權債務關系復雜、利害關系人眾多的情況下,應原則上不得免予制作遺產清單。已制成的遺產清單,除了交給繼承人外,其他利害關系人亦有權查閱。對于遺產清單所記載的事項,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可提出異議并要求遺產管理人進行說明或重新制作。遺產管理人怠于制作或制作效果不佳的,可因此被解任。
(二) 管理遺產
在分割遺產之前,應由遺產管理人對遺產進行妥善管理,對此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均無異議。但問題是,在被繼承人死亡后、遺產管理人產生之前,遺產應由何人進行管理?當遺囑執行人和遺產管理人同時存在時,二者的管理職責又該如何分配?
關于第一個問題,無論是繼承人推選還是法院指定,必然要經歷一個遺產管理人缺位的“過渡期”。即便是被繼承人選定和僅有一名繼承人時,也可能因某些主客觀因素影響導致遺產管理人不能立即到任。鑒于客觀情況的復雜多變,“過渡期”可能會非常漫長;而在此期間內,可能出現遺產罹于滅失或毀損的緊急情況而需要對部分遺產進行改良、保全以及變價處理等,也可能存在已屆期限的稅費、債務等需要由遺產進行清償。在這種情況下,應由繼承人作為“臨時遺產管理人”對遺產進行管理;一旦遺產管理人到任,繼承人應立即退出,由遺產管理人對遺產進行全面管理。
關于第二個問題,遺囑執行人,指的是使遺囑內容得到實際執行的人。為保證其執行符合遺囑內容和被繼承人的利益,遺囑執行人須對遺產內容和狀態進行全面了解并進行必要的管理。遺囑執行人與遺產管理人在適用范圍、產生方式等方面存在區別,二者同時存在的情況完全可能發生。?但《民法典》 并未就二者的職責分配作出規定。筆者認為,遺囑執行人因被繼承人的遺囑產生,其對遺產的管理須以遺囑的存在為前提。根據遺囑的記載,遺囑執行人所執行的遺產可以是某特定遺產,也可以是全部遺產。若是第一種情況,則遺囑執行人所執行的部分遺產應從遺產管理人所管理的遺產中剔除,由遺囑執行人根據遺囑的要求,獨立、自主地進行管理,并有權排除遺產管理人的“干擾”。這是因為,遺囑執行人是根據被繼承人的意志所直接產生,其只需對被繼承人負責,而無需對繼承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負責。當然,這并不影響遺囑執行人所管理的遺產被分割或清償債務。若是第二種情況,則遺囑執行人實際上轉化為遺產管理人,其應與被繼承人推選或法院指定產生的遺產管理人共同管理遺產。有職責分工的,按分工各自履行職責;沒有明確分工的,則共同履行職責。作為遺產管理人的遺囑執行人,同樣可隨時辭任,但須對因辭任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也可被繼承人解任,但鑒于其為被繼承人選定,需要滿足前述“怠于執行職務或其他重大事由”的條件。
(三) 管理遺產之必要行為
一般情況下,遺產管理人出于管理遺產之需要,在不變更遺產之物及權利性質的情況下,可對遺產作出相應的保存、改良及利用等行為,但不得處分遺產。然而,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為了防止遺產的毀損和滅失,法律特別賦予遺產管理人可對遺產作出必要的處分。比如,對某些極易腐敗變質的遺產,遺產管理人可立即變價處理,而無需事先向繼承人或法院報告,更不必征得其同意。此外,遺產管理人還可能因取回被第三人占有的遺產而提起訴訟等。這些都是管理遺產之必要行為(以下簡稱必要行為)。為了使表述更為清晰,筆者分別從非訴和訴訟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1.非訴必要行為
非訴必要行為主要包括不涉及訴訟活動的遺產管理和處分行為。其中,管理行為除了對遺產進行保管和維護以外,還包括必要的修繕、收取遺產債權、訂立和解除涉及遺產的相關協議(如倉儲、保管等)、請求第三人返還所占有的遺產等。遺產管理人有權排除一切影響遺產管理的妨害,包括來自繼承人的妨害。比如,繼承人事先已占有特定遺產的,遺產管理人可以要求其交出,甚至可以請求法院強制執行。處分行為是遺產管理人基于管理遺產需要,在職責范圍內對遺產進行處分,而無需征得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同意,包括變賣、抵銷、訂立和解除涉及遺產的相關協議(如租賃、抵押等)、根據遺囑內容以遺產進行捐贈或出資等。此外,兼具遺囑執行人身份的遺產管理人,還可能根據遺囑內容作出捐贈、出資等行為。
有觀點認為,繼承開始后,被繼承人的繼承權由期待權變為既得權,遺產的權利主體亦由被繼承人變為繼承人,故繼承人有權對其所繼承的遺產進行處分。?但這實際上混淆了繼承人對遺產的繼承權和所有權。繼承權的結果當然是所有權,但它本身并非所有權,而是獲得所有權的權利,無處分之含義。?換言之,在遺產管理人履行職責期間,繼承人對遺產的處分屬無權處分,若其處分行為確已對遺產管理造成妨害的,遺產管理人有權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排除。
2.訴訟必要行為
遺產管理人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可能需要就遺產管理問題,與被繼承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占有遺產的繼承人或第三人等進行交涉。但在交涉無果的情況下,遺產管理人能否以自己的名義向對方提起訴訟?對此,《民法典》未予明確,司法實務中的做法亦是各有千秋。
在《民法典》出臺之前,《繼承法》遵循“繼承人中心主義”,只對繼承人參加訴訟的問題作了規定。?但這種立法模式過于粗陋,容易造成繼承人與其他利害關系人之間的利益失衡。隨著《民法典》對這一模式的變革,繼承制度的價值取向由單一轉向多元。?遺產管理人制度就是調和多元價值的關鍵所在。顯然,基于遺產管理的需要,賦予遺產管理人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的權利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學界關于遺產管理人職責的性質存在“固有權”和“委托代理權”之爭。但不論是何種觀點,均不否認該職責是不依附于被繼承人或繼承人而獨立存在的;而若要使該職責能夠獨立地行使,也就必須要讓遺產管理人獨立于被繼承人和繼承人,能夠就遺產管理問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便是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即便不考慮遺產管理人職責的性質,遺產管理人與遺產繼承具有“直接利害關系”,屬于實體法上的“正當當事人”?,亦符合《民事訴訟法》中關于原告資格的要求,完全能夠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
在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期間,若利害關系人以遺產為標的提起訴訟的,比如受遺贈人請求履行遺贈義務之訴,應當僅以遺產管理人為被告。司法實務中,一些法院僅將繼承人列為被告而不列遺產管理人,是不正確的。這是因為,在遺產分割之前,繼承人尚未取得遺產的所有權,亦未承受遺產上的債權債務關系。而且,若僅以繼承人為被告,很可能使訴訟陷于徒勞,因為繼承人完全可能放棄繼承而使遺產陷于無人繼承的境地。而遺產管理人雖然可能發生變更,但可以保證始終有人擔任。當然,法律也不能禁止利害關系人直接向繼承人主張權利。對此,不妨借鑒德國的做法,即雖然遺產債權人可以要求繼承人以遺產清償被繼承人的債務,但不能通過訴訟途徑進行;若要進行訴訟,應以遺產管理人為被告。?
(四) 清償債務
處理被繼承人的債務是法律賦予遺產管理人的一項重要職責,是保證遺產繼承平穩、有序進行的必要前提和關鍵步驟。司法實務中最富爭議的問題是,當被繼承人的債權人不止一人時,遺產管理人應按照何種順序進行清償?關于清償順序,僅有第1159 條有所提及,即分割遺產時,“應當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同時還需“為缺乏勞動能力且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但這一規定所考慮的情形過于單一,對解決實際問題的幫助非常有限。對此,不少專家學者提出了有益的見解,其中以主張“參考破產清算規則”的觀點居多。?筆者認為,是否參考破產清算規則不應一概而論。顯然,在遺產充足、債權債務關系簡單的情況下,并無按破產清算規則進行清償的必要,否則只是徒增訴訟程序之累,還將造成遺產不必要的減少。換言之,參考破產清算規則進行遺產債務清償應以遺產“資不抵債”為前提。至于遺產是否“資不抵債”,可通過清理遺產和制作遺產清單加以判斷。
此外,清償債務應以遺產清單為依據。如前所述,遺產管理人制作遺產清單,不僅要記載被繼承人的積極財產,還應記載作為消極財產的債務。為了全面真實地記載,遺產管理人應盡職調查,并盡可能地通知債權人申報債權。對此,比較法上的公示催告、公示搜索和遺產訴訟等制度可資借鑒。?遺產清單在清償債務階段的意義在于:對遺產管理人而言,其僅對清單所記載的債務進行清償;對被繼承人的債權人而言,其不能就未被遺產清單記載的債權要求遺產管理人對其進行清償。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出遺產清單規定的價值,促使遺產管理人和利害關系人認真對待遺產清單的制作。實踐證明,把清償債務的問題解決在遺產分割前,更有利于維護被繼承人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確保遺產分割的順利進行?,而這離不開對遺產清單的有效利用。要求遺產債務的清償須以遺產清單為依據,可以使遺產管理人充分發揮其功能和價值,有助于遺產管理人制度乃至整個繼承制度向程式化、規范化的方向演進,從而盡可能地使矛盾和糾紛都在一個可控制、可預期的范圍內。
三、遺產管理人的法律責任
根據第1148 條之規定,遺產管理人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繼承人、受遺贈人和債權人損害的,應承擔民事責任。從上述規定的表述來看,該民事責任在性質上屬于侵權責任,其構成要件、承擔責任的方式等應適用侵權責任編的相關規定;立法者于此“再做強調”,旨在督促遺產管理人善意、勤勉和忠實地履行管理人職責。對該規定作相反解釋可知,若遺產管理人沒有過錯,即便其管理行為對繼承人、受遺贈人和債權人造成了損害,亦無需承擔責任,以避免對遺產管理人的履職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對此,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均無異議。
然而,頗具爭議的問題是,非因遺產管理人過錯而造成第三人損害的,相應的法律責任應由誰承擔且如何承擔。比如暴雨使遺產管理人所管理的房屋出現墻體滲水,造成電器短路而失火,進而燒毀供電設備,給供電單位和其他居民商戶造成巨額損失。個別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比附援引”第1253 條、第1254 條之規定,以“遺產管理人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為由判令其向第三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是不妥當的。暴雨是遺產管理人無法避免、無法抗拒,甚至無法預見的自然“災害”,由此導致房屋墻體滲水并造成電器短路屬于小概率偶發事件。法律不能要求遺產管理人一遇雨天就全面檢查房屋并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偶然事件做好萬全的預防措施,這與遺產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職責定位不符。誠然,遺產管理人擔任著遺產管理和遺產分割的重要工作,需要承擔特定的職責,但這種職責必須是“確定”和“適度”的。所謂“確定”,指的是不論是被繼承人的遺囑還是繼承人的要求,抑或是法律的規定,對遺產管理人來說,必須是明確且可知曉的,否則任何不可預見的損失都可追究至遺產管理人處,不僅極不公平、有礙遺產管理工作的順利展開,長此以往也不利于遺產管理制度的良性發展。所謂“適度”,指的是遺產管理人的職責、法律責任和其所擔負的遺產管理工作是相適應的,不應使其承擔過高甚至不可能完成的職責,并由此追究其法律責任。對于上述舉例中的情況,遺產管理人并無過錯,法律亦無此要求,法院判令其承擔法律責任于情無理、于法無據。對于第三人的損失,應在充分發揮保險機構和社會公益組織的作用的前提下,根據公平原則進行處理。
當遺產管理人為二人以上的,應如何承擔法律責任?有學者引德國民法典的規定指出應由全體遺產管理人負連帶責任。?但筆者認為,由于《民法典》并未要求全體遺產管理人須共同履行管理職責(與德國民法典不同),司法實務的情況各異,不應一概而論,而須視個案的具體情況而定:若是全體遺產管理人共同履行管理職責的,由其承擔連帶責任并無不妥;但若遺產管理人之間的職責和權限明確,則各自就其職責和權限范圍承擔責任。此觀點亦為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通說觀點。
需要指出的是,在比較法上,限制和縮小遺產管理人的法律責任,已經逐漸成為司法實務的主流做法。比如,在美國,法院通過判例確立了遺產管理人“僅承擔善意保管義務”的原則。?德國法院則普遍認為,盡管遺產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獨立于被繼承人,但其管理權應不超過被繼承人生前對財產的管理權限,其責任自然也不應大于被繼承人生前的責任。?而日本法院亦已明確通過縮小權限以否定職責的方法,來減輕乃至免除遺產管理人和遺囑執行人的法律責任。?臺灣地區法院的通行做法是,即便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作出侵權行為,雖然尤其個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繼承人作為管理遺產行為的受益人,須應以遺產對遺產管理人負責。?這些都值得我國司法實務深入思考。
還需注意的是,司法實務中存在把第1148 條中遺產管理人的“民事責任”與第43 條中失蹤人財產代管人的“賠償責任”相混淆的情況。兩個條文看上去非常相近,但實際上區別很大。從法律地位上看,財產代管人相當于《繼承法》時期的遺產保管人,對其所保管的財產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僅就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導致的失蹤人財產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其原因在于,財產代管是一種無償的利他行為,財產代管人無須盡自己事務同等的注意義務,其對失蹤人財產的管理是一種消極的管理。?因此,《民法典》沒有賦予財產代管人請求報酬的權利。遺產管理人的注意義務顯然高于財產代管人,其對遺產的管理顯然是積極和主動的,甚至帶有一定的“進攻性”。因此,遺產管理人的法律責任不僅限于對遺產的損害,還包括對繼承人、受遺贈人和債權人的損害。當然,現實生活中亦有遺產管理人不收取任何報酬的情形,對此,法院應以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的標準認定其法律責任。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對遺產管理人的法律責任另有約定的,若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的情形,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約定。
四、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取得權
關于遺產管理人就其遺產管理行為取得報酬的問題,僅有第1149 條“可以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約定獲得報酬”之規定,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在司法實務中,存在以遺囑載明、繼承人與遺產管理人約定、繼承人與遺囑執行人約定以及繼承人自行確定等方式明確遺產管理人報酬的情形。此外,也存在法院直接確定的情形,但相對較為少。無論是何種情形,出于遺產管理人履行遺產管理職責的鼓勵和褒獎,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但除了專司遺產管理或遺產信托業務的組織機構以外,不同法院對遺產管理人是否有權要求取得報酬,抑或說取得報酬能否構成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仍存有一定的疑義。這是因為,在《繼承法》 時期,司法實務對“遺產保管人”索取報酬的行為普遍持否定態度,而這種否定態度或多或少地“延續”到了遺產管理人身上。但如學者所指出,若法律只強調遺產管理人的職責和法律責任,卻不賦予其取得報酬的權利,“實有違背權利義務均衡之原則”。?管理遺產必然要耗費遺產管理人的時間和精力,甚至還可能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使其能夠獲得相應的報酬合乎情理。盡管《民法典》對遺產管理人取得報酬是否構成民事權利這一問題規定得較為含糊,但相關立法釋義在此問題上諸如“權利義務相匹配”、“可以要求獲得報酬,也可以不要求有報酬”的表述卻都完全符合對民事權利的描述。?因此,取得報酬當屬于遺產管理人的法定權利無疑。在比較法上,通過立法或判例明確遺產管理人具有報酬請求權的國家和地區亦越來越多。這說明,將取得報酬作為遺產管理人的權利是順應遺產管理人制度的發展趨勢的。至于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取得權在司法實務中該如何落實,筆者認為,法院應當鼓勵當事人之間就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問題進行協商,必要時亦可主動釋明;當事人之間約定不明的,應根據遺產管理人履行職責的實際情況,并結合遺產類型、遺產價值、相近服務的市場價格水平等情況予以酌定。
遺產管理人的報酬應當從遺產中支出,對此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均無異議。但《民法典》并未明確遺產管理人的報酬之于被繼承人應繳納的稅款和債務,以及分割遺產等,應孰先孰后。對此,筆者認為,為了鼓勵遺產管理人的盡職履責、避免遺產管理人制度被虛置,應優先保障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取得權。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取得,不僅優于被繼承人應清償的債務,還優于被繼承人應繳納的稅款得到實現。?這亦是比較法的主流做法,又被稱為是對遺產管理人的“正向激勵機制”。但從實踐經驗來看,根據工作完成的質量和效果確定報酬,同樣有利于督促遺產管理人盡職履責。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遺產管理人取得報酬應以其職責履行完畢為前提,相當于是對遺產管理人的“反向激勵機制”。“正向激勵機制”與“反向激勵機制”并不矛盾,二者相互配合,共同促進遺產管理人制度的功能實現:在確定遺產管理人時,即應同時確定遺產管理人的報酬方案;未能同時確定的,則應盡快確定。報酬方案一經確定,遺產中屬于遺產管理人報酬的部分就應當被“預留”出來,待遺產管理人職責履行完畢后向其如數支付。如此一來,遺產管理人對取得報酬有了穩定的預期,其自然也會更加盡職地管理遺產。當然,考慮到從繼承開始到繼承結束的期間可能會非常漫長,應允許遺產管理人以其他更為靈活的方式取得報酬,比如定期支付、按項支付等,以避免其因管理遺產而造成自身物質經濟上的損失。繼承人亦可以根據遺產管理人履行職責的實際情況,對報酬方案進行適當調整。
五、結語
遺產管理人制度具有許多獨特的作用和優勢,對實現被繼承人意思自治、保證私有財產的代際移轉和促進物盡其用等具有重大意義。《民法典》確立遺產管理人制度,填補了遺產管理的立法空白,完善了我國的繼承法律制度,為司法實務處理相關案件提供了法律遵循。同時,《民法典》的遺產管理人制度融合了比較法上遺囑執行人制度和無人承認之遺產管理制度,兼取二者之所長,既符合司法實務的實際情況,又避免了制度設置上的重復累贅,具有高度的現實意義。無論是遺囑執行人制度還是無人承認之遺產管理制度,其理論和體系構建都相當完備。對比之下,《民法典》對遺產管理人的規定仍較為粗略,難以應對復雜多元的客觀需要,需要作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
注釋:
①該案中,法院認為《結婚協議書》并非遺囑故不予采信,《結婚協議書》中關于楊某文遺產的管理和分配的內容無效;參見貴州省黃平縣人民法院(2017) 黔2622 民初1100 號民事判決書。
② 參見《德國民法典》 第2197 條、第2198 條;《日本民法典》 第1006 條; 《韓國民法典》 第1093 條;臺灣地區“民法”第1209 條;《瑞士民法典》第517 條;《法國民法典》第1025 條。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條文中規定的是“遺囑執行人”如何產生,但結合上下文可知其與我國《民法典》中的“遺產管理人”并無實質區別。
③“親屬會議”源于日耳曼固有法的“上級監護”,我國古代和近代時期亦有類似制度。晚近以來,因大家族逐漸被小家庭所取代,親屬多散居各處,“親屬會議”在實操層面的意義有所減退,因此包括德國、法國和日本在內的大陸法系國家紛紛取消了這一制度。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修訂仍保留了“親屬會議”的內容,但其權限已大幅刪減,改由法院行使。盡管臺灣地區學者對“親屬會議”的存廢爭議頗多,但對其在遺產繼承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還是普遍持肯定態度的。
④林秀雄: 《繼承法講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版,第201 頁。
⑤比如,在“徐某與楊某等申請指定遺產管理人”案中,徐某向法院申請指定自己為遺產管理人,參見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2021) 滬0114 民特171 號民事判決書;在“喻某繼承糾紛”案中,喻某向法院申請指定某律師事務所為遺產管理人,參見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2021) 川0107 民特142 號民事判決書;在“張某與鄰水縣鼎屏鎮五岔村村民委員會繼承糾紛”案中,張某向法院申請指定鄰水縣鼎屏鎮五岔村村民委員會為遺產管理人,參見四川省鄰水縣人民法院(2021) 川1623 民特28號民事判決書。
⑥???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三民書局2011 年版,第320—337 頁。
⑦比如,在“黃某和黃某浩等繼承糾紛”案中,繼承人要求法院指定自己為遺產管理人,但法院最終根據被繼承人生前留下的文書資料指定被繼承人的兄長為遺產管理人,參見四川省隆昌縣人民法院(2021) 川1028 民特32 號民事判決書。
⑧參見《德國民法典》第2226 條、《日本民法典》第1019 條、《韓國民法典》第1105 條。
⑨楊立新: 《我國繼承制度的完善與規則適用》,《中國法學》2020 年第4 期。
⑩比如,在“睎某和欽某繼承糾紛”案中,法院指定欽某為遺產管理人,但欽某“再三拒絕”,故法院準許欽某拒絕擔任并重新指定遺產管理人,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9) 滬02 民終1307 號民事判決書。
??史尚寬: 《繼承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531、531 頁。
?王葆蒔、吳云煐:《〈民法典〉遺產管理人制度適用問題研究》,《財經法學》2020 年第6 期。
?戴炎輝、戴東雄: 《中國繼承法》,三民書局1998 年版,第220 頁。
? [日] 中川善之助、泉久雄: 《注釋民法(26)相續》,有斐閣1992 年版,第290—291 頁。我國亦有此類司法裁決,比如“翁某、呂某第三人撤銷之訴”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0) 最高法民再113 號民事判決書。
? [日]我妻榮:《債權各論(中卷二)》,周江洪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8 頁。
?參見臺灣地區“民法”第1210 條、第1215 條。
??唐義虎、周璐:《美國繼承法判例選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0、146 頁。
?楊立新:《中國民法典釋評·繼承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89 頁。
?王歌雅:《〈民法典·繼承編〉:制度補益與規范精進》,《求是學刊》2020 年第1 期。
?楊立新、李怡雯:《中國民法典新規則要點》,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594—595 頁。
?楊震、王歌雅: 《繼承權向所有權轉化探究》,《學習與探索》2002 年第6 期。
?陳杭平:《論債務人的繼承人放棄繼承之程序進行》,《現代法學》2020 年第2 期。
?陳振安: 《遺產管理人的法定訴訟擔當資格研究——以無人繼承情形為視角》, 《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21 年第6 期。
??林秀雄:《民法親屬繼承爭議問題研究》,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308、308 頁。
?張衛平:《民事訴訟:關鍵詞展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88—91 頁。
? [德]雷納·弗蘭克、托比亞斯·海爾姆斯:《德國繼承法》,王葆蒔、林佳業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7 頁。
?汪洋:《遺產債務的類型與清償順序》,《法學》2018 年第12 期。
?陳葦:《外國繼承法比較與中國民法典繼承編制定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646—670 頁。
? 張黎: 《遺產分割前遺產處理規則的制度安排——兼評〈民法典·繼承編(草案)〉 (二次審議稿)》,《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9 年第6 期。
?參見《德國民法典》第2219 條第2 項。
? [德]霍特斯·艾登穆勒、馬丁·弗里斯:《德國繼承法案例研習》,胡堅明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28—29 頁。
? 趙莉: 《我國遺囑執行人法定權責模式的選擇——管理清算型抑或監督保全型?》,《金陵法律評論》2016 年第1 期。
?王利明:《中國民法典釋評·總則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0 頁。
?黃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及適用指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1743—1744 頁。
?陳葦、石婷:《我國設立遺產管理制度的社會基礎及其制度構建》,《河北法學》2013 年第7 期。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