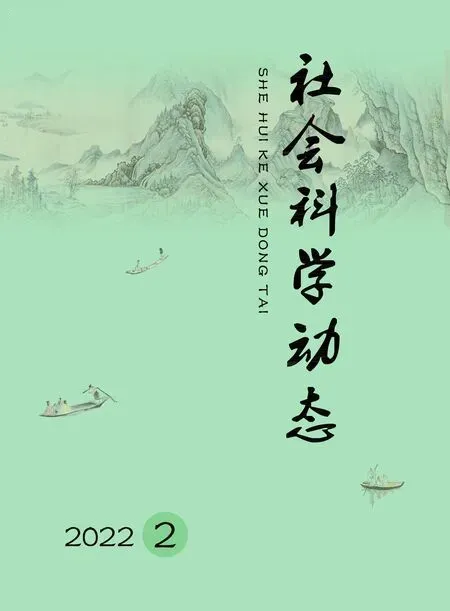新鄉土視野下的扶貧書寫
——評湖北作家韓永明扶貧系列小說
趙亞琪
鄉土文學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作為一個農業文明古國,鄉土傳統幾乎就是中華文明的根脈。費孝通曾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①中國現代鄉土文學開始于魯迅。1926年文學史家張定璜稱魯迅先生的創作為“鄉土小說”。作家劉紹棠則認為“鄉土文學”的確立應該從1935年3月魯迅寫作《中國新聞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開始。“他的小說 《孔乙己》 《風波》《故鄉》 《阿Q正傳》 《社戲》 《離婚》和 《祝福》,不但寫的是紹興地方的農民生活,而且寫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紹興農村的風土人情,是中國鄉土文學創作的不朽豐碑。”②此后,現代中國鄉土文學分成兩大流派:一派是以魯迅、王魯彥、許欽文等為代表的作家,他們批判鄉村落后愚昧,反思農村社會中的世態炎涼與弱者的不幸。另一派是以沈從文、廢名等為代表的作家,沉醉于山水秀麗的田園風光,以農村淳樸文明來反抗現代工業文明的烏托邦。此后,趙樹理、孫犁、從維熙、周立波等人的文學創作,從不同維度反映了中國農村社會的情況。1970年代后,又先后出現了一批新的鄉土書寫者,以柳青、韓少功、阿城、王安憶、路遙、閻連科、賈平凹、莫言等為代表的作家,承續鄉土傳統,書寫著中國大地上不同地域的人物風情。在當前中國快速發展進程中,“鄉土”早已是今非昔比,時代在變,農村在變,農民在變,文學在變,作家也在變,新農村題材需要文學創作新突破。劉醒龍、陳應松、韓永明等一批湖北作家,不斷地嘗試打破既有鄉土書寫模式和審美表達,進一步呈現當下中國真實的鄉土風情,并試圖通過自身的文學創作將鄉土書寫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鄉土文本結合當下扶貧發展轉型的書寫,是目前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選題。作為鄉土小說一個重要的分支,一些優秀的扶貧小說不僅真實記錄了中國扶貧工作的歷史進程,表現了當下扶貧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提煉總結了多種扶貧經驗模式,而且反映了社會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態,以及普通人在波瀾壯闊的扶貧浪潮中的成長故事。其中,韓永明的新鄉土書寫已然成為了一種新的文學表達,這既是對時代的回應,也是一種新的審美探索。
一、從解綁土地到重新回歸土地
近年來,隨著精準扶貧方略在全國范圍內積極推行,鄉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時代召喚作家聚焦于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一系列反映精準扶貧的作品脫穎而出,豐富了鄉土文學的內涵和表達。韓永明在對鄉土書寫的過程中,有意避開“苦難敘事”“挽歌”“牧歌”模式,而是著力書寫農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聚焦扶貧干部、扶貧對象、村干部等不同人群的精神成長,這是韓永明扶貧題材小說不同于其他作家同類題材小說創作的一個特點。
韓永明聚焦在現有“開發式扶貧”理念指導下基層鄉村干部的工作重點:通過開發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發展商品生產,改善生產條件,轉換銷售模式,提升百姓生活質量。在小說 《春天里來》中,夏香久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婦,她在一次意外住院時,有幸結識了幾位視野開闊的病友,他們的身份包括醫生、攝影師、教師等。大家在一起閑聊著食品安全問題,談論著轉基因食品對于人體的危害。由此,夏香久借用新興科技智能手機的便利,開始在微信朋友圈售小籽黃給城里朋友。在作品《驕傲的父親》中,父親為給兒子在縣城里買房,花掉了畢生的積蓄,只為取得“城里人”這一身份。兒媳婦香云與兒子離婚后,她又回到農村生活,并利用網絡直播方式賺錢,很快成為網紅。這里,“縣城的房子”已不再只有房屋本身的物質價值和使用價值,而是轉換為一種符號價值,它所代表的是兒子所謂“階級身份的轉變”。而香云運用互聯網媒介來直播鄉土原始播種方式的行為,可以說是當代農村人現有思維方式的一次重大轉變。他們充分利用網絡平臺開展活動,也在無形中影響或改變了農村人樸實耕種的傳統面貌。
此類現象的發生和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密不可分。過去農民和土地是牢牢捆綁在一起的,祖祖輩輩從地里刨食,對土地充滿著依戀和尊重。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資料,被賦予了更多的現實內涵。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進一步松散,大量鄉村農民紛紛涌入城市,變身為一種新的身份——“農民工”。他們擠進城市,成為企業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小商品生產者、城里的小商販,或者小企業經營者,甚至不少人在摸爬滾打中成為成功的商人或企業家。但是,隨著近年來國家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資本的巨量投入,環境的極大改善,很多農民開始重新回歸鄉村。他們可能還是會依靠土地賺錢,但已不再僅僅滿足了從土地里獲得簡單的食物,而是開始利用網絡科技直播農耕生活,兜售一種樸拙的農村生活方式,以滿足城里人對田園生活的想象。這種變化是耐人尋味的。韓永明非常敏銳地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在韓永明的筆下,青年農民在進行這種直播的時候,是以一種“打破落后,站在田園生活前沿”的形象來滿足著城里人對于鄉村田園風光的向往,一改往日“農村人”迫切希望有一個窗口可以窺探“城里人”生活的狀態,這種城鄉憧憬不經意間就互換了身份位置。相比于以往城里人對農村人那種高傲的“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鄙夷,韓永明筆下呈現出的是代表著溫馨、祥和的田園風光的“農村人”,熱忱接納“城里人”對自己生活的關注和好奇,并熱心引導“城里人”了解現階段農村的生活狀態。故土也不再是單指作家心中“遙遠的清平灣”,更多的是對在城市化浪潮沖擊下,一批來自于農村的城市作家對“烏托邦”生活的回望與憧憬。農村人對于土地的認知在接納城市新鮮文明的同時發生了巨大變化,土地本身的意義某種程度上已被娛樂化消解,過往那種對土地無比尊重的耕作飲食文化,轉換成為一種用“土地”賺得網絡流量的飲食文化。
韓永明對于農村群體現狀的關注已超越原有鄉土文學的思維定式。在他的筆下,農村人的思維方式已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跳舞、刷抖音、讀網絡小說等已經成為日常。從曾經的“輸血式扶貧”,鄉村像一個嗷嗷待哺地孩子那樣,等待著國家和政府大量資金投入式的攙扶著發展,到農民不斷自覺地接受高科技和新事物,轉變為“開發式扶貧”,農民自發利用現有的科技力量將自己生產的農產品銷往城里,增強經濟發展內驅力,來完成新的產銷結合。很顯然,韓永明已關注到農村群體的思想變化,并將“農民進城”作為書寫主題之一,但這早已不同于“陳奐生上城”的書寫模式,即明寫農民和城市(先進文明的代表)的接觸,實寫農民真正走進全新的現代文明時因文化程度、習慣風俗等差異而感到窘迫,作者似乎是站在一個至高點捎帶諷刺地觀察農村人的愚昧。相比之下,韓永明以一個更貼近現實生活的創作方式,以親身實地來觀察和書寫鄉村生活的巨變。在他的筆下,農民已不再是沒有文化、沒有見識的人,保守、愚昧、貧窮、自私,甚至誠實、勤勞、純樸這些形象都在漸行漸遠。
二、從城鄉二元對立到外來者入鄉
打破城鄉二元對立,聚焦主體精神成長,是韓永明小說創作的另一大特色。韓永明筆下的扶貧干部,大多是以“外來者”視角進入鄉村,他將基層駐村干部的成長與鄉村面貌以及村民命運的改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貧工作既是幫扶他人的過程,也是扶貧干部自我成長的機遇,很好地表達出“人”的成長。
深入鄉土的過程,是基層駐村干部作為“外來者”如何進入鄉村內部的過程,農村發展的內生力量必須和政策的外在幫扶兩相結合,才能真正打好脫貧攻堅戰役。駐村干部融入鄉村內部的過程,也關涉到文學所呈現的鄉村經驗,如何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性化表達,是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突出特征。
在作品《小羊咩咩》中,駐村干部為幫助牧羊人老萬走下山住進扶貧安置房屋,想盡了辦法。老萬醉心于自己的羊群和山上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死活不愿接受下山安置。駐村干部王天麻、小楊和魯隊長先是裝成“羊販子”,設法購買羊群勸導老萬下山,后又將扶貧物資放置在扶貧安置房中,想誘迫老萬下山,結果還是不成。扶貧干部最終無奈妥協,單獨為老萬在山上安上電、網,并購置手機囑咐老萬每日和駐村干部通電話報平安。通過多次設法希望老萬下山的舉動,將扶貧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和宗旨展現得淋漓盡致。文中體現出很重要的兩點:一是牧羊人老萬對傳統生活模式的執著,明顯帶有對現代生活的排斥;二是扶貧干部小魯隊長對老萬這種個人生活方式選擇的尊重,這也是對人格的尊重。小說《酒是個鬼》更像是韓永明新時代鄉村書寫的序篇。小說中,王大用作為單位里的“邊緣人”,被局長“委以重托”前往農村扶貧。他下定決心戒酒,卻在實際扶貧工作中七次破戒,為的是讓扶貧對象石頭順利脫貧,住進政府集中改造的磚房。在扶貧工作中,王大用逐漸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價值,一改往日的精神風貌,從“穿什么不像什么”到“穿西裝和黑呢大衣變精神了”。韓永明試圖用西方的審美體系來建構“王大用”這一人物形象,“無用之用以為大用”,其內在主體性的自我認同感,幫助王大用獲得了職業生涯的自我成長、自我拯救,同時這也顯現出作者思考的高度和深度。在小說《我們跳舞》中,廣場舞直接拉近了農村與城市生活方式上的距離,官民一起參與到鄉村廣場舞隊,既豐富了農村居民的業余生活,又在精神層面縮短了城鄉文化差距、官民心理差距。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在物質生活基本飽和之后,農民對精神生活的積極追求和自我成長。
“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工具。”文學是人學,韓永明在對扶貧文學的書寫過程中,將筆觸投射到駐村干部、扶貧對象的身上,駐村干部不辭勞苦、辛勤工作,只為將自己所負責的村落脫貧致富;扶貧對象不斷突破思維局限,響應扶貧干部的號召,努力改善現實生活。在這里,韓永明將基層干部自我價值的實現和鄉村振興發展不斷相融相匯連成一脈。正如蔡家園所評論的:“敏銳關注社會重大問題,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傳奇性因素,注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即便是凌厲的社會批判也不掩內里的溫暖。”③
在韓永明的扶貧書寫中也客觀地剖析了農村發展前期難脫貧困的原因。一是扶貧干部思維固化,扶貧方式單一。前期扶貧工作中,常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味地直接“輸血”,只給魚不教織網,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用發展的角度促進農民生活質量上的提高。早期農村扶貧,一味送錢送物,久而久之竟讓一些貧困戶形成了慣性思維——聽說上面有領導來看望貧困戶,就把家里的值錢東西藏起來,以示貧困,意圖得到更多的物資幫扶。還有一些貧困戶在政府幫扶下進城找到工作,但干了幾天就不想干了。這種簡單輸血式扶貧,結果反而使不少農村滋生了一大批“被動懶惰”的人。二是扶貧對象的致富信心缺失。從根本上來說,要想真正脫貧還要先扶智、扶心、扶技。前期扶貧工作的開展不注重激活發展動力,村民思想并未轉變、發展技能也未得到提升,致富信心極度缺乏,這也是韓永明在小說里塑造的類如牧羊人老萬等人物形象,他們從小生活在貧困鄉村,對當代新興科技一無所知,唯有腳下的土地才讓他們覺得踏實,這些人更需要扶貧干部深入基層,切實做好扶貧脫貧的思想工作,首先就是幫助他們樹立脫貧信心。
韓永明在小說中不僅將眼光投射在了前期扶貧出現的問題上,同時也關注到正在變化著的扶貧方式。小說中的香云、夏香久等人利用微信朋友圈、互聯網直播平臺將鄉村的農產品、鄉野生活方式兜售展示給城里人,這充分體現了韓永明對農民精神生活變化的關注,以及到對國家發展中底層人民生活最關切地思考。從城鄉二元對立,到外來者入鄉,韓永明立足鄉村實際,刻畫鄉村新面貌新事物,觀察扶貧干部工作方式的轉變,挖掘扶貧對象貧困原因,這種尊重社會現實,冷靜理性展現鄉村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態度和方法,無疑填補了扶貧文學這一新領域的空白。
三、從再現典型到進場寫作
從解綁土地到重新回歸土地,從城鄉二元對立到外來者入鄉,韓永明將自己對鄉土中國的觀照始終落實在“土地”與“人”。誠然,鄉土文學作家大都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力圖真實客觀地反映人民生活的現狀,對自然或當代生活作出準確的描繪和體現。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就自稱是法國社會的“書記員”,其作品深刻體察人性,塑造出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繪廣闊的、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圖景。韓永明的鄉土小說創作遵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手法,真實地呈現當下的鄉村,創作出了具有時代精神的新形象。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原則之一。韓永明作品中的人物在具體生活環境中個性鮮明,是不同于以往的新人物。在《酒是個鬼》中,扶貧干部王大用費盡心力幫助偏執的石頭脫貧,在《小羊咩咩》中,駐村干部王大麻、小楊、小魯隊長想方設法三次請老萬下山住扶貧房;在《春天里來》中,夏香久披荊斬棘,一定堅持要種老玉米種子;在《我們結婚》中,村官小鄺在扶貧工作的開展中給余哈兒與李桂歪打正著湊成美好姻緣的故事。韓永明塑造了一系列“偏執”的人物形象,其筆下的人物“認死理”,但又向往美好的生活,形象各具特色,極大地豐富了扶貧文學的人物畫廊。用人物性格發展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典型人物的性格處于典型環境之中,這也使得扶貧工作的困難成為現實之必然。其扶貧小說專題以八個主要文本為依托,如以《鷓鴣天》為代表的早期作品中,韓永明較好地用小說的形式表現扶貧行動,呈現了扶貧工作的脈絡,也體現了農村人民的生活從物質追求向精神追求的轉變。
關注社會轉型期間人們的心態變化,人的自我成長,是文學書寫一個永恒的話題。“藝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個老話題,將生活升華為藝術,首先必須要有生活。”④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影響也是值得關注的。汪曾祺與高郵文化、沈從文與湘西文化、張愛玲與上海文化、莫言與高密文化,地域文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家的思考方式與創作特色。韓永明用“進場寫作”的方式,按照他所了解所熟悉的現實生活的具體狀貌及本來特征,形象的真實描寫,揭示出了現實生活的內在特征。
文學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國家政策的發起與推行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人的生活方式,而文學也會無可避免地反映生活的變化。以扶貧題材文學創作為例,國家和政府從“輸血式扶貧”到“開放式扶貧”的轉變,真實客觀地展示了當代新農村農民生活的發展變化,農村生活已然不再是曾經的落后、愚昧,其接受新思想與新技術的速度正加快縮小城鄉差距。從聚焦土地與農民問題,到關注城鄉結合發展改革中農村生活的變化,韓永明的小說無疑真實地反映了現代中國在社會精準扶貧政策引導下新鄉村面貌的變化,以及新農民思想深度及接受先進文明的程度的精神變化。
文學應把握時代的脈搏,反映時代的呼聲,真實客觀地揭示人民生活的新變化、新氣象。新鄉土觀照下的扶貧書寫呈現出一種全新的矯健姿態,并以此助力鄉村文化倫理建設,這應該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但“文學并不能給予這種重建做出評判,它要做的事是呈現和參與這種重建,從而使生活變得更合理”⑤。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傳統鄉村的書寫模式已不能適應新的歷史視野和理論資源的表達需要。韓永明在扶貧文學的鄉土書寫中將眼光投射至新鄉土背景下黨和國家對于鄉村的扶貧工作,試圖在文學作品中以深沉的思考、細膩的筆觸、豐富的感受來觀照當下新鄉土文學的時代主題,轉變扶貧書寫的表達方式,實現新的美學表達與價值線索,這無疑是韓永明對當下農村題材創作的突出貢獻。
注釋:
①費孝通:《鄉土中國》 (修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② 李建民:《中國鄉土文學的“中間性”表述》,《文藝報》2009年2月5日。
③周新民:《現實比文學更精彩——對話韓永明》,《文學教育(上)》2019年第2期。
④⑤吳佳燕、韓永明:《尋找鄉村題材創作新的審美表達》,《長江文藝》2020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