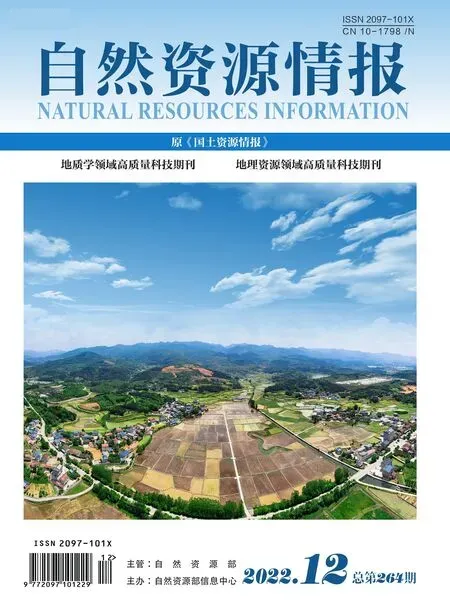中央財政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構建與應用
周海東,張慧君,王 雪
(中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院,北京 101149)
自1999年我國開始在新一輪國土資源大調查中設置地質調查項目以來,為規范地質調查項目管理,以《中央財政地質調查項目管理辦法》(國土資規〔2016〕19 號)提出探索開展重點項目實施效果評估為標志,推進了相關試評估工作。作為地質調查項目監督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門,自然資源部不斷完善管理制度體系,目前已初步構建地質調查預算績效管理制度框架[1],有效促進了地質調查項目質量的提高。但由于地質的復雜性,其成果不確定性較強,因此地質調查項目質量效益難以量化。隨著建立與公共財政框架相匹配的績效評價體系的財政體制改革的推進[2],特別是《關于印發中央財政地質調查項目管理辦法的通知》(自然資辦法〔2021〕17 號)將“監督和指導中央財政地質調查項目實施,并通過第三方對重點項目實施效果進行評估”作為地質調查項目管理的重要辦法。然而目前管理實踐中并未明確實施效果評估的具體方式方法,學界有關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的研究亦不多見,因而開展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研究具有現實迫切性。
1 地質調查項目評估研究綜述
自1988年國家計委正式委托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進行第一批國家重點投資項目的后評價開始,我國政府投資項目評價在我國得到了快速發展,一些政府部門相繼開展了本部門項目的后評價工作。在評價實踐的引領下,2003年,中央明確提出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2008年,國家發改委頒布了《中央政府投資項目后評價管理辦法(試行)》,由此我國政府投資項目后評價制度正式形成。隨著我國財政投資項目績效評價制度建設的推進,地質調查項目績效評估逐步為學界關注。2001年,任景明等重點考慮直接經濟效益、間接經濟效益、地質調查研究程度、潛在資源保證程度、地質災害社會效果、技術進步、成果信息量7 個方面的指標[3];2012年,王文等構建了包括績效目標評價體系(用于事前評價)、項目績效評價體系(用于事中、事后評價)在內的地質調查項目績效評價模型[4];2020年,瞿永澤等提出地質調查項目績效評價工作中存在績效指標設置不科學,部分定量指標缺乏,過于注重績效指標形式合規性等問題[5];2020年,游曉梅從投入、過程、產出、效果四個方面構建了公益性資源與環境調查項目績效評價指標體系[6]。
綜合相關研究,相關研究多重在尋求反映地質調查項目支出績效評價成效指標,而圍繞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開展的研究并不多見,部分研究將項目實施效果作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一部分內容進行考量,關于中央財政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的定量評價幾近空白。因此,本文旨在嘗試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為準確評估、科學指導地質勘查項目投入和引領支撐自然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創新提供基礎支撐。
2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的基本考量
2.1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的內涵與認識
中央財政地質調查項目(以下簡稱“地質調查項目”)作為國家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7],是由中央政府財政資金開展的基礎性、公益性和戰略性礦產勘查[8]最重要的載體,在全國地質勘查工作中發揮著引領和示范作用,其實施效果對地質工作保障國家能源資源安全和支撐生態文明建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推進全國地質勘查行業高質量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關乎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探索開展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對于改革創新地質調查項目監管方式、引領支撐自然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創新、提升地質工作決策管理具有重要意義。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全面實施績效管理的重大戰略部署為重要指引,以推進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和改革創新地質調查項目監管方式為雙重主攻方向,以支撐自然資源高質量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作用的發揮為總體目標,持續推進地質調查項目組織實施順暢、成果質量提升。
2.2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總體思路與基本原則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構建應圍繞地質調查項目實施的相關要求,以項目績效管理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為依據,借鑒相關經驗,按照地質調查項目管理的內在邏輯組合形成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圍繞提升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相關指標體系構建應堅持以下原則:一是目標導向性。要遵循地質規律和地質工作規律,聚焦地質調查項目管理決策、實施運行和監督管理中存在的關鍵問題,指標選取應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性,引導地質調查項目實施從“重設計”轉向“重實施”,從“成果數量增加”轉向“成果質量提升”,從“績效管理驅動”轉向“成果轉化驅動”,通過評估引導提高地質調查項目的實施質量和監管實效性。二是科學性。要遵循項目管理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兼顧自然資源管理能力與水平的現實性,以及地質調查項目管理的必要性,依據科學理論與相關指標標準,科學確定指標。三是可測度性。指標體系要具有易獲取、較穩定與可靠數據來源,便于動態監測與評估。
3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構建
3.1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設置總體情況
緊扣地質調查項目管理的內在邏輯,確定立項效果、組織效果、實施效果3 個主題。每個主題下,按照地質調查項目管理的程序與內容,結合地質調查項目自身特點構建立項依據、目標任務、技術路線、部署安排、成果質量、成果轉化6 個一級指標。圍繞一級指標,確定可以全面反映一級指標屬性的更為細化的二級指標14 項,包括立項必要性、立項充分性、目標任務、技術路線、技術方法、工作部署、工作量、目標完成率、成果規范性、成果水平、成果可靠性、成果應用、學術成果轉化水平、學術成果轉化數量。
3.2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及其內涵
立項必要性主要評估立項是否符合中央財政地質工作的定位;立項充分性主要評估項目預研究水平;目標任務主要評估目標任務是否明確,主要考察項目制定的目標任務是否具體、集中,是否便于考核;技術路線主要評估技術路線能否滿足完成項目目標任務、完成工作內容的需要;技術方法主要評估項目實施采用的技術方法是否科學、合理,是否符合綠色勘查要求;工作部署主要評估工作部署和安排是否合理,是否重視環境保護;工作量主要評估工作量是否圍繞目標任務布置;目標完成率主要考核取得成果與預定目標的符合度;成果規范性主要評估成果報告規范性和可讀性;成果水平主要評估項目發現和創新;成果可靠性主要評估成果結論的可靠程度;成果應用主要考察成果或相關對策建議的使用效果和頻次;學術成果轉化水平主要考察發表論文期刊、發明專利、著作的綜合水平;學術成果轉化數量主要考察在核心及以上期刊發表相關論文的數量(表1)。

表1 中央財政地質勘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
4 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指標體系應用實證分析
4.1 評估過程
采用隨機遴選方法,選取了14 個單位承擔的16 個二級項目作為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實證案例,包括5 個基礎地質調查類項目、4 個環境地質調查類項目、4 個礦產地質調查類項目和3 個地質科技和信息化類項目。16 個項目分布于7 個計劃、15 個工程中,案例項目分布相對均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專家評議法和統計分析法相結合,分別對抽樣項目進行評估。第一步,對抽樣項目進行評估。在評估過程中,首先,專家組中的各專家根據項目單位提交的成果資料情況,結合相應的指標體系,分別對抽樣項目各指標進行評分;其次,利用平均值法計算出項目的各指標及總的實施效果評分;最后專家組編寫評估報告,對抽樣項目的各指標及總的實施效果進行評述,總結抽樣項目優點和不足,提出改善建議。通過對抽樣項目評估,一方面起到抽查的作用,為項目監督管理提供技術支撐;另一方面,抽樣項目評估結果為下一步綜合評估提供了基礎信息。第二步,綜合評估。利用統計分析方法,對所有抽樣項目及其各指標評分結果進行統計,總結所有抽樣項目在立項、組織實施、成果質量和成果轉化等方面指標評分的分布規律,結合抽樣項目的評估報告和對項目組補充調研了解項目實施過程中的經驗總結和遇到的問題、難題,分析總結抽選項目周期內項目實施效果的經驗和不足,提出對策建議,為優化項目管理和制定下一步項目規劃決策提供依據。
4.2 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表明,地質調查項目總體實施效果良好。16 個項目實施效果均達到優良級,其中6 個優秀級,10 個良好級(圖1)。總體上,項目都取得了良好的地質成果和理論成果,符合中央級地質勘查項目基礎性、戰略性的定位,并在全國地質工作中發揮了較好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圖1 案例項目三個主題平均評分
第一,立項方面。設立的項目符合中央級項目定位,但項目的預研究水平(對應立項充分性指標)偏低。16 個案例項目中,有13 個項目立項必要性指標評分超過90 分,優秀率81.25%。立項充分性指標,有9 個項目評分超過90 分,優秀率56.25%。立項充分性水平對是否會重復立項或者更好地利用已有工作基礎信息、合理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工作量有重要影響,關乎經費使用效率的高低。評估結果顯示,低于立項依據指標。究其原因,地質調查項目管理機構和組織實施單位十分重視項目立項環節,尤其是在選題方面,每年均會根據國家重大需求,增設急需地質項目或臨時調整已設項目目標任務,所以項目立項均切中了國家所需,因而項目制定的目標任務也較為明確。項目預研水平相對較低,除受限于項目團隊研究能力水平外,更主要的是受預研時間不足的影響。每輪或每年立項的時間正是全國大部分地區野外作業的黃金期,尤其是我國北部,適合野外作業的周期較短,立項時期相關人員大多忙于野外生產,難以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對項目實施地區以往研究成果進行收集和系統總結。
第二,組織實施方面。地質調查項目工作部署總體良好。16 個案例項目中,項目部署平均評分為87.75 分。其中,4 個項目的評分超過90 分,優秀率25%。根據規定,項目需編寫項目總體實施方案,根據目標任務和工作內容對總體項目進行系統的部署安排,且每年編寫年度工作方案,根據年度目標任務進一步深化、細化工作部署。根據近年來的經驗,一般來說,地質調查項目“一上”(立項或續作可行性評估)階段完成后,部分項目“二上”(編寫工作方案)階段會進一步縮減經費,但此時項目已經入庫,制定的目標任務和績效目標難以調整,這導致了項目經費與目標任務和工作內容、工作量的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項目的組織實施和工作部署。
第三,成果質量方面。地質調查項目總體成果質量良好,目標完成率普遍高,但成果集成創新和轉化應用較弱。16 個案例項目中,實施效果指標平均為88.96 分;其中,6 個項目超過90 分,優秀率37.5%。項目目標完成率指標評分最高96.4 分,最低87.6 分,平均為92.06 分;其中,13 個項目超過90 分,優秀率81.25%,這表明地質調查項目績效完成情況普遍好。究其原因,地質調查項目成果驗收管理采用績效目標管理,即項目立項之初每年編寫年度工作方案要填寫年度績效目標表,明確項目擬完成的各方面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在項目成果驗收時,對照項目績效目標進行考核驗收。這種定量化管理方式具有剛性約束效應,項目承擔單位和項目組較重視績效目標數量指標的完成。與之相對應的,包括項目的新發現、新理論、新工藝、新方法、新標準等在內的項目成果水平稍顯遜色。16 個案例項目中,成果水平指標平均得分88.81 分;其中,超過90 分的項目6 個,優秀率37.5%。主要問題表現為項目成果綜合分析、提煉深度不夠等。究其原因,除績效目標管理方式導致項目單位和項目組不夠重視綜合分析、總結提煉定性指標的因素外,還與地質調查項目經費逐年減少密切相關,每年增設項目對已有部分項目經費產生了一定擠壓效應,導致一些項目調整目標任務、壓縮工作量,這些被迫調整的項目的組織實施和成果的完整性、質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四,成果轉化方面。地質調查項目成果轉化應用效果不夠好,對基層單位的服務支撐有待加強。16 個案例項目中,平均評分89.04 分;其中,評估得分超過90 分的項目有4 個,優秀率占25%。通過對所有案例項目評估報告內容進行分析,發現地質調查項目普遍對政府工作的支撐作用顯著,但向基層單位轉化應用的積極性不夠高,實際服務支撐有待加強。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圍繞地質調查項目的立項效果、組織效果、實施效果3 個主題,構建了14 項指標的評估指標體系。地質調查項目實施效果評估是一項創新性研究,其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有待不斷完善。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和嘗試,有待繼續優化,比如指標體系有待在實踐中運用、修正與檢驗。此外,地質調查項目目標任務差異明顯,服務領域廣,不同類型項目服務對象差異大,產生效果的方式、途徑等方面差異化較大,為準確地評估各類項目實施效果,有必要根據項目實施效果的特征分類探索構建分類型的評估指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