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共同體問題的范式轉(zhuǎn)換:一個(gè)黑格爾辯證法批判的特殊視點(diǎn)
陳 琦
(復(fù)旦大學(xué) 文學(xué)院,上海 200433)
柏拉圖“四書”(《普羅塔戈拉》《會(huì)飲》《斐德若》《斐多》)開啟了西方哲學(xué)對(duì)“愛”的思考,其中以《會(huì)飲篇》的討論最為全面。這篇文本贊頌愛神,將愛的地位全面拔高。它通過雅典名醫(yī)厄里刻希馬庫斯、喜劇家阿里斯托芬、悲劇家阿伽通等人的論辯表明了:愛不止是肉體的享樂要受靈魂的駕馭,愛更多是二分的,既在肉體之內(nèi)也在靈魂之中;它可以調(diào)節(jié)存在于身體、精神乃至宇宙萬物間的對(duì)立元素,是溝通人與人、世俗與神圣之間的媒介,幫助生命通往善與永恒,回歸原初的完滿狀態(tài)。在文本高潮部分,蘇格拉底登場總結(jié)道,“愛介于兩端之間”[1],它所渴求的是它缺乏的東西,而缺乏的東西集中表現(xiàn)為生命的變化無常和其可朽性。也就是說,《會(huì)飲篇》對(duì)愛的定義為愛與哲學(xué)的關(guān)系奠定了這樣的認(rèn)識(shí)論范式:(1)愛是思維活動(dòng)的內(nèi)在驅(qū)力;(2)愛使人意識(shí)到自我的匱乏并使自我外化;同時(shí)留下了一個(gè)公案——愛是否可以調(diào)節(jié)二元分裂,它是否意味著一種和諧的狀態(tài)——這是蘇格拉底沒有講清楚的部分。其后青年黑格爾在對(duì)自然之愛、宗教之愛的闡釋中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且這種愛的形象已經(jīng)顯現(xiàn)了辯證法的雛形。
而在黑格爾之后,學(xué)者們給出了諸多反對(duì)意見,這些意見逐漸構(gòu)成對(duì)辯證法的批判。海德格爾在1932年夏季學(xué)期研討班(整理講稿為《研討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中討論《斐德若篇》時(shí)提出,愛是無法完成的統(tǒng)攝運(yùn)動(dòng),它只欲求存在卻不達(dá)到存在,愛的運(yùn)動(dòng)不完滿也不停歇。[2]《色情史》《愛神之淚》中的巴塔耶更為激進(jìn),他關(guān)于“耗費(fèi)”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把愛的運(yùn)動(dòng)方向倒轉(zhuǎn)過來,說愛不是填滿自我而是掏空自我,是與勞作相對(duì)立的情色活動(dòng),是無目的、非生產(chǎn)性的“耗費(fèi)”[3],愛意味著分享、犧牲、獻(xiàn)祭和死亡。這種愛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確立了一種反傳統(tǒng)共同體模式的“共同體”(communauté,也有譯作“共通體”),并為其后的南希、布朗肖、德里達(dá)所繼承。“情人共通體”“友愛的政治學(xué)”,他們?cè)谶@條路徑中發(fā)掘的愛之哲學(xué),呈現(xiàn)出政治倫理實(shí)踐層面的轉(zhuǎn)向,且明確把黑格爾及其辯證法思想視作政敵。到這里,當(dāng)代法國哲學(xué)似乎是要與黑格爾勢(shì)不兩立的,但明顯事實(shí)并非如此,尋其發(fā)展的根源,其中一條主線是科耶夫引入黑格爾后所開啟的“欲望”之思,而對(duì)愛與共同體的思考正包含在其中。那么我們是否可以順著這條“愛的哲學(xué)”的脈絡(luò),發(fā)掘黑格爾與南希、德里達(dá)為代表的當(dāng)代法國哲學(xué)之間的連接和變異之處呢?借此或許可以弄清楚愛在掙脫完滿、和諧的意味之后究竟要走向何處——首先需要關(guān)注一個(gè)現(xiàn)象,就是黑格爾討論愛的過程本身就存在一次轉(zhuǎn)向。
一、黑格爾論“愛”的多重面向:辯證法的雛形到普遍倫理的載體
(一)早期黑格爾論“愛”:愛作為生命的驅(qū)力和回歸點(diǎn)
法蘭克福時(shí)期的黑格爾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運(yùn)》等神學(xué)著作中,表現(xiàn)了他對(duì)“愛”的極高期待。黑格爾以為的愛不僅是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即溝通在耶穌與信徒之間、親如兄弟的信徒之間的神圣之愛,受到古希臘靈欲觀的影響,尤其是柏拉圖《會(huì)飲篇》和亞里士多德“努斯”精神的啟發(fā),他將愛界定為一種“美的直觀”或“生命沖動(dòng)”。黑格爾認(rèn)為,愛是一種出自生命本性的具有創(chuàng)生性的主體精神,是純粹直觀的感性體驗(yàn),愛的體驗(yàn)可以打破個(gè)體的有限性并獲得全體感,可以調(diào)和生命存在的分裂。分裂帶來了現(xiàn)實(shí)和思想上的苦難,它具體呈現(xiàn)為兩方面的來源:一是猶太教為代表的實(shí)定性宗教,二是康德哲學(xué)尚未能克服的二元論思想。黑格爾試圖借助對(duì)猶太教的批判完成對(duì)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二元論的克服。它們的共同點(diǎn)在于建構(gòu)了具有無限力量的異己客體,這個(gè)客體無法為主體把握,需要主體作為奴仆臣服于它的暴力。因此就有了挪亞的洪水神話和亞伯拉罕殺子的故事。黑格爾說猶太神話首先把自然、現(xiàn)實(shí)和人的本能建構(gòu)作敵人,唯有依靠征服、統(tǒng)治和立法的手段,在有限的范圍內(nèi)才能獲得和平和安寧。人不是對(duì)外在于它自己的東西施以壓制,就是使自己作為客體服從于外在的東西,這產(chǎn)生了:(1)一種具有排他性的道德律;(2)強(qiáng)調(diào)占有、分割的財(cái)產(chǎn)概念;(3)律法對(duì)于個(gè)人而言的絕對(duì)權(quán)威、絕對(duì)義務(wù);(4)一個(gè)被要求克制自我意識(shí)的有限的人。因此黑格爾認(rèn)為,要抵抗實(shí)定性宗教和異己客體帶來的暴力,就必須釋放人的主觀性、能動(dòng)性和自我意識(shí),而支持它的核心能量就是“愛”。
“猶太教的命令要求單純地對(duì)主的崇拜、直接的奴役,無歡樂、無人情、無愛的服從,與崇拜神的命令正相對(duì)立,耶穌提出了人的沖動(dòng),亦即人的需要。由于宗教行為是最精神性的、最美的,是在發(fā)展過程中還必然分離開的東西中尋求統(tǒng)一的努力,也是把這理想中的統(tǒng)一性表明為充分存在著、不復(fù)與現(xiàn)實(shí)相對(duì)立的東西。”[4]黑格爾在基督教中發(fā)掘出一種關(guān)懷個(gè)人意志的愛與美的精神,這種精神旨在尋求主體與客體、個(gè)人與全體、意識(shí)與現(xiàn)實(shí)的和解:它將異己客體的強(qiáng)權(quán)、暴力視作生命的缺陷,是自我意識(shí)外化、斷裂的產(chǎn)物;在愛的驅(qū)動(dòng)下,通過純粹直觀的感性體驗(yàn),自我意識(shí)到這個(gè)缺陷和分裂,認(rèn)識(shí)到每一個(gè)生命的存在、每一股力量都是生命的全體,于是生命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回歸自我、成全自我,重新進(jìn)入友愛——對(duì)于異族人、陌生人,我們也要愛他;沒有征服和統(tǒng)治,相應(yīng)地也就沒有奴役、沒有財(cái)產(chǎn),愛是饋贈(zèng)和禮物;所有的人都在一種和諧的愛的關(guān)系中“共鳴”著,共同感受生命自發(fā)的自由、愉快。[5]
總的來說,青年黑格爾將“愛”理解為一種統(tǒng)一了肉體和精神并以生命存在本身而呈現(xiàn)的感性和諧,它存在于知性、概念之前,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生命活動(dòng)的源泉。愛雖然初步解決了二元分裂的問題,但同時(shí)也顯現(xiàn)了它的局促性——黑格爾說分裂(即自我意識(shí)的外化與客觀化)與和解都是生命本身,這意味著生命是一個(gè)自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fā)展過程。顯然,感性、知性、理性都是生命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愛作為整個(gè)生命歷程的核心驅(qū)力,它不應(yīng)該是靜態(tài)、前歷史與非理性的,生命的和解不應(yīng)該回歸到感性直觀的幼童階段,否則就要被揚(yáng)棄掉。于是神學(xué)論以后的黑格爾對(duì)此進(jìn)行了修正。
(二)神學(xué)論以后的修正:愛的揚(yáng)棄過程與其抵達(dá)的國家共同體
早期黑格爾所論述的“愛”,具有原始、直觀、非理性甚至無產(chǎn)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特質(zhì),自《精神現(xiàn)象學(xué)》時(shí)期開始,他就揚(yáng)棄了神學(xué)論階段的選擇,愛所引起的欲望和熱情仍然是生命活動(dòng)的內(nèi)在驅(qū)力,但不再作為生命的回歸點(diǎn)。他說,宗教所指示的愛與美與神圣的精神只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直接性,一種“自己愛自己的游戲”,沒有正視真理發(fā)展運(yùn)動(dòng)過程中的外化問題。愛的感性直觀導(dǎo)致二元分裂的困境簡單化了,從分裂到和解實(shí)際經(jīng)歷了一個(gè)曲折漫長的中介過程。哲學(xué)需要繼續(xù)思考如何克服分裂,但它已經(jīng)走出了愛的素樸階段,人類自我意識(shí)的覺醒恰恰源自亞當(dāng)、夏娃對(duì)上帝之愛的背叛。在經(jīng)歷了偷吃禁果后的首次反思,人類意識(shí)到了自我,也和自然的直接存在、感性直觀分裂開了。這種分裂是必經(jīng)的階段,如果他沒有繼續(xù)向前尋求更普遍的知識(shí)而是困頓于個(gè)人有限的知性,甚至返回到更早的感性階段去追尋自然欲望的滿足,那么他就陷入了一種主觀的有限性。
黑格爾認(rèn)為有兩種障礙橫亙?cè)诙至训镍櫆现希环N是實(shí)定性宗教代表的異己客體,一種就是為私欲和偶然性支配的有限主觀性。因此思維為了達(dá)到真理和自由,既需要從異在的客觀化走到自在的主觀意識(shí)的覺醒,也需要從主觀意識(shí)的有限性、個(gè)別性走出去,通過不斷的否定、揚(yáng)棄、否定之否定,抵達(dá)與普遍物相統(tǒng)一的客觀精神。并非要回歸原初的動(dòng)物性的自然和諧,而是走出分裂以后人類意識(shí)自身和自身、每一環(huán)節(jié)和每一環(huán)節(jié)的結(jié)合,從自在的生命存在走向積極的自為的生命存在。這一最高階段被黑格爾命名為“愛”:“思維就是一種解放,而這種解放并不是逃避到抽象中去,而是指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事物通過必然性的力量與別的現(xiàn)實(shí)事物聯(lián)結(jié)在一起,但又不把這別的現(xiàn)實(shí)事物當(dāng)成異己的他物,而是把它當(dāng)成自己固有的存在和自己設(shè)定起來的東西。這種解放,就其是自為存在著的主體而言,便叫作我;就其發(fā)展成一全體而言,便叫作自由精神;就其為純潔的情感而言,便叫作愛;就其為高尚的享受而言,便叫作幸福。”[6]因此,結(jié)束了神學(xué)論的黑格爾與其說是揚(yáng)棄了愛,不如說他將愛的考察范圍擴(kuò)大了,愛不再是美的直觀或者情感、欲望的自然活動(dòng),它是絕對(duì)理念的化身,是一種理智的愛,一種生命精神;愛所涉及的倫理關(guān)系跳出了自然、家庭和宗教的限定,抵達(dá)了共同體的普遍倫理。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黑格爾拿“理性”“科學(xué)”等概念去修正愛的界限的同時(shí),他早期思考愛的基本邏輯沒有發(fā)生改變。我們看到,黑格爾提出以基督教代替猶太教,不僅因?yàn)楠q太教是實(shí)定性的,而基督教以人能動(dòng)的主觀性為出發(fā)點(diǎn),同時(shí)也因?yàn)榛浇桃馕吨环N更普遍的倫理關(guān)系——即放棄財(cái)產(chǎn)的占有,超越血緣宗族的聯(lián)系,最終指向“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的博愛精神——基督教建構(gòu)了一個(gè)超自然的更具普遍性的“愛的共同體”。也就是說,神學(xué)論階段的黑格爾就已經(jīng)在考察倫理問題,且他考察的著力點(diǎn)在于推進(jìn)考察的主體視角以尋求對(duì)于倫理行為的普遍規(guī)定性。他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說對(duì)于倫理行為的規(guī)定性,如果從家庭倫理這種個(gè)別有限的現(xiàn)實(shí)中尋求就過于狹隘了,所以在神學(xué)論階段他選擇參照基督教的超自然倫理,而后他又意識(shí)到了宗教本身的有限性,于是他轉(zhuǎn)從“理性國家”的角度入手。
黑格爾認(rèn)為,決定家庭成員之間倫理關(guān)系的并非是直接存在的血緣關(guān)系或情感關(guān)系,更不能著眼于某種特定功能,比如:認(rèn)為組建夫妻關(guān)系是為了滿足性快感的需求以及生育義務(wù)(這意味著人的動(dòng)物化);或把家庭視作為一個(gè)經(jīng)濟(jì)單位,起決定作用的是權(quán)力財(cái)產(chǎn)的繼承、分配(即人對(duì)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絕對(duì)服從);以及認(rèn)為家庭關(guān)系的主軸是“父母-子女”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父母掌控著對(duì)子女的生殺大權(quán),而子女的成長意味著父母的衰亡(子女是父母的奴隸,也是父母潛在的敵人,他們互為彼此的異己客體)。黑格爾說,倫理行為的基本前提首先是人的自由,它所關(guān)涉的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個(gè)體,所以首先要揚(yáng)棄倫理關(guān)系中的個(gè)別元素,比如人的動(dòng)物本能、自然存在,以及財(cái)產(chǎn)、權(quán)力等異己客體對(duì)自我意識(shí)的限制與壓迫;而當(dāng)人走出了有限的家庭關(guān)系,去尋求更普遍的規(guī)定性時(shí),他可能會(huì)進(jìn)入宗教社團(tuán)的階段但卻不應(yīng)該只停留在這個(gè)階段。黑格爾指出,宗教社團(tuán)“在它的這種自我意識(shí)里還沒有得到完成”[7],宗教的虔誠精神沒有認(rèn)識(shí)到他者是內(nèi)在自我意識(shí)的外化,反而當(dāng)作是外來、異己的恩賜;自我意識(shí)還沒有意識(shí)到自我,甚至放棄了自我潛在性的實(shí)現(xiàn)——宗教的和解就是立基于自我與他者之統(tǒng)一關(guān)系的純粹否定和對(duì)遙遠(yuǎn)統(tǒng)一未來的承諾。“這永恒的愛,它只是感覺到,但沒有作為現(xiàn)實(shí)的直接的對(duì)象在它的意識(shí)內(nèi)直觀到。因此它的和解只是在它的內(nèi)心里,但同它的意識(shí)還是分而為二的,并且它的現(xiàn)實(shí)性還是破碎而不完整的。”[8]黑格爾指出了宗教倫理的核心是異在的精神實(shí)體,宗教之愛仍然保留了自我與他者、意識(shí)與現(xiàn)實(shí)二元分裂的困境,因此從這個(gè)階段開始,黑格爾的“理智之愛”揚(yáng)棄了存在于家庭中的有限的自然關(guān)系和情感關(guān)系,揚(yáng)棄了宗教對(duì)愛的永恒承諾,在“理性國家”這里正式出發(fā)。愛經(jīng)歷了漫長的揚(yáng)棄過程,最終和人的最高自由以及實(shí)現(xiàn)最高自由的國家共同體合一。而這個(gè)階段的“愛的哲學(xué)”正是后人開啟批判的關(guān)鍵戰(zhàn)場。
二、黑格爾之后“愛”的轉(zhuǎn)向:從辯證法批判到共同體重建
(一)愛與辯證法的分離:南希對(duì)國家共同體的拆解
南希曾在《非功效的共通體》的系列續(xù)篇之一《碎裂的愛》(L’amourenéclat)中談及《會(huì)飲篇》。他指出《會(huì)飲篇》給“愛的哲學(xué)”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史圖式。正如我們開頭所總結(jié)的,《會(huì)飲篇》說愛是思(pensée)開始的地方,愛給思考提供了有關(guān)匱乏的經(jīng)驗(yàn)和抵達(dá)完滿的欲求,哲學(xué)思辨就是關(guān)于愛欲的思辨。由此,愛進(jìn)入認(rèn)識(shí)論的框架并遭遇哲學(xué)的界定、規(guī)劃和分配,它被賦予總體性與矛盾性也即否定性與肯定性的雙重特征,愛是展現(xiàn)矛盾并解決矛盾、撤離自身又回歸自身的意識(shí)過程;愛首先區(qū)分開了接受者和發(fā)出者兩個(gè)互為異在同時(shí)被愛組合起來的人,換言之,愛拉開了自身與他者、同一與差異相對(duì)立的兩極,這構(gòu)成了辯證法的基本邏輯鏈條。“愛之思是辯證之思……愛提供了普遍存在的法則和邏輯。”[9]愛的哲學(xué)圖式在黑格爾那里得到了高度完成并預(yù)先設(shè)定了愛的必然命運(yùn)——愛只為辯證法服務(wù)。在辯證法之后,愛就要被拋棄、被取締了,這對(duì)應(yīng)了黑格爾神學(xué)論階段后用“理性國家”對(duì)愛進(jìn)行的收編。南希認(rèn)為,愛的哲學(xué)圖式對(duì)愛本身產(chǎn)生了遮蔽,現(xiàn)在他要說出一些有關(guān)于愛的其他可能性,并使辯證法給愛讓路。
在黑格爾那里,愛讓自我意識(shí)覺醒,通過穿越(traverser)他者而成為主體,但南希認(rèn)為,愛并不能構(gòu)成主體。愛不是完滿和諧的狀態(tài),它只提供這樣的假想和欲念,它讓自我意識(shí)和生命存在本身受到激蕩并讓激蕩的狀態(tài)持續(xù)。愛不是從我這里出發(fā),不是從我這里去發(fā)現(xiàn)他異性、穿越他者再撤回自我,它不是統(tǒng)攝的活動(dòng),不是結(jié)合再結(jié)合,而是倒轉(zhuǎn)過來,從外向內(nèi)穿透了我,是被穿透的自我向外無限展露(exposer)我的傷口。這意思是說,即使自我在表白,但“我愛你”很明顯是被普遍使用的一句話,現(xiàn)在只是發(fā)生在我身上的一個(gè)言說的行動(dòng)借用了它,而非自我占有了它或者對(duì)它作出了什么影響,反而是這句表白影響了我。言說的過程使我的生命存在被打開了一個(gè)裂口,這個(gè)裂口是用來期待他者的回應(yīng),通過排空自我,使自我成為空無,為即將到來的他者進(jìn)入我、影響我、填滿我而作出的讓位——但愛只打開裂口讓自我暴露卻不真的要填滿我,不為此作出補(bǔ)償。布朗肖也說:“如此的愛情會(huì)以損失的唯一模式來實(shí)現(xiàn)自身……并不是失去那已經(jīng)屬于你的東西,而是失去一個(gè)人從未擁有的東西。”[10]愛的確回撤到我這里,但愛或他者不能為自我所居有,愛顯示了他者于我而言不可彌合的距離,他者處在“尚未”(pas encore)或“已經(jīng)不再”(déjà plus)的位置,愛懸置了占有的可能性并昭示著自我絕對(duì)的匱乏、耗費(fèi)。
愛的真正特質(zhì)是無法居有和永遠(yuǎn)錯(cuò)過。愛無法居于主體之內(nèi),它是主體跳動(dòng)的心,讓主體綻出并擊碎了主體試圖通過自我保留得以產(chǎn)出的“存在”,愛恰恰是一種毫無保留的、在擊碎存在時(shí)發(fā)生的“與-在”。于是,對(duì)于所謂以愛之名建立的家庭、城邦、宗教、國家等倫理實(shí)體,愛從它們那里逃逸了。愛并不構(gòu)建秩序,它只使秩序解體,對(duì)愛的思考和客體化都是不可能的。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南希對(duì)早期黑格爾“無政府主義之愛”的借鑒,即愛取消了財(cái)產(chǎn)的概念、自然血緣的紐帶和權(quán)利義務(wù)的秩序。隨著《精神現(xiàn)象學(xué)》時(shí)期的黑格爾對(duì)愛所代表的更高倫理內(nèi)涵的不斷推進(jìn),從家庭到宗教社團(tuán)再到公民國家,愛最終停留在它無法推進(jìn)、確定無疑的階段——這其實(shí)也是南希所做的事情,他就站在黑格爾的這個(gè)位置持續(xù)進(jìn)發(fā),直到最后干脆連國家也不要了,他要將愛只忠誠于自己的非專有性、非功效性從哲學(xué)限定的框架內(nèi)爆裂出來。
由黑格爾到海德格爾到巴塔耶,“愛”到南希這里正式劃定了它相對(duì)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辯證法而言獨(dú)立存在的問題域。南希并不試圖讓愛去摧毀辯證法的合法性,讓愛做辯證法的敵人(實(shí)際上他保留了很多辯證法的邏輯),他是要把愛和辯證法分清楚,辯證法無法窮盡愛,哲學(xué)的言說也永遠(yuǎn)在觸及愛的同時(shí)錯(cuò)過它——唯有保持言說的姿態(tài);愛無法定性、無法分類,它在思想史上所閃現(xiàn)的唯有碎片,并且它隨時(shí)離開這些碎片。[11]或者我們可以說,南希展示出了愛在解構(gòu)意義上新的本體論圖式。當(dāng)愛從辯證法的邏輯中跳出,辯證法其愛的合法性消失以后,它所指向的國家共同體的普遍倫理就崩塌了,另一重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倫理實(shí)踐隨之浮出水面。這正是阿甘本、德里達(dá)等人的出發(fā)點(diǎn),他們找到了辯證法與戰(zhàn)爭、敵意和極權(quán)主義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二)辯證法中的敵意與暴力:阿甘本論內(nèi)戰(zhàn)
受惠于卡爾·施米特“例外決斷”論的阿甘本,一直致力于從政治的原初結(jié)構(gòu)中挖掘戰(zhàn)爭邏輯的痕跡。在其2015年短篇《停滯:作為一種政治范式的內(nèi)戰(zhàn)》中,阿甘本指出,根據(jù)妮可·羅洛(Nicole Loraux)在《家族之戰(zhàn)》(Laguerredanslafamille)中對(duì)古希臘政治史的考古,以及柏拉圖《美涅克塞努篇》等文本的記述,古希臘城邦政治建立、運(yùn)作的合法性基礎(chǔ)并非來自單一的契約精神或者至高律法,而是內(nèi)戰(zhàn)的極端情境。具體來說,就是通過激化城邦內(nèi)戰(zhàn)(stasis,也可譯為“內(nèi)亂”“內(nèi)訌”)拆解家庭自然存在的“血親關(guān)系”(kinship)以重組新的“血親關(guān)系”。[12]在城邦發(fā)生內(nèi)戰(zhàn)的時(shí)刻,每個(gè)家庭成員都被要求參與其中,即使沒有親身作戰(zhàn)或作出明確的政治表態(tài),他們也會(huì)被這場政治事件打上身份標(biāo)記,于是他們天然的血緣聯(lián)系、家庭倫理就被取消了,戰(zhàn)爭中的敵友關(guān)系成為規(guī)定他們倫理行為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就像家庭內(nèi)部存在諸多矛盾、沖突的因素(包括黑格爾討論過的對(duì)財(cái)產(chǎn)權(quán)力的爭奪、父母子女之間的生死沖突),最終能以家庭倫理的框架調(diào)和這些分裂,相應(yīng)地,城邦政治所依照的內(nèi)戰(zhàn)范式也是一種沖突再和解、矛盾與統(tǒng)一并存的政治模式——內(nèi)戰(zhàn)是注定要和解的戰(zhàn)爭。阿甘本認(rèn)為,作為古希臘城邦政治運(yùn)作范式的內(nèi)戰(zhàn)反映在當(dāng)下的政治現(xiàn)實(shí)中,其極端化的表現(xiàn)是納粹執(zhí)政期間懸置魏瑪憲法的有效性,它確立自己最高行政權(quán)的方式就是在人民內(nèi)部制造敵人。這種方式在今天的極權(quán)主義國家、種族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沖突中屢見不鮮。掌權(quán)者并不是要通過內(nèi)戰(zhàn)解散國家,而是通過劃分?jǐn)秤勋@得政治決斷的至高主權(quán)。施米特曾在《政治的概念》中提出劃分?jǐn)秤咽钦位顒?dòng)的基本準(zhǔn)則,而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指出,這種政治活動(dòng)以主權(quán)神學(xué)的形式招致了革命政權(quán)的暴行,它會(huì)持續(xù)激化內(nèi)戰(zhàn),“在一場辯證運(yùn)動(dòng)的血腥化裝舞會(huì)上,創(chuàng)造出所要求的喬裝者,將叛國的面具扣在任意選定的人的頭上”[13]。要追溯這種內(nèi)戰(zhàn)范式的理論源頭,可能還得回到黑格爾。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阿甘本內(nèi)戰(zhàn)論真正想要表達(dá)的東西——家庭、城邦與貫注其中的內(nèi)戰(zhàn)模式其實(shí)是一種辯證法的邏輯,辯證法沒有如黑格爾所愿解決暴力,而是成為了權(quán)力暴行的策略手段。一方面,對(duì)象化的否定性邏輯意味著敵人的產(chǎn)生。辯證法每一步向外的演進(jìn)都在制造敵意,而當(dāng)外化的意識(shí)向內(nèi)回撤,這種敵意就變得更為恐怖了——對(duì)自我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自我轉(zhuǎn)化,這個(gè)動(dòng)作不斷讓自我內(nèi)部產(chǎn)生敵人并且自我并不會(huì)為了敵人而解體,它會(huì)消化敵人或者說是利用敵人讓它重新成為我的盟友。另一方面,全體中的每個(gè)要素其定位都是含混不清的:就個(gè)別的現(xiàn)實(shí)來看,它是狹隘的,妨礙全體進(jìn)程的,但從其內(nèi)蘊(yùn)的普遍規(guī)定性來看,它也是為全體所用的。這使得個(gè)體要素遭遇了雙重的征用和雙重的排斥。正如城邦政治打開了家庭倫理的界限,使得每個(gè)人不再局限于自然賦予的身份,于是他在掙脫家庭限制的同時(shí)也遭遇了家庭的排斥,我的兄弟不再是我純粹的兄弟血親了,他很可能是我的敵人。個(gè)人所牽涉的家庭關(guān)系對(duì)城邦來說也是要揚(yáng)棄的部分,在更高的國家善行的要求面前,我很可能要大義滅親,否則我就是負(fù)罪者,因?yàn)槲冶撑蚜顺前钜脖撑蚜宋易约海冶粋€(gè)別有限的現(xiàn)實(shí)與意識(shí)給困住了。所以阿甘本想要指出的是,從家庭到城邦/國家共同體的演進(jìn),并不意味著自我意識(shí)、倫理行為向更高普遍性、必然性的推進(jìn),它反而讓自我意識(shí)紊亂了,因?yàn)榧彝]有消失,且和城邦之間構(gòu)成了一種張力—— “政治是政治化與非政治化,家和城邦之間的張力流不斷橫穿的場域。在這些相互對(duì)立的極點(diǎn)之間,張力彼此分離卻又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張力——用羅洛的診斷來解釋——是無法解決的……古希臘可能就是這種張力一時(shí)不確定且不穩(wěn)定而無法達(dá)到平衡的地方。在隨后的西方政治歷史中,由血緣關(guān)系或僅由經(jīng)濟(jì)運(yùn)作所主宰的,將城邦轉(zhuǎn)換為家庭或家族的去政治化趨向,會(huì)與其相對(duì)稱的也就是將非政治化的一切事物動(dòng)員起來并政治化的階段,相互交替運(yùn)作……只要‘家庭’和‘城邦’,‘私人’和‘公共’,‘經(jīng)濟(jì)’和‘政治’這兩個(gè)詞保持著即使微弱的含義,內(nèi)戰(zhàn)就不可能從西方政治舞臺(tái)上被消除”。[14]
城邦并非相對(duì)家庭而言更高程度的綜合,而是雙方持續(xù)的震蕩角逐,致使居于其間的生命無從安居,它需要隨時(shí)轉(zhuǎn)換自己的立場,隨時(shí)面臨任一方的征用與拋棄。從阿甘本的角度來看,辯證法意味著一種對(duì)個(gè)體生命實(shí)施去主體化控制的權(quán)力策略、政治程序,他通過內(nèi)戰(zhàn)論指出了黑格爾所謂“愛的哲學(xué)”的敵意所在——辯證法在轉(zhuǎn)化愛的過程中自行生產(chǎn)出敵意。南希通過從辯證法中摘出愛的獨(dú)一性存在,釋放了愛解構(gòu)共同體的潛力;阿甘本從內(nèi)顛覆了黑格爾之“愛”在倫理行為方面的演進(jìn)過程,共同體已經(jīng)崩潰了,它還在家與城邦之間來回?fù)u擺;德里達(dá)對(duì)這兩個(gè)人進(jìn)行了匯總(即使他的工作開展在阿甘本前面),他想在祛除了敵意和辯證法邏輯以后,找到重建未來人類共同體的新的可能性。
(三)“解政治化”的共同體:德里達(dá)重建“友愛-共同體”
德里達(dá)在《友愛的政治學(xué)》中提出要重建“友愛-共同體”,這個(gè)觀點(diǎn)的理論基礎(chǔ)是傳統(tǒng)共同體的崩潰。一方面是20世紀(jì) “解政治化”趨勢(shì)的來臨,社會(huì)取代了國家;另一方面是警惕這一世界趨勢(shì)的施米特所提出的“敵對(duì)的政治”,在沒能解決這個(gè)問題的同時(shí)反而進(jìn)一步暴露了傳統(tǒng)共同體的弊端。德里達(dá)指出,造成這個(gè)弊端的是辯證法的雙重邏輯——否定性邏輯制造敵人并由此獲得至高決斷力,而統(tǒng)一性邏輯以友愛之名暫時(shí)調(diào)節(jié)分裂的局面,在分裂沒能使政權(quán)解體的情況下,持續(xù)挑起內(nèi)戰(zhàn)并對(duì)人群進(jìn)行凈化。辯證法本身沒有固定的前提,但它固定下了一套分裂再和解的運(yùn)作程序,這套程序招致了權(quán)力暴行。所以德里達(dá)認(rèn)為對(duì)于“解政治化”,某種程度上算是“解-共同體化”的大勢(shì),更應(yīng)該正視它而不是以更高的決斷力去阻攔。“解政治化”釋放了一種“也許”(vielleicht,perhaps)的邏輯[15],對(duì)應(yīng)當(dāng)前的世界局勢(shì),它反映了和平與戰(zhàn)爭的界限已然模糊的事實(shí),友愛與敵意隨時(shí)轉(zhuǎn)化,沒有真正的敵人也沒有真正的朋友,敵人和朋友于在場與不在場、確定與不確定、過往與未來之間搖擺不定,世界虛無主義的內(nèi)核被暴露了。現(xiàn)在需要從虛無和匱乏中尋求一些被遺忘的線索,這個(gè)線索就是遭遇了西方政治譜系多次標(biāo)記以至于面目全非的“友愛”。德里達(dá)試圖從中清理出一個(gè)可以建立新型共同體關(guān)系的友愛模型。
德里達(dá)的“友愛”觀脫胎于南希,也受到了黑格爾極大的啟發(fā)。他模仿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推演的步驟,依次排除權(quán)力對(duì)友愛存在的征用。首先是家庭關(guān)系對(duì)友愛的限制。據(jù)德里達(dá)的考古,友愛最初是一種維系家庭關(guān)系的自然紐帶。施米特曾在《政治的概念》中指出,“朋友”一詞在德語中(Freund)的含義首先是家人,是有血緣、姻親關(guān)系的人。友愛受到作為初級(jí)經(jīng)濟(jì)政治單位的家庭的影響,它不是純粹的情感聯(lián)系,它牽涉到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長幼親疏的權(quán)力等級(jí)秩序以及生產(chǎn)、生育功能的要求。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看到了這種家庭之愛對(duì)人意識(shí)發(fā)展的局限性,而德里達(dá)則關(guān)注這種家庭式友愛,是如何進(jìn)入城邦政治、宗教社團(tuán)而成為一種策略性的生物學(xué)技術(shù),以及如何憑借人的自然聯(lián)系排斥異邦人的同時(shí)組織本邦人并使其具有團(tuán)體使命感。因此進(jìn)入宗教之愛的環(huán)節(jié)后,德里達(dá)的批評(píng)比黑格爾更加激烈了,他認(rèn)為宗教的博愛精神、信徒之間的兄弟之愛,就是家庭關(guān)系的翻版:它首先以排斥異教徒的基本原則掌控團(tuán)體內(nèi)外的所有生命,極端的原教旨主義會(huì)任意屠殺生命;其次它受經(jīng)濟(jì)邏輯的支配,強(qiáng)調(diào)平等互惠的原則,宗教之愛是一種要求回報(bào)并有固定標(biāo)準(zhǔn)能衡量、計(jì)算收支的愛;最后,宗教以誓言、盟約的形式提出約束成員的規(guī)范、義務(wù),以完成對(duì)信徒在道德倫理、思想觀念方面的規(guī)訓(xùn)和管控。德里達(dá)認(rèn)為,無論家庭或宗教,為實(shí)施對(duì)人的馴化,友愛律令都是采取否定自然生命存在并對(duì)其進(jìn)行“再度自然化”即否定的肯定性轉(zhuǎn)化的策略。[16]這種依托辯證法程序的馴化手段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生命存在的全盤捕獲和收編,被排斥的生命被重新征用來維護(hù)程序的再生產(chǎn)過程。
黑格爾在尋找倫理行為的普遍性規(guī)定時(shí)對(duì)家庭和宗教進(jìn)行了揚(yáng)棄、轉(zhuǎn)化,而德里達(dá)為尋求“好的友愛”則選擇推翻所有的友愛團(tuán)體,他推翻了友愛過往的記憶、歷史和傳統(tǒng),這意味著一種沒有本質(zhì)、根基或記憶,沒有被結(jié)構(gòu)化,沒有同一性、契約關(guān)系,甚至沒有忠誠、誓約的友愛。“好的友愛”意味著無法共同、不可共度的共同體——它是南希自我匱乏性的外展,以此方式為他者進(jìn)入自我而讓位;傳統(tǒng)友愛所強(qiáng)調(diào)的經(jīng)濟(jì)邏輯,即分享、互惠、共同占有的原則隨之不復(fù)存在,人不是共同體的附屬物,他者不是自我意識(shí)的映射,人與人的關(guān)系走出了對(duì)稱性和混融性的經(jīng)濟(jì)計(jì)算;“我愛你”表明了自我與他者之間永遠(yuǎn)的離散,以及哪怕我們無法再次相遇也在表白的瞬間被聯(lián)系在一起的確定無疑。這種友愛不是出現(xiàn)在遙遠(yuǎn)的彼岸,它發(fā)生在當(dāng)下的每一瞬間,倡議每個(gè)人都承擔(dān)起表白友愛的責(zé)任,表白友愛不是為了獲得確定的回應(yīng),它不承諾必然性,在表白如同“飛行的響箭”一般迅速的后退并穿透我的時(shí)刻,友愛是一種敞開自我的姿態(tài)。在德里達(dá)重建友愛的工作中,我們最終看到了他對(duì)黑格爾的差異性回歸。
三、結(jié)論:由馬克思回到黑格爾——專有之愛的終結(jié)與哲學(xué)、政治的“回撤”
黑格爾哲學(xué)從一開始就賦予“愛”兩個(gè)使命,創(chuàng)生性與和諧性,超越性與反思性,黑格爾對(duì)愛兩重性的思考奠定了他辯證法的基本模式。雖然神學(xué)論階段的愛表現(xiàn)為處在歷史初級(jí)階段一個(gè)靜止的點(diǎn),但它已經(jīng)為辯證法和思想的演進(jìn)歷程做好了準(zhǔn)備:愛是展露自我的缺陷和差異,這種展露建立在自我外化并從他者那回返、反思的基礎(chǔ)之上。與其說這之后黑格爾的愛被辯證法收編了,不如說它有限的界域被打開了,愛就是辯證法本身,它是生命和思想發(fā)展、揚(yáng)棄的整個(gè)過程,且在與倫理實(shí)體相結(jié)合之后,最終以公民國家共同體的形態(tài)呈現(xiàn)。這個(gè)現(xiàn)實(shí)的落腳點(diǎn)遭到了后人的炮轟。以南希、阿甘本和德里達(dá)為代表,他們接續(xù)完成了這樣的工作,從愛掙脫了辯證過程到愛自己建立起獨(dú)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體。這樣的愛沒有回到青年黑格爾的歷史起點(diǎn),即所謂的原初和諧,它完全為了他者,它擊碎所有的和諧并以擊碎的過程為真無限的存在——它與黑格爾之愛最根本的區(qū)別在于改變了一種“回撤”的方式,也就是徹底終結(jié)專有之愛的可能性,而這種范型的轉(zhuǎn)換最初是由馬克思完成的。
我們知道,從黑格爾的“理性國家”到馬克思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所發(fā)生的轉(zhuǎn)換,從生產(chǎn)方式和經(jīng)濟(jì)體制的角度來看,是勞動(dòng)分工和私有制的廢除,但從普遍倫理的角度來看,它是在試圖解決黑格爾“國家共同體”殘留的自我異化,以期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意志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真正的統(tǒng)一。黑格爾的異化問題源于他所推演的普遍國家共同體保留了私有財(cái)產(chǎn),而財(cái)產(chǎn)邏輯恰恰是黑格爾辯證法一開始就要揚(yáng)棄的東西。早在神學(xué)論階段,他就已經(jīng)指出實(shí)定性宗教強(qiáng)調(diào)財(cái)產(chǎn)和占有會(huì)導(dǎo)致人與自然、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分裂,它會(huì)激化相互征服的敵意并樹立異己客體的權(quán)威。在這之后,他又在論述人的普遍倫理規(guī)定時(shí)揚(yáng)棄了家庭對(duì)人的限定,限定性的因素就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有財(cái)產(chǎn)。現(xiàn)在馬克思順著黑格爾的辯證過程對(duì)共同體中的財(cái)產(chǎn)問題進(jìn)行清理,提出唯有在人的意志不可被財(cái)產(chǎn)衡量、規(guī)定和區(qū)分的時(shí)刻,他才是真正自由的人。自由人從他的勞作而非勞作的否定形式中獲得滿足,這意味著否定之否定過程的完成,人回到了自我本身,這個(gè)共同體才是人之為人本身的普遍倫理的實(shí)體化,而構(gòu)成這個(gè)共同體普遍原則的也由異化的客體(比如階級(jí)、財(cái)產(chǎn)、分工、國家機(jī)器)回歸到人的普遍需求。
南希在馬克思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當(dāng)下政治的“回撤”(retrait),他認(rèn)為馬克思對(duì)私有制、財(cái)產(chǎn)邏輯的廢除和對(duì)人之普遍性的解放還不夠。《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的馬克思仍然是人本主義的,他強(qiáng)調(diào)革命活動(dòng)是一種“占有”(Aneignung)活動(dòng),強(qiáng)調(diào)人對(duì)自然的創(chuàng)造和占有,人自認(rèn)為是自足的且有能力生產(chǎn)他的自然,人對(duì)自然的掌控、為自然立法的做法不是一種無限,而恰恰是一種有限的財(cái)產(chǎn)邏輯、領(lǐng)地意識(shí),人性化的自然與占有、征服的活動(dòng)成為人的終極目的。所以南希說現(xiàn)代政治學(xué)還在受著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檢查[17],這是政治總體主義和極權(quán)化的來源。政治首先預(yù)設(shè)一種以管理生產(chǎn)生命活動(dòng)為中心的家政形態(tài)(oikology),并將其作為政治的本源,于是它演化為一種對(duì)生命進(jìn)行宏觀調(diào)控與微觀馴化的“生命技術(shù)”(ecotechny)。而馬克思所謂人潛能的普遍滿足則演化成一桿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且可隨時(shí)調(diào)節(jié)的標(biāo)尺,這是自由人聯(lián)合體尚未解決的問題,它仍為權(quán)力意識(shí)形態(tài)所圍困——在這桿標(biāo)記著普遍性和共通性的確定數(shù)值的標(biāo)尺之下,人以為自己可以賦予自己價(jià)值,但實(shí)際他仍為異己的共同體所奴役。更嚴(yán)重的問題是這種政治學(xué)形態(tài)已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秩序的發(fā)展深入日常生活各個(gè)角落,“一切皆為政治”或“一切皆為經(jīng)濟(jì)”,生命技術(shù)與主體哲學(xué)相互綁定,異化的問題被無限保留。所以政治的“回撤”即是哲學(xué)的“回撤”,即是在辯證法回返到自我的時(shí)刻撤出對(duì)自我和他者的占有,撤出主體完整統(tǒng)一的存在,這種“回撤”即是南希所謂的愛粉碎一切的“解總體化”的力量。
反過來說,這解釋了為什么法國哲學(xué)的辯證法批判會(huì)從對(duì)愛欲的思考入手,從愛所意味的政治倫理實(shí)踐入手。辯證法的批判工作本身就與一種無產(chǎn)主義的政治立場緊密結(jié)合。他們與黑格爾的連接點(diǎn)是通過馬克思對(duì)勞動(dòng)和私有制的廢除,同時(shí)借助愛的匱乏性、碎片化及它對(duì)自我的離棄,進(jìn)一步掃蕩資本主義權(quán)力現(xiàn)實(shí)所蘊(yùn)含的占有邏輯和異化邏輯,包括辯證法作為權(quán)力策略對(duì)人的雙重征用和雙重排斥。于是到了德里達(dá)的“友愛-共同體”那里,愛重建了這樣的局面——政治回到了它本身,它是不可共度性,是絕對(duì)的外展和絕對(duì)的赤裸,政治決斷是對(duì)不可決斷之物的決斷,擊碎了所有規(guī)則固有的合法性,并在此過程中形成“離散的綜合”(disjunctive synthesis)。這就是巴迪歐所謂的“一個(gè)事件激活了一個(gè)普遍化的獨(dú)一進(jìn)程”[18],普遍性不再是一個(gè)固定的終點(diǎn),它是一個(gè)獨(dú)一的行動(dòng)或事件所開啟的內(nèi)爆的整個(gè)過程;它將揚(yáng)棄的“回返”轉(zhuǎn)換為“回撤”,不僅是對(duì)黑格爾辯證法“他異性”的繼續(xù),更標(biāo)示了思想是開啟普遍性并切中現(xiàn)實(shí)的媒介。“不論那時(shí)的‘揚(yáng)棄’是什么意思,哲學(xué)的自我揚(yáng)棄一直延續(xù)至今,成為思想的唯一任務(wù),成為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共同的工作。”[19]黑格爾以后對(duì)愛的思考承擔(dān)了這樣一種責(zé)任,即通過承接、轉(zhuǎn)換黑格爾揚(yáng)棄工作的思想范式,通過終結(jié)愛的專有性,以“回撤”呈現(xiàn)哲學(xué)與政治共謀的可能性以及“解總體化”后思想“溢出”自身而全面推進(jìn)現(xiàn)實(shí)的總體局面。“一切為了他者”“一切向著他者”,已然從認(rèn)識(shí)論的樊籬中掙脫出來,發(fā)展成為一種主動(dòng)為他人擔(dān)責(zé)的政治倫理實(shí)踐目標(biāo)。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法國哲學(xué)歸根結(jié)底是在思考資本主義全球化秩序所內(nèi)含的極權(quán)主義隱患,他們?cè)噲D構(gòu)建新型的共同體關(guān)系以謀求一種開放的普遍性秩序且同時(shí)保留個(gè)體人的平等和自由,這無疑與疫情當(dāng)前、面臨全球化各項(xiàng)挑戰(zhàn)的中國語境、中國道路形成深刻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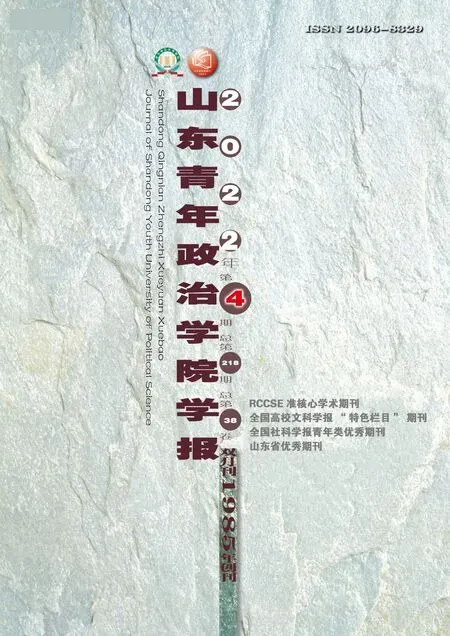 山東青年政治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2年4期
山東青年政治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2年4期
- 山東青年政治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論離婚房產(chǎn)分割協(xié)議的法律效力
——以不動(dòng)產(chǎn)執(zhí)行異議之訴為分析視角 - 法秩序統(tǒng)一視野下處理公開信息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
——基于38例刑事案件的分析 - 學(xué)業(yè)自我效能感、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對(duì)高校英語專業(yè)學(xué)生學(xué)習(xí)倦怠的影響
- “生生之氣”的當(dāng)代呈相與發(fā)用
——以北京冬奧會(huì)開幕式為例 - 崔骃《達(dá)旨》作年辨正
- 論賈誼正朔觀念的轉(zhuǎn)變
——兼論“鄧通讒害賈誼”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