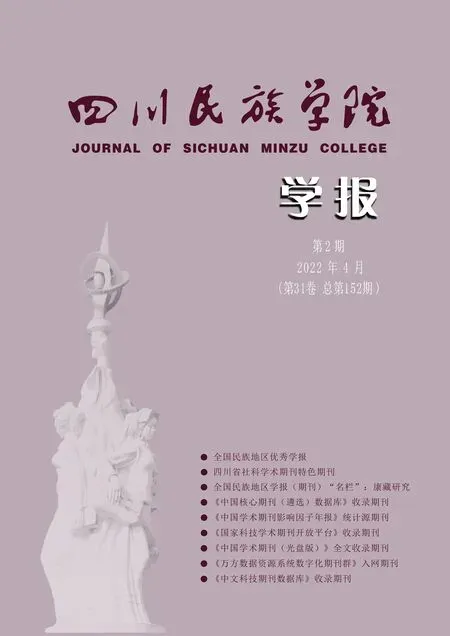沃日河谷勃發的生命力
——論小說《沃日河谷的太陽》
郭曉藝
(西華大學,四川 成都 610039)
涉藏地區文化的書寫成為近年來文學表現的熱點,尤其是在阿來的《塵埃落定》出版之后,四川涉藏地區獨特的文化形態進入廣大讀者的視野。近日,王躍、澤里扎西合著的同題材長篇小說《沃日河谷的太陽》(2020)出版,被稱為一部文學的民族史,呈現了百年歷史大事件背景下的沃日河谷的社會生活,以宏大的敘事結構、豐富的歷史史料、瑰麗而又奇幻的文字,展現了土司制度籠罩下川藏高原人們的生活百態。此書出版后,廣受好評,許多讀者驚嘆其“龐大的篇幅”、娓娓道來的精妙寫法,稱其為“史詩性”的經典之作。因此,對此書加以探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沃日河谷的太陽》展示了三代人之間的糾葛,以土司洛桑郎卡、多吉馬、三木羌,百姓才旺措美、丹蓉娃、絨布仁欽三代人為主體,蔓延出一系列故事情節;又以清廷與土司之戰、土司與土司之戰、土司與山民之戰構建彼此之間的聯系。作品中有人性的陰暗之處,也有人與牲畜之間最原始的情感;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在新的生命里的延續,也有現代文明的侵蝕……這一切在小說中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廣闊的沃日河谷的壯烈圖景。通過少數民族獨特的生活形態、自然法則下的生命欲望、土司制度從繁華到消亡等,展現了沃日河谷勃發的生命力。
一、嘉絨地區生命力的文化符號表征
小說在展現河谷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將嘉絨地區的典型文化符號羅列出來,如碉樓、豬膘文化、沃日河、藏族民謠等。這些文化符號顯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從而凸顯出沃日河谷富有野性而又勃發的生命力。
據調查,嘉絨藏族大約分布在北緯 30-32度,東經101-103度之間,地跨四川省阿壩、甘孜兩州以及雅安部分地區。[1]2獨特的區位條件使嘉絨文化在藏文化體系中有著鮮明的特色,促使嘉絨文化成為各界研究的熱點。嘉絨文化是藏文化體系中極具地域特色的一個亞文化系統。墨爾多山、瓊鳥、苯教、碉樓、嘉絨語、豬膘、“三片”等符號,既是這個獨特文化系統的固態內涵,也是這個獨特文化系統的物質性表征。[1]7《沃日河谷的太陽》中有不少文字是對這些文化符號的描繪,展現了獨特的嘉絨文化。
小說開篇這樣介紹碉樓:“才旺措美家的碉房是擦耳寨的頭一家,擇險而居,有百年歷史。家碉的左右墻和后側墻留有槍眼,砌法精湛。不遠處的碉樓用沃日山上的阿嘎土和石塊加石灰和糯米汁勾縫砌成,四周的墻體則用片石壘疊……大小金川及丹巴等地是一個千碉之地,碉樓林立,蔚為壯觀……”[2]3-5。碉樓是嘉絨地區最為典型的建筑,無論是土司還是百姓都以碉樓作為自身的居住場所,這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獨特建筑,更是地理與環境等綜合因素下最適宜的選擇。碉樓,漢文史籍中稱之為“邛籠”[1]4,普遍認為“邛”即“瓊”,指的是瓊鳥或瓊鳥圖騰的族落,邛籠則指瓊鳥之巢。因為嘉絨地區以瓊鳥作為自己的圖騰,所以以瓊鳥為尊,也就可以將碉樓的解釋引申為瓊鳥圖騰的族落居住的地方。
嘉絨地區的碉樓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用于純軍事防御的碉樓,即人們平常所稱的“高碉”;另一類為純民居建筑,也是目前嘉絨地區較常見的一種民居。[1]4-5小說中對高碉的描述主要是將其作為戰役時的防御碉堡,清廷與土司之戰尤為體現碉堡的作用。正是有了碉樓的存在,才使清軍久攻不下,寸步難行,若不是才旺措美失誤點燃了火藥庫的引線,擦耳寨也絕非如此輕松地被攻下。另一類碉樓是人們的居住地,碉樓是地理區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晶,同時也與河谷人的性格相呼應,碉樓的原始與粗獷是人們豪放、野性的性格特征的體現。沃日河谷的獨特環境賦予了嘉絨人勃發的生命力,這樣勃發的生命力下的智慧所凝結出來的碉樓,賦予沃日河谷更具野性的魅力。河谷邊屹立的一幢幢碉樓正是嘉絨人野性生命力的寫照,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具有充盈生命力的群落。
嘉絨地區的“豬膘文化”也是小說中所敘述的一大特色。豬膘文化是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小說中寫道:“才旺措美家的屋頂是嘉絨地區特有的密梁構造,板棚里有整片的豬膘肉,有些肉已放置了好些年,早已風干,沃日河谷干燥的陣風使豬膘肉愈久彌香,直接用刀削一片放在嘴里,嚼得口舌生津。豬膘肉的豐足顯示著才旺措美家的殷實……”[2]4。豬膘作為一種食物是人們智慧的結晶,人們充分利用寒冷干燥的氣候特點,采用風干的形式使豬肉能夠長時間地保存;同時豬膘也是財富地位的象征,它代表著人們的經濟狀況,稍微富足的人家都會將豬膘肉晾曬在顯眼的地方,借以顯示自己的財富實力。豬膘肉的形成過程是自然與原始的融合,才旺措美吃豬膘肉的方式也是充滿了隨意與豪放,是自然欲望支配下隨心所欲的任意而為,顯示出原始的生命激情。
沃日河是河谷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人類文明起源于河流文化,河流推動社會的發展,與人類文明息息相關。沃日河是一條生命之河,接納了無數有形或無形的生命,它默默陪伴著嘉絨人演繹了一段又一段的歷史故事。人們面向沃日河修建了幢幢碉樓,日常生活與沃日河密不可分。河谷人在湍急的水流、陡峭的地勢中生長起來,形成了豪放、粗獷的性格特點。丹蓉娃與守備的女兒在河邊肆意地擁吻,階層的界限全然被打破,守備的女兒完全不顧周圍人的眼光,隨心所欲地釋放自己的情欲,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作為曾經在狗群中領頭的西娃,選擇以悲壯的方式來告別,一頭扎進了湍急的河流,將自己的生命回歸于河流。河流見證了河谷生命的喜怒哀樂,也最終接納他們的逝去,包容著河谷的一切生命形態。
小說還有一大特色則是藏族民謠的運用。民間歌謠是民間文學中可以歌唱和吟誦的韻文作品,是反映民眾生活、表現民眾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詩歌形式。民間歌謠可謂是藏族人民最早的語言藝術之一,算得上是藏族民間文學的鼻祖或乳娘,在整個藏族文化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3]小說中充斥著民間歌謠,小說中的歌謠不僅是一種文體,更是一種文化符號的表現形式,傳達出藏族人的生活習俗和性格特點。藏族人歷來以能歌善舞著稱,歌舞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迎接遠方客人、歡慶節日、慶祝重大喜事時都必然有歌舞的身影。藏族人借助歌謠來傳達難以明喻的情感,傳達美好的祝愿,祈求美好的希冀等。在藏族傳統文學中,歌謠和格言在塑造人物、結構安排、行文敘事等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作用。[4]這樣的傳統表達方式自然在當代藏族文學的創作中延續,體現出獨特的藏族風味。《沃日河谷的太陽》在表現人物形象時,自然而然地融入民謠,其中尤其以情歌為主,使藏族人的形象更為具體可感。
丹巴嘉絨藏族的情歌是甘孜藏族民歌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它以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涵、優美的曲調、純美的音色、親切自然的表現聞名于川西高原,是嘉絨地區數量最多、傳唱頻率最高、最具特色的歌種。[5]旺姆在阿牛走后一直以歌謠寄托情思:“納尼色莫,納納喲耶,納尼色莫,納納喲呀!布扎戲綻芬芳,撒拉子繡畫廊,口弦子飄過沃日河,在蛇皮梁子悠悠傳響,穿過枷擔灣的牧場,醉了嘉絨的吉瑞香……”[2]102。入營路上的漢子唱情歌來聊以慰藉:“郎在山上打石頭,妹娃河壩放黃牛,石頭打在牛背上,看郎抬頭不抬頭,郎在坡上蓋石屋,妹在屋后摘石榴,郎說熱得嗓冒煙,妹扔石榴讓你酸……”[2]127。王軒為桑吉巴拉所唱的情詩:“愛情滲入了心底,能否結成伴侶?答曰:除非死別,活著永不分離……”[2]206。這些情歌或是表達思念之情、或是互訴柔腸、或是激情澎湃時打發無聊時光的調味品,成為嘉絨人日常交際的必備品。民謠深入嘉絨人的骨子里,人們似乎生來就會唱幾句,就連牲畜也能以別樣的方式哼唱,才旺措美養的狗也會應和主人的歌聲:“關鍵是西娃,它也不會閑著,會把歌唱得嗚嗚咽咽,還會跳狗舞,雙腿直立,轉著圈……”[2]35。這些歌謠都是直白、裸露而又熱烈的,凸顯出嘉絨人率真、熱情的性格,從而展現出嘉絨人充滿激情的生命力。
小說中展現了嘉絨地區特有的文化符號,碉樓、豬膘肉、沃日河、民謠都是嘉絨地區獨特的象征,除此以外,還有五香味糌粑、酥油茶、燒饃饃……這些文化符號無一不彰顯著嘉絨人的性格特征,凝聚著嘉絨人的審美偏好和生活習慣,故而是他們自身品性的濃縮,是他們民族性格的融合。這些文化符號充滿著原始氣息,體現嘉絨人骨子里的自然性,是勃發生命力的展現。
二、河谷中的野性生命力
人性總是具有兩面性,能夠震撼人心靈的優秀作品總是能夠將最真實的人性細致地描繪出來,不管是善或惡,只有將最真實的人性展示出來,看到其中令人唏噓的愚昧,令人扼腕的可悲,才使文學更靠近現實。小說中的人物都是立體化的人物形象,作者將人性中的善惡都不加掩飾地暴露出來,展現出沃日河谷中富有野性的生命力。
《沃日河谷的太陽》中章節的名字是極有特色的,大量的章節名由人物的名字構成,比如“丹蓉娃”“老羅布的兒子”“格桑玫朵”“旺姆”“丹巴拉加”“管家仁青”等等。有的人物不是主角,只在個別章節出現,這些人物不是單純善惡的化身,他們只是普通的民眾,但是他們共同構成了沃日河谷中富有野性的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平民百姓只敬重摸不著看不清的神,對一清二楚的東西視為無物。多吉馬太親民,不像他父親把自己當成神一般供在神龕之上,所以多吉馬不受人尊敬,百姓朝拜的是天神,多吉馬不是神,只是一個凡人,因而無人來朝……”[2]268。人們崇拜的是難以言明的事物,對于可以感知的,便覺得失去了威嚴性。正如現實中不少人都有崇洋媚外的心理,正是我們不夠了解其他國家的具體實際,在一些表面的情況下不斷地美化心中的陌生形象,越發覺得這個形象偉岸;對于自己國家,太了解其中的藏污納垢,才會生出更多的怨氣。究其根本,我們只是太了解自身的情況,而缺乏對外在事物的了解,我們也對陌生的事物有著太多的包容心,對自己熟悉的事物卻毫無耐心。多吉馬太親民竟成為人們不愿尊崇的理由,可以見到其中的荒唐、可笑,但正是這樣的荒唐才更靠近嘉絨人。人性的愚昧暴露無遺,這種不加掩飾的愚昧引發了讀者的同情。
地窩子主人羅布丹專干殺人越貨的勾當,憑一張牛皮大被攔殺過往旅客,以獲取足量的財物,毫無憐憫地將敗兵彭措晉珠悶死在牛皮大被之下。敗兵娶了老婆就出來打仗了,卻因怕被清剿而在外游蕩,滿心期待回鄉卻死于非命。羅布丹殺人后反而哼起了歡快的曲調,對他而言,殺人無非就是捏死了一只螞蟻。在艱難生存的年歲里,平安活著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各自都為生計奔波忙碌。地窩子令人聞風喪膽,但是去的人還是不計其數,只因它能夠提供較為便宜的落腳地方,而安全與否全憑命運造化。羅布丹代表著人性的惡,但這樣的惡是在特殊的時間點和環境下所催生的,他的存在也是生命力的表現,是尋求生存的表現,他為著生存掩蓋溫情的人性,麻木不仁地活著。
人性也并非完全沒有溫情,小說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至深情誼。在土司制度的籠罩下,等級制度也不是不可逾越。洛桑郎卡與才旺措美之間的情誼延續到了多吉馬與丹蓉娃、三木羌與絨布仁欽身上,他們之間更多時候是超越了主仆情誼,是依依惜別、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誼。丹蓉娃在迎接多吉馬 “毛辮”的路上離奇失蹤、絨布仁欽拼死保護三木羌的骨血……沃日河谷人們展現的是由河谷所養育的豪放、不拘小節、淳樸的品性,釋放出最原始的自然欲望。張家的不顧周遭的眼光毅然與年紀大的寡婦丹巴拉加結合、丹蓉娃與守備的女兒在河邊肆無忌憚地擁吻、桑吉巴拉與王軒跨越階層的結合、格丹巴措與絨布仁欽違背道德倫理的相愛……他們所展現的都是藏族人民骨子里最原始的沖動,不受外界抑制自然而然地生長,即使道德倫理會在心中形成阻擋的力量,但卻難以抑制其內心深處的欲望。
小說中人與牲畜之間展現著人類最本原的愛。西娃終其一生保護著才旺措美一家,從守護才旺措美到蓉娘,再到丹蓉娃。西娃不忍讓主人傷心,以跳河的形式悲壯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它與才旺措美一家完全是等同于家人般的存在;老馬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這家人,一家人也盡可能地回報,老馬年老時喂養它的是比人類的食物還要好的蠶豆,一家人也舍不得讓它干任何事;邊巴次仁喂養在山里的牲畜,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即便現在的一批沒有再受邊巴次仁的飼養,但它們仍舊保留著舊時的習慣,每天太陽落山前就成群結隊回到老屋轉悠,王蒼遠回到老屋悼念母親后,離開時,豬群為他們送行。“山豬留戀老屋,更留戀老屋的主人,它們早已幻化成這山林的精靈……”[2]308。人與牲畜之間互相依存,建立起深厚的情誼,成為小說中的一大亮點。
沃日河谷中生長的人、牲畜都帶有濃厚的野性色彩,他們未被現代文明完全裹挾。他們的身上充滿了野性和古樸,充滿了不可抑制的欲望,這樣原始的力量,使得生命勃發出旺盛的生機。這樣野性的生命力不僅沒有在時代前進后受到壓抑,反而迸發出更強的活力,成為催化土司制度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三、野性生命力的反抗
土司制度在嘉絨地區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是嘉絨地區特定歷史時期的典型特征。土司制度是小說最核心的存在,土司的統治維持著所屬范圍內的表面平和。河谷人們在土司制度的壓抑下麻木地活著,但嘉絨人骨子里的野性生命力在時間的推移中越來越不可抑制,最終迸發出巨大的活力,成為土司制度消亡的重要因素。
小說預示著土司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而這樣的消亡與生命力的反抗作用是分不開的。土司制度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通過分封地方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當地人民的一種政治制度。[6]土司擁有極大的權利,奉行的規章制度也是最大化地維護土司的統治,土司政權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土司一方面利用暴力來鎮壓、威懾一切違抗其命令的群眾,同時,又用宗教來使民眾精神臣服。民眾處于神權的壓迫之下,反抗的結局不單單是暴力的處決,而且還有心靈的巨大折磨。因此民眾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土司的統治,將土司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并將這樣的觀念世代沿襲下去,這也就導致了命運的輪回。一方面是土司代表著權利的中心,驕奢淫逸,隨意處置民眾的性命;另一方面是民眾的艱難度日,科巴身份的婦女甚至不如土司家的一條狗。民眾的生命不斷被踐踏,他們的兒女繼續重復著他們的命運。身為管家的仁青享有極高的地位,他手下掌管著其他各類管家,他只需要在土司面前畢恭畢敬,伺候土司的一切雜事,而他自己也有差役侍候,他可以趾高氣昂地指揮一切地位比他低的人,即使百姓非常厭棄,但也只得服從。由來已久的制度賦予他地位與權利,臣服、遵從的觀念也根植于百姓頭腦中。
自古以來強調“民貴君輕”,受民眾愛戴和擁護的必然是“仁君”,這些觀念放在土司制度下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土司成為一方主人,他們有義務維護統治地區內人們的安居樂業,小說中的土司只是保障了統治區內人們的基本生存權利——單純的活著。女傭山丹被誤會為奸細,遭到慘無人道的點天燈處置,字子君也遭受到嚴酷刑罰,這些人固然犯了錯,但在土司的眼中,他們不過是可以隨意處置的貓狗。這還是在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背景下產生的事件,是受過大儒教育的三木羌做出的處罰,十多年的教育仍然沒有改變他血液中的極端利己主義,他所受的儒學教育只是短暫地壓抑內心的殘暴,而當他一回到故土時,娶妾、暴打發妻、處決仆人……一一上演。“他爺爺洛桑郎卡是河谷之鷹,可以飛上天空去翱翔;他父親多吉馬是河谷之豹,在河谷里縱橫捭闔;到了他這一代已經掉光了羽毛……”[2]314,并非一代不如一代的衰敗現象,而是人們開始喚醒骨子里的野性,以推翻不合理的制度。他仍然想要固執地維持古老的秩序,堅決收取買路錢,造成了大量的山民摔下懸崖。三木羌固執地維持古老的秩序,為的無非是用無上權力來維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在這樣的秩序下,反抗自然也就成了必然,推翻土司制度也就勢在必行。
新一代的青年成長起來,他們對于等級觀念也是遵循的,但并非像父輩一樣盲目信仰。他們開始抹去原本的界限,管家仁青的話不再是絕對的命令,桑吉巴拉可以公然挑戰管家的權利;丹蓉娃不理解為何自己不能和守備的女兒結合;作為大儒之子、少土司兄弟的王軒,卻與一個地位低下、相貌平平的侍女結為夫妻;山地女子格丹巴措公然挑釁土司太太,并對其反復戲謔,這些“不可能的事件”都在嘉絨地區上演了,原本的秩序不再是堅不可摧,年輕的一代奮起抗衡舊秩序。年輕的一代在新事物的影響下喚醒了血液里的野性與激情,用自身的行為來一步步瓦解土司制度。
小說中也有鴉片帶給沃日河谷沉重災難的描繪。“牛老三挖到金子要下山去懋功交易,把金子換成銀子,然后去窯子把銀子敗光,淘金人走的都是這條路。后來發財的就去抽大煙,再多的金子也不夠他們敗。懋功的街上有二百多家煙館,而人口不過二三萬……半山土地貧瘠卻非常適合種植大煙,那里開滿了罌粟花。靠賣煙土,饒壩比河谷富裕,河谷就是饒壩大煙的傾銷地……”[2]22。種植大煙是走向富裕的捷徑,挖金人用性命換取的金子在煙館無盡地揮霍,用完再繼續挖金,挖到金繼續揮霍……陷入無止境的循環。兩三萬人口的街上卻養活了兩百多家煙館,可以想象人們對大煙的需求量之大,人們的生活成了沒有目的性的存在,生存好像只是為了那稍許的慰藉。饒壩土司借助鴉片使自己領地的百姓富裕起來,洛桑郎卡土司在享受到了大煙的“無窮樂趣”后,命令才旺措美取回罌粟種子,使自己也能盡情享用。土司放縱鴉片在土地的泛濫,把其視為財富的重要來源,受壓抑的人們把鴉片當作撫慰精神世界的“良藥”。鴉片作為一種外來的物品流入嘉絨地區,給這些地區帶來了短暫、畸形的繁榮。“從1935年起,國民政府厲行禁煙,聲言6年內予以禁絕。清末以來禁煙的規律是,每禁一次,鴉片種植就向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轉移一次。”[7]罌粟帶給我們的都是沉痛的記憶,往往代表著腐化、墮落,無盡的深淵。在罌粟的迷幻下,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都處于一種迷醉的狀態,連烏鴉也患有煙癮。長此以往,原本擁有富裕糧食的領地也將落入糧食短缺的局面,無一例外的成為罌粟控制的傀儡,何談富足?反抗也就隨之而來。
土司制度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可阻擋地走向了末路。小說詳盡地突出了這些因素,明晰地展現出這種制度的不可挽救。土司制度在歷史潮流下必然走向滅亡,個人勃發的生命力也將推翻土司制度。
《沃日河谷的太陽》展現了一幅富有生命力的少數民族畫卷。畫卷中有展現嘉絨人質樸野性生命力的文化符號、有凸顯勃發生命力的立體化人物形象、有生命力的反抗加速土司制度的消亡……我們通過這本小說更能感受到一個明晰的嘉絨圖景,感受到嘉絨人們的痛苦與歡樂,感受到嘉絨人充滿欲望與生機的旺盛生命力。除此以外,這本小說在某些方面將阿來《塵埃落定》所挖掘的嘉絨土司的過往歷史進一步細致化,讓讀者再次看到在這里生活著的人們的歷史生活,激勵更多的人去挖掘這片土地的價值,使其文化得以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