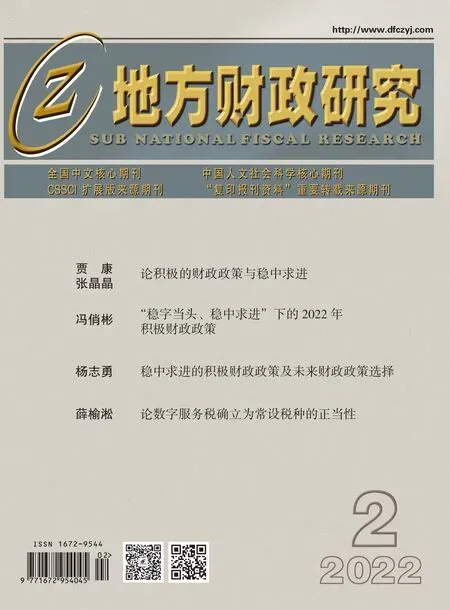論數字服務稅確立為常設稅種的正當性
薛榆淞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數字經濟的發展嚴重沖擊了傳統跨境稅收征管秩序,在新的國際稅收規則建立之前,不少國家選擇開征“數字服務稅”以保護本國稅基。這有助于減輕傳統企業與數字企業之間橫向稅收負擔分配不均衡的問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恢復稅收的公平性。但上述兩種目標在底層邏輯上迥然不同,使得這一稅種在正當性上面臨著諸多詰難。此外,OECD的“雙支柱”改革方案近期實現了歷史性突破,有望從根本上重塑國際稅收制度。此種情況下,已經開征的數字服務稅作為臨時應急措施的功能將被逐步弱化。由于數字經濟在價值創造上的特殊性,故即使中美等在數字經濟領域具有優勢地位的國家,從完善一國稅收體制的角度看仍不能忽視此種特殊價值。因此,很有必要引入“壟斷租”范疇,破除僅以反避稅或貿易保護措施理解這一稅種的既有觀念,系統論證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數字服務稅應作為一般性的長期措施持續征收、確立為常設稅種的正當性。
一、問題的提出:臨時應急抑或長期措施
在跨境交易中,傳統企業需要在市場國設立生產機構、營業機構或分銷機構等實體,但數字企業可以在虛擬空間完成跨境交易,而無須依賴設立在市場國的各類實體。此種轉變極大地沖擊了基于傳統制造業生產模式所建構的現行國際稅收征管體系,使得市場國的稅收主管機關無法依據傳統的聯結度規則對跨國互聯網企業主張來源地管轄權。
此種情況下,若居民國僅主張屬地管轄權,互聯網企業的境外數字收入實質上處于雙重不征稅的狀態。即使居民國同時主張屬人管轄權,由于預提所得稅、稅收抵免和稅收饒讓等消除雙重征稅措施的影響,此類企業的實際稅負也明顯偏低。這將產生以下兩方面的不利影響:第一,從競爭公平的角度看,數字企業所享受的雙重不征稅或稅負明顯降低的效果,實質上是不當地利用了現行稅收征管制度的漏洞,通過監管套利的方式形成了相較于傳統企業不合理的競爭優勢。第二,從國家財政能力的角度出發,此種雙重不征稅或稅負明顯偏低的情況無疑是侵蝕了市場國的稅基。
為此,各國提出了諸多局部改革方案,主要包括無形資產轉讓定價指南、征收預提所得稅和修改傳統的常設機構規則等內容。但均未能突破對境外實體的依賴,且難以準確捕捉數字服務所創造的價值,導致其成效十分有限。同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主導的“雙支柱”改革方案(以下簡稱OECD方案)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停滯,為避免數字企業對國內稅基的侵蝕,一些國家已經采取了征收數字服務稅的單邊措施①本文所涉及的域外數字服務稅方案,主要是參考了歐盟、法國和英國的數字服務稅提案或法律規定。為了行文的簡潔,在沒有特殊說明的情況下,后文討論中涉及這三個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數字服務稅方案所依據的規范文本來源如下:歐盟的數字服務稅提案:European Commission.Proposal for a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EB/OL](2018-03-21)[2021-10-24].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system/files/2018-05/d_proposal_common_system_digital_services_tax_21032018_en.pdf,法國的數字服務稅立法:LAW no.2019-759 dated 24 July 2019 concerning creation of a tax on digital services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downward correction of the corporation tax,英國的數字服務稅立法:HM Treasury.Budget 2018 Digital Services Tax.[EB/OL].(2018)[2021-10-23].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52172/DST_web.pdf。。例如,法國在2019年7月率先宣布,將對在法國經營的大型互聯網企業的數字廣告及跨境數據流動等數字交易行為開征3%的數字服務稅。此后,英國也決定對部分大型互聯網企業在其國內所產生的在線營業收入征收2%的數字服務稅[1]。截至2021年3月,已有46個國家開征或擬征直接數字稅,其中包括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比利時、丹麥、加拿大、墨西哥、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主要經濟體②周念利,王達:《數字稅的影響、挑戰和建議》,載騰訊研究院2021年 3 月 31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22300256976517&wfr=spider&for=pc,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0月23日。。
但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大部分國家在征收數字服務稅時都強調該稅種只是一項臨時的應急措施,包括英國、法國、土耳其和印度在內的多個國家已承諾將在支柱一生效后取消征收數字服務稅以及其他類似的單邊措施③《美國與歐洲五國就數字稅爭端達成妥協》,載新華社2021年10月 21日,http://www.news.cn/2021-10/22/c_1127984877.htm,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3月11日;“Turkey and US agree on phase-out of digital tax”,MNE Tax,https://mnetax.com/turkey-and-us-agree-onphase-out-of-digital-tax-46280,2021-11-23;“ India and US agree on transition from India′s ‘equalization levy’digital tax”,MNE Tax,https://mnetax.com/india-and-us-agree-on-transition-from-indiasequalization-levy-digital-tax-46299,2021-11-29。。但尼日利亞、肯尼亞和斯里蘭卡等三個OECD成員國仍對雙支柱持有反對意見,且尼日利亞總統在2021年12月31日簽署的《2021年財政法案》中已正式要求征收數字服務稅④Kevin Pinner,“Nigeria To Assess 6%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Foreign”,Law 360,https://www.law360.com/tax-authority/articles/14527 94,2022-1-5。。作為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尼日利亞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將會對非洲大陸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此外,剛剛簽署該方案的加拿大也選擇繼續推進其數字服務稅的立法進程,引發了美國的強烈反對,其貿易代表辦公室已正式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書面意見⑤Doug Connolly,“Canada adv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 bill despite OECD pact,USobjections”,MNE Tax,https://mnetax.com/canadaadvances-digital-services-tax-bill-despite-oecd-pact-us-businessobjections-46454,2021-12-5。。由此可見,雙支柱方案并未完全平衡各國在數字產業上的稅收利益,不僅未能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稅收利益,也未能滿足那些在數字產業上缺乏競爭優勢的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本文籍此提出了一個重要追問,即數字服務稅除了能作為應對稅基侵蝕的臨時措施外,是否還存在著某些尚未被發掘的稅基,使之能夠成為一個具有正當性的長期措施?換言之,數字服務稅目前的困境是否源于其同時承載了臨時措施和長期方案的雙重定位。
基于此,本文首先明確了設立數字服務稅在正當性層面主要的困境,并區分了該稅種作為短期措施與常設稅種所不同的立法目的,指出上述困境從根本上說是源于現行方案的雙重定位所無法避免的矛盾。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壟斷租”這一概念在數字經濟下的重要性,并結合OECD方案最新進展,論證了將該稅種確立為常設稅種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整體而言,本文試圖破解該稅種所面臨的理論困境,改變僅以反避稅或貿易保護措施理解這一稅種的既有觀念,試圖說明我國作為一個在數字領域具有國際優勢地位的大國,為何仍將其作為我國常設稅種,以期能更好地促進我國現代稅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二、現行數字服務稅方案所面臨的正當性困境
目前,各國在數字經濟①本文所討論的數字經濟,在概念界定上是基于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所達成的《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即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基于同一邏輯,本文所討論的數字企業(或稱互聯網企業)是以數字經濟作為其主營業務的企業,典型的代表公司包括谷歌、亞馬遜、蘋果、微軟、騰訊、阿里和百度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兼營軟硬件服務的公司,其銷售硬件的收益與數字經濟無關(即使其設備是通過線上銷售的),本文的討論僅涉及其所提供的數字服務。以美國蘋果公司為例,其典型的數字交易收入是指基于蘋果應用商店(AppStore)所產生的收入。領域的發展極不平衡,這不僅加劇了建立跨境數字稅收規則的難度,也使得部分國家單邊開征的數字服務稅面臨著諸多質疑。考慮到該稅種旨在恢復稅收公正的立法目的,此處主要關注現行方案在正當性上所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法律性雙重征稅問題
一般認為,稅收抵免通常僅限于居民企業境外繳納的所得稅。以OECD《關于避免對所得和財產雙重征稅的協定范本》②OECD.Model Convention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EB/OL].(1977-10-19)[2021-10-24].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055919-en.pdf?expires=1634716718&id=id&accname=oid010242&checksum=FBFD316D44079C112BF346C0DA40AC0D。為例,該范本的第二條第二款就規定了該協議僅適用于對所得或財產征收的稅款。但現行的數字服務稅方案多將該稅種界定為間接稅,對于非居民企業而言,這就意味著其在市場國繳納的數字服務稅無法在其居民國主張抵免。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如果市場國希望以此來完全彌補當地法律實體缺失對其造成的所得稅“損失”,由于無法主張抵免,此類企業的整體稅負反而會高于傳統企業,很容易因矯枉過正而引發新的稅收不公。
歐洲銀行聯合會也因此反復強調,只有全球性方案才能確保公平競爭和避免意想不到的雙重征稅,對數字經濟的局部性征稅不僅存在很大困難,而且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雙重征稅問題。現行OECD 2017年版《轉讓定價指南》已經清楚地規定了金融機構所應遵循的規則,其所實現的利潤也在跨境交易的相關實體之間按照價值創造地和承擔的風險被征稅。在此種情形下,對數字金融活動征收任何特別稅都會造成重復征稅[2]。
(二)選擇性征收所產生的“歧視性”問題
從前述已經開征或公布的數字服務稅方案看,其大多設置了較高的征稅門檻,從而將實際的納稅主體限定為大型互聯網企業,且主要是針對美國的互聯網巨頭。以法國為例,其數字服務稅的課征范圍主要包括互聯網廣告服務和數字界面服務,而美國企業在這兩類服務中都占主導地位。因此,法國如果對互聯網廣告征稅,預計有9個公司集團會被涵蓋在內,其中8個是美國企業。此外,其征稅門檻為每年全球營業收入7.5億歐元以上,且來自法國的業務收入2500萬歐元以上。從實際情況看,符合該門檻的公司往往是美國公司,在法國提供應稅服務的許多非美國公司都被免除了納稅義務。
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此種選擇性征收模式很可能會構成對稅收協定中“無差別待遇條款”的違反。具體而言,在國際貿易法領域,WTO成員影響服務貿易的稅收措施受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管轄。基于GATS的要求,成員國所實施的稅收措施不能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由前文可知,現行方案多設置了較高的納稅門檻,導致實際納稅人十分有限,故可能構成對GATS下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的違反[3]。
(三)對營業收入征稅的合理性問題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9年12月發布了《301條款調查:關于法國數字服務稅的報告》③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Fr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EB/OL].(2019-12-02)[2021-10-24].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France%27s_Digital_Services_Tax.pdf。,并在2021年3月發布了《301調查:外國數字服務稅》④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s:Foreign Digital Services Taxes(DSTs).(2021-03-01)[2021-10-24].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564。。這兩份報告指出,現行的數字服務稅方案將征稅對象指向了營業收入而非利潤,違背了國際稅收的基本原則,不僅會加重互聯網企業的負擔,也不利于行業發展。
具體而言,目前全球有效的稅收協定多是基于OECD或聯合國范本所制定的,而這兩個范本都是針對所得(利潤)征稅的準則,并沒有提供對毛收入征稅的準則。同時,由于對毛收入征稅不考慮成本因素,即使稅率再低,對那些利潤率低的企業也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以毛收入為計稅依據的稅收一般被認為是一種“低效率、阻礙經濟增長、不公平的稅收”。此外,由于利潤率低的企業所繳納的數字服務稅可能會超過其利潤總額,甚至會出現一家企業沒有利潤也要繳納數字服務稅的情況,這使得數字服務稅并不利于鼓勵投資和創新[4]。
三、現行方案中數字服務稅的雙重定位
由前可知,現行的數字服務稅方案面臨著諸多正當性困境。最令人困惑的是,致力于恢復稅收公正的數字服務稅為何會產生一種歧視大型跨國企業的不正義感?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現行方案在制定時沒有準確界定其立法目的。基于此,結合OECD方案的最近進展,區分數字服務稅作為短期措施與常設稅種不同的立法目的,指出前文所述的諸多正當性困境就源于立法目的差異對制度設計的影響。
(一)作為臨時措施的立法目的
在國際稅收征管及協調方面,OECD認為“數字經濟”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是涵蓋于“經濟數字化”這一更大的范疇。因此,若要更好地應對數字經濟挑戰,長期來看不能僅靠引入特殊的數字稅,而是要改變現有的稅收規則[5]。基于此,自2013年啟動BEPS行動計劃以來,OECD始終致力于建構新的稅收征管規則,試圖通過解決“經濟數字化”的影響來回應“數字經濟”的挑戰,其在2019年5月發布的《形成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共識性解決方案的工作計劃》(下文簡稱《工作計劃》)①OECD.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EB/OL].(2021-10-08)[2021-10-20].https://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中提出了區分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的雙支柱方案②如無特殊說明,下文所提到的雙支柱方案即指這一方案。但需要說明的是,除了2019年通過的《形成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共識性解決方案的工作計劃》外,在實質內容還應包括OECD此后對這一方案所提出的各項改進措施,包括2021年的最新聲明。,即“修訂的聯結度和利潤歸屬規則”與“全球反稅基侵蝕提案”。
2021年10月8日,OECD發布聲明稱:“合計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90%以上的這些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同意實施雙支柱國際稅改方案,以應對經濟數字化帶來的稅收挑戰。該方案的支柱一是將確保規模最大、利潤最豐厚的跨國企業利潤和征稅權在各國之間更公平地分配。新規則要求跨國公司在其經營活動所在國納稅,而不僅僅是在其總部所在地。支柱二是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設為15%。從2023年起,年收入超過7.5億歐元(約合8.7億美元)的公司都將適用這一稅率。該方案實施后,超過1250億美元來自全球約100家大型跨國公司的利潤將被重新分配給各國,這些公司無論在哪里經營和創造利潤,都將公平納稅”③《經合組織宣布136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達成國際稅改協議》,載新華社 2021年 10月 9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13109341036426304&wfr=spider&for=pc,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0月24日。。
與上述思路相契合的是,許多開征數字服務稅的國家認為該稅種僅是多邊協議達成前的一項臨時措施。具體而言,主要是基于短期內無法就數字稅收達成多邊協議的預期,通過單邊開征數字服務稅的方式應對數字經濟對本國稅基的侵蝕,以期恢復稅收公正和增加財政收入,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本土互聯網企業。因此,獲取財政收入和保護市場國稅基是該稅種作為臨時措施最為重要的立法目的,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反避稅措施,旨在以相對簡單直接的方式應對互聯網企業日益復雜的稅收籌劃,且具有一定的貿易保護屬性。
(二)作為常設稅種的立法目的
從官方表態看,已開征數字服務稅的國家基本都同意在OECD框架下形成數字稅收的國際規則,并將該稅種界定為一項臨時的應急措施。但從各國實際行動看,此種表態很有可能只是權宜之計。具體而言,雖然OECD此前在推動數字稅收改革上出現一些停滯,但以其2019年發布的《工作計劃》為標志,各國在應對經濟數字化所帶來的稅收挑戰方面正不斷形成共識,OECD所推動的雙支柱改革圖景日漸清晰。在此種情況下,如果僅將數字服務稅作為臨時的應急措施,就無法解釋包括新西蘭、加拿大、巴西在內的諸多國家繼續積極推進數字服務稅的相關立法和研討。其中,非洲稅收管理論壇(ATAF)在2020年9月3月發布的《數字服務稅法范本建議》①ATAF.ATAF Suggested Approach to Drafting Digital Services Tax Legislation.[EB/OL].(2020-09-03)[2021-10-24].https://events.ataftax.org/index.php?page=documents&func=view&document_id=79。尤其能說明問題,這一范本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稅收上的利益訴求。由此可見,各國并未放棄將數字服務稅作為常設稅種的可能,強調臨時措施的定位或只是在爭議較大的情況下為數字服務稅的開征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
事實上,在數字稅立法的路徑選擇上,一直以來就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支持設立新稅種的觀點認為,數字稅應是單獨開征的稅種,數字稅立法也不能局限于既有的稅收制度,而恰恰是要結合數字經濟的特殊性,對相關課稅要素進行獨立的制度設計[6]。筆者認同,是否針對數字經濟開征新稅種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政策考量的問題,也涉及法律的穩定性問題,但稅法研究必須指出的是:數字經濟在價值創造上實現了顛覆性的創新,使得傳統領域中難以識別的“壟斷租”在數字經濟下變得十分明顯。在此種情況下,若仍堅持以傳統規則衡量數字企業的稅收負擔能力,顯然違背了量能課稅原則的要求。而如果放棄這一部分的稅收,將導致數字企業的很大一部分收益就不會被征稅,既無法實現營造一個公平的稅收環境,也不利于保障國家的財政能力。
綜上,從數字服務稅作為常設稅種②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數字服務稅并非是指現在國際社會已經推行的數字服務稅方案,而是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即針對數字經濟所建立的新的稅種。從概念的嚴謹性出發,數字稅收是一個更為嚴謹的表達,但由于現行的數字服務稅方案中包含了此種作為長期措施的數字稅收的某些立法目的,故本文在此沿用了數字服務稅的名稱。的定位出發,該稅種除了要具備組織收入的功能外,還應強調其捕捉數字經濟創造的新價值、恢復橫向稅收公正的立法目的,以期能貫徹量能課稅原則,補充現行稅制在衡量數字企業的稅收負擔能力方面的不足,并最終實現數字企業與傳統企業的整體稅負均衡。
(三)雙重定位所產生的矛盾
基于臨時措施和常設稅種的不同定位,數字服務稅在目標導向上存在著一定差異。但問題在于,這兩種不同的思路會導致立法者稅制設計上產生不同的思路。為更加形象地說明這一問題,本文假設A國境內的互聯網市場同時存在B公司(居民國為A國)和C公司(居民國為D國,且在A國沒有設置任何法律實體),以此為基礎分別討論臨時措施和常設稅種的定位對立法的影響。
從臨時措施的角度看,前述“歧視性”的根源在于臨時措施對征稅范圍及納稅門檻的必然要求。具體而言,由于A國認為C公司在其境內的運營構成了對其稅基的侵蝕,并希望通過開征數字服務稅予以回應。因此,在稅制設計上會將C公司的經營事項納入征稅范圍時,并將B公司的經營范圍排除在外,且以C公司的營業額為依據確定起征點。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各國的互聯網市場差異很大,本土企業的優勢領域也不相同,故在征稅范圍和起征點問題上會出現很大的國別差異,而這種差異難以在稅法理論層面予以合理化解釋,使得致力于恢復稅收公正的數字服務稅產生一種歧視大型跨國企業的非正義感。但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不正義感并不意味著數字企業在實質上被區別對待。事實上,如果以稅收規避的懲罰措施來界定作為臨時措施的數字服務稅,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弱這種不正義感③在不考慮稅收優惠和稅收規避的情況,由于B公司通常會在A國設有各種法律實體,故即使B公司在A國豁免了數字服務稅的納稅義務,其在A國所實際負擔的納稅義務并不必然低于C公司。此外,如果進一步考慮B公司在D國所可能被征收的數字服務稅,這一問題的結論便更加明顯。。
此外,臨時措施的定位也使得立法者傾向于在稅基確定上選擇營業收入而非利潤征稅。簡言之,在臨時措施的定位下,立法者更關注的是能否保證實現組織收入的目標。由于法律實體的缺失和稅務信息交換渠道有限,市場國稅收主管部門實際上難以獲知跨國企業在其境內的實際利潤率,故現行方案將稅基建立在營業額的基礎上,既能實現臨時措施的定位下對懲罰稅收規避的功能,也能實現基于實際征管能力的必要妥協。
但從常設稅種的角度出發,前述問題將得到消解。在歧視性問題上,若將該稅種界定為常設稅種,顯然是立法者關注到了現行稅制無法捕捉B公司和C公司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而希望通過數字服務稅予以彌補。因此,稅制設計的重點在于對數字經濟下一些特殊價值的識別。換言之,立法者此時不再區分B公司和C公司具體的經營范圍,而是關注現行稅制能否完全識別其所創造的價值,若答案是否定的,則會將其經營范圍納入該稅種的征收范圍。此外,在起征點的確定上,主要的考慮因素也并非C公司的營業額,而是稽征成本和產業發展目標。在稅基確定上,一旦OECD方案能最終落地,市場國的稅務主管部門將有能力獲得企業的利潤信息,此時作為常設稅種的數字服務稅顯然可以選擇以企業的利潤作為稅基①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意味著以利潤作為稅基是必要的,事實上,下文將說明為何應以營業收入作為數字服務稅的稅基。。此外,如果肯認定該稅種作為常設稅種的獨立性,此時就不存在一個需要消除的雙重征稅問題,前述的法律性雙重征稅問題只是復合稅制下的普遍現象。
綜上可知,無論是依據臨時措施還是常設稅種的定位建構數字服務稅體系,雖然都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但至少在內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現行方案的問題在于,其以臨時措施為出發點建構數字服務稅,但沒有采取傳統的反避稅措施,而是試圖建構一個全新的稅種,且無論是否有意為之,在稅制設計的過程中都體現了將之作為常設稅種的要求。此種雙重定位所產生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一方面嘗試以“用戶參與”理論體現其作為常設稅種的合理性,試圖建構一般性的規則體系;另一方面,過于強調組織收入的功能,忽視了對其稅基選擇作出合理解釋的重要性,且為實現保護本土企業的立法目的,在征稅范圍及納稅門檻上呈現出極大的國別差異。
四、數字服務稅常設的正當性:“壟斷租”
由前可知,現行方案所面臨的正當性困境主要源于其雙重定位的不合理性。對此,最好方式是簡化數字服務稅的立法目的,而OECD方案的最新進展無疑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一旦該方案最終落地,向數字企業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傳統困難將會緩解。這將大大降低利用數字服務稅作為應對稅基侵蝕的臨時措施的需求,這無疑有助于數字服務稅回歸其作為常設稅種的立法目標,但也有觀點認為這同時宣告著數字服務稅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基于此,本部分首先說明了OECD方案為何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數字稅收的問題,以及數字服務稅層面既有的“用戶參與”理論所存在的弊端。在此基礎上,引入了“壟斷租”的概念,討論了以此為依據重新建構數字服務稅的課稅依據,并將之確立為一項常設稅種的積極意義。
(一)數字稅收的重要性及OECD方案的局限性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如何實現數字行業與傳統產業的橫向稅負均衡問題成了無法回避和繼續解決的重大立法問題。具體而言,跨國互聯網巨頭的巨大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對當地公共資源的經營性排它使用(即后文所說的“壟斷租”)。對于此類人為原因形成的租金,傳統上認為只要存在著可以自由進入的競爭性市場,長期而言就沒有任何主體能夠獲得此類租金。但數字經濟下“馬太效應”過于明顯,且其高度依賴的無形資產在邊際成本與可變成本方面也構成對市場進入的實質阻礙,這使得競爭法難以發揮調節作用。這導致互聯網企業的稅收負擔明顯低于傳統行業。以歐盟委員會2017年的統計為例,跨國互聯網企業在歐盟的平均稅率僅為10%左右,而傳統行業的平均稅率則為23.2%[7]。因此,從橫向公平的角度看,對互聯網企業“加稅”既符合分配正義的要求,也能回應國內民眾及其他行業經營者對這種明顯不公平稅收負擔的質疑。
從國際稅收規則的發展看,OECD方案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無論是支柱一對稅款的跨境分配還是支柱二所希望建立的稅收競爭底線,都重塑了國際稅收征管的傳統邏輯。法律實體的缺失將不再成為市場國對跨國互聯網巨頭行使其屬地管轄權的障礙,筆者認為僅在OECD所建立的框架下不能完全解決數字領域的稅收問題,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從應對思路上看,OECD認為“數字經濟”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是涵蓋于“經濟數字化”這一觀點就決定了,無論是BEPS行動計劃還是雙支柱改革均無法從根本上回應“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挑戰。為此,有必要區分“經濟數字化”與“數字經濟”的差異。本文在第二部分已經對“數字經濟”進行了界定,而所謂的“經濟數字化”,則是指現代科技為傳統企業的賦能,本質上是對傳統生產模式的效率提升。由此可見,“數字經濟”與“經濟數字化”雖然都依托于現代的信息技術手段,但體現的其實是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因此,以“經濟數字化”的應對為目標的稅制改革只能將數字經濟納入現行的稅收體系,但難以實現對其所創造的全新價值征稅的目標。
第二,從立法目的上看,雙支柱方案旨在建立稅收競爭的底線,而非以此徹底解決數字經濟的稅收問題。具體來說,該方案關注到了對跨國企業“超常規利潤”征稅的重要性,但如前所述,該方案并不致力于消除稅收競爭,而是希望建立稅收競爭的底線,故除了稅率以外,各國企業所得稅的稅基設計并不會因此發生大的變動。而此種征稅模式仍會引發以下問題:首先,該方案所稱的“超常規利潤”并不特指數字企業,而是針對包括數字企業和傳統企業在內的大型跨國企業,更為關注的是企業的利潤水平。其次,由于該方案無意改變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實際上就無法超越現行稅制所能捕捉的價值,無法真正界定數字經濟下的“超常規利潤”為何,即使采用利潤率水平進行估算,對常規利潤和超常規利潤適用同樣稅率也無法體現稅法對此種“超常規利潤”的獨立評價。說明為何對從類利潤適用與常規利潤相同的稅率。最后,過于關注利潤會導致數字企業只要不創造利潤,就能以接近零的稅收成本利用當地的公共資源,而傳統企業無論盈利與否都需要負擔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稅收。此外,即使能通過技術手段實現對數字企業的特殊處理,只會將本就過于復雜的雙支柱方案變得無比繁復,不符合簡并稅制的整體趨勢①以該方案的支柱一為例,為了實現“市場國”對理論上由本區域創造的價值——超常規利潤征稅,首先需要劃分認為更容易產生超常規利潤的經濟活動,目前包括“自動數字服務”和“面向消費者業務”兩大塊,而且為了考慮不同行業特性,同時采取正面、負面清單的方式確定業務范圍;其次,需要重新調整計算屬于這兩大范圍內的業務所實現的總利潤,按一定的利潤率水平估算總利潤中所含的常規利潤,以計算可用于分配的總超常利潤;再次,按一定比例折扣后計算可供所有符合條件的市場國進行分配的“可分配超常規利潤”,或稱可分配稅基;最后,按分配因子在各市場國之間進行分配。其分配(計算)的復雜程度可見一斑,對這一問題的詳細闡釋,可參見龔輝文.數字服務稅的實踐進展及其引發的爭議與反思[J].稅務研究,2021(1):44。。
綜上,OECD方案實難從根本上解決數字稅收的問題,故即使其所倡導的雙支柱方案能最終落地,仍有必要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現行稅制難以評價數字企業的稅負能力的傳統問題,使得一國的稅收制度能夠涵蓋數字企業所創造的全部價值。
(二)重拾數字服務稅作為常設稅種的障礙——“用戶參與”理論的缺陷
如同當年針對制造業所建構的增值稅一樣,數字經濟在價值創造上的特殊性使得立法者有必要專門建立新的常設稅種。對此,前文已經指出了現行的數字服務稅方案實質上隱含了將之作為常設稅種的定位,如果能強化和突出其作為常設稅種的定位,顯然是有助于應對OECD方案的局限性。但從稅種的正當性上看,既有理論沒有提出合理的課稅依據。
一般認為,對特定稅種的正當性討論不能脫離“可稅性”標準。具體來說,國家在確定征稅范圍時,主要應考慮的因素是收益性、公益性和營利性,只有綜合考察這三個方面,才能在理論上有效地確定某類行為和事實是否具有“可稅性”[8]。由此可見,討論課稅依據的意義在于,其指明了立法者希望針對何種收益予以征稅,即在具體稅種中明確了“收益”的內容,對“可稅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在數字服務稅領域,目前主流的“用戶參與”理論顯然無法作為該稅種合理的課稅依據。
所謂的“用戶參與”理論,首先由英國政府正式提出,其認為用戶在數字化經濟活動中以提供數據的方式創造了價值,基于BEPS行動計劃所確定的“價值創造地征稅”原則,用戶所在國有權對這部分價值征稅[9]。根據英國財政部先后發布的《公司稅與數字經濟立場性文件》①HM Treasury.Corporate tax and the digital economy:position paper.[EB/OL].[2021-10-24].(2018-03-13)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corporate-tax-and-the-digital-economy-position-paper。和《英國數字服務稅咨詢稿》②HM Treasury.UK Digital Services Tax:Consultation.[EB/OL].(2018-11)[2021-10-24].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54975/Digital_Services_Tax_-_Consultation_Document_FINAL_PDF.pdf。可知,其認為用戶參與行為所創造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用戶使用平臺軟件提交生成數字化內容;(2)用戶持續投入時間深度參與平臺建設;(3)用戶體驗具有的網絡性與外部性特征為平臺企業創造超額利潤;(4)用戶參與提供的內容和服務彰顯平臺企業的核心價值[10]。
筆者認同,收益性的判斷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且不同于將“收益”等同于“所得”的理解,此時的“收益”是與征稅對象的整體相對應的,指相關主體“得到的利益”(或者說是其“經濟能力或某種福利的增加”)[11]。但如下所述,上述觀點顯然過于夸大了用戶參與的價值,也錯誤地理解了此時的“收益”。
第一,該理論忽視了互聯網企業的數據處理技術對相關產業的推動作用。具體而言,雖然數字經濟中的許多業態都極為強調“用戶參與”,但這與價值變現之間仍有很大的鴻溝,并不能直接肯定二者間的因果關系[12]。換言之,用戶參與所創造的數據本身固然是有價值的,但這種價值只有通過互聯網企業的進一步加工才能產生現實的商業價值。以微博為例,用戶發表和關注微博等參與行為固然體現了其行為偏好,但這些基礎數據在未經加工的情況下就只是用戶在某個時刻進行某項操作的記錄。而平臺方想要利用這些數據獲利,還需要以這些數據為基礎,通過技術手段生成“用戶畫像”,以此為基礎吸引企業在平臺上精準投放廣告或進行其他商業運用。
第二,該理論忽視了傳統產業中的用戶參與行為。上下游產業鏈的融合并非新的現象,對“用戶參與”的強調也非數字經濟所獨有,互聯網的優勢僅在于更好地記錄和留存用戶參與所產生的相關信息。以傳統的餐飲行業為例,食客間的口口相傳顯然為其創造了價值,但顯然不會有人認可能將此作為征稅依據。在同樣創造了價值的情況下,為何僅對在虛擬空間中的價值創造征稅。對此,“用戶參與”理論顯然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
綜上,在無法準確界定用戶參與行為所創造的具體價值,且不能說明基于何種稅收目的在數字經濟下捕捉此種價值的情況下,無論“用戶參與”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為企業創造了商業價值,徑行征稅的做法只會將稅基建立在一個不確定的“價值”之上,不僅違背了“價值創造”原則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可稅性”原理對“收益性”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出一個更為合理的課稅依據。否則,如果只是重復數字服務稅作為一項特殊稅種的優勢,顯然不能充分論證繼續征收該稅種的合理性。基于此,下文將以“壟斷租”為依據,重新建構數字服務稅的課稅依據。
(三)數字經濟下“壟斷租”范疇的引入
所謂的“壟斷租”,并非一個特定的立法用語,可認為這是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對LSR的理解與適用,LSR 英文全稱為“Location Specific Rent”,直譯成中文是特定位置租金。目前,LSR的概念尚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故不存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立法語言可資借鑒,較為權威的理解主要來自于IMF、OECD、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聯合發起的稅收合作平臺(PCT)所發布的《對境外間接轉讓的稅收征管工具包》①The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The Taxation of Offshore Indirect Transfers— A Toolkit.[EB/OL].(2020-06-04)[2021-10-24].https://www.tax-platform.org/sites/pct/files/publications/PCT_Toolkit_The_Taxation_of_Offshore_Indirect_Transfers.pdf。,其認為雖然通常難以識別LSR,但其在某些情況下是相當明顯的,往往與政府創造的權利有關,尤其是在采掘業和電信業。基于此,LSR指向的應當是一種類似于現代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下的“經濟租”。具體而言,是由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如制定關稅和進出口配額,對企業發生生產、銷售許可證,實行價格管制等)抑制了市場競爭,造成人為的稀缺后所產生的價差收入[13]。
但理論上也存在不同觀點,如有學者認為LSR指向的是地域性特殊租,本質上是服務于對數字經濟中“用戶參與價值創造”的精確化解釋,旨在確定生產者或消費者剩余的特定位置來源問題。以平臺市場為例,由于雙邊業務中B邊市場的參與者關注的是A邊市場中的用戶規模,故平臺方在A邊市場可以低于邊際成本定價(即向該方提供補貼或其他激勵機制),而通過在B邊市場加大收費力度來彌補A邊市場的損失,通過供需端的信息不對稱來獲取利潤。在此種情況下,雖然平臺方的獲利依賴于B邊市場對A邊市場的需求,但企業的主要利潤并不直接來自于A邊市場,平臺經濟下的LSR由此就產生了[14]。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理解都關注到了LSR的某些特征,但從數字經濟的角度來看,都存在一定問題。第一種觀點關注到了LSR的本質在于對特定資源所享有的排他性支配權,但過于強調行政權力在此種支配權產生中的作用。在傳統市場中,此種關聯是能夠成立的。而數字經濟特殊的“馬太效應”使得傳統的規制模式失效,只能寄希望于加大行政干預的力度,通過各類經濟法規范進行外部監管。第二種觀點雖然關注到了LSR與特定地域的關聯,即LSR的產生必然會指向對特定區域資源的利用。但問題在于,這一理解將LSR的產生歸功于企業在信息不對稱下的優勢。問題在于,互聯網企業所賺取的利潤固然來源于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但這一數額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用戶參與的數量,且二者間往往是指數關系而非簡單的倍數關系。換言之,對于互聯網企業而言,更為關鍵的不是保持或擴大信息的不對稱,而是如何能在其所參與的市場內更大范圍地排他性利用當地資源。
事實上,信息不對稱幾乎存在于所有的行業中,是商業活動得以維系的根本,之所以要在數字經濟領域強調LSR,是因為其所特有的“馬太效應”能放大此種信息不對稱,使少數幾個頭部企業能利用相同或類似的產品獲取遠超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因此,在數字經濟下識別或界定LSR應結合上述兩種觀點,此時的LSR應被理解為一種“壟斷租”,即互聯網企業基于其產品優勢地位對相關地域市場內的公共資源所實際享有的排他性支配權。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特定位置不意味著“壟斷租”只能附著于不動產之上,而只是要求基于“壟斷租”所主張的稅收管轄權只能是屬地管轄權。換言之,稅收主管部門只能對企業在其管轄的地域范圍內賺取的“壟斷租”主張稅收管轄權。
(四)“壟斷租”與數字服務稅的正當性
在討論數字經濟稅收問題時,一個重要的共識是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征稅[15]。由于“壟斷租”的形成根本上說是來自于對市場國公共資源的利用,故基于“壟斷租”所獲取的利潤對于投資者而言構成了超額回報。對于此種超額回報,從“收益性”的角度看,即使采取全額征收的方法,理論上也不會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產生影響。因此,“壟斷租”提供了一個完全有效的稅基,可以認為是完美的征稅對象。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稅收合作平臺(PCT)認為,在稅制設計上的最優選擇是對此類“壟斷租”開征特定的稅種。但問題在于,企業會通過各種形式的稅收籌劃來轉移或隱藏這些超額回報。因此,如何識別此類“壟斷租”就成為稅制設計方面最大的阻礙,這一問題在稅收征管能力相對較弱的低收入國家更為突出。為解決這一問題,各國普遍采取了由資產所在國對其轉讓收益征稅的方式,以此作為一種有效的替代手段來平衡效率與公平間的沖突。
但數字經濟的特殊性有助于改變實體稅制被迫向征管壓力妥協的局面,即可以擺脫傳統上對客體的依賴,從主體角度實現對“壟斷租”的識別。以傳統的不動產交易為例,一般認為不動產在交易中的增值構成了可以識別的“壟斷租”,其所關注的是不動產這一客體而非所有者的主體身份。在數字經濟下,雖然市場主體所享有的數字資源或權利(如對互聯網空間的經營權)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由于互聯網市場所特有的“馬太效應”,絕大部分的利潤是由少數幾個企業所賺取的,這些企業事實上構成了對數字資源排他性利用。在這種情況下,就能夠基于其市場地位實現對“壟斷租”的識別,在判斷上不再依賴于特定的實物或權利,在“壟斷租”的識別上實現從客體向主體的轉變。同時,不同于客體識別在時間上需要等到交易發生,在程度上受制于評估結果的可靠性,這種基于主體的識別更為高效可靠。
由此可見,數字經濟的特殊性大大降低了識別“壟斷租”的征管成本,即使是征管能力較弱的國家,也不再需要使用替代手段,可以直接對此類“壟斷租”征稅。但仍需回答的問題是,這種以“壟斷租”為課稅依據的稅種為何僅針對數字企業,而非針對所有的商業模式?對此,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理由:
第一,從橫向公平上看,有助于恢復競爭中性。由于數字經濟特殊的“馬太效應”,總是存在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其經營活動即使符合競爭法的要求,所獲利潤中也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壟斷租”賺取的。由于反壟斷制度難以消除此類企業賺取的超額利潤,故從橫向公平和分配正義的角度看,應通過其他制度予以矯正,稅收措施能在這一問題上發揮“寓禁于征”的作用,也有利于保證企業整體稅負均衡。否則無法解釋的問題是,既然要求企業就正常經營所獲得的利潤納稅,為何會對此種超額利潤予以免稅。
第二,從征管上看,在實體經濟下識別此類“壟斷租”極為困難。在傳統領域,市場主體所占有的市場支配地位本身并不意味著其獲得了“壟斷租”,故主管機關也就難以基于企業的主體身份識別“壟斷租”,而基于交易直接捕捉此類價值的困境前文已經述及。
第三,從稅制結構看,數字服務稅僅具有補充性。理由在于,傳統企業所賺取的“壟斷租”多體現為土地或無形資產的增值。因此,在現行稅制下通過增值稅、契稅、印花稅等方式就能夠在交易環節實現對此類“壟斷租”征稅的目標,將數字服務稅用于捕捉此類“壟斷租”不僅會出現上述的征管困難,還會產生法律性雙重征稅的弊端。
綜上,從數字經濟的價值創造模式、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保證當地財政收入等實體性因素出發,并兼顧征管的可能性與稽征成本等程序性因素出發,以“壟斷租”作為課稅依據具有堅實的正當性基礎,以此為基礎建構的數字服務稅制度顯然能回應OECD方案在數字稅收方面的局限性,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稅收體制。
五、結論
作為數字稅收領域最新的立法實踐,數字服務稅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在數字產業上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所采取的臨時措施。但通過引入“壟斷租”的概念,本文不僅強調了數字經濟在價值創造上的特殊性,還進一步說明了中美等在數字經濟領域處于國際領先地位的國家將之作為常設稅種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在具體的稅制設計上,還應強調以下幾點:
在征稅范圍上,應嚴格限定其范圍,不能將之從狹義的數字經濟擴展至其他產業,否則將違背該稅種作為現行稅制補充的基本定位。在稅率上,應考慮如何實現傳統企業與數字企業的橫向公平,即實現互聯網企業基于該稅種所承受的稅負與傳統企業在市場國設立實體本身的稅收負擔相接近。在起征點上,由于“壟斷租”主要存在于頭部企業中,且基于稽征成本的考量,該稅種的起征點不宜過低,可參照特定企業的市場份額以及OECD方案所設定的起征點加以確定。在稅基的確定上,由于“壟斷租”的本質是對區域內公共資源的經營性排他使用,故仍應以營業收入而非利潤作為稅基確定的標準。但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部分在市場國內設立實體的數字企業,考慮現行稅制能對其所賺取的部分“壟斷租”征稅,故應在稅基確定或適用稅率上有所區別,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法律性雙重征稅。同時,若擔心由此會使得該稅種過于復雜,也可考慮不從主體的角度進行區分,而是在整體上確定一個較低的稅率。此外,對于發展和促進本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問題,可通過基于稅收優惠或制定產業政策的方式予以解決,但不應以此為由影響基本稅制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