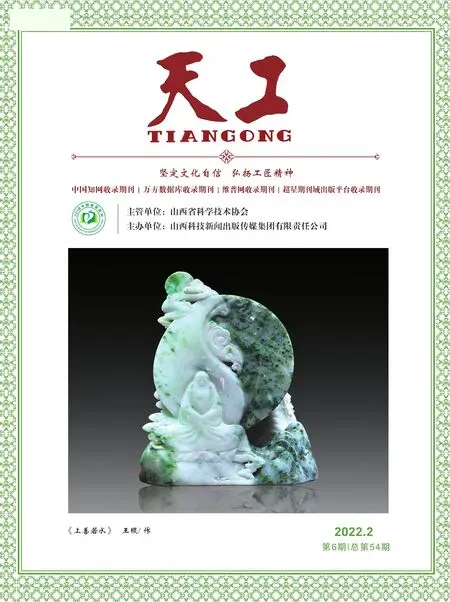論日本漆器蒔繪技法在陶瓷金繕修復工藝中的應用價值
水弘宇 湖北美術學院視覺藝術設計學院
一、金繕工藝的由來和發展
江戶時代的儒學家伊藤東涯的著作《馬蝗絆茶甌記》中記載,室町時代中期的足利義政將軍(1449—1473在位)有一只龍泉青瓷的茶碗,他很是喜歡,但因其底部有裂痕,所以將之送回中國要求更換一只相同的茶碗,然而當時的中國也沒有這樣一模一樣的青瓷茶碗,便用當時中國鋦瓷的技法修補后送回日本。但鋦瓷技術更多強調的是修復之后的實用性,足利義政將軍不太滿意其修復后的效果,日本的工匠就開始研究新的修繕手段,以此為契機,于是“金繕”誕生了。[1]
由此看來,金繕的起源也和中國古代修復技法“鋦瓷”有著一定的聯系,是“鋦瓷”促使著“金繕”的出現。雖然金繕所用到的技法是從中國的漆藝中提煉的,但日本的金繕工藝以他們自己的審美觀念和美學思想作為基礎,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修繕技法,產生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金繕是在修繕的部位用“金”粉飾,經過金繕后的器具上會有一條條纖細的金線,是為了給修繕的裂縫處增加效果,仿佛劃破黑夜的閃電和金色的樹杈一般。
金繕技法的根基還應歸屬于中國漆藝,是一種使用天然大漆修繕殘缺器皿的工藝,但在修繕器物之余,也有一定的裝飾效果。金繕強調以“金”來修繕器物,屬于漆藝的延伸,具體來說,就是用天然的大漆黏合瓷器的碎片或者填充缺口,涂滿欠缺的地方,在大漆上用金粉和金箔勾繪,被修繕的器物其裂縫處就像是融了些許的金子,裂紋處略微會凸出,但并不會顯得特別突兀。[2]
金繕工藝的快速發展,與日本的侘寂美學密不可分,侘寂是日本美學意識的一個組成部分,一般指的是樸素又安靜的事物,從老舊、破碎的物體外表下顯露出的一種充滿歲月感的美;“侘寂”作為日本一種古老的審美傳統,逐漸成為一種設計法則,金繕正是這一美學思想的物化,帶有一定的隱含理念。
近年來,由于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金繕已經普及到日常器物的修復之中,也走進了人們的生活,并產生了各種新型材料的技法,還可以將不同器物的碎片拼合形成新的藝術品。修繕的字面意思無疑是將器物還原成本來的面貌,而金繕的目的是修復且凸顯修復的技藝。金繕作為大漆藝術中的一種,傳統上屬于修復的領域范疇,但要達到一定的藝術造詣也需要匠人們有良好的美學思想及藝術功底,這樣修繕出的器物是帶有一定藝術色彩的。
二、“蒔繪”在金繕技法中的藝術性表達
“蒔繪”是以日本傳統漆器工藝為基礎所延伸出來的一種裝飾技法,是符合日本人審美趣味的工藝美術形式,產生于日本奈良時期,遠早于金繕工藝的出現。歷經鐮倉、室町時代繼續發展,每個時期都會出現一種代表不同時代的蒔繪技法(見表1)。

表1 710—1867年日本奈良至江戶時代蒔繪技法發展表
蒔繪作為一種大量使用黃金來裝飾的技法,工藝繁復、材料講究。由于運用金銀作為裝飾花紋,在做完推光之后,會使作品顯得十分華麗。蒔繪的工藝只能全手工來完成,沒辦法借助機器的力量,所以蒔繪是相當耗人力的一種工藝,是花費時間和精力造就出的藝術品。蒔繪講究雕琢的技藝,紋樣多樣,以一種清新淡雅且優美的表現形式,卻不拘泥于自然景象的描繪。蒔繪為了增強表現力來豐富作品,還會采用螺鈿、銀絲進行勾勒繪畫等,工藝的復雜、煩瑣程度會遠高于金繕。[3]后來通過蒔繪技法的完善,作品不斷在技巧上、意匠上有了創新,技法水平也愈發精湛,手法新穎且獨特,給世界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物。尤其作為蒔繪技法最輝煌的江戶時代,蒔繪工藝在制作上構思大膽、做工精良,有相當細膩和精美的成就。硯盒方形圓角,蓋面隆起,另刻有細紋似波,像一葉小舟正從拱橋下蕩過,極具裝飾性的工藝貫穿古今雅俗(如圖1)。隨著蒔繪技法的發展,出現了更多精美的器物,對裝飾的描繪從山水轉變為某一古典題材,在硯盒的圖案中,木板橋通過薄薄的鉛板來表現,盛開在木橋周圍的燕子花葉使用了金粉,花瓣則使用了鮑魚的貝殼進行裝飾。器物精美典雅,設計和創意手法十分大膽,黑與金銀的對比,凸顯了主題和本質(如圖2)。

圖1 舟橋蒔繪硯盒,本阿彌光悅(1558—1637),創作于17世紀日本江戶時代,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

圖2 八橋蒔繪螺鈿硯箱,尾形光琳(1658—1716),創作于18世紀初日本江戶時代,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
蒔繪的強裝飾性運用在金繕工藝中,提升了修繕的多元化,除了符合金繕的發展趨勢之外,對藝術創作的態度也有重要的影響。擺脫常見于金繕修復后的簡單樣式,脫離金繕看似拼湊的感覺,打破局限,能夠進一步加強修繕后的創造性和藝術性。如果金繕重在用漆修繕,那么蒔繪則重于描繪,在金繕修復過程中,使用蒔繪工藝的表達,可以讓器物更加生動,賦予獨特的美感,既保證了器物修繕后的完整又體現了工藝的質感和層次感。金繕修復之后的器物會存在幾根相交錯落且流暢的金線,運用蒔繪技法進行點綴,形成新的紋樣、凝重的色彩和微妙的細節處理,在不同的形式上展現出新的生命力,呈現特殊的肌理表現特征,豐富作品的立體感。蒔繪在金繕工藝上的藝術性表達更多體現在拓展與創新,相互借鑒和學習,融于自我的審美意識,再現的不應該只是器物曾經的輝煌,從凸顯金繕的線創造成器物上一個個的浮雕作品,再考慮器物本身的整體性,尋找最符合它們氣質的表現方式,發散出多樣的藝術風格。對于工藝應用上的藝術性,在不斷延展綜合技法的同時,也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提升作品的藝術品位。
三、蒔繪技法在金繕中的可實施應用和價值
通過熟練地把握金繕和蒔繪技法,將多種表現方式融合并用,在尊重傳統的同時積極創新,為修復器物的藝術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綜合技法上的融合,能夠賦予器物更多的美,展現工藝的技術和藝術,探索蒔繪、金繕的美學價值。
繪紋是蒔繪技法中最主要的方法,對裝飾花紋設計各種圖案,施加金銀或箔片描繪,可以輔助金繕工藝提供更多的創意,使殘缺的器物具有紋理的裝飾性能。在修繕的同時,要整理優化殘缺,從紋飾本身的美感到與殘缺的形狀是否契合,對于創造做取舍,通過漆繪圖案來彰顯審美趣味,豐富表現形式(見圖3)。螺鈿作為蒔繪工藝中常見的技法,將鮑魚貝殼的珍珠層磨平,切割成圖樣貼于器物表面,屬于對器物的鑲嵌修法(見圖4)。螺鈿的介入,是修繕器物的色澤依光線而呈現微妙的變化,強調的是色彩關系。不同的光澤和色彩可以滿足器物以鑲嵌裝飾的需求,但要求搭配和諧,銜接流暢自然。在繪制的漆紋上堆高,被稱為堆高繪紋,塑成浮雕式的紋樣,這是蒔繪技法從二維平面到三維立體創作的一個突破(見圖5)。紋飾圖案高出器物平面許多,有很強的表現力,使裝飾更加清晰立體,整體生動流暢。金繕和蒔繪都屬于漆工藝的文化,兩者既是風格迥異,又可以相互融合,蒔繪技法可以很好地修飾金繕工藝,使金繕工藝得到更大的進步,從而產生出更加優異的工藝品。

圖3 平蒔繪漆繪圖案

圖4 高臺寺蒔繪螺鈿

圖5 肉合蒔繪堆高繪紋
蒔繪技法在金繕工藝上的運用,能夠突出實用意義和藝術價值。金繕的最終目的是修復器物,蒔繪技法可以為金繕的藝術表現形式提供技術支持和審美指導,強調材料包容性的情況下相互轉化與發展。蒔繪技法運用于金繕工藝之中,這種再創造的方式,并不只是將器物重新復原,而是通過殘缺的痕跡表露出來,豐富金繕修復效果,蒔繪在金繕工藝上的運用已達到華麗、創新而又不失淡雅的效果,把技術精細的特色發揮到極致,這才是將漆藝發展和發揚的重要手段。[4]單一的線條不存在強有力的裝飾效果,以蒔繪形式來表現繪畫的效果,千變萬化的創作讓工藝變得有創意,也能從眾多金繕器物中脫穎而出。蒔繪技法帶給金繕工藝新的影響,藝術表現形式的融合豐富了視覺效果,也是為工藝創新提供了借鑒。把破碎的器物通過獨具匠心的藝術手法,打破固有的思維和藝術界限,加入個人審美觀念和情感表達,為工藝實踐提供了參考價值。在保護的基礎上不斷做加法,變通和創新是文化融合的手段,也是文化傳承的一種方式。
四、結語
金繕和蒔繪都屬于漆藝,不同的工藝形成了它們各自的運作方式,也都成為世界文化寶貴的組成部分。二者在工藝風格上也具有較多的相通性,蒔繪本就可以成為金繕的藝術創作手法,金繕工藝強調缺憾美,把蒔繪技藝運用在修繕的最后一步,這不單單是對器物的還原,也在追求有意境并且精巧的裝飾,融合方式的呈現最終是以“美”為規律進行設計的。有深切的美學思想和創新的工匠精神,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聯系,見證文化的傳承,對傳統工藝保持尊重的態度,將技術與藝術精巧地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在每一件器物中都得到精心的演繹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