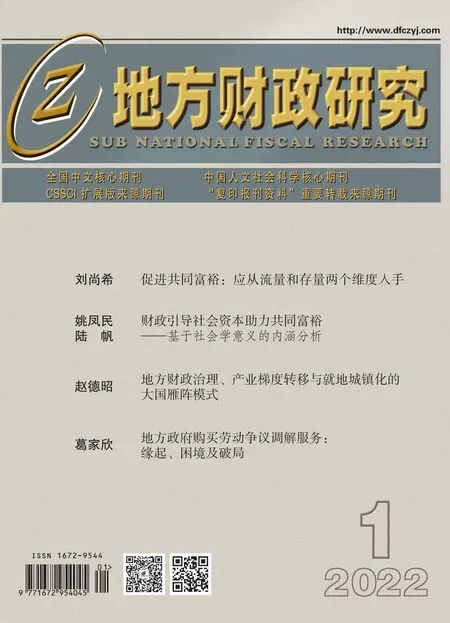促進共同富裕:應從流量和存量兩個維度入手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142)
內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而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推進共同富裕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收入分配。但是,研究收入分配不能忽視存量財富分配,存量財富在客觀上決定了流量收入的分配情況。因此,要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僅著眼于在流量分配上做文章已略顯不足。相關方面可將存量和流量兩個維度結合起來思考,從完善市場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機制,發揮公共消費的積極作用,增強稅收再分配能力等方面入手,構建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共同富裕實現機制。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下稱《意見》)公布。《意見》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無疑,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最直接方式。但從客觀角度出發,更應從存量和流量兩個維度來分析貧富差距的問題,進而找到促進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從存量來理解貧窮與富裕,體現在財富或財產積累的多寡上,富裕不只是收入高,更是財富多,而貧窮意味著“無產”,沒有財富的積累,所謂一貧如洗。走向共同富裕,不能只考慮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財富分配,因為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獨立地發揮作用,并自發地擴大收入分配差距。俗話說的“有錢的越有錢,沒錢的越沒錢”,其話中的第一個“錢”就是指存量財富,第二個“錢”字是指收入。存量分配與流量分配一旦形成一種自發的分配循環機制,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將會邊際遞減,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將會體現到家庭貧困的代際傳遞之中,也會反映到社會階層和整個社會分配之中。
一、收入流量和財富存量共同決定了社會富裕水平
在大家的習慣性思維中,經常混淆了“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概念。事實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區別,前者是指流量分配,而后者是指存量分配。盡管存量是流量的歷史性沉淀,但存量分配卻現實地決定了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規模越大,對流量分配的決定作用就越大。
收入體現為當期的流量,在初次分配過程中,是以市場為主體的分配,通過要素價格機制進行分配,本質上是一種經濟交換;在再分配過程中,則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分配,通過所得稅、財產稅、社保繳費、轉移支付、社會救助等方式進行分配,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契約。除此以外,還有以社會為主體的第三次分配,本質上是一種基于道義的慈善行為。我們平時強調的分配公平,更多是基于當期的收入流量來認識的,包括再分配政策,也是強調與企業、家庭、個人等主體的當期收入直接相關。比如,白領階層的收入高,無償轉移性支出就更多,如繳納個稅;反之,失業人員等低收入人群則能獲得更多的轉移性收入,如領取救濟金。顯然,這是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財富屬于存量概念,是居民、企業和政府年復一年積累的結果。財富進入經濟循環過程變為資產。資產包括實物資產、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把消費之后的剩余轉化為各種資產,以及由于資產的增值、貶值,從而帶來富裕水平的變化。例如,城市住宅價格的大幅上漲導致市民存量財富的增加。當然,這種財富的增值并非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得益于城市空間價值的“漂移”,公共價值外溢到了私人財富上面。再如,少數商人廉價獲取國有資產經營權或自然資源開采權,由此形成的財富積累也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所造成的,而是利用公共產權制度的漏洞形成對全民資產的侵蝕。另外,還可以通過金融市場發揮作用,比如,借助股票、期貨、基金、信托等金融產品的市場交易,蝕本者的存量財富被轉移,實現社會財富的集中和集聚。在金融市場不健全的條件下,財富流動就會很快拉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二、財富存量的分配會加速擴大貧富差距
由于我國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均衡性特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過去有所擴大。這些年來,城鄉收入差距又有所縮小,與改革開放初期水平相當。但若從存量分配的角度來看,城鄉居民貧富差距遠遠大于收入分配造成的差距。比如,在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前,城鄉居民的財富差距并不大,表現為當期貨幣收入的差距有限。但在之后的20余年內,由于房地產市場的高歌猛進,僅住房一項就形成了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
事實證明,農民收入增長再快,也趕不上市民資產增值形成的財產差距。這意味著農民與市民處于不平等的地位,農民的市民化仍面臨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縱向流動受阻,社會貧富差距固化甚至擴大所蘊藏的公共風險值得高度關注。金融資產也是如此,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難以伴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升值,有些金融資產反而出現了貶值,意味著存量財富被轉移了。在金融泡沫、金融抑制和金融壟斷并存的背景下,居民的金融資產價值很可能通過銀行存款、貸款、股票、債券、基金、信托等金融工具向金融部門或處于優勢地位的交易方隱性轉移。例如,普通民眾將其積蓄投入股市或互聯網借貸平臺,可能面臨財富損失,甚至“血本無歸”。而一些高凈值人群,更容易獲得專業的理財服務或更及時的市場信息,有更大可能實現可觀的資產收益。這種“財富效應”會導致財富存量的再分配,擴大貧富差距。在法律不健全、信息不透明、職業道德水準不高的條件下,尤其是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如基金公司、理財公司更是發揮著這種存量再分配的作用。
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財富存量日益累積。積累的財富都會通過資產化,也就是金融化,進入經濟循環過程,相應地,財富的再分配規模也越來越大。再分配機制與現行的各種制度之間的隱性關聯以及金融市場的發育不健全,可能導致財富的過度集中化趨勢,從而造成更為明顯的貧富差距。
三、存量改革和流量改革的協同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充要條件
相比于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轉移和再分配功能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是隱性的,不易被覺察,但往往又是決定性的。因此,要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僅著眼于流量分配上做文章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維度來討論分配問題,最終難以縮小貧富差距,甚至可能因“誤診”而導致適得其反的結果。最終必須從存量和流量兩個維度來追溯貧富差距擴大的內生機制,通過政府的再分配與市場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兩手抓,推動構建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共同富裕實現機制。
一是完善市場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機制,矯正財富存量分配扭曲與不公平現象。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市場分配具有天生的“馬太效應”,這不僅體現在以要素貢獻為衡量標準的初次分配中,還體現在市場的存量再分配機制中。交易主體雖然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但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如雇主與被雇傭者之間;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實體企業與金融企業之間等等。尤其在金融市場中,信息不對稱更容易導致財富存量的不公平再分配。因此,必須建立一套公平、規范、透明的制度框架,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特別是打造透明、公正、法治化的金融市場環境,盡可能保障普通民眾的財富存量不受到隱形侵害和掠奪。
二是從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發揮公共消費在縮小能力差距中的積極作用。從社會個體來看,貧窮終歸是能力的貧窮。公共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個人消費差距所導致的能力差距,有助于增進不同群體發展的起點公平、機會公平,促進人力資本投資均等化,為縮小收入和財富差距奠定基礎。因此,堅持以人為本,擴大政府在公共消費領域的人力投資、社會投資,是逐步縮小以至消除能力的群體性鴻溝(如農民與市民),進而破解收入差距、增進機會公平的關鍵所在。農民市民化,在城鎮化中減少農民,使我國從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按照戶籍,目前農民占到55%)轉變為一個以市民為主體的國家,這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徑。具體來說,應加快城鄉分治改革,實現公民基本社會權利的平等化,加快破除農民與市民、編制內與編制外、工人與干部等阻礙縱向流動的社會身份,這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在此基礎上,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持續加大對社保就業、醫療衛生、基本住房保障、基礎教育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和投入,并建立健全標準體系和動態調整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與人口、勞動力流動及其分布變化相匹配,使公共消費變成促進人的發展的有力工具。
三是把稅收調節功能寓于稅收收入功能之中,增強稅收再分配能力。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和政策,多渠道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具體來說,應著力完善直接稅制度,擴大稅基,并優化財產稅制度,增強稅收的調節功能;同時,完善社會第三次分配的稅收政策,積極發揮稅收對慈善捐贈的激勵和引導作用;鼓勵社會力量在促進人的發展,提升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