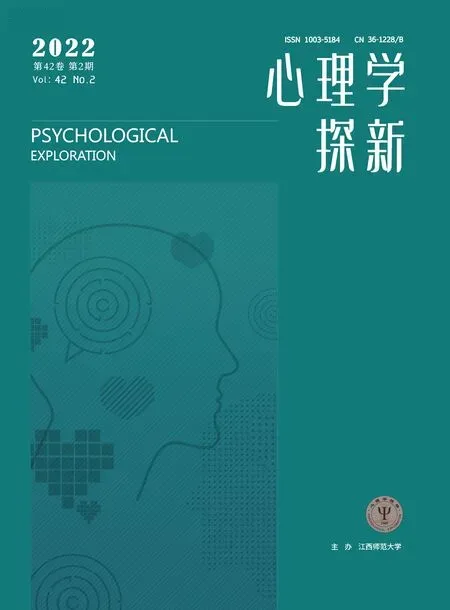漢字飽和現象:證據、因素與展望*
王晨旭,李 利,袁 杰
(1.華南師范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漢語學習與國際推廣省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631; 2.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廣州 510631)
1 引言
長時間注視某個字后,人們會產生一種這個字變得陌生或者開始解體的感覺,這是一種文字飽和現象。研究者普遍認同文字飽和現象的存在,但是文字飽和現象發生的階段仍沒有統一的定論。賈建榮和張德玄(2013)曾對文字飽和現象及其發生的認知加工階段進行了系統的介紹,他們認為文字飽和研究最大的爭論仍是這種現象發生的認知加工階段,使用不同實驗任務得出的結果提示,文字飽和可能發生在知覺加工階段、語義加工階段和知覺-語義聯結階段。
在文字飽和現象研究的發展歷程中,實驗范式得到了改進(仝文,閆國利,2013),現代技術運用到了研究中(Stroberg et al.,2017),研究者對于這一現象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其中,漢字飽和現象也得到研究者更多的關注。相比于拼音文字,漢字是形體復雜的方塊結構(黃伯榮,廖序東,2017),其具有獨特的正字法規則。那么,漢字飽和現象是否具有其獨特性,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該文通過對漢字飽和現象實驗任務與實驗材料內部邏輯的探究,進一步梳理了漢字飽和現象發生的證據,歸納了影響漢字飽和現象的因素,并嘗試開拓思路,針對漢字飽和,從漢語二語和具身認知等視角對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2 漢字飽和現象的證據
研究發現,相比于拼音文字的飽和現象,漢字作為方塊字,更易在前語義,即字形加工階段發生飽和,且被命名為字形飽和。此外也有研究者認為,隨著重復次數或者注視時間的延長,漢字飽和可能不是發生在特定某個階段,而是體現多階段特征(仝文,2015;秦釗,2017)。
2.1 漢字字形飽和的證據
漢字由方塊結構構成,其部件與整字的復雜關系和結構差異可能對飽和結果產生影響。Cheng和Wu(1994)以漢語母語者為被試,采取自我報告任務,被試需持續注視一個漢字,直至認為這個漢字開始解體,報告這個感覺后開始下一個試次。結果發現,獨體字飽和最慢,左右結構的字飽和最快。主觀報告法對文字飽和現象的報告是全或無的,且被試容易受到研究者的暗示,為避免這個問題,Lan(2007)采用了更加客觀的詞匯辨別任務。實驗一以獨體字和左右結構的字為實驗材料,同樣發現左右結構的漢字更容易飽和;實驗二控制了整字與部件的音義相似性,發現整字與部件意義不同條件下飽和速度較快。此外Lan將同音真假詞和非同音真假詞為實驗材料,探究假詞性質對漢字飽和發生速度的影響。然而無論真假詞是否同音,被試在看到呈現的詞時,就已經開始了字形的加工,然后再開始語音的加工(Yuan et al.,2017),因此無論假詞是否同音,被試都會不自覺地先對字形進行加工。Cheng和Lan(2011)在Lan(2007)研究設計的基礎上引入一個新的指標β,發現字形解體的程度是隨重復次數的增加而不斷增大的。根據多語義激活假說(Activation of Multiple Lexical Entries,AMLE)的預測,字形飽和與漢字部首意義有關,為了驗證這一假說,Cheng和Lin(2013)選擇部首獨立(具有意義)和部首非獨立(脫離整字無意義)的左右結構漢字為實驗材料,發現兩種實驗材料都可以觸發飽和。由此他們推測漢字飽和出現在字形加工階段的原因是當人們長時間注視一個漢字時,先是對漢字進行整體加工,然后開始對部件進行局部的加工,但是在部件加工整合時出了問題。
袁靖嘉(2015)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區分了漢字的字形飽和與語義飽和。實驗一對真字、不符合正字法規則的假字和筆畫組合為實驗材料進行飽和操作,發現真字材料的N170成分波幅變化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漢字飽和出現在字形階段是因為正字法規則受到了限制。
Cao等(2019)以漢語母語者為被試,選用生僻字(如:艓)為實驗材料,盡可能減少語義對實驗的干擾。這些漢字都是左右結構的,且由三個部件組成。實驗采用類別匹配任務,先呈現較少使用的漢字,再呈現部件,被試需判斷部件是否是所呈現漢字的一部分,這個實驗揭示了重復過程中飽和現象相較于練習效應逐漸占據上風的競爭關系,實驗結果為字形飽和提供了證據。
2.2 漢字字形-語義聯結階段飽和的證據
袁杰(2011)和Yuan等(2017)將快速重復啟動范式和類別匹配任務運用到漢字飽和的研究中。實驗一的實驗材料為“花-月季”這樣的配對,“花”為類別詞,“月季”為樣例詞,被試的任務是判斷所呈現的樣例詞是否屬于類別詞;實驗二的實驗材料換為“月季-玫瑰”這樣的配對,被試需要判斷兩個樣例詞是否屬于同一個類別詞。實驗三則是需要對“月季-月季”這樣的配對作出匹配反應。其中,實驗一涉及到字形加工階段,字形到語義的聯結階段和語義加工階段。實驗二只涉及語義加工階段,實驗三只涉及字形加工階段。結果顯示,只有實驗一出現了飽和現象,實驗二和實驗三都未發生明顯的飽和。袁杰(2011)和Yuan等(2017)認為由于漢字主要是通過字形與語義表征之間的直接映射關系被識別的,當字形和語義之間的這種直接映射關系被反復重復時,便發生了飽和現象,因此他推斷漢字飽和現象發生在字形-語義的聯結階段。
張積家等(2014)研究了漢英雙語者的文字飽和現象。在其實驗2中,實驗2a讓漢英雙語者完成英文類別詞-中文樣例詞(如:fruit-香蕉)匹配任務,實驗2b完成中文類別詞-英文樣例詞(如:水果-banana)的匹配。研究發現在中文類別詞-英文樣例詞的任務中,對不熟練二語者來說,一語的重復加工促進了他們二語語義加工,而對熟練二語者來說,一語的重復加工阻礙了熟練二語者的二語語義加工。他們認為,跨語言情境下的實驗沒有出現飽和現象,因為當一種語言的啟動詞的字形到語義的通路雖然被多次使用出現了疲勞,但是另一語言的字形到語義的通路卻未被使用,因此當這種語言的目標詞出現時,由于其字形到語義的聯結通路未被使用,就不會出現疲勞,飽和現象也就無從產生。張積家等(2014)結果也為字形-語義聯結階段飽和提供了證據。
吳迪等(2016)利用Tian和Huber(2011,2013)的實驗范式,以中文詞對作為對象,論證了漢字飽和現象發生在字形-語義聯結階段,并在此基礎上考慮到漢字的部首和詞素都包含了豐富的語義信息,研究了漢字表意部件的飽和現象。他們在實驗4選擇具有相同表意部件的材料,如:昆蟲為類別詞,螞蚱、蝴蝶等為樣例詞,被試需要判斷樣例詞-樣例詞之間的匹配性。結果發現,表意部件的重復可以引發被試的漢字飽和現象,這說明漢字的表意特點使得漢字飽和相比于拼音文字的飽和有其特殊性。
2.3 漢字語義飽和的證據
許樂山(2012)以漢語詞對為實驗材料,將Tian和Huber(2011,2013)實驗的重復次數調整為20次,通過增加重復次數,許樂山首次發現了漢字語義加工階段的飽和現象,與袁杰等人認為的文字飽和是發生在字形-語義聯結階段的結果不同,為漢字語義飽和提供了證據。
Smith和Klein(1990)對類別詞(如:FURNITURE家具)進行飽和操作后,新的樣例詞之間(如:CHAIR椅子和TABLE桌子)也出現了顯著的語義飽和,說明語義飽和有擴散性。袁靖嘉(2015)據此選用60組語義相連的詞語為實驗材料(如:房/屋/樓,桌/椅/凳),第一個字作為啟動字(房),第二個字作為關鍵項(屋/樓),每個啟動詞重復18次,第1次和第18次后都隨機呈現一個關鍵項,關鍵項有50%的可能性與啟動字語義相關,被試不需要做出行為反應。結果發現了N400波幅在語義沖突的條件下仍明顯減弱,袁靖嘉認為是由于語義網絡中概念節點發生過度激活,這種激活在相鄰節點之間發生擴散,降低了目標詞(如:桌)與背景語義(如:房)之間的語義沖突,N400振幅的顯著衰減說明發生了飽和現象,且飽和發生在語義加工層面。但是袁靖嘉(2015)的研究缺少行為實驗的數據支持,因此對漢字飽和現象過程的觀察有所欠缺。
張虹(2018)借鑒張積家等(2014)的思路,以蒙漢雙語者為被試,采用實驗材料為蒙語類別詞-漢語樣例詞、漢語類別詞-蒙語樣例詞的匹配任務。張虹認為,蒙語、漢語屬于不同的語系且詞性不同,可以排除字形加工飽和的干擾。張虹還認為如果飽和是發生在字形-語義聯結階段,那么概念層就不會受飽和的影響,概念層所在的語義網絡更不會疲憊,跨語言的飽和就不會發生。因此對啟動詞進行飽和處理后,如果能引起目標詞的加工困難,則有理由說明飽和是發生在語義加工階段的。其結果發現蒙漢雙語者的漢字飽和發生在語義加工階段。
除上述三種飽和階段外,許樂山(2012)推測飽和現象隨重復次數呈倒U形曲線發展,仝文(2015)受其啟發,用眼動儀來記錄被試飽和實驗時的注視時間。行為實驗的結果顯示飽和現象都是先增大后減小的,呈倒U形趨勢。而眼動實驗中,只有涉及飽和現象所有階段的總實驗呈現出倒U型曲線趨勢。秦釗(2017)以古漢字為實驗材料,采用經典的啟動范式,被試需要判斷屏幕上的兩個字是否匹配。他通過分析腦電成分N170的平均波幅,發現字形飽和的時間進程的確呈倒U形曲線。因此他們都認為漢字飽和有多階段發生的可能,但是這個觀點仍需更多實驗結果的認證。
3 漢字飽和現象的影響因素
3.1 語義加工深度
在較早的研究中,基于類別匹配任務與詞匯判斷任務的結果并不一致。Neely(1977)選用詞匯判斷任務研究拼音文字的飽和現象,沒有觀察到飽和現象。Smith和Klein(1990)認為詞匯判斷任務的語義加工不夠深入,分別采用詞匯判斷任務與語義加工更深入的類別匹配任務研究語義飽和,結果只在類別匹配任務的組別中發現了飽和現象。Smith和Klein的實驗說明,語義加工深度可能對語義飽和現象的出現產生影響。
之后的研究中,基于類別詞-樣例詞匹配任務與樣例詞-樣例詞匹配任務的研究結果也不一致。對比李小華(2013)和吳迪等(2016)的研究發現,同樣選擇具有相同表意部件的漢字為實驗材料,李小華采用類別詞-樣例詞的匹配任務沒有激發飽和現象,而吳迪等采用樣例詞-樣例詞的匹配任務成功激發了被試的漢字飽和現象。實驗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判斷兩個樣例詞是否是一類,比判斷一個樣例詞是否屬于啟動詞類別需要更加純粹的語義加工。因此通過對文獻的整合,本文認為漢字的飽和也受到語義加工深度的影響。
當部件與整字的關系不同,個體對于漢字意義加工的程度也不同。Lan(2007)的實驗二發現當漢字的部件與整字意義不一致時更容易產生飽和現象,被試需要更深的語義加工來進行判斷。同樣,Cheng和Lan(2011)發現部件與整字意義一致時更不容易觸發漢字解體。
研究者通過對實驗材料語義透明度的控制也能發現語義加工深度對漢字飽和現象的影響。邵云(2019)發現語義不透明低頻字更容易發生飽和現象,且更穩定。語義不透明低頻字的飽和現象顯著早于語義不透明高頻字。相對于高頻字和語義透明度高的字,被試在加工低頻字和語義透明度低的字時,需要更深的語義加工。
3.2 實驗材料的重復次數
同樣是使用類別匹配任務,由于研究者對實驗材料重復次數設置的不同,其結果中漢字飽和現象發生的階段也存在爭議。
Tian和Huber(2011,2013)的實驗中,不同水平的實驗材料分別重復出現10次,袁杰(2011)和Yuan等(2017)選取了相同的重復次數,結果支持Tian和Huber(2011,2013)的結論,即漢字飽和也是發生在字形-語義聯結階段。此后采用相同重復次數的研究同樣認為漢字飽和現象發生在字形-語義聯結階段(張積家,劉翔,王悅,2014;吳迪 等,2016;邵云,2019)。
而許樂山在Tian和Huber(2011,2013)實驗的基礎上,把重復10次調整為重復20次,結果發現漢字飽和現象發生在語義加工階段。對比張積家等(2014)的研究,張虹(2018)關于蒙漢雙語者的研究將重復次數設定為22次,同樣認為漢字飽和現象是發生在語義加工階段。
由此可見,對實驗材料的重復操作是引發飽和現象的重要步驟。如果漢字飽和確實是多階段發生的(仝文,2015),那么可能需要對實驗材料進行不同次數的重復操作,才會引發相應加工階段的飽和現象。
3.3 實驗材料類型
現有漢字飽和研究多使用單字、詞組為實驗材料,且漢字的部件組合方式與構造方式不同也會對漢字飽和現象產生影響。
在以單字為實驗材料的研究中,研究者考慮到了不同部首與漢字結構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當實驗材料為上下結構和左右結構,且控制實驗材料的部首時,荊玉(2016)將真字和假字都放在一個矩陣中,被試需要判斷每一個字的真假,實驗發現了漢字的字形飽和。當控制實驗材料部件與整字的關系時,李小華(2013)以含字內義符的形聲單字為實驗材料(如:女-姐),被試需要判斷整字與部件的匹配性。可能由于被試采取了部分線索的策略,實驗沒有發現飽和現象。而Cao等(2019)以生僻字為材料,讓被試對整字和部件進行匹配,卻發現了漢字的字形飽和現象,相比于李小華(2013)的實驗,Cao等(2019)實驗出現字形飽和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選取的實驗材料相對復雜,被試需要進行更仔細的判斷。此外,研究者還通過控制單字的語義熟悉度,選擇古文漢字或與漢字結果相似的韓文來探究字形飽和現象(Cao et al.,2019;秦釗,2017;仝文,2015)。
相比起單字,在以詞對為實驗材料的研究中,更凸顯了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聯。當采用語義加工程度較淺的詞匯判斷任務,且以語義透明度與詞頻高低為自變量時(如:語義透明高頻詞-時間;語義透明低頻詞-踢球;語義不透明高頻詞-法律;語義不透明低頻詞-榨菜),研究者發現語義不透明的低頻詞更容易出現飽和現象。當采用類別匹配任務時,被試需要匹配類別詞(如:花)-樣例詞(如:玫瑰),樣例詞(如:玫瑰)-樣例詞(如:月季)之間的語義關系,且大部分實驗都得到了顯性的結果,比較容易觀察到漢字的飽和(邵云,2019;吳迪 等,2016;袁靖嘉,2015;袁杰,2011)。
4 未來研究展望
4.1 漢語為二語者漢字飽和現象的進一步探究
在二語語義加工研究方面,早期雙語兒童可以直接通達概念意義,但是二語詞匯語義通達的強度要弱于一語詞匯通達的強度(李利 等,2010),可見二語加工在某些方面與一語存在差異,隨著研究的深入進行,研究者們開始好奇二語者是否也能產生像母語一樣的飽和現象。未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漢語為二語者的漢字飽和現象進行探討。
二語熟練度會對二語飽和現象有影響。劉玉萍(2019)以漢語高度熟練的留學生為研究對象,觀察到了漢字飽和現象,且此現象發生在語義通達階段。張虹(2018)在熟練蒙漢雙語者的身上觀察到了二語飽和現象,但沒有在非熟練蒙漢雙語者身上觀察到。對于非熟練蒙漢雙語者,張虹認為被試在進行實驗任務時,可能會選擇翻譯的策略,借助母語通達二語的語義。張積家等(2014)以漢英雙語者為被試進行文字飽和的研究,發現即使是通過英語專業八級的被試也只對中文材料產生飽和,未對英文材料產生飽和。對未通過英語六級的被試來說,也只觀察到了練習現象,因此他們認為文字飽和只發生在母語文字材料中。他們的實驗結果沒有產生飽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每個類別詞下只選擇了4個樣例詞,被試受到的重復刺激不夠。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進一步操縱實驗材料的數量及選擇不同漢語水平的漢語學習者為被試,深入探究二語熟悉度對漢字飽和現象的影響。
實驗材料的重復程度也會影響二語飽和現象的產生。張積家等(2014)未在熟練的英語為二語的被試身上觀察到二語飽和現象,而許樂山(2012)的實驗卻在熟練使用英語的被試身上發現了二語飽和現象,且許樂山(2012)將實驗材料的重復次數從10次增加到20次。因此二語飽和現象的產生除受被試二語熟練度的影響外,實驗材料也需要達到足夠多的重復次數。
語言間距離對二語飽和現象的影響。張金橋和王燕(2010)探究了中級漢語水平韓國和印尼留學生對高頻漢字識別過程中形音義信息激活的相對時間進程,發現漢字文化圈的韓國留學生是字形—字義—字音的激活順序,而非漢字文化圈的印尼留學生是字形—字音—字義的激活順序。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學生對高頻漢字形音義信息激活的時序不盡相同,因此其漢字飽和發生的時間進程是否也會存在差異呢?秦釗(2017)以韓文作為沒有語義,但與漢字結構相似的實驗材料,以中國學生為被試,結果發現了韓文的字形飽和現象。這可能是由于漢語與韓語的語言間距離較近。對于歐洲國家的二語者來說,若母語為英語,二語學習法語可能會相對輕松,而中文與其他語言文字體系差異較大,且學習難度大。因此二語為漢語的學習者相較于其他二語學習者,文字飽和現象會不會存在差異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4.2 語義飽和與字形飽和的進一步分離
就已有研究來看,漢字飽和有發生在各個加工階段的可能,但是以往研究還未真正將字形加工和語義加工階段完全區分開。Cheng和Lan(2011)采用了詞匯判斷任務來研究漢字的字形飽和,詞匯判斷任務會產生語義的通達,那么這個實驗任務的過程中既包含了字形加工又涉及語義加工,因此在發現字形飽和的證據中,仍不能剝離語義的參與。Yuan等(2017)的實驗雖然得出了飽和是發生在字形-語義聯結階段的結論,但是他們所選用的實驗材料是有意義的,即使在進行字形飽和的任務時,語義加工任務也會自動激活。而且,類別匹配任務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字形飽和與文字飽和的關系,因此研究者在探究字形飽和時,需要盡可能排除語義的干擾。
已經有研究者努力嘗試剝離語義與字形的相互影響。例如,仝文(2015)考慮到語義加工與字形加工相互干擾的問題,在實驗材料上選擇了韓文和現在已經棄用的古代漢字,進一步地將字形加工和語義加工分離。但事實上,雖然中國韓國同為亞洲國家,但是兩國的文字卻不屬于同一個體系。因此被試對于古漢字和韓文的加工是否采用了相同的正字法規則還有待進一步考察。同時,依據先前的研究,部件與漢字一致性等也是未來研究的考慮因素。Cao等(2019)選擇了不常使用的漢字為實驗材料,在保證正字法規則一致的情況下,也進一步減少了語義的加工對字形飽和的影響。
未來如何在語義任務中降低字形的干擾?拼音文字的飽和研究中,Stroberg等(2017)通過改變啟動詞的字體大小和格式(如:普通、加黑、斜體)來最大限度減少非語義過程的混淆。未來的漢字飽和研究也可以借鑒類似的方法減少字形對語義加工的影響,從而使飽和現象涉及的加工階段更加純粹。此外,在漢字飽和的研究中,仍要依據漢字的特點,考慮控制漢字筆畫數、漢字結構等因素。
4.3 漢字作為實驗材料的進一步挖掘
漢字作為表意文字,漢字的義符也影響著漢字的語義加工和漢字飽和(吳迪 等,2016)。而義符家族的大小與類別一致性等也對語義激活產生影響(章玉祉,張積家,2017),因此漢字飽和現象是否會受義符類型的影響也值得繼續探究。邵云(2019)發現語義不透明的低頻字較早發生飽和現象。同一個義符(如:艸)也可組成語義透明度不同的漢字(如:語義透明度高的漢字-苗,語義透明度低的漢字-莫)。如果將實驗材料細化到包含同一義符的漢字,那么相比于語義透明度高的漢字,語義透明度低的漢字會不會同樣更容易發生飽和?此外一些義符與身體動作有關(如:扌),研究表明動作動詞可以引起感覺運動區的激活(García et al.,2019),動作動詞的飽和會不會造成感覺運動區激活的減弱?動作動詞的飽和與其他動詞的飽和時間進程上是否有差異?包含動作義符的漢字飽和與包含其他義符漢字的飽和所需要的重復次數上是否有差異?考慮到以上問題,未來可將具身認知與文字飽和相結合進行研究。
5 結語
綜上所述,漢字作為獨特的、典型的文字體系,其飽和現象應當進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在梳理現有漢字飽和現象證據的基礎上,該文發現漢字的飽和現象不僅會發生在字形加工階段、字形-語義聯結階段、語義加工階段,還可能在不同加工階段相繼產生飽和現象。有哪些原因導致漢字飽和現象發生在不同的加工階段?該文從語義加工深度、實驗材料的重復次數和實驗材料類型的角度對影響飽和現象的原因進行了歸納。未來,漢字飽和現象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諸如漢字飽和現象整體的時間進程是如何發展的?漢語為二語者的漢字飽和現象是怎樣的?當前的研究大多以名詞為實驗材料,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以動詞等其他詞匯類型為實驗材料,甚至將漢字飽和與具身認知研究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