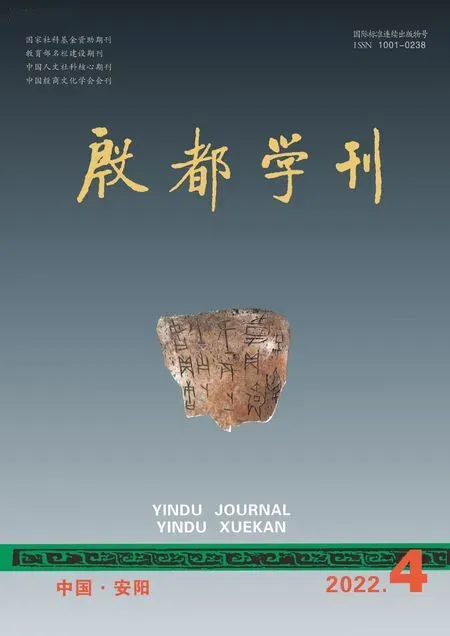中國古代民間借貸研究述評
張慧然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2400)
古代民間借貸是一種以償還為條件的,有息或無息的實物、貨幣的讓渡活動。中國古代民間借貸包括私人間的借貸和私人與民間機構間的借貸。20世紀80年代后,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無息及適當利息的借貸對穩定社會生活秩序,促進小農生產有積極作用。隨著民間文書的陸續整理與出版,依托借貸文書進行的斷代史、區域史、法律史研究也日益活躍,并取得了諸多成果。2000年后,隨著民間借貸的再度興起,一些學者從經濟學交易成本、風險因素等視角切入,試圖對古代民間借貸內在運行的市場機制、高利率的成因等展開分析。
一、對民間借貸的性質與利率的研究
(一)古代民間借貸的性質
學者們最早是從高利貸角度研究民間借貸的。中國古代并沒有“高利貸”一詞。“高利貸”一詞來自英文usury(拉丁文usura)。在歐洲中世紀,不論取息高低,只要是要求得到報償的借貸都被歸入usury。18世紀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usury的含義才轉變為高于法定利率的放款行為。(1)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87頁。清末,高利貸一詞傳入中國,意思是“重利盤剝”。20世紀30年代,恰逢“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的社會性質如何”是史學爭論的熱點,民間借貸的剝削性和破壞性自然就成了研究的重點。部分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高利貸應該是以各種方法、以盤剝重利為目的的金錢借貸,合法的典當業并不是高利貸(2)宓公干:《典當論》,上海書店出版社,1936年,第9頁。。
新中國成立后,“高利貸剝削”論和放貸者“超經濟強制”論成為學界主流觀點。如傅筑夫、謝重光等均討論了高利貸的破壞作用。(3)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第540-546頁;謝重光:《晉唐寺院的商業和借貸業》,《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盡管彭信威提出“應當區別(一般)借貸和高利貸”,但這種觀點和思考并未引起反響。
20世紀80年代起,學者們開始注意到高利貸對維持人們生活、促進生產的積極一面。如漆俠、趙毅等都不同程度地認可了適當利息借貸的積極作用。(4)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45頁;趙毅:《明代豪民私債論綱》,《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二)影響利率的因素
民間借貸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很大程度上受利率高低的影響,因此,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的研究重點從對借貸性質的評判轉移到了對影響借貸利率上。因為能否正確認識高利率形成的內在機制,關系著我們能否將民間借貸利率規范在合理范圍之內。
近年來,經濟學學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林展對滿鐵檔案中的借貸情況進行量化分析,認為供求機制決定利率,違約風險、交易成本、有無不動產抵押等因素則影響利率。(5)林展:《高利貸的邏輯——清代民國民間借貸中的市場機制》,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60-119頁。而在歷史學界,重視對借貸利率影響因素的探究,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提出“一個家庭式農場,并不以資本主義企業行為的邏輯來支配活動”,“一個饑餓的家庭,幾乎可以忍受任何利率”(6)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第191頁。。方行認為清代民間借貸利率總體上有降低的趨勢,主要原因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借貸資本供給增多以及高利貸者之間的競爭。(7)方行:《清代前期農村高利貸資本問題》,《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在正常的、供求平衡的情況下,俞如先認為,法律、鄉族關系、成本等因素的影響更大。(8)俞如先:《清至民國閩西鄉村民間借貸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7-326頁。
二、對民間借貸機構的研究
中國古代民間借貸機構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活躍于唐宋元時期的寺院質庫;第二種是設置于市鎮、縣城的典當行;第三種是廣泛存在于農村的“合會”。
(一)對寺院放貸的研究
寺院放貸自南北朝始。日本學者仁井田陞、堀敏一、北原薰等率先通過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其放貸情況,但最全面系統的研究要屬唐耕耦,他將記錄寺院借貸信息的資料分為三類,第一,借貸契約和請便牒狀;第二,便物歷;第三,諸色入歷和諸色入破歷會計中的利潤部分。(9)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7頁。乜小紅探究了便物歷的起源和性質,認為便物歷最早起源于6世紀初北魏佛寺推行僧祇粟時期,是出便糧者自留的底帳,可以作為追還欠債的依據、寺院審計的根據、佛教僧團檢驗各類倉糧流向的憑證。(10)乜小紅:《中國古代佛寺的借貸與“便物歷”》,《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外,謝和耐、姜伯勤等在研究寺院經濟時,也都對寺院放貸活動有特別關注。(11)參見謝和耐:《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8-197頁;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中華書局,1987年,第325頁。
明代寺院放貸活動得到了抑制(12)何孝榮:《明朝佛教史論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51頁。。清代內蒙古地區的寺院放貸活動十分普遍,其放貸以貨幣借貸為主,借入者還本無望時,用以支付利息的地租或地鋪錢便永遠歸寺廟收取。(13)參見胡日查:《清代內蒙古地區寺院經濟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73-181頁。
(二)對典當業的研究
20世紀初,學者們抱著為傳統典當業和農村融資尋求出路的目的,對當時的典當業進行了研究,代表作有楊肇遇的《中國典當業》(14)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商務印書館,1929年。和宓公干的《典當論》(15)宓公干:《典當論》,上海書店出版社,1936年。。20世紀90年代后,學者們在典當業的起源、分類、當稅的產生等關鍵問題上產生了爭論。關于典當的起源,大部分學者支持宓公干的“南北朝佛寺起源說”;關于典當的分類,楊肇遇按照資本大小將典當業分為“典、當、質、押”。(16)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5頁。而黃鑒暉認為典、當、質是一樣的,只是因區域不同而稱謂不同(17)黃鑒暉:《中國典當業史》,山西經濟出版社,2006年,第75頁。;關于典當的當稅,劉秋根將典當稅的萌芽追溯到宋代,并認為正式的典當稅于明后期已誕生,糾正了楊肇遇典當稅產生于“康熙三年”的說法。(18)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53-263頁。
另,從“典商”角度對典當業進行研究也是一大熱點。王廷元、王世華等對徽州典商的興衰過程、經營規模和方式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19)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論》,《安徽史學》1986年第1期;王世華:《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劉建生則著眼山西典商,對其經營的主要業務、放貸情況、利率等進行了研究。(20)劉建生:《山西典商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2007年。
(三)對合會的研究
對于古代從事放貸活動的民間合會的研究也始于民國年間。王宗培抱著改革傳統合會以使其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對當時的合會現狀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在合會的起源問題上,他否定了“龐公創始說”“竹林七賢遺傳說”“青苗法演變說”“印度傳來說”,推測合會起源于唐宋之間。他將合會總體上分為金融類、儲蓄類、保險類、防衛類及其他,并對合會的各類文書、會金的計算和分配、合會的優缺點、城鄉合會之差別、合會改革的具體方向進行了全面研究。(21)王宗培:《中國之合會》,中國合作學社,1931年。目前學者們對合會的分類以及運行方式的表述都多是沿用他的研究。楊西孟利用合會的會規進行數學計算,進一步分析了會金和利息分配的不公平性。(22)楊西孟:《中國合會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34年。
近年來,學者們大多從清至民國時期的合會文書入手,進行區域性、個案性的研究。如章毅著眼于浙江南部帶有宗教性質的“定光會”,認為其放貸活動具有封閉性、非盈利性的特點。(23)章毅:《祀神與借貸:清代浙南定光會研究——以石倉〈定光古佛壽誕會薄〉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張介人、朱軍對清中后期浙東地區的民間錢會、糾會、田會、錢莊等各類民間金融組織的管理方式、規模大小、營收情況等進行了研究。(24)張介人、朱軍:《清代浙東錢業史料整理和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賓長初等則依托徽州的錢會文書,利用計量史學的方法或經濟學的視角,研究了其特點和作用。(25)賓長初:《清代徽州錢會的計量分析——基于<徽州文書>第二輯所收會書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
總的來說,對于寺院放貸和典當行的研究受到的關注比較早,成果頗豐。對于合會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且集中于清代、民國的情況,對其起源和發展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學界對“合會”的定義并不明確,在行文中對其概念的外延、分類也存在諸多分歧。
三、關于民間借貸文書的研究
借貸文書中關于還款期限、利息高低的約定能折射出借貸雙方地位強弱及某一時期借貸的活躍與否。因此,對古代民間借貸文書的研究,也可讓人們從中體察到古代適當利息借貸的必要性和不當利息借貸的破壞性。
(一)借貸契約(券書)的種類
借貸契約在唐代以前多是“合同文”式的券書,隋唐時期轉變為單契。學界對借貸契約的分類主要有四種:第一,直觀地從借貸契約本身出發進行分類,如玉井是博將敦煌借貸契約分為借錢契、借絹契、借地契、雇駝契(26)[日]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の契》,《支那社會經濟史研究》,巖波書店,1943年。。第二,將契約本身與契約形成的時間過程相結合,如唐耕耦將借貸契約分為原生形態和次生形態,原生形態即第一次借貸所訂立的契約,次生形態即借貸關系成立后,未能按時歸還本息而續訂的契約,(27)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童丕將敦煌地區的契約分為兩大類:主要發生于吐蕃時期(9世紀前半葉)的糧食借貸和10世紀的織物借貸(28)[法]童丕:《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第15頁。。第三,以現在的借貸種類劃分標準去對古代民間借貸進行分類,將不能適應這些標準的特殊借貸形式單列出來,如羅彤華將唐代民間借貸分為信用借貸、質押借貸及特殊形式的借貸,特殊形式的借貸包括賒賣、預租、預雇等(29)羅彤華:《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7-80頁。。第四,服務于研究目的,進行多層次劃分,如楊淑紅認為根據借貸目的,可分為生活消費性借貸和生產經營性借貸;從有無利息方面,可分為有息借貸和無息借貸;從借貸的保證方式來看,有信用借貸和質押借貸。她認為第一類劃分有利于經濟史研究中分析借貸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和說明借貸主體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后兩類劃分有利于從契約關系角度分析借貸利率、債務履行、權利義務等問題。(30)楊淑紅:《元代民間契約關系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5頁。
(二)借貸契約(券書)的形制與發展
漢簡中,借貸券書在形制和內容上都有所殘缺。傳世文獻記載此時借貸券書一式兩份。居延漢簡中有很多貰賣券書其形制也是一式兩份,記錄債務關系成立的時間、雙方姓名和身份、債的標的物及價格、清償期限、旁人(即見證人)的姓名身份。(31)李均明:《居延漢簡債務文書述略》,《文物》1986年第11期。借貸券書可能也與此類似。
隋唐時,“合同文”式的券書轉變成了單契,但形式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如,與“合同文”式相匹配的署名習慣經過了漫長的過程才逐漸消亡。(32)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內容方面,此時借貸契約的基本格式已經形成,即立契時間、某地某人因何原因向某地某人舉貸錢物若干、利率、還債期限,違約處罰,擔保典押,契尾署名畫押等事項。
宋元時,目前發現的主要有西夏文書、蒙元時期回鶻文文書、元代契約文書。史金波認為西夏借貸契約大多是西夏文草體,也有部分行書或行楷,其內容和格式也相對于唐代借貸契約有一些變化。(33)史金波:《西夏糧食借貸契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86-204頁。回鶻文文書則反映了宋元時代新疆畏兀兒地區的社會生活。楊富學對比了其與唐代漢文契約的不同之處。(34)楊富學:《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借貸文書概述》,《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許偉偉將元代借貸契約與西夏黑水城文書進行了對比。(35)許偉偉:《黑城夏元時期契約文書的若干問題———以谷物借貸文書為中心》,《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明清借貸契約的形式較為穩定和統一,乜小紅指出明清借貸契約比中古時期的簡單了許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各種情況在明清的律令及條例中都有界定,無需私契多言”(36)乜小紅:《中國古代契約發展簡史》,中華書局,2017年,第78頁。。
總之,囿于史料,對借貸文書形制的研究呈現出朝代和地區的不平衡性,秦漢、宋元時期的中原腹地以及明代的成果較少。對于清代借貸文書的情況,學者們多以區域研究為主,還缺乏宏觀層面和區域對比方面的研究。另外,學者們仍然主要是以王朝斷代去劃分研究的時代范圍,這使得借貸契約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更難以被把握。
四、依托民間借貸文書進行的斷代史、法律史研究
(一)斷代史研究
學者們利用文書提供的正史中未記錄的信息,對歷代民間借貸的情況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對以往學術界的一些觀點進行了糾正。
秦暉研究了漢代西北居延地區的借貸情況。(37)秦暉:《漢代的古典借貸關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3期。石洋考察了借貸期限、收息周期與借貸目的之間的關系。并指出以往學界認為漢武帝時期的一般年利率是20%的結論存在錯誤。(38)石洋:《秦漢時期借貸的期限與收息周期》,《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對唐代的民間借貸,學界基本上達成了這些共識:一年一季的耕作規律導致敦煌吐魯番的糧食借貸多為“春借秋還”,利率一般為50%。西州舉錢生息已經形成了鄉利,可能是月利率10%,各類借貸都有極高的100%的利率。文書中有很多不寫利息的,但并不代表都是無息借貸。保人往往是借入方的親屬,也有僧人充當保人的情況。(39)參見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羅彤華:《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等。另外,不少學者還貢獻了極有價值的觀點和研究方法,如韓森將放高利貸者左憧熹墓中隨葬的15件契約進行了系統研究,這種以人為中心對文書進行研究的方法突破了之前按時代、按種類對文書進行研究的范式,形象生動地展現了高利貸者通過放貸兼并土地的過程。(40)[美]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7頁。余欣提出,異乎尋常的高利率不能以“特例”或“民間借貸往往有很大的隨意性”等理由來敷衍,而是要考慮其深層的社會因素。(41)余欣:《唐代民間信用借貸之利率問題——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契券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
西夏民間借貸“按日計息”十分常見。(42)杜建錄:《黑水城出土的幾件西夏社會文書考釋》,姜錫東、李華瑞編:《宋史研究論叢(第九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37-644頁。貸糧利率一般總利率是50%,月利率是20%,日利率是1%左右。(43)史金波:《西夏經濟文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84-199頁。郝振宇還發現谷物典當借貸利率和賠付方式根據放貸者身份不同而不同。(44)郝振宇:《西夏民間谷物典當借貸的利率、期限與違約賠付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3期。
清代借貸文書數量龐大,所以學者們充分考慮各區域的生產結構、人群構成、經濟發展水平等特點,從區域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其中臺灣地區的“胎借”、旗人群體的借貸等民間借貸情況,都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45)周力農:《清代臺灣的“胎借銀”》,《清史論叢(第六輯)》,中華書局,1985年;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50頁。
(二)法律史研究
法律史學者主要通過借貸文書來探討擔保、借貸規制、契約秩序等問題。
在擔保制度方面,仁井田陞認為“質”就是債權的擔保方式,并推測“擔保制度在先秦時已經出現”(46)[日]仁井田陞:《漢魏六朝的債權擔保》,見《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由此,中國古代“以物為質”擔保制度的出現,被提前到了戰國時期的秦律。
在借貸規制方面,霍存福認為國家承認“私契”的地位,但在實踐中,契約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保人代償等問題與法律又有明顯沖突。(47)霍存福:《論中國古代契約與國家法的關系———以唐代法律與借貸契約的關系為中心》,《當代法學》2005年第1期。明清時期,國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債,契約中的抵赦條款也隨即消失”。(48)霍存福:《敦煌吐魯番借貸契約的抵赦條款與國家對民間債負的赦免———唐宋時期民間高利貸與國家控制的博弈》,《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在契約秩序方面,馮海洋認為在中國古代熟人社會中,中人對契約的簽訂和履行起到了促進作用。(49)馮海洋:《倫理道德在清代借貸契約中的約束力》,《法律史評論》2015年第8卷。于光建認為在西夏國的典當借貸中,中間人可以在借貸完成后抽利,同時擔負著價格調節、明細借貸典當來源是否合法、中介代理等職責。(50)于光建:《西夏典當借貸中的中間人職責述論》,《寧夏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五、民間借貸研究的展望
除了在前文所述的以往學界的研究熱點和尚未解決的課題上繼續深耕外,學者們也意識到應該更多地從古代民間借貸中挖掘其對于現實的借鑒意義和教訓。已有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如陳志武、彭凱翔、袁為鵬、林展等對清代刑科題本中因民間借貸導致的命案進行了量化研究,發現貸方的死亡比例高于借方。(51)陳志武、林展、彭凱翔:《民間借貸中的暴力沖突:清代債務命案研究》,《經濟研究》2014年第9期。他們還認為書面契約盡可能地減少了民間借貸利息、還款期限等關鍵要素的模糊性,是減少交易糾紛、暴力沖突的重要方式。(52)陳志武、彭凱翔、袁為鵬:《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債務命案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桑本謙考察了歷史上的高利貸后,認為以利率管制為核心的打壓高利貸的各種舉措往往因市場反彈而屢屢受挫,因此“洞察法律背后的市場邏輯對于優化法律決策至關重要,不僅可以減少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和失誤,還可以為提升立法質量提供建設性的參考”(53)桑本謙:《民間借貸的風險控制——一個制度變遷的視角》,《中外法學》2021年第6期。。不過,我們要避免為附和“現實主張”而影響了對歷史真實的判斷。
另外,對民間借貸文書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傳統研究范式的更新。以往學者們往往選定某一朝代或某一區域,敘述其借貸種類、放貸者身份、利率情況等,然后評價其社會影響。但隨著契約文書的不斷整理,學者們發現普通自耕農、佃農也會放貸,而且放貸者也會成為借貸者,所以學者們逐漸放棄了借貸雙方二元對立的研究模式。
綜上所述,史學界依托出土文書、傳世文獻、檔案資料對中國民間借貸問題的研究成果頗豐,且大致經歷了一個從民事習慣調查,到受“高利貸剝削論”的影響急于對中國古代民間借貸進行定性,到重新回歸對傳統民間借貸的內涵、種類、文書特點等全方面的梳理,再到承擔起“以今觀古,由古知今”的時代命題的過程。以往學者們生動地為我們展現了借貸對普通人巨大的影響,未來學者們必將在中國古代民間借貸的研究上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