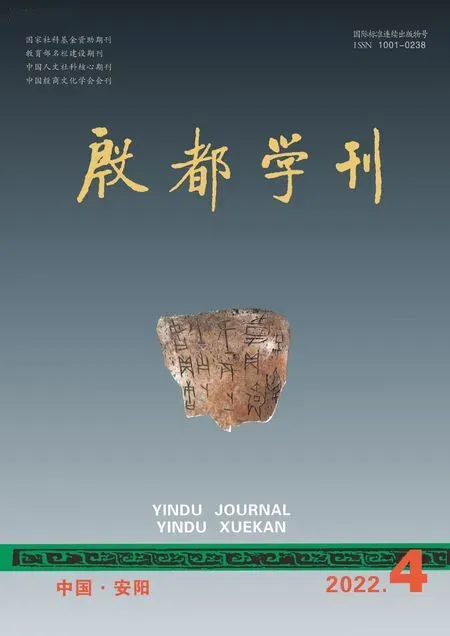甲骨卜辭檔案說再辨析
王小茹,趙俊杰
(安陽師范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甲骨卜辭是否為檔案,已爭論許久。最近,禹劍先生重新梳理甲骨卜辭相關材料,兼顧了甲骨“檔案說”和“非檔案說”兩種觀點,認為甲骨卜辭的性質分為兩個階段,在商代使用時應為檔案,稱為“甲骨檔案期”,而使用后埋藏,稱為“甲骨埋藏期”(1)禹劍:《論殷墟甲骨卜辭的性質——兼論殷墟甲骨占卜之后的“甲骨檔案期”和“甲骨埋藏期”》,《檔案管理》2018年第6期。。這一觀點認識到了甲骨卜辭在不同的時期擁有不同的性質,將其分為“檔案期”和“埋藏期”,有一定新意。仔細分析發現,此觀點將甲骨卜辭的“檔案期”和“埋藏期”前后混淆了。本文就這一問題進行論證,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甲骨卜辭“檔案說”的爭論
甲骨卜辭“檔案說”認為殷墟發現帶字的甲骨是檔案。最早由陳夢家先生在1950年撰寫《殷虛卜辭綜述》中提出,稱為“王家檔案說”。1980年,董儉先生正式提出“甲骨檔案”說,并詳細解釋了“甲骨檔案”的概念。后來,這一概念被檔案界廣泛使用,并將“甲骨檔案”寫進檔案學教材。但是,詳細討論這一概念的論著并不多見。1999年,考古界張國碩先生在《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一文中提出甲骨“非檔案說”(2)張國碩:《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檔案學研究》1999年第5期。。隨后,倪道善和張翠華兩位先生分別在(《〈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質疑》《〈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質疑——兼與張國碩老師商榷》(3)倪道善:《〈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質疑》,《檔案學研究》2000年第2期;張翠華:《〈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質疑——兼與張國碩老師商榷》,《檔案學研究》2000年第2期。論證“甲骨檔案說”。任漢中先生在《早該走出的誤區——析殷墟卜辭是“殷代的王家檔案”論》一文中,也認為殷墟甲骨卜辭不是檔案(4)任漢中:《早該走出的誤區——析殷墟卜辭是“殷代的王家檔案”論》,《檔案學研究》2000年第2期。。張國碩先生再次著文《再論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論證甲骨并非檔案(5)張國碩:《再論甲骨文在商代非檔案說》,《檔案學研究》2000年第3期。。劉一曼先生從甲骨埋藏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殷墟遺址出土甲骨的埋藏情況,否定了甲骨檔案說(6)劉一曼:《論殷墟甲骨的埋藏狀況及相關問題》,《三代考古(一)》,科學出版社,2004年。,很具說服力。焦凡力和桑毓域合作撰寫了《殷商甲骨卜辭檔案性質淺析——兼與任漢中先生商榷》(7)焦凡力、桑毓域:《殷商甲骨卜辭檔案性質淺析》,《檔案學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再次肯定甲骨應是檔案。至此,考古界認為甲骨并非檔案,檔案界形成“甲骨檔案說”和“甲骨非檔案說”兩種不同的觀點。最近,禹劍先生辯證的認識這一問題,提出“甲骨檔案期”和“甲骨埋藏期”值得我們思考。想要正確理解甲骨卜辭的檔案價值,需要重新辨析。
二、商代并非“甲骨檔案期”
甲骨在商代并無檔案功能,可分為“甲骨使用期”和“甲骨埋藏期”兩個階段。甲骨卜辭是否為檔案需要從檔案最基本的定義分析。檔案一般是指社會組織和個人從事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價值的、歸檔集中保存起來的文件材料(8)①國家標準局1985年發布的《檔案著錄規則》、國家檔案局教育處1987年編寫的《檔案管理學概要》等論著;②1980年陳兆主編的《檔案管理學》、1985年李培清編著的《檔案學概論》等論著。。一般將這一定義拆解為五個方面。第一,檔案是社會活動的記錄,是第一手原始材料;第二,檔案具有憑證和參考作用。第三,檔案是人們有意長期保存的可供查閱的材料;第四,檔案是經過整理、分類甚至立卷、編目,才能最后成為檔案;第五,檔案應集中保存在專門的檔案機構(檔案館、室)或其它特定場所。有關第一和第二方面幾乎沒有爭論,毫無疑問,甲骨卜辭是一種記錄商代社會或活動的原始材料,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第四和第五方面不是必要因素,在此不做討論。
第三個方面爭論較大,而甲骨卜辭并不是有意長期保存供人查閱的檔案。
首先,甲骨卜辭在商代是十分稀有的,這一屬性決定了其僅被少數人使用。商代重視祭祀,卜骨卜甲在很多重要遺址有所發現,但是卜辭僅發現于鄭州商城、殷墟、大辛莊3處遺址。早于殷墟的鄭州商城,截止到目前僅有四塊有字卜骨(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鄭州二里岡》,科學出版社,1959年;楊育彬:《華夏文明的豐碑》,《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一百周年論文集》,齊魯書社,2000年,第242頁。。三片卜骨上僅寫一或兩字,僅有一塊卜骨字數較多,共約11字(10)李維明:《鄭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辭新識》,《中國文物報》2003年6月13日。,但因出土時因層位關系不明,部分學者懷疑其時代為殷墟時期,多數學者認為是鄭州二里崗時期的習刻甲骨。鄭州商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自發現以來其都城性質從未被懷疑,只是存在仲丁隞都和商湯亳都之爭,近年來隞都說堅持者逐漸減少,亳都基本被認同。商代存在主輔都制度,商代前期鄭州商城作為主都一直沒有變遷,仲丁時期同樣如此。如此重要的都城遺址僅見習刻甲骨,而同時期的小雙橋遺址僅見到朱書文字并無卜辭,可見甲骨卜辭的使用范圍是非常有限的。
殷墟之外的大辛莊遺址僅發現7片刻辭卜甲,其中四片綴合為1片,另外3片僅有三個字和一個兆序“二”字。從出土層位和共存遺物判斷,卜辭年代為殷墟二、三期之間。再從甲骨修整、鉆鑿形態、字形和文法分析,大辛莊卜辭都應與安陽殷墟卜辭屬于同一系統(11)方輝:《濟南市大辛莊遺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只是在行款和一些字的寫法上存在著自身特點,也應為習刻卜辭(12)孫亞冰、宋鎮豪:《濟南市大辛莊遺址新出甲骨卜辭探析》,《考古》2004年第2期。。大辛莊遺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被認為是商文化東擴的重要據點,是商代東方的一處中心性聚落,或者是一處重要的方國都城。大辛莊是殷墟之外,唯一發現刻辭甲骨的遺址。但甲骨的數量稀少、刻辭為習刻等特點說明,刻辭甲骨十分稀缺。
在殷墟遺址內,刻辭甲骨的發現地點也十分局限,絕大部分發現于宮殿區內,包括小屯北、小屯村中、小屯村南、花園莊東地、花園莊南地等諸多地點。宮殿區外僅6處遺址有少量發現,分別為四盤磨、薛家莊南地、候家莊南地、苗圃北地、后崗、大司空。據統計,宮殿區外僅出土刻辭卜甲12片、刻辭卜骨8片共20片,且絕大多數字數很少且被認為是習刻(13)劉一曼:《安陽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97年第5期。。僅大司空村的一片字骨有“辛貞在衣”四字,發掘者認為從文辭上看,也很像是習刻卜辭。小屯北、小屯村中、小屯村南、花園莊東地、花園莊南地等諸多地點均屬于宮殿區內,在這個區域內發現大量大型建筑基址,部分基址具備朝、宗廟、社的性質,屬于王室成員活動場所。該區域內出土大量刻辭甲骨并不稀奇,只能說明王室成員和少量為王室占卜活動服務的人員才能接觸刻辭甲骨。
其次,甲骨卜辭并非可以查閱。
第一,絕大多數甲骨卜辭在宮殿區內散亂分布且毫無規律可循。自1899年至1928年,小規模的甲骨盜掘持續不斷,大規模私人挖掘也有9次以上。據董作賓先生記述,挖掘地點涉及洹河岸邊、小屯村大路旁、小屯村內等廣大的區域,幾乎涉及整個宮殿區。自羅振玉先生大舉搜求之后,數年之間出土者萬。胡厚宣先生認為“明義士所藏甲骨在1917年出版《殷墟卜辭》一書時,就說已有5萬多片”。后來還有人調查后認為“農田之內,到處多有。”截止到目前,殷墟甲骨卜辭共有約15萬片,有統計稱約有8萬多片出自1928年以前。
1928-1937年出土約3萬多片(包括H127的1.7萬余片),大多數散亂分布在整個宮殿區。1928年第一次發掘在洹河的沿岸,收獲帶字甲骨784片。第二次發掘,在小屯村中部、南部、北部,出土帶字甲骨684塊。第三次發掘分兩階段,發掘地點在村北高地和村西北的霸臺,出土帶字甲骨的有42坑,共計出土帶字甲骨3114片。在第三次發掘的同時河南博物館在小屯村獲得有字甲骨3656片。第四次發掘地點在小屯村北,出土字甲751塊、字骨31塊及鹿頭刻辭1件。第五次發掘在小屯村北和村中,出土甲骨卜辭481片。第六、七、八、九次發掘地點在村北,發現字甲719塊、字骨10塊、大龜板7版。前九次發掘共計4412片、字骨1980片,共計6000余片,小屯村周圍和洹北沿岸均有發現,這種散亂分布的狀態說明甲骨卜辭并不是有意保存的。第十至十二次發掘,轉移至西北崗發掘王陵,未出土甲骨。第十三次發掘在小屯村北發現H127,出土17096片,其他零散甲骨708片。第十四次發掘,在兩坑內發現帶字卜甲2片。第十五次在小屯村北發掘24坑,出土帶字甲骨601片(14)魏慈德:《殷墟YH127坑甲骨卜辭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7-34頁。。可以看出,甲骨卜辭幾乎遍布整個宮殿區(圖一),且這些甲骨絕大多數十分破碎且毫無規律的零散分布,充分說明并非有意保存的。

圖一 殷墟宮殿區內甲骨坑分布圖
第二,部分集中埋藏的甲骨也并非可查閱的檔案。甲骨檔案說舉例最多的莫過于小屯YH127、花園莊東H3等。H127坑填土可分三層,上層灰土厚0.5米,中層厚1.6米,下層綠灰土2.7米。所有甲骨均在中層,共17096片,少有其他遺物,僅有一架人骨夾雜其中。中層甲骨層呈北高南低,疑似從北側將甲骨傾倒入坑中,甲骨散亂毫無規律。從發掘記錄看,所謂的分層只是人為的劃分,并不是存儲時有意的分層。甲骨可分8層,室外清理兩層后,打木箱搬運至室內清理。各層出土甲骨卜辭的內容散亂而無規律,顯然無法讓人查閱。H127共深4.8米,最底層2.7米均填綠土,為生活垃圾,將甲骨隨意放置在垃圾坑內應無法查閱。
此前的討論多忽視了一個問題,H127中出土的甲骨絕大多數并不完整。17096片甲骨卜辭中僅有8片卜骨且殘缺不全。卜甲17088片,完整的僅為三百片。我們知道該坑因戰亂輾轉到南京和重慶,它的室內清理也分為南京和重慶兩個階段。清理后部分甲骨可以綴合,但整體而言該坑套箱提取甲骨大部分并未丟失,說明埋藏時的甲骨已經殘缺不全。顯然,不完整的甲骨是無法作為檔案讓人查閱的。發現的人骨卷身側肢,大部分被甲骨掩埋,像是商代普遍流行的一種祭祀行為。用于祭祀者多為奴隸或戰俘,應不會是檔案的管理者。
花園莊東地H3坑內的甲骨卜辭可能是有意埋藏,但并不具備檔案的查閱功能。坑壁規整并有三個腳窩,整個坑深約2.2-2.5米,甲骨層厚0.8米。坑內填土分4層,第三層和第四層發現甲骨,甲骨層的上層即第二層為堅硬的夯土。劉一曼先生發現甲骨的存放有一定規律,不少距離相近的甲骨卜辭內容有一定關聯(15)劉一曼:《花東H3坑甲骨埋藏狀況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2017年第3期。。但是,這些僅占少數,大部分距離相近的甲骨并無關聯,說明并無查閱價值。從甲骨的擺放看,應是有意細心放置在坑內的,在掩埋過程中有一定的方式與程序。埋藏之后,在甲骨之上將土夯實,這樣的做法通常出現在墓葬之中。最大的可能性,是因為甲骨卜辭的神圣性,需要將其埋入地下并夯實。花園莊東地H3出土甲骨共1583片,刻辭者579片,僅占三分之一,多數并無刻辭。大多數甲骨并不完整,完整的卜甲755版,刻辭整甲不足300版,不足半數。甲骨總數的80%為半塊或大板塊,很多刻辭在埋藏前就已殘缺不全且同時埋藏了很多無字甲骨,顯然不是為了讓人查閱。
三、考古發掘之后為“甲骨檔案期”
在商代,甲骨卜辭并不是檔案,商代只有甲骨卜辭的“使用期”和“埋藏期”。甲骨卜辭發現之后,才激發了它的檔案價值,可稱之為“檔案期”。我們知道甲骨卜辭記錄全面,商王世系、軍事、農業、災害等諸多信息,已經成為研究商代歷史必不可少、最為可靠的材料。從檔案定義可知,檔案的第一個屬性即社會活動的記錄,是第一手原始材料。甲骨卜辭無疑是商代歷史最原始的記錄,且多數卜辭為商王卜辭,記錄了很多與王室有關的活動,是研究商代上層社會最重要的檔案。檔案的第二個屬性即具有憑證和參考作用。毫無疑問,甲骨卜辭具有很高的查詢和參考價值,自王國維先生列出商王世系之后,甲骨卜辭的內容成為研究商代歷史必備的參考史料。
近年來,黨和國家對甲骨卜辭的研究尤為重視。甲骨卜辭的研究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一是人員缺乏。據統計,專門從事甲骨卜辭研究的人員,全國不足50人。需要加大人才培養力度,讓更多的青年才俊從事甲骨卜辭研究,讓冷門絕學研究后繼有人。二是甲骨卜辭分散。受戰爭和盜掘的影響,很多被西方列強掠走散布國外,國內的館藏也是零散分布。國內民間還存在很多甲骨,需要進行收集,并進行鑒偽與整理。三是甲骨卜辭著錄零散,難以全面掌握。《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補編》收入的甲骨最多,總數可達,共13450片。還有諸多著錄資料,各種著錄之間存在重復,尚無一套著錄能夠集齊所有甲骨卜辭,需要大量人員進行資料整理工作。四是甲骨卜辭數字化進展緩慢。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應用于甲骨卜辭研究尤為重要。但是,目前僅有少數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展大數據建設,且工作任務重、專業性強,進展緩慢。今后,我們需要加大人員投入,一是加強甲骨研究人員的培養;二是加快原始卜辭材料的再搜集再整理;三是對一些甲骨文字進行基礎性辨識;四是加大甲骨材料數字化整合力度;五是加深甲骨卜辭內容的挖掘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