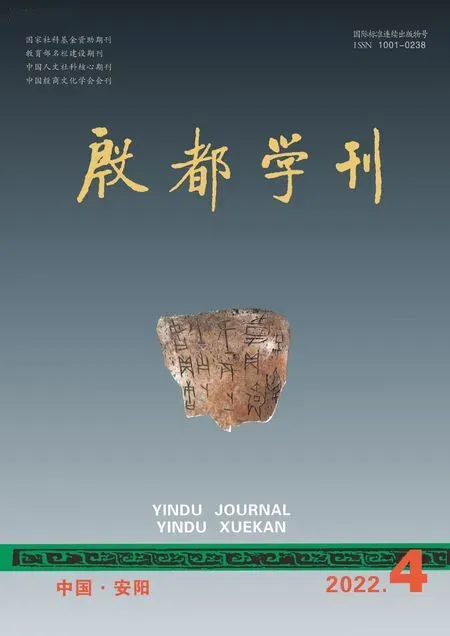守正創新,金針度人
——訪著名清史學家李治亭研究員
朱昌榮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為系統梳理新中國清史研究的發展脈絡,總結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繼承老一輩史學工作者求真務實、學以致用優良學風,《清史名家面對面》課題組在全國范圍內遴選20位左右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著名清史學者進行專訪。現推出著名清史學家李治亭先生訪談,以饗讀者。(1)李治亭,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有影響的清史學者之一,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山東莒南縣人,1942年出生。1965年畢業于遼寧大學歷史系,先后在東北文史研究所、吉林省委組織部、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吉林省史學會副會長、省社科聯委員,河北師大、吉林師大、河北大學兼職教授。退休后,入選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清史及東北史研究,出版著作近40部,發表論文300余篇。專著《吳三桂大傳》《清史》,論文《清朝遜國九十年祭》《關東文化論》《清代大一統與邊疆問題》《評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等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
一、如何走上學術研究的路子
李先生好,感謝您接受專訪。我的大學老師說,學習清史,必須清楚國內研究清史的主要機構和代表人物。他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原歷史研究所)以楊向奎先生、王戎笙先生、何齡修先生、陳祖武先生、高翔先生為代表的團隊,中國人民大學以戴逸先生、李文海先生、王思治先生領導的團隊,中央民族大學以王鐘翰先生為首的團隊,南開大學以鄭天挺先生為首的團隊。再有一支隊伍就是李洵先生、孫文良先生、李治亭先生為主力的東北地區學者。如今,上述諸位先生或已作古,或已老疾,難以再從事學術研究。您年屆80,仍耳聰目明,精力充沛。
李先生,您從事清史研究近60年,出版著作近40部,論文300余篇,在學術界有重要影響力。請扼要談談您的學術經歷,包括家庭影響、個人興趣和教師影響。
遴選學者進行訪談的創意非常好。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搶救性保存和發掘歷史文化遺產。學術需要傳承,老一輩史學工作者把求學、治學的經歷告訴學術界尤其是青年朋友們,把好的學術傳統傳下去有重要意義。
我是在父親影響下走向史學研究道路的。父親喜歡講古,擅長用樸素生動的語言講《水滸傳》《三國演義》《楊家將》等。潛移默化中,我對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初中結束,我越發熱愛歷史。高中期間,我有幸接觸到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同志的著作,我反復研讀《郭沫若文集》,受到了很多啟發。此后,我堅定了學習歷史的決心。高中文理分科,我報了文科,主要是想學習歷史。畢業后,我如愿考取遼寧大學歷史系,開始接受正式的史學訓練。
感謝父親,是他無意識地將我領入歷史領域。我更要感謝孫文良老師,是先生有意識地領我進入清史領域。先生給我留下極深刻印象。講課不看講義,滔滔不絕;板書豎著寫,寫粉筆字像寫毛筆字。理論水平高,諳熟馬克思主義語錄。文史素養好,能背史料、背詩,能以詩證史。
學術自模仿始,學無所向、學無所宗,就找不到中心,抓不住特色。孫老師把我吸引住了,我就模仿他。我的鋼筆字就是跟著孫老師學的。我喜歡文學,時常看《古文觀止》、唐詩等,搞研究喜歡以詩證史,這些都是老師的影響。
1965年大學畢業后,我進入原東北文史研究所工作。“文革”爆發,東北文史研究所撤銷,我先是上了“五七干校”,后來分配到吉林省委組織部工作。當時我是一個連隊的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又是校革委會委員,從發展的前景看還不錯。但我越干越沒興趣,還是喜歡歷史。1972年吉林省成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出于個人興趣,再加上老領導佟冬同志的提攜,我如愿回到了研究崗位。1976年,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改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我被任命為歷史研究所副所長,1985年任所長,1997年退居二線。2002年退休后,我被推選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歷任傳記組副組長、篇目組特聘專家,一直工作到現在。
在我的經歷中,有兩個“大躍進”:一是政治上的,入黨沒有預備期,一步到位;一是學術上的,從助理研究員一步到位,破格升為研究員。這兩個“大躍進”不是靠關系,而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二、研究了什么,取得怎樣的成績
1.您長期致力清史研究,對民族史、軍事史、文化史、地方史等均廣泛涉獵,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史學月刊》等報刊和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300余篇,不少成果被《新華文摘》轉載。請圍繞上述研究領域,列舉比較滿意的研究成果,主要觀點是什么?
我對自己的成果大都滿意。論文方面,首推《清朝遜國90年祭》。我認為,與歷史上其他王朝相比,清朝有三大特點:第一,清朝是中國歷代創業史上的奇跡。一方面是時間之長,沒有一個朝代超過它。漢高祖劉邦創業用了五年時間,唐太宗李世民用了七、八年時間,宋太祖趙匡胤兵變只用了幾天,明太祖朱元璋創業也就用了十多年時間。而清朝從努爾哈赤1583年起兵,到1644年,花費了六十余年。時間之長,歷代不及。正因此,清在入關前,主要的政權組織就已經基本完備,比如八旗制度、治國理念等。第二,清朝盛世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歷代出現的盛世不少,但如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明永宣之治持續時間都不長。而清朝康雍乾三帝統治時期,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持續時間最長,內容豐富,規模宏偉,氣勢磅礴,涉及的問題多,解決的問題也多,對中國歷史影響非常大。第三,清代遜國是特例。清亡國不是通過戰爭攻伐才下臺的,而是投降。清朝統治者認識到歷史潮流不可違,以和平的方式主動交出政權。這種主動是特例。
第二篇是《關東文化論》。學界關于東北文化有許多說法,如遼河文化、遼沈文化、盛京文化、長白文化、龍江文化等,名稱比較雜亂。我認為東北區域文化可以統稱為關東文化,關東文化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共同體。關東的“關”指山海關, “關東”的本意是山海關以東的地方, 包括今遼寧、吉林、黑龍江。總之,我對關東文化的內涵、特色和價值等內容都做了界定。
第三篇是《康熙處理三藩問題辨》。康熙對三藩問題的解決并不妥當,康熙撤藩實際上有五種方法可選,康熙帝選了下策。例如,可以緩撤,現在先不撤,等吳三桂等老一輩去世,新一代藩王上任再撤。也可以分期撤,尚可喜主動提出撤藩,朝廷就先撤尚可喜,其余藩王分期撤。吳三桂等藩王固然背地里擴張自己的勢力,但也是朝廷論功行賞撥給的領地,朝廷突然撤藩,違背了此前對他們的承諾。
專著方面,我比較滿意《吳三桂大傳》《清史》。以《吳三桂大傳》為例:1990年以來,包括香港共六家出版社先后再版。我試圖真實再現吳三桂的人生,不給他扣政治帽子,也不加桂冠,而是堅持秉筆直書,不論好壞,都寫清楚,是非對錯,交給讀者評價。我應邀給吳三桂的墓寫碑文,也是寫實。上聯是:“敢為天下難為之事,獨創歷史”。意思是,他敢做天下人不敢做的事,好事、壞事都敢做,其中可能是光彩的,也可能是陰暗的,但都是歷史。下聯是:“不計身后成敗榮辱,任人評說”。意思是,他不考慮后人怎么評價他。我反復在多個場合強調要把吳三桂當成有血有肉,有思想,有實踐的人,不能簡單地以好人壞人、英雄叛徒評價他。學術界喜歡使勁吹英雄、使勁罵叛徒,這都不是研究歷史的科學態度。歷史事實永遠不變,但人的觀念和時代在變,過去否定的反面人物,或許今天就變成正面人物,再到明天又不一定站得住了。
2.人物評價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點和難點。明清易代之際人物評價,又打上不同民族政權更迭烙印,增加了道德和民族的考量,如何評價,更是難上加難。您對吳三桂、尚可喜等政治家進行過很多研究,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成果。就您來看,人物評價的關鍵在哪?怎么才能做好人物評價?
人物是歷史研究的永恒主題!研究歷史不能沒有人物及實踐活動,歷史總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各領域活動,但無論研究什么,都離不開人物。沒有永恒不變的原理,人物評價的標準從來都是順應時代的變化而確立,都要有利于服務國家治理和政權建設。但歷史人物的實踐活動是已經發生的、不可再變的,這是我們衡量、考察的基本根據。分析歷史人物,要特別看其實踐活動是有利于當時還是有利于將來?產生了什么影響?是順應歷史發展方向,還是逆著時代方向?比如明清交替之際,統一是大方向。無論是李自成、張獻忠統一,南明統一,還是清朝統一,都是合理的。在中國境內,為統一而做的努力,我們就該肯定;逆著潮流走,搞破壞的、不贊同統一的,就應該否定。
對易代之際降清人物的評價是大問題。一些學者秉持老觀念,用漢奸、叛徒、賣國賊這些貶義詞定性降清人物。這不對,這種標簽式評判,割裂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一國之內政權的更迭,歷史人物選擇從一個政權投到另一個政權是正常現象,他們擁有自己政治選擇的權力。漢奸、叛徒、賣國賊是針對向外國投降的人來說的,比如汪精衛就是典型的賣國賊。我們要看歷史人物的實踐活動是否有利于國家統一,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
歷史人物評價,應堅持三條基本原則:第一,不要站在一個王朝的立場,去反對和否定另一個王朝。應該站在客觀立場,以歷史發展的方向,勝利的發展方向作為判斷的依據。第二,不要站在一個民族的立場,去反對和否定另一個民族。應該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數民族也有權統一天下并實施國家治理。我決不贊同滿洲征服中國、征服漢族的論調,這是西方的觀點,也是部分中國學者的認識。征服是指一國對另一國的征服,是軍事暴力,不能在一國之內隨便使用,只能用統一、分裂、割據來界定。第三,不要站在道德立場,以道德為標準。應該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界定。有學者按照道德標準譴責那些投降清朝的人物,認為他們不忠于明朝。但明朝已經滅亡了,再讓他忠于明朝有什么意義。我們要用人物的實踐行動及發生的作用評判其功過是非,而不是道德品質。乾隆出于服務現實政治的需要,強調忠君,將尚可喜等對清朝統一有大功的人都定為“貳臣”,這就是貼道德標簽。我肯定尚可喜,是因為他忠于清朝,更忠于國家大一統。
寫好人物傳記,要注意處理好三種關系。一是要處理好人和時代的關系。二是要重視人和生活環境的關系,研究人物在什么樣的環境長大。三是要注意處理好個性與共性的關系。人物千差萬別,研究人物不突出個性,就算不得成功。我在研究中努力保持這一點。比如,我研究吳三桂,就特別注意他的個性,甚至他的舉手投足。我注意到他說話時有個小動作,時常把鼻子抹一下,掩蓋鼻子上的疤痕,小動作能反映他的心理狀態。
3.您強調治史可以分為“發現歷史”“解釋歷史”和“應用歷史”三個層次。請問就“好”的角度講,怎樣才能發現“好”歷史,解釋“好”歷史,運用“好”歷史?
90年代,我曾專門撰文談研究歷史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發現歷史。就是通過歷史記載,弄清楚歷史的來龍去脈。這是基礎,是前提。第二個層次是解釋歷史。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發現歷史之后,如何解釋是大問題。第一種是沒有解釋,即重復書寫,把歷史記載匯總起來,再用自己的敘述方式重寫一遍,這樣做研究沒有大意義,充其量給別人提供基礎知識罷了。第二種是進行淺層次解釋,即解釋歷史的表面現象。第三種是深層次的解釋,即本質性解釋。比如我在《康熙緣何廢長城》一文中指出,秦始皇修長城,把中國的界限具體化了。長城以內為中國,長城以外是附庸,長城是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分界線,用于區別內外。康熙帝廢長城,使得內外一體,中外一家,意義重大,但是學界少有人認識。所以,要解讀史料,解讀后要看到本質。再如學界不少人對“大一統”內涵的揭示明顯是荒唐的。實際上,“大一統”和體制、國土大小、民族都沒有必然關系,主要就是強調統一。第三個層次是應用歷史。有學者否定經世致用這個觀點,認為不能以史為鏡,這是不對的。中國傳統史學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經世致用,“夫學不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以史為鏡并不是拿歷史上的事和現在簡單類比,而是要從歷史中總結認識與智慧,并轉化為實際行動。學歷史就是要總結經驗,總結認識,用以指導實踐。
三、學術個性
1.在當下的學術界,存在著一些老好人類型的學者。突出的表現在關鍵命題繞開走,重大問題避開談,學術態度模棱兩可。在我看來,您是一位在立場上很徹底的學者,我很敬佩。請問您怎么看這一現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辦?
一些學者對史學的本質缺乏清楚認識。史學的本質是辨是非、明真理,歷史科學就是要闡揚真理,批評邪惡。搞學術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不是為了發表而發表,而是要解決問題。遇到問題、矛盾、是非繞著走,是不行的,也是不可取的。現在學界存在不辨是非的現象,對錯都沒人問,也不敢爭論。
我寫過幾篇商榷性質的文章,點名道姓進行學術批評。比如《南明史辨》。雖然我跟作者是好朋友,但他認為康乾盛世原本不存在,只是幾個學者捧出來的。這種認識不對,我就要批評。再如,講壇類節目大行其道的時候,我寫了《透視“講壇現象”》,強調這類節目糟蹋歷史、戲說歷史,開了惡劣的先河。我在上海做報告,批評有人專門講一些討老百姓喜歡的史學,老百姓喜歡聽什么就講什么,后來就有報道說“李治亭炮轟某某某”。我還批評某清史學者,他對努爾哈赤的評判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在我看來,努爾哈赤所處的時代給他的成功創造了條件,和努爾哈赤同時代的都是平庸之輩,明朝衰落了,他獨樹一幟,所以他成功了,這樣分析才是符合歷史的。2015年,我撰寫《評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專門批判“新清史”,學術界褒貶不一。美國學者顛覆中國歷史,尤其是清史,我能不發表自己的看法嗎?“新清史”學者和他們的擁躉宣稱:“中國”只是一種設想,中國只是滿洲的一部分,清朝皇帝也不是中國皇帝。這簡直是奇談怪論!稍有常識都知道,滿洲屬于東北,東北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是實體、是各民族共同體,把中國說成“設想”,其居心何在!這些人顯然有肢解中國、分裂中國的險惡用心。我在《清史論叢》發表《清軍入關辯》駁斥“清軍入關偶然說”,指出清軍入關是整裝待發,積蓄多年才成功的。入關是必然的,怎么能說是偶然!恩格斯說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必然通過偶然體現。
第二,要有勇氣,要敢于爭論,敢于辯駁。在學術問題上,不要怕得罪人,我一直堅持。近來,我覺得要謹慎了,要是自己被人批也不好受。但是我們要有明確的意識與堅定的信念,如果連對錯都不知道,你就永遠不知道什么是對錯,就永遠在踏步走。堅持自己的觀點,才是真正搞學術,才能真正學到東西,這是個性,是個人的信念。現在學術界一片沉寂,不好爭論。“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真理越辯越明。
第三,要學習理論。理論有兩方面:一是科學方法論,一是政治方面。不學理論,沒有理論指導,憑著感覺走,什么也看不明白。成果發表了,但對學術界沒有推動和貢獻,對自己提高作用也不大,這有什么意義!我的個性就是敢于反世俗、反潮流,我是在學術的規范內反,不是濫反!學理論能益智。必須學習方法論,學習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比如說偶然性和必然性、個性和共性等。不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放在頭等位置來講,就是丟棄了最根本的立足之地。沒有理論,什么問題也認識不了,什么問題也看不清楚。
此外,建議大家學點文學。我們的詞匯太少、情感太少、想象太少。描述歷史場景、歷史狀況,專靠歷史專業的那點術語是不夠的,要靠文學的語言來表達。文史不分家,把語言練好,有助于史學書寫生動化。
2.您的學術研究富有創造力、創新性,得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認識。您是怎樣形成這種學術特質的?有什么感受?
第一,歷史研究需要不斷推陳出新,要努力創新。已經發生的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永遠不可改變。雖然史實無法改變,但我們需要將不準確的歷史描述考證過來,恢復歷史原貌。雖然歷史客觀存在,但人們的觀念、評判一直在變。改革開放前,人們認為李鴻章辦洋務是賣國賊的勾當。改革開放后,認識改變了,又看到了他辦近代工業的功績。過去突出階級斗爭,人們因左宗棠鎮壓太平天國、陜甘回民起義而否定他。改革開放后,大家又認為他是愛國英雄,看到他不畏艱辛西征新疆,維護了國家統一。再如,學術界對秦始皇、隋煬帝等的評價也都在發生變化。以往說秦始皇殘暴,后來又認識到他在統一全國、創立郡縣制的卓越貢獻。先前講隋煬帝修運河勞民傷財,現在又強調其罪在當時,功在千秋。總之,歷史是不變的,觀念和評價可以改變。我們必須推陳出新,不斷改變我們的觀念與評價機制,提出新觀點,這是歷史科學發展的需要。
創新是學術發展的生命,沒有創新就沒有學術生命。把創新掛在嘴上容易,真正做到很難。創新不是有想法就能做到的,必須拿出點真本事,要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能看出問題,有一定的解讀歷史的能力。思想意識不明,創新意識不強,就是能力不足,缺理論,缺文采,怎么解釋歷史?怎么分析歷史?有些所謂推陳出新,其實是在朝錯誤方向發展。如,有學者認為,康乾盛世是“饑餓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暴力的盛世”,這是謬論,不是推陳出新。這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個別代替整體,在哲學上犯形而上學的錯誤。在任何狀態下,個別現象都是存在的,不能見了幾個窮人,就認為是貧窮的時代。文章沒有新觀點,不寫也罷。推陳出新是學術永恒的生命,也是學者的使命感。沒有創新,就沒有學術,創新不論大小,小的創新點也是創新,在某一點上能有突破,就是創新。
第二,要多讀多想多寫。思想是練出來的,雖多讀,但不寫不想等于白讀。讀完后不寫讀書筆記,不寫感想,過后就忘了。通過讀書,慢慢形成思維,養成習慣,一有靈感的火花閃現,就要趕快記下來。學術是個積累的過程,一開始我也半知半解,后來慢慢體會,形成思維定勢,就好了。多讀多想多寫,三者相輔相成,不讀就是空想,想了以后不寫,靈感稍縱即逝。一定要寫堅持寫讀書札記,寫日記,鍛煉筆頭,熟能生巧。
自2003年我應邀來北京,參加國家清史編纂工作以來,我已經寫了三十八本筆記了。每天晚上堅持記錄重大事件。我過去的日記,有時候批評自己荒廢學業,沒有抓緊時間。自然科學靠靈感,史學靠積累,不斷的總結,不斷的積累,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的飛躍。比如寫文章,文章開頭難,萬事開頭難。寫文章,要講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你這個問題在清代是屬于什么位置的問題,重要性如何?第二個要素,學術界有沒有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第三個要素,要點題,點明文章的主題。三個要素合在一塊,有三五百字即可。
第三,要注意加強學術聯系。通過學術交往,吸收信息與各種學術見解,豐富自己的見識和想法。真正的歷史學者,任何成就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勞動,以苦為樂,樂在其中。過去談戀愛,我常常寫信,這也是一種鍛煉,可以表達情感,練習寫作能力。車要有兩個輪子才能轉動。歷史科學也要有兩個輪子,一個輪子是文學,一個輪子是哲學。文學講想象、講形象,哲學講方法、講邏輯、講條理。青年朋友們,要多練習思想,要多練習寫作,要加強理論素養,要提升文學素養。
3.近年來,各種“虛無主義”盛行,歷史研究領域是重災區。您覺得有哪些表現?解決的途徑和渠道是什么?
歷史虛無主義從表面來講,就是對歷史事實視而不見,認為都是虛的,沒有實的。有的把小問題放大,以偏概全;有的看不到重大問題,只抓碎片;還有的看不到正確的歷史記載,只憑當然臆測、歪解。歷史虛無主義是習慣于用個別代替全面,以局部代替整體,以現象代替本質。最可恨、最嚴重的是無中生有!有人認為乾隆在位六十年沒干過一件好事,這就全是虛無了。還有學者編造杜撰疑案、謎案,把沒有的事情描繪的聲情并茂,說孝莊和多爾袞結婚了,順治帝出家了,無中生有,或者以假當真,這也是虛無主義。
克服虛無主義,就是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詳細占有資料。要避免虛無主義,關鍵要樹立唯物史觀,唯史料是論。沒有史料就不寫文章,沒有根據就不說話,有這樣一種責任感,才能克服虛無主義。再一點,就是要用唯物史觀正確地解讀歷史。離開正確理論的指導,你的解讀往往會違背歷史的真實和本質,就會變成虛無。掩蓋歷史的本質,也就掩蓋了歷史真相。決不能以想象代替客觀事實,以想當然代替理論分析,以感覺代替實際操作。
四、寄語青年史學工作者
1.您曾在多個場合強調,史學研究要“堅守唯物史觀”。請談談您的認識。我國70年史學實踐唯物史觀的基本情況,成敗得失。
解放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我們批判了封建史學、資產階級史學,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史學。這是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白壽彝、劉大年、尹達等老一輩學者的突出貢獻。
文化大革命開始,教條主義盛行。一些研究和宣傳以論代史,生搬硬套,空發理論,借題發揮。還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用成分論代替理論分析,凡是農民起義的,都是正確的,把農民起義抬得很高。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是行動的指南,是教你怎么走路,讓你怎么走的更好,往哪個方向走,不是讓你貼標簽。雖然當時理論學得好,但是走偏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沒有完全樹立起來,出現很多錯誤傾向,比如出身論、成分論等。后來強調要史論結合,就是為了糾正虛無主義的流弊。
2.您能不能談一下在研究中是怎樣堅持唯物史觀嗎,對青年學者有什么建議。
我畢業于六十年代,正是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我注重學馬列,讀了很多相關書籍,慢慢形成了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識。我不是機械地用,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去收集史料、分析史料。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條件不具備,創造不了歷史,史學研究的關鍵是考察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都要講時代背景。
堅持唯物史觀要做到六個字,即繼承、發展、改變。比如評價歷史人物,就看他比前代人增加了什么,改變了哪些,繼承了哪些,這樣,問題就出來了。再比如清以前都修長城,清康熙廢長城,這就是重大的突破。不僅在觀念上突破,民族觀上突破,還要在疆域觀上突破。廢長城,標志著邊疆、內地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通過和前代比較,就能看到清朝做出了劃時代的改變,劃時代的創見,劃時代的前進。
現在理論的應用反過來了。學者們理論興趣弱化,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不用。不學理論,后果非常嚴重,是當前史學危機的根源。在史學研究中,不用馬克思主義,就是學術盲人,無問題意識,即使發現了問題,又解釋不明白,這就是看不清、理不清,更不能提出新觀念。
3.您在主持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工作時,曾提出“作天下第一篇文章,寫天下第一本書”。請問,如何準確理解您強調的“天下第一”!
我的本意是鼓勵創新。“天下第一”不是說自己的研究成果天下第一、研究水平最高,而是說:寫別人沒寫過的內容,我第一個寫。比如我的專著《吳三桂大傳》《關東文化大辭典》《明清戰爭史略》《愛新覺羅家族全書》《清康乾盛世》等,論文《論清朝歷史地位》《康熙處理三藩問題辨》《“大一統”與“華夷之辨”的理論對決——〈大義覺迷錄〉解讀》《長城新解》《清代邊疆論》等,都是別人沒寫過的文章。有人認為,我是第一個喊出“大一統”觀念的學者。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就把大一統應用到學術研究上去了,并給大一統一個解讀、一個定位、一個評價。我又把大一統運用到了清代西北的“離心運動”,從康熙二十九年到乾隆二十四年,我用大一統解釋“離心運動”怎么最后合為一心,這就是創新。我在《長城新解》中批評了一些對于長城的錯誤觀點,并提出了新觀念。我不愿意嚼別人嚼過的饃,不愿意寫別人寫過的文章或著作。我喜歡推陳出新,比如現在已有四十多部《清史》,我主編的《清史》上下兩卷,優點在于長短適中,觀點鮮明,文字簡潔明快,行云流水,這是讀者和出版社的評價。
4.立足新時代,發展中國史學,我們的努力方向在哪?前景如何?
我對史學研究前景持謹慎態度。一是從傳承來講,當前這一代史學工作者的學術與老一輩史學家的學術是失聯的,老一輩和新一代之間形成了一條溝,這涉及到史學繼承、發展和改變的問題。二是我們對前面的學術沒有很好的總結,沒有得到好的傳承;對當代的學術現狀也不夠清楚,不知道研究推進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該在哪些方面推進。三是缺乏創新,習慣就事論事,把歷史記載的東西重新歸納一下,重復書寫。四是缺乏理論指導,研究得出的結論既沒有高度,也沒有深度。
展望未來,要特別注意五點。第一,要對前代的學術進行總結,有所繼承,有所發展,有所改變。第二,要重新對中國歷史的主線和關鍵問題展開研究,從斷代史入手展開全新研究,重點在國家治理、農民問題、土地問題、邊疆民族問題等,其他問題都是派生的。第三,要對西方的史學理論進行揚棄,不能盲目的全盤接受。不能正確的對待西方理論,缺乏創造性的吸收借鑒,就容易陷入生搬硬套的境地。第四,要開展學術爭鳴。學術爭鳴十分重要,沒有爭鳴,學術就沒有發展。我們要通過爭鳴來批判錯誤的東西,樹立正確的東西。第五,要勤奮治學。成功有很多因素,勤奮是第一位的。勤奮未必成功,還要注意方法。人巧不如家什妙,家什不如方法妙,方法很重要,人人都需要。思想不端正,方法不對,一樣寫不出好東西。要勤奮、方法正、思想正,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考慮問題。
最后,一定要關注社會現實。了解社會現實,是解讀古代史的一把鑰匙,要善于以學者的身份關心、關注并主動服務現實,這就是經世致用。歷史是一個過程,前后是相互繼承、改變和發展的關系。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處理好前后的關系,才能真正認識歷史,從中獲取智慧,為現實提供歷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