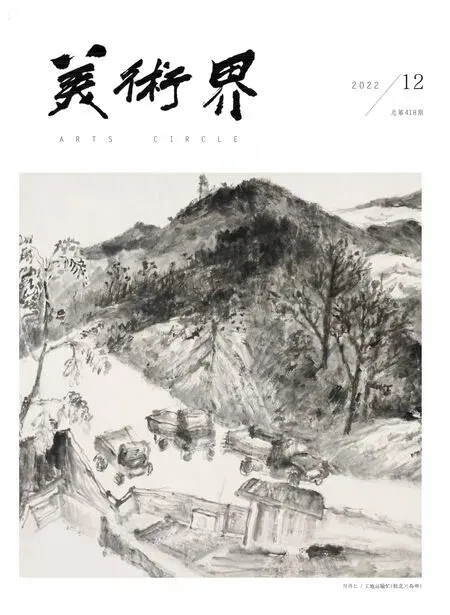明代壁畫世俗化傾向略論*
文/肖晶[南通大學藝術學院]
中國繪畫發展到明代以后,世俗化傾向是美術發展的重要潮流之一,這不僅主要來源于社會文化變革的歷史成因,更因工商業發展與市民文化的形成,導致美術發展的世俗化變成一個不可避免的社會思想潮流。即便是作為小眾把玩趣味的文人畫,由于有了廣大底層社會的認可與推崇,繪畫作為商品可以在社會交流中體現出更為廣大的審美價值,因此明代的文人畫與宋元時期的文人畫家不同,他們不可避免地參與到了世俗化的文化潮流當中,而文化思潮的開放性影響勢必波及美術領域的方方面面,作為“成教化、助人倫”發揮其最主要社會功能的壁畫,同樣不可避免地面對世俗化而受其影響。在現存的明代壁畫當中,除了表現其主題的宗教言說功能外,在表現儒、釋、道的宗教精神、教義教規、神話故事、世俗風情的過程中,更是利用圖像表達的方式向信眾及觀賞者展示內在的精神思想,而在其圖像繪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創作者所處時代的文化風潮。由此,世俗化傾向成了明代壁畫圖像中一個最為明顯的特征。
在現存與考古發現的明代壁畫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壁畫的設計與繪制都強調了故事性的直觀表達,這種表達方式在繪制圖式上呈現為強調場景式的營造,這種場景式給人一種現場感,即便你沒有審美修養的基礎都可通過讀圖知曉故事的具體內容,這是世俗化繪畫的重要特征,是普羅大眾都可以讀得懂的故事性闡述。由于強調故事性的直觀表達,圖像的構成中出現的人物角色也增多,很多沒有具體身份定位的小人物也成為壁畫描繪的對象,這一方面使得故事的空間拓展得到進一步加強,增強了圖像故事表述的豐富性。這種多種類型或多重身份人物的參與,是明代壁畫世俗傾向的又一特征。使得不同社會身份的觀賞者在欣賞壁畫的過程中都能找到與自身角色相符的藝術形象,找到自我社會身份的認同感,這也使得壁畫本身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起到了積極的社會教化之功效。再者,在藝術表現中,明代壁畫絕大多數的作品都具有較強的“密滿”構圖,豐富的內容一方面加強了圖像本身的敘事性,這使得壁畫的繪制不同于其他繪畫門類,深沉的哲理性與個性的取舍被宗教的神圣性與故事的復雜性所取代,用一種密滿且充實的圖像視覺效果“震撼”更多的信眾或觀賞者,這是壁畫社會功能所決定的。密滿構圖與故事的豐富與多樣,一方面把欣賞者拉入故事中而忽略了對藝術語言及藝術美感的關注,對于絕大多數的欣賞者而言,故事本身的警示作用遠遠比圖像本身的藝術審美好看要重要得多;在藝術語言方面,明代壁畫的色彩運用更為繁復絢麗,所使用的繪制材料與表現技法也根據地域特征的材料特點加以靈活運用,色彩的選擇更傾向于世俗所能理解與接受的角度出發而加以表達,并不是美術歷史所形成的固定法則,這又是明代壁畫世俗化傾向的又一重要特征。
一、故事性的直觀表達
在諸多的明代壁畫中,比如四川新都龍藏寺、邛崍磐陀寺、山西太原多福寺和永寧寺、河北蔚縣觀音殿和清涼寺、湖南婁底出土的明代墓室等,這些壁畫都注重故事性的直觀描繪。在這些壁畫中,作品無一例外地講究故事性的描寫,使得觀賞者在觀看時,第一時間被壁畫所描繪的近似人間生活的各種故事情節所吸引,故事的情節表現成為壁畫的重要特征,這一故事性的表述成為觀眾駐足參觀的最主要原因。
新都龍藏寺的壁畫具有極強的故事性表現,故事雖然描寫的是佛教題材,然而當地民俗生活融入其中也顯而易見。其中,大雄殿墻壁的東西兩壁各有三鋪,前、后鋪各高2.8m,寬2m,中鋪高2.8m,寬7.6m;大殿的橫壁是也繪制有壁畫,三鋪各高4.7m,寬3.5m。繪制的內容包括佛教的經典故事,比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天龍八部”“西方三圣”“華嚴世界”“釋迦應化事跡”等。這些故事通過壁畫圖像轉化,將人腦中想象的故事變成圖譜,更形象得將佛教思想在民間傳播開來,而圖像的固定化模式比佛經記載的文字故事更方便記憶與傳播。與此相同的故事性描寫在其他的壁畫中同樣存在。
為了突出這些故事的直觀感,壁畫著重描繪故事的細節,使得觀賞者可以通過細節的觀察加深對故事的理解。比如邛崍磐陀寺壁畫中,對于佛祖講法、眾僧徒聽法的描繪就特別注重細節的刻畫,河北蔚縣觀音殿壁畫中幾組錯落安排的神仙形象,神仙的神情各異但又相互間各有照應。這些細節的描繪增加了壁畫的故事情節,使得神佛形象更為生動多樣,他們似乎與人類的情感表達存在著某種共鳴。這種細節描繪不僅是對宗教故事的解讀,同時也把人間情態賦予藝術形象當中。在這些壁畫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人日常情感樣貌的某些特征,這無疑是明代壁畫世俗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二、小人物表現意識增強
在明代的壁畫畫面中往往多次出現一些次要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沒有明確的身份定位,也沒有特別設定的角色分工,然而就是這一類形象組成了明代壁畫的豐富內涵。這種刻意表現小人物角色的現象是明代壁畫的一個特征。一方面,這種人物設定豐富了主題表現的內涵,擴大了畫面敘事性的維度,使得畫面在眾多角色的切換中得到了內涵的提升。另一方面,小角色的豐富與表現可以與現實的普羅大眾產生對應,觀賞者可以通過角色的切換找到與自己身份相近的形象,無形中讓人產生“我也在其中”的審美移情,這對于教化功用為主的壁畫來說,無疑是一種重要的審美熏陶與心理暗示,也是世俗角色在壁畫上的投影,本質上也是壁畫世俗化的結果。
湖南婁底明代壁畫墓在2014年10月被發現,出土的墓室壁畫中,東西兩壁都畫有出行場面。東、西兩壁的主人公一個坐轎、一個騎馬,并且都放大處理,突出了主人公的地位。除此之外,出行的隊伍浩浩蕩蕩,有抬轎、牽馬、耍戲、吹奏等人物形象排列其中,還有沒法定位的人物角色也在畫上出現。這種盡可能多的場景描寫可能是現實生活中某種儀式的再現,抑或是創作者想象墓主歸天的宏大場面,這種盡可能多的人物角色參與其中,本身就是世俗生活的寫照。而河北蔚縣觀音殿壁畫諸多神仙的描繪,除了主要的神仙有角色定位之外,許多的“神仙”的角色定位十分含糊,他們的人物造型與衣服著裝,與當時所處的人物背景并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僅僅屬于籠統的“神仙”角色,而并沒有具體的名稱。這無疑也是創作者豐富角色所需,這類“小角色”成了豐富壁畫不可或缺的形象,其產生與世俗生活的角色多樣化存在密切關聯。
四川省蓬溪縣的寶梵寺壁畫繪制了各種各樣的宗教形象,除了主體的藥師佛、達摩、布袋和尚、四天王等主要神佛形象外,其余的天人與眷屬占了人物形象的絕大部分。藥師佛形象周圍就畫了眷屬13人,西壁的第三到第十鋪除了繪制幾個天人形象,其中多數則繪制世俗人物形象及飛禽走獸之類。“第三到十鋪的上方皆繪天人數位,中下方主像之間各安排數量不等的侍僧及世俗人物。另有龍、虎、獅等獸類,與人物同處在云水山林之間。現存可辨認的題記十二處,其中標明人物身份者十位。通體壁畫突出羅漢像主體地位,其他人物按照一定規律配置,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圖像系統”①。壁畫的組成強化了非主體人物表現的分量,這是世俗化影響下的審美結果。
三、畫面構成的“密滿”特征
畫面構成是壁畫視覺的一個重要特征,明代壁畫另一個重要特征是畫面都具有“密滿”的特征。壁畫作為表現與主題內容相契合的圖像作品,除了設定的主要藝術形象,如主要的神佛或特定場景的主人公之外,還得配上相應的背景人物、亭臺樓閣、仙禽瑞獸、吉祥花草等內容,部分作品還必須強化故事情節的描繪,這使得壁畫作品的表現不僅考慮內容的完整性與復雜性,眾多題材的表現與繁多的內容要完美結合起來,畫面構圖勢必不能如一般的山水畫創作來考慮虛實搭配與空間轉換,而是盡可能利用畫面空間,把需要講的故事圖像化展開進行描繪與解說。因此畫面的密與滿就變成壁畫的一個重要構圖特征,而這一特征發展到明代以后則更為突出。
河北省石家莊市西北郊的毗盧寺壁畫,包含了儒、釋、道三教人物題材的人物形象,是三教融合的經典圖像范本,這一方面反映了明代文化與宗教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間對不同類型文化類型的發展都具有較強的接受度,各種文化之間相互影響、互相滲透可以通過世俗的接受而轉化為圖像表達。寺內壁畫的代表是摩尼殿壁畫,該壁畫以佛教故事為題材,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繪有儒釋道三教各類各式天神帝君、菩薩天王、護法諸神、往古人物等500多個人物形象,這些藝術形象密集于壁畫當中,視覺上給人一種直觀的震撼感。同樣的構圖特征在蔚縣故城寺壁畫也有出現,寺內釋迦殿的壁畫高約3.6m,總長約34m,能夠看得清楚的人物形象就有530多位。“壁畫內容包括儒釋道三教眾神像,如佛祖、菩薩、十大天王、護法等,以及冥府獄主眾圖像、冥府八寒等眾圖像等。故城寺壁畫帶有明顯的民間繪畫特征,是典型的民間繪畫藝術”②。這些密密麻麻的藝術形象組成了壁畫獨特的構圖特征,這無疑也是世俗審美影響下的時代文化特征。
四、色彩運用的絢麗繁復
傳統繪畫由于具有了規范性的理論指導,色彩運用都傾向于規整化、法則化,“六法”中的“隨類賦彩”就是一種規范化的色彩運用指導。而壁畫的色彩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受這一理論影響較小,一是由于壁畫的創作者更多是民間工匠所為,他們在師徒傳授中會接觸到一定的粉本或模式化的圖譜作為創作參照,這當中多少都有習慣性的色彩表現特征,然而壁畫本身面積大、人物眾多、故事情節豐富,使得色彩運用在實際繪畫創作過程中必須相應的復雜化,才能烘托壁畫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二是由于在壁畫創作中,描繪的景象多數情況下都以世俗的現實世界作為參照,以期通過壁畫喚起更多人的情感共鳴,這使得顧及普羅大眾所能理解的圖像模式是創作者要考慮的立足點。這樣的心理期待使得色彩運用過程必須熱烈而多姿,從而能夠在視覺層面上吸引更多的信眾。
四川明代寺廟繪制的菩薩像中,所使用色彩的變化都極為豐富,不同菩薩形象頭部的色彩描繪,都存在不同的色彩傾向變化,即使在同一個色系中,也突出了人物的不同而作了精微的變化處理,使得色彩在壁畫的總體特征中,既存在統一元素而實際上又包含有多元變化。比如平武報恩寺所繪制的菩薩像,辨音菩薩、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的頭部總體上都傾向于一個赭紅色調,而辨音菩薩是在赭紅中偏向青色,金剛藏菩薩則傾向于朱紅色,彌勒菩薩則傾向于胭脂色的調性更為明顯。當我們把三者的圖片放在一起對比時,這種細微的色彩差別就易顯現。相同的賦色手法在蓬溪寶梵寺也有出現,菩薩像的頭部色彩乍一看色調相同,但只要細心留意就會發現,日光菩薩、月光菩薩、地藏王菩薩的形象在深紅、淺紅、粉紅間出現了細微的明度色彩變化傾向。這種精致繁復的色彩使用在壁畫中不僅是神仙、人物形象中存在,衣紋飾物、器具背景、山水樹石等,創作者在繪制過程中,并無概念性的“隨類賦彩”,而是在繪制過程中,結合不同的人物場景與故事情節,在色彩使用上作了細微變化與差別對待。
除了以上色彩的色相、純度、明度的用色之繁復外,另一方面,明代壁畫的色彩在技法表達中還運用了瀝粉貼金技藝和金色的使用,這無疑也增加了繪畫過程中的技術難度與色彩的復雜化,這種技術更能體現壁畫的獨特裝飾效果。“瀝粉貼金的裝飾感一方面是由于其高于平面所產生的立體效果,讓畫面在視覺上具有層次感、豐富性。通過瀝德粉與水進行調和成黏稠的液體,可將液體滴到畫好的菩薩頭飾上,對需要裝飾的飾物邊緣線條一滴一滴地堆砌成線條,留出飾物本身的附色部分,主要是讓輪廓高于畫面,增加飾物的立體感,有著類似低浮雕的效果”③,“瀝粉貼金”的技法與濃重裝飾元素的強化突出了世俗審美意趣。
結語
明代壁畫世俗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根源于明代王權至上的時代特性。從明太祖朱元璋通過強勢政令推行了其對佛教僧伽組織的劃分,敕令天下寺院及僧人界的劃分與開設僧官機構及任命僧官員同步進行,教僧可以堂而皇之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世俗社會開始,明代壁畫的世俗化就拉開了帷幕。壁畫的藝術圖像功能可以輔佐帝王教化民眾,明代壁畫具備了輔助治化的世俗社會功用,此功用轉化到圖像上呈現為生動場景式故事敘述,故事中小人物角色形象的塑造,民間世俗生活的生動演繹,畫面的密滿構圖,艷麗繁復、錯彩鏤金的設色技法,將明代壁畫的世俗化彰顯得淋漓盡致。
注釋:
*基金項目: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明代佛教壁畫世俗化元素研究”(項目批準號:2018SJA1211)。
①范麗娜:蓬溪寶梵寺明代壁畫羅漢圖像考察》,《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第38頁。
②田紅巖、代曉蕾、郝建文:《以清涼寺為代表的河北省明代寺觀壁畫研究》,《美與時代》2021年第4期,第114頁。
③甘鈺萍:《四川明代佛寺壁畫菩薩頭部造型研究》,四川師范大學專業學位碩士論文,2021,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