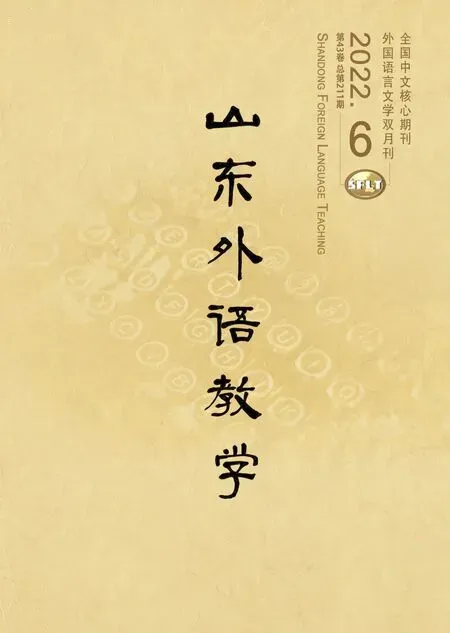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的間接譯介及其影響
李文婕
(北京師范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875)
1.導言
安徒生作品是丹麥文學經典的一部分,面世不久就進入了丹麥中小學教育體系。根據相關學者的統計(Bom & de Muckadell, 2021:412)及筆者的追蹤,19世紀收錄安徒生作品的中小學生推薦書目包括1840年由Reiβel出版社出版的《兒童熟讀詩歌選》(DigteogRiimforBrntilUdenadslsning)、1858年由Helsingr出版社出版的《學生詩歌30首》(30Skolesange)以及1859年由Erslev出版社出版的《學校童詩讀本》(DigteforBrntilSkolebrug)。最初入選中小學必讀書目的作品多為詩歌,這與安徒生在其本國的文學形象和解讀有著密切聯系。正如著名安徒生學者約翰·德·米留斯(de Mylius, 2006: 166)所說:“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甚至在德國、法國以及東歐,安徒生遠不止是個兒童文學作家,他還是小說家,詩人和游記作家”①。
德·米留斯的評價符合安徒生對自己的定位。安徒生最初的文學嘗試集中于詩歌、戲劇、小說,并憑借這些作品在丹麥文壇嶄露頭角;直到1835年才創作出版了4篇童話,收錄于童話集《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Eventyr,fortalteforBrn)。1835至1841年間,安徒生創作了六部以“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為題的童話集,共收錄19篇童話;1843年起將新創作的類似作品集命名為“新童話”(nye eventyr),1952年改為“故事”(historier);后來又將兩個名稱并置,創作了多部“新童話和故事”和“童話和故事”集。然而,即使在《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系列獲得丹麥讀者的廣泛認可,摯友物理學家奧斯特(Hans Christian ?rsted)高度評價安徒生“必將因其童話而不朽”時,其本人也并不認同,回應稱“我并不這么認為”②。顯然,安徒生從未將自己僅視為兒童文學作家或者童話作家。
然而,安徒生在歐洲以外的地方常常以兒童文學作家的形象進入經典文學殿堂,許多國家的讀者只知安徒生童話而不知其詩歌、小說。在中國,安徒生也被歸入童話作家之列,那么是什么因素塑造了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國的形象呢?本研究將考察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的早期譯介,重點分析1909至1929年間極具普遍性的間接翻譯與間接解讀兩種譯介行為,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安徒生童話故事中國形象的建構因素。希望研究有助于揭示間接譯介行為發生的環境因素,有助于解釋間接譯介行為對源語作品及作家在目的語文化中形象的影響,從而為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提供值得借鑒的經驗。
2.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的早期譯介概述
20世紀初,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劇烈變化,各種理論與學說經由翻譯進入中國,成為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思想工具。在文學和思想領域,現代兒童文學和兒童教育成為知識分子關注的話題,以魯迅、鄭振鐸為代表的知識領袖們紛紛呼吁“救救孩子”,希望以現代兒童文學滋養中國的未來。1909年,孫毓修在《東方雜志》發表文章《讀歐美名家小說札記》,篇首便向國人介紹了童話作家安徒生,這是安徒生在中國的初次亮相。筆者利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以“安徒生”為主題詞統計了1909至1949年間在我國主要期刊和報紙上發表的與安徒生及其作品相關的文章數量。統計結果表明,從安徒生首次被介紹到中國(1909年)直至新中國成立(1949年)的40年間,20年代是安徒生作品譯介的第一個高潮,其中1925年作為安徒生誕辰120周年譯介活動更是達到最高峰。筆者觀察安徒生中文譯介的整體歷史進程,發現在20世紀20年代、50年代及90年代分別出現了三次譯介高峰(Li, 2017),若結合中國近代至今的社會歷史發展分期來看,1909至1929年可視作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國譯介的早期階段。
除了孫毓修的首次介紹,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國譯介的早期階段中幾次重要的譯介事件分別是:1918年,陳家麟、陳大鐙合譯的首個安徒生童話單行本《十之九》出版;1919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安徒生童話譯文《賣火柴的女兒》;1923年趙景深發表首個白話文安徒生童話單行本《安徒生童話集》;1925年文學研究會三次在其旗下的《小說月報》及《文學周報》推出安徒生專刊。以這些重要譯介事件為線索和場景,我們可以觀察早期譯介所涉及的人的因素與非人因素,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交聯互動。行動者網絡理論(Latour & Woolgar, 1986:187-230)將社會活動中的人類行動者(human actor; Latour, 2005:4)與非人類行動者(non-human actor; 同上)都納入研究視野,重視各類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聯系,為深入觀察分析譯介活動所處的社會場景、所涉的動因以及動因交聯機制提供了比較完善的描述框架。社會實踐理論(Bourdieu & Wacquant, 1992)認為場域(field)是行動者的社會實踐空間,其結構對行動者的活動帶來影響和限制。行動者帶有開放性、生成性、偏好性的性情傾向系統,即慣習(habitus),能夠對場域施加影響。同時,行動者掌握各類資本(capital),主要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即行動者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在社會場域中,各類行動者使用其掌握的各類資本通過博弈等方式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各類資本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互動或聯合,呈現出不同的象征資本。下文將借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及社會實踐理論描述安徒生早期譯介史的基本面貌。
首先,該時期內的重要譯介事件涉及兩類人類行動者,即包括孫毓修、陳家麟、陳大鐙等在內的晚清知識分子和包括鄭振鐸、周作人、徐調孚、趙景深、顧均正等在內的五四新知識分子。由于學術背景的差異,兩類行動者的文字主張不同。例如,陳家麟與陳大鐙、孫毓修等人使用文言組織譯文,而周作人、趙景深等人則堅持使用白話文進行翻譯。周作人(1918:286)甚至專門撰文批評二陳的譯本,斥其將安徒生作品譯為班馬文章,盡失其妙。由于翻譯目的差異,兩類行動者的翻譯策略和介紹重點也有所不同。例如,陳家麟早年畢業于北洋水師學堂,曾任北洋政府官員,是林紓小說翻譯活動的主要口譯合作者(古二德, 2016);他翻譯安徒生作品只屬閑來之筆,多采用歸化策略,根據中國的文化道德語境做了多處增刪,安徒生的特色“不幸因此完全抹殺”(周作人, 1918:288)。孫毓修在清末民初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兒童讀物《童話》叢書,其中收錄的編譯故事都使用文言;出于道德教化目的,他常常在所編譯的童話之前加上說教式的按語,甚至改動故事情節,其根據安徒生童話編譯的《海公主》就屬此例。而以周作人、趙景深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推崇在譯文中保留安徒生童話原作中的口語化特征和兒童視角,以期為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引入新的范式,同時改良中國社會的兒童觀。從行動者人數和譯介數量來看,這一時期譯介安徒生的主力是擁護新文學運動的新知識分子,多數為文學研究會成員。
同時,安徒生作品早期譯介中人類行動者的共同點也非常突出。首先,前文列舉的主要譯介人無一能讀丹麥語卻幾乎都懂英語,且多數僅掌握英語一門外語,因此他們主要以英譯文為底本翻譯安徒生作品。其次,他們幾乎都譯介并舉,不僅翻譯作品也寫介紹或評論文章。例如,孫毓修曾三次撰文介紹安徒生生平及其文學成就,同時也有譯作《女人魚》《海公主》發表于其主編的《童話》叢書(Li, 2017:102);周作人除撰寫了數篇評介文章之外,也翻譯了《賣火柴的女兒》《皇帝之新裝》等幾則童話故事(同上:103);而趙景深不僅翻譯了約30則安徒生童話故事,也翻譯了數篇介紹安徒生生平及藝術特點的評論文章(同上:111)。再次,有許多譯介人兼有贊助人和出版人的身份。例如,文壇領袖周作人和鄭振鐸同時也是譯介贊助人,而孫毓修、鄭振鐸、徐調孚還是當時著名的出版人。這些譯介人在中國文壇和出版界的影響力和人脈為安徒生作品的譯介提供了社會資本(Bourdieu, 1986:248)和象征資本(同上:254)。最后,多數譯介人都屬于文學研究會這個影響廣泛的文學社團,有著相似的文學觀和意識形態觀念。上述四點人的因素使得早期安徒生譯介在翻譯規范和作品理解上趨同,形成了主流規范和解讀。
在非人類行動者方面,這一時期對安徒生譯介活動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意識形態因素、詩學因素和翻譯規范因素。首先,安徒生早期譯介活動發生于中國社會劇烈變化的歷史時期,文人政客期望通過譯介西方強國的理論學說來改良國人思想并從中找到救國之途。自梁啟超提出“小說救國”論后,文學被知識分子看作是宣傳新觀點和政論的最佳載體,于是晚清至民國初期,包括小說、戲劇及童話在內的大量新文類作品被譯入中國。安徒生童話故事及其所代表的童話文類就是在這種意識形態因素的推動下承載起譯介人改造兒童觀、顛覆儒家“文以載道”教育觀的期許。其次,20世紀10年代末,白話文運動在我國興起,除了創作白話文作品,以白話翻譯外國作品也是白話文寫作的重要實踐。安徒生童話故事因其平如白話的語言風格得到了主張文字改革的知識分子的推崇,而以更貼近口語的白話文組織譯文也逐漸成為安徒生作品的翻譯規范。20年代創造社成員與文學研究會成員圍繞文學“為藝術”還是“為人生”展開的一系列辯論也對翻譯選材產生詩學影響。文學研究會成員注重文學的社會功用,倡導“為人生”的文學,主張譯介來自“弱小民族”及“被損害民族”的文學以啟發激勵國人,而北歐國家文學就被歸于此列(宋炳輝, 2002),安徒生等北歐作家的作品也因此被文學研究會成員大量譯介。此外,在翻譯規范方面,間接翻譯在這一時期是廣受認同并被普遍采用的翻譯路徑。雖然文學界曾就間接翻譯的合法性問題進行過激烈論爭(穆木天, 1934/2000; 魯迅, 1934/2005),但長年閉關鎖國導致的多語種譯者短缺的現實和引進外國文本及文類的急迫,讓間接翻譯成為譯者和讀者都能夠接受的一種翻譯方式。
在以上三個主要非人因素的作用下,早期安徒生譯介活動被注入了強烈的現實考量,即引進新文類、學習歐洲兒童觀以及推廣白話文。然而,由于當時國內鮮有現代意義的原創兒童文學作品,更無成熟的兒童文學理論,對于安徒生童話故事的評價和解讀仍需借助外國的視角和理論。
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共同構建了譯介活動的生產場域并交互聯絡,最終促成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國的第一次譯介高潮。通過觀察,我們不難發現早期譯介活動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間接性。這種間接性由譯介人特質、主流翻譯規范、本土兒童文學實踐和理論空缺等因素共同導致,既體現在翻譯路徑上,也體現在對安徒生作品的解讀中,決定了安徒生作品譯介的選材原則、翻譯規范、接受視角以及中國文學系統對安徒生個人和文學成就的評價,并進一步建構了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國最初的形象。下文將詳細介紹這種間接譯介現象并分析其影響。
3.早期譯介中的間接翻譯和間接解讀
間接翻譯是翻譯活動中長期存在的現象,國內外學界都有對間接翻譯的專門研究和討論,從權力關系、翻譯倫理、翻譯效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假設(St. André, 2003; Pi?ta, 2021;盧冬麗、邵寶, 2021)。對間接翻譯本質的關注從早期的二手翻譯(Toury, 1995/2012: 129)發展到其建構文化間性(Dollerup, 2014)乃至復合間性(李宏順, 2019)的社會文化功能。然而,迄今為止多數研究聚焦于翻譯過程中的間接現象,對解讀中的間接現象著墨甚少。據筆者觀察,僅有斯皮克(pirk, 2014)在研究捷克文學譯介的論著中提出了間接接受(indirect reception; 同上: xii)的概念,將間接翻譯與借助另一文化解讀源語文本的行為都歸于間接接受并討論了這兩類行為對目的語文化接受源語文本的影響(同上)。然而,斯皮克將間接翻譯定位為間接接受的下義概念在學術邏輯上存在含混不清之處,因為在實踐中翻譯過程與譯文接受是時間上的先后關系而不是從屬關系;此外,他也未對間接解讀包含的具體行為作出明確的界定。但無論如何,其研究率先提出了間接翻譯往往伴隨著間接解讀的觀點,值得學界關注,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究兩類行為對源語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形象可能產生的影響。
本文在斯皮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間接譯介(indirect mediation)的概念,以之指代包括間接翻譯(indirect translation)和間接解讀(indirect interpretation)在內的譯介活動;其中間接翻譯是指借助其他中介語譯本進行翻譯,而間接解讀是指通過閱讀中介語譯本、借助來自中介文化的理論和評論解讀源語文本,類似斯皮克所言之“透過另一種文化的視角接受譯作”(同上: 143)。下文將詳細分析安徒生作品早期譯介活動中的間接翻譯和間接解讀現象,從產生原因、譯介路徑和文本關系三個方面詳盡深入地揭示它們的本質特征。
3.1 間接翻譯
譯者語言能力缺乏是采用間接翻譯方式的主要原因。上文所述重要翻譯事件所涉譯介人都沒有學習丹麥語的經歷,不具備閱讀丹麥語的能力,因此安徒生作品早期譯介中的所有中譯本均產自間接翻譯。同時,這些譯介人都通過各種途徑學習過英文,陳家麟、顧均正、趙景深等人還長期從事英漢翻譯工作,具備英譯漢能力。查閱題名、署名、譯者后記及評論等副文本,可確定該時期發表的安徒生作品中譯文多是從英文間接翻譯而來。那么究竟哪些英文譯本被選作了中間譯本呢?
首先,20世紀早期的安徒生作品中譯文多數散見于《小說月報》《文學周報》《婦女雜志》等各類報刊之中,也許是出于報刊體例要求,譯者常常不注明源語文本。其次,部分譯者可能在翻譯時參考了多個中間譯本。這些因素都為勘定中間譯本帶來了極大困難。然而在翻譯研究中,勘定中間譯本是明晰源語文本進入目的語文化的路徑、分辨中間譯本對目的語文本的影響的前提,因此研究者必須通過可靠的勘定程序盡力找到最可能的中間譯本。筆者同意王劍(2022:104)的觀點,認為“從歷史上某一文本的副文本和元文本中發掘相應的身份標識”是一種可靠的中間譯本勘定方法。據此,本研究采取的勘定程序分為三步:第一步是查找譯者生平資料,特別是與其語言學習和翻譯工作相關的史料,以此初步確定譯者的外語能力。第二步需要搜集并分析與譯本相關的副文本(paratext; Genette 1997: 2),既包括如前言、后記、封面、插圖、注釋在內的內文本(peritext; 同上:5)也包括通信、日記、隨筆在內的外文本(epitext; 同上),這些副文本或許會包含中間譯本信息。將譯者生平資料與副文本信息結合起來,有時已經可以基本確定中間譯本,有時只能得到數個疑似中間譯本的選項。因此,還需要進行第三步勘定工作,即目的語譯本、疑似中間譯本與源文本之間的對比與分析。第三步分析工作需要仔細觀察三類文本之間的關系,比如觀察目的語譯本中是否有和疑似中間譯本完全一致的偏離源文本的現象。一旦在目的語譯本中發現大量從某個疑似中間譯本繼承而來的文字偏離,就基本可以確定后者為間接翻譯的中間譯本。
經過以上三個步驟的勘定,我們發現,周作人的兩篇譯文《賣火柴的女兒》和《皇帝之新裝》主要基于克雷吉夫婦(Craigie & Craigie, 1914)參與重譯的安徒生童話及故事。《小說月報》1925年9月及10月兩期專號中所登載的21則安徒生童話故事譯文主要依據的是1899年由Dent & Dutton House出版的盧卡斯夫人(Mrs. Lucas)的譯本FairytalesfromHansChristianAndersen、1867年由Warne出版的波爾夫人(Mrs. Paull)新譯本HansAndersen’sFairyTales.ANewTranslationbyMrs.H.B.PaullWithaSpecialAdaptationandArrangementforYoungPeople以及1914年克雷吉夫婦重譯本。趙景深1924年發表的《安徒生童話選集》、1928年發表的《安徒生童話新集》和1929年發表的《月的話》三本譯文集所依據的中間譯本是卡羅琳·皮奇(Peachey, 1908)的譯本及克雷吉夫婦重譯本。而陳家麟與陳大鐙的《十之九》近乎譯寫,無法考證中間譯本。對比分析中文譯文與中間譯本可知,中國譯者大多奉行忠實的翻譯原則;即使是曾奉行“寧順而不信”原則的趙景深,其譯文也都基本忠實于中間譯本,在語義與情節方面均無明顯添刪(Li, 2017:118)。這就使得中文譯文能夠較為完整詳盡地反映出英文中間譯文的特點。
3.2 間接解讀
在安徒生作品的早期中文譯介活動中,“透過另一種文化的視角接受譯作”(pirk, 2014: 143)是普遍現象,首先是對安徒生作品的間接閱讀和賞析。一方面,早期譯介人不具備閱讀丹麥語原文的能力,只能借助中間譯本閱讀、評析安徒生童話故事作品;另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僅有極少數中國人有機會學習外語或留學他國,普通讀者中具備外語閱讀能力的人稀少,更遑論掌握丹麥語。因此可以說,當時的中國讀者主要通過英譯文③或中譯文來間接閱讀安徒生作品。
其次是早期中文評介文本展現的間接解讀現象,不論是以譯介安徒生作品為工作內容的專業讀者還是在閑暇之余將閱讀安徒生作品作為消遣的大眾讀者,都在透過其它文化的視角了解安徒生的生平、藝術成就與作品特點。具體而言,由譯介人、評論人、出版人等專業讀者發表的安徒生作品評論文章大量引用歐洲學者的評價性觀點。例如,周作人(1937:108)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博耶森(Boyesen, 1895)及勃蘭兌斯(Brandes, 1886)對安徒生的評價對自己理解安徒生作品產生了重要影響。后來,他在《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周作人, 1913)一文中對安徒生作品的解讀也與文中所引的戈斯(Gosse, 1900)、勃蘭兌斯、博耶森等人對安徒生的評價高度一致。顧均正在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6卷第8期的《安徒生評傳》文后列舉了9條重要參考書目,其中8條都是歐洲學者署名的英文資料。顯然,由于無法閱讀丹麥語原文,加之當時我國沒有成熟的現代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和安徒生研究成果,早期專業讀者在解讀安徒生作品時較多地依賴歐洲學者的觀點。而通過閱讀專業讀者的評論文章,中國大眾讀者也接觸到這些來自異國的觀點,并最終將其內化為自身對安徒生作品的解讀。
最后,除對安徒生作品的評介文章外,安徒生傳記以及一些歐洲學者對安徒生的評論研究也在這一時期被譯為中文,成為中國讀者解讀安徒生作品的重要依據。經過文本對比可以發現,這一階段譯入中文的安徒生傳記主要有1908年由Gyldendalske Boghandel Nordisk Forlag出版的安徒生自傳MitLivsEventyr節選,1921年由The Macmillan Company出版的湯姆遜(M. Pearson Thomson)所著Denmark一書中的安徒生生平介紹以及貝恩(Robert Nisbet Bain)所著安徒生傳記,其中安徒生自傳節選轉譯自1871年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的斯卡德爾(Horace Scudder)的英譯本。譯入中文的評論研究主要包括1870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的斯卡德爾為安徒生童話故事英譯本StoriesandTales所寫的序言,1890年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出版的戈斯專著NorthernStudies中關于安徒生的章節及其(Gosse, 1990)為安徒生童話英譯本所寫的序言,博耶森專著(Boyesen, 1895)中對安徒生的評論以及勃蘭兌斯專著(Grandes, 1886)中介紹安徒生的章節,其中勃蘭兌斯著作的中文節譯轉譯自英文譯本。《小說月報》的兩期安徒生專號及《文學周報》的安徒生專刊是這一時期集中刊發安徒生評介文章的期刊報紙,其中幾乎所有介評都譯自上述文獻。總結此階段翻譯及引用傳記和評論研究成果的情況不難發現,中國讀者對安徒生的了解及對其作品的解讀主要受到戈斯、勃蘭兌斯、博耶森等外國學者的影響。
無論是通過閱讀安徒生作品的譯本,還是通過閱讀外國學者對安徒生的介評來了解安徒生及其作品,都可看作是借助中介語視角解讀安徒生的間接行為。經過史料考證和文本對比不難發現,早期中國讀者對安徒生的解讀主要受到英文文獻的影響,其中一部分是譯自丹麥語的英文文獻,另一部分直接以英文寫就。而這一時期的間接翻譯與間接解讀行為將共同對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國的接受產生影響。
4.間接譯介對安徒生及其作品在華接受的影響
間接翻譯使目的語文本無可避免地繼承中間譯本的特點,包括語言風格及增刪、改譯、誤譯等文本層面的改變。例如,周作人翻譯的《賣火柴的女兒》繼承了克雷吉夫婦在其英譯本中增添的內容;趙景深發表于《小說月報》安徒生專號的《鎖眼阿來》和顧均正翻譯的《飛箱》中都有很明顯的皮奇英譯本的痕跡。
例1:
原文:“Sulten og forfrossengikhun ogsaae saa forkuet ud, den lille Stakkel!...Ud fra alle Vinduer skinnede Lysene og saa lugtede der i Gaden saa deiligt af Gaasesteg; det var jo Nytaarsaften, ja det t?nkte hun paa.”④
中間譯文:“Shiveringwith cold and hunger shecrept along, a picture of misery,poor little girl! ... In all the windows lights were shining, and there was a glorious smell of Roast goose, for it was New Year’s Eve. Yes, she thought of that!”(Craigie & Craigie, 1914:343)
周譯文:“凍餓的索索的抖著,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街上窗欞里,都明晃晃的點著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為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咦,他女所想的正是這個。”(周作人, 1919:30)
例1中,安徒生的原文第一句只是平實地描述“她又冷又餓地走在路上,顯得十分無助,可憐的小東西!”。周作人譯本繼承了克雷吉夫婦對原文本的添改,增加了安徒生文本中沒有的“索索的”(shivering)一詞,細化小女孩走路的樣子為“奔走”(與英文“crept along”語意有所不同),以及增加了原文中沒有的語意“窮苦生活的圖畫”(a picture of misery)。這些增譯突出了小女孩悲慘凄涼的形象,也使得對這種境遇并不陌生的中國讀者對小女孩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事實上,這種共情綿延至今,使得《賣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國成為表現童年悲劇的作品,以至于安徒生原文所傳遞的另一種意蘊——宗教和死亡帶來安慰與解脫——被遮蔽和減損。
例2:
原文:“Hankan rigtignok fort?lle!”
中間譯文:“Oh!Hisare delightful stories.”(Peachey, 1908: 49)
趙譯文:“他的故事實在都是些很有趣的故事呢!”(趙景深, 1925: 104)
例3:
原文:“Saa spr?iter han B?rnene s?dM?lkind i ?inene ...”
中間譯文:“... and all on a sudden throwsdustinto the children’s eyes.”(Peachey, 1908: 49)
趙譯文:“……忽然將一把沙子撒在孩子們的眼睛上。”(趙景深, 1925:104)
《鎖眼阿來》譯自英文譯文“The Sandman”,丹麥語題名為“Ole Luk?je”,故事的主要內容是夢神奧列·路卻埃(Ole Luk?ie)為小男孩兒埃爾瑪(Hjalmar)在一周里所講的七個睡前故事。例2是故事開頭安徒生對奧列·路卻埃的評價“Han kan rigtignok fort?lle!”(他真會講故事!),趙景深譯文中評價的對象變成了路卻埃講的故事,顯然是受到皮奇英譯文的影響。這樣的改動使中英譯文都失掉了原文本的互動感和對話性,并且使中譯文顯得有些冗長。
安徒生筆下的奧列·路卻埃原型為西方神話中的夢神(Sandman)。在英國及許多歐洲國家,夢神會在孩子的眼睛里撒一把有魔力的塵土(dust),然后孩子就會進入夢鄉。安徒生在自己的故事里將沙子改成了甜牛奶(s?d M?lk);而也許是為英國讀者考慮,皮奇將這個細節改回了塵土;趙景深的譯文則繼承了皮奇的改動,將英國文化中的夢神形象傳遞給中國讀者。
例4:
原文:“... hun var saa deilig, at Kj?bmandss?nnen maattekysse hende;”
中間譯文:“She was so beautiful that the merchant’s son could not helpkneeling down to kiss her hand...”(Peachey, 1908:310)
顧譯文:“……她是這樣的美麗,使商人底兒子忍不住跪下去吻她底手。”(顧均正, 1925:108)
《飛箱》譯自英文譯文“The Fly Trunk”,丹麥語題名為“Den flyvende Kuffert”,故事中商人的兒子繼承了父親的豐厚遺產之后開始與酒肉朋友們大肆揮霍,最終變得一文不名。一位朋友送他一口箱子裝僅剩的衣物,他發現箱子有神奇的魔力,乘箱飛行時結識了公主。憑借講故事的本事,他先是俘獲了公主的芳心,后又獲得了國王和王后的青睞,最終娶了公主為妻。在這一幕中,商人的兒子乘坐飛箱來到了公主的閨房。在安徒生的原文中,當商人的兒子看到熟睡中的公主時,他忍不住要親吻她(kysse hende),顧均正的譯文將這個動作具體化為“跪下去吻她底手”,顯然是依據了皮奇的譯文。跪下去吻手的行動使得男主人公的舉止更加符合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規范,卻多少失去了些安徒生故事中的天真爛漫。
間接翻譯行為使得中文譯本呈現出某些與英文中間譯本一致的特征,諸如此類的譯例在早期中文譯本中屢見不鮮。有學者評價,維多利亞時期一些安徒生童話故事的英文譯本在語言風格上“追求文學化”(Bredsdorff, 1954:500),略顯“冗長浮夸”而“不太貼近兒童”(Pedersen, 2004:109, 186);在翻譯方法上,對細節增譯過多(同上:109),而對不符合維多利亞兒童文學規范的文字和情節有明顯的改動(同上: 104,186)。由于早期中譯活動采用的底本多為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文譯本,因此也不可避免的維多利亞化,最終使得中國讀者讀到的安徒生更加接近英國文學傳統中兒童文學的樣貌。
如果說間接翻譯影響了中文版安徒生作品的面貌,那么對安徒生作品的間接解讀則進一步加深了對這種面貌的印象。前文勘定的戈斯、勃蘭兌斯及博耶森對中國讀者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安徒生文學成就的評價,二是對安徒生童話故事寫作風格和特點的評價。首先,中國讀者普遍認為安徒生的童話故事代表了其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類似的按語在博耶森(Boyesen, 1895)、戈斯(Gosse, 1890)、勃蘭兌斯(Brandes, 1886)的評論中均有出現,也出現在孫毓修(1913)、周作人(1913; 1918)、鄭振鐸(1925a)等人的評論中。其次,在體裁和寫作風格方面,博耶森、戈斯以及勃蘭兌斯比較一致地認為安徒生童話故事屬于“文學童話”,與取材于民間傳說的格林童話等傳統童話故事相比具有更多的詩學美感(Boyesen, 1895:155);故事不以道德說教為要,有許多“離經叛道”的內容,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同上: 156);同時使用的是兒童的語言(Brandes, 1886:62; Boyesen, 1895:158)。以上觀點在孫毓修(1909)、周作人(1913)、趙景深(1922/2005)、鄭振鐸(1925a; 1925b)等人的評論文章中也多次出現。此外,對安徒生自傳英文譯本的節譯以及對安徒生英文傳記的閱讀也幫助中國讀者構建了對于作家本人的最初印象。不論是安徒生的自傳,還是貝恩(Bain, 1895)等人所著的安徒生英文傳記都傳達了安徒生生于困苦、天賦過人、經過不懈努力最終取得成功的形象,這一形象也廣為中國讀者所接受。最突出的例證莫過于趙景深在《安徒生評傳》(1922/2005)里著重描述了以上三個特點,而在《安徒生童話里的思想》(1925/2005)一文中,安徒生貧苦出身及抗擊命運的生平背景被引作解讀安徒生童話故事的根據。
綜上所述,受到早期間接譯介行為的影響,在中文語境中,安徒生本人是出身低微卻天賦異稟的童話作家,他創作的童話故事充滿同情心、想象力與詩意的美感,作家及其作品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被消解。這些早期解讀對安徒生作品在中國的翻譯、接受以及研究產生了長遠而深刻的影響,使得安徒生譯介鮮有童話故事之外的作品,安徒生研究也長期局限于童話研究。
5.結語
在世界文學場域中,兩個相距甚遠且彼此陌生的文化往往通過間接的方式實現交流,而交流的樞紐往往是某種強勢的中介語言和文化。許多曾處于邊緣地帶的文學作品都經由間接譯介進入世界文學系統并實現經典化,安徒生作品在中國的譯介便是如此。不論間接譯介受到怎樣的質疑與詬病,其在文學翻譯實踐中的普遍存在不應被忽略,其促進文學交流及驅動文學創新的功用也不應被抹殺。當然,實踐者和研究者應該注意間接譯介可能為目的語文化對源語文本的解讀帶來第三方文化的視角和痕跡,這種雙重折射可能使目的語讀者獲得與源語文本讀者不同的閱讀體會及文學印象。這種“偏差”一方面會讓原作變形,使目的語讀者對其產生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讓源語作品獲得世界文學的特性,使其更容易融入目的語文學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的早期譯介和接受也許能為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和推廣工作帶來一些啟發。
注釋:
① 本文所有外文文獻的中文直接引用均為筆者所譯。
② 見安徒生1835年3月16日寫給好友亨麗埃特·武爾夫(Henriette Wulff)的信,全信內容見https://andersen.sdu.dk/brevbase/brev.html?bid=880。
③ 周作人曾在《隨感錄(二十四)》(1918: 290)中提及兩個他認為可靠的全譯本,分別為克雷吉夫婦的英譯本及威廉·曼哈特(Wilhelm Mannhardt)的德語譯本,因此他可能也參考過曼哈特的德語譯本。余祥森1923年在《文藝旬刊》上發表譯文《無畫的畫貼》時曾給出外文題名“Bilderbuch ohne Bilder”,由此推斷他所依據的中間譯本為德語譯本。除此之外,并無更多資料提示還有其他譯者參考了英語之外的中間譯本。
④ 本文所有舉例中的文字加粗效果均為后加,例句原文均來自丹麥國家圖書館網站https://tekster.kb.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