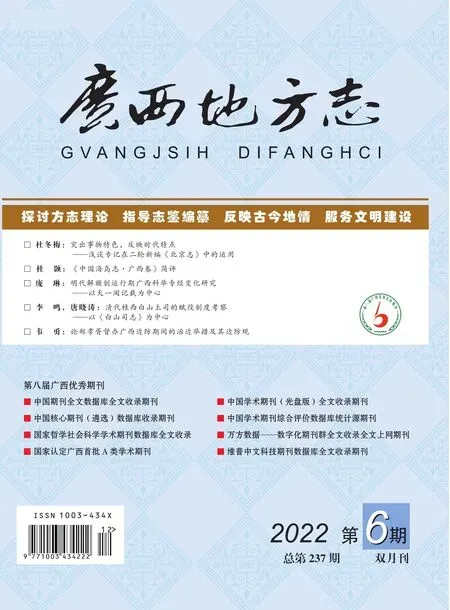倉事記載及其歷史價值分析
——以廣西永安州為例
刁光全
(蒙山縣史志研究中心,廣西 蒙山 546700)
倉,最初為收藏谷類的建筑物,后來與儲藏錢、貨等物資的庫合稱倉庫。倉與人類的關系非常密切,可以說自有人類以后即有藏糧儲物的倉。自古以來,前人已從考古和各個歷史時期及多種角度對倉進行研究。如杜葆仁《我國糧倉的起源和發展》;張顯運《宋代糧倉管理的律令措施》;張建軍《中國古代糧倉的建筑典范——豐圖義倉》;許秀文《淺議南宋社倉制度》等,分別對各種倉的起源和發展、管理律令措施、建筑、制度等進行探討,已經取得比較完善、系統的成果。本文以廣西永安州為例,分析倉事相關記載及其史料價值。
一、永安州志書文獻關于倉事的記載
(一)《永安州志》對倉事的記載
今蒙山縣自唐宋設蒙州和立山縣時,已有州縣志。至明成化十三年(1477)設永安州后至清代,都曾幾次編(續)修《永安州志》,將唐宋以來州縣志資料收錄書中。但“自前明成化始,屢經兵燹,其志遂湮沒無傳”。[1]其中關于倉的記載隨之缺失。目前僅存清代所修嘉慶十七年(1812)版和光緒二十四年(1898)版《永安州志》。
嘉慶十七年(1812)版《永安州志》在卷之五官署中記載:“常平倉,在州署內,康熙十八年知州丁亮工建,三十年知州沈增,雍正六年知州閔家權重建。永阜庫,在大堂西,知州丁亮工建。”說明康熙十八年(1679)知州丁亮工開始把儲藏糧食的官倉改建為常平倉,并建儲存錢幣的永阜庫。
光緒二十四年(1898)版《永安州志》記載:“常平倉,嘉慶初年遷東偏城守衙前。咸豐兵燹后傾圮無存,遞年糧谷仍于州署衙東起倉存儲。”續修該版《永安州志》時,永安州已經歷咸豐年間的太平軍攻占州城戰事和天地會張高友軍戰事,以及其他天地會軍襲破州城搶掠官倉錢糧等戰事。但太平天國把常平倉改設“圣庫”,和張高友軍把常平倉設為“國庫”之事都未提及。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版《永安州志·財用志》載《光緒十七年知州鄧文淵勸建義倉稟》(摘錄):“查常平倉而外,厥有義倉,就地籌備,以便借放,由官曉勸,聽民經理,其法最善。廣西地瘠民貧,倘遇歉收即虞艱食,義倉之設更不容緩。飭令凡已經捐有義谷者,即將建倉處所谷石,實效數經管之倉,正副姓名,免予造冊,準其開單通報,以憑查核立案。其未經捐有義倉谷者,即就地斟酌情形,是否能以一律勸辦。所有存儲民間之谷,經理不得其人,難免挪移侵蝕,亦屬徒有其名。伏查卑州常平倉,咸豐年間地經兵燹,焚燬無存。前經張署牧師仲奉文舉辦義倉,勸諭各里糧戶捐谷存儲,為數無幾。且經管不得其人,難免侵挪等弊。卑職履任,倡捐廉銀二百兩,領作義倉谷價,諭令勸辦。稟定章程,分作上、中、下三戶,量力捐谷儲倉,以備荒歉。將各里捐谷實數,以及倉處所經管紳董姓名,分晰開列清折。捐谷二百石以上者,大憲賞給匾額。茲查卑州告養在籍之黃參將政球,奉諭勸辦義倉甚為得力。其妻蔣氏,操作勤苦,以及奩資所積,存有余粟,自愿捐谷三百石存儲義倉,以為本處備荒之舉。似此好善樂施,實為不可多得。”
(二)蒙山志書對倉事的記載
1.《蒙山縣志》對倉事的記載
蒙山縣,唐宋設蒙州及立山縣,明清時期置永安州,民國元年(1912)改永安縣。民國三年,因當時國內有三個同名的永安縣,改蒙山縣至今。
民國二十五年(1936),蒙山縣政府成立修志局編修《蒙山縣志》,至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僅編成《蒙山縣人物志材稿》和《蒙山縣地理志材稿》。其中《蒙山縣人物志材稿》記載黃涵章倡置路會田設路會戶倉,被永安州府旌表為孝義可風者:“清嘉慶年間黃村富戶黃涵章倡捐資財,倡置路會田,年收租谷千余斤,存現金數百出貸生息,為水竇渡下至藤縣白馬灣七十里內修路架橋之預備,路會碑猶存。”黃村歲貢生黃立林捐資在家中創辦“映雪軒”學館,不征學費。“指定土地垌私產每年租谷八千斤存學倉,助族中貧寒子弟學膳”。
在《蒙山列女傳》中記載:“蔣氏,清副將銜參將黃政球繼室,光緒二十年捐谷三百石存義倉,以為備荒之舉,知州鄧文淵稟請撫院賞給匾額以示優異,民國初年曾經中央政府褒揚。”
1993年版《蒙山縣志·政務志》在“太平天國在永安政權”一節中記載:“太平天國實行圣庫制度方面規定:沒收地主浮財,沒收所有社倉、義倉和州衙的常平倉(今縣人民政府左側處)的積谷。發動農民對地主、豪紳展開清算斗爭;所得果實,部分歸圣庫,部分分給參與斗爭的農民。”
2.《中國共產黨蒙山歷史》對倉事的記載
《中國共產黨蒙山歷史(第一卷)·農民協會的成立》記載:“農會成立后建立農會倉,藉以領導團結農民與地主豪紳作斗爭,使廣大農民擺脫高利貸剝削。在佃戶‘二五減租’所得租谷中統一抽取20%作為基礎,在縣城和各鄉村設立農會倉,簡稱農倉。農倉設立后,由農會公開選舉辦事公道、大公無私的農會會員管理,并設立專門賬本登記數目,定期在農會向會員公布收支情況。每年春荒青黃不接時節,農倉以低息將倉谷借給困難的農會會員及農民渡過饑荒,到夏糧收割后歸還。對資金缺乏的農會會員及農民,農倉借給倉谷作生產資金,購買生產資料發展生產。建立農倉后,農民擺脫高利貸的剝削,使農會更加得到農民的擁護。”
(三)其他史料對倉事的記載
倉事除地方史志記載外,其他史料記載常見的有民間各姓氏家族譜和碑刻等。有的記載較詳,有的則較簡略。但所記倉事,在官修志書中較難看到,可與地方史志的記載一起,形成記載倉事比較完整的資料,而且還可與地方史志互相補充和印證,具有較高的存史和研究價值。
清乾隆三十年(1765)三月二十四日刻《昭蒙兩路修路田碑記》(今存仙回鄉伏龍村黃氏祠堂)記載:“清雍正十二年(1734),仙回里伏龍村黃正衍捐資置修路田,每年租谷存路會倉,維修仙回到永安州官路,每年春秋各修割一次。”
清乾隆年間刻《群峰里路會碑》(原碑已失)記載:“查群峰里水峽口至馬鬃道路常遭水毀,經里人商合,設路會,在古蘆村購置二十四擔路會租田,設會倉由路會管理,每年維修道路,架設橋梁,清除道旁草木,所需費用均在路會田租開支,每年結算,剩余部分由路會股東分紅。”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龍定里三石村關四公祠《祠志》碑記載:“我祖遺龍定二八十甲田糧計租壹千零,眉江二六十甲田糧共計租壹萬壹千零,存祠倉為遽年祭典,余存修葺以及延師于戲……子孫入泮者,獎花紅銀貳兩,補廩出貢者亦幫銀貳兩,副貢幫銀貳兩,中舉拔貢入京助銀八十兩,中進士亦八十兩,以示鼓舞。”
民國十四年(1925)版《蒙山莫氏族譜》記載,莫氏宗祠田產每年收取租谷達30余萬斤存祠倉。田租除修繕宗祠及祭祀費用外,還用作獎勵家族子弟入學與科舉取得功名之用。
1999年文圩鎮木護村《重建古法廟碑》記載:“古法廟清末設上鑒團、上鑒鄉、公益義倉,貯糧數十萬,低租鄉民,架橋修路,興建學校,造福于民。”
二、永安州有關倉事記載的事例補遺
(一)從圣庫記載看太平天國“永安堅守”與突圍原因
清咸豐元年閏八月初一(1851年9月25日),在金田起義后的太平軍攻占永安州城后,洪秀全把州署改設天朝建立太平天國,封“五王”和建立軍制、官制和各種制度。同時,洪秀全頒布《命兵將殺妖取城所得財物盡繳歸天朝圣庫詔》詔令,將城中常平倉和永阜庫改為糧錢圣庫。1993年版《蒙山縣志·太平天國在永安政權》第159頁記載:“太平天國實行圣庫制度方面規定,沒收地主浮財和所有社倉、義倉和州衙常平倉(今縣人民政府左側處)的積谷。”當時永安州城內唯一的儲糧倉庫是常平倉,存錢倉庫是永阜庫。錢財則繳歸永阜庫改設的錢物圣庫,積谷則繳歸常平倉改設的儲糧圣庫。
太平軍在永安建立太平天國后,清廷調集數萬清軍從四面八方進行圍攻和經濟封鎖,意欲一舉消滅太平天國。但只有二萬五千多軍民,作戰部隊僅有五千人的太平軍,卻在永安堅持半年多,始終打敗清軍,得以完成建國封王和建立各種制度,最后勝利突圍北上。除其他因素外,由常平倉和永阜庫改設的錢糧圣庫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一,建立完整的圣庫體系和制度,為太平天國的供給提供保障。太平天國將州城中的常平倉和永阜庫改為糧錢總圣庫后,還在水閗(今水秀)太平軍中心據點中營嶺和東鄉翼王石達開“東王府”駐地各設分圣庫。另外,又在各重要據點設戰地倉庫,形成完整的圣庫體系。在制度上,實行“人無私財,一切歸公,生活所需全部給于圣庫”的公有供給制。為維護圣庫的嚴肅和制度的實行,洪秀全在《命兵將殺妖取城所得財物盡繳歸天朝圣庫詔》詔令中規定:“在向永安州進軍途中,以及攻克州城后所繳獲的財物盡繳歸天朝圣庫,逆者議罪”。
第二,保證圣庫的供給來源。太平天國建立圣庫后,圣庫的錢糧來源,一是常平倉和永阜庫及義倉的原有錢糧。據《永安州志》記載,太平軍北上永安州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州城中常平倉有“倉儲谷九千七百七十六石四斗七升五合”,永阜庫“年征一千二百多兩地糧熟銀”,因連年發生戰亂,稅銀多年未得上交,庫中積銀甚多。蒙山縣志辦編《太平天國在永安資料專輯》記載1958年西街吳宏中提供的資料:“永安城內有個東平義倉,是清朝官府所立,每年收谷幾千擔。太平軍進城后,動用義倉存谷解決糧食問題。”二是采取“上等之人欠我錢”政策,令占領區內的財主富戶捐納錢糧,以及沒收與太平天國對抗的豪紳地主錢糧,充實圣庫。1993年版《蒙山縣志·太平天國在永安政權》第159頁記載:“太平天國實行圣庫制度方面規定,沒收地主浮財和所有社倉、義倉和州衙常平倉(今縣人民政府左側處)的積谷。發動農民對地主豪紳展開清算斗爭,所得果實部分歸圣庫,部分分給參加斗爭的農民……晚造稻谷大熟,太平軍發動群眾搶收財主的稻谷,將財主的田插上標簽,軍民共同收割,所得稻谷與農民均分。”
當時與太平天國對抗的富戶豪族主要有占領區內的莫家村,宗祠田每年收取租谷三十余萬斤,祠倉設在祠堂廂房。南王馮云山駐莫家村莫若璟進士第后,將莫家祠倉內的糧谷全部收歸圣庫;文圩三石村關家祠倉,年收租谷十二萬余,太平軍西王蕭朝貴在三石設據點時,也將祠倉糧谷收歸圣庫。其他較大規模的宗祠倉還有黃、韓、李、陳、梁等姓,都各存儲數萬斤以上租谷,這些姓氏富戶的祠倉都不同程度地被太平軍征收或沒收過倉谷。有代表性的是蒙山縣志辦編《太平天國在永安資料專輯》記載1958年那拉村彭壬昌口述的資料:“富豪村的李九,因為不愿交錢糧,太平軍派人去沒收他家的財產,去挑谷米和財物的共有幾千人,挑了五天五夜。”1960年水秀村何五伯、何祖秀說:“中營嶺山腳是姓孔的財主住的,太平軍攻水秀,孔家躲到城里,留下四百多擔糧谷,全給長毛沒收了。”
第三,頒布天朝田畝制,與占領區內的農民“二五”分成,收取田租。據1993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山縣志·太平天國在永安的軍事活動》記載:“太平軍在永安州的占領區為今蒙山鎮、西河鎮除古排、壬山村以外的全部、文圩鎮的秀才、大明村,面積約一百平方公里。”這些地區內的耕地46300畝,其中水田42000畝。據2008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山縣土地志》記載:“這些水田是永安州境內土地最肥沃,灌溉條件最好的水田。當時稻谷產量是頭造畝產600斤(生谷),晚造400斤。”
太平軍攻占永安州城是農歷閏八月,不久即搶割占領區內的晚稻,42000畝約產稻谷1600萬斤左右。太平軍與農民“二五”分成,太平軍所得稻谷800萬斤,折干谷約600萬斤,加上沒收州城常平倉與占領區內各地義倉、祠倉,以及地主富戶私倉中的稻谷,一共是1700多萬斤。太平軍2.5萬人,按平均每人每月需糧食50斤,月需稻谷125萬斤,年需1500萬斤計算,也可以滿足糧食供應。
食油方面,據《蒙山縣志》記載,清道光至民國,永安州(蒙山縣)每年產茶油30萬公斤,太平軍進城后,征收或沒收州城各街道商鋪中的油料,并用錢與產油區油戶購買,已足夠食用。
食鹽方面,永安州商業倉中的鹽倉為太平軍提供來源起到關鍵作用。據有關史料記載,清康熙六年(1667),黎大年捐資疏通眉江(今水秀)至藤縣五屯所河道,永安州水運得到進一步發展。至道光年間,有從事水運的船只200余艘,其中運鹽商船稱為“鹽船”,沿眉江水道的陳村塘、樟村、平灘、水閗、夏陽壩、州城等碼頭都設有銷售批發食鹽的圩市,并專門設有儲存生鹽的鹽倉。其中以州城的長壽圩鹽倉儲鹽最多,作為戰時或發生洪水災害時食鹽供應的專用倉庫。
太平軍北上永安州前,曾在武宣、象州等地發生因缺鹽軍心不穩的事。咸豐元年閏八月(1851年9月)進入永安州境后,沿途在各圩市購買食鹽。蒙山縣志辦公室1986年編印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在永安資料專輯》記載:“洪軍進入永安時沒有鹽吃,用黃糖煮豬肉。樟村是鹽埠,有幾十萬鹽,洪軍用錢買,一時買不完”。太平軍攻占州城后,城中長壽圩的大鹽倉更成為全體軍民食鹽供應的保障。
太平軍突圍后清軍進入永安州城,發現庫中“米糧油鹽所遺甚多,倉谷未動”。[2]說明太平軍在永安期間,始終不存在米糧油鹽缺少的問題。另外,清軍有關記載也反映出太平軍的糧食和生鹽儲備及配給情況:“(二十四日),東路之勇由紅泥嶺行近永安州城之大教嶺,遙見嶺上有賊炮臺……即將附近賊屋二十余間放火焚燒。內有四間屯谷千余石,一間藏鹽五六百斤,全行燒毀。”[3]文中記載的“大教嶺賊屋”,即太平軍設在大教嶺南炮臺據點的戰地倉庫,正可作為太平天國庫內系統和糧鹽充足的見證。
在太平軍撤離永安突圍北進的問題上,因《清實錄》中有“逆匪占據永安州城,經官兵迭次攻剿,斷其接濟,賊勢窮蹙,于二月十七日丑刻冒雨突圍,由東路奔竄”的記載。成書于光緒十五年(1889)的《平桂紀略》(卷一)亦持同樣說法,故后來太平天國史學界多沿“食盡說”。
距太平軍撤離永安僅46年后編修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版《永安州志》,僅在《兵志第五》中略記城陷時殉難官紳及簡要戰事,對太平軍設“天朝”建國封王、設圣庫,取官庫商庫等史事只字未提。致使太平軍在永安州為何能始終不敗,所設的“圣庫”又在哪里?至今仍成為史學界爭論的問題。太平軍在永安設錢糧圣庫及圣庫制度,進而保證全軍的錢糧供給的史實,正好從各方面回答了這些問題。
(二)常平倉與張高友建立“永平國”
清道光至同治年間,廣西天地會相繼拜臺起義,成為天地會活動的鼎盛時期。發生在永安州,以及外地天地會襲擊永安州城的戰事達27起(次),其中23次打入州城搶奪錢糧。當時社會動亂災害頻發,多地發生災民搶劫官倉、義倉事件。為此,防守力量薄弱的市鎮義倉、鄉村社倉和富戶私倉多不敢儲存錢糧,將錢糧集中或轉移到州、縣城中有官兵鎮守的常平倉。參加天地會拜臺的會眾多是荒年饑民,要找到錢糧活命,只有攻占州縣城奪取官倉中的官銀和糧食。
最有代表性的是繼太平天國之后,清咸豐四年(1854)發生在廣西東部荔浦、永安州(今蒙山縣)、昭平一帶的張高友起義。張高友正是利用災荒之年官府加重賦稅,饑民幾無活路的時機,在荔浦縣城北門圩拜臺起義,并向群眾號召:“愿意參加起義的,發給憑單,到縣倉任取米谷”,得到百姓擁護,饑民蜂擁響應。
張高友起義后,率領義軍八次南下,其中三次攻占永安州城,咸豐九年(1859)正月,張高友在永安州建立政權,以永安州城為“國都”,將州署大堂改為“朝堂”,把城中的常平倉改為“國庫”,取“永享太平”之意取國名為“永平國”,張高友自稱“永平王”,并封五位結拜兄弟為“五虎將軍”。
張高友在永安州建國,一是有四面環水易守難攻的永安州城利于長期固守;二是因為常平倉和永阜庫中有充足的錢糧,可以保證義軍的供給;三是永安州物產豐富,不但可以為“國庫”提供錢糧來源,而且可以作為義軍的基地。張高友在永安建國后,前后堅持斗爭達十一年之久,勢力縱橫十四州縣。與在潯州(今桂平市)建立“大成國”的陳開、李文茂義軍一起,成為太平天國之后,廣西最大的兩股建立政權的農民起義。致使咸豐皇帝驚呼:“粵西賊勢,以平(樂)潯(州)兩處為尤重。”[4]
張高友在永安建立“永平國”時不但將常平倉改為“國庫”,起義后所到之處也是奪取官倉錢糧,一半留作軍餉,一半分給窮苦百姓。咸豐五年(1855),張高友率義軍攻占昭平縣馬江,繳獲團練及富戶錢財,在馬江大竹塘巖洞設錢庫。當時老百姓都躲到山上去了,馬江圩空無一人,義軍買不到給養。張高友采取賞錢趕圩的辦法使百姓回家并趕圩,解決義軍購買給養問題。
咸豐七年五月,張高友攻克昭平縣城,查封府庫錢糧,開倉救濟百姓。張高友建國以官倉改設“國庫”,除在當時有較大影響外,還給當年曾在張高友部下任親兵隊長的永安州人蘇元春在抗法戰爭和建設邊防中極大的啟發。光緒年間蘇元春任廣西提督及廣西軍事督辦,不但在中法戰爭中以張高友傳授的獨特戰法,與馮子材一道指揮清軍打敗法軍。而且直接受張高友的影響,在建設邊防中設錢糧倉庫,以“賞錢趕圩”的辦法移民實邊,使中法戰爭停戰后,法軍始終不敢越邊界半步,成為重要史事。[5]
(三)私放義倉糧米與“三位婦女打州官”事件
光緒二十二年(1896)夏,永安州一帶因發生大旱,米價飛漲,街市無米可買,不少居民被迫賣兒賣女,有的餓死街頭,有的流落外鄉乞討度日。知州江鑒不顧朝廷“官倉負責平準糴糶、調節糧價、賑貸救濟”的規定,將義倉中的糧米私放出關牟取暴利。一邊是百姓瀕臨死亡邊沿的現狀,一邊是州官借荒年中飽私囊的貪欲,終于激起民眾義憤。
據1983年12月蒙山史志辦公室編《蒙山史志通訊》第三期刊登趙培正《三位婦女斗州官》記載:當時州城十八弄有三位婦女,看到州官不顧百姓死活,出于義憤替百姓打抱不平,帶領饑民沖進州衙痛打州官。江鑒被痛打后,被迫打開義倉放糧,街市上始有米糧出售,一州百姓得以活命,史稱“三位婦女斗州官”和“打衙門”。江鑒被打后認為斯文受辱,下令把城東鰲山上的文筆炸倒,將三位婦女處以站刑,行刑處得名“站人塘基”。三位婦女綽號分別叫豹母、老鼠母和芋頭母,人們為紀念她們痛打州官救活百姓,將十八弄改名“三母村”,地名沿用至今。
在封建社會中,掌管一州政權的州官被百姓特別是婦女痛打,是罕見的嚴重事件。在這場因災害導致的事件中,引起官民矛盾的焦點是官府的義倉。編修光緒二十四年(1898)版《永安州志》時,距事件發生僅兩年,官修志書卻“為尊者諱”不記此事。1993年版《蒙山縣志》只在《大事記》中記“二十二年(1896)夏,旱。永安州民餓死及賣兒賣女甚多,饑民聚眾搶劫官府,蒙館晚姐等三名婦女痛打州官”。對江鑒私放官倉糧米出關牟利的違紀枉法行為隱諱不提,所記“饑民聚眾搶劫官府”也與史實有不符之處。
(四)州縣學倉與百姓集體請愿
據清嘉慶十七年(1812)版《永安州志·卷十八·藝文》記載,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趙崇夏任立山縣(今蒙山縣)令,報請昭州府撥銀修復夫子廟兼作學宮,“乃搜括縣籍,得逃戶何納等若干余畝以充學糧”,設學田和學倉,成為本地設學田、學倉之始。學田由學正或州府招佃承耕,令佃耕者交納田租,所納田租有銀兩、谷物等儲存于學倉。
據《蒙山縣志·教育志·學校》記載:“明萬歷四年(1576),永安州知州廖憲在城外立禮街(今中文街原公安局院內)建學宮設義學,增置學田,在學宮中設學倉儲藏學田租谷供義學費用,名為義學倉。萬歷三十七年學倉擴大,改名三學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8),學宮遷進城內,原學宮改為考棚,三學倉仍設在考棚。清嘉慶至道光年間,永安州學田租每年收入租谷二萬四千斤,作為書院院長束修和學童膏火費。其他開支有資助舉人、拔貢、生員入京赴省考試路費和獎學費用等。”
據《蒙山縣志·土地志·解放前土地制》記載:清代,書院田租是“看剪均分,地租均為五成。不但規定用白銀繳納賦租,而且每石加差銀三錢四分,鋪墊水腳六絲。有的佃農交不起地租,被迫以工抵租或被奪佃。為了對抗沉重的地租和奪佃,東平里營潘、夏朝等村的客家人,曾聚眾到衙門請愿”,要求減低地租和不許地主奪佃,很快得到東、西二鄉農民的支持,形成一次載入史書的農民請愿運動。
學倉本屬公益性設施,按當時田租,一般是10%~20%,最高為30%。但永安州官員卻以學田牟利,提高學田租額為“看剪均分”,即50%。沉重的負擔很快引發官民矛盾,使東鄉數千客家人集體到衙門請愿,要求降低學田租。
自古以來,百姓到官府請愿上訪,都屬于地方的嚴重政治事件和社會動蕩的因素。今蒙山縣自南北朝梁天監元年(502)置縣到清朝末年,見于史載的群眾請愿事件僅此一次,為了解和研究地方官府和群眾關系的變化提供史實依據,成為一段具有重要價值的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