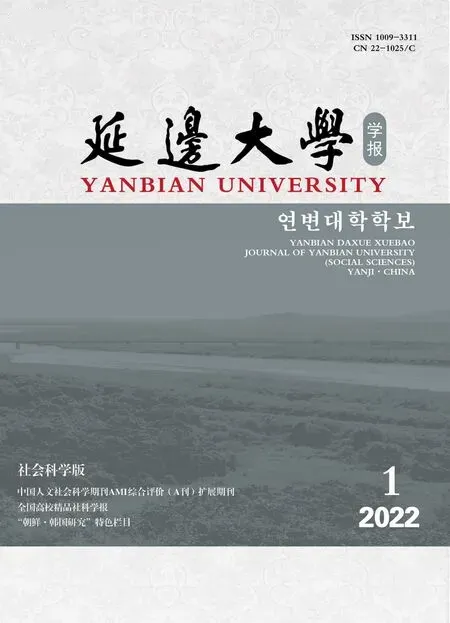高麗時代的災異及其應對方式考略
李 祥 李宗勛
“災異”指自然災害或某些異常的自然現象,是天災地異的簡稱。“災”一般指自然災害,如地震、旱災、水災等;“異”一般指異變,如日食、河水變色、桃李華、牛生馬、鬼哭等。“災”和“異”是不同的概念,但是由于古代認識水平有限,通常將“災”和“異”結合在一起考慮,構成一套系統完整的災異思想體系。(1)上述關于“災異”的概念,據百度百科、naver百科等綜合整理而得。
高麗(918-1392年)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文明古國之一,也是繼統一新羅之后朝鮮半島上又一統一的國家,國祚綿延近五百年,在東北亞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對于高麗的災異及其應對觀念,韓國學者進行了一些研究,但是研究成果還不是很豐富。(2)國外研究方面,參閱[韓]陳英日:《高麗國王和災異思想》,濟州:濟州大學出版部,2010年;[韓]韓政洙:《高麗前期天變災異和儒教政治思想》,《韓國思想史學》第21輯,2003年;[韓]韓政洙:《高麗后期天災地變和王權》,《歷史教育》第99輯,2004年;[韓]李正浩:《〈高麗史〉五行志的體裁和內容——以自然災害的發生趨勢為中心》,《韓國史學報》第44輯,2011年;[韓]李正浩:《通過高麗前期異變現象記錄來看災異觀和危機認識——以〈高麗史〉五行志記錄為中心》,《歷史和談論》第80輯,2016年。國內目前暫無研究高麗災異、災害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以《高麗史》一書中高麗災異記載為中心,對高麗時代災異的類型、特點、影響及相關應對措施進行研究,旨在進一步理解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的災異觀念,對中韓兩國的災異史、災害史研究有所裨益。當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災異已成為人類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而研究古人在應對災異時的一些應災舉措、賑災思想等,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應災防災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高麗時代災異的類型
高麗的災異情況大多被記錄在《高麗史》中。《高麗史》成書于1451年,是朝鮮朝文人鄭麟趾等奉王命編撰的高麗時代的正史。書中記載了大量的高麗災異記事,是研究高麗時代災異及其應對觀念的重要史料。
根據《高麗史》中對高麗災異的記載,可知高麗時代共發生災異7 551次,也即平均每年約有16次災異發生。總體而言,高麗時代災異種類繁多,可以把高麗的災異大致分為天文災異、地質災異、氣象災異、水文災異、動植物災異、社會人事災異、特殊災異7種類型(3)中國學者宋正海將自然災害與異象分為九大科,分別是天象、地質象、地震象、氣象、水象、海洋象、植物象、動物象、人體象。這種分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詳見宋正海:《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詳見表1)。

表1 《高麗史》所見高麗時代災異統計(4)本表及文中出現的高麗時代災異統計數據系作者根據《高麗史》統計所得,特此說明。
天文災異在《高麗史》中有4 694處記載,占了整體災異記錄的62.16%。高麗的天文災異包含日變、月變及星變三大類。其中,“日變”包含日食及與太陽相關的異象,《高麗史》所載高麗475年間“日食”記錄132次,與太陽相關的異象包括日珥、日暈、白虹貫日、日中黑子,共計318次。“月變”包含月食及與月亮相關的異象,《高麗史》所載高麗月食記錄226次,與月亮相關的異象包括白氣貫月、月五星凌犯等,共計1 827次。“星變”包含五星變、彗星流星變、其他星變等。歲星、熒惑、太白、鎮星、辰星在古代被稱為“五星”,《高麗史》記載五星變共計1 405次,其中星晝見195次。《高麗史》所載彗星變121次、流星變756次、其他星變22次、隕石25次、天鳴17次、夜光(夜如晝)7次、夜妖(晝如夜)7次。除此之外,還有五色氣等天文異象386次,具體如下:黑霧、黑云、黑氣、黑祲23次,黃霧、黃赤氣、黃紫氣、黃赤云23次,赤氣、紫氣、赤祲224次,青赤氣、青白氣4次,白氣、白虹、白霧、白祲112次。
地質災異有地震、山崩、地陷等,據史載高麗共有260次地質災異,地震是地質災異的主要表現形式,共有129次。地陷、地坼的記載有5處,如史載:“明宗二十一年(1191年)八月,德水縣地陷,深三丈”。[1]山崩(包含石頹、石落)的記載有50次,許多是由大水所引起的次生災害,如史載“穆宗五年(1002年)六月,耽羅山開四孔,赤水涌出,五月而止,其水皆成瓦石”。[1]此外還有石鳴的記載1處,石自行的記載3處,土堆(沙土)記載1處,如史載:“睿宗十六年(1121年)十一月庚子,王輪寺北岡巖石鳴”。[1]
氣象災異是高麗時代發生最為頻繁的災異現象,有1 940處記載,占了整體災異記錄的25.69%,僅次于天文災異,位列第二位。氣象災異指氣象災害和氣候異變兩種形式,氣象災害有旱災、大風、寒災、大雪、霜雹、雷災、雨災、霧災等。旱災在所有氣象災異中占比最高,共有409處記錄,旱災多被記載為“旱”“干旱”,有時也會以“不雨”的方式記載。這樣的記載有11處,如史載:“毅宗二十三年(1169年)四月辛卯,雩,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1]除此之外,還有風災136處,寒災、雪災68處,霜災44處,雹災190處,火災170處,雷電327處,雨災137處,霧災195處,木冰(木稼)122處,虹見42處等。可見,旱災、霜災、風災、雹災、雷電是高麗時代發生率最高的氣象災異。氣候異常指不符合自然規律的氣候現象,包括無雪、無冰等,其中無雪17處、無冰16處,如“睿宗九年(1114年)十一月,無雪”,[1]“睿宗十六年(1121年)十一月,無冰”[1]等。此外,還有極其怪異的氣候現象被記錄,有雨土48處、雨白毛6次、雨谷2處,如“肅宗九年(1104年)七月戊戌,雨谷于通海縣”。[1]
水文災異指水災和水文異象等。水災在史料中又被稱為“大水”,有關高麗“大水”的記錄有46處,京城、京西、京畿等地均發生過大水,如史載:“毅宗元年(1147年)七月戊辰,京畿大水,人馬多溺死”。[1]水文異象包含“水異”和“水變色”。水異指井水、池水、江河水等水涌、水涸、水濁、水沸、井鳴等,這樣的異象共計15處。水變色包含水黑3次、水赤9次、水黃2次、水白2次,如史載:“康宗二年(1213年)三月,東海水赤如血”。[1]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地鏡”(地上積水如鏡)現象,共出現4次,如史載:“毅宗五年(1151年)六月乙丑,西京梯淵至普賢經坊地鏡見”。[1]
動植物災異分為動植物災害和動植物異象兩類。高麗時代最主要的動植物災害是蝗災,記錄有22處。蝗災是“威脅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生活最嚴重的三大自然災害之一”。[2]其次是松蟲害,《高麗史》中“蟲食松”記錄有21次。除此之外,《高麗史》關于動植物的異象記錄有331處,其中動物異象305處,包括龍蛇變9處、魚變5處、馬變6處、豬變7處、(鵂鹠、雉、群鳥、烏、鶴、雀)變100處、羊變1處、雞變4處、鼠變1處、虎兔獐變147處、狗變2處、(蟾、蚯蚓、蜂、毒蟲、蟻)變11處、螟變2處、牛變10處。植物異象26處,包括花開13處、僵樹自起7處、枯樹復生2處、珊瑚樹2處、木實隕1處、樹自顛1處。動物異象既有常見的動物異象,如史載:“忠定王三年(1351年)十一月己酉,三豬入城”。[1]也有傳說中動物的異象,如史載:“元宗二年(1261年)四月丁巳,太子行至西京,黑龍見于大同江”。[1]植物異象如史載:“忠惠王元年(1331年)十月,桃李華”。[1]桃李冬季十月開花,顯示氣候變暖,顯然不符合節氣。另有“樹鳴”,這類怪異現象2處,如“明宗二十五年(1195年)正月癸巳,西京監軍使廳北榆樹自鳴,凡十余日”。[1]
社會人事災異指瘟疫、饑荒等社會人事災害和社會人事異變。關于人的瘟疫方面的記錄有8處。瘟疫一般多發生在冬季和春季,同時多伴有旱、饑等其他災異,如史載:“元宗三年(1262年)十月,京城大疫”。[1]《高麗史》中有關饑荒的記錄多達30處,可見高麗時代受災異影響導致民眾出現饑荒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有的時候甚至達到“人相食”的地步,如史載:“恭愍王十年(1361年)三月,龍州饑,人相食”。[1]社會人事異變方面,有“顯宗十年(1019年)十一月丙子,鸚溪坊民崔老妻一產三男”。[1]這種古代醫學解釋不了的“多胞胎”現象也被劃入異象記載。這樣的記載多達14處。除此之外,還有象頭自落忽亡2次,鐘鳴13次,哭聲、鬼嘯各1次,服妖1次,門自頹14次,鐵佛流汗1次,訛言20次等這樣的社會人事異象記載。
特殊災異。本文認為祥瑞與災異是密不可分的。祥瑞象征君主德政、天下平和,是上天對君主施仁政得民心的褒獎,《高麗史》指出“吉者休征之所應也,兇者咎征之所應也”。[1]這里把祥瑞稱為休征,災異稱為咎征。祥瑞是一種特殊災異。可見研究災異不能離開祥瑞。《高麗史》所載祥瑞總共20處,占比僅0.26%,包含瑞草(瑞芝、朱草)2次、連理木2次、卿云1次、白雉1次、白鵲1次、白鸛1次、玄鶴1次、白獐1次、嘉禾(穗變)7次、老人星2次、壽星1次等。按王代劃分,顯宗3次,太祖、成宗2次,睿宗2次,光宗2次,禑王2次,定宗、景宗、文宗、肅宗、仁宗、毅宗、恭愍王各1次。可見祥瑞多集中在高麗初中期幾個王時期,高麗34個王中,有祥瑞記錄的僅13個王,仁宗之后,連續12個王均無祥瑞記錄,尤其末代王恭讓王不僅沒有祥瑞記錄,有關災異的史料記載竟多達137條。
二、高麗時代災異的特點
爬梳文獻記載,高麗時代的災異呈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就地區而言,高麗災異發生的地域具有空間范圍的廣泛性。比如《高麗史》所載高麗“大水”災異46處,其中明確提到地點位置的記載有31處,具體如下:京城、都城4處,西京1處,西北路1處,密城郡等1處,禮成江1處,九龍山2處,奉恩寺1處,清州4處,東界1處,京畿1處,靈通寺1處,松岳4處,川邊1處,東京符仁寺1處,西京妙德寺1處,安邊府1處,洞鳳二州1處,定長等六州1處,三洲、天磨山1處,淮陽1處,慶尚道1處等,其余未提到地點的只是記載了災異的類型及時間等有15處。已標明區域的和未言明發生區域的災異則證明高麗災異地域的廣闊性。
第二,高麗時代的災異具有多樣性特征。高麗時代的災異包含天文災異、地質災異、氣象災異、水文災異、動植物災異、社會人事災異、特殊災異7種類型。天文災異分為日變、月變和星變,地質災異有地震、地陷、山崩等表現形式,氣象災異包含旱、風、雪、霜、雹、火、雷等自然災害及無雪、無冰等氣候異常,水文災異包含水災、水文異象等,動植物災異分為動植物災害和動植物異象等,社會人事災異包含瘟疫、饑荒等,特殊災異包含17種異象變化。
第三,從危害程度看,高麗時代的災異可分為一般災異、較重災異和嚴重災異。一般災異只記載災異的時間、地點和類型,如“(高宗)四十三年(1256年)七月庚寅,都城大水,多漂沒人家”。[1]對于災異,史書上如有“發倉賑給”等則視為較重災異,如“(睿宗)四年(1109年)正月,以西京驛路百姓饑饉,發倉賑之”。[1]而如有祈禳或民饑、人相食等的,則視為嚴重災異,這種災異通常是久旱引發的蝗災、饑荒以及瘟疫等,如“(恭愍王)十年(1361年)三月,龍州饑,人相食”。[1]
第四,高麗時代的災異具有明顯的持續性和群發性。持續性是指一定的年代段內,部分災害持續幾年在同一地區不斷發生。群發性是指許多自然災害,特別是等級高、強度大的自然災害之后,常常誘發次生災害的接連發生,[3]如旱災往往伴有蝗災、水災之后常出現旱災、冬季無雪引發瘟疫等。現以《高麗史》仁宗元年至五年(1123-1127年)所見災異情況為例進行分析(見表2)。

表2 《高麗史》仁宗元年至五年(1123-1127年)所見災異統計(5) 表中史料據《高麗史》世家卷第十五“仁宗一”和《高麗史·五行志》整理所得,特此說明。

續表2 《高麗史》仁宗元年至五年(1123-1127年)所見災異統計(6) 表中史料據《高麗史》世家卷第十五“仁宗一”和《高麗史·五行志》整理所得,特此說明。
從表2中可見,1123-1127年這短短的5年間,與五行之水、火相關的災異就有20次。平均一年就有4次災異發生,這一時期的災異呈現出天文災異、氣象災異、水文災異、動植物災異循環發生的樣態。可見,這一時期內高麗災異具有明顯的持續性和群發性特點。現代地理學也認為,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生物圈、人類圈是一個互相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其中任何一個圈層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圈層的變化。[4]
三、災異對高麗社會造成的多方影響
災異的發生給高麗社會帶來多方面的影響。學者鄧云特認為:“災荒嚴重發展的最主要結果,就是社會的變亂。而所謂社會變亂的主要形式,不外乎人口的流移死亡,農民的暴動和異族的侵入。”[5]高麗作為東北亞古國之一,其受到的災異影響大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眾的大量死亡或流徙。雖然史書中僅有“有死者”“死者多”等只言片語,沒有準確有效的數字,但從史籍記錄的內容來看,高麗因災異而導致民眾死亡或流徙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有的民眾因為疫情而死,如“忠烈王七年(1281年),疫,死者甚眾”。[1]另外,大水導致的人口流徙情況同樣嚴重,如“顯宗十七年(1026年)九月己酉,西京大水,漂毀民家八十余戶”。[1]據此可知,因災異而導致人口流徙,大量民眾在水災、地震中流離失所。不僅如此,因饑荒而造成“人相食”的事件,如“恭愍王十年(1361年)三月,龍州饑,人相食”,[1]甚至還有父母“食其子”的事件發生,如“忠烈王十三年(1287年)三月,全羅道饑,人或有食其子者”。[1]災異對高麗民眾人倫觀念造成巨大沖擊。
第二,農業生產受損。學者鄭功成認為災害問題的實質是經濟問題。[6]高麗農業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很大。災異對高麗農業生產造成極大影響。高麗時代因災異導致農業生產受損的情況不勝枚舉,具體見表3。農作物的減產、糧食歉收是災異帶來的直接結果。高麗農業生產災害中,主要是霜、雹等災害,一般在七八月份比較嚴重,并且有時伴有嚴重的饑荒。表3中有關高麗農業生產受損情況的記錄,只是實際情況的一小部分,不難看出,災異對高麗農業生產的破壞是難以估量的。

表3 高麗農業生產受損部分情況統計
第三,嚴重威脅高麗社會的穩定。災異引發的高麗社會問題,多表現在因災異引發的農民起義上。因為災異,農業生產遭受破壞,農民饑寒交迫,勢必揭竿而起。鄧云特曾如此描述:“農民窮乏與饑餓,既達極點,流移死亡的現象,繼續擴大,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普遍起義,勢不可免……農民起義,往往逐漸醞釀,愈演愈劇”。[5]因饑荒引起“盜賊峰起”甚至農民起義,在高麗歷史上普遍發生,嚴重威脅高麗政權的穩定,如史載:“恭愍王十年(1361年)四月,西北面大饑,盜賊蜂起”。[1]此外,高麗佛教活動慘遭破壞,如史載:“睿宗十七年(1122年)十月癸丑,大風雨雹,震開國寺塔”。[1]佛寺、佛塔遭到破壞,佛教活動無法正常進行,也不利于整個高麗社會秩序的穩定。
第四,外力的侵入,學者鄧云特認為:“災荒之延長,消磨民族內在之力量,內力不充,外力遂得以侵入,此尋常之理也”。[5]災異造成高麗社會經濟矛盾急速激化,民族的內在抵抗力完全喪失,外力趁機得以侵入,如史載:“恭讓王二年(1390年)六月戊寅,太白晝見,己卯亦如之。楊廣道觀察使報倭賊入寇,議修山城”。[1]
四、高麗時代的災異應對方式
(一)災后的補救措施
1.政治上的應對措施
災異嚴重威脅高麗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災異發生后,統治者在政治上會采取一系列應對舉措。
第一,“責己”“避正殿”“減常膳”。君主表示接受上天的警告,通過“責己”“避正殿”“減常膳”等方式祈求災異的結束。“責己”,如“成宗八年(989年)九月甲午,彗星見,赦,王責己修行”。[1]“避正殿”“減常膳”,如“顯宗八年(1017年)九月,旱、蝗,王避正殿,減常膳”。[1]
第二,祈禳。災異發生后,統治者會通過祈雨祭等儒教的方式進行應對。古人認為大旱是因王的“不德”引發的,通過實施祈雨祭等向上天祈禱。高麗國王則通過祈始祖廟、祈山川、幸佛寺等多種方式祈雨,如史載:“睿宗元年(1106年)六月,旱。戊子,祈雨于法云寺”。[1]有時候因為災情特別嚴重,需要徙市、畫龍祈雨,如“宣宗三年(1086年)四月辛丑,有司以久旱請造土龍,又于民家畫龍祈雨,王從之,是日徙市”。[1]在重大災異發生時,依靠宗教力量祈雨,則成為應對災異重要的救災形式之一。借助佛教力量,如“睿宗元年(1106年)七月庚寅朔,召王師德昌講經,祈雨”。[1]舉行道教的醮禮,如“明宗十七年(1187年)五月,京城大疫,命五部設道符神,醮以禳之”。[1]祈禳儀式時一般要設佛教、道教的消災道場,如“明宗九年(1179年)七月壬午,月犯太白,太史奏:‘避正殿,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十日以禳災變’”。[1]除此之外,還有祈雪、祈晴的儀式。祈雪,如“顯宗七年(1016年)十一月丙辰,祈雪于群望”。[1]祈晴,如“靖宗元年(1035年)五月甲辰,祈晴于川上”。[1]由此可見,祈禳常為統治者所重視,已成為高麗統治者應對災異的一種途徑。
匯總本文數據,所有數據均經過SPSS20.0版進行處理,兩組高血壓伴心力衰竭患者的血壓水平與生存質量評分均以均數差表示,用t檢驗。若P<0.05則代表兩組數據比對差異具統計學意義。
第三,施德政。面對災異,君主應及時調整統治政策,施行德政以順應天意。據史載:“明宗十六年(1186年)正月戊子,歲星犯右執法,已亥,月有冠兩珥。二月丁丑,太史奏:‘歲星自乙巳十月守太微,至十二月十五日退行,至今年二月丁巳犯右執法,實為咎征,請修德銷變。’”[1]又如:“光宗元年(950年)正月,大風拔木,王問禳災之術,司天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常讀《貞觀政要》”。[1]有時候災異發生時,大臣通過上疏的方式向君主“問政得失”,規勸君主施行德政。據史載:“顯宗十二年(1021年)六月,東北界蝗,七月癸酉,教文官常參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1]有的大臣認為災異的發生是國家沒有賢才的緣故,希望國王征賢納士以贏得民心,如史載:“仁宗二十三年(1145年)七月,……太史奏曰:‘今蝗蟲四起,此乃國多邪人,朝無忠臣,居位食祿如蟲,宜舉有道之人,置之列位,以弭其災’”。[1]又如,“恭愍王九年(1360年)秋七月乙丑,司天臺以天文失序,請征賢用士,行科舉”。[1]
第四,赦免。這是以國家命令的方式減輕或免除對罪犯的刑罰,赦免主要有大赦和錄囚兩種方式。大赦作為國王固有權力是對犯罪者全面解除正在執行的法律效力或對審判結果確定的刑罰減刑,即赦其罪又赦其刑的制度,[7]如史載:“成宗八年(989年)九月甲午,慧星見,赦,王責已修行”。[1]錄囚也是高麗時代應災的重要方式之一,如史載:“靖宗十一年(1045年)三月丙子,以谷雨節降霜錄囚”。[1]通過赦免,國王可以樹立權威,減輕財政支出,增加勞動力,有利于災后生產的恢復和社會矛盾的緩和,特別是災異時可以抑制難民的產生,減輕災異的危害程度。[7]
2.經濟上的應對措施
除了政治上的應對措施之外,還有一些經濟上的應對舉措。(7)中國學者史柏年認為,中國古代災異救助的政策與實踐大致可概括為養恤、蠲緩、賑濟、貸賑、工賑、安輯等方面。詳見史柏年:《社會保障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國學者鄧云特把中國歷代救荒政策概括為消極和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包括賑濟、調粟、養恤、除害、安輯、蠲緩、放貸、節約,積極方面包括重農、倉儲、水利等。高麗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消極救災措施是臨災時的治標之策,有賑濟、調粟、養恤、除害四項。
第一,賑濟。賑濟是指國家打開倉庫,對因自然災害中受到損害的民眾無償地給予救濟的方法。賑濟一直是經濟應對舉措中最直接、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應對方式。[8]從整個高麗歷史來看,賑濟主要有賜谷、賜物和發使開倉等形式。賜谷、賜物,如史載:“文宗六年(1052年)三月,又以京城饑,命有司集饑民三萬余人,賜米粟鹽鼓以賑之”。[1]對災民賜谷、賜物,說明高麗君主十分重視賑災工作。發倉賑濟是賑濟中最為直接、普遍的救助方式,一般多在饑荒之后實施。“顯宗三年(1012年)五月,教曰:‘去年西京,水旱為災,谷價騰踴,民用困乏。朕夙興夜寐,念之惻然。其令所司發倉賑之。’”[1]這是高麗史上首次發倉賑濟災民的記錄,此后靖宗、文宗、宣宗、肅宗、睿宗等都有發倉賑濟的記錄。
第二,調粟。移民就粟。“高宗四十六年(1259年)正月,城中饑,人相食,移昇天府,給糧與田。”[1]移粟就民。“文宗六年(1052年)四月,移龍門倉粟八千石于鹽、白二州,以給農民……文宗八年(1054年)四月,又移春、交、東等州倉粟給種食。”[1]平糴。“忠烈王六年(1280處)五月,是月旱蝗,元中書省牒加糴米一萬石。”[1]減糴。“恭愍王三年(1354年)六月,以年饑,發有備倉粟減價以市民。”[1]
第四,除害。據《高麗史》記載,高麗時期共發生嚴重“蟲食松”事件21次。松蟲取食松葉,常把松葉吃光,松林似火燒狀,造成成片松林死亡,給林業資源造成損失。高麗政府積極組織民眾“捕松蟲”,如史載:“恭讓王元年(1389年)五月乙亥,蟲食松葉,乙未,令重房率五部人捕松蟲”。[1]
除了上述四項臨災治標措施之外,在經濟應對上的災后補救措施還有如下四項:
第一,安輯,即安撫。這是對因災異而受損的災民進行安撫的一種舉措,包括王親撫慰和遣使安撫存問等不同方式,這也是高麗經濟應對舉措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其中遣使安撫存問是安輯災民的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如史載:“文宗八年(1054年)五月,制:諸道州郡,民多饑歉,流移失業。令諸州通判以上官吏巡行存問”。[1]
第二,蠲緩,即免除或暫緩征收租稅或徭役的形式。蠲緩在高麗災異史上較為多見,也是高麗政府應災的一種方式,也證明高麗統治者對災異應對舉措足夠重視,如史載:“光宗二十六年(975年),景宗即位,蠲欠債,減租調”。[1]高麗政府通過減免租調形式緩解災情,但此法多發生在偏遠地區,使用范圍較為有限,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災異問題。
第三,賑貸,即由政府貸給災民耕牛、種子等,以助其恢復生產,如史載:“恭愍王五年(1356年)丁丑,籍萬戶洪瑜家,以米千石賑貸貧民”。[1]“(恭愍王)十一年(1362年)夏四月庚寅,發龍門倉谷一萬石,賑貸京畿饑民”。[1]“顯宗二十二年(1031年)五月,令公私貸民谷米者,只取其本,蠲其息”。[1]賑貸與之前的臨時救災對策不同,是一種“恒式”的保護措施。頒行之后,“內外大悅”。在通常情況下,國家會多種政策并用,以緩解災情,穩定社會秩序。
第四,節約,減少食物。“古時君主,每遇饑荒,往往即下詔減膳,用示節約克苦,且常以身作則,為天下倡”。[5]史載:“忠穆王四年(1348年)二月,置賑濟都監,王減膳以充其費”。[1]災異發生,君主表示接受上天的警告,通過“減常膳”祈求災異的平息,很明顯,高麗君主的應對措施體現出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禁止釀酒。學者鄧云特指出:“歷代禁酒,概由于年谷不登,其馳也則以豐稔,蓋釀酒靡費糧食,實不可以量計。故歷代每遇饑荒,輒禁釀酒,以資節約糧食。”[5]據史載:“忠穆王三年(1347年)四月辛丑,監察司以旱,禁酒。”[1]禁屠宰。據史載:“文宗元年(1047年)四月癸亥,王以自春不雨,避殿,輟常朝,斷屠宰,止用脯醢,令中外慮囚。”[1]停建工程。據史載:“仁宗八年(1130年)四月,旱。戊子,詔再雩祈雨。太史奏:‘……宜當兩京內外公私罷土木興作之役。’從之。”[1]這反映君主如大興土木,會招致災異,體現出一種節約的思想。鄧云特的《中國救荒史》也認為“節約”是消極救荒政策中災后補救政策之一。
(二)災前的防災措施
比起災后的補救措施,災前的積極防災舉措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災害一旦發生,其對農業生產的損害是最為嚴重的。高麗關于災異的積極防御,主要針對農業生產,體現在勸農、倉儲、興修水利等方面。
第一,勸課農桑。針對自然災害帶來的糧食歉收等情形,《高麗史》中的記載體現出重農意識的災異預防思想,如史載:“德宗三年(1034年)三月庚辰,教曰:‘農桑,衣食之本。諸道州縣官勉遵朝旨,無奪三時,以寧萬姓’”。[1]史籍中也可見各種勸農、歸農的記載,如史載:“高宗十二年(1225年)夏四月戊戌,禁內外興作,勿奪農時”。[1]“顯宗十六年(1025年)三月己丑,白氣貫日,庚寅,停諸營作,放農民”。[1]統治者以政令方式勸勉百姓回歸農事,足以證明高麗政府對以上防災措施的高度重視。統治者也很重視農田的保護工作,如史載:“肅宗六年(1101年)夏四月庚申,割平虜鎮關內楸子田與民耕之”。[1]
第二,倉儲備荒。高麗統治者也很重視倉儲備荒工作,據史載,早在太祖時期,就設置黑倉,賑貸災民,至“成宗十二年(993年)二月,置常平倉于兩京、十二牧”。[1]常平倉的設置,“饑不損民,豐不傷農,誠救荒之良法也”。[1]
第三,興修水利。水利建設也是預防災異的重要舉措之一。碧骨堤是新羅時期著名水利工程。據《與地勝覽》所載《碧骨堤重修碑文》記載,高麗顯宗時依原貌重修碧骨堤,并于仁宗二十一年(1143年)、二十四年(1146年)再次增修。仁宗后,高麗歷代國王又多次增筑碧骨堤。通過興修水利,有效地防御了水旱災害,減輕了災異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損害。
高麗統治者在政治上、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應對災異,構成了災前防御、災中救助、災后恢復的災異應對體系。應災舉措有效解決與緩解了當時的災情,高麗災異的應對能力也日趨提高。
五、高麗時代的災異觀
高麗時代災異頻仍,通過這些災異,可以考察高麗人的災異觀及其對統治階層決策的影響,并通過與中國歷代史書中的災異觀比較,考察其異同。考察高麗災異觀,離不開對中國儒教陰陽五行觀的分析。中國的災異觀由來已久,在《左傳》《春秋》《公羊傳》中都有災異方面的記載。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理論,之后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傳》,劉向作《洪范五行傳論》,劉歆又對劉向的《洪范五行傳論》進行了補充和修改,最為重要的是《漢書·五行志》將災異和五行聯系起來,第一次在官方正史中運用陰陽五行說對災異進行解釋。《高麗史》所載高麗災異記事,明顯深受《宋史》《元史》等中國正史的影響,特別是《高麗史》專門設置了《五行志》,《高麗史》的《五行志》序言部分與《元史》的《五行志》序言部分高度相似。《高麗史》還按照五行思想把高麗災異進行歸類并解讀,而肅宗元年(1096年)夏四月癸酉,中書省奏章對《洪范五行傳》《京房易傳》又大段引用,可見高麗君臣對陰陽五行說的熟悉程度。由此可見,高麗的“陰陽五行觀”明顯受到中國災異思想的影響。
高麗作為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災異觀作為一種儒家政治觀念,同儒學一同傳入高麗。“仁宗八年(1130年)七月辛亥,暴風拔木,雷電震五正里人家松木,太史奏:‘……齋祭修禳,不足以消變,愿殿下省躬修德,上答天譴’。從之”。[1]結合史實,仁宗八年是1130年,剛好處于“李資謙叛亂”之后、“妙清叛亂”之前高麗王朝這一段政治動蕩期。因為災異頻仍,太史提醒仁宗注意反省修德,上答天譴。可見高麗人已將災異與政治聯系在一起進行解讀,這顯然深受中國災異祥瑞說的影響。但是,高麗災異觀也有與中國災異觀不同的地方。例如,“明宗十年(1180年)辛丑,有氣如煙,生廣化門左右鴟尾……或者謂:‘此非煙也,蓋蚊虻聚飛使然,不足怪也。’重房喜,令太史局祀之,太史乃阿其意曰:‘飛蟲也。’識者恨之。”[1]這里的“煙氣”,依據中國災異觀的解讀是不吉之兆。而高麗太史顯然根據自然的變化用未來指向性的方法進行解釋,將災異解釋為祥瑞。可見高麗固有的土著信仰對高麗的影響很大。由此可見,高麗時代的災異及其應對觀念,顯然受到董仲舒“天人感應”和“五行五事”災異學說的影響,但是與中國的“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論”略有不同的是,高麗時代對災異的解讀還受到高麗自身固有觀念的影響,呈現出一套獨具高麗特色的系統完整的災異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