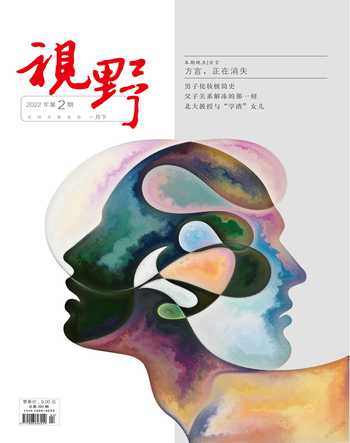遺忘的方言,老去的故鄉

1
“如果你從未認識過一個西北人,你的人生多多少少有點不完整。”跟我說這話的人是甘肅定西人,我大學的homie老張,他說他們那個地方是蘭州的鎖鑰,甘肅的斯大林格勒,整個西北的梵蒂岡。
那時我才剛上大學,什么都不懂,對大西北的印象只有窯洞。
老張用前后鼻音混淆的普通話說沒關系,讓我來幫你打開大西北的大門。
我說你這個手勢,像是大西北要走我的后門。
那兩年里,老張的確讓我認識了一個非刻板印象中土氣直爽的西北人,他帶我聽冷門樂隊,在廣場舞里跳秧歌,吃蘭州牛肉面。
他嘆了口氣:可惜這里不正宗,有朝一日你來西北,吃一吃正宗的牛肉面,嘗一嘗啥叫毛細啥叫二細,再喝一喝啥叫三泡臺,兄弟,我跟你講,在滾滾黃河大水車旁喝完一杯茶,五千年的傳承就一瞬間從天靈蓋上拍了下來。
我說真美。
他夾走了我的牛肉,然后迷離著眼神,在煙霧飄渺中輕嘆:西北偏北,羊馬很黑,你飲酒落淚,把蘭州喝醉。
后來畢業了,臨走前那天我喝多了,他也喝多了,他紅著眼眶跟我說,一想到要跟你分開,唉太難受了,扯著嗓子就給我唱了首花兒民歌。
我也敏感地表示,想不到每個西北人都會花兒,我一定要去西北,去看看滾滾黃河,把蘭州喝醉。
他猶豫地說,其實我也不會,只是氣氛到了,為你們特意學的。
我說那牛肉面一定要吃。
他說倒也不必跑那么遠,樓下這家的確是蘭州人開的,我每次請你吃這個就為了省錢。
還有每次開學我回你的特產,我說這是我們土豆之鄉定西的特產,也就是從門口超市里買的普通土豆。
我大怒:合著你他娘的是真的為了蹭我飯,我還以為你家特別貧困呢!他又笑了:哎呀,不要帶著刻板印象嘛,西北人也可以炒股致富嘛。
臨走前,他教我一句話,發音是:集組色日涅。
這句定西話的意思是,你永遠是我的好兄弟,是我一生至死不渝的好友。見到定西人,你就可以講。
我說我怕你又騙我,更怕西北人打我。
他搖晃了手指,唉,你可以不信我,但請相信黃河,相信大水車。
2
后來我真的循跡去了甘肅。
認知世界的途徑,有時候是從認識一個人開始,一同經歷了事,最后對這個人背后的土地感興趣,因此留下了對這個符號的深刻記憶。
只是他當初跟我說的那一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死活找不出答案。
那年我坐著火車沿著西安向西,一路植被稀疏,整個天空毫無遮攔地被太陽染紅,任由它溶進戈壁遠端的地平線中。
稀疏的雜草被風吹得擺動,我才意識到這是古來征戰無人回的西北,這是雄渾遼闊的西北。
火車上有個定西大叔,他挑著泡面說小伙子第一次來西北啊,我突然靈光一現想起了那句西北話,他眼睛一亮,然后泡面的手一抖,回復我,他在泡面呢。
我重復了一遍,他又說了一遍在泡面,我們一來一回許久,他終于失去了耐心,說你是不是有病,我不是說了我在泡面嗎,你還問我在干啥。
我笑了,我又被這小子耍了,他在臨走前,又給我開了個玩笑。
在此之后,我每次聽到西北口音,都會想起那片雄渾的土地,和土地上滿是活力的人。我回想起車上那位大叔,他聽到老家口音的那一刻的舉動,也是仿佛一瞬間回到了家鄉,想起了西北老家里的人。
我的一句方言,就成了穿越時空,穿越空間,將他與老家聯系起來的文化符號。
這樣短短幾個字,也成了我和老張的一個暗語,每當我說起時,就會回想起當年的荒唐胡鬧,和年少時的人。
思考了很久之后,我明白了方言的意義——它是熟人社會的特殊語言,更是用來傳情達意的情誼附著體。
舊時我們生活在一個鄉土社會,人們生于斯,長于斯,互相有機地團結在一起,村社之間友愛互助,以親戚和鄰居的形式互相幫襯,語言和動作被簡單化,最后凝聚出的特殊語言元素,叫方言。
再由方言相同的一群人,構成了特定的地區性文化、習俗。
代代相傳,形成了群體性記憶。
可土地的承載力有限,終將有勞動力外出,成了一個個游子。
這時方言的作用愈發彰顯,哪怕兩方不認識,憑借著共同的方言就能夠迅速達成共識,雙方能夠延續熟人社會的情誼互幫互助。
這時語言很難說僅僅是一個溝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它背后凝結著鄉情,喚醒了你對一片土地的認知,和游子最需要的歸屬感。
你會說某地方言,你愛某片土地,或許你不是本地人,但你能感受到熟人社會的情誼。
所以他鄉遇故知,是一大喜事,因為對面人開口說出方言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在逃離孤獨。
3
我們需要方言,但也需要面對的一件情況是,方言正在消亡。
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說,文字是間接的說話,且是一個不太完善的工具。
語言只能在一個社群所有相同經驗的一層上發生,群體越大,包含的人所有的經驗越繁雜,發生語言的一層共同基礎也必然越有限,于是語言趨同簡單化。
工具用得少,就會被淘汰,冷門的工具,更是如此。
隨著時代的變化,熟人社會不斷被打碎,游子外出變多,歸來的卻越少。盡管我們交流溝通得越發頻繁,留給方言的世界卻越少了。沒有人讓我們張開嘴說方言,也沒有人讓我們回憶起熟悉的土地,喚醒那片久違的情誼。
我們總會覺得孤獨,是因為我們總以游子的心態,在陌生的環境中生存,用文字和普通話溝通,方言無處使用,那一份情感紐帶便越發成了一條纖細的線。
現在有沒有感受不同方言的機會?
有,短視頻。
在互聯網文字時代被抑制的方言們,正在短視頻時代迅速重生。
我在抖音上特別喜歡看一位叫冰洋江子的用戶的內容,她也是定西人,她的父親會在炎熱的午后用大蓋碗喝茶,興起時唱起一首民歌,這一首歌唱起時,我一瞬間想起了老張,想起了大西北,想起了他跟我說的黃河和水車。
文字還需要努力構造的環境,短視頻中西北方言出嘴的那一刻迅速就復現出來,再結合上直播這個新形式,千里外的景象實時構建在我面前。
這種傳遞效率的提升,讓更多人迅速共情。
如今抖音舉辦了一個很有趣的挑戰賽,叫“西北方言大挑戰”,短時間內已經達到7698萬次的播放量,在隨后開啟的“花兒一唱美滴很”專場直播中,更是在一眾知名花兒歌手的演唱下,聽到了正經地道的西北民歌。
打開挑戰賽標簽,一個個或段子、或配音、或探店的視頻,迅速刻畫出了西北宇宙下的熟人社會家長里短飲食起居,也在打破著對一個地區人的固有的刻板印象。
這是短視頻時代的紅利,它要求人們展現不同,人們在文字時代的基礎上,能夠用本土文化進行填充,方言有了土壤,就自然能夠在這個過程中在手機端復生,游子能通過最短時間最低成本找回那個熟人社會。
而這時我們再來看,這個過程由抖音來做,其實是水到渠成。
它擁有6億多日活,這些人組成了一個橫貫東西,從上至下的微觀社會,短視頻這種形式已經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人們樂于在其中分享生活,通訊交友,比起電視上唱方言民歌這種形式,方言在短視頻之中融入得更好,就算存在著傳遞的門檻,創作者的語言動作及字幕,都能將具體含義完美復現。
抖音拉低了表達門檻,就會有無數西北人通過視頻傳遞內容,成為優質內容創作者,將方言用最快捷的方式分享出來。
這些人,就能塑造出一個熟人社會,而熟人社會帶來的溫暖,正是每個人都缺的。
或許你聽不懂西北方言,但是你看過《山海情》,喜愛那片厚重的土地,你有情感需求,你就是潛在的西北方言愛好者,就能夠通過短視頻了解一種方言。
比起以往人、事、環境這樣的方式,我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也更加高效。
進一步講,當刻板印象被打碎,方言有了環境能夠傳遞時,那更多本土、小圈子文化就得以傳承。
以往我們總提花兒和少年,但是我們不懂,也沒興趣了解。但是短視頻時代塑造了獨特的文化環境,就讓這些文化能聽,能懂。
就像是前段時間抖音流行的內蒙呼麥,現在抖音直播中的花兒也在傳唱間火了起來,知名的花兒歌手馬俊、張存秀 、嚴美穎等人能夠將技藝以最日常最舒服的方式對我們展現出來,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有了關注,活了下來。
以往文化遺產最缺傳遞渠道,現在有了抖音短視頻這種高效渠道,就能夠傳遞。
這是文化傳承中的一件好事。
歌手們、內容創作者們能發聲,他們也會為了給這個渠道更好地提供內容而不斷精進,自我實現。
手機對面的愛好者、游子們,也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溫暖,尋回鄉情,找到了那條根。
我愿稱之為互聯網時代的人性關懷,真實,不假。
4
在看完挑戰賽內容,定期瞅瞅花兒直播的這幾天里,我其實舉一反三,聯想到了許多內容。
許多小圈子文化、鄉情文化,缺的不是創作者,而是被看見。
以往我們受制于一個環境中,對遠處不了解,但是當這些小圈子文化、鄉情文化在短視頻環境中逐漸成長精進后,就會讓你看見,讓你了解。
西北如此,花兒、信天游、呼麥等火了;那抖音就可以同樣幫助西南的山歌、東北的曲藝、福建地區的游神民俗傳承下來。
在這個趨勢下,文化能夠得以保護傳承,用最輕松最歡快也是最有力的方式交流溝通,刻板印象被打破,我們也可以從愛好者,成為半個那里的人。
了解,傳承,下一步就可以提發展。
總有一天,你可以去那個耳濡目染的地方好好看一看,對那里的區域經濟來說,就是無限新商機。
七八年前,我要認識一個定西人,要通過兩年的時間交朋友,認識那里,然后坐著綠皮火車去喝一杯三泡臺。
現在,我在休息的間隙中,被某地的人的方言逗的哈哈大笑,要是有一天得閑時,就可以飛過去好好看看。
這個距離更短,愛好者,傳承者,地區經濟,平臺,四贏。
這是短視頻真正做到的事情,我可以確定的是,或許有一天短視頻會被更高階的形式打敗,但是不得不承認,在這個階段內,短視頻的確讓更多人參與了進來,讓更多逐漸式微的文化,傳播了出來。
這是吶喊,也是回響。
還是游子忘不掉的故鄉。
(摘自微信公眾號“半佛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