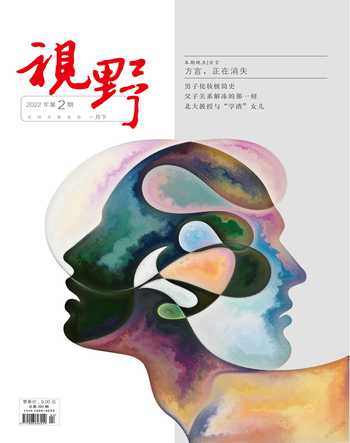一個(gè)小縣城的方言,為什么成了13億人使用的普通話?
盛博 朗博

要說(shuō)普通話最標(biāo)準(zhǔn)的,莫過(guò)于《新聞聯(lián)播》里每天出鏡的播音員了。誰(shuí)想說(shuō)好一口能和他們相媲美的普通話,不下足功夫是不行的。然而,你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國(guó)有這樣一個(gè)小鄉(xiāng)村,普通話就是當(dāng)?shù)氐姆窖浴?/p>
也就是說(shuō),這里的老人小孩,不用后天刻意學(xué)習(xí)就個(gè)個(gè)能說(shuō)普通話,且發(fā)音標(biāo)準(zhǔn),吐字清晰,圓潤(rùn)流暢,韻味十足,水平堪比播音員。
現(xiàn)在,大部分人認(rèn)為的普通話,就是北京人的方言,但是這個(gè)看法并不準(zhǔn)確。北京人的普通話與《新華字典》里的發(fā)音其實(shí)是有一定區(qū)別的,最明顯的就是那股 “京城味”,兒化音特別多。
而普通話最標(biāo)準(zhǔn)的發(fā)音,其實(shí)來(lái)自這個(gè)地方——與北京一山之隔的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
這還得從一個(gè)真實(shí)的故事講起:
1953年春,在灤平第四完全小學(xué)讀書(shū)的14歲同學(xué)白鳳然,突然被老師叫到辦公室,辦公室里面坐著兩位來(lái)自北京的神秘人物。
神秘人物讓白鳳然別緊張,只要按要求讀報(bào)紙中的一篇文章即可。白鳳然就按照平時(shí)在家里說(shuō)話的語(yǔ)氣,大聲朗讀起來(lái)。然后,他們又讓他讀了一篇語(yǔ)文課文。讀完以后,兩個(gè)神秘人物連連點(diǎn)頭,讀得真好啊!
接著,還有另外三名同學(xué)被請(qǐng)來(lái),給神秘人物讀了幾篇文章。
除了這些同學(xué),這兩位神秘人物還先后在金溝屯鎮(zhèn)、巴克什營(yíng)鎮(zhèn)和火斗山鄉(xiāng),找了三名村民,也是一樣的要求——說(shuō)話、朗讀。
這幾個(gè)神秘人物就是中央政府政務(wù)院派來(lái)的語(yǔ)言專家,他們來(lái)灤平是為了考察采集取音,為制定通用語(yǔ)言規(guī)范收集資料。
不過(guò),讓白鳳然他們想不到的是,他們的語(yǔ)音竟成為日后普通話的標(biāo)準(zhǔn)發(fā)音,大家尊稱他們?yōu)椤罢Z(yǔ)音七老”。所以,灤平方言發(fā)音最接近今天普通話的標(biāo)準(zhǔn)讀音。
60年后,白鳳然再次被選中成為語(yǔ)音采集對(duì)象之一,74歲的他每天凌晨在地下錄音室要錄音四個(gè)多小時(shí)。
今天,灤平人的一口普通話,使很多年輕人在北京及各地都做了播音、話務(wù)員工作。
看到這里,有人會(huì)奇怪:為什么偏選灤平方言為普通話的發(fā)音基礎(chǔ)呢?
600年前,明朝永樂(lè)時(shí),那個(gè)從自己侄子手里奪來(lái)皇位的朱棣,由南京遷都北京,大批操著南京口音的官員、士兵來(lái)到北京,南京口音與元朝的老北京口音慢慢融合,就形成明朝的北京話,這也是當(dāng)時(shí)官話。
朱棣為了防止北方蒙古人的進(jìn)攻,將古北口外的居民和軍隊(duì)全部撤回長(zhǎng)城以內(nèi)。所以,在長(zhǎng)城外形成了大范圍的軍事隔離無(wú)人區(qū),而灤平就處在這個(gè)無(wú)人區(qū)的最南邊。從此,灤平再?zèng)]有人居住,原來(lái)的方言就消失了。
清朝建立后,滿人入主北京,開(kāi)始積極學(xué)習(xí)漢文化,也學(xué)說(shuō)北京話,不過(guò)其中也加入了滿族語(yǔ)音要素。
所以,清朝的北京話實(shí)際上包括了元朝北京話、南京話以及滿族話三種發(fā)音的特點(diǎn),集眾家之長(zhǎng),這種口音當(dāng)然具有優(yōu)勢(shì)了。
康熙帝時(shí),建了避暑山莊,灤平就成了北京與承德之間的重要通道。清政府鼓勵(lì)旗人建立“口外莊田”,于是,很多旗人來(lái)到肥沃的灤平,建起莊園。
畢竟是皇家莊園,豈是一般平民能隨便出入的地方,再者,灤平地區(qū)交通不便,相對(duì)封閉,與外界隔絕,正是這種環(huán)境上的優(yōu)勢(shì),讓灤平人那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得以完整保存下來(lái)。
而北京則因受到外來(lái)人口影響,加上清末民初的社會(huì)動(dòng)蕩,經(jīng)過(guò)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北京人生活及其語(yǔ)言都發(fā)生變化,這時(shí)候北京話反而不如灤平口音純正了。
新中國(guó)成立之初,國(guó)家要建立一套通用語(yǔ)言規(guī)范體系,經(jīng)深入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灤平的北京話最純正,于是就有了文章開(kāi)頭的灤平采音的故事了。
說(shuō)到這里,聰明的讀者就明白了,所謂的普通話其實(shí)就是官話,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語(yǔ)言。灤平的方言,正因完整保留了首都所在地——北京的語(yǔ)言,所以才被國(guó)家選入普通話。
那么,如果按這個(gè)規(guī)律來(lái)算,中國(guó)古代歷朝的普通話又都是什么呢?
中國(guó)各朝代官話多次更變,因定都、政權(quán)變遷等因素在不斷變化,都城在哪里,哪里的話就是當(dāng)朝官方語(yǔ)言,它代表著至高無(wú)上的皇權(quán)。這也方便于各地人的互相交流溝通。
西周社會(huì)是古代中國(guó)文化制度的奠定時(shí)期,西周首都洛陽(yáng)話就成了當(dāng)時(shí)的標(biāo)準(zhǔn)音。西周的“洛語(yǔ)”,就成官語(yǔ),美其名曰“雅言”,它也是以后中國(guó)各朝代國(guó)語(yǔ)的基礎(chǔ)。
秦朝后來(lái)統(tǒng)一全國(guó),具體用什么語(yǔ)言無(wú)法考證,據(jù)估計(jì)就是西安一帶的關(guān)中話了,至于怎么發(fā)音,可以參考陜西的秦腔。
劉邦推翻了秦朝,當(dāng)然不能以“秦人之腔”為官話國(guó)語(yǔ)了,漢朝就承襲先秦時(shí)代的“雅言”,洛語(yǔ)是兩漢的普通話了。但可以想到,這發(fā)音一定有關(guān)中語(yǔ)的特點(diǎn)。
到了南北朝的時(shí)候,東晉遷都建康(今天的南京),承襲漢代,還以洛語(yǔ)為國(guó)語(yǔ),洛語(yǔ)與中古吳語(yǔ)結(jié)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稱“吳音”,為南朝沿襲。南京話就成了國(guó)語(yǔ)了,開(kāi)始登上了歷史舞臺(tái)。
隋朝統(tǒng)一中國(guó),定都長(zhǎng)安,以南京話和洛陽(yáng)話雅音為基礎(chǔ)正音,形成長(zhǎng)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西安話“秦音”就是國(guó)語(yǔ)了。
到了宋朝,定都河南開(kāi)封,與洛陽(yáng)不遠(yuǎn),所以,國(guó)語(yǔ)還是“雅音”洛語(yǔ)。
元朝定都北京,定蒙古語(yǔ)為國(guó)語(yǔ),元代的普通話恐怕是充滿蒙古味道的北京話。
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南京官話為官方的標(biāo)準(zhǔn)語(yǔ)。后來(lái),他兒子朱棣遷都北京,從此,北京話就一直成為中國(guó)的官話了。
從整個(gè)歷史看,今天的普通話可不是現(xiàn)在一個(gè)地方的方言,它的發(fā)音兼有洛陽(yáng)話、西安話、南京話、蒙古語(yǔ)及滿語(yǔ)等多種語(yǔ)言的發(fā)音元素。
灤平的方言其實(shí)就是中國(guó)主要朝代各地方不同官語(yǔ)融合而成的,所以才能被全國(guó)廣大地區(qū)人接受,因含有不同地方發(fā)音特點(diǎn),也容易上口。
因?yàn)閺闹形覀兠靼琢酥袊?guó)的文化為什么具有活力,能夠綿延不絕。
就單從普通話發(fā)展歷史來(lái)看,今天的普通話就是各地方語(yǔ)言兼容并包的結(jié)果,因吸引眾家之長(zhǎng),具有各地區(qū)廣泛的代表性。
整整經(jīng)過(guò)了三千年,華夏各地域的人不斷摒棄地方文化不足與狹隘,不斷地吸收其他地方文化精髓,才融合成現(xiàn)在這個(gè)偉大民族。
今天,這樣的融合說(shuō)來(lái)起簡(jiǎn)單,但是有誰(shuí)能知道當(dāng)時(shí)不同地域和文化經(jīng)歷了怎樣激烈的沖突和碰撞的,也不知道經(jīng)過(guò)多少血與火的洗禮……在多災(zāi)多難中,我們的文化淬煉得愈加堅(jiān)韌。
(摘自《世界華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