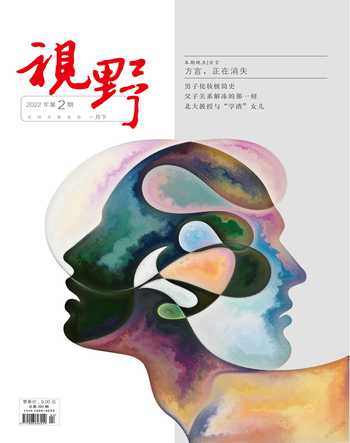深目如愁
張宗子

大約從漢朝開始,直到唐代,詩文里頭,“愁胡”二字經常出現。字典上解釋說:胡人深目,狀似悲愁。最早出自東漢辭賦家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于上楹,儼雅跽而相對。……狀若悲愁于危處,憯顰蹙而含悴。”晉人孫楚在《鷹賦》里把這個意思縮為一個詞:“深目蛾眉,狀如愁胡。”以后就成為習語,用來形容鷹眼。老杜詩中屢次寫到,如《畫鷹》:“?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我們家的人,稍有點高鼻深目,我上學時,屢被開玩笑,說是西域人,甚至巴基斯坦或阿富汗人。畢業的留言簿上,各種開玩笑的比喻里頭,多的就是卓別林和普希金了,除了眉目,還因為兩人都留著小胡子。而我那時候,以為胡子越刮越旺,一直不敢刮,便成了這樣的結果。在紐約,幾次被誤認為別的族類,令人哭笑不得的一次是,盛夏某日走在公園附近略偏僻的路上,被一個中年女同胞跟了很久,后她快步趕上來,鼓起勇氣用中文問了一句:“你會說中文嗎?”我說會啊。她釋然:想問路,打量半天,覺得你是老西(南美人),不敢開口。其實人到中年,身上假如有過一絲半點的異域特質,也讓幾十年讀過的子曰詩云淘洗得差不多了,加上歲月的恩賜,眼睛也漸漸混濁起來。
以后想起深目如愁的說法,覺得很有趣。深目為何給漢人以悲愁之感?至今不得其解。在王延壽的賦里,胡人形象畫在宮殿高處,看上去,他們仿佛因身處險危而驚恐不已。后來的引申如果都由此而來,不過一尋常典故罷了,我還是覺得“狀似悲愁”更有意味。凸睛予人滑稽之感,老家方言形容某人暴怒或強橫,說“翻眼努睛的”。眼皮大翻,眼球鼓出,怒氣勃發,咄咄逼人,細想之下,卻有漫畫的效果,不是兇,而是可笑,就如鼓脹著肚皮的青蛙一樣。眼睛垂下,讓人覺得安詳和可敬。目光投向遠處,讓人覺得似近而遠,直至遙不可及。眼眶稍深,屏蔽了光線,雙眸退隱,好像站在洞口看端坐在山洞深處的人,不免留下懸猜的細節。這些未知的事物,不可能一一表達。
李白在《上云樂》里描寫過神話一般的胡人:“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戌削風骨。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睹詭譎貌,豈知造化神。”不是尋常胡人,更像得道的番僧,像是從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里走出來的。李白說胡人之貌“詭譎”,他自己若是胡人,或有胡人血統,一定不會覺得胡人的長相怪異。
晉代的阮孚,字遙集,這個“遙集”,就出自王延壽的賦。《世說新語》里有他的故事:阮仲容喜歡姑媽家的鮮卑丫頭,姑媽搬家到外地,曾說要把那位已有身孕的姑娘留下,結果走的時候忘了這事,還是把她帶走了。仲容聞訊,借了一頭毛驢追趕,把她追了回來。仲容說:“人種不可失。”可不嗎,姑娘懷著他的兒子呢。這個鮮卑丫頭,就是阮遙集的母親。阮仲容大名鼎鼎,乃是竹林七賢里的阮咸,李白所謂“三杯容小阮”中的小阮。《阮孚別傳》里講:“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鮮卑人身材較高大,皮膚白。唐代的美女,以長白為上,也許正反映了鮮卑人的審美觀。這個阮孚,不知形象如何。看寫真畫上同樣有一半鮮卑血統的唐太宗,可以想象出大概。唐太宗應該也是深目的吧,雄姿英發,哪里有一點悲愁的影子。
唐人酒器中有一種行酒令的酒具,叫酒胡子,造型為一碧眼卷發的胡人。行令時,讓酒胡子旋轉,停止轉動時,它的手指著哪位客人,那位客人就要飲酒。酒胡子的面部造型夸張,給人滑稽之感。唐三彩中騎駱駝的胡商,彈琴歌唱,其樂融融。唐代胡人形象的藝術品很多,神態莊重甚至悲苦的當然也都有,但觀看者先入為主,一說胡人,不是怪異,就是滑稽。就連詩中常用的“愁胡”二字,也僅僅是一個比喻,和字面的“愁”字沒有關聯。
我喜歡唐三彩,無論馬還是駱駝,都剛健明朗,胖乎乎的貴婦人和神貌恭敬的小文官,不卑不亢,快樂而自信,就連一臉諂媚表情的太監,身上也沒有險惡之氣。和唐人的馬相比,徐悲鴻的馬太急于表現一日千里的雄駿了,而唐人的馬一昂首,就是“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的豪邁。唐三彩里的駱駝,是大漠的驛車,是不沉的沙海之舟,更是一個歡樂的游樂場,常見五六個胡人各執樂器,坐在駝背,不問天荒地老,只管歡歌笑語,散襟暢懷,哀愁何在?此處的胡人,如同傳奇中的神仙,成為自由生活的象征。
(丁丁摘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