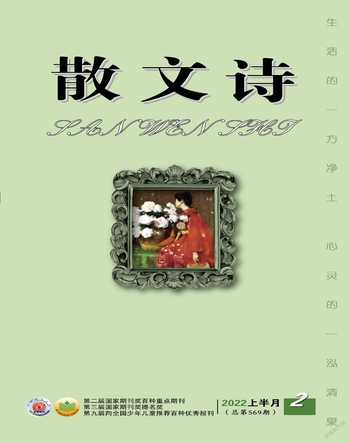自然敘述
江錦靈

春 泥
對泥土的深耕,必然先行握緊春風的犁鏵。
春風一路走低,一路吹拂泥土。
春風與泥土一相逢,便完成世間最美的相遇——春泥。
泥土是她,春風是他。他們,成就古典且綿長的佳話。
春泥,是簡約的復數,是相濡以沫,是渾然一體,訴諸于春天,給這個加長版的蜜月奠基。
早已超越季節。從華美的外殼出走,以春天的身份作掩護,瞥見過烈日的覆巢、凋葉的歸宿、冰雪的腹地。
時而逡巡在繁華的外圍,在鄉村,乃至荒涼之境,執著為一片花園,或花園的藍圖,不斷消解自己。
同時,也豐盈自己。
玫瑰與牡丹固然美麗,不如傾情于野薔薇、狗尾草、蒲公英的夾敘夾議。
春風,是一把萬能鑰匙,從容地打開板結的嚴冬。
系于鑰孔的流穗,順帶厘清門檻的殘雪。又似柔韌的墨條,研磨于新泥的硯臺。
草木以春泥的彩料,或工筆地,或寫意地,把江南岸皴綠,鵝黃還給嫩芽,堅冰換回絲雨。每一處無聲地綻放,皆能掀起春天的風暴。
柴
火的素材。鍋的謂語。粗茶淡飯前傳的艱辛敘述。
鍋,已忘卻柴的執著。柴本身,遺忘了體內的燈火。
一座山,越發不習慣砍柴人的缺席。樵夫,把柴刀丟失于時間的溝壑。
當下的語境,防火更甚,防盜式微。
火的舞蹈,只偷偷摸摸彩排。柴的水袖是火。灶堂,是坍塌的舞臺。火鉗緘默銹的皺紋。
火柴,把火柴盒躺成墓碑。
米
不得不脫下鎧甲,奔赴挨家挨戶的食欲與愿景。
一枚枚微型的梭子,穿梭于生活的機紓,編織于晝夜的經緯。多少肉身被織進時光之錦。
歲月的布匹,描繪喜怒哀樂的紋理。
米,穿越數千年的火候,依然是米,依然最大程度恪守糧食的德行和風度。
無論面對什么容器,皆可為家。
無論面對什么炊具,都可長成飯粒。
無論面對什么胃,都能卸下鋒芒和堅硬。
無論面對什么風,都可以濾出特有的甜。
米香,氤氳于鄉愁的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