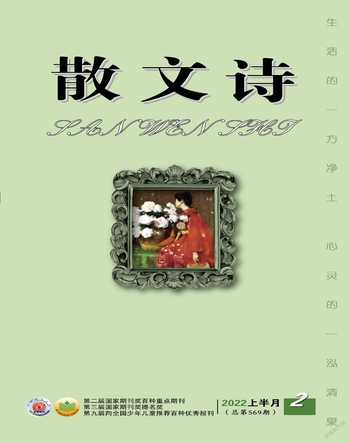詩是最后的身份標識 (一)
草樹

一 聽聞有客從遠方來,主人趕忙迎至門口。樹枝上傳來喜鵲喳喳的叫聲。貓在瓦楞上悄行,忽然安靜了。大黃狗先前狂吠,此刻停下來,甩著尾巴,在主人的腳邊來回打轉。
招呼。握手。遞煙。將客人延請進屋。
這是遙遠的鄉村記憶親切的一幕。它其實可以替換,比如將喜鵲的喳喳換成門鈴的音樂;握手遞煙一類動作,可以換成女主人躬身打開鞋柜,拿出拖鞋;至于狗,換成孩子吧,他總是第一時間沖出去,急切地打開門鎖。
如果孩子接受父母反復的教導,站在門口大聲地問:“誰?”那也不過是一種身份核實。現代城市生活的復雜和封閉,使身份的辨識艱難起來,要稍稍多費一點口舌。
一首詩的到來,和那門外來客,很有幾分神似。
主人和客人之間,總是有熟識的基礎,或親戚,或朋友,其關聯是有人生的一段經歷作為針腳的。不過,詩人對前來拜訪的客人,是有相當感覺的。這位客人或許很久不露面了,或者新近才來過,又一次到來,是那種不見不能釋懷的親密使然。偶爾會有不速之客,陌生,突然,但它對于詩,與其說是一次唐突的來訪,不如說是一種神秘的饋贈。詩人只有誠懇,熱情,以家常之道款待客人,才是正道。家是人類的歸宿地,是靈魂的庇護所。常是常規,長久,常態,秩序,是“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常(《荀子·天論》),是天命。詩人為天地立心,為世界守常,在一個語言之家,以家常之道,為心靈持存那瞬間到來的晦暗不明的事物,以形象呈現,以文明之,文明便不斷升高它的大廈。
詞語當然需要申明身份,身份明了才不會導致疑慮。那聲音是親切的、熟悉的,就不需要孩子反復核實,甚至立即激起一種愉悅的情感。因此,一首詩首先是一種默契的交流,包含一顆坦誠的心。來就茶杯向天,不來就茶杯鋪起,那不是待客之道,不是詩人的態度。
只要真誠,毋需炫耀。告訴客人你如何如何把碗盞清洗了一番,說明碗盞上的污垢會如何如何對客人造成不恭,即便不是矯情做作,至少也缺少一種坦誠實在的精神。
客人作何感想?一直尷尬站立,還是進門入座?
客人落座。事物有了存在的形式。這一把椅子,有它的此時此刻絕對的位置,但它又并非是絕對的——在客人離去之后,你可能在隨后的打掃活動中挪動了它。因此存在是一個“being”,是“是”的進行時,并且需要一個時空的坐標系方能清晰地標注。它之所在,是在這所房子里有一個確定位置,而這所房子,又是以海平面為起點測定的海拔,即縱坐標和從我們的歷史、傳統的某個點引來的橫軸坐標所確定。此時,是過去、未來和現在的此時,是共時性的此時。詩有了時空交叉的現場,就有了存在的基本前提。同時它是對話性的,建立在主客坦誠親切的交流之上。詞語承擔了某種明晰性的使命,好比椅子,既支撐了客人的各種坐姿,又以自身的力量和客人的體重達成平衡。
此平衡是測量,是稱重。
如何按照人體力學原理制作一把更為人性化的椅子,是一個木匠的技藝所在。詩人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木匠。過多談論木匠的技藝是一種撒嬌的行為。椅子的制造工藝是常識。在這個層面上言說,把詩歌作為一種方法,以談論詩學本身的形式去編織語言的織錦,并不是以關乎存在為主的。阿什貝利是詩歌史上所謂關于詩歌的詩歌的寫作者,作為一個語言的主人多少有些饒舌。
當代詩人有相當一部分采用這種模型來建構自己的詩歌大廈,不論是寫作主體高調出場,還是將觀念小心翼翼潛藏于意象背后,都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種腔調。這種腔調帶有某種排他性,也顯示出藝術上一種潛意識的顯擺姿態。
不是關于制作椅子的技藝如何精湛留住了客人,而是清晰的身份和親切的情感使相聚成為愉快的經歷。
詞語召喚。形象涌現。時空位移。這一切都發生在熱情和專注之中。在存在的門廳附近逡巡,從詞語繞道詞語,詩最終會消隱于現象的宏闊蕪雜或知識的陳詞濫調。
二 中國大部分農民一輩子的理想就是建一棟氣派的、屬于自己的房子。沒有房子,何以安居?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農民建造房子,廣泛地采用了城市那種套間式結構。這無疑是一種文明的標志。不管它們的外形仿歐還是仿古,無一例外在房屋正中保留了一間堂屋,在堂屋正中設置了神龕。
中國鄉村的建筑沒有忘記給神——如果說逝去的先輩也是神的話,或至少是家神——留一個位置,給禱告、紙錢和香案留一個位置。這樣,從爺爺到父親,從父親到我,一代又一代站在神龕下,躬身作揖,敬奉先祖的語調和形式,得以保留。一些詞語最初的聲音在這里得以延續。
詩歌的建筑當以詞語的鐵鍬去挖掘,為基礎的建立做好準備。挖掘,通常會碰到石頭、沙子等干枯堅硬的事物,也可能遇到蚯蚓、泥蛙等靈動的東西,但是,最為動人的時刻,是到了一定深度,泥土開始濕潤,空氣變得清新,泥土氣息越來越濃烈。水,汩汩而來。
它是深藏于大地的,那偉大的傳統的汩汩涌出。在那里,當挖掘的行動停止片刻,一個最新的平面形成了。你俯身,可以看見自己的臉;你用舌尖嘗一點,它沒有半點腐朽之氣,味道甘洌清新。
沒有哪一個詩人能夠和傳統割裂,傳統蘊藏著語言的血脈。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詩人們站在語言的最前沿,不斷地創新和發展著傳統。
當然,這汩汩的水,也可以隱喻時代。在“我”的深處,時代和“我”交匯了。唯有經過身體之井過濾的時代,從現象的蕪雜中剝離了,就像剝開的煮雞蛋一樣富有質感。
當貴州高原的一座大型水庫將淹沒一個古老的縣城之時,那里的決策者在新址規劃了一個典型的帶有苗侗文化色彩的新城,每一條街道都以吊腳樓和青石板等元素構成。居住在新城的人們,迷失在自己的家鄉——因為,他們每次回家都要站在街口仔細辨認,外鄉人更是進入了一個八卦城堡,因為,在那里除了門牌號的不同,再也找不出可以區分的特征。在這樣一個地方是不可能演繹奧德修斯的神話了,記號和神秘,都被一種功利性的專制力量抹掉了。
建筑風格最終決定于個人的喜好,但對于一座城市來說,它更可能是意志和欲望的產物。整齊劃一,或對民俗文化的粗暴圖解,留存了符號卻抽離了基因,制造了共性而抹殺了個性,已經不能形成風格,而是淪為了某種意識形態的空洞形式。
風格的多樣化是一種民主精神的內在彰顯,一方面最大可能地接近自然,像春天,百花齊放,色彩紛繁;一方面它具備了足夠的辨識度,允許個性的共存。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一塊分路碑是善和救贖之渴念的標記,而一條條面目趨同的街道是一種簡單的專制和暴力。
對于棲居在大地上的人類,建筑是擋風遮雨的庇護所,也是精神的、靈魂的庇護所。家以建筑為主要形式,無論鄉村民居,還是城市按照一定規劃要求建設的小區住宅。但是,現代建筑要成為真正的庇護所,仍需要在雙層真空玻璃窗上開啟另一扇窗,在帶有指紋鎖的門上打開另一道門。一個詩人扶窗遠眺,是另一種看。他(她)將觀看人之不看。詩人在詩的意義上的回家,是一種構建,在那晦暗不明的林中路,栽上一塊塊指引靈魂的分路碑。
每逢佳節,父親在堂屋神龕下禱告。他的聲音與其說接近宗教,不如說更接近詩。以禱告和問卦,實現和祖先的交流。他的語調也許可以追溯到《詩經》時代。除了一代代延續,還有什么能存留莊嚴虔誠的語調?
詞語。詞語以一種適當的形式,可以存留傳統的聲音和語調。語言是綿綿不絕的。語言的割裂就是傳統的斷裂、血脈的斷裂。人最終在詩中,辨認自己的身份和認領生命的來路。
傳統是一個死去的龐然大物,但它有活著的詞語。任何一個詩人不能和傳統割裂。反傳統不過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叛逆姿態。優秀的詩人一定會為傳統自覺保留一個像堂屋里的神龕那樣的位置,傳承語言的血脈。
古典主義永遠不會過時。
三 當代詩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市,或許有一部分來自鄉村,依然保留著鄉村生活的記憶,但是,其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大部分人口還將不斷向城市集聚。如果說城市生活已經成為現代文明的沃土,那么農耕文明,不過是村口樹梢上空巢里空洞的風聲。
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大量樹木的“移民”,小鳥也飛來了,它帶給我們鳥鳴的早晨,就像當初住在鄉下一樣。但是,夜晚的狗吠,遠山磷火的閃爍,以及螢火蟲的飛舞等等,已不復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密集的建筑物和喧囂的汽車,擋住了它們的路徑。也許因為天賦,小鳥比人類更容易尋找棲身之所,而人要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必須首先在現代性的土壤上種植屬于我們自己的作物。現代性不是洪水猛獸,不是高樓大廈,不是地鐵和BRT,也不是霓虹和KTV,而是摩天大樓之間那蓬勃生長的、我們時代的最新自然。
人類的聚居使得秩序的維護空前增加難度。交通標識,綠地上的警示牌,密密麻麻紅白相間的鐵樁,三角形的鐵制車位鎖,公共空間的絞盡腦汁的溫馨提示,凡此種種,都試圖規范人的行為,但是,現實仍然令人憂慮。我們總能看見車站的不銹鋼圍欄上翻越的人影一閃,或者草地上一朵花驟然迎來一只大腳。
更多的混亂來自于資源的爭奪。
人脈資源,自然資源,土地資源,信息資源,等等,在這個時代,一切都成了資源——連知識青年最初下鄉的地方也成了旅游資源。
耶穌臨世,布道于世上。他是上帝之子,沒有生存之虞。生存固然會強化愛,但更極大程度會異化愛。上帝賜食物于飛鳥,卻要求人類以自己的雙手去創造。創造,源自人性最基本的欲望和最高級的沖動,帶來了世界的萬千奇觀,但是,也使人在精神上淪為了秩序的踐踏者和混亂的制造者。耶穌受難召喚人類的正義、良知,但是,人卻在自己的局限中流放自己,不能進入神的殿堂。
在一個沒有真正信仰的國家,詩,是要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宗教的使命的。對事物進行重新命名,建立事物最新的秩序,為靈魂構筑真正的庇護所,讓亡靈有一個另一種形式的神龕。
城市沒有家神的位置。死去的城里人以一種千篇一律的形式和一大群陌生的靈魂群居在公墓。形式劃一,松柏整齊,同樣尺寸的墓穴,祭奠者尋找被祭奠者,被無形地設置了記憶上的難度。它們或許比鄉村墳山上的野草和樹木更具遮蔽性。但是,詩將以更豐富的標記引領記憶,開辟通向靈魂的道路。
套間或別墅是另一種家宅,更符合人性的、現代性的棲居空間。現代詩同樣不可能因循古老的韻律形式——韻律是歷史性的,但作為語言家宅的本質不變。對于現代人,物質上的家宅也許只是人生一個短暫的驛站,語言的家宅是永恒的。生活的急劇變動,人生的飄忽不止,是現代人的普遍生存特征。在存在的意義上,不只是那些受到體制驅逐的人是流亡者,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是精神的流亡者,流放他們的,或許是生活,也可能是他們自身,就像人們意識不到自己終有一死,是必死者,因而總是遠遠眺望別人的死,把死亡看成風景。詩人或許是所有流亡者中最能體察人的流亡境遇的。一個真正的流亡者,去國的經歷和生活,會加強他對語言的親近感。他沒有家,母語是他的家;沒有朋友,母語就是他交談的對象。沒有離開自己的祖國的人,不會對“祖國”這樣的詞有太深的感受,正如詩人多多所說,他一回國,這個詞就從他身邊消失了,或者這種感觸沒有了。但是,一個真正的詩人遲早會感受到自己的“流亡”處境,越是深思,越是強烈。在這個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時代,詩人是不合時宜者,即便在詩人本身的“小社會”里,也互不認可,爾虞我詐。名或許是比利更大的魔鬼。在世俗的層面,它或許會激發人的活力和能量,但是在詩的層面,它是十足的破壞者。一個真正的詩人,在本質上是一個流亡者,孤獨者。而對于詩來說,不進入孤獨的境地,是不能真正和語言達成交談的。現實總是一股巨大的洪水,可以輕易地把一個詩人推到不能自控的、隨波浮泛的境地。
“大海是最后的醫院。”(于堅《在布里斯本》)
語言的大海。詩人是潛水者,深深潛入大海,傾聽那黑暗里的聲音。或與那黑暗的聲音展開持續的對話。不是因為孤獨,而是要消弭更多的孤獨,讓那孤獨的聲音,化為言語、文字。為流亡的靈魂造一個語言的家宅。
詩的本質是對話性的。顯性或潛在的對話。基于此,它有了抵抗孤獨的力量,也生成了不和流俗迎合的獨立精神,甚至它還有某種糾正的力量和療救的功效,正如謝默思·希尼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