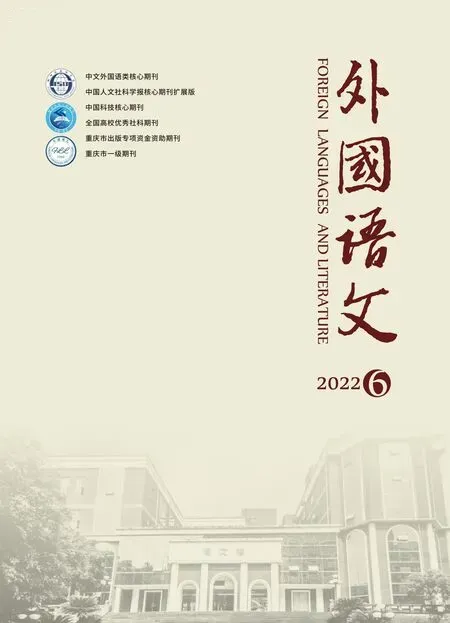“他者”的困境與“自我”的突圍
——形象學視域下《西游記》女妖形象的西譯研究
宓田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0 引言
形象學研究最初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范疇之一,發軔于20世紀的法國,學者讓-瑪麗·卡雷(Jean-Marie Carré)將形象學定義為“各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莫哈,2001:19),為形象學奠定了基礎。此后,國內外學者們紛紛對形象學展開了探討。狄澤林克(Deserinck,2009:153)認為形象學主要研究的是“文學作品、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中有關民族亦及國家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巴柔(Pageaux,2001a:121)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中提到:“所有形象都源自一種自我意識(不管這種意識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它是對一個與他者相比的我,一個與彼此相處的此在的意識。”2001年,國內學者孟華主編了《比較文學形象學》一書,為國內學者較為全面地引介了國外有關形象學的重要論述。
盡管自形象學設立以來,也有學者將其冠以“民族主義”和“不科學的跨學科性”之名,但形象學不僅為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也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跨學科性,而被逐漸引入到其他學科的研究之中。2015年,由盧克·范·多爾斯勒(Luc Van Doorslaer)、彼得·福林(Peter Flynn)和葉普·列爾森(Joep Leerssen)主編的《翻譯研究與形象學》一書匯編了16篇論文,以形象學為主要研究視角,探討了翻譯與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的構建等問題。國內學者如譚載喜對翻譯與國家形象的建構問題進行了分析,王運鴻、閆曉珊、藍紅軍等對翻譯形象學研究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和個例的分析實踐。
“形象指‘群體象征系統’或‘群體標記’,它既可以指政治形態上的國家或民族形象,亦可以指一些較小的次屬文化群體形象。”(狄澤林克,2007:153)女性作為文化群體之一,其形象研究引起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他們主要從外國翻譯小說、中國歷代小說及其英語各翻譯版本,來探討女性形象的歷史變遷、建構方式以及跨文化再塑等問題。孔慧怡以晚清翻譯小說為研究對象,分析得出譯者通過對人物性格和人物外形的改寫,按照譯入語文化規范塑造異域女性形象。學者朱全福以“四大奇書”為考察對象,研究了女性形象的階段性歷史變化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他認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的女性角色只是“作者演繹故事的工具和表達小說意圖的傳聲筒”,而相較之下,《西游記》中的女性角色主體意識增強,雖然依舊只起到了陪襯的作用,但她們的形象已相對豐滿。
在西語世界中,《西游記》最早的西班牙語單行本是在1945年由英語轉譯而成的,后來還出現了《西游記》的全譯本、節譯本、改編本和漫畫本等版本。其中,西魯埃拉出版社(Siruela)于1992年推出了《西游記:猴王的冒險》(ViajealOeste:lasaventurasdelReyMono,以下簡稱西本)。該本的譯者為恩里克·P.加頓(Enrique P.Gatón)和伊梅爾達·黃·王(Imelda Huang-Wang)。該譯本收錄在“時代之書”系列叢書之中,是西語世界中最早的、由中文直接翻譯成西語的全譯本。
本文基于自制的《西游記》中文-西班牙語平行語料庫(CCVAO),提取西本中對女性角色的翻譯描述,并以女性角色中的女妖群體為研究對象,考察西本譯者是如何對這些女性形象進行轉化與再創造,并呈現給目標語讀者的。《西游記》中的這些女妖,兼有人和神的屬性,她們一方面囿于凡塵,受到封建男權社會的輿論監管,另一方面又能力超群,游離于俗世之外,敢于表達情感和欲望,向封建男權提出挑戰。正如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娜·德·波伏娃(Beauvoir,2011:24)所述,“女人的悲劇,就是這兩者之間的沖突:總是作為本質確立自我的主體的基本要求與將她構成非本質的處境的要求”。在翻譯文本中,對于這些女性角色在社會規制的壓制(構成非本質的環境壓力)和自由意志的表達(確立自我主體的需求)搭建的坐標軸系統中的定位,不僅可以探尋到譯者對這些女性形象的理解,還可以窺得譯者受譯入語文化、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對原文中女性形象進行跨文化再塑,從而反觀其“自我形象”。
1 《西游記》中女性的“從禮”與“逾矩”
在《西游記》中,“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魯迅,2008:171)。人物角色千奇百怪,各路神仙精怪輾轉登場,共同構建了一個光怪陸離的多維時空。其中的女性人物雖算不上數量眾多,但她們在唐僧師徒取經之路的途中所扮演的角色各異,或不吝指點迷津,為其出謀劃策并鼎力相助,或施才逞兇,謀取圣僧以求真元,抑或只是匆匆打個照面;她們個性不一,有的神通廣大,有的柔弱多姿,有的奸猾狡詐,也有的溫婉多情。有學者將這些女性角色分為三類,即凡間女子、女神及女妖。
凡間女子主要有殷溫嬌、百花羞、女兒國女王、金圣娘娘等人。作者在描繪凡間女子時,有簡單一筆帶過的無名無姓者,也有粗線條勾勒幾筆的次要角色,對唐僧之母殷溫嬌與女兒國女王著墨較多。殷溫嬌貴為宰相之女,奉夫為綱,自覺遵行封建男權社會的準則,自身則處于附庸的從屬地位,使其自我意識陷到女性集體無意識之中,成為當時社會輿論場中“節婦烈女”的典范。《西游記》中的女神大多神通廣大且地位尊崇,主要包括觀音菩薩、毗藍婆菩薩、王母娘娘、驪山老母、嫦娥等眾,其中以觀音菩薩的出場率最高。觀音自《西游記平話》起就被融入其敘事中,直到百回《西游記》實現了“觀音信仰的徹底中國化”(屈麗蕊,2020:121)。作者在著力刻畫其大慈大悲的女神形象的同時,也不忘勾勒她的脾性,為其增添了幾分人間煙火氣,使觀音形象更為飽滿,也更加親近。
作者筆下的各路女妖大多都身懷絕技,其中與唐僧師徒有正面交鋒的女妖包括白骨精、蝎子精、鐵扇仙、玉面公主、杏仙、金鼻白毛鼠等妖精。蝎子精在佛前聽講,被如來一推,來一計倒馬毒樁,令如來也疼痛不已;鐵扇仙勤于修道,能夠三扇得雨,造福一方百姓。她們大都花容月貌,“端端正正美人姿,月里嫦娥還喜恰”,卻也兇狠狡詐,膽大妄為。白骨精三次幻形,令師徒離心;白面狐貍幻化的美后,竟要用小兒心肝做藥引;金鼻白毛老鼠精三天之內連吃了六個和尚。她們勇于直抒自己的愛欲,大呼“我和你耍風月去來”,便強行把唐僧擄去。她們大多都追求修道成仙,但終因女妖的身份和另辟旁門的手段,而落得個不得善終的下場。唯一的例外就是鐵扇公主,她“兇比月婆容貌”,卻是個得道的女仙,受人供奉之后,為人消災解難。她恪守婦道,院內無一尺之童,對丈夫更是包容忍讓,雖與玉面狐貍共事一夫,依舊克己守禮。她不慕唐僧真元,也不為非作歹,與取經一行人的仇怨也不過想為孩子討回公道,最后雖然也是家人離散,但畢竟得以尋一處安身,靜心修煉。
作者筆下的凡間女子多囿于禮教束縛,自覺地恪守三從四德,稍有逾矩便會以悲劇收場。作者筆下的女神,除了觀音以及幾位為取經隊伍設障或解難的菩薩以外,其他女神多為符號性的人物,被作者簡筆略過。這些女神們大多都有“無限的神通,清心寡欲,完美無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化身”(張紅霞,2004:67)。女妖群體大多自恃武藝,敢于挑戰男權,沖破禮教的束縛;她們個性獨立,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或愛情而孤注一擲,最終也難以沖破樊籠,成為封建男權社會下的犧牲品。
2 《西游記》西班牙語譯本對女妖形象的解讀與重塑
女妖群體是《西游記》中女性角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女性藝術形象中最具有多元性的群體。她們從各式各樣的生物幻化成人形,游走于凡塵之間,卻一心想要修道成仙,練就上天入地之能,好脫離于“五蟲”之列,擺脫世俗的規制。作者將她們的精怪特征、身份及法力凝聚在稱謂之中,仔細地描摹她們的外貌,并通過她們的言行舉止來刻畫她們鮮明的個性,以此將這些女妖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作者在描繪這些女妖的形象時,無論是在細節的刻畫上,還是在對她們的命運安排上,都反映出了作者的態度及評價。譯者在解讀這些女妖的形象時,亦會以己之志來選擇是接受還是反對這些形象描繪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從而對她們的稱謂、外貌以及言行的描繪進行跨文化的再塑造。
2.1 名稱與稱謂之西譯: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
若是算上作者一筆略過的卵二姐,《西游記》中出現過的女妖共計12個/伙,而除了前者以外,其他女妖均無名無姓,只有一些稱號。這些稱號有的表現出她們的體貌或精怪特征,有的則突出了她們的技藝法力。萬圣老龍王的女兒萬圣公主,不僅花容月貌,還藝高膽大,膽敢偷取王母娘娘的靈芝草。西本則將其譯為Princesade Todoslos Espíritus(萬千精怪之公主),體現出了她的地位超群。金鼻白毛老鼠精獲罪下界之后,自號為“地涌夫人”,大抵因為自己善于打洞,能在地上地下自由穿梭的原因。西本譯為Dama que Corre por la Tierra(在地里往來穿梭的貴婦人),體現出老鼠精自封的稱號的尊貴,也直觀地表現出了她的神通。
《西游記》中的女性稱謂十分豐富,其中對母親、姐妹和姻親的稱謂有近十種,對妻子的稱謂有十余種,這些女性稱謂幾乎分布在各個章節。女妖群體在虛擬的社會人際關系中,也扮演著母親、姐妹、姻親和友人的角色。西本的譯者變換地使用“tú”和“vos”的人稱代詞來稱呼這些女性,前者意為“你”,一般用于熟悉的朋友和家人之間,而后者意為“您”,這一人稱在現代西班牙中一般只用于稱呼地位尊崇或令人敬仰的人。
文中壓龍山壓龍洞的九尾狐被金角、銀角大王尊為“老母親”,西本中使用“vos”(您)這一尊稱,來體現兩大王對九尾狐的尊敬。原文中對妻子的稱呼眾多,包含像“拙荊”“山妻”“渾家”“老婦”這樣的謙稱。牛魔王在稱呼鐵扇仙時就使用“山妻”這一謙稱,黃袍怪將寶象國公主稱為“渾家”。西本對這些稱謂大體不做區分,都譯成“mujer”或“esposa”(兩者都為“妻子”之意),略去了原文中的語義蘊含。再者,在第64回中,杏仙迎客時使用“妾”這一自謙詞以自稱,譯者直接使用“我”這一人稱代詞來翻譯,并在其他樹仙稱呼她時,使用“vos”這一尊稱。
人名蘊含著豐富的信息,“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宗教信仰及語言特征等,無不顯示在人名這人類生命的底版上”(胡芳毅 等,2012:1)。西本譯者對女妖的名號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將女妖的精怪特征、能力以及個性以更為凸顯的方式傳遞給了目標語讀者。另一方面,中國古代講究“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稱謂的使用可以直接體現出親疏和等級關系。西本譯者略去原文中用來稱呼女性的謙稱,大量地使用西語中的尊稱來稱呼女性,在譯入語中抬高了她們的社會地位。
2.2 心理與言行之西譯:女性個性與主體性的凸顯
“一個形象最大的創新力,即它的文學性,存在于使其脫離集體描述的總和(因而也就是因傳統、約定俗成的描述)的距離中。”(莫哈,2001:29)在《西游記》描繪的眾女子畫卷中,有些女子本該是囿于禮教束縛的大家閨秀,卻敢于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欲,有些女子已然得道成佛,本該超然世外,卻依然不改脾性,令這些女子形象脫離我們對古代女子集體想象的總和,賦予她們鮮明的個性,體現出她們的語言美、類型美和張力美。
在西本中,譯者會根據自己對情境的理解,穿插加入對女妖們心理和形態的補充性描寫,這些描寫主要出現在女妖們進行對話時所使用的報道動詞的前后,共計28處。例如在第59回,大圣第一次請借鐵扇仙的芭蕉扇時,文中描述“羅剎女咄的一聲道”,西本譯為replicó la Diablesa con desprecio(羅剎女輕蔑地回答道)。在第64回,杏仙興濃,對唐僧“低聲細語呼道”,西本譯者譯為preguntó con vozseductora(用誘惑的嗓音問道)。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人物心理活動和形態描寫進行顯化處理,令這些女妖形象更為生動,個性更為鮮明。
譯者有時也會在譯文中創造性地使用夸張和比喻等修辭方法,著意突出女妖們不同的個性特點。第七回中,唐僧無意闖入蜘蛛精的巢穴化齋,眾女子為他準備了“剜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西本增譯了unossesoshumanos,cubiertos todavía de sangre, y los cortaron con tanta pericia, que daban la sensación de ser, en realidad,‘dou-fu’ fresco(這些人腦還滴著鮮血,她們熟練地把它切開,看上去真像是新鮮的豆腐)。西本譯者不僅按照自己的想象,描繪了人腦鮮血淋漓的情狀,還刻意突出了蜘蛛精們熟能生巧的刀工,突出了她們吃人成性的特點。又如在第55回中,蝎子精將唐僧擄回洞穴,百般施魅,“活潑潑,春意無邊”。西本則譯為La diablesavibraba de pasión, comounahoja de bambúen alas del viento(女妖激動不已,宛若迎風的竹葉)。譯者創造性地使用帶有中國特色的比喻,形象地刻畫出一個肆意表達情欲的女子形象。
2.3 外貌描繪之西譯:西方語境下套話的強化
“《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也,可無喻乎?”(《文則》)比喻自古就是中國文學中極為重要的修辭格之一。根據袁興群(2020:7)統計,《西游記》中有關女性形象的比喻多達171例,其中有關女妖的比喻表達數量最多,有關女人和女神的比喻數量次之。雖然這些女性角色的身份背景各有不同,但在外貌描繪的比喻表達上則多有類似。她們大多都有著蛾眉或柳眉,生著杏眼,眼如秋波或星辰,口如櫻桃,指如春筍或春蔥,足若金蓮。這些外貌上的比喻早就成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用來描繪美女的套話。
法國學者巴柔(2001:158-162)提出,“生理詞匯是用來描述和生產套話的”,而所謂的套話則是“單一形態和單一語義的具象”。早期在西方文學中描繪中國女人外貌的套話就包括“吊眼”和“小腳”(德特利,2001:244)。在原文中便用金蓮來比喻或借代中國古代女性的小腳,西本則多用“diminutospies”(極小的腳)或“deun tama?o asombrosamente peque?o”(大小出奇地小)來取代金蓮的比喻,或將喻體改為“杏仁”和“百合花的花冠”來比喻腳的大小,甚至將三寸金蓮一般大小的腳的尺寸直接譯為cinco centímetros de longitud(5厘米長)。西本譯者將喻體改為目標語讀者較為熟悉的事物,或省略喻體而把腳的尺寸直接呈現給目標語讀者,可以讓他們更直觀地想象出長著一雙小腳的女子形象,這些尺寸與實際多有出入,更多了一些夸張的成分,以此強化西方語境中描述中國女性外貌的“套話”。
我們考察了原文中其他出現頻率較高的容貌描寫,包括女子的眉眼、唇和肢體共56處比喻,發現西本的譯者對其中約16%的比喻都采取了省略的處理方式,而對其中約23%的比喻,西本譯者不僅將原文中的本體和喻體都直譯了出來,還在譯文中為目標語讀者指出本體和喻體在顏色或樣貌上的相似點,令原文中的意象具象化。例如,譯者會在譯文中指出這些女子嘴唇的紅色和形狀好似櫻桃一般,眼眸就好像擁有秋水一般平靜,手指猶如春筍一般細長。譯者對這些西方讀者不太熟悉的生理描繪刻意地進行弱化,或者依照自己的理解進行解釋,而對那些早已為西方讀者所熟知的套話則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發揮想象,有意識地進行夸大渲染。
3 作者眼中的“他者”與譯者心中的“自我”
吳承恩(1506—1580)生于明朝正德元年,卒于萬歷十年。有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從正德時期開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開始轉型。商品經濟自明中葉以來,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發達地區的文化普及率高,通俗文化煥發著勃勃生機。這個時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近乎瘋狂、雜亂而人欲橫流的時代”(商傳,2019:13)。人們過去將“克己復禮”“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主張奉為圭臬,而如今人們倡導“格物致知”“心之所發即是意”的心學理念,強調個人主觀的合理性。“己者,天地萬物之主也”,人們不再壓抑個性,而是積極地探尋自身的主體性。
吳承恩生長在商賈之家,又自幼有才名,博覽群書,應對當時繁榮的商品經濟和市民文化有著切身的體會,對當時的文化思潮也有著深刻的領悟。在《西游記》中,吳承恩雖對世情多有針砭之意,但他也不免站在封建男權本位主義的立場,將女性異化為“他者”。在故事的整體架構上,作者以每十回一段落,在每個段落的第三、四回往往設置與色欲相關的情節,其中各路女妖成為取經人除之而后快的障礙,大多落得個被搗成“一團爛醬”的境地。作者還模擬說書人的口吻,在文中穿插“佳人二八好容妝,更比夜叉兇壯”“婦人家水性”之類的對女性的負面評價,以及像“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遭殃”這樣的勸誡。
除《西游記》之外,吳承恩(1991:6)在《陌上佳人賦》中寫道:“至美畢惡,色哲得兇”,并奉勸世人“子無愛佳人之難得,須知尤物之當懲。”如此評述在20世紀初的歐洲依然能找到回響,里爾克(Rilke,2009:40)認為“因為美無非是可怕之物的開端”。在西方傳統中,早在古典文化時期,亞里士多德便認為:“女性之為女性,是由于缺失某些品質。”(波伏瓦,2011:8)古希臘、羅馬的哲人和藝術家將女性劃定為第二性,將女性與惡關聯在一起(Casanova et al.,2005:10)。集合一切天賦的潘多拉打開了寶盒,給世界帶來了無盡的災難。眾所周知的女妖如美杜莎和斯芬克斯,最終都落得被英雄所殺的境地。自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的建立一直到16世紀的西班牙黃金時代,西班牙文學和藝術傳統中的女性經常被刻畫成妖魔或怪獸的行狀。女性更易受到惡魔的蠱惑而成為女巫,依從其意志行事。中世紀末期西班牙文學中著名的“紅娘”——塞萊斯蒂娜(Celestina)便是一個被惡魔做了標記的女巫形象。在宗教意識形態和男權社會的架構下,女性長期被束縛在內在性之中。
《西游記》的西本譯者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著手并完成翻譯,一方面,他們基于西方傳統,對原著中異化女性的敘事建構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在19世紀中旬和20世紀60—80年代,由于受到西班牙社會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世界婦女運動的開展等因素的影響,西班牙的女性主義運動迎來了數次高潮并取得了成效(Fraile,2008: 15-16)。譯者們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對原著中女性角色所受到的環境壓力作了改寫。例如在第23、24回中,八戒因為貪戀女色,被普賢文殊等四位菩薩幻化的美女所戲弄,作者以一首《西江月》為證:“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添囊。好將資本謹收藏,堅守休教放蕩。”清代內丹家劉一明評此詩曰“語淺而意深,讀者須當細辨”,并進一步解釋:“蓋此原本,乃生天、生地、生人之根本”,此本具有唯一性,無增亦無減。后句“資本”應復指“原本”,實為勸誡修道者應當慮險防危,謹慎收藏好此原本。西本將兩者分別譯為“suma”(總和)和“capital”(資本)。譯者為讀者傳達了資本的總量是不變的,應當保存好而不得隨意花費之意,但略去了原文中勸誡修道者,越是年輕貌美的女子就越危險,只有遠離女色才能固守真元,保全其身的含義。
另一方面,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西班牙,中國翻譯文學體量不大,譯介的主要對象還是中國古代詩歌、傳說故事和一些先哲的哲學思想著作。這些文字成為西班牙人對中國女性形象進行深度解讀的窗口之一。對于西班牙人來說,包括中國女性在內的亞洲女性留給他們的刻板印象是嬌弱、美麗、順從且服務于男性,而“小腳”也成為他們用來描述中國古代女性外貌形態的一語“套話”。由于通過翻譯而進行的改寫能夠“投射出原作者/系列作品在另一個文化中的形象”(Lefevere,1992:9),因此,譯作的字里行間難免滲透著譯入語文化對原作中人物形象的固有認識。此外,譯者的翻譯總是受到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的影響,因此譯者也不免對原作中的形象進行加工與再塑造,從而將作者眼中的“他者”部分轉變成了譯者心中的“自我”。
4 結語
譯本中所呈現出的文學形象經過譯者的加工,“受到自身文化的接受程序而重建,是主觀和客觀、情感和思想混合的‘創造性想象’”(科利,2001:43)。吳承恩筆下的女妖群體雖然身處封建男權社會的輿論體系之下,但卻敢于挑戰,勇于表達情欲和追求理想,但終究為世所不容,而以悲劇收場。這些女妖形象經過西本譯者的“創造性想象”,個性更為凸顯,社會地位也有所提升,而同時在外貌上又更趨向于西方語境一向對中國古代女性的認知想象。這些經過了跨文化再塑的女性形象在對構成非本質的環境壓力和確立自我主體需求的坐標系統中,與原作所呈現出的女性形象有所偏離。譯者將作者筆下的“他者”,經過自我意識形態的改造,塑造成了“自我”投射的創造性想象物。通過對比譯本和原著中的藝術形象,不僅可以考察譯入、譯出語的語言差異,還可以探究作者與譯者的思想形態乃至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性,從而為在跨文化交流中自我形象的構建提供一些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