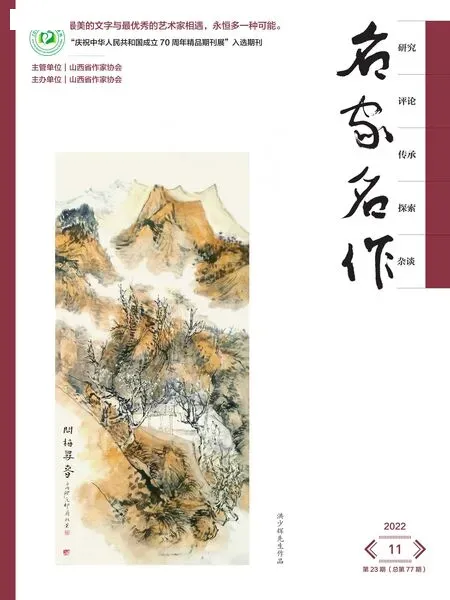從遠古走來的長調
——新巴爾虎左旗長調民歌
馬小龍
一、緒論
“巴爾虎”是蒙古族古老的游牧部落之一,一萬多年前,“扎賚諾爾人”(形成中的蒙古人)便在巴爾虎繁衍,哺育了原始的草原文化。一千多年前,蒙古族生產方式也由狩獵轉為畜牧,蒙古族長調這一新的民歌形式也逐漸萌芽。
蒙古族長調民歌(蒙語為“烏日汀〈圖〉·道”,“烏日汀”譯為長久,“道”意為歌)具有節奏悠長、音域寬廣、旋律悠遠、結構豐富且自由等特點。歌曲種類包含祝酒歌、草原贊歌、頌歌、牧歌、情歌、訓誡歌、思鄉曲、宴會歌等;題材則表現在思鄉、思親及贊馬等方面,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蒙古族長調民歌體系。
二、新左旗長調民歌代表作品
新左旗所處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地區,歷史上是成吉思汗肇興大業的戰略后方,也是蒙古族山林狩獵文化的集中地,薩滿教歌舞、狩獵歌舞等都保留著山林狩獵時期的痕跡。明朝中期以后,外來牧民帶來的草原牧歌與山林狩獵音樂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長調民歌。
目前有記錄的巴爾虎民歌有300余首,例如“穹廬文化”所代表的“三個寶日”《褐色的雄鷹》(寶日獵鷹)、《五歲的鐵青馬》(蘇優格寶日)、《褐色的雀》(寶日寶日雀)等著名的長調民歌,它們保留著蒙古族音樂古調式的輪廓,具有結構短小、粗獷明朗、曲調平直等特點。
新巴爾虎左旗草原上的牧民們,幾乎人人都會演唱長調民歌,長調民歌在這里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在各大場合,他們都樂于演唱長調民歌來表達情感。新巴爾虎左旗長調民歌的美學特色,大致可概括為情感極致抒發、意境極其自由、調式變化支撐情感變化。
新左旗長調民歌善于運用轉調和離調手法,最常見的就是羽調式向下屬音方向轉調或離調,旋律中常出現清角音。《褐色的雄鷹》就是典型的代表。
(一)《褐色的雄鷹》
這是一首訓誡歌,告誡年輕人莫虛度光陰,歌詞具有教化功能。歌曲以“宮”音開頭,結束在“商”音(主音)。旋律布局獨特,如由四度音程“角”音至“羽”音連續跳進(E-A),凸顯高亢的意境;再如第六小節旋律級進下行,每個音都伴隨一個短促的同音反復作裝飾,讓原本平穩的旋律變得靈動有力,仿似雄鷹在不同的高空盤旋。

(二) 《思鄉曲》
除了羽調式離調和轉調,有些長調民歌也運用徵調式轉調的手法。
《思鄉曲》前四小節為G徵調式,從第五小節開始轉為C徵調式,旋律最終結束在C徵。這首作品的曲式結構相對簡單,節奏較單一,旋律朗朗上口。轉調前的旋律可看作在描寫景色和羊群,旋律風格歡快幸福;轉調后進入思念情緒,音區也逐漸變低,在C徵結束。這首作品表達了牧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對家鄉的思念,旋律簡單,適合民間傳唱。

(三)《五歲的鐵青馬》
在新左旗長調民歌中也有復樂段曲式結構的歌曲。 其內容豐富,一般由四個樂句構成(引子、副歌、尾聲、補充段),配合“諾古拉”的裝飾性花腔唱法使其表現力更豐富。這類作品的樂句數量常為偶數,樂句內部由不規則旋律和節奏組成,歌曲的小節數量以奇數為主,奇偶相嵌,使樂曲交織緊密。
節奏方面多采用混合拍子。常見3/4拍—4/4拍—5/4拍—2/4拍—4/4拍的節奏組合,基本規律是“密—疏—更疏—更密—疏”,由此產生的律動制造出了一種持續且富于變化的推進感,增強了旋律的動力。

《五歲的鐵青馬》是一首長調情歌,上、下兩個樂段構成了復樂段的結構,每一段歌詞都由牧歌體詩句寫成,且歌詞和旋律的結構并非一致。作品由四個樂句構成,為3小節 + 4小節 + 3小節 + 4小節。尤其第四樂句將第一樂句的旋律動機與第二樂句的旋律動機組合起來,相互扣嵌形成新的樂句,由此可見,長調民歌在結構和旋律發展上已經運用了專業的作曲技法。
三、演唱藝術
(一)氣息控制
長調民歌對氣息控制的要求很高。著名長調藝術家哈扎布說:“氣息是長調民歌的生命線。”長調民歌在演唱時注重中低聲區氣息的流暢性和吐字發音的連貫性,在良好的中低音技術的前提下,高音區才能駕馭得穩健自如。這些演唱理論雖然和西洋的美聲唱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但長調民歌的一些特殊唱法是其他唱法沒有的。
(二)呼麥
呼麥是蒙古民族古老的唱法之一,可追溯到匈奴時期,是一種罕見的多聲部發聲方法,“高如登蒼穹之巔,低如下瀚海之底,寬如于大地之邊”。演唱時聲帶時而震動時而不震動,可一人同時演唱兩個以上的聲部。演唱低音聲部時需運用閉氣技巧,令氣息沖擊聲帶,發出粗壯寬廣的氣泡音;演唱高音時則需調節口腔共鳴來強化泛音,發出帶有金屬音色的高音聲部。演唱呼麥時,可一人同時模仿瀑布、森林、動物等的聲音,并讓它們產生和聲。在中國各民族民歌中,它是獨一無二的。
呼麥藝術曾一度在我國內蒙古地區失傳,由于近年來外蒙古的呼麥大師頻繁來到內蒙古地區交流,才使“呼麥”這一文化遺產在我國內蒙古大草原上重新繁榮起來。
(三)“諾古拉”唱法
“諾古拉”(蒙語意為“曲折”)是長調民歌特有的音樂形態,具有華彩性的音調和節奏。其特點是通常在較長的節奏之前,出現短促、顆粒性的裝飾音。

例如《遼闊的草原》就是由若干短促的倚音構成的。在音程布局上,由同音反復(同音倚音)的形式呈現,或以二度、三度輔助音組成裝飾音來修飾長音。歌曲語言節奏獨特,開頭部分“雖然”一詞,節奏舒緩,兩個字跨越了兩個小節,是一個長托腔,緊接著“有遼闊的草原”先密后疏,有序地向下發展。
再如寶音德力格爾演唱的《褐色的雄鷹》,在中聲區多以“嗬咿”等音進行修飾。在第四小節(第二樂句)“多么”一詞處,唱出“諾古拉”,就像馬頭琴演奏時的“打指、顫音”,音響效果豐富靈動;第六小節連續地級進下行,“諾古拉”的出現頻率也越來越密集,制造出雄鷹階梯式俯沖而下的氣勢。
四、節奏處理
(一)華彩性“諾古拉”節奏
華彩性長音既可以在句末出現,又可以在某一樂句內部出現。長音的音符數量一般較多,旋律走向并不具備很強的華彩性。華彩性的結構拖腔有三大特征:(1)沒有歌詞,一般都以“啊”或者“嗬咿”這些襯詞來演唱;(2)篇幅大且結構獨立,有時一個華彩性的結構拖腔就可以單獨成為一個樂句;(3)可以多次重復出現。在音樂表現力方面,結構性的拖腔更利于情感的抒發。
(二)抒情性長音節奏
這是處于主導地位的節奏型,且演唱時相對簡單。長調民歌的長音節奏形態大致可歸納成三種:華彩性拖腔、結構性拖腔和詞尾性長音。詞尾性長音是指在每個樂句結束時,把歌詞節奏自然地延長,形成詞尾性長音,讓樂句的結尾更舒展。
(三)陳述性語言節奏
這類節奏形態通常出現在歌曲的開頭或中間段。演唱時,一般是先把歌詞“說”(陳述)出來,再進入拖腔部分抒發情感。結構短小的長調民歌,第一個樂句開始時,以均勻的節奏“說”出歌詞,歌曲快結尾時才出現拖腔;大型的長調民歌曲式結構、旋法復雜,樂句之間注重起承轉合,一般除第一樂句外,其余樂句在轉折時通常也是“說”出歌詞。二者都具有陳述性的語言節奏特征。
在演唱陳述性的語言節奏時,要注重咬詞清楚,每個音都要有彈性,詞語短句需陳述清楚,不能囫圇吞棗。因而在演唱長調民歌之前,要先全面分析歌曲的結構和語言節奏特征,才能在這三種語言節奏形態中游刃有余,把握住應有的風格。
五、新左旗長調藝術家
新巴爾虎左旗也是歌唱家的搖籃。著名歌唱家寶音德力格爾、那楚格道爾吉、巴德瑪等都是地道的新左旗人。
寶音德力格爾(1934—2013年)出身貧寒,父親是盲人藝術家。她少年時跟隨父親,耳濡目染了當地民歌。父母雙亡后,她拜歌手塔巴海為師。1947年,在那達慕大會上演唱長調民歌,聲名大震。
寶音德力格爾老師是享譽海內外聲樂界的知名唱將。她先后訪問朝鮮、蒙古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被譽為“罕見的民間女高音”,代表曲目有《褐色的雄鷹》《五歲的小青馬》等。同時她也是承前啟后的長調藝術教育家。1975年,被調往內蒙古藝校任教;1980年,整理出版了《巴爾虎民歌集》;1993年,創辦了牧民音樂學習班。
她把蒙古族長調民歌帶上了正規的音樂教育講臺,培育了拉蘇榮、德德瑪等知名弟子。她見證并引領了當代蒙古族長調民歌從民間走向世界舞臺、從草原跨上講臺的艱辛歷程,積累了大量供后人學習和參考的寶貴經驗。
那楚格道爾吉(1953—1994年)13歲以優異成績考入呼倫貝爾歌舞團。他的聲音凈透、音域寬廣、高亢嘹亮,有豐韻的草原民族風情,代表曲目有《遼闊的草原》《肥壯的白馬》等。在繼承長調民歌唱法的基礎上,他大膽借鑒西方美聲唱法,為長調民歌乃至我國民族聲樂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六、結語
蒙古族長調民歌的地域性非常明顯,按風格可分為九大區域:察哈爾(錫林郭勒)風格區、昭烏達(赤峰)風格區、鄂爾多斯風格區、呼倫貝爾風格區、科爾沁風格區、烏蘭察布風格區、阿拉善風格區、新疆衛拉特蒙古部風格區、青海和碩特蒙古部風格區。這九大風格區又可以劃分為若干個更小的風格區。
呼倫貝爾風格區新巴爾虎左旗的長調民歌從遠古走來,在后人傳承的同時,也吸收了多民族的音樂特色,現已發展成蒙古族長調民歌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