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楨的“思友”探究鐘嶸五言詩的“淵源”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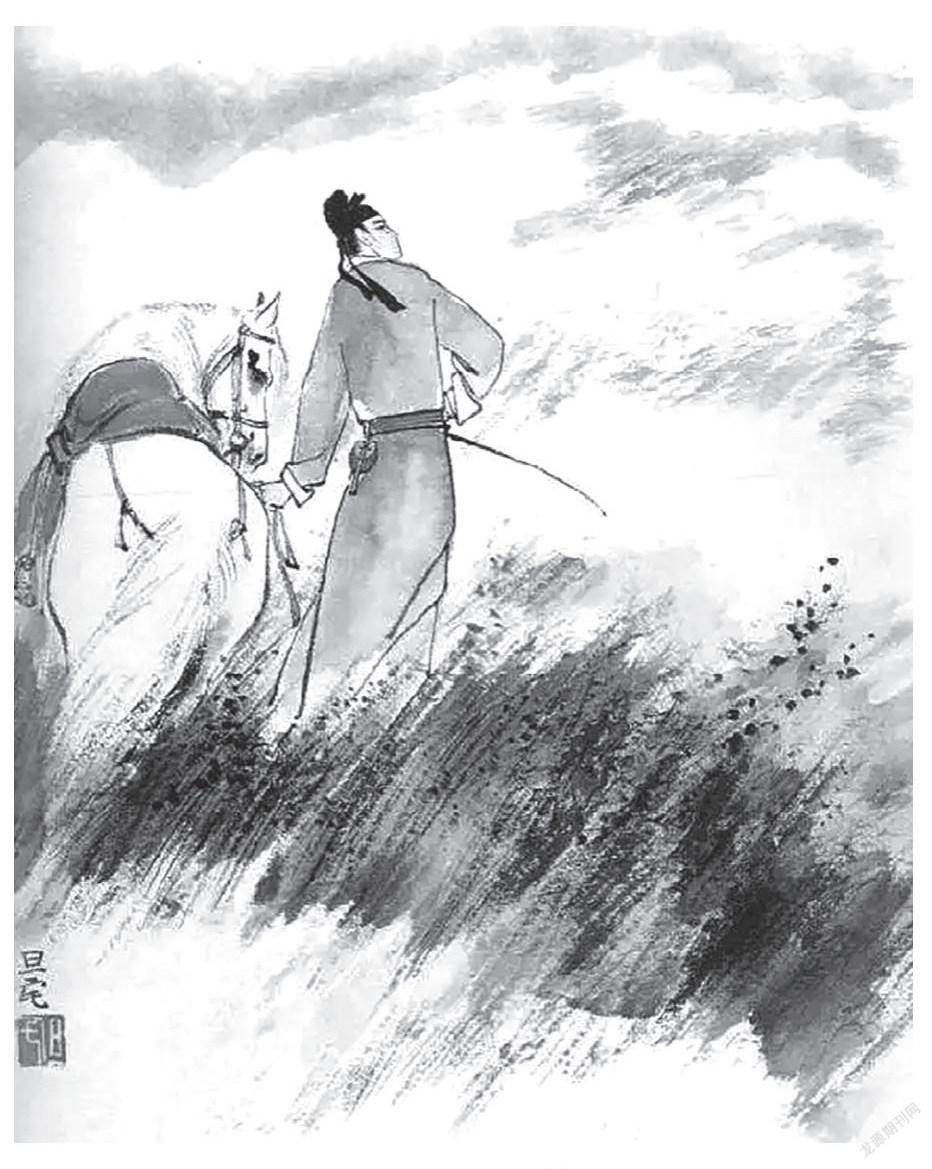
摘要:劉楨的詩以氣盛聞名,鐘嶸在《詩品》中將其列于上品的同時,更區別于曹丕和劉勰等人之見,將其與曹植并稱為“曹劉”。此外,在《詩品·序》中,鐘嶸棄《贈從弟》而將盛氣相對不足的《贈徐干》一詩與陳思贈弟詩并稱為“五言之警策”。二者在“氣”的表現上不同于單純的豪邁俊逸之詩,而強調人生沉淀,給予五言詩悲壯慷慨的情志。通過探析二者詩歌淵源和詩歌表現風格可見鐘嶸對五言詩表現傾向及其“淵源”思想。
關鍵詞:劉楨;曹劉;思友詩;氣;淵源
一、鐘嶸“曹劉”之論及其繼承
劉楨作為“建安七子”之一,南朝鐘嶸在《詩品》中將其詩作列在上品,并與曹植并稱。這一點引起了后世對“曹劉”與“曹王”的爭辯。在劉楨和王粲地位的看法上,鐘嶸在《詩品·序》中稱“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1]17可見鐘嶸認為陳思之下,劉楨與王粲并肩而立。但其又說“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1]38將劉楨與曹植并稱為“曹劉”,二者看似矛盾,但深究曹植與劉楨詩風及鐘嶸五言詩傾向可以發現,實際不然。鐘嶸“曹劉”這一觀點在后世,特別是唐代以后,得到了諸多學者的認可,稱“曹劉”一說的更是不在少數。如殷璠“至如曹劉多直語……而逸駕終存”[2];杜甫“方駕曹劉不啻過”;唐元稹稱“氣奪曹、劉”;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二》:“曹、劉坐嘯虎生風”;明唐時升《祭大司寇王弇州先生文》 “或如曹劉,遒壯縱橫”等等。上述種種可以發現,后世將曹劉二人并稱主要在于推崇二人詩中的“氣”,稱贊其氣“壯逸”的特點,是對鐘嶸評價曹植“骨氣奇高”和劉楨“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的繼承。“曹劉”并稱,始自鐘嶸《詩品》,但鐘嶸這一觀點并不與時人同。鐘嶸對劉楨的推崇雖然在后世受到眾多文人追隨,但在當時看,鐘嶸極力推崇“曹劉”在六朝時期實屬個例,有必要對其進行探究。
二、劉楨的“思友”與悲慨之“氣”
時人在談及劉楨時多提到“氣”。曹丕稱“劉楨壯而不密”“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5];鐘嶸《詩品》評曰:“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1]38;劉勰道“公幹氣褊”[3]55。在品評劉楨作品時,時人多關注其詩中之“氣”。關于“氣”的概念歷來有多種解釋,按許慎《說文解字》,氣的本義是指云氣即自然之氣。而《周易》《莊子》進一步將其引入哲學范疇,使之具有哲學本體論之意。孟子將氣與人的生命力和精神氣聯系在一起,提出“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曹丕在繼承孟子“養氣說”后將其與文學結合,提出了自己“文以氣為主”的論斷,推崇剛健有力、雄壯遒勁的文學創作,欣賞“豪邁俊逸”的創作風格,在論及劉楨的“逸氣”方面認為,劉楨具有超逸不群的精神氣質和生命態度。南朝劉勰基本上秉承曹丕的觀點。對劉楨“氣”的評價,后世常以《贈從弟》為代表,認為他借萍藻、松柏、鳳凰三個物象來贊美從弟,同時也以這些來自喻,從而展現慷慨之氣和“真骨凌霜,高風跨俗”的品格。詩歌超逸有力,氣勢浩然,這實際符合當時曹丕、劉勰等人尚文學“陽剛之氣”的態度。但鐘嶸不同,他在《詩品·序》中認為“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1]29-30。思友詩應指劉楨在受刑監禁后所作的《贈徐干》,鐘嶸一反他人推崇的《贈從弟》,而是推崇豪邁俊逸之“氣”相對不足的后期詩作《贈徐干》,這一點值得深思。
三、“贈弟”“思友”之生命體驗
《詩品·序》中提到“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1]19,而“風力”和“丹彩”也被認為是鐘嶸評詩的標準。在“曹王”與“曹劉”之爭中,大家對曹植的態度是一致的,而王粲與劉楨以何與曹植并稱是判斷這場爭辯的關鍵。鐘嶸在《詩品》中將曹植的《贈白馬王彪》、王粲的《七哀詩》、劉楨的思友詩《贈徐干》納為佳作,而通過對比發現,這些詩作都是詩人在感受過生命磨難之后寫就,相比較前期語調激昂的《白馬篇》《贈從弟》等作品,健氣稍弱,更多了一種悲壯慷慨之氣。如果說曹丕推崇的是好男兒壯年意氣風發,那鐘嶸所尚的就是經歷世事沉浮后,仍心中放達,詩中包含了歲月的沉淀,更具厚重感,讀之使人潸然淚下又豁然開朗。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論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6],認為文人在經歷過種種“不平”之后,其創作往往更能夠表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吶喊,進而創造出富有力量和感染力的作品。《贈徐干》作于劉楨受刑監禁以后,詩中劉楨向好友徐幹訴說著自己的哀愁,整體氛圍帶有淡淡的哀怨,但全詩可以說哀而不傷,并無頹靡之氣。反觀其他文人多推崇的《贈從弟》三首,情感基調明顯不同于劉楨受刑之后所作詩歌的風格,分別以卑賤而清潔的萍藻、傲寒而挺拔的青松、志大而勤奮的鳳凰為意象,贊揚從弟這樣守志而高潔的世人,整體風格壯闊渾厚,如壯年男子意欲揮斥方遒的壯志豪情。但鐘嶸卻將劉楨后期之作《贈徐干》稱作“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那是鐘嶸對劉楨經歷艱難之后仍心有向往態度的肯定,這種態度融合進詩歌中,使詩歌充滿時間沉淀而更具感染力,這也是鐘嶸對五言詩抒情的深層認同。
考及劉楨生平家世,其祖父劉梁為“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于市以自資”“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7],雖任小官亦能恪盡職守,謹遵教化。劉楨從小亦深受家風和祖父輩文學素養的熏陶,“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賦數萬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答,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8]壯年時又舉孝廉入仕。可見劉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身上具有強烈的文士之氣,并表現在其詩作中。早期的劉楨滿腹豪情,在儒家積極報國的思想和自身才華的推動下,對未來抱有極大的樂觀與期待,其詩作中也表現出強烈的風發意氣和面對亂世依舊無所畏懼的桀驁之態,如《贈從弟》中寫道“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何時當來儀,將須圣明君”。[9]471但與前期詩中表現出的滿腔豪氣不同,其后期受刑詩作《贈徐干》一詩悲壯之氣更濃。“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纮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9]478此詩寫于劉楨受刑之后,面對官場的沉浮,劉楨對人生境遇上的態度已不同于剛入仕時。雖是思友,但主要是向好友訴說自己的慨嘆,感嘆在這建功立業的好時機里,沒有能及時成就一番事業,反而虛度了光陰,悲嘆自己有志不能明,有才不能用,后半段中表現出的吶喊將整首詩歌提升至哀而不傷的境界,在悲情中積聚著力量和希望,實乃“發憤”之作。這也使得整首詩的風格上升到悲而不哀、慨中有壯的高度。
四、鐘嶸五言詩的“淵源”觀
縱觀《詩品》的評價方式可以發現,鐘嶸具有明顯的比較意識。雖然其在《詩品》中道“一品之中道:‘略以世代為先后,不以優劣為詮次。”,但從具體的人物編排來看,仍舊表現出來比較意識。曹旭在《詩品集注》中對此也認為“蓋亦微存優劣之意也”。[10]鐘嶸的比較意識體現之一在于他對詩人詩歌風格淵源的追溯,往往第一句就點明其詩風源頭,因此可以說鐘嶸在評述詩人詩歌時具有一種“淵源”意識。“淵源”意識在上品中的體現非常多,如稱《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曹植“其源出于《國風》”;劉楨“其源出于《古詩》”等等。上、中、下三品的詩人詩作有的直接來源于《詩經》和《楚辭》,有的則是間接,如《古詩》源于《國風》,而劉楨源于《古詩》,左思源于劉楨。總體來說,鐘嶸將最終源頭歸到《詩經》和《楚辭》,而在上品的《古詩》和其余十一人中,最終源于《詩經》的占半數以上,由此可見鐘嶸對《詩經》的重視。
鐘嶸將曹植推崇到極高的地位,稱其“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毛詩序》道:“雅者,正也。”[11]“情兼雅怨”即說曹植詩中的感情,兼有雅正和怨刺之情。鐘嶸認為曹植詩源于《國風》,表現出對于現實人生的感嘆,蘊含雅怨之氣。如最為鐘嶸推崇的《贈白馬王彪》一詩不同于曹植早年《白馬篇》,抒發一位好男兒志在四方,滿懷激情的豪言壯語。整首詩的情感具有強烈的層次感,既悲述自身艱難遭際,又以豪言勸慰祝福好友,不失男兒情志,也正體現其五言詩在抒寫情志上的特點,也體現出鐘嶸對五言詩表現出的悲壯慷慨情志的傾向。同是思友,劉楨《贈徐干》一詩在情感表現上與曹植此詩有異曲同工之效。而李陵、王粲等《楚辭》一脈的詩人缺少這種氣概。王粲《七哀詩》亦被鐘嶸稱之為“五言之警策”,其詩反映社會離亂,頗有《國風》特點,但在詩歌表現上更多呈現出凄愴憂怨的情緒。總之,鐘嶸推崇曹劉,并將劉禎提到曹植之下,而曹植、劉楨詩歌皆歸源于《詩經》,表現出《詩經》中的“雅怨”之氣,特別是《贈徐干》尤為鐘嶸稱道。相比之下,王粲源于李陵,李陵源于《楚辭》多“凄愴之語”,缺少骨氣與風力。因而鐘嶸更推崇劉楨,將其與曹植并稱。
五、結語
鐘嶸對“曹劉”的觀點與時人不同,在對思友詩的看重上也顯示出其特殊性。從曹植“贈弟”看劉楨“思友”之警策,分析劉楨《贈徐干》中表現出的真摯坦率、哀而不傷,以及悲情之下蘊含骨力的特點,可以看出,鐘嶸對劉楨詩中“氣”的看法不僅僅局限于豪邁俊逸的一面,這也表現了鐘嶸對五言詩情志的傾向性。
作者簡介:陳洋(1996—),女,漢族,四川遂寧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魏晉)。
參考文獻:
〔1〕鐘嶸,周振甫譯注.詩品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 1998.
〔2〕殷璠.河岳英靈集[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3〕劉勰.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5〕夏傳才,唐紹忠校注.建安文學全書·曹丕集校注[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6〕韓愈撰,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8〕杭世駿. 三國志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9〕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10〕曹旭.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1〕郝敬.毛詩原解[M].北京:中華書局,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