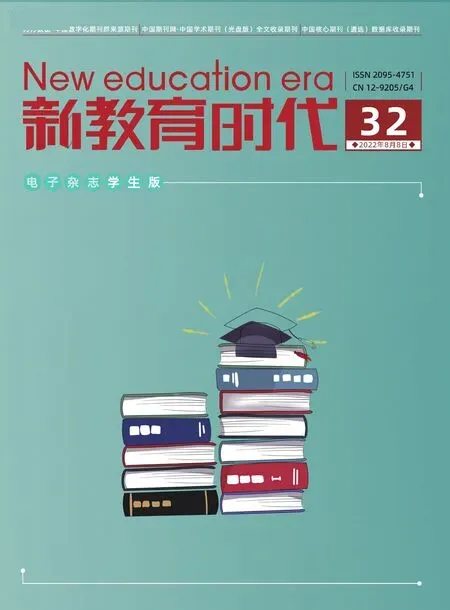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構建意義及融合初探
邵思民
(廣西民族大學 廣西南寧 530006)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在順應當今思想政治教育時代化需要的條件下應時而生,此學科屬性來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學與民族學之間的跨越性。它的形成對穩定社會發展、民族繁榮等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1]
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概述
(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基礎內涵
一門學問能否被定義為一門科學,最主要的就是看它能否對研究對象的概念和本質的規律達到理論化的層次,從而構成一套專屬于自身的學科定位和學科屬性,并為自身的理論指導設立更為精細化的知識體系。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關鍵因素,即有其內部基本理論的普遍性,也有其現實發展規律的特殊性,這是它發展特質中區別于一般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所研究范圍的差異之處。“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社會成員進行一定的民族觀教育,促使社會成員認同民族、民族共同體和國家的社會實踐活動。”[2]我國自古就是由眾多民族組合而成的統一的國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則是秉承中華民族認同與民族團結的教育觀念作為主要指導思想,在民族發展的工作進程中,選擇恰當且有效的方式實行治理,實現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特點
馬克思強調民族和國家同屬于歷史范疇,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指出:“在氏族制度下,只有當聯合在同一個管理機關之下的各部落融合為統一的人民時,民族方才產生。”[3]多民族同舟共濟、一脈相連的特征,是我國發展繁榮的主要因素。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認知觀念作為一種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都客觀地存在于民族交融之中,從而推動了中國多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史為鑒,西周王室從殷商“暴民而亡”中取得教訓,提出了一套“天命”觀。倡導“以教為先”,強調“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觀念,通過保民、修德這兩種方式來實現民族融合,加強民族關系。春秋戰國時期,以先秦哲學中的儒家“仁愛”思想的為倡導,開展了“以人為本”“大一統”的思想教育。西漢時期,統治者以《禮記·學記》中“化民成俗,必由乎學”的理念,用道德觀念去改善邊遠區域的民族組合力與邊民向心力,主張在民眾生活中開展道德教化內涵,側重“以德化民”。隋朝時期,隋煬帝采取儒家民族觀“大一統”的思想,發出了“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為家”的指令,他認為華夷不僅要成為一家,并要求其歸于一個正統王朝的統治之下,從而減少不同地域之間的沖突,使四海九州走向一統。唐太宗時期,對邊疆少數民族頒布了“視四海如一家”的寬容政策,加強了民族之間的團結,起到了穩定地區的作用。現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則相當關注民族教育,他認為民族教育的興盛要重視教育學生的榮辱觀念和國家認同感,創建相互團結的統一國家,并將其歸納至民族教育的政策之中。要把維護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教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加強馬克思主義民族宗教觀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4]上述信息明確地表明了各領域對民族教育實施計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理論知識的培養下,深刻了解到民族關系的教育不僅是少數民族需要學習的內容,也是社會公民需要學習的內容。步入21 世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愈加受到重視,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各高校組織相繼設立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政策的相關課程,對民族概念以及思想道德素質等進行規范引導,梳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在實施過程中所積累的知識、方法和成果。
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方法
(一)構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特征方法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主要的四個內容構建了其發展過程的研究方法。在社會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以及各地域文化的融合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則必須呈現出特有的定義,其理念方式表明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必須富有鮮明的民族個性。因此,在運用方法的過程中必須要思索各個民族之間的民族關系、地理分布、人文風俗和歷史背景等差異性,從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各民族之間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引導與教育。
構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方法可應用其民族性特征從以下四個層面探討。第一,指導性方法。如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堅持群眾路線、解決思想問題與實際問題相結合的方法等。這都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在實踐過程中常用的指導性方法,將實際理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民族性特征的全過程。第二,社會實踐方法。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理論雖然尚未成型,但其社會需要的理論方法仍需跟隨當前民族關系、民族融合、民族工作中現實問題進行實踐指導,開展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實踐指導還需根據前沿性、指導性和科學性的社會實踐方法,如科學性和價值性的統一方法、實用性與規范性的統一方法、滲透性與交叉性的統一方法、科學性與人本化的統一方法等。將這些社會實踐方法應用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各個過程和步驟,能夠有效防止和規避建構理路中的偏差傾向。第三,原則方法。在對受教育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廣泛采用說理教育的方法、實踐鍛煉的方法、心理咨詢的方法、紀律約束的方法、評價激勵的方法、自我修養的方法等基本的原則方法,并結合各民族層面的規范體系進行綜合檢測,實現多種方法的操作與運用。第四,情感教育方法的創新和示范性。這類方法是人們根據受教育者的思想行為、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轉變,從而探索出來的實效方法,它與教育者的“傳道、授業、解惑”的品行魅力、思想道德修養等德行密切相關。這四種方法兼容并蓄、密切銜接,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構建了一個較為系統化的研究方法體系。
(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邊界方法
邊界意識是明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定位邊界的關鍵意識,要從學科屬性、內容規則、研究方法等規劃和解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定位中的明細觀點。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邊界意識具備以下三種情況: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就是在成長的進程中連續地汲取、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知識并逐漸形成“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建設體系;另一方面,邊界意識則是自身的“有限性”“自成目的性”等對思想政治教育定位層面上的化界能力,對此可以概括為邊界意識的“領域分化”原則。強調“領域分化”原則也必須堅守“以服務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為本”的思想,既不能影響其定位中需要區分的因素,也不能影響其學科構建的守正創新。第二,在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發展需求中,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主,它將民族學的理論成果應用到本學科發展的知識體系。如果一旦混淆了二者專業化的理論邏輯,就會造成其他成熟學科的“強勢介入”,將會違背原先想要融入與整合的初衷,洗刷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底色”。第三,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學與他者學科構建的“邊界意識”,可以判定思想政治教育學與民族學的學科分化及功能結構的不同之處,更有利于構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礎理論的“互動”與知識“共享”。
三、探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科學化確立
(一)建立戰略眼光
建立戰略眼光的長遠趨勢關系到新時代民族思想政治教育這門學科能否厚積薄發。一是要緊密圍繞處理民族工作發展中的重要目標,從實際情況中開展對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科學化戰略。深化不同時期黨關于民族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研究,主動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納入黨的民族事業發展戰略規劃之中。[5]在當今復雜嚴峻的形勢中,既要加大對民族認同觀等教育內容的學習,更要把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繁榮發展放在首位,增強民族學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點范疇。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從多種視域和界限關注實踐問題,就要從不同民族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堅持用基礎理論的穿透力和對研究對象的辨析能力以及處理問題的能力從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范圍領域出發,由點及面,深化對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理解,提供應用性理論和實踐對策。
(二)強化問題意識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始終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一是要從現實問題中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整體,運用好基本觀點、辯證思維、基本矛盾等層見疊出的問題形成,在促進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規范有序的標準下,除了要站在學科基礎性理論問題的創新過程之中,也要進一步發現研究對象和復雜問題的強意識性,更要注重于加強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基礎理論等邏輯問題,從現實性出發,以理論基礎為主體,樹立實踐性過程的特點,重視研究對象的銜接性、價值觀念的共同性、實踐問題的融合性,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途徑兩者的統一、互融,規避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在實際應用中“水土不服”的現實問題,增強時代感和吸引力。二是要對準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實問題”,堅持問題導向和方針規劃,增加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題活動,有效發揮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理論本質的引領和規范作用以及黨開展民族工作的實踐措施;最后是從指導思想、資源配置、內在要求、發展目標、隊伍建設、方針政策和成果評價等層面深化研究并解決實際問題,并將其納入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知識博弈”的重點研究范圍之中。
(三)培育人才隊伍
隨著現代科技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才的專業化和綜合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因此,馬克思主義民族認同觀、民族國家觀、社會歷史觀、民族文化觀等教育內容是一種相輔相成的協同關系,融合研究需要綜合型人才的培養,綜合型人才又是學科構建的必要前提。但是在各個培養體系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的培養目標過于寬廣,人才培養模式過于普遍性,且方案與實際目標相差甚遠。二是大部分課程體系設立了公共基礎課程與專業理論課程,但是課程培養體系的實踐內容“食古不化”,遠遠不能達到高層次人才需求的目標。“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人才作為新時代的引導者,其道德教養都在潛移默化地接受著文化的熏陶,應杜絕以過于機械化的灌輸模式傳授給受教育者。所以,要重視民族價值觀的人才培養體系、教育課程體系、師資力量等各個方面的優勢結合,主動借鑒高層次院校的經驗方案,把對人才隊伍的培養作為開展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首要關鍵。
(四)社會服務能力
開展社會服務能力,能夠增強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實用性,施展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實際探索與研究,根據社會需要與實際情況培養服務型人才,為民族地區的規范化建設發揮整體效能。二是要深入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運用“大思政”的合理性,有效施展其社會之“用”的本領功能,增強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體系的實際效用,并積極拓展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