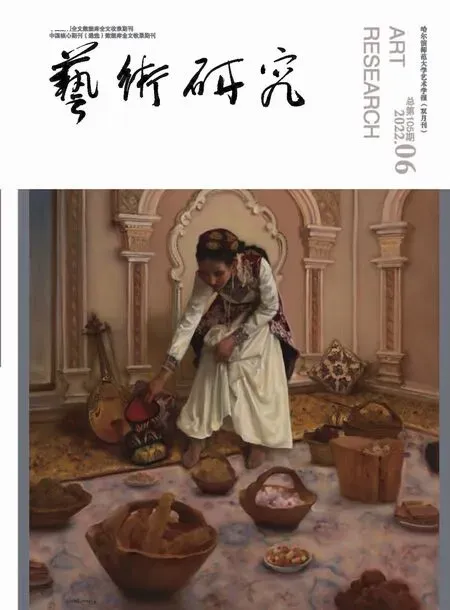一幅濃淡相宜的水墨畫
——齊爾品音樂會練習曲《敬獻中華》作曲技法探究
哈爾濱師范大學/ 王 曄 滕 悅
亞歷山大·尼古拉維奇·車列浦寧(Alexandr Nikolaevich Tcherepnin,1899.1.21-1977.9.29),美籍俄國鋼琴家,作曲家,指揮家。“齊爾品”是因其師從于戲曲理論家齊如山所取的中國名字。20 世紀初,由于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被迫打開了千年的封建之門,各種西方文化和藝術涌入,鋼琴音樂也隨之初步發展。后因“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黃自、蕭友梅、趙元任等人開始嘗試本土鋼琴創作,但依舊有西方創作模式的痕跡。作為一名從小受傳統歐洲音樂熏陶下的音樂家,為了拓寬自己的創作視野,萌發了對東方民族民間音樂的興趣。故1934年齊爾品來到中國,舉辦了“征求有中國風味之鋼琴曲”的活動,成為了中國鋼琴音樂創作的轉折點。之后的三年間,他受邀在上海國立音專教學,鼓勵中國學生以五聲音階進行創作,為中國的音樂教育與演奏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并創作了一系列具有中國元素的作品。其中《五首音樂會練習曲》(Op.52)就創作于此時期,開辟了具有“中國風格”練習曲創作的先河,第一首《皮影戲》(Shadow Play),第二首《古琴》(The lute),第三首《敬獻中華》(Homage to China),第四首《木偶》(Punch and Judy),第五首《贊歌》(Cantique),其中《敬獻中華》最初發表在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五聲音階的鋼琴教本》第五部分中,于1934年在中國創作并首演,同時也是五首練習曲中最早完成的一首,被稱之為“齊爾品的第一首完全在五聲音階基礎上創作的作品”。①做到了中國五聲創作與西方作曲技法的完美融合。
一、“點線結合”的主題發展手法
此曲的旋律形態分布是以“點”狀為主,“線”狀為輔②,通過模進的手法來發展主題的。1-7小節為完整的“點”狀旋律呈現,調性建立在降E宮調上,根據譜面標記的重音和力度記號,提煉出的單聲部旋律為:
例1:

至23 至43 小節,四個調式的旋律動機還是通過“點”狀方式來表達:一種是八度雙手交替的方式,一種是通過左手隱約出現的重音來呈示旋律動機。例如23 小節開始,降E音從小字二組至大字一組直轉急下的同音反復,后出現兩次八度交替的五聲旋律動機,經過兩小節的八度同音反復后,突然回到小字二組再次重復此動機,這是第一種方式;在第32至35小節可見左手重音勾勒出的隱約出現的旋律動機,這便是另一種表達方式。此段中,兩種表達方式相互交融、配合,再加上音域和調式的頻繁變化,使旋律的表達更加豐富了。
如果說以上的旋律都是“點”狀形態的隱性分布,那么從第44小節開始,“線”性旋律占據了主導,旋律更加流動和抒情。該樂段的主旋律是在3-4小節的基礎上進行發展的。
首先在44-46 小節的高音部旋律有了明顯的呈示,但隨后旋律又到了低音部。左手的伴奏音型多以級進為主,以大二度和小三度相連接的“三音組”作為其音調特點,是五聲音調作品常用的創作手法。③以分解和弦手法的螺旋式上升更增添了此部分的連貫和流暢性,左手與右手的伴奏聲部與旋律聲部的交替變換,更體現出了豐富的色彩變化。
例2:

至56 小節,旋律線條又回到了“點”狀,與開頭相呼應。56-57 小節、58-60 小節、61-62 小節分別圍繞降E 音(宮音)、G音(角音)和C音(羽音)采用模進的手法進行構筑,對旋律動機進行重復和發展。63 小節后,旋律中心音逐漸回到降E音直至結束。水墨畫中,山水輪廓連綿不絕,鋪滿畫面,與浮云相輝映,漸沒于遠端;曲中,主題旋律點線的相互交融、配合,猶如水墨畫的明暗交替,具有獨特的“中國之美”。
二、“豐富多變”的調式調性
開始,核心音高降E音的同音反復出現比較明顯地表現為降E 宮調式,持續了九小節之后,降B 宮調式出現直至22 小節結束。這一部分的調式變化比較單一,兩個調式都是圍繞著各自的中心音(宮音),通過主題的隱現來發展的。第23小節又回到降E宮調式,以模進的形式和動機式的旋律音調進行展開,遵循“以清角為宮”的旋律,進行了四次同主音調式轉換,分別為:降E宮調——降A宮調(即降E徵調)——降D宮調(即降E商調)——降E宮調。這四次調式的轉換手法比較急促而直接,前三調都是不斷通過以前調的清角為宮音的方式,也就是等音轉調的方式向后推進,后回到降E宮調,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此處的調式轉換看似無形卻有形,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的轉調手法。
從第44小節開始,一改之前調性的有序進行,進行了自由、頻繁的調性變化,并且具有相對密集的音群,較前面相比,呈現出高度的復雜化,造成了結構的不穩定感,音樂形態在色彩上發生轉變,調性變化為:F 宮調——降E 宮調——G宮調——F宮調——降E宮調,各調宮音相隔較近,多為二度和三度關系,調性轉換是游移而委婉的;這里急促而直接的轉調方式與前面相差四度的轉調關系形成了鮮明對比。至56小節,調性又回到降E宮調,在織體形態上與開頭點狀、顆粒的聲音遙相呼應,調式調性回歸至明確地降E宮調上。此段的音域不斷地疊置升高,至63-66 小節旋律逐漸停滯,多以降E音的同音反復來鞏固調性直至結束。在最后兩個小節中,對核心音高材料“E”音做了綜合的再現,樂曲的最后三個結束音的調性變化為:降G宮(降E羽)——降A宮(降E徵)——降E 宮。這微妙的調性轉換,與“承”樂段中的同主音轉調呼應。
調性既有規律的形態變化,亦有豐富多變的內容,濃淡得宜,首尾呼應,如同水墨畫中的筆法,有繁有簡,美不勝收。
三、“歐亞合璧”的曲式結構
《敬獻中華》在曲式結構上比較明確地彰顯出了中國音樂的結構特點,整體織體形態以“點”狀為基礎,“線”狀為點綴,“點”與“線”結合,勾勒出音樂的骨架,全曲分為“起、承、轉、合”四個部分。
“起”這一部分的整體音響是比較平緩的,很節制地使用音高材料,通過大量的同音反復勾勒出隱藏的內在旋律主題,著重于對琵琶音色的描寫。
“承”部分和“起”部分類似,通過八度同音反復來加強對琵琶輪指技巧的模仿,并在調式調性上比“起”部分更加多元化,不像“起”段中那么單一和明確。節奏節拍的交替變化,音域音區的反復橫跳,調式調性的急速轉換,音樂表情的豐富變幻,旋律動機的隱約出現,使“承”這一段的音樂語言豐盈飽滿。
“轉”的部分在織體寫法與前兩部分形成了鮮明對比,色彩更加柔和、流動,猶如傾訴之態。如果說前兩部分的在音響上體現出的是“顆粒感”的“點狀”聲音形態,那么這一樂段則強調的是“線條化”的旋律特點,這一部分的調性不停地游移、變化,造成了結構的不穩定。
“合”這一樂段具有明顯的回歸意義,在整體結構和調性布局上頗具三部曲式中“再現”的意味,與“起”段相呼應,調式再次回降E宮調,聲音又回到“點”狀形態,最后兩個小節是對核心音高降E進行重復和再現。這一樂段的“回歸”不僅表現在調式上,還表現在速度上。54-55 小節恢復原速后,從56 小節開始速度為Presto(急板),力度為p(弱),后面持續的漸強直至最后一小節,樂曲的力度和音域達到最高點,采用強力度、高頻率的琶音音型來演奏,緊接著降低和弦的強弱,以頗具補充終止意味的三組和弦收尾。此段的力度由弱到強,速度也從Allegro(快板)變為Presto(急板),有飛流直下,勢如破竹之意。
總的來說,作品在曲式結構上既具有西方傳統曲式的中的“嚴謹”,又具有傳統民間音樂的“自由”,這正是齊爾品“歐亞合璧”理念的體現。
從表1可見,整部作品是架構在對核心主題的不斷變奏發展上的,采用“多主題變奏”的曲式結構特點;主題間的穿插反復循環,又頗具“回旋曲式”的性質,呈現出自由的多段體結構。
四、“極盡意境”的樂器模仿
1.對琵琶音色的模仿
《敬獻中華》是模仿琵琶輪奏聲音作成的幻想曲,體現出了鮮明的“中國風格”。琵琶是我國的民族樂器之王,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演奏力和表現力突出。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把演奏琵琶時的狀態描寫得繪聲繪色,筆者認為這首詩歌與這首《敬獻中華》的意境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人通過詩句來表達,那么音樂家就用音符來擬態。齊爾品先生做到了這一點,具體運用的手法就是在鋼琴上對琵琶中的輪指和掃拂技術進行模仿。
輪指是在琵琶演奏中常用的特殊技巧,精髓在于將右手五個手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拇指、大拇指)依次觸弦,連續輪動,使著力點持續不斷,發出似珠落玉盤的鏗鏘之聲④,這與鋼琴中的“同音換指”技巧相似。此技術貫穿全曲,但除此技術,“起”段還加入了“掃拂”技法。在琵琶演奏中,“掃”為食指從右到左急彈四根弦,“拂”為拇指從左向右急挑四根弦,“掃”與“拂”如出一聲,兩種技法結合在“起”段,氣勢磅礴,一唱一和,頗具琵琶武曲之妙。
譜中的第1、8、9、18 小節出現的三十二分音符構成的五聲音階,是琵琶“掃”技法的體現,17、19是“拂”技法的體現,迅速將聽眾帶入琵琶疾風驟雨般的場景,展示出“四弦一聲如裂帛”的感覺,表達了琵琶的清脆、明亮、極具穿透力的音色特點,模擬出民間彈撥樂的風味,隨后雙手交替的輪指技術模仿了琵琶演奏中的輪指演奏技法,具有鮮明的顆粒性。
例3:“掃”

例4:“拂”

“承”部分的織體形態與“起”相似,依舊是大篇幅地運用同音反復,對琵琶的輪指奏法特點進行模仿,但這里又運用了八度重復,比前一段的單音重復更有張力,左右手的交替演奏更有“嘈嘈切切錯雜彈”之意,有琵琶武曲的氣勢磅礴之感;至“轉”段可以看出織體的明顯變化,旋律表達更加流暢、婉轉,“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就是說的此段,具有琵琶文曲的高山流水之妙。“文”中有“武”的因素,使全曲的表達層次更加豐富,維度更顯多元化。最后一段又回到了對輪指技術的模仿,雙手的交替螺旋上升,極具層次感,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意境。
2.對鑼鼓因素的運用
主要體現在“混合拍子”和八度同音交替反復上。“混合節拍”在中國民族打擊樂中極為常見,此曲采用這種多節奏的形態,大大地凸顯了其中國風格。此曲一開始為4/4拍,后來在第5、6、11、13、22、23、27、28、37、38、56、57 小節,以4/4 拍為軸心,共轉換12 次,分別為5/4、4/4、3/2、4/4、3/4、4/4、3/4、4/4、3/2、4/4、5/4/、4/4拍。⑤頻繁的節拍反復變換,在這首篇幅較小、只有68 小節的曲子里,體現出了相當了的表現力,具有鮮明的戲曲鑼鼓效果。
以鋼琴的八度同音交替反復既可以表現琵琶輪指的聲音,也可以表現鑼鼓形象。例如54-55 這兩個小節,我們可以看到上方的速度標記a tempo(回原速)和力度標記sff(突強)。速度的急劇變化以及突強的力度效果,好似鑼鼓密集而有力的敲擊,暗示了對民間鑼鼓樂器因素的運用。
例5:

水墨畫中,畫面的留白手法加強了形神兼備之感,如同曲中自由、多變的節奏,既有運筆流暢,又有重墨陪襯。
五、結語
對琵琶奏法的模擬,鑼鼓元素的加入,旋律的若隱若現、調式調性、速度以及節拍的急劇變化,勾勒出一幅富有張力又別具風格的中國水墨畫,虛實交替、濃淡相宜,體現出了鮮明的“中國風格”,在這部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齊爾品那顆熾熱的中國心。⑥
注釋:
①Reich,Willi:Alexander Tcherepnin.Bonn:M.P.Belaieff 1961.P30
②李吉提.中國音樂結構分析概論[M].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
③彭靜雯.齊爾品《Five Concert Etudes》的“中國風格”探討與教學演奏[D].上海師范大學,2013.
④李文清.淺析琵琶輪指練習方法[J].大眾文藝,2010(24).
⑤竇青,楊成秀.齊爾品的中國風格鋼琴練習曲創作[J].中國音樂學,2006(4).
⑥梁茂春.齊爾品的中國風格鋼琴曲——為“向齊爾品致敬音樂會”而寫[J].鋼琴藝術,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