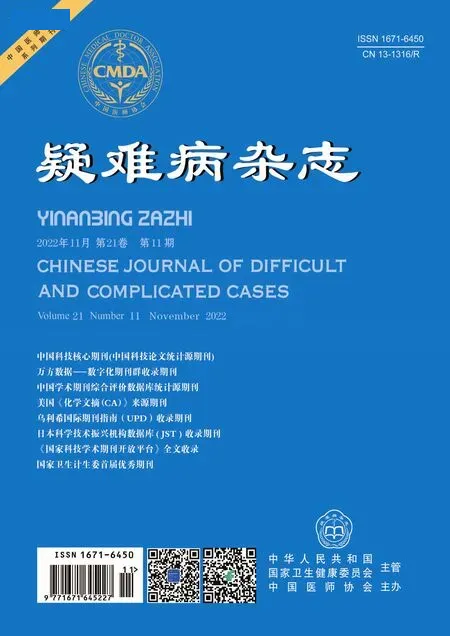益生菌治療炎性腸病的研究進展
楊敏琪,張吉翔綜述 董衛國審校
炎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組病因尚未闡明的慢性非特異性腸道炎性疾病,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CD)。UC主要為局限于黏膜和黏膜下層的連續性炎性反應,病變多自直腸開始,可累及全結腸甚至末段回腸;CD則為節段性的肉芽腫性炎性反應,可累及消化道任何部位,但多常見于末段回腸和鄰近結腸。IBD的傳統治療方法包括氨基水楊酸制劑、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生物制劑等,都可抑制腸道炎性反應,但存在價格高、安全性低、不良反應明顯、治療作用有限等缺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注意到益生菌在治療IBD中的顯著作用。本文就腸道菌群與IBD的關系、益生菌在IBD治療中的臨床應用及其作用機制作一綜述。
1 腸道菌群與IBD
1.1 腸道菌群 人體腸道微生物群由10萬億~100萬億微生物組成,其數量約為人體細胞的10倍[1]。腸道菌群種類多達1 000余種,主要分為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放線菌門、變形菌門[2],其中擬桿菌門和厚壁菌門為優勢菌門。在消化道的不同部位,細菌的種類和數量均存在差異,從胃到結腸,細菌的數量逐漸增加,結腸的細菌數量約為1012CFU/ml,以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為主[3]。近年來,腸道菌群被認為是一種“內分泌器官”,它們在維持腸道正常生理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營養代謝、促進機體免疫系統的成熟、參與腦—腸軸調節等功能;其與機體為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研究表明,吸煙、飲食、抗生素的使用及情緒的變化等因素均可作用于腸道菌群,引起有益菌的豐度下降,致病菌的豐度升高,從而引起腸道炎性反應[4]。
1.2 菌群與IBD 許多研究表明,IBD的發病機制為在環境、遺傳、飲食、腸道菌群等因素的作用下,啟動了腸道免疫反應,破壞腸道免疫穩態[5-6],進而引起腸道慢性炎性反應。近年來,腸道菌群與IBD的關系越來越受到重視。一些動物實驗表明,在腸道無菌的條件下,遺傳易感小鼠不會發生腸道炎性反應;此外,IBD最好發于腸道細菌數量最多的部位,且在腸道細菌數量最多和豐富度最大的部位疾病活動最明顯[7];抗生素治療可在一定程度上使IBD患者獲得臨床改善[8];益生菌、糞菌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等調節腸道菌群的方式也被證明是安全且有效的方法[9]。以上均可說明腸道菌群與IBD發病的相關性,但腸道菌群與IBD之間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研究發現,IBD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腸道菌群失調,主要表現為總體微生物多樣性降低,腸道有益細菌數量減少,致病細菌數量增多[6, 10]。IBD患者腸道菌群中,厚壁菌門豐度減少,而變形菌門,包括大腸桿菌豐度增加[5]。一項研究表明,病變部位不同的患者,其腸道菌群存在差異;有研究表明,疾病活動度越高的患者,其腸道中腸桿菌數目也越多,但未發現UC患者疾病活動度指數與腸道菌群間有明顯關聯;此外,病程較長的IBD患者的腸道菌群中變形桿菌的豐度增加[11],即IBD患者的病變部位、疾病活動度及病程等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腸道菌群。綜上所述,腸道菌群與IBD關系密切且相互影響。因此,治療腸道菌群失調越來越成為IBD綜合治療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2 益生菌在IBD治療中的臨床應用
根據國際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學學會(ISAPP)發表的共識聲明,益生菌是指“當施以足夠量時對宿主健康有益的活的微生物”[12]。益生菌種類繁多,人體內就有超過400種。從目前已報道的益生菌來看,大致可分為以下5類:乳桿菌類,如干酪乳桿菌、植物乳桿菌、嗜酸乳桿菌等;雙歧桿菌類,如長雙歧桿菌、短雙歧桿菌等;芽孢桿菌類,如布拉地芽孢桿菌、丁酸梭狀芽孢桿菌等;鏈球菌屬:如嗜熱鏈球菌;腸球菌屬,如耐久腸球菌、糞腸球菌等[13]。已有大量研究證實,益生菌在緩解或治療IBD中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益生菌可提升腸道黏膜自身預防機制,且可拮抗致病菌的致病作用,還可以控制炎性因子的釋放及短時間內恢復腸道菌群[14]。
2.1 益生菌作用于UC 大量臨床研究表明,益生菌及其制劑對于UC患者的活動期誘導臨床緩解和緩解期預防復發均有一定作用[15]。日本的一項多中心試驗結果顯示,長雙歧桿菌可有效促進輕至中度活動性UC患者的臨床緩解[16]。乳酸桿菌GG在緩解UC效果方面與美沙拉嗪差異無明顯統計學意義,但在延緩UC復發方面則更有優勢[17]。一項研究評估了不同條件下益生菌對IBD患者的療效,結果顯示不同益生菌在不同條件下對UC患者均有明顯療效[18]。VSL#3是一種益生菌混合物,其已被證實可減輕腸道炎性反應及促進腸黏膜修復[19]。Akkermansia 菌是一種屬于疣狀結腸菌門的益生菌,對宿主腸道炎性反應有著顯著的緩解或治療作用,已有動物實驗證實其可顯著改善葡聚糖硫酸鈉(DSS)誘導的急性結腸炎小鼠的癥狀[20],未來有望成為治療UC的有效制劑。但目前益生菌在維持UC患者的臨床緩解方面尚未顯示出明顯優勢[21]。
2.2 益生菌作用于CD 有研究表明,益生菌對于CD活動期的治療及緩解期的維持方面未有明確優勢[22]。一項對照試驗表明,布拉迪酵母菌可使CD患者的腸道屏障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23]。研究發現,給CD患者補充可產生丁酸鹽的細菌可增加患者腸上皮屏障的完整性[24]。CD患者在接受回腸切除術和回結腸吻合術后30 d內接受VSL#3治療,其90 d和365 d內鏡復發率及結腸黏膜促炎細胞因子水平均降低,早期使用VSL#3治療能獲得更好的療效[25]。在一項研究中,將61例CD患者隨機分為2組,分別給予益生菌補充劑及安慰劑,結果顯示2組患者之間的黏膜炎性標志物水平及臨床疾病活動度沒有明顯差異,亦未觀察到嚴重的不良反應[8]。益生菌對于CD是否具有治療作用仍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
3 益生菌治療IBD的作用機制
隨著對益生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其緩解或治療IBD的機制也逐漸被揭示出來。其在IBD中的作用機制如下。
3.1 調節腸道菌群 腸道菌群失調是促進IBD發生與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研究發現,益生菌能夠通過Toll樣受體促進Th1細胞分化,進而改變黏膜免疫系統,增強腸道保護功能,增加腸道菌群多樣性[7]。有研究表明,植物乳桿菌Q7的細胞外囊泡(EV)可調節腸道微生物群,增加腸道中乳酸桿菌、雙歧桿菌等有益細菌的豐度并降低變形桿菌等有害細菌的豐度[26]。益生菌還可通過競爭營養、拮抗等方式與腸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降低致病菌活性,以及產生某些抑菌性物質,如有機酸,直接抑制病原菌的生長[27]。上述研究表明,益生菌可以通過調節腸道菌群影響IBD的發生和發展。
3.2 調節腸道免疫,減輕腸道炎性反應 宿主與腸道菌群之間的互利共生關系被破壞,腸道免疫穩態被破壞,可導致IBD的發生。免疫和炎性反應需要細胞因子的參與,IL-6是一個關鍵的炎性反應因子,其水平在IBD中升高[28];TNF-α是IBD的重要調節因子,也是調節腸上皮細胞增殖和凋亡的主要因子;IL-10可限制并最終終止T細胞對微生物病原體的過度反應,以防止慢性炎性反應和組織損傷。梭狀芽胞桿菌屬會影響結腸中上皮內淋巴細胞(IELs)的積累并增加Treg細胞的數量,從而抑制炎性細胞因子(TNF-α、IL-12、IFN-γ、IL-1β和IL-6)的表達,并上調抑制性細胞因子(IL-10)的表達,此外,丁酸梭菌產生的丁酸鹽可以通過抑制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直接促進Tregs的分化[29-30]。研究表明,DSS誘導的結腸炎小鼠應用Q7-EV下調了Toll樣受體4(TLR4)及MyD88基因表達,與配體結合后,MyD88依賴性信號轉導可能導致NF-κB的磷酸化,從而調節IL-1β、IL-6和TNF-α轉錄因子的水平,即Q7-EV通過調節TLR4-MyD88-NF-κB途徑改善了結腸炎[26]。一項評估了不同益生菌在二硝基苯磺酸(DNBS)結腸炎模型中的抗炎作用的實驗結果顯示,IL-1β和TNF-α與miR-155和miR-223之間存在正相關性,EcN能夠顯著降低miR-155和miR-223的上調表達[31]。最近有證據表明,益生菌可以通過調節樹突狀細胞(DC)的成熟和產生耐受性DC(tolDC)來影響免疫調節,反過來又可能抑制炎性反應。脆弱雙歧桿菌衍生的外膜囊泡(OMV)的多糖A(PSA)能夠通過影響DC來改善DSS誘導的小鼠的結腸炎[32]。綜上,益生菌及其代謝產物可通過多種途徑調節腸道免疫功能,減輕腸道炎性反應。
3.3 增加機體抗氧化能力 氧化應激在IBD相關組織損傷中起重要作用。氧化系統主要包括產生過量的ROS,可誘發氧化應激,引起脂質過氧化,導致結腸黏膜損傷[33]。SOD是一種重要的過氧化物分解酶,其可以抑制腸道中的脂質過氧化,并通過降低氧自由基的水平來穩定細胞膜[34]。植物乳桿菌ZS62通過改善腸道氧化應激對DSS誘導的IBD發揮緩解作用,其可促進GSH-Px的產生并催化H2O2的分解,從而消除過氧化應激產物,防止ROS介導的細胞損傷,同時可以通過增加體內T-SOD、Cu/Zn SOD和Mn SOD的水平來清除自由基[35]。Nrf2信號通路在細胞抗氧化防御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生理條件下,細胞質蛋白伴侶Keap1與Nrf2相互作用以保持靜止狀態。在發生氧化應激時,Nrf2能夠從Keap1中逸出并轉移到細胞核并誘導一系列抗氧化酶(SOD、CAT和GSH)基因的轉錄,布拉氏酵母菌可促進Nrf2信號傳導激活,減輕氧化應激導致的結腸損傷[36]。總之,上述研究證實了益生菌在增加腸道抗氧化應激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3.4 降低腸道通透性,增強腸道屏障功能 腸道屏障由單層柱狀上皮細胞組成,這些細胞由緊密連接蛋白(TJP)連接,包括occludin、ZO-1、claudin等。分泌蛋白黏蛋白-2(MUC-2)也是結腸中保護性黏液層的主要成分。UC中TJP復雜性受損和TJP的下調可能是導致腸屏障功能障礙的重要機制[37]。研究表明,雙歧桿菌可上調ZO-1、MUC-2、Claudin-3和E Cadherin-1 這4種TJP的水平[38],植物乳桿菌-12也通過上調MUC-2表達來增強腸道屏障功能[39]。在DSS誘導的結腸炎小鼠中,MUC-2水平與Akkermansia菌豐度呈正相關,可通過補充Akkermansia菌增加結腸黏液層厚度,加強結腸黏膜屏障[20]。短鏈脂肪酸(SCFAs)是腸道微生物的代謝產物,包括乙酸鹽、丙酸鹽和丁酸鹽等,具有緩解炎性反應、保護腸道屏障功能、維持上皮完整性等重要作用。丁酸梭菌可以通過丁酸激酶(buk)途徑產生丁酸鹽,這可能是其發揮腸上皮保護作用的機制之一[30]。另一項研究表明,在急性腸道損傷后,IL-17A可以通過調節TJP水平來降低腸道通透性并保持屏障完整性[40]。有研究證實,丁酸梭菌588(CBM 588)顯著促進了結腸固有層(cLP)中產生IL-17A的γδT細胞和CD4細胞的擴增,這有助于保持腸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37]。綜上所述,益生菌可通過上調TJP水平、增加腸道黏液層厚度等方式發揮其腸道保護作用來緩解或治療IBD。
4 總結與展望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益生菌在調節腸道菌群、調節腸道免疫,減輕腸道炎性反應、增加機體抗氧化能力、降低腸道通透性、增強腸道屏障功能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益生菌或可成為緩解或治療IBD的新手段。但目前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益生菌的給藥劑量、給藥間隔及療程等,且其不良反應尚存在爭議,未來需要更多的臨床試驗進行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