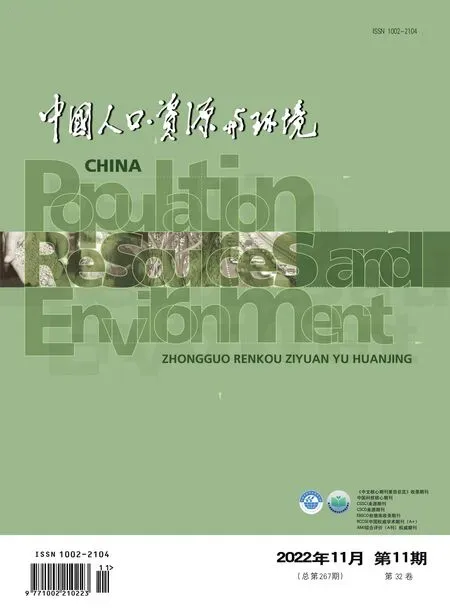碳交易機制下林業碳匯產品類別比較與價值核算模型甄別
張 楠,儲安婷,楊紅強,3
(1.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37; 2.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林產品經濟貿易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37; 3.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92)
在碳達峰及碳中和氣候背景下,中國宣布國家自主減排貢獻新舉措,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然而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仍以高碳為主,需要發揮林業生態系統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的作用,以抵消實施減排措施后剩余的碳排放[1]。以林業碳匯被納入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為起點,通過碳市場交易核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推動林業活動,發展林業碳匯已成為促進碳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技術路徑[2-3]。中國為主要的森林碳匯貢獻國之一[4],但尚未建立成熟完備的林業碳匯交易體系,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交易市場依托建立于CDM開發機制框架下,但碳匯產品開發難度大、成本高,市場交易不活躍,2017年為規范碳市場繼而暫停CCER 項目的審定和備案申請[5]。2021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正式啟動,國家鼓勵通過林業碳匯項目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的替代、吸附或減少[6-8]。在碳中和目標背景下,借鑒現有碳交易減排機制推動林業碳匯CCER項目已成為新的發展訴求。
1 研究背景
林業碳匯交易推動林業系統納入氣候框架,林業成為緩解氣候變化的重要方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COP3,1997年)通過《京都議定書》,基于《京都議定書》建立了三種靈活的碳減排機制,包括“聯合履約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潔發展機制”和“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s Trading, ET)。其中,JI和ET是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碳減排機制,CDM建立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減排項目合作機制。《京都議定書》積極倡導將林業碳匯納入CDM碳交易市場,通過市場機制促進碳匯林業發展。基于《波恩政治協議》(COP6, 2001年)和《馬拉喀什協定》(COP7, 2001年),第一承諾期(2008—2012年)的CDM項目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林業碳匯項目抵消其部分溫室氣體排放量,標志著林業生態系統的氣候價值得到世界范圍的正式承認。
基于林業碳儲量的經濟激勵會引致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決策變動,進而影響林業碳匯項目的實施效果[9]。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COP13,2007年)通過《巴厘行動計劃》,根據相對于基線的額外碳儲量給予生態補償以促進森林碳儲[10-11],相關林業活動包括延長人工林輪伐期,進而在輪伐期內積累更高碳儲量[3]。在此基礎上,《巴黎協定》(2015年)將林業視為氣候解決方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REDD+(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保持和增加森林碳匯)等造林再造林項目籌集資金,林地所有者可根據碳儲量獲得碳補償[9-10]。然而林業碳匯項目的經濟激勵面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困境[9],需要通過有效的市場交易機制充分發揮林業碳匯項目在緩解氣候變化中的作用。
林業碳匯進入碳交易機制有利于賦予林業碳匯經濟價值,發揮林業減排功能。林業碳匯產品是能在碳排放權市場進行交易的林業碳匯[12]。林地所有者利用林木資源所產生的碳匯量,通過計量與核證成為標的資產,在碳排放權市場進行交易,抵消重點排放單位的碳排放量,進而發揮林業碳匯產品的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6,12]。人工林碳匯成為減少二氧化碳的低成本替代方案[13],CDM林業碳匯項目將土地用途轉變為可儲碳的人工林[3,14-16]。新造林和幼齡林吸收二氧化碳,但需要生長時間產生木材收入[17-18],因此在生長初期需通過林業碳匯產品的交易獲取經濟激勵促進造林項目的實施[19]。林業碳匯項目可持續經營是提高森林碳儲量并協調溫室氣體減排的有效方式[20],需通過林業碳匯產品進行核算與支付,從而發揮林業碳匯抵消作為重要補充機制的作用以促進碳中和目標的實現[21]。
中國林業碳匯以林業碳匯項目為載體,通過核證獲得的CCER入市交易,獲取碳匯收益。源于CDM的CCER項目原為能源部門減排項目,核證標準依托建立于CDM方法基礎之上[22],缺乏針對林業碳匯特征的產品分類及價值核算模型。林業碳匯項目的價值實現需通過碳匯產品的核算與支付,但目前林業碳匯產品與林業碳匯項目及交易機制之間尚未建立成熟完備的體系,林業碳匯項目的發展面臨挑戰。隨著CCER政策重啟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碳抵消市場及科學經營森林管理的現實需求,需要明晰林業碳匯產品分類及價值核算模型,結合CCER現存問題與林業生態實際情況優化林業碳匯產品的核證規制框架。
該研究通過梳理林業碳匯產品的市場化進程,比較不同碳匯產品類型及其價值核算的模型選擇,為科學評估林業碳匯項目的碳價值并助力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提供科學依據。首先,比較國內外林業碳匯交易市場機制,分析中國林業碳匯市場化困境;其次,明確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決定因素,辨析林業碳匯產品及林業碳匯項目的關聯機理,闡明主流林業碳匯產品的分類和差異;最后,基于“碳量”標準,闡釋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的針對性及適用性。以中國林業碳匯產品特征及交易機制現狀為現實基礎,為林業碳匯產品市場化發展和規模開發林業碳匯CCER項目提供對策建議。
2 林業碳匯交易機制及中國林業碳匯的市場化困境
林業碳匯交易既能充分發揮林地自然資源資產權能的經濟價值,也能兼顧碳中和目標的實現[12]。林業碳匯項目作為林業碳匯開發、交易、碳匯價值實現與管理的重要載體[23],通過林業碳匯交易實現氣候減排和經濟效益雙重價值。要正確識別林業碳匯產品及其功能實現,有必要梳理國內外林業碳匯交易機制,分析中國林業碳匯的市場化困境。
2.1 當前國內外兩種林業碳匯交易機制
國內外林業碳匯交易可分為自愿性碳減排市場機制與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圖1)[22]。在林業碳匯交易市場發展初期,林業碳匯產品主要通過自愿性碳減排市場機制交易,隨著碳市場交易總量攀升及政府強制減排政策完善,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的交易量明顯增加,形成多類型的林業碳匯項目[24]。

圖1 國內外兩種主要林業碳匯交易市場機制及碳匯產品比較
國際自愿性碳減排市場機制主要涉及國際核證碳減排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和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 GS)兩種類型。VCS強調企業通過林業碳匯交易在減少大氣溫室氣體方面的貢獻,而GS旨在提高林業碳匯交易透明度及減排有效性[22,25]。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以CDM林業碳匯項目為主體,通過造林再造林等林業活動進行以CER為標的物的林業碳匯交易[22]。
中國林業碳匯交易以CDM林業碳匯項目起步,分別從國家和區域層面構建了自愿性與強制性相結合的林業碳匯交易機制。自愿性碳減排市場機制下,林業碳匯主要通過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CGCF)和大型活動碳中和兩個國家平臺進行交易;區域層面以單株碳匯交易與林業碳票交易為主。強制性碳交易市場以國家層面的CCER 林業碳匯項目為主,輔以區域層面的碳普惠林業碳匯項目[22],各省根據森林生態資源稟賦在 CCER 基礎上開發林業碳匯項目。這些林業碳匯項目亦可參與大型活動碳中和的自愿碳減排交易項目。
自愿性與強制性兩種機制類型的林業碳匯項目在項目標準、實施目的、交易要求等均存在較大差異。首先,兩者減排目標設定存在差異。自愿性碳減排市場機制下的減排量額度為協議制定;而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下由國家界定排放配額[26]。其次,兩者項目實施目的不同。前者多為企業提升綠色環保形象,而后者有明確減排目標。基于以上差異,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對土地合格性要求更為嚴格。林業碳匯交易引入自愿性碳減排機制降低了總體減排成本, 同時以CDM為主體的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吸引了總量限額范圍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 擴大了林業碳匯市場化交易的影響范圍。
2.2 中國林業碳匯參與碳市場的困境
中國自愿性碳減排市場機制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設計上為林業碳匯產品自愿交易保留發展空間。此外,中國碳市場允許林業碳匯項目通過核證獲得的CCER入市交易,明確了林業碳匯可參與強制性碳交易市場。為促進中國林業碳匯的市場化進程,先后頒布《造林項目方法學》等文件用于林業碳匯CCER項目的開發,但從前期市場來看林業碳匯項目在CCER市場中所占比重很小。從CCER體系2013年啟動至2017年暫停,已進行審定公示的林業碳匯項目占3.4%,備案公示的林業碳匯項目僅占1.5%[22,27]。林業碳匯CCER項目的開發與經營存在限制,中國林業碳匯參與碳交易市場面臨著諸多困難。
一方面,現存林業碳匯項目方法學難以適配中國林業碳匯的市場化需求。源于CDM的CCER項目方法學很大程度上沿襲了CDM項目減排量抵消碳排放的方法框架,缺乏林業碳匯產品在基線設定、項目邊界、額外性規定等方面的方法學改進[9,28]。另一方面,林業碳匯產品未能通過碳交易充分發揮實際抵消碳排放的水平[22]。林業碳匯產品分類不明晰,產品的價值決定尚未形成嚴格且明晰的碳核算機制,監管機構對林業碳匯交易的監管不足[12],存在核算方法學的錯配,降低林業碳匯產品的減排有效性[29-30]。中國林業碳匯參與碳交易市場仍存在林業碳匯產品分類體系和價值核算方法學的挑戰。
3 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決定與類別比較
3.1 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決定
林業碳匯產品以“碳量”為標的資產進行交易,具有自然資源屬性、資產可交易性、時間期限性等特性[2,12,22]。因此,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決定涉及林業碳匯類型、碳匯交易制度、項目投資周期及價格決定機制等四個方面[12,31-34]。第一,林業碳匯類型包括造林碳匯和森林經營碳匯,前者通過造林促進增匯,后者則是通過對現有林木資源的合理經營而提高碳匯水平,農戶對碳匯林具有高度依存性,造林性質的林業碳匯產品更能發揮自然資源資產權能的經濟價值[12]。第二,碳市場是制度性市場,林業碳匯的市場需求源于政府對限排企業的抵減規定[31],碳匯需求量的變化決定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實現。但中國林業碳匯交易制度供給有效性的欠缺,終致自然資源資產權能的錯配和失效[12],折損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32]。第三,林業碳匯交易受到林木生長周期性的影響,林業碳匯項目的長期性需利用林業碳匯產品的時間期限以提高投資管理靈活性[33]。因此,契合項目投資周期的林業碳匯產品更具交易價值。第四,通過碳匯交易形成碳匯產品的價格決定機制[34]。林業碳匯產品由于方法學的復雜性和碳排放的抵消受到比例限制,其在碳市場的價格低于碳配額的價格,價格波動性大,從而阻礙林業碳匯產品價值實現。
3.2 林業碳匯產品和林業碳匯項目的關聯機理
林業碳匯項目通過林木種植,依據木材收益與碳匯收益不同的森林管理目標,優化選擇采伐方案,通過市場交易林業碳匯產品以實現價值,二者的關聯機理見圖2。林業碳匯產品結合輪伐期模型與碳量計算標準,重點考慮林業碳匯項目的長期性和非持久性,二者的關系還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圖2 林業碳匯產品與林業碳匯項目的關聯機理
第一,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核算需依據林業碳匯項目的最優輪伐期和“碳量”評估[35,39]。林業碳匯項目涉及木材收益和碳匯收益的雙重核算問題。其中木材收益需確定最優輪伐期問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經典的Faustmann模型、林租模型、木材產量模型等[35-38];碳匯收益需通過林業碳匯產品合理計算項目期內的碳匯價值變動,即“碳量”是其本質問題,主要包括碳總量模型、碳均量模型及碳增量模型[2,40-41],這是該研究后續甄別比較的重點問題。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核算,需要通過Faustmann等模型確定林業碳匯項目的最優輪伐期,更進一步需要基于“碳量”核算模型確定輪伐期變動引致的碳匯價值波動。
第二,林業碳匯產品的碳量標準是林業碳匯項目長期決策的重要依據[42-44]。基于項目期碳儲量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變動,林業碳匯項目對樹種選擇、森林管理及采伐方案作出長期性決策調整[45-48]。以碳量計算為標準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可與Faustmann模型結合,基于林地的資產和生態雙重價值特征,依據林業碳匯項目期內采伐管理方案變動引致的碳收入及碳支出項,優化提出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核算公式,為林業碳匯項目的長期性決策提供依據[42-44]。
第三,林業碳匯產品的“時間期限”是林業碳匯項目非持久性的解決方案[49-50]。林業碳匯產品具有有效期,其“時間期限”會對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提供靈活性。林業碳匯項目所產生的碳匯不能夠被永久固定,因而非持久性是林業碳匯項目區別于其他CDM項目的重要特征。項目期碳儲會因林業采伐等管理活動重新釋放回大氣中[51],這段持續時間是研判林業碳匯項目價值的重要因素[50]。林業碳匯產品可結合貼現率變化和永久性碳匯產品的預期價格,調整時間期限以符合林業碳匯項目期內的價格期望及管理靈活性,解決林業碳匯項目的非持久性[21,49]。
林業碳匯項目需通過林業碳匯產品為中介進行市場交易,因此需明晰林業碳匯產品的類別與特性差異,以期為林業碳匯項目提供林業碳匯產品選擇標準。
3.3 林業碳匯產品的類別比較
3.3.1 兩種市場機制下林業碳匯產品的主要類別
林業碳匯產品依托林業碳匯項目進入自愿性碳減排、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進行交易,以項目減排目標為前提,獲取經濟收益以促進造林和再造林項目實施,充分發揮林業生態系統的作用。當前兩種市場機制下碳匯產品主要有兩類,分別是基于政府碳減排目標而設定的排放配額和基于減排機制項目的減排量(圖1)。
減排機制涉及ET、JI和CDM項目,其中ET允許締約方之間直接通過交易配量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 AAU)或清除單位(Removal Unit, RMU)實現減排承諾。JI和CDM要求締約方之間進行減排項目合作實現減排,前者涉及減排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的交易和轉讓,后者以CER為交易標的[52]。這4種碳匯產品適用于包括所有減排項目,其中CER是目前交易最為廣泛的碳匯產品類型。
該研究的林業碳匯項目重點問題中,自愿性碳減排市場下,VCS項目依托造林、森林管理等林業碳匯項目進自愿交易自愿碳單位(Voluntary Carbon Unit, VCU);強制性碳交易市場下,通過實施CDM造林再造林等林業活動獲得CER以抵消排放量。國內的林業碳匯交易沿襲CDM 基于林業碳匯項目減排量抵消碳排放的機制,林業碳匯是CCER交易的一種產品類型。CDM框架下的碳匯產品和碳核算體系是林業碳匯價值研究的主流[20],以CCER為代表的國內林業碳匯產品在方法學設計上借鑒CDM框架,因此下文將深入梳理CDM框架下林業碳匯產品的類別差異,為中國林業碳匯產品在碳市場發揮更重要參與度并助推全社會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提供依據。
3.3.2 三種碳市場交易核證減排量碳匯產品的比較
(1)臨時核證減排量(Temporary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tCER)、長期核證減排量(Long-term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lCER)及CCER的關聯屬性。CDM有減排項目和增匯項目兩種項目類型,均通過交易CER實現減排,其中“減排項目”主要涉及能源項目通過交易CER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增匯項目”指通過造林、再造林等林業碳匯項目活動交易CER。上述增匯項目中,1單位CER為樹木中儲存的1噸二氧化碳當量 (1 t CO2e),其驗證由 CDM 執行機構每5年核查1次[53],根據不同驗證期的碳儲量變化發布 tCER和lCER兩種碳匯產品。CCER林業碳匯項目沿襲CDM機制框架,因而CCER與CER本質相同,均通過林業碳匯項目的造林再造林等活動產生碳匯抵消碳排放以實現減排目標。
(2)tCER、lCER及CCER的時間期限。上文論述到,“時間期限”是林業碳匯產品的重要特征,基于時間期限尺度定義tCER、lCER及CCER三類碳匯產品,其中CCER是永久性CER,tCER是永久性CER的年租金形式,而lCER介于年租金和永久性減排之間,后兩者旨在降低交易成本。 tCER、lCER不存在普遍適用的定價機制[54],價值取決于項目購買者對未來承諾期價格的期望,因而在tCER、lCER之間的選擇存在投機性[55],前者忽視采伐方案的合理性,后者忽視碳吸收的時間路徑。CCER對核證減排量的劃分未效仿tCER、lCER的期限劃分標準,仍是作為永久性信用進行碳匯交易,因此會通過穩定的定價機制提高減排有效性[21]。
(3)tCER和lCER的差異比較。CDM框架下的碳匯產品核算是林業碳匯價值的主流,有必要就tCER和lCER兩類林業碳匯產品的差異化進行分析,以利正確處理林業碳匯產品進入碳交易并發揮其減排有效性(圖3)。第一,林業碳匯產品有效期不同。根據 CDM 規定,tCER在《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承諾期結束時到期,必須由其他項目取代;lCER的到期因項目期而異,僅在森林碳匯項目生命周期結束時到期[53]。第二,項目期簽發碳信用額的計算標準不同。每5年簽發的tCER數量等于自首個驗證期以來的碳儲總量,而每5年簽發的lCER數量基于兩個驗證期間的碳儲量差異[56]。第三,林業碳匯產品的替換條件不同。林業碳匯項目的非持久性需要林業碳匯產品可被替換來促進項目增匯減排的功能[9],tCER和lCER可被減排機制下的碳匯產品(即AAU、RMU、ERU及CER)替換,其中tCER可用其他項目產生的tCER來替換,但lCER的替換只能使用來自同一項目的lCER[53,57]。

圖3 tCER與lCER的林業碳匯核算差異
基于以上差異,從林業碳匯產品購買者角度來說,tCER與lCER可滿足林業活動的碳匯交易的時間靈活性要求[21]。在5年核查周期內,每年都可利用tCER抵消減排量,到期后需簽訂更多林業碳匯產品;lCER因有效期延長而具有傳遞性,從驗證期到項目結束可用做有效的林業碳匯產品抵消,使其購買者在特定年份增加排放量。
4 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甄別
林業碳匯項目的現行規則允許運用不同林業碳匯產品核算,厘清不同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核算模型有助于完善林業碳匯價值評估,優化林業碳匯產品交易機制,促進碳中和目標的實現[58]。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方法主要有凈現值法、實物期權法、邊際機會成本法及價格替代法等[2,9,40,59],考慮到林業碳匯項目涉及木材和碳匯雙重收益,凈現值法可就整個項目期的收益提供完整的評估框架。該研究以凈現值法為方法學基礎,對不同核算模型的適用性進行比較與甄別。首先,基于“碳量”標準,運用碳總量、碳增量及碳均量三種模型進行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其次,具體分析三個碳量模型對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時的適用性,并比較三個模型應用中的優劣。最后,結合林業碳匯項目的特殊性,從碳價波動反應、樹種適用性、項目管理特性等方面對林業碳匯產品三個碳量模型進行甄別。
4.1 基于“碳量”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
林業碳匯產品的核心價值在于考察其碳儲能力及碳量水平,其價值核算應將“碳量”作為基本前提。基于碳量計算的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將輪伐期變動與項目期碳量計算標準相結合,選擇最合適的核算模型以促進林業碳匯項目的價值實現,其差異在于項目期碳儲量核證及其價格的確定[59-60]。基于“碳量”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主要涉及碳總量模型、碳均量模型及碳增量模型。
4.1.1 碳總量模型
碳總量模型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分為確定CER價格、核證項目期碳儲量及計算項目碳匯價值三步驟(表1)。此處的核算方法假設CER的首次驗證發生在第5年,項目期設置為30年,定義Ct是在時間t(t=5,10,…,25)時森林碳儲量(以噸為單位)。
首先,根據林業碳匯產品碳量計算標準核證碳儲量。項目期碳總量使用tCER核證,為首次驗證期以來的碳儲總量,該標準下的核證碳儲量分別為C5,C10,…C25。其次,確定林業碳匯產品價格。核證項目期碳總量的tCER有效期均為5年,因此無論何時發布,其價格都保持相同,tCER的單位價格定義為p5。最后,計算項目期內林業碳匯產品價值,依據凈現值法定義為WtCER,即式(1)[59],其中r是折現率。

碳總量模型下,林業碳匯產品價格保持相同,每個驗證期的碳儲總量對林業碳匯產品價值的影響更為明顯,因此運用碳總量模型需明確碳儲的核證數量。
4.1.2 碳增量模型
碳增量模型的核算也采取三步驟(表1),差異在于項目期碳儲的核證及其價格的確定[59-60]。首先,碳增量計算標準下的核證碳儲量對應于兩個驗證期間的碳儲量差異,分別為C5,C10-C5,…C25-C20。其次,確定碳增量模型的林業碳匯產品價格。核證項目期碳增量的lCER是根據驗證期間的額外碳儲量發放,有效期因發布年份而異,有效期更長的lCER價格更高[54]。5年期lCER因有效期與tCER相同,價格為p5,不同有效期的lCER價格,使用公式定義,其中,plCERti定義為有效期是ti的lCER的價格。最后,依據凈現值法,碳增量模型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為式(2)[59]。

表1 碳總量、碳增量模型對比

碳增量模型通過價格水平考慮了林業碳匯產品的時間期限性,因此運用碳增量模型需考察驗證期的碳儲量差異及其對應有效期的產品價格。
4.1.3 碳均量模型
除了利用碳總量、碳增量模型核算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林業碳匯項目碳儲量會隨著采伐管理決策而變動,碳均量模型能考慮因采伐決策波動的碳儲量變化進而提高價值核算準確性[3]。用式(3)定義碳均量模型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9],其中:WTτ為項目期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Pc為林業碳匯產品價格,θ表示將木材材積轉化為二氧化碳質量,T為采伐決策前的林業碳匯項目輪伐期,Tτ為因進行后續林業碳匯交易而延長的輪伐期,r是折現率。

碳均量模型可評估采伐決策引致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變動,因此運用碳均量模型時,需考慮歷史碳匯基線以及輪伐期的變動對碳儲量的影響。
4.2 三種“碳量”模型的適用性及優劣比較
4.2.1 三種“碳量”模型的適用性
以項目期“碳量”計算為標準,可利用碳總量、碳均量及碳增量三種模型進行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其中,碳總量、碳均量核算模型對應于tCER、lCER兩類林業碳匯產品,tCER考慮項目期碳總量而lCER考慮項目期碳增量,因此碳總量、碳增量模型適用于造林再造林項目。碳增量核算考量林業碳匯項目的整體減排性,考慮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決策及項目期碳匯量變動,為CCER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核算提供參考,碳均量模型更適用于營林項目[3,9]。
4.2.2 三種“碳量”模型的優劣比較
(1)碳總量模型提高管理靈活性但降低減排有效性[58-59,61]。該模型下,利用tCER分析其對林地所有者的采伐決策、土地使用分配和碳信用供給的影響,提高項目管理靈活性。tCER離散驗證碳總量會導致無效的輪伐期增加,在利率較高時會出現不一致的輪伐周期,將森林的固碳功能內部化,降低林業碳匯產品的減排有效性[58,61]。因此,碳總量核算模型需要結合政策工具為不能容忍長周期林業碳匯項目的林地所有者提供安全的信貸渠道[58]。
(2)碳增量模型鼓勵林地經營但引致道德風險[9,59]。該模型選擇lCER核算,根據其核算標準,時間期限長的lCER價格水平更高,為其他土地轉換為林地提供經濟激勵。但由于林業碳匯項目長期性會引致道德風險,林地所有者會通過縮短或延長輪伐周期降低因懲罰引致的損失,因而lCER和碳增量模型會引致碳儲量的減少[62]。碳增量模型的林業核算可引入基于碳匯量減少的懲罰機制,提高林業碳匯產品的減排有效性。
(3)碳均量模型考慮林業碳匯項目長期性但降低項目參與意愿[63]。該模型下,從項目期整體核算林業碳匯產品價值,為林業CCER的價值核算提供解決方案。項目期碳儲量會因林業采伐活動釋放[47,60],碳均量模型通過核算采伐后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以確保額外的碳儲存,降低林業碳匯項目道德風險[60]。但是,碳均量模型會降低林業碳匯項目的參與意愿,促使管理者傾向于經濟價值高的速生樹種經營而舍棄生態價值高的慢生樹種經營。
4.3 三種“碳量”模型的甄別
對林業碳匯產品三個碳量模型的甄別,需考慮林業碳匯產品對碳價波動的反應及項目樹種對林業碳匯產品類別的敏感程度,并結合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特性[61,64-65]。
(1)基于碳價波動反應的模型甄別。以碳價波動反應甄別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有利于分析林業碳匯產品的減排有效性。碳總量模型下,tCER對碳價變化更為敏感,但tCER的頻繁驗證涉及高額交易成本,該模型在碳價較高的情況下才能使林業碳匯產品獲益更多[64]。碳增量模型下,有效期更長的lCER價格水平更高,因而在項目前期林業碳匯產品價值對碳價波動更為敏感,項目后期更側重于木材價值[52]。碳均量模型下,可基于歷史基線和額外平均碳儲量從項目整體減緩項目期碳價波動的影響,提高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的穩定性[3]。
(2)基于樹種適用性的模型甄別。以樹種適用性甄別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可促進林業碳匯項目的可持續管理。基于“碳量”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易受樹種影響,不同樹種對林業碳匯產品價格及利率的敏感程度不同[61]。碳總量模型下,林業碳匯項目傾向于為慢生樹種的人工林提供資金;但速生樹種的林業碳匯項目更適用于碳增量模型;碳均量模型下,通過分析每單位額外碳儲量的成本效益,慢生樹種是更具成本效益的氣候變化緩解策略,而速生樹種能獲取更多經濟收益[3,59]。
(3)基于管理特性的模型甄別。以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特性甄別林業碳匯價值核算模型,可為政策制定者選擇何種核算模型提供依據。碳總量模型下,tCER的有效期僅為5年,林地所有者具有重新分配林地的靈活性,可適時調整項目經營策略[59];碳增量模型下,lCER可為林業碳匯項目提供長期管理方案,以履行其二氧化碳減排承諾[40];碳均量模型下,CCER可考慮林業碳匯項目的歷史碳匯基線,制訂合理的碳儲量水平,降低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65]。
5 主要結論及研究展望
5.1 主要結論
該研究首先梳理國內外林業碳匯交易市場機制,分析中國林業碳匯市場化困境;其次明晰林業碳匯產品的價值決定因素,闡釋林業碳匯產品分類及差異比較;最后基于凈現值法,分析了三種碳量模型的適用性及優劣比較,并從碳價波動反應、樹種適用性、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特性等方面對碳量模型進行甄別。主要結論如下。
(1)“時間期限”是林業碳匯產品的重要特征。基于時間期限尺度定義tCER、lCER及CCER三類林業碳匯產品,其中tCER和lCER具有時間期限的靈活性,旨在降低交易成本;CCER可通過永久性信用及穩定定價機制提高林業碳匯產品的減排有效性。
(2)林業碳匯產品的核心價值在于其碳儲能力及碳量水平,基于“碳量”的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主要涉及碳總量模型、碳均量模型及碳增量模型。碳總量、碳增量模型與tCER和lCER相結合可解決林業碳匯項目的非持久性,適用于造林再造林項目;碳均量模型與CCER關聯可考慮林業碳匯項目的額外性和長期性進而提升林業碳匯交易的減排有效性,適用于營林項目。
(3)以碳價波動反應甄別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碳總量模型易受碳價波動影響;碳增量模型的側重隨項目進行從碳價波動轉為木材價值;碳均量模型下可從項目整體減緩項目期內碳價波動的影響。以樹種適用性甄別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碳總量模型傾向為慢生樹種項目提供資金,而速生樹種項目更適用于碳增量模型;碳均量核算模型能依據生態價值調節為樹種選擇提供最優方案。以林業碳匯項目的管理特性甄別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模型,碳總量模型能加強管理的靈活性,碳增量模型可提供長期管理方案,碳均量模型能結合項目的歷史基線,合理核算林業碳匯產品價值。
5.2 研究展望
為促進全社會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需要發揮林業碳匯抵消的重要補充機制作用。從林業碳匯產品加快納入碳交易市場機制來看,以下方面的問題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①在穩步推動強制性碳交易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應明確林業碳匯產品的合理基線,優化額外性的方法學改進,構造林業碳匯產品的懲罰機制,通過政策工具提高林業碳匯產品價值核算的準確性。②自愿性碳交易市場應結合“雙碳”目標,考察補貼等政策工具對自愿參與的林業碳匯項目的激勵性補償,或根據林地稟賦以及管理偏好,在項目期內通過延長輪伐期或提高林地經營水平提高林業碳匯,促進自愿選擇機制下的碳匯最優。③林業碳匯產品的時間期限各異,應重視永久性減排信用與期限性碳匯產品的協調,需解決暫時碳補償與永久減排量的兼容性,以利林業碳匯項目時間期限問題的合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