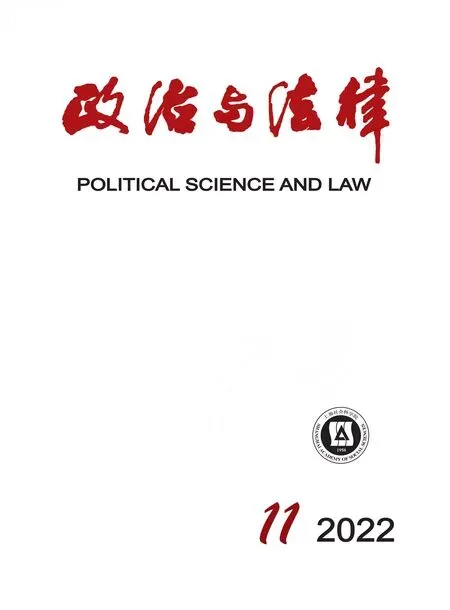虐待罪的刑罰配置檢討:一個憲法與刑法融貫的視角*
唐冬平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江蘇蘇州 215006)
一、問題的引出
我國《刑法》第260條在故意傷害罪之外另行規定了虐待罪,以對在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虐待行為進行刑法評價和刑事制裁,這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可謂意義重大。原因在于,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毆打、體罰等肉體虐待和辱罵、諷刺等精神虐待行為一般達不到故意傷害罪、侮辱罪等犯罪的程度,但刑法仍將它們作為處罰對象,主要目的在于保護弱勢的家庭成員。〔1〕參見陳洪兵:《人身犯罪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換言之,我國立法者似乎有意降低了刑法調整同類社會關系的一般標準,其目的是運用刑法對家庭成員實施特別的保護,這體現了國家對于建構平等和諧家庭關系的用心以及中國法律體系對家庭價值的呵護。
然而,這一意義重大的立法,卻因虐待罪的刑罰配置與故意傷害罪等其他相關犯罪相比較輕而在學理上存在爭議,并因司法實踐中的一些熱點案件,如2009年的北京“董珊珊案”和2019年的山東“方洋洋案”而受到社會公眾的頗多關注和責難。概覽學理上的爭議,大致有兩類觀點:一種是認為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存在合理性問題,主張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罰,可稱之為“不合理說”;另一種則認為虐待罪的現有刑罰配置具有合理性,沒有必要提高,可概括為“合理說”。在刑法學理上,罪刑配置上的正義是刑罰正義的重要方面。〔2〕參見彭文華:《刑罰的分配正義與刑罰制度體系化》,載《中外法學》2021年第5期。而刑罰的合理配置恰是刑法充分發揮其功能的重要前提。學理上認識分歧的存在和實踐中社會公眾對此類熱點案件的頻繁議論,說明虐待罪的刑罰配置是否真正完全實現了對中國人一直珍視的家庭價值的保衛仍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因而,筆者嘗試采用新的分析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二、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之爭及其困局
(一)虐待罪刑罰配置合理性爭論的緣起
虐待罪的刑罰配置之所以在理論上有爭議并因熱點案件而受社會廣泛關注,主要是因為與故意傷害犯罪等相關犯罪的刑罰相比,立法者為虐待罪配置了較輕的刑罰。拿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來看:一是虐待罪基本犯的法定最高刑是2年有期徒刑,而故意傷害罪基本犯的法定最高刑可以達到3年有期徒刑;二是刑法對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的兩種后果即重傷、死亡不加區分,法定刑為2年至7年有期徒刑;而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區分了重傷、死亡后果,重傷后果的法定刑為3年至10年有期徒刑,死亡后果的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另外,拿虐待罪與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相比也是如此,因為虐待被監護人、看護人罪的最高法定刑為3年有期徒刑,而虐待罪基本犯的最高法定刑為2年有期徒刑。
此種刑罰配置狀態帶給公眾的一種直觀感受是,對家庭成員實施虐待并造成傷害的行為,刑法卻只處以較輕的制裁,虐待罪似乎成了施暴者逃避刑法制裁的一把“保護傘”。這沖擊了中國民眾日益強化的平等觀念、權利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于現代家庭生活的理想與期待。在以北京“董珊珊案”和山東“方洋洋案”為代表的熱點案件中,法院的“依法裁判”與社會公眾的質疑十分鮮明地表征了上述立法狀態與公眾的樸素感受之間的張力。當然,普通人的樸素感受不能取代理性的專業判斷。然而,學理上對此刑罰配置狀態也有認識分歧,形成了“不合理說”與“合理說”之間的爭論。
(二)“不合理說”及其不足
所謂“不合理說”即認為虐待罪的刑罰配置過輕,不足以對構成虐待罪的行為進行適當的刑事制裁,應該通過提高法定刑的方式予以調整。
事實上,自1979年《刑法》制定開始,如何為虐待罪配置適當的刑罰,就成為立法過程中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在1979年《刑法》制定過程中,針對當時的刑法草案,衛生部指出,“虐待致死,判十年以下,輕了”,彼時的商業部和政治部也提出,“虐待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沒有什么區別,應當從重”。〔3〕高銘暄、趙秉志編:《新中國刑法立法文獻資料總覽》,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2頁。但立法者最終沒有采納這些意見。1979年《刑法》第182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引起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在1996年修訂刑法的過程中,再次有地方和部門針對刑法修訂草案提出提高虐待罪刑罰的建議。〔4〕參見高銘暄、趙秉志編:《新中國刑法立法文獻資料總覽》,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9頁。但這一建議仍未獲立法者接納,因而1997年《刑法》繼續保留了1979年《刑法》關于虐待罪的刑罰設置。現行刑法已歷經多次修訂,但有關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始終未有調整,可見立法者并不認為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存在不當之處。
與立法者的態度截然不同的是,認為虐待罪刑罰配置并不合理的學理主張在1997年《刑法》實施后陸續被提了出來。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有觀點提出,基于親屬道德倫理關系,應在虐待罪條款中增加對虐待直系尊親的行為加重處罰的規定。〔5〕參見王玉杰:《親屬犯罪刑罰處置研究》,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進入21世紀后,更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反思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問題。概括而言,包括以下三種視角:(1)家國關系的視角。有觀點認為,在《刑法》中,虐待罪的刑罰輕于普通的過失致人死亡罪,說明虐待罪已經失去維護家庭倫理的意義,這是現代國家主義和個體主義強勢排擠家庭親情倫理的結果,為緩和刑法的道德主義危機,有必要重新在刑法中吸納親親原則。〔6〕參見沈瑋瑋、趙曉耕:《家國視野下的唐律親親原則與當代刑法——從虐待罪切入》,載《當代法學》 2011年第3期。(2)虐待犯罪的危害性角度。有部分學者認為,虐待罪的危害性比較高,應該提高刑罰制裁力度。如有觀點指出,虐待罪的構成要件與法定刑配置不相稱,理由在于構成虐待罪的行為具有反人倫性,在侵犯受害人人身權的同時也對其他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和居家安寧造成損害,應該提高。〔7〕參見陳航:《值得深思的刑法“寬”“嚴”倒錯問題——以常見多發型家庭暴力犯罪為例》,載《犯罪研究》2007年第1期。另有觀點也表明,無論是從自身的社會危害性,還是與其他同類犯罪的法定刑相比,虐待罪的法定刑都過低,不利于保護受害人的權利以及遏制虐待案件的頻繁發生,故應該加重和提高。〔8〕參見徐文文:《關于完善虐待罪的法理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14 年7月16日,第6版。(3)虐待罪刑罰配置的目的角度。有觀點認為,對虐待行為給予較輕處罰的總體目的是維護家庭穩定,由于行為人和被害人對于一般家庭矛盾的產生都具有過錯,因而虐待罪基本犯的刑罰配置合理,只有在已無維護家庭穩定的可能和必要時,虐待致人重傷、死亡的才應該加重刑罰,并提高到與故意傷害罪之刑罰相當的水平。〔9〕參見隋林熹:《虐待罪法定刑配置須輕重結合》,載《檢察日報》2018年4月15日,第3版。
“不合理說”的最大價值在于,為虐待罪刑罰配置可能存在的缺陷提供了學理上的說明,用專業理性印證了樸素的法感受的合理性,但依然存在以下論證方面的不足之處。
第一,以輕罰不足以保護家庭倫理或是人倫傳統作為批評立法的理由,是在法律外部對虐待罪的刑罰配置直接進行合倫理性判斷。此種判斷方式將可能面臨兩個方面的困境:一是家庭倫理作為一種傳統在現代社會中對法律正當性的證成與批判能力事實上存在限度。法律與一個國家的傳統存在緊密聯系,而中國發達的家文化傳統在中國法律體系中也有諸多彰顯。〔10〕參見張龑:《論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家與個體自由原則》,載《中外法學》2013年第4期。但如果不清楚地界定傳統的內容并篩選出適應觀念、制度已改變的現代社會的合理成分,傳統對于法律正當性的證成與批判能力就會大打折扣。二是即使家庭倫理已得到清晰界定以及其中合理的內容被挑選出來,仍然不能改變它們作為法外理由的屬性,在法律與道德存在區別的語境下,它們的立法批評能力仍有所欠缺。例如,認為虐待直系尊親屬應該加重處罰的建議,其出發點在于維護家庭倫理,但這一尊卑有別的觀念,與現代社會的平等觀念和家庭法中重申的平等原則都不契合,因而其批判能力被極大削弱。
第二,以虐待行為之危害性高作為批判虐待罪刑罰過輕的理由,雖通過刑法學概念的轉介,試圖在刑法知識體系內部來檢討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具有一定的啟發,但卻沒有展開體系化的論證。
第三,以維護家庭穩定證成虐待罪刑罰配置較輕的總體理由與現代社會的平等權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家庭觀構成沖突。家庭整體關系的穩定固然重要,但以犧牲家庭成員之間應有的平等、互相尊重等基本價值以及生命、身心健康等重要權益而片面追求所謂的“家庭穩定”,與現代家庭觀念并不相符。進言之,家庭穩定價值與成員個人權利價值之間的關系是,后者對于前者而言是構成性、支持性的,即現代意義上的“家庭穩定”一定是建立在個人基本權益得到保障的基礎之上的,犧牲了個人價值的“家庭穩定”價值,并不是真實而值得追求的“家庭穩定”。盡管重新強調家庭之整體性、倫理性以回應個人主義觀念在家事法領域中所暴露出的弊端已成為中國家庭法制完善的價值基礎,但抑制極端個人主義并不代表彰顯個人價值的平等、自由等基礎性的理念應該被放棄。另外,即使家庭成員對于矛盾的產生都負有責任,這也不應該成為一方對另一方施加虐待的理由。
第四,在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具體調整方案上尚未形成共識,也未注意到相關方案與既有刑法學知識的可能矛盾。從既有觀點看,對于虐待罪基本犯的法定刑是否存在合理性問題,以及如何調整虐待罪的整體刑罰配置,既有學理并沒有形成統一方案。另外,個別觀點主張,將虐待致人重傷、死亡的刑罰提高到與故意傷害罪的刑罰相當,但這與既有刑法學理認為虐待致人重傷、死亡屬于過失致人重傷、死亡存在矛盾。因為,基于既有刑法學的認識,同樣致人重傷、死亡,故意犯罪的惡性程度及其應受懲罰程度肯定高于造成同樣結果的過失犯罪。如何回應這種可能矛盾,現有研究并沒有進行闡釋。
(三)“合理說”及其疏漏
“合理說”認為,對于嚴重的家庭暴力行為,通過正確界定虐待罪與其他犯罪的關系,從而適用刑罰制裁更為嚴厲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其他罪名,也能達到正確評價和制裁嚴重虐待行為的目的。“合理說”的形成與刑法學研究重視解釋論而非立法論的方法論立場有很大的關系。在此立場之下,由于刑法學理上并不懷疑現有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所以并未對其進行直接性說明。但是通過考察刑法學理對于虐待罪及其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分,以及對司法實踐中虐待罪適用疑難問題所提出的教義學方案,可以推斷出“合理說”是如何認定虐待罪刑罰配置合理性的。
第一,以行為后果的惡性程度說明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此種間接說明方式體現為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在基本犯的區分上。“合理說”認為,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在行為的客觀特征方面是完全不同的:虐待罪在客觀方面的表現主要是,行為人對被害人持續性地實施精神摧殘和肉體折磨,如打罵、凍餓、禁閉、諷刺、咒罵等;〔11〕參見高銘暄、馬克昌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85-486頁;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9-1190頁;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頁。而故意傷害罪的客觀方面是,行為人進行損害他人身體正常機能的行為。〔12〕參見高銘暄、馬克昌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57頁;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5頁、第1117-1118頁;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頁、第22頁。進一步而言,雖然虐待行為和故意傷害行為都會對被害人的身體造成損害,但與故意傷害相比,虐待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程度在刑法評價上相對較輕。因為刑法理論和實務一般認為,傷害行為只有造成輕傷以上后果,才符合故意傷害罪對于傷害結果的要求。由此而言,虐待行為通常只是一種身體上的折磨,如果達不到輕傷以上標準,就不構成故意傷害罪。罪刑相適應是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如果從客觀后果的層面間接承認了虐待行為的惡性程度較故意傷害行為低,那么相應的虐待罪的刑罰幅度輕于故意傷害罪的刑罰幅度也就自然而然地沒有違背現代刑法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第二,以主觀內容的惡性程度說明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在刑法中,犯罪主觀內容的惡性程度不同,也會影響到刑罰配置的輕重。“合理說”通過說明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在主觀內容上的不同進一步間接闡述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
首先,虐待罪基本犯的刑罰合理性。有觀點指出,虐待罪的故意是追求被害人肉體或者精神上的痛苦,而故意傷害罪的故意追求的是被害人身體機能遭受不可逆轉的損害。〔13〕參見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4頁。雖然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都屬于故意犯罪,但在刑法評價中,主觀惡性程度及其應受懲罰的程度仍然取決于主觀要素內容的危害性高低。由于虐待罪的主觀故意內容是追求精神和身體折磨而非故意傷害罪的追求損壞他人身體正常的生理機能,因而傷害的故意顯然要比虐待的故意在應受懲罰程度上更高。如果承認虐待罪的行為惡性程度較故意傷害罪低,那么虐待罪較故意傷害罪在主觀內容上的惡性程度也就相應地降低,因此虐待罪的刑罰配置輕于故意傷害的刑罰配置也就是合理的。
其次,虐待罪結果加重犯刑罰配置的合理性。“合理說”以故意犯罪的應受懲罰程度高于過失犯罪為依據來證成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依照現有刑法學理,虐待罪結果加重犯的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都與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不同。一方面,虐待致人重傷、死亡,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受害人因虐待逐漸產生身體損傷或最終導致死亡后果;二是受害人因不能忍受虐待而自殺、自傷。〔14〕參見潘新哲、楊華:《關于虐待罪問題的探討》,載《理論探討》2004年第2期。另一方面,與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死亡最大的不同是,虐待致人重傷、死亡的,在主觀方面是過失。〔15〕參見高銘暄、馬克昌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85頁、第486頁。因此,相較于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應受更輕的制裁。
第三,基于刑法解釋論的方法論立場,在對虐待罪的整體刑罰配置的合理性加以說明后,“合理說”還對于司法實踐中虐待罪因法定刑配置結構過輕導致的適用難題提出了教義學上的應對方法。在司法實踐層面,虐待案件中常有被害人重傷、死亡的后果發生,由于在刑罰配置上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要輕于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因而如何對導致重傷、死亡后果的虐待行為進行刑法評價,并處以合理的刑罰制裁,就會成為司法適用層面的難題。“合理說”主張正確運用刑法適用原理來應對。
首先,明確虐待罪與其他犯罪的非排斥關系。為了對個案中較為嚴重的虐待行為進行全面評價和適宜處罰,“合理說”認為,正確區分虐待犯罪與其他犯罪固然正確,但這并不能否認在個案中虐待罪與其他犯罪的并存關系。這種非排斥關系為將一個案件中的虐待行為同時評價為構成虐待罪或故意傷害罪等其他犯罪提供了認識上的前提和可能。對此,有觀點指出,從立法目的上看,為了保護家庭生活中弱勢家庭成員的權利,立法者才在故意傷害、殺人罪之外另設虐待罪,此種設計有助于將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并不構成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的虐待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庭成員之間的虐待行為只能以虐待罪論處。〔16〕參見陳洪兵:《人身犯罪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如果否認虐待罪與其他犯罪在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的非排斥關系,難免造成“虐待罪成為家庭成員犯罪的避難所”這一損害刑法價值和社會公眾法感情的不利后果。〔17〕參見《學者:虐待罪不是家庭成員間犯罪的避難所,否則還會出現下一個方旸》,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7669270128869 78&wfr=spider&for=pc,2020年1月18日訪問。
其次,運用刑法學上的罪數區分理論來回應司法實踐層面的難題。所謂罪數區分是指,區分一個人所犯之罪的數量,其關系到定罪和量刑的準確性。〔18〕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56頁。在具體判斷層面,包括了“行為究竟成立一罪還是數罪”和“對于數罪是實行并罰還是不并罰”兩個問題。〔19〕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58頁。為應對虐待罪的司法適用問題,“合理說”還從罪數的認定以及數罪的處罰兩個維度提供了解決思路。
(1)在認定是一罪還是數罪方面,大致有兩種代表性的認定方法。第一種是“主觀目的判斷法”,即從行為人主觀目的是實施傷害、殺人還是虐待來認定嚴重虐待行為的性質。例如,立法機關的內設部門發布的法律問答指出,在適用虐待罪的過程中,“實踐中應當注意:如果行為人是故意要致使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而采取長期虐待的方式來實現其犯罪目的的,不應按虐待罪來進行處罰,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了故意傷害罪或者殺人罪,應依照故意傷害罪或者殺人罪的規定定罪處罰”。〔20〕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刑法問答(分則部分)》,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頁。第二種是以虐待罪的限度為標準的“分割法”,即將虐待行為予以分割,將超出虐待罪限度的虐待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等其他犯罪,對于沒有超出的則認定為虐待罪,從而將一個人的虐待行為在刑法上評價成數罪。對此,有觀點指出:“如果在虐待的過程中,行為超過了虐待的限度,明顯有傷害、殺人的惡意且實施了嚴重的暴力行為,直接將被害人毆打成重傷,甚至直接殺害被害人的,應該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21〕郎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434頁。至于說如何對嚴重的虐待行為進行刑法評價上的分割,刑法學理上又提出了兩種基本的判斷方法。一是“最后一次性暴力說”,即認為在虐待過程中,因一次性暴力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應該將該行為分離出來認定為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22〕參見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頁。二是“綜合判斷說”,即應該結合行為人的暴力手段、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傷亡后果及其主觀故意內容進行綜合判斷,不表示只有一次行為導致傷亡才可以認定為故意傷害罪。〔23〕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0頁。這種判斷方法也為實務部門所采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15年3月2日聯合印發的《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中指出:“準確區分虐待犯罪致人重傷、死亡與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犯罪致人重傷、死亡的界限,要根據被告人的主觀故意、所實施的暴力手段與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傷亡后果等進行綜合判斷。”〔2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法發〔2015〕 4號),2015年3月2日發布。
(2)在對數罪是否應實行并罰的問題上,又大致存在著擇一重罪論和數罪并罰兩種思路。例如,有觀點認為,在連續性虐待的過程中,行為人既實施了未造成輕傷以上后果的行為,又實施了造成輕傷以上后果的行為,雖然既構成虐待罪也構成故意傷害罪,但故意傷害行為以虐待行為為前提,則應該按照吸收犯的原理,故意傷害行為吸收虐待行為,最終應按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25〕參見羅猛、蔣朝政:《虐待中故意傷害行為對虐待罪的超出與吸收》,載《中國檢察官》2011年第14期。另有觀點則指出:“虐待行為本身已經構成犯罪,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又實施了故意傷害行為的,則應實行數罪并罰。”〔26〕陳興良:《判例刑法學(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頁。無論是通過數罪并罰,還是擇一重罪處理,都實現了對于嚴重虐待行為的合理評價,更為重要的是為采取嚴厲的刑事制裁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總的來說,“合理說”試圖基于法律內部視角來主張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因合乎現有刑法體系而具備合理性,但依然存在以下諸多漏洞。
第一,忽略了虐待罪保護法益的相對獨立性。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該與行為人所犯罪行和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一規定首先意味著刑法適用應該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但事實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應在立法上得到貫徹,這是其能夠在刑事司法中得以落實的前提和基礎。〔27〕參見趙秉志、于志剛:《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貝卡里亞早就指出,明智的立法者在確定刑罰時,應避免使最高一級的犯罪受最低一級的刑罰。〔28〕參見[意]切薩雷?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為每一種犯罪確定科學的刑罰?這需要回到犯罪的本質,即對法益的侵害性。立法者應該基于每一種犯罪行為對法益侵害的相對獨特性,建構與之相適應的刑罰體系。“合理說”在證成虐待罪的刑罰配置正當性時,基本上將虐待罪的保護法益與故意傷害犯罪的保護法益作了等同處理,即認為虐待罪保護的法益也是人體的正常、健全生理機能,而且虐待罪對這一法益的侵害性遠小于故意傷害犯罪。這一認識顯然忽略了虐待罪保護法益的相對獨立性,違背了立法層面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第二,輕視了虐待罪保護法益的復合性。虐待罪保護的法益具有復合性,“合理說”將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作為虐待罪的保護法益,從而輕視了這種復合性。我國《刑法》將虐待罪規定在“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從解釋論的角度出發,似乎可以認為虐待罪的保護對象也是人身法益,因而以同屬保護人身法益的故意傷害罪作為參照對象來說明虐待罪的法益侵害性小及其較輕的刑罰配置具有合理性并不存在問題。然而,此種形式化的解釋對于虐待罪所保護的人身法益僅作了完全形式化和表面化的理解。
首先,從邏輯上而言,《刑法》第四章中的人身法益在總體上看是“屬法益”,而第四章中與人身權相關的具體罪名所保護的法益是“屬法益”之下的“種法益”。人身法益在總體上應受刑法保護,但其在各個具體罪名之下應受保護的具體法益內容彼此之間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刑法》第246條規定的侮辱罪和誹謗罪,同樣屬于保護人身法益的犯罪,但該罪保護的具體內容并非單純指向生物學意義上身體的完整和自由,而是指向建立在人身基礎上的名譽等人格性利益。〔29〕參見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頁、第72頁。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所欲保護的總體對象雖然也是人身法益這一“屬法益”,但兩者所保護的具體法益內容卻是不同的“種法益”。因而,將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等同于虐待罪的保護法益,從而衡量后者的法益侵害性大小,忽視了刑法中“屬法益”和“種法益”的區別,在邏輯上本就存在不足。
其次,就法理來說,作為法律所保護對象的人有著不同維度,既包括物質維度上生物學意義的身體,也包括精神維度上建基于身體的靈魂。甚至在精神維度,身體上的靈魂還有著多元的構成,如欲望、理性和激情。〔30〕參見[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版,代序,第14頁。我們只有理解人的多維度特性及其在社會秩序中的限度,才可能建構出完整的法律保護制度,也才能夠理解法律制度賴以存在的“人學”基礎。對于刑法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和不明白人在社會中的發展和意義,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刑法所保護的法益”。〔31〕車浩:《刑法教義的本土形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頁。因此在解釋和應用刑法上保護人身法益的犯罪時,應該考慮到具體罪名所欲保護的不同法益內容實際上是對人多向度的保護這一基本法理。刑法立法者之所以將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長期性的打罵、毆打等行為作為犯罪行為予以評價和制裁,考慮的是在家庭生活場景中人的多個維度的法益應受保護。因此,反思虐待罪的刑罰配置,也應該以明確其保護的究竟是人的哪些維度為理據。
最后,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內容與故意傷害罪保護的法益內容不能等同。既有刑法教義學在解析虐待罪的構成要件時,都提及了“身體摧殘”和“精神折磨”兩個行為要素,因此虐待罪保護的法益內容并不只是包括個人的身體健康這一利益,還包含個人在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性利益。通過既有刑法教義學對故意傷害罪構成要件的解釋來看,故意傷害罪所欲保護的法益主要指向的是個人的身體健康,即身體的正常機能。結合上述刑法規范中“屬法益”和“種法益”的分化,以及刑法保護人的多維度這一基本法理,即可明確虐待罪所保護的法益內容與故意傷害罪所保護的法益內容并不相同,且具有一定的復合性。
第三,對虐待罪刑罰配置合理性的論證存在其他漏洞。
首先,以故意傷害罪為參照進而認定虐待罪的法益侵害性低的前提存在問題。“合理說”之所以認為構成虐待罪在法益侵害性上輕于故意傷害罪,主要是因為在刑法理論和實務上,長期有一種觀點認為,故意傷害罪的入罪標準是看傷害后果是否達到了輕傷以上。“合理說”在證成虐待罪現有刑罰配置正當性時,也是以之作為參照標準,即實施虐待行為對于身體的傷害,通常都達不到故意傷害罪的入罪標準,因而虐待罪的刑罰配置輕于故意傷害罪也就有了正當性。然而,以傷害行為是否對身體造成輕傷以上后果作為故意傷害罪的入罪標準這一論證前提并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刑法》第234條對于故意傷害罪的罪狀的規定為“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實際并未規定必須輕傷以上才能構成故意傷害,將輕傷與否作為認定故意傷害罪的一個客觀標準,其實是對《刑法》第13條中“犯罪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的一種錯誤地對應和運用。〔32〕參見石經海:《故意傷害“輕傷與否”定性共識的刑法質疑——以刑法總分則關系下的完整法律適用為視角》,載《現代法學》2017年第3期。
其次,對結果加重犯之刑罰配置合理性的論證沒有消解刑法規范之間存在的矛盾。依“合理說”的看法,行為人對于因虐待行為造成的重傷、死亡后果并非故意而是過失,因而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視角看,對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配置比故意傷害罪加重犯相對更輕的刑罰就獲得了正當性。但這一證成又會引申出另一問題。既然虐待致人重傷、死亡在主觀層面是過失,那么虐待致人重傷、死亡事實上也會構成刑法上規定的過失致人重傷、死亡罪。不過,我國《刑法》第233條規定的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要重于虐待致人死亡罪。該條又規定“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依此,家庭成員之間實施虐待致人死亡的行為,雖也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但仍應適用法定刑更輕的虐待致人死亡罪。為何《刑法》要如此規定?“合理說”對此問題保持了沉默。
第四,對虐待罪適用問題提供的教義學解答也不無問題。司法實踐中,之所以出現對于嚴重虐待行為的定罪量刑爭議,其爭點并非只是指向刑法上罪名的認定及其代表的刑法評價,更為重要的是指向對于嚴重虐待行為進行刑罰制裁的力度適當性問題。“合理說”通過刑法解釋學的建構來回應司法實踐中對于嚴重虐待行為的評價和制裁問題,實際上是以現有虐待罪刑罰配置具有合理性為前提的。此種學說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對于嚴重虐待行為的刑法評價問題,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將嚴重虐待行為認定為其他犯罪的標準不甚清晰。無論是通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還是以虐待罪的限度為標準對行為予以分割評價,都存在不足。對于“主觀目的判斷法”,刑法上犯罪的主觀目的通常也要結合客觀化的行為及其后果予以判斷,行為人對于重傷、死亡后果的主觀目的是傷害還是虐待在認定上本就存在難度。“因為主觀故意源自深層次的動機,而動機則是復雜多變的。此外,不同的環境會對人體機能產生不同的影響,比如在人體抵抗力較弱的情況下,以折磨故意所實施的暴力行為也能造成傷害的后果。這使得以客觀結果推主觀心態的方法也會存在誤差,如此,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的分野就顯得更加模糊不清了。”〔33〕母磊:《刑法規制家庭暴力犯罪困局探析——以丈夫家暴為視角》,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而對于“分割法”而言,困難也同樣存在。要對嚴重虐待行為予以評價上的分割,仍然要以明確虐待罪的限度為前提,從而有可能把超出該限度的行為定性為其他犯罪。但虐待罪加重犯的后果與故意傷害加重犯的結果從客觀上來說是同樣的,那么所謂虐待罪結果加重犯的限度事實上就很難明確。其中,“最后一次性暴力說”最大的問題是,容易忽視前期虐待行為與最終傷亡后果的因果關系。因為,如果行為人對被害人長期虐待,前期的虐待已經對被害人造成傷害,后期的繼續虐待最終導致傷亡后果。在此條件下,將最后一次性的暴力行為認定為超出虐待罪限度的其他犯罪,如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犯罪并不合理。另外,“綜合判斷說”主張的判斷方法僅僅提供了一個認定框架,具體化程度并不高。并且,目前刑法學理對于虐待行為在刑法上構成數罪的情況如何處罰,既有數罪并罰說,也有擇一重罪說,并未形成共識。
其次,以現有刑法體系為基礎進行解釋學上的建構和回應,回避了對虐待罪之刑罰配置合理性的反思。毫無疑問,在肯定現行法規范之合理性的前提下通過解釋學的建構回應法律的司法適用問題,當然具有維持法律安定性的優勢。可是,固執于解釋學的建構而絲毫不考慮甚至排斥立法論層面的反思,也并不可取。“在立法者的紕漏面前,理論不能放棄批判而淪為單純提供解釋服務的工具。”〔34〕車浩:《刑事立法的法教義學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 的分析》,載《法學》2015年第10期。“合理說”主張通過準確適用其他刑罰配置更重的罪名來對嚴重的虐待行為予以性質認定和制裁,的確回應了對嚴重虐待行為進行嚴厲制裁的現實需要。但是此種處理,依舊忽略了虐待行為相對特殊的法益侵害性。原因在于,刑法不僅具有通過刑罰實施的制裁作用,還具備通過具體犯罪認定對于行為法益侵害性的評價作用。透過適用法定刑配置更重的故意傷害罪固然能夠實現對嚴重虐待行為的法律制裁需要,但故意傷害罪的評價對象是行為損害人體正常機能這一法益侵害性,而虐待罪所要評價的法益侵害行為并不完全等同于對人體正常機能的損害行為,因而前者不能替代后者對行為的評價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刑法解釋學的回應,“合理說”似乎強化了對虐待罪現有刑罰配置的合理性證成,但也更進一步遮蔽了直接對虐待罪刑罰配置予以深度反思的可能性。
綜上,對于虐待罪的現有刑罰配置是否合理這一問題,“不合理說”與“合理說”都存在論證上的諸多不足。前者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以文化傳統、家庭倫理等作為批判理由始終是一種法律外部的視角,未能對接法律的內部視角,批判力量不強;另一方面,以虐待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高為理由的批判,雖嘗試進入到法律的內部視角,但相關論說并不充分,體系化程度不高。后者的問題在于,在恪守教義學立場的前提下,將故意傷害犯罪的保護法益等同于虐待罪的保護法益并說明虐待犯罪因其對法益的侵害性低而應予配置較輕刑罰,雖屬于內部視角的辯護,但依舊存在論證上的疏漏,且沒有充分回應外部視角的批判。因此,找到一種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相銜接,并且更加充分的論說,就成為檢討虐待罪刑罰配置合理性問題的可行且必要的思路。
三、憲法與刑法融貫視角的引入
為了走出虐待罪刑罰配置合理性爭論的學說對峙困局,亟需引入新的分析視角。鑒于憲法在實在法體系中的最高地位,將憲法與刑法融貫作為一種新的分析視角可以完成對虐待罪刑罰配置進行全面檢討的學理任務。
(一)憲法與刑法融貫的含義
在一國的實在法體系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構成部門法的制定和實施根基。此種法體系內部的憲法與部門法關系,更為具體地表現為兩個維度、三種關系:即在法制定維度,法律應對憲法加以具體化;在法實施維度,法律應作合憲性解釋或接受合憲性審查。〔35〕參見張翔:《憲法與部門法的三重關系》,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正是通過憲法對法律的制定、實施的指引和調控,一國的法律體系才在動態運作中具備了融貫性這一品質。在法理上,法律體系的融貫性要求各個法律部門及其制度與憲法及其制度之間建立起評價上的積極關聯,這不僅意味著各個法律部門及其制度的規范不能與憲法規范相沖突,還意味著前者在實質評價上要與后者保持一致。〔36〕參見雷磊:《融貫性與法律體系的建構——兼論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融貫化》,載《法學家》2012年第2期。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憲法與刑法相融貫即指,刑法應該落實憲法的精神、原則和規范,刑法關于犯罪的設定與刑罰配置應該與憲法的相關評價與指示保持一致,避免出現矛盾和沖突。
(二)憲法與刑法融貫作為分析視角的合理性
引入上述憲法與刑法相融貫的分析視角,將有助于擺脫關于虐待罪刑罰配置合理性爭論的既有學說困局,對虐待罪之刑罰配置作更為科學地檢討,主要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對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檢驗需要根據憲法的法益作為判斷工具。通行的刑法學理主張,刑法的任務在于保護法益。〔37〕參見[德] 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德]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上)》,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3頁;[日] 西田典之:《刑法總論》,王昭武、劉明祥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頁;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4-25頁;黎宏:《刑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頁。這里作為刑法保護對象的法益,應該立足于憲法而被界定。作為一國法秩序之基石的憲法,既具有外在于刑法立法者的超脫特性,又具有與法秩序相關聯的規范性,因而是填充法益內容的唯一來源。〔38〕參見陳璇:《法益概念與刑事立法正當性檢驗》,載《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3期。對此,德國刑法學者指出,“一個在刑事政策上有拘束力的法益概念,只能產生于我們在基本法中載明的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上的法治國家的任務。”〔39〕[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在將刑法任務界定為法益保護的前提之下,通行的刑法學理更進一步主張,法益概念具有對刑事立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加以批評的功能。〔40〕參見張明楷:《法益初論(上)》,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84頁。基于刑法的法益與憲法的關聯性,以憲法為根據的法益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批判刑事立法的能力。這也印證了日本刑法學者仲道祐樹的判斷,即“作為法益論的補充,刑事立法分析框架的憲法化方向是妥當的。”〔41〕[日]仲道祐樹:《法益論、危害原理、憲法判斷——刑事立法分析框架的比較法考察》,蔡燊譯,儲陳城校,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年第3期。將批判刑事立法的法益建立在憲法的基礎上,也就實現了憲法規范國家刑事立法權或者說國家刑罰權的基本功能。
具體而言,憲法憑借自身對法益的確定而具備的對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檢驗功能包括消極取向和積極取向兩種類別。前者是指,憲法被用作論證刑事立法不合理的判準:一是沒有憲法依據的法益不能通過刑事立法加以保護;二是具備憲法依據的一些法益,如公民的生命、財產等基本權利,不能因刑事立法而受到不合理的刑罰制裁或者剝奪,即作為刑事立法所要限制的法益受到憲法保護。后者是指,憲法被用來證成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即經過憲法確認的法益,刑事立法者必須積極地履行保護義務,通過科學合理的犯罪設定和刑罰配置落實憲法的指令。
然而,對于這兩類取向,傳統法學理論更多關注的是消極取向而非積極取向。這是由經典的刑法觀和憲法觀所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刑法學理認為,由于刑罰對社會成員具有嚴厲的制裁性,因而刑法應該保持謙抑性和對法益保護的輔助性,這就決定了立法者不宜隨意動用刑法手段治理社會;而另一方面,憲法學理則主張,憲法是對國家權力的限制法,國家的刑罰權理所應當地接受憲法限制。這兩種學理前提所共同導出的結論便是,憲法對刑事立法之合理性檢驗應該取向于對刑罰權的范圍與力度擴張的限制而非相反的證立或支持。
但此種漠視積極取向的認知存在著需要加以厘清的誤區。首先,刑法是憲法的直接實施法,即刑法是對憲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一種直接保護。〔42〕參見高銘暄、曹波:《當代中國刑法理念研究的變遷與深化》,載《法學評論》2015年第3期。在刑法學上,刑法謙抑性或法益保護作用的輔助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將刑法作為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的認識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只有當民法、行政法等法律不能保護法益時,才可以動用刑法手段。但事實上,“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之間具有補充性,但并非單純地刑法補充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而是基于法整體秩序之保護需要的互補關系”。〔43〕袁彬:《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模式及其反思》,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換言之,刑法可以與其他部門法協同發揮法益保護作用。因此,應該否定“只有在其他部門法無效時才動用刑法”這一教條,確立“在維護憲法的權威、保障憲法的實施確有必要時,即可以動用刑法”這一新理念。〔44〕參見付立慶:《論積極主義刑法觀》,載《政法論壇》2019年第1期。其次,限制國家權力擴張已非現代憲法的唯一功能,其也不能作為準確詮釋中國憲法功能的話語。在世界憲法史上,西方的憲法功能轉型歷經了以“限制國家權力侵害市民社會”為特點的自由主義憲法范式到以“對社會領域適度干預”為特質的福利國家范式的過程,而中國憲法功能體系一開始就屬于以“國家、社會、個體的同質化”為特點的社會主義范式。〔45〕參見李忠夏:《憲法功能轉型的社會機理與中國模式》,載《法學研究》2022年第2期。進言之,不僅西方憲法已不再將限制國家權力作為其唯一目的,而且中國憲法也沒有把限制國家權力作為自身的唯一功能。如果上述刑法之于憲法實施的直接性以及憲法功能轉型的原理得以成立,那么,基于憲法的法益檢驗刑事立法合理性之積極取向就應得到肯定。事實上,已有刑法學者指出,以憲法為根據的法益對立法的批判功能包括“要求廢除沒有保護法益的犯罪”和“要求為法益保護增設新罪”兩個方面。〔46〕參見張明楷:《論實質的法益概念——對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機能的肯定》,載《法學家》2021年第1期。換言之,憲法不僅可以限制刑罰權,也可以證立刑罰權,這是憲法規范刑罰權的兩個方面。如果是否應該犯罪化都可以憲法作為標準,那么在已經犯罪化之后的刑罰配置問題自然也能透過憲法審視獲得答案。因此,判斷虐待罪的刑罰配置是否合理,應該以憲法指引下虐待罪應予保護的法益構造而不是既有的刑法體系為準據。
第二,憲法承擔著溝通法律體系與外部社會的獨特功能。作為一國實在法體系之根基的憲法具有其他部門法所不具有的特性,即其能夠通過民主機制理性地吸納、整合和表達一個社群的文化傳統和道德倫理共識。可以說,“憲法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價值、原則體系,是對社會共同體的價值共識的最高規范表達。”〔47〕劉茂林、王從峰:《論憲法的正當性》,載《法學評論》2010年第5期。換言之,憲法以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形式,對具有共識基礎的文化傳統和道德倫理共識實現了實定法化。對此,有觀點指出,憲法是包括道德規則、宗教規則、法律規則等在內的社會規則實現競爭、轉換的平臺和結果。〔48〕參見石少劍:《作為社會規則和秩序統一的憲法》,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否認憲法之下的部門法就不能承載和表達社群內部關于文化傳統和道德倫理的共識,而是說為了維護法律體系相對于道德倫理、文化傳統的獨立性,憲法可以將法律體系之外的道德倫理、文化傳統通過民主機制加以甄別、固定,再通過部門法加以具體化和落實。也就是說,社會上的文化傳統、道德倫理要想成為法律體系內容合理性的評判標準,必須透過憲法所架設的價值整合、表達機制的轉化,而不能徑直作為批判法律體系內容的依據。憲法的這種溝通法律體系與社會的功能,既可避免法律體系無法回應社會而陷入僵化,又可維持法律體系的自治性。因此,對于刑法體系內容的評判就無須完全借助于法律體系之外的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而只需要回到憲法。這實際上也是刑法學理要將法益建立在憲法基礎之上的原因所在,因為“憲法性法益概念沒有將刑法的保護范圍與客觀現實直接相聯系,而是設定體現全體國民意志的憲法這個中介。從客觀現實進入刑法的保護范圍在理論上就要經歷兩個階段,即從客觀現實進入憲法,再從憲法進入刑法。”〔49〕劉孝敏:《法益的體系性位置與功能》,載《法學研究》2007年第1期。因此,虐待罪的刑罰配置是否合理,不是看現有刑罰配置是否真正實現了相關的道德倫理與文化傳統,而是看憲法上已經固定下來的價值共識是否獲得了實現。
基于上述憲法與刑法、憲法與社會的關聯,憲法與刑法融貫視角下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問題就可轉化為:憲法對立法者通過虐待罪所應予保護的法益下達了何種具體指令?上述“合理說”與“不合理說”支持或反對現有虐待罪刑罰配置的論證是否契合憲法上虐待罪所應實現的法益構造以及保護要求?總之,以憲法與刑法相融貫為視角,探究憲法上虐待罪應予保護的法益構造以及相應的刑罰配置要求,便可以走出既有學說“批評不足”“辯護無力”的對峙困境。
四、憲法與刑法融貫視角的展開
我國《憲法》第49條第1款明確規定了“家庭受國家的保護”,第4款則明確規定了“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就立法目的而言,1979年《刑法》明確開始規定虐待罪,主要是為了懲治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維護平等、友愛和和睦的家庭關系。〔50〕參見王愛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69頁。故而,從憲法學角度看,虐待罪的這一立法目標表明,虐待罪的設置及其刑罰配置是在實施《憲法》第49條第1款和第4款的相關規定,其憲法性質是國家通過刑事立法履行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所謂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是指,“憲法規定基本權利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真正實現公民的自由與平等,那么當公民基本權利遭到私法主體(私人)的侵害時,國家有義務采取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51〕陳征:《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功能》,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而立法者設置虐待罪、配置相應的刑罰,一方面是在對實施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進行犯罪化評價和制裁預設,另一方面也是在保護受害者的基本權利。這符合適用基本權利國家保護義務理論的法律關系結構,即存在“受害人—國家—加害人”的關系結構。〔52〕參見[日]小山剛:《基本權利保護的法理》,吳東鎬、崔東日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3-45頁。
既然虐待罪的罪刑設置是國家在履行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那么虐待罪所應保護的法益結構就應立足于憲法上相關的基本權利內容予以確定。由于虐待罪及其刑罰的制裁對象是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虐待行為,其保護對象是家庭成員的權利,因而憲法學視角下虐待罪及其刑罰應予實現的法益,即公民在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基本權利。在明確了憲法對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的保護要求后,就可以對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構造進行合理界定,從而對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理性進行合憲性判斷。
(一)憲法對家庭生活場景中基本權的加重保護
結合憲法上家庭生活場景中基本權利規范的體系解釋以及憲法確立“家庭應受國家保護”的法理基礎后可以明確,憲法對家庭生活場景中公民的基本權利實行的是加重保護,即范圍更寬和程度更高的保護。這就使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呈現出更加“厚實”而非“稀薄”的形態,從而對刑事立法者設定虐待罪及其刑罰發出了特別的指令。
第一,憲法對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利實行加重保護。在憲法理論上,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越窄,其受保護程度越高;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越寬,則其受保護程度越低。〔53〕參見杜強強:《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和保護程度——對我國憲法第35條和第41條的規范比較》,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1期。具體而言,即當個人依據憲法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都能享有的一般性基本權,如平等權、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等進入制憲者所限定的特定社會生活場景中時,這些基本權的應受保護程度就被大幅度提升了,因為這些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變得具體因而更加狹窄了。在一般性的基本權保護力度能夠實現特定生活關系中的權利保障需要時,制憲者不會無緣無故地設定一些特定的應受到憲法保護的社會關系。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么,我國憲法有沒有專門為保護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利建構獨特的保護規范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我國憲法通過“顯白規范”和“隱含規范”兩類規范專門建構出了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的保護體系。
首先,“顯白規范”是指制憲者通過明示的方法設定了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基本權利應受重點保護的憲法指令。(1)制憲者通過憲法文本設定了加重保護的總體框架。《憲法》 第49條第1款明確規定“家庭受國家的保護”。我們不應粗糙地將其視為一條意義十分薄弱的憲法規范。應該說,在前述基本權利規范領域與保護程度的關系理論下看,這其實彰顯了制憲者明確肯定家庭生活場景作為憲法直接保護對象的立場,也為國家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奠定了總體性基調。(2)制憲者通過個別條文設計一定程度地具體化了加重保護立場。《憲法》第48條、第49條等條文為家庭生活場景中的一些具體基本權設定了特別保護規范。《憲法》第48條規定“婦女在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這便是國家加重保護家庭生活中的性別平等權的規范依據。因為《憲法》第33條第2款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規定建構了適用于所有生活場景中的平等權,但由于制憲者通過第49條奠定了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立場以及第48條明確建構了家庭生活場景中的男女性別平等權,則第48條規定的平等權就因規范領域狹窄而應受保護程度更高。《憲法》第49條則通過主體、權利義務內容等多個維度對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建構出了特別具體的保護規范。譬如,第1款中的“母親、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從主體維度突出了對特定家庭成員的保護,而第4款中的“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兒童”則從主體和內容兩個維度強調了對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的特別保護。在理解第1款的規范含義時應留意到,母親、兒童基于憲法在一般社會生活領域所享有的基本權因憲法建構了關于家庭生活場景的專門保護規范,而使得他們的基本權之規范領域變得狹窄化,因而在家庭生活中應受保護程度被提高。在理解第4款的規范含義時則應該注意:一方面,制憲者從主體維度明確將“老人”“婦女”“兒童”作為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典型弱勢主體加以保護。當然這里對“老人”“婦女”“兒童”的列舉應視為例示規定,并不排除其他在家庭生活中可能處于弱勢地位的成員亦應受憲法加重保護。另一方面,在根本法層面對虐待行為給予否定性評價并設定禁止性立場,更加明顯地體現出憲法對家庭成員的基本權實行加重保護。因為,《憲法》第33條“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之規定所隱含的生命權〔54〕參見《憲法學》編寫組:《憲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07頁。和《憲法》第38條“公民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之規定所明定的人格尊嚴等個人基本權原本毫無疑問地要適用于家庭生活,但制憲者卻專門建構了對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的保護規范,即將對相關的一般性基本權利的保護濃縮為對家庭成員間的虐待行為的禁止。
其次,除“顯白規范”以外,憲法事實上還對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基本權保護設置了“隱含規范”。原則上而言,公民在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所應享有的一般性基本權應適用于家庭生活場景。如果制憲者對其中的部分基本權沒有基于加重保護立場特別轉化為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具體基本權,那么它們仍將適用于家庭生活場景,如《憲法》 第34條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憲法》第36條的宗教信仰自由等。更為重要的是,因《憲法》第49條“家庭受國家的保護”,這些沒有明文轉化的基本權也應在家庭生活場景中受到更高程度的保護。這些基本權應受加重保護則構成了所謂“隱含規范”。
第二,家庭生活場景中基本權應受憲法加重保護的法理基礎。雖然運用憲法學上基本權利規范領域與保護強度的關聯理論能夠對相關憲法規范作體系化理解,并說明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應受高度保護,但此種規范分析沒有進一步追問家庭生活以及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為何應受憲法高強度保護。因而,明晰家庭生活及家庭生活場景中個人基本權應受憲法高強度保護的法理基礎依然十分必要。過往法學界關于憲法中國家對家庭的保護義務分析主要從制度性保障理論、憲法權利理論和憲法原則理論等視角展開,〔55〕參見王鍇:《婚姻、家庭的憲法保障——以我國憲法第49條為中心》,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2期;李震山:《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載《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004年第16期;楊遂全:《論國家保護婚姻家庭的憲法原則及其施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但都沒有關注到憲法要求國家應對家庭生活以及其中的個人基本權實行加重保護的法理。
事實上,從家庭、國家、憲法的關系來看,家庭作為社會結構要素仍舊在現代社會中履行不可替代的社會職能,而這些社會職能又具有特別重要的憲制意義。這就要求制憲者必須承認家庭生活應受保護的憲法地位,并要求國家對家庭生活及其中的個人基本權實施高強度的保護。
首先,家庭的諸多傳統社會職能已轉移給社會和國家,但并不徹底,并且衍生出新的重要社會職能。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家庭是社會、國家得以產生的基礎,可以說“沒有家庭就沒有社會”,〔56〕[法]安德烈?比爾基埃等編:《家庭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序言,第7頁。也不可能有國家。伴隨社會的演進,家庭的部分社會職能逐步向社會組織、國家轉移。現如今,家庭不再是文化教育、經濟生產、生活保障等社會職能的唯一承載單元。學校、企業和國家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承接了家庭的上述社會職能。特別是對于國家而言,如果它不能承擔家庭轉移過來的一些職能,其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國家這種制度如果能存在下去,就必須能夠像家庭那樣撫育無助無援的個體”。〔57〕[德]維托利奧?赫斯勒:《道德與政治講演錄:歐中對話》,羅久、孫磊、韓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01頁。但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社會組織—國家”三種社會結構之間的社會職能轉移和承接,并不是徹底、單向的過程,而是社會職能保留、轉移、更新和發展的復合進程。在社會變遷中,家庭的社會職能轉移并非完全徹底,如家庭的教育職能的確是轉移給了社會組織和國家,但并不意味著家庭就不再承擔教育職能。與此同時,家庭也出現了新的社會職能。隨著一個社會的深度現代化,社會的陌生化程度就會持續加深,每個人都處在各種非人性化的社會交往之中。這些非人性化的社會關系,一方面豐富了現代人的社會生活以及自由、平等,但也在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十分強烈的個體認同需要。對此,社會學研究指出,“恰恰因為我們的交往中有很多是在某種非人性化的背景下實施的,對人性化關系的需要才變得如此迫切和尖銳”。〔58〕[英]齊格蒙特?鮑曼、[英]蒂姆?梅:《社會學之思》,李康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頁。進言之,一個社會越是陌生化,個體對于能夠承認、尊重和接納自己獨特性的親密關系的需求也就越旺盛。而家庭恰恰就是一種穩定化和制度化的親密關系。因而家庭也就具有了實現個體相互承認、生成自我認同的新功能。
其次,家庭在現代社會所履行的社會職能無不深度關聯于社群的公共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憲制意義。現代家庭生活已超越公私分割,對社群公共生活的影響愈來愈深。一方面,社會組織、國家對家庭社會職能的承接并不會完全取代家庭的地位,社會、國家和家庭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持合作關系,家庭的公共性由此凸顯。比如,國家建立的生育支持制度仍只是部分承接了家庭的人口撫育功能,不僅不可能替代家庭,反而要依賴于家庭。另一方面,現代家庭不再承擔傳統社會職能后,其日益私人化和情感化將是大勢所趨,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庭成為完全絕緣于公共生活的孤立生活單元。家庭育化個體、實現承認和生成認同的作用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逐漸被很多理論家所洞見。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奧金吁請現代社會的人們注意,“家庭生活是我們大部分早期社會化發生的地方”。〔59〕[美]蘇珊?穆勒?奧金:《正義、社會性別與家庭》,王新宇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頁。社會理論家霍耐特則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指出:“如果人們能夠從中看清,一個民主性共同體,是多么依賴于它的成員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實現一種相互合作的個人主義,就不會長久地一直否認家庭領域的政治—道德意義;因為要想讓一個人把他原先對一個小團體承擔責任的能力,用來為社會整體的利益服務,這個人必須擁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個和諧的、充滿信任和平等的家庭里建立的。”〔60〕[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自由的權利》,王旭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頁。社會學家吉登斯更認為,當現代社會的親密關系日益純粹化,個體在親密關系中的自主性也就得以提升,這也為社會整體的民主化注入了新的動力。〔61〕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欲》,陳永國、汪民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頁以下。這些社會理論觀點均表明,現代社會憧憬個體應具有的合作精神和道德責任感仍需通過美好的家庭生活逐步確立。這也進一步佐證了家庭社會職能的公共性。
最后,欲發揮美好家庭生活的憲制功能,就需要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由于憲法在性質上是指示人應該如何行動的“當為”規范,〔62〕參見王旭:《中國憲法學中的法實證主義命題及理論反思》,載《清華法學》2020年第6期。那么這必然意味著憲法所規范的社會生活以及身在其中的憲法主體的行動還沒有完全達到憲法規范所設定的理想狀態。這同樣適用于憲法所欲加重保護的家庭生活。實際的家庭生活與憲法期待的家庭生活完全是兩回事,現實的家庭生活質量可能遠未達到憲法的要求。因而,憲法指示國家對家庭生活的保護也意味著國家有義務通過法律與公共政策手段對實際的家庭生活加以干預。〔63〕參見唐冬平:《憲法如何安頓家——以憲法第49條為中心》,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5期。再加上,家庭生活狀態在本質上是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場景中行為的總和,因而對家庭生活的干預也就要求對家庭成員行為實施規制。只有在國家對家庭成員實施適宜干預的條件下,具有憲制價值的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的家庭生活才可能形成。因此,憲法要加重保護具有憲制價值的家庭生活,就必須通過法律或政策工具防止家庭成員相互之間實施侵害對方基本權利的行為。而只有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這一憲法目標才可能實現。
(二)憲法指示下虐待罪所欲保護法益的構造
在明確了憲法對家庭生活以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加重保護立場后,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構造就可以重新根據憲法加以厘定和呈現。
第一,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將表現出“個人法益+集體法益”的雙重屬性。憲法之所以要指示國家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的個人基本權,一是因為家庭的社會職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二是因為只有個人基本權能夠得到高度保障的家庭生活才會產生憲法所期待的正向公共效應。而在憲法學理上,憲法上的基本權在作為個人性的主觀權利時,其內容不僅只是作為一種狹義上的人權或公民權,而且它們還能夠保障某種法律制度或某一生活領域的自由。〔64〕參見康拉德?黑塞:《聯邦德國憲法綱要》,李輝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26頁。可以說,憲法上的個人基本權利具有超越于個人的結構性價值。〔65〕參見姜峰:《憲法的結構性與公共審議功能——兼對全能論憲法觀的反思》,載《中國法律評論》2020年第6期。簡言之,基本權利兼具個人性和公共性的雙重面向。因此,家庭生活中的個人基本權既有保護具體家庭成員個體的作用,也有建構抽象家庭法制度從而促進美好家庭生活之憲制功能的意義。與此同時,在刑法學理上,那些對人類生活具有重要價值且關乎社會整體高效運轉的社會制度屬于集體法益,應該得到刑法的保護。〔66〕參見李志恒:《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原理及其實踐展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6期。而家庭法制度正好是高度關聯于社群公共生活的一種社會制度,故而家庭生活中的個人基本權也就在個人法益屬性之外又獲得了集體法益的屬性。直觀上看,構成虐待罪的行為似乎只是侵犯了憲法所欲高度保護的家庭生活中的個人基本權,但其危害性卻是雙重的,既侵犯了具體家庭成員的個人法益,又侵害了抽象家庭法制度這一集體法益。
雖然,現行刑法典中有關家庭的犯罪,如虐待罪、重婚罪、遺棄罪等,都被置于“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中,因而這些犯罪所欲保護的法益似乎只是公民個人的法益。但從實質上看,符合這些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在侵犯個人權益之外,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具有獨特憲法意義的家庭法制度。我國1979年《刑法》將涉及家庭領域的犯罪,如虐待罪、重婚罪,置于“第七章 妨害婚姻、家庭罪”而非“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實際更好地體現了憲法的意旨。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刑法》卻改變了以前的立法體例,在法典結構上將相關犯罪移入到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之中。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們從解釋學的角度認識相關犯罪所欲保護法益的雙重性。
第二,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還將呈現出“客觀法益+主觀法益”的豐富內容。憲法指示國家應加重保護家庭生活,與現代家庭生活能夠促進個體之間的相互承認、生成自我認同,幫助個體形成既自我尊重又善待他者的健康心理狀態,以提升社群公共生活的品質是密切相關的。為了塑造出理想意義上的家庭生活,使其發揮出憲制性功能,憲法就要求國家不僅要加重保護家庭生活中的一般性個人基本權,而且要正視個體在家庭生活中的獨特需求并給予法律上的積極評價與完整保護。黑格爾曾指出,家庭作為一個倫理實體,其規定性是愛。〔67〕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9頁。而現代社會的愛,必然是建立在愛者與被愛者處在平等地位、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脫離這一規定性的“以愛之名”往往會異化成暴力、恐懼、支配甚至是悲劇。因此,在以愛為規定性的家庭生活中,個體在一般社會生活關系中所享有的生命權、健康權等客觀層面的權益在應受加重保護的同時,其渴望獲得承認、信賴和尊重等主觀層面的權益也應該獲得承認和保障。對此,有觀點指出:“道德感、信念和信仰確實舉足輕重,立法時必須納入考慮范圍。”〔68〕[美]圭多?卡拉布雷西:《理想、信念、態度與法律:從私法視角看待一個公法問題》,胡小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頁。也就是說,對于那些在生活關系中至關重要且值得保護的主觀需求,立法者不能輕視它們的存在及其正當性。事實上,晚近以來,通過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為刑法保護主觀層面的感情法益劃定邊界已成為一種有價值的方法論。〔69〕參見張梓弦:《感情法益:譜系考察、方法論審視及本土化檢驗》,載《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1期。因此,刑法上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即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個人基本權不僅包括客觀層面的法益,更為重要的是包含容易被忽視的主觀層面的法益。
(三)虐待罪刑罰配置的合憲性判斷及其完善方案
基于憲法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立場,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構造得以被重新界定。在此前提下,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合理性判斷就可以從既有學說爭論所代表的合倫理性判斷、合刑法性判斷轉變為合憲性判斷。可以說,在罪的設置層面,立法者對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虐待行為予以犯罪化,落實了憲法的指令,具有合憲性。刑事立法者在同類型的侵犯人身法益的犯罪體系中,單獨設定虐待罪對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直接落實了我國《憲法》第49條第1款中“家庭受國家的保護”和第4款中“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之規定。立法者動用了刑事制裁手段來保護家庭生活中的個人基本權,履行了憲法上國家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義務。
然而,在罰的配置層面,刑事立法者為虐待罪設置的法定刑罰體系有違憲法上的“禁止保護不足”原理。所謂禁止保護不足是指,國家在履行基本權利保護義務時應該達到憲法的要求。〔70〕參見陳征:《憲法中的禁止保護不足原則——兼與比例原則對比論證》,載《法學研究》2021年第4期。從是否犯罪化的角度看,立法者通過設置處罰虐待家庭成員行為的犯罪,似乎已因采取了最為嚴厲的制裁手段從而達到了憲法對家庭生活中個人基本權的高度保護要求。但事實上,僅有保護基本權利的立法形式還不夠,當相應保護性立法的“內容尚不充分時,保護義務就會責令立法機關制定或修改必要的法律”。〔71〕[日]小山剛:《基本權利保護的法理》,吳東鎬、崔東日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頁。就刑法落實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保護義務而言,罪和罰的合理設置這兩方面是相互協調、不可偏廢的。罪的設置一方面將某種類型的行為納入刑事規制范圍,起到了對該類行為進行法律負面評價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犯罪與刑罰上的對應關系,可明確對該類犯罪行為予以制裁的具體手段。但須注意的是,如果沒有為某種犯罪配置適當的刑罰,僅有罪的負面評價作用以及實質上并不適當的刑罰,就不可能發揮出刑法的應有保障功能。
就虐待罪而言,立法者既然已經選定通過刑法手段來履行保護家庭生活中個人基本權的憲法義務,那么就要在罪的設定和罰的配置兩個層面都完整落實憲法指令。前文分析表明,構成虐待犯罪的行為所侵害的法益既有個人屬性又有集體屬性,既有客觀層面的內容又有主觀層面的內容。因此,以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內容作為虐待罪的保護法益,從而證明虐待罪的法益侵害性低于故意傷害犯罪繼而肯定現有刑罰配置是不太恰當的。在憲法與刑法相融貫的視角下看,此種刑事立法不足以讓國家權力充分履行憲法上的基本權保護義務,存在憲法所禁止的保護不足的瑕疵。
既然從憲法的視角觀察,虐待罪所欲保護的法益具有更加“厚實”的形態,那么虐待罪的刑罰配置就應該擺脫既有學理認識上的“稀薄”法益觀。為了實現以憲法為規范基礎和價值基礎的法律體系融貫性,部門法的規范與學理都有向憲法調整的必要。〔72〕參見張翔:《刑法體系的合憲性調控——以“李斯特鴻溝”為視角》,載《法學研究》2016年第4期。為此,立法者對虐待罪的刑罰配置作符合憲法要求的實質性調整是有必要的。首先,對虐待罪的基本犯而言,刑法應該設置比故意傷害犯罪基本犯更重的刑罰。原因在于,從憲法視角來看,虐待罪的法益侵害性實際遠高于一般故意傷害犯罪。其次,對于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在總體上應該對虐待致人重傷、死亡兩種情形加以區分,分別配置刑罰。一方面,虐待致人重傷的刑罰應按照高于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的刑罰予以調整;另一方面,虐待致人死亡的刑罰也應按高于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刑罰進行調整。通過上述刑罰配置的調整,便可以全面落實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憲法精神。
依據憲法調整刑法上虐待罪的刑罰配置,不僅具有實現憲法與刑法相融貫,展現法體系之科學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法治實踐也是有所助益的。
首先,虐待罪的刑罰配置調整后,將有助于減少該類案件的司法裁判爭議及其增加的程序成本。在過往一些爭議性個案中,社會公眾、受害者及其家屬對嚴重虐待行為有著極其強烈的嚴厲處罰訴求,而一審法院依現有刑罰配置的虐待罪進行定罪處罰后經常招致批評并且容易引發案件的二審程序,二審法院則往往需要通過適用故意傷害罪等其他罪名或者與虐待罪實行數罪并罰來回應此種訴求。調整刑罰配置后的虐待罪實現了立法與民眾訴求的良性互動,將有利于減少法院裁判引發爭議和增加訴訟制度成本的潛在可能性,最終實現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其次,虐待罪的刑罰調整也對家庭生活場景中其他人身侵權犯罪的刑罰設置與適用提供了啟示。為了落實憲法對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加重保護立場,在被害人無嚴重過錯的情況下,家庭成員之間實施人身侵權犯罪應該作為一種加重處罰情節以對加害人進行嚴厲處罰。但需要反對的是,以傳統家庭倫理中的尊卑秩序作為人身侵權犯罪的加重刑罰的考量因素。
(四)可能的質疑與回應
對于虐待罪法定刑罰的提高,可能存在三種比較典型的反對意見。在此作一些回應性論證。
第一,中國仍處在社會轉型階段,社會保障制度依然有發展空間,家庭對于個體的生存和發展依然關鍵,一部分社會成員仍然追求整體和諧的家文化。虐待罪的刑罰提高可能會破壞個案中既有的家庭關系,提高家庭關系恢復的難度。尤其是在受害人需要加害人履行撫養照顧義務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權益反而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同時,此種調整也可能與社會成員的文化態度相悖。此種擔憂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并不構成對應提高虐待罪法定刑這一觀點的有力反駁。理由有如下兩方面。
首先,受害人的權益保護問題與既有的家文化可以在刑事法制度中得到解決和接納。(1)刑罰調整并不改變我國虐待罪“自訴+公訴”的追訴機制。按照刑法規定,對于虐待罪的基本犯,受害方才享有追訴權,對于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國家公訴機關有追訴權。此種追訴機制的設置,本就為家庭關系的恢復提供了一定彈性空間。對于虐待罪的基本犯,即使刑罰提高了,但受害人仍有選擇是否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的權利。對于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一方面希望加害人能夠繼續履行對受害人或其家屬撫養照顧義務的期待可能性已經下降(如虐待致人重傷)甚至不可能(如虐待致人死亡),另一方面即使具有一定的期待可能性,在造成受害人重傷的情況下,仍企圖由加害人履行撫養照顧義務,也可能違背受害者的意愿,再次增加受害者的危險。(2)在虐待致人重傷、死亡的個案中,如果受害人或其家屬仍舊需要加害人履行法定義務,這一訴求在刑事訴訟制度上仍然可以得到回應。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的規定,對于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從而對被告人進行從寬處理。在調整刑罰配置后,立法機關仍可考慮將虐待案件納入刑事和解制度的適用范圍。正是因為虐待罪刑罰配置調整并不改變追訴機制,并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制度,既有的一些家庭文化仍舊可以被刑事法律制度所容許。
其次,任何社群對價值的選擇都需要承擔制度的體系化成本并對相應所需的文化變遷采取一種溫和的態度。我們所承認和力圖實現的平等、自由等現代價值,都需要一套成體系的制度來對這些價值選擇所帶來的問題或風險加以回應。上述擔憂提醒我們,刑法要真正落實憲法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立場,還需要相關配套制度的協同與一套現代家庭文化態度的支持。在加害人因受刑事制裁無法履行對受害者或其家屬撫養照顧義務時,應該建立完善的社會救助機制,由國家和社會提供充分的撫養與照顧,以保護受害者或其家屬的權益。毋庸置疑的是,轉型的中國要真正形成一種以重視個人權利為根基的現代家庭文化仍然需要更多時間與制度的力量,而現有刑事法制度也為此文化的更新提供了足夠多的空間。對此,我們應采取一種溫和的態度。但即使如此,通過體系化的制度去形塑現代家庭生活的理想也不應該就此放棄。既然我們已經通過憲法堅定地表明了對于現代家庭生活的理想,那么應該做的不是用現實來否認這種理想,而是通過科學的行動積極地去實現這種理想。因此,與其對虐待罪刑罰的提高可能不利于保護加害者權益而憂心忡忡進而反對它,還不如通過配套制度建設與文化更新來實現它。
第二,刑事立法已經將虐待行為犯罪化的情況下,試圖通過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配置來威嚇潛在的加害者,對于減少虐待犯罪發生的作用可能是不明顯的。的確,從社會科學的視角看,法律對人行為的影響機制和效果是復雜而多樣的,〔73〕參見[美]勞倫斯?弗里德曼:《碰撞:法律如何影響人的行為》,邱遙堃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頁。甚至常常遠離我們的設想和初衷。但這也不構成對提高虐待罪刑罰這一觀點的實質性反對意見。法律不能百分之百地或者即刻將社會成員的行為引導至法律所預期的方向,只是事實的一部分。法律至今仍作為治理社會的一種重要方式在發揮著作用,并且沒有被國家所拋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發揮著規范主體行為的作用,這同樣是不可漠視的另一部分事實。在刑法規范主義立場下,刑法不僅僅是裁判規范,更是行為規范。〔74〕參見陳曉明:《風險社會之刑法應對》,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6期。刑法所發揮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功能依然被大家所承認。給某一犯罪配置輕或重的刑罰,可以把立法者通過將某種行為犯罪化所欲表明的對某類行為的否定性評價立場加以具體化,更加清晰地表明法律對行為的態度。社會成員也能更加準確地接收到法律所傳達出來的信息。這便是罪與罰相結合才能讓刑法更好發揮一般預防功能的機理所在。虐待罪刑罰配置的調整將更加旗幟鮮明地表明我們對建設、保衛現代家庭生活的美好理想與堅定立場,對于現實家庭成員的行為提供更加準確的指引。
第三,虐待罪刑罰配置的提高可能構成了對刑法保護法益之輔助性原則的放棄。這一可能的反對意見也不成立。理由在于,一方面,我國對家庭生活及其中的個人基本權已建立起了多元化的保護性制度,虐待罪刑罰配置提高并沒有破壞這一制度格局。對于家庭生活中的個人權利,我國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編、反家庭暴力法、婦女權益保護法、刑法等法律制度共同構成了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等在內的多元化保護手段。這說明立法者堅持了刑法保護法益的輔助性原則。在此制度體系下,虐待罪刑罰配置的調整只是完善了刑法手段,而沒有削弱其他手段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積極作用。加重虐待罪的刑罰,也不反對通過完善其他手段來實現對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保護。另一方面,虐待罪的刑罰配置調整并不改變虐待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是否入罪的標準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這就為其他法律手段發揮作用提供了必要空間。
五、結 語
“很顯然,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家庭都是社會實在的基本單位,也必然是建構一切更大的社會單位的原料。”〔75〕[英]拉里?西登拖普:《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賀晴川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頁。自由、平等且和睦的家庭生活,不僅對于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會產生關鍵性影響,也與良好的社會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息息相關。此種具有憲制意義的家庭生活,需要通過保護家庭成員的基本權來加以形塑。基于上述法理,《憲法》通過第49條規定“家庭受國家的保護”確認了國家應加重保護家庭生活及其中個人基本權的根本法立場。以憲法為準據,虐待罪應予保護的法益會呈現出更加“厚實”的形態,其刑罰配置也應作實質性調整。通過憲法與刑法相融貫的視角觀察,既有學說上的爭論也可以獲得重新評價。認為虐待罪刑罰配置不合理的學說,其實可以訴諸憲法上的相關基本權利及其應受高強度保護的要求,從而擺脫在外部對法律直接作合倫理性判斷的窠臼;而認為虐待罪的刑罰配置符合刑法自身體系邏輯的觀點,其實經不起憲法的檢驗。通過回歸憲法與刑法相融貫的視角,虐待罪保護法益的構造得以重構,其刑罰配置合理性問題也有了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