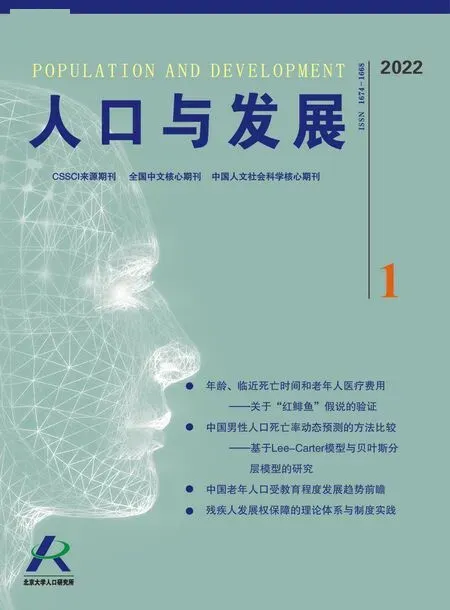晚年獨居意味著孤獨嗎?
——基于社會網絡的調節與中介作用分析
劉軼鋒
(中國人民大學 老年學研究所,北京 100872)
1 問題的提出
人口轉變和工業化推動家庭結構逐漸走向小型化,強調獨立自主的“責任倫理”成為中國傳統家本位文化外解釋親子關系的另一種內在邏輯(楊善華,2011)。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也由與子女共爨為主,向多代同堂和單獨居住并重轉變(王躍生,2014;胡湛、彭希哲,2014)。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單身老年戶占總家庭戶比例達到2.30%,2010年這一數字則上升至3.59%;其占老年家庭戶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1.46%,增加到2010年的16.40%。
與此同時,老年人的孤獨感也在不斷增加(Victor et al.,2002),老年人居住方式和家庭關系的變化被認為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Ng and Northcott,2015)。當配偶去世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會因獨居而顯著上升(沈可等,2013)。隨著喪偶期的延長,孤獨感會更加強烈(Brittain et al.,2017)。代際是否同住也影響著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江克忠、陳友華,2016),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通過“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所樂”緩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緒(沈可等,2013)。而獨居老年人因缺少家人的陪伴和照料,面臨血緣、地緣和業緣的多重缺失,社會支持資源明顯不足,在醫療服務可及性、經濟支持和社會交往等方面遭遇多重困境。隨著他們身體機能的下降,精神世界極度空虛,孤獨感十分強烈(Greenfield and Russell,2011;靳永愛等,2017;Park et al.,2017;Smith and Victor,2019)。近年來,媒體所報道的老年人“孤獨死”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無緣社會”似乎已成為獨居老年人的現實寫照。
盡管這些研究和報道引發了人們對獨居老年人的廣泛關注,但忽視了現實生活中獨居的復雜性,也遮蔽了獨居老年人在構建和維護社會網絡中的主體性地位。獨居是家庭在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老年人個體化傾向和獨立性不斷增強,與家庭結構小型化和家庭養老資源弱化等因素共同形塑的結果,這些因素不僅沖擊著老年人“多子多福”的養老觀念(風笑天,2006;于長永,2012;鄭丹丹、易楊忱子,2014;石智雷,2015),也重塑了他們的人際關系格局。家庭成員并非影響老年人精神狀態的唯一關系主體,部分老年人會通過積極構建、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Aday et al.,2006;Lou and Ng,2012;Baranowska-Rataj and Abramowska-Kmon,2019;Tong et al.,2019;Mair,2019;李強等,2019),從多元化的社會網絡中汲取所需資源,達到情感的自我滿足(Wenger et al.,2007;Utz et al.,2014;Zebhauser et al.,2015)。因此,獨居并非一些老年人不得已的選擇,而是會視獨居為其最優的居住方式(Birditt et al.,2019)。在這種情況下,獨居反而會改善他們的心理狀況。現有關于社會網絡對獨居老年人孤獨感影響的研究多基于國外經驗,對中國的相關研究還十分欠缺。相對于西方,中國傳統社會有著更強的家庭凝聚力。研究表明,在具有家庭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獨居老年人的孤獨感將更加強烈(Hansen and Slagsvold,2016;Grundy et al.,2017)。
因此,本文致力于探索如下研究問題:獨居老年人的孤獨感狀況究竟如何?他們又具有何種社會網絡?社會網絡在獨居和孤獨感兩者之間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清晰地認識獨居老年人的真實境況,可為社會養老服務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學的支撐。在新的歷史時期,以社會網絡為分析視角,對中國獨居老年人孤獨感的研究具有理論與現實的雙重意義。
2 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2.1 結構與行動視域下的老年人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是一群特定個人之間的聯系(1)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是一對相近但又有所差別的概念。兩者的基本內涵均指嵌入于人際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資源。差異主要有三點:一是學科背景的差異,社會網絡概念多為人口學和傳播學等學科使用,而社會資本概念則多見于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二是發揮功能的差異。社會網絡所發揮的功能多為信息傳遞、情感慰藉和身體照料等,社會資本更講求資本的回報屬性,功能多為收入增加、工作搜尋和地位獲得等。三是研究范圍差異。社會資本除微觀個人關系的資源外,集體性質的社會信任也屬于社會資本的研究范疇。由于絕大多數老年人已經退出了經濟活動,社會資本中所蘊含的信息、關系等資源的地位生產功能已經讓位于社會網絡所承擔的情感慰藉和生活照護等功能,故一般老年學領域文獻多采用社會網絡的概念。。社會網絡既具有關系結構的意涵,也包含了人際關系的投資、維系和利用的行動,是兼具結構和行動雙重取向的歷時性過程(林南,2005)。
從結構角度看,多種人際關系社會角色的集合構成了社會網絡的結構,如親子關系、夫妻關系、朋友關系和鄰里關系等。費孝通(1998)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準確地描繪出了中國人親疏有別的、同心圓波紋式的人際關系。老年人的多種關系模式也發揮著不同的功能。雖然子女和配偶在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但在一些個體化傾向較強的國家中,老年人對家庭成員有著較低的角色期待,反而更重視同輩群體中的朋友關系。朋友是個體自主選擇的結果,他們年齡相近,工作、生活和成長于同一年代,生活習慣與價值觀相仿,有著共同的愛好。在某些情形下,朋友會替代親屬的角色(Ellwardt et al.,2017;Mair,2019)。老年人的社會網絡結構具有伸縮性,規模和具體形式也受地區文化和福利制度所形塑,緊縮型的社會網絡在東歐和南歐等“家文化”濃厚的國家更為常見(Djundeva et al.,2019;Li et al.,2018)。社會福利的低水平和家庭友好政策的缺失會加深老年人對家庭成員的依賴,形成規模較小的社會網絡(Albertini and Mencarini,2014)。除宏觀層次的文化與制度外,教育、健康和遷移等個體層次變量也是影響老年人社會網絡結構的重要因素(Miche et al.,2013;Li and Zhang,2015;張文娟、劉瑞平,2018)。
在行動方面,只有蘊含強文化規范的社會網絡才具有可利用的資源(Agneessens et al.,2006),這些規范性因素并不能憑空產生,而是在關系者彼此互動中不斷地被建構出來。在這一過程中,原有的責任和義務被修訂,賦予老年人和其社會網絡成員新的角色期待,產生新的規范性因素,成為再次互動的動力基礎。關系越親密的個體,互動過程越加頻繁。傳統中國社會所講求的“攀關系、講交情”,也正是個體對人際關系投資和利用的生動體現。
2.2 老年人社會網絡類型與研究假設
類型分析是探索概念內在模式、分析群體異質性的一種手段。現有研究從不同角度將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劃分為多種類型。一是單一結構角度。這些研究多以老年人的核心角色關系為基礎,將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劃分為多元型、朋友型、家庭型和匱乏型四種類型(Litwin,2001;Li and Zhang,2015;Li et al.,2018;Djundeva et al.,2019)。二是結構功能角度。單一的角色關系往往會忽略社會網絡所蘊含的諸多信息,除社會網絡結構維度外,網絡功能和關系質量亦是劃分社會網絡類型時應考慮的因素。將老年人的角色關系、親密程度和相應的支持資源相互組合,可劃分出綜合社會網絡結構和功能因素的社會網絡類型(Fiori et al.,2007;Miche et al.,2013)。

圖1 老年人社會網絡類型劃分示意圖
無論是單一結構還是結構功能角度,都未能體現出老年人社會網絡的核心內涵。正如前文所述,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實際上是一個兼具結構約束和行動建構的過程。本文根據社會網絡的概念定義,依據結構維度的多元與單一、行動維度的活躍與消極的雙重面向,構建了2×2的四維象限圖。如圖1所示,處于第一象限的為多元-活躍型,是指社會網絡結構的多元化和積極主動地構建社會網絡。第二象限的是多元-消極型,是指社會網絡結構的多元,但社會網絡行動上的消極。第三象限的是單一-消極型,是指社會網絡結構的單一,同時行動上也無擴大社會網絡的傾向。第四象限的是單一-活躍型,是指雖然社會網絡結構單一,但卻有著積極的行動取向。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具有多種類型,可將其劃分為多元-活躍型、多元-消極型、單一-消極型和單一-活躍型。
社會網絡蘊含的豐富資源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質量施加著重要影響,可以促進老年人的身心健康(Miller and Mcfall,1991;Zunzunegui et al.,2003),降低其對家庭和公共福利體系的依賴,提升他們的幸福感(張君安、張文宏,2019)。預期壽命的延長使得老年人對情感需要大大增加,而社會網絡所具有的情感慰藉功能則可以避免老年人陷入精神空虛的境地(Gray,2009)。在家庭向現代轉型的進程中,老年人更需要擴大自己家庭外部的人際關系,以豐富自己的養老資源。實際上,獨居這一居住方式就意味著傳統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難以通過家庭成員滿足其養老需求。若老年人仍然固守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社會網絡成員較為單一,獨居將使他們的孤獨感更加強烈。故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對于具有單一-消極型社會網絡的老年人,獨居會顯著提升他們的孤獨感。
當配偶健在或與子女同住時,老年人形成了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家庭的照料責任占據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黃國桂等,2016),他們往往無暇參與社會交往活動,與外界朋友或親屬的聯系相對隔絕。相反,獨居老年人雖然失去了配偶和子女的支持,人際關系處于一種“空心化”的狀態,但他們也不承擔照料家庭成員的責任,從而有更多的精力經營自己的人際關系,推動社會網絡不斷擴展,在多元化的社會網絡中獲取自己所需的養老資源(Antonucci,et al.,2013)。一些研究也發現,老年人會與朋友、鄰里等非親屬形成“準親屬”(quasi-kinlike)的關系,并在彼此的互動中構建新的角色義務、責任和期待,以應對晚年期可能發生的各類風險(Stevens,2001;Barker,2002)。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與非獨居老年人相比,獨居老年人的社會網絡更可能為多元-活躍型。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社會護航模型(Social Convoy Model)成為分析老年人社會網絡的重要理論框架。根據社會護航模型,老年人的社會網絡是一個類似于“差序格局”的圈層式護航軌道,由內及外的保護圈層將給予老年人不同層次的支持,滿足老年人生活照護、精神慰藉等多樣化的生活需求,促進生命質量的提升(Kahn and Antonucci,1980;Antonucci and Akiyama,1987)。盡管獨居老年人從家庭外部社會網絡中獲得的照料支持相對較少,但能從中得到更多的情感性支持(Stevens,2001)。當老年人面臨喪偶、生病等不利事件時,社會網絡所蘊含的支持性資源將起到“緩沖器”的作用,可以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心理狀況(Cohen and Wills,1985)。同時,多元化的社會網絡也有助于打破原有社會群體之間的邊界,破除群體同質性所帶來的資源限制(Son and Lin,2012)。規模大、質量高、異質性強的社會網絡將有效改善老人的心理狀況(Sicotte et al.,2008),緩解老年人的孤獨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設4:
假設4:相對于其他社會網絡類型,擁有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老年人孤獨感更低。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老齡健康與家庭研究中心組織實施的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2014年數據,該項目基線調查于1998年進行,隨后進行了六次追蹤調查。自2002年第三次調查始,該調查將老年人年齡范圍擴大至65歲及以上。該數據質量較好,廣泛應用于人口學、社會學等研究領域,是研究老齡問題的代表性數據之一。2014年數據詳細調查了老年人居住方式、心理健康狀況以及社會網絡等相關問題。初始數據共有7192個老年人樣本,在刪除部分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后,最終納入模型的有5200個。
3.2 變量設置
3.2.1 老年人社會網絡
現有研究主要有三種方式來測量老年人社會網絡,一是提名法(name-generator),即由受訪者列出所有認識的社會網絡成員。這種方式存在一定的主觀選擇性,而且受訪者列出全部的成員并非易事,容易遺漏較疏遠的人際關系。二是根據社會網絡的屬性進行間接測量。如將與社會網絡成員的居住距離作為代理變量。這種方式易于操作,也最為普遍,但無法呈現出社會網絡的規模、程度及所發揮的功能。三是測度功能性的社會網絡。主要做法是詢問受訪者照料和情感等需求由哪些成員來滿足,這一方式既避免了前兩種方式的局限,又具有一定的針對性(Wenger,1996)。
基于概念界定和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在借鑒功能性測量方式的基礎上,選取了結構和行動兩個維度共七個指標,作為后文潛類別分析的變量來源。結構維度上,通過老年人“經常與誰聊天”“有心事和誰說”和“遇到事情或困難找誰”三個指標來反映滿足老年人情感和工具性需求的社會網絡。三項活動的主要承擔者分別為配偶、兒子、女兒、兒媳、女婿、孫子女或其配偶、其他親屬、朋友/鄰居、社會工作者、保姆。本文將兒子、女兒、兒媳、女婿、孫子女或其配偶歸為子女;其他親屬和朋友/鄰居歸為親朋;社會工作者和保姆歸為社會成員。配偶、子女、親朋和社會成員四類主體若為上述三項活動中,任一活動的被求助者,則將其視為老年人的社會網絡成員。行動維度上,采用與子女聯系的頻率作為代際互動的指標。若老年人有多個子女,則所有子女均經常聯系的為高聯系頻率,超過一半的子女不經常聯系則為低聯系頻率,居于兩者之間的為中等聯系頻率。若老年人無子女,則子女的聯系頻率為0,歸入低聯系頻率一類。本文采取現有研究的一些做法,將老年人是否打麻將/打牌以及是否參加社區組織的活動作為維護家庭外部社會網絡的行動指標(Li and Zhang,2015)。
3.2.2 老年人居住方式與孤獨感
老年人孤獨感的測量主要采用的是CLHLS2014年數據中“您是不是經常覺得孤獨”題項,有總是、經常、有時、很少、從不5個選項,本文將其正向編碼,賦值越高,孤獨感越強烈。從廣義上看,獨居可以分為夫婦獨居和單人獨居兩種類型(王躍生,2014),夫婦獨居又被稱為空巢老人;在狹義上,獨居僅指老年人單人居住(劉一偉,2018)。由于不同獨居類型在社會網絡和孤獨感上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故本文采取廣義的獨居概念,將獨居劃分為夫婦獨居和單人獨居。CLHLS數據中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主要包含與家人同住、獨居和養老院居住三種類型,這里的獨居是指老年人單人居住,夫婦獨居則屬于與家人同住。本文利用同住人數和同住人員關系兩個變量,將夫婦獨居從與家人同住中拆分出來。同時,雖然在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并非獨居,但和與家人同住的老年人也存在較大差別,故將在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作為居住方式的一個類型。不過,在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和孤獨感并非本文的研究重點,本文僅在行文中對結果進行簡單介紹。因此,居住方式包含與其他家人同住、夫婦獨居、單人獨居和養老院居住四類,分別賦值為1-4。在回歸模型中,與其他家人同住為參照組。

表1 老年人居住方式與孤獨感(%)
表1為老年人居住方式和孤獨感的交叉表。從表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孤獨感在不同居住方式下有著明顯差異(卡方值達到253.945,且在1%統計水平下顯著)。具體而言,與其他家人同住和夫婦獨居的老年人孤獨感程度較低。居住于養老院的老年人經常和總是感到孤獨的老年人比例達到23.189%,且孤獨感程度較為集中,有時感到孤獨的比例達到了53.623%。單人獨居的老年人則有著更高的孤獨感,經常和總是感到孤獨的老年人比例達到了37.638%,為四種居住模式最高。
3.2.3 控制變量
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和孤獨感受多種因素影響,為控制其他因素對分析結果的干擾,本文參照現有研究,主要選取了老年人的年齡、戶籍、性別、婚姻、失能程度、養老金、活著的子女數、教育水平和現從事或退休前職業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中。樣本的社會人口特征呈現于表2中。

表2 樣本主要特征
3.3 研究方法

(1)
第二,本文主要采用分樣本logistic回歸考察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采取分步logistic回歸和Sobel中介效應檢驗考察社會網絡的中介作用。logistic回歸模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較為常見,在此不再贅言。
下面主要對Sobel中介效應檢驗作簡要介紹。由于本文的核心自變量、中介變量和因變量為類別變量或序次變量,模型之間尺度并不相同,故首先需要將回歸系數標準化,再利用Sobel法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方杰等,2017)。公式(2)為Z統計量的計算公式,Za為納入控制變量后,居住方式對社會網絡類型影響系數的標準化,標準化公式為Za=a/SE(a)。Zb為納入控制變量和居住方式變量后,社會網絡類型對老年人孤獨感影響系數的標準化。同理,公式為Zb=b/SE(b)。
(2)
潛在類別分析在Mplus7.0中完成,數據預處理和logistic回歸則在Stata14.0中實現。

表3 老年人社會網絡潛在類別分析模型的擬合優度
4 實證結果
4.1 老年人社會網絡的潛在類別分析
本文首先根據模型的擬合指標,對老年人社會網絡的潛在類別數量進行選擇。如表3所示,隨著社會網絡類型數的增多,模型的對數似然比逐漸升高,卡方值在不斷下降。當類型數為4時,潛類別模型的BIC和Entropy指標均為最小。因此,四類別是老年人社會網絡類型的理想數量。
確定模型類別數量后,需要計算老年人社會網絡潛類別的概率,以及各類別外顯變量為特定賦值的條件概率,并可通過這一條件概率所揭示的特征命名各潛在類別。表4呈現了老年人社會網絡的潛在類別概率和外顯變量的條件概率。據此,本文將四個潛類別變量分別命名為多元-活躍型、社會-消極型、子女-消極型單一-活躍型。其中,社會-消極型和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的結構均較為單一,或以社會成員為主,或以家人為核心,且并無積極構建社會網絡的行動。因此,兩者在理論上均屬于單一-消極型。將這一結果與假設1比對可以發現,除多元-消極型外,其余三類社會網絡類別均可通過潛類別分析予以識別。假設1部分得到了驗證。

表4 老年人社會網絡類型的潛在類別概率和條件概率

表5 老年人社會網絡類型命名及主要特點
四個潛類別的概率分別為0.153、0.062、0.596和0.189。從潛類別變量的實際分布來看,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的老年人占比最高,高達57.5%;單一-活躍型次之,為25.6%;多元-活躍型再次,為12.7%;僅有4.2%的老年人社會網絡類型為社會-消極型,為四個類型的最低值。
四個類型社會網絡具有鮮明的特點(見表5)。類別1為多元-活躍型。該類型社會網絡成員身份更加多元化。雖然社會網絡成員包含社工和保姆的概率僅為0.061,但在四個社會網絡類型的條件概率中,也排在第二位。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家外的親朋,以及社工、保姆等社會成員共同構成了層次分明、有序協調的社會網絡圈層。同時,他們不僅與子女聯系較為緊密,而且也會通過打麻將和參與社會活動來延展自己的社會網絡。
類別2為社會-消極型。該類型社會網絡包含親朋和社會成員的概率最高,配偶、子女為社會網絡成員的概率相對較低。而且在行動方面較為消極,與子女不經常聯系,較少參與打麻將和社區活動。
類別3為子女-消極型。該類型的社會網絡將子女作為核心成員,且與子女有著緊密的聯系。但除子女這一關系主體外,他們的社會網絡成員包含配偶、親朋、社工或保姆的概率都相對較低;擴展社會網絡的主動性也非常不足,打麻將/打牌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條件概率均不到0.1。這部分老年人,生活上極度依賴子女,可獲取的社會網絡資源十分匱乏。
類別4為單一-活躍型。該類型的社會網絡成員主要為配偶和子女等家庭成員。盡管結構相對單一,但卻有著積極的行動,和子女聯系的頻率為所有類型最高值,打牌/打麻將和參與社區活動的概率也相對較高。以動態眼光觀之,若繼續保持積極的行動去維護社會網絡,該類型將向多元-活躍型轉變。
4.2 老年人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分析
本文首先進行了全樣本和分社會網絡類型的分樣本回歸(見表6),以考察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在獨居和孤獨感之間起到的調節作用。全樣本回歸結果表明,在控制了老年人的年齡、性別、健康狀況、教育水平、以及子女數量等變量后,居住方式對老年人孤獨感仍然有著顯著的影響。和與其他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相比,夫婦獨居老年人的孤獨感并無明顯區別,單人獨居老年人孤獨感升高的風險比比與其他家人同住高49.2%,表明配偶在滿足老年人精神需求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孤獨感升高的風險比是與其他家人同住的1.397倍。與現有研究一致,老年人所處地區、家庭因素和資源稟賦等控制變量對老年人孤獨感也有著顯著的影響,城市、有配偶、高教育水平、有養老金、子女數量多的老年人孤獨感程度更低。同時,失能、過去或現在從事農業勞動的老年人孤獨感程度更高。
由分樣本回歸結果可見,僅在子女-消極型的社會網絡類型中,老年人的孤獨感在不同的居住模式下才體現出明顯的差異。具有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的單人獨居老年人,相對于與其他家人同住,孤獨感上升的風險要高54.2%,結果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在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孤獨感升高的風險比是與其他家人同住老年人的1.549倍。這一結果也部分印證了假設2。根據社會護航理論,多元化的社會網絡構成了圍繞老年人的保護性圈層,社會網絡的各個層次都發揮著工具性或情感性功能,從而有效降低老年人的孤獨感。但若社會網絡結構單一,則可獲得的支持性資源也相應更低。在單人獨居的情況下,如果仍然保持著子女-消極型的社會網絡,以子女為中心,沒有營造家庭外部社會網絡的意識,其孤獨感勢必更加強烈(Gierveld et al.,2012)。

表6 獨居對孤獨感影響的全樣本與分樣本回歸
4.3 老年人社會網絡的中介作用分析
獨居老年人是否會通過擴展自身的社會網絡,以緩解孤獨感?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主要采取兩個步驟。首先考察獨居這一居住方式對老年人社會網絡的影響。其次,分析社會網絡與老年人孤獨感之間的關系。兩個步驟的實證結果分別呈現于表7和表8之中。

表7 居住方式與老年人社會網絡
由表7的多分類logistic回歸結果可知,單人獨居老年人更可能具有社會-消極型和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夫婦獨居老年人具有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可能性更大。具體而言,相對于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夫婦獨居老年人為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相對風險比是與其他家人同住的1.580倍,單人獨居老年人則為1.624倍。除印證了假設3外,實證結果也顯示,單人獨居老年人也更可能具有社會-消極型的社會網絡,相對風險比是與其他家人同住的4.765倍。居住在養老院的老年人為社會-消極型社會網絡的相對風險比是與其他家人同住的老年人15倍多,原因在于他們日常生活的接觸對象主要為護理員或社工等人員之故。
老年人所擁有的資源稟賦與社會網絡的類型有著緊密的關系。資源稟賦越豐富,越可能具有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具體而言,隨年齡增長,老年人為多元-活躍型和單一-活躍型社會網絡的可能性逐漸降低。男性老年人更不可能具有子女-消極型的社會網絡。配偶是多元-活躍型和單一-活躍型社會網絡的主要成員,故有配偶的老年人為這兩類社會網絡的可能性更高。失能老年人日常活動能力有限,主要依賴家庭成員的照料,缺乏通過社會互動構建社會網絡的能力,故其為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概率更低。高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獨立意識更強,會主動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實證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為多元-活躍型和單一-活躍型社會網絡的相對風險比分別是未受過教育老年人的2.907倍和1.775倍。過去或現在從事農業勞動的老年人難以形成多元-活躍型、單一-活躍型社會網絡,這部分老年人收入缺乏足夠保障,也固守著鄉土社會中“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現實與觀念的制約使他們生活重心局限在家庭之內,生活上依賴子女,社會網絡較為狹窄。養老金是老年人晚年生活重要的制度保障。有養老金的老年人生活相對寬裕,更有時間和精力構建和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回歸結果也表明,有養老金的老年人為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相對風險比是無養老金老年人的1.497倍。子女數量越多,為社會-消極型和單一-活躍型的可能性更低。雖然多子女老年人代際支持的可得性相對較高,但也易形成以子女為核心的消極型社會網絡。
獨居老年人更可能具有社會-消極型和多元-活躍型兩種社會網絡類型,反映出這一群體兩種截然不同生活狀態。獨居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老年人獨立性增強,自我養老能力提高后的主動選擇;二是因家庭養老資源不足而被迫選擇獨居。前者的獨居老年人雖然并不和子女同住,但他們和子女還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同時,獨居也讓他們也擺脫了繁瑣的家庭事務(如為子女做家務或照看孫子女等),有足夠的時間參與社交活動來聯絡與親朋的感情,從而形成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后者老年人主要為部分資源稟賦較差的單人獨居老年人,他們并無擴展自己社會網絡的行動意識,雖然社會網絡較為社會化,這更可能是少子化時代高齡喪偶后不得已的選擇。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也表明,當子女數量較多時,擁有社會-消極型社會網絡的可能性也更低。而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則與老年人子女數量無關,多與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等資源稟賦(如失能程度、教育水平和養老金)相關,這些也正是決定老年人獨立性的重要因素。

表8 老年人社會網絡與孤獨感

表9 中介效應檢驗
不同的社會網絡類型又會對老年人的孤獨感產生怎樣的影響?表8為社會網絡對老年人孤獨感的回歸分析結果。結果表明,多元-活躍型老年人有著更低的孤獨感,其孤獨感升高的風險比比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老年人低15.4%。而具有社會-消極型、單一-活躍型社會網絡老年人的孤獨感和具有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老年人的孤獨感并無顯著差別。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設4也得到驗證。盡管獨居老年人為社會-消極型和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可能性更高,但僅有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才能有效緩解老年人的孤獨感。親屬、朋友、鄰里和社會組織等人際關系的聚集,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網絡,為老年人供給豐富的支持性資源(Utz et al.,2014)。
在社會網絡各類型的中介路徑中,由于僅有“夫婦獨居→多元-活躍型→孤獨感”和“單人獨居→多元-活躍型→孤獨感”兩條路徑上的各節點的影響系數均顯著,故僅對此兩條路徑展開中介效應檢驗。基于表7和表8的回歸系數和標準誤,本文計算了相應中介變量的Z統計量,并利用Sobel法檢驗其顯著性。如表9所示,與其他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相比,無論是夫婦獨居,還是單人獨居,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都起到了中介作用,且效應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表明獨居老年人會通過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來緩解自身的孤獨感。
5 結論與討論
隨著家庭向現代化轉型,獨居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老年人普遍的居住方式。與此同時,老年人的孤獨感也在不斷攀升。本文以社會網絡為切入點,認為社會網絡是在角色關系結構和互動中,人際關系的角色義務、責任和期待不斷重塑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利用潛在類別模型和logistic回歸模型考察社會網絡對老年人獨居和孤獨感之間關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老年人獨居并不意味著會感到孤獨。具體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以子女和配偶為中心的差序格局仍然主導著中國老年人人際交往的邏輯。中國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可以分為多元-活躍型、社會-消極型、子女-消極型和單一-活躍型四種類型,占比分別為12.7%、4.2%、57.5%和25.6%。西方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網絡比重多在9%-30%之間(Litwin,1998;Litwin,2001;Litwin and Shiovitz-Ezra,2011;Djundeva,et al.,2019),明顯低于本文的83.1%(單一-活躍型和子女-消極型合計)。社會福利制度的低水平運行,家庭友好型政策的缺失使得相當一部分老年人不得不依賴家庭成員度過晚年生活,他們的精神需求仍然需要通過家庭成員來滿足。實證結果中,資源稟賦較差的老年人對家庭成員有著強烈的依賴,易形成以家庭成員為核心的社會網絡。
第二,具有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的老年人,單人獨居會顯著提升他們的孤獨感。獨居作為家庭向現代化轉型中出現的一個典型現象,這個過程往往與家庭養老資源弱化相同步,是推動老年人社會網絡向家外發展的“離心力”,但養老資源的不足和福利供給的缺乏又構成了老年人走向獨立的羈絆,兩個反向的力量使他們正經歷著半個體化的階段。對于依然保持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的老年人而言,他們在生活上極度依賴子女,又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動去拓展自己的社會網絡,他們往往難以適應一個人的獨居生活,最終處于孤獨的狀態。
第三,無論是夫婦獨居,還是單人獨居老年人,都會通過構建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來緩解孤獨感。這部分老年人教育水平更高,有著更加穩定的保障性收入。他們有能力,也更向往獨立自主的生活。他們的社會網絡形成了“親疏兼有”的社會護航圈層,主體多元且彼此協調,發揮了“緩沖器”功能,來化解精神世界的孤獨。同時,單人獨居老年人還更可能具有社會-消極型的社會網絡。社會-消極型的社會網絡更可能是部分單人獨居老年人不得已的選擇,他們在行動上并未積極地向家外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可能仍然固守“養兒防老”的養老觀念,但囿于現實狀況(無子女、代際分居、配偶去世等),不得不將親朋、社工或保姆等非親屬群體作為自己社會網絡的核心成員,當現實情況允許時,子女仍然是其晚年生活的主要依賴對象。實證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多,社會-消極型的社會網絡將向子女-消極型轉變。顯然,這種類型的社會網絡在緩解老年人孤獨感上,與子女-消極型的社會網絡并無顯著差別。
本文的研究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破除社會各界對獨居老年人標簽化和片面化的認識,有助于促進社會各界科學、辯證地看待老齡化進程中的獨居問題。
一是獨居老年人并非家庭結構轉變過程中被動、消極的應對者。社會各界往往將獨居老年人視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認為其是養老服務體系中最需要支持的重點人群。實際上,空間地理位置的孤立并不等于人際關系的隔離。一些老年人雖然獨自居住,但仍然可以通過經營自己的人際關系,逐漸形成圈層式的、功能分異的社會護航網絡。當家庭養老資源不足時,他們并非被動的承受者,可以通過積極地搭建自己的社交網絡,在與社會網絡成員的互動中消除自身的孤獨感。從本文的研究結論也可以看到,夫婦獨居老年人不僅沒有體現出更強烈的孤獨感,還更可能具有多元-活躍型的社會網絡。即便是單人獨居老年人,也僅在具有子女-消極型社會網絡的情況下感到孤獨。因此,最值得關注的正是社會網絡匱乏且單人獨居的老年人。在實際工作中需要對這部分老年人進行有效識別,并展開精準幫扶。
二是未來的老齡工作需要通過積極的公共政策,促進老年人多元-活躍型社會網絡的形成。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表明,作為一種伴隨人口轉變和社會發展所出現的現象,獨居本身并不構成問題,重要的是全社會如何適應獨居的普遍化。豐富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可以作為今后老齡工作的一個重要方向。長遠來看,公共政策的制定除關注老年人的資源稟賦和獨立性提升外,還要在活躍基層活動基礎上重建社區環境,重視社區中的人際交往,注重社區內部互助氛圍的營造,鼓勵老年人走出家門,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就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而言,應該看到獨居老年人社會網絡的異質性,識別出社會網絡最匱乏的老年人,從而實現養老服務遞送的精準匹配。
最后,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在于實證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即未能消除不可觀測的因素,如老年人的性格、心態等對社會網絡和孤獨感同時產生影響。工具變量法可以在實現本文研究目的基礎上,盡可能地避免內生性問題。遺憾的是,該數據未能出現合適的工具變量,這也是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