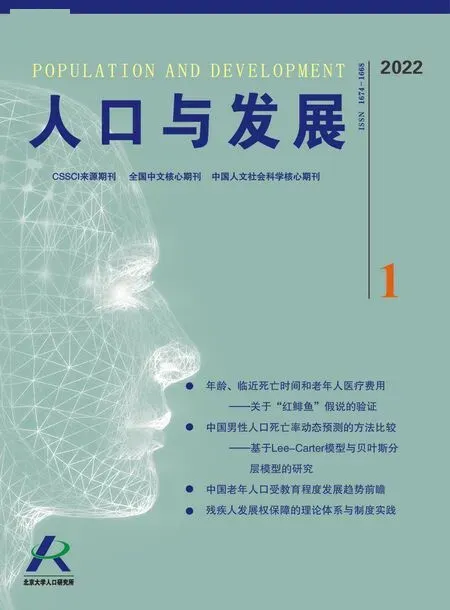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理論體系與制度實踐
蘇暉陽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1 引言
殘疾人發展權是殘疾人群體因其集體特征而享有的,以殘疾人個體全面發展為目標,以保障殘疾人公平、公正地分享發展成果和平等參與社會實踐、完成殘疾人社會融合為基本內容的發展權利。作為人類社會中較為特殊的一類群體,其發展權利毋庸置疑需要得到重視。縱觀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法律與政策發展,殘疾人發展權保障已成為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價值共識與文化共識。雖然殘疾人發展權是一般發展權概念的延伸,但殘疾問題的特殊之處在于殘疾人在常規的社會環境下會遇到更多障礙,因而面臨正常生活的困難(關信平,2017)。由此,殘疾人特殊的社會需求決定了殘疾人發展權需要在一般發展權的基礎上獲得深入和具體的保障(劉崇順,2006)。
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時期,我國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理應追求更高的目標。《“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1)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中明確提出應當提升殘疾人的發展能力,實現“完善殘疾人就業支持體系”“提升特殊教育質量”“完善無障礙環境建設和維護政策體系”等要求。然而,我國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仍然存在不足:法律法規缺乏執行力和強制力保障,信息基礎設施與無障礙環節融合不暢,教育建設參與主體單一,殘疾人社會融合程度仍有待提升等(葉靜漪,蘇暉陽,2021)。如何正確揚棄外國福利國家建設、全球殘疾人事業發展特別是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經驗,提出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中國方案?如何進一步系統性地建立起完整完善全方位的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理論體系?如何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政策及其實踐,提升殘疾人發展權保障水平?都是在我國殘疾人發展權保障事業推進過程中需要著重和深入思考的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在新時代推動我國殘疾人社會融合的背景下展開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探討,以殘疾人發展權的理論與實踐為主要線索,對殘疾人發展權的理論體系和制度實踐進行梳理和分析。
2 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政治與法律基礎:價值內涵與規范依據
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正當性源自法律制度層面和政治參與層面的平等要求。制度的形成與運作就是將價值不斷灌注到規范的結果,法律規范對于殘疾人發展權的實現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它從宏觀意義上奠定了殘疾人發展權保障制度的價值取向,在具體意義上確立了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規范依據,體現了殘疾人發展權從應然人權到法定人權的演變。(2)此處的應然人權指的是根據國際條約或一般法理承認殘疾人享有人權,是發展權的“權利主體”,由于國際條約和一般法理對主權國家并沒有強制約束力,故而這種發展權由于沒有實定化而仍停留在“應然”層面;相應地,法定人權就是指是殘疾人發展權的憲法化和法律化。與此同時,政治參與權利也是殘疾人享有的基本人權,殘疾人通過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培養、鍛煉自身的政治能力,既是殘疾人作為人的本能需求,也是實現殘疾人自身發展、實現殘疾人發展權的重要路徑。
在國際規則層面,《殘疾人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作為聯合國第一部專門保障殘疾人權益的國際法律文件,為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奠定了國際法基礎。在此之后,各國際組織和國家都以此為共同價值基礎與規范藍本,為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提供更為具體細致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撐。在各國國內法層面,許多國家都在憲法或憲制層面確認了殘疾人的發展權,比如依據憲法制定綜合性的殘疾人權利保障法,并出臺專門的單行法和具體政策,積極采取計劃、行動等等。
對于政治參與的國際共識,《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第二十一條規定:“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3)聯合國,https://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參與權利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在選舉民主的層面包含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本文更加強調其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或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面向(王錫鋅,2008)。(4)之所以并非強調選舉面向并不是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本體性價值,而是基于其群體特殊屬性,殘疾人群體在社會中屬于少數群體、特殊群體的地位,在民主機制中天然處于弱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方式能夠更有力地反映殘疾人群體的訴求。在實踐中,不少國家通過設立專門的殘疾人機構,與殘疾人群體的協商來體現殘疾人的政治權利。例如英國成立了“英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DRC)(5)負責執行殘疾立法和審查1995年《殘疾歧視法》,2007年,它被平等和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取代。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isability-rights-commission,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其職能之一就是幫助殘疾人實現自己的各種政治權利。美國于1978年成立了“美國全國殘疾人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n Disability,NCD)(6)NCD是一個獨立的聯邦機構,負責就影響殘疾人的政策、計劃、實踐和程序向總統、國會和其他聯邦機構提供咨詢。https://ncd.gov/about,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負責監督、評價《美國殘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的執行情況,并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征求殘疾人個人或相應團體的意見(秦玉彬,2008)。
然而,盡管各國殘疾人發展權保障制度的價值基礎基本一致,但由于各國的憲法或憲制各有不同,故而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制度設計也各自呈現了不同的特色。
美國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鮮明特色是殘疾人的發展權由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共同保障,部分州在《美國殘疾人法》的基礎之上,出臺專門的殘疾人法案,且超過半數的州均在其民權法案中明確了對殘疾人違反反歧視規定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例如《田納西州殘疾人法案》(Tennessee Disability Act,1990)中對殘疾人就業歧視、處罰、申訴程序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并且要求政府積極重視殘疾人在公共服務部門的招聘、評估和就業,對于殘疾人就業權的保障進行更為細致的規定。并且,美國逐漸將更多權利和發揮的空間留給地方政府和社會,促進參與主體的多元化(葉靜漪,蘇暉陽,2021)。例如,《讓每一個學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2005)相較于《不讓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2001),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教育部僅制定全國整體的教育目標,具體做法則由各州自行決定(黃暉,2020)。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7)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G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所有國家機關的義務”,“人的尊嚴”由此成為德國憲法以及依據憲法制定的其他法律所貫徹的核心價值。相應地,德國對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呈現出注重殘疾人社會融合的特征,致力于實現殘疾人平等參與社會生活、融入社會,體現出通過積極保障發展權來彰顯殘疾人“人的尊嚴”的努力。德國的“殘疾人保障法”在該國的《社會法典》中通過專章(8)Sozialgesetzbuch IX的形式頒布,并以“殘疾人的康復與參與”(9)Rehabilitation und Teilhabe behinderter Menschen的名稱生效,這標志著德國不僅僅只關注為殘疾人或面臨殘疾風險的人提供照料,而且致力于減少他們自主參與社會和獲取平等機會中存在的障礙(程子非,2020)。此外,《重度殘疾人法》(10)Schwerbehindertengesetz,SchwbG(1953)《勞動促進法》(1969)為殘疾人參加就業、接受培訓提供了規范依據(喬慶梅,2009);《殘疾人平等法》(11)Gesetz zur Gleichstellung behinderter Menschen,BGG(2002)《普遍平等對待法》(12)Allgemeine Gleichbehandlungsgesetz,AGG(2008)等法律則為殘疾人提供了相對公平的社會環境。
《日本國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全體國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權利”“國家必須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為提高和增進社會福利、社會保障以及公共衛生而努力”。在日本憲法的指引下,日本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法律規范也呈現了從以特定殘疾類型人群單行立法為主到統一規定的特點。其中,日本的《殘疾人基本法》是其保障殘疾人權益的基礎性法律文本依據,著重增強的是政策的綜合性和一致性,在其2011年的修訂中,增修了其社會建設的目標——建設人人相善其群的“共生社會”,(13)障害者基本法(昭和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律第八十四號),參見https://www8.cao.go.jp/shougai/suishin/kihonhou/s45-84.html.,2021年6月16日最新訪問。提出既要注重從殘疾人個人出發,鼓勵發揮殘疾人的能動性,又要關注社會大環境對于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要求國家、地方公共團體等機構能夠為殘疾人發展提供保障,注重多元共治。日本《殘疾人福利法》(1960)第一條之二也對“共生社會”的建成提出了相應的制度性規定,要求“所有殘疾人應通過主動克服自身殘疾,發揮自身能力努力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同時第二條要求“國家及地方共同團體應為前條第二款規定的理念的具體實現著想,努力為殘疾人提供康復援助和實施其康復所需的保護。國民應當基于社會連帶觀念,努力對殘疾人克服殘疾,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努力予以協助。”(14)《知的障害者福祉法》(昭和三十五年法律第三十七號),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35AC00 00000037_20200401_430AC0000000044&keyword=知的障害者福祉法,2021年6月3日最新訪問。《日本無障礙法》當中也提出要增強“軟政策”體系的充實和完善,促進國民對老年人及殘疾人的困難感同身受,從而實現“內心無障礙化”(賈巍楊,王小榮,2014)。
作為《殘疾人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殘疾人職業康復和就業公約》(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Disabled Persons)Convention)等幾大核心人權公約的締約國,我國亦構建了較為全面的殘疾人發展權保障機制。
第一,我國保障殘疾人發展權在憲法層面得到了體現,《憲法》第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另外,《憲法》第三十三條為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灌注了“平等”以及“尊重人權”兩大價值。它們成為支撐我國殘疾人發展權的規范基礎。
第二,為了更好貫徹憲法的要求,我國在制度層面進行了綜合性立法,制定了具有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基本法——《殘疾人保障法》。此外,我國通過出臺《殘疾人教育條例》《殘疾人就業條例》《殘疾預防和殘疾人康復條例》《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等行政法規,為特定領域的殘疾人發展權保障提供了具體法律依據,以幫助殘疾學生最大程度地融入普通教育,促進殘疾人就業,為殘疾人創造無障礙環境,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殘疾人保障法制體系。
第三,我國明顯區別于其他國家的特色是在法律之外尚有系統性的政策、規劃、計劃為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提供制度支撐。例如國務院在2016年8月印發的《“十三五”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規劃綱要》,是匹配《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殘疾人小康進程的意見》,依據《殘疾人保障法》和“十三五規劃”制定的,對增進殘疾人民生福祉、促進殘疾人全面發展、幫助殘疾人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建共享全面小康社會做出了戰略性部署。這些公共政策雖然不具有完整的法的外在形式,卻有具備實質性法律特征的條文規范,常常被視為“軟法”或“準法律”,使法律的落地和實施更具活力和實效(肖金明,2013)。
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我國也在保障殘疾人平等參與政治生活上做出了巨大努力。《殘疾人保障法》第六條明確了法律與政策制定時應當聽取殘疾人意見,以及殘疾人有權提出自己的意見。在殘疾人群體的參與之下,公眾參與型立法逐漸取代了最初的專家主導型立法,越來越能夠真正滿足受眾的多元發展需求。(15)例如甘肅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堅持問題導向增強立法實效”,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09/18/content_2061436.htm.,2021年6月3日最新訪問。從利用專家經驗給予單向法律保護,到聽取公眾意見定向提供保障,與《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所強調的“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做有關我們的決定”理念高度契合。
實踐中,我國也構筑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殘疾人政治參與體系。
一方面,我國從立法上確立和保障殘疾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除《憲法》中明確規定包括殘疾人在內的所有公民都依法享有政治權利和自由之外,《殘疾人保障法》第三條、第六條都明確規定殘疾人有權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等。并且,《選舉法》第三十六條更是對殘疾人行使選舉權作出了特殊規定,規定選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殘疾不能寫選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寫,為其參加選舉提供便利。2018年,共有5000多名殘疾人、殘疾人親友和殘疾人工作者擔任縣級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
另一方面,黨和政府為殘疾人平等參與政治生活保駕護航。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宣傳、貫徹《殘疾人保障法》的規定,溝通政府、社會與殘疾人三方,與相關政府部門協調與推進與殘疾人相關政策。2020年,各地殘聯協助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議案、建議、提案735件,辦理議案、建議、提案1109件,(16)參見中國殘疾人聯合會:《2020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s://www.cdpf.org.cn/zwgk/zccx/tjgb/d4baf 2be2102461e96259fdf13852841.htm.,2021年4月18日最后訪問。有效拓寬了殘疾人政治參與的渠道,推進了殘疾人發展權的實現。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注《殘疾人保障法》實施情況,多次開展執法檢查活動,以此推動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工作(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全國政協亦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協商議政活動持續推進殘疾人的權益保護。2021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針對殘疾人教育、就業、康復服務、社會保障、無障礙建設等發展要求提出了多項議案和提案。(17)例如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殘聯副主席呂世明提出,要依法推進無障礙環境建設,提高無障礙出行信息服務水平。參見http://www.cappd.org/news/show-7198.aspx.,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年的工作報告中也強調要切實保障殘疾人權益,為殘疾人訴訟開辟綠色通道。(1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15/c_1127212486.htm,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針對目前我國殘障人士的出行障礙,檢察機關也積極行動,開展無障礙公益訴訟,激活公益保護機制,并在無障礙公益訴訟訴前聽證會中邀請殘聯代表、殘障人士代表等參與,聽取殘疾人群體聲音,保障其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協同行政機關加強無障礙設施建設。(19)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無障礙環境建設公益訴訟典型案例,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105/t20210514_518136.shtml.,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
3 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具體途徑
政治與法律的基礎是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正當性來源,為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具體途徑提供了規范依據。在此基礎上,遵循《殘疾人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的要求,結合各國殘疾人發展權保障實踐,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具體途徑可以總結為社會保障、無障礙環境、文化與教育和司法保障四大方面。其中,社會保障解決殘疾人的康復和就業問題,保障殘疾人的基本生活;無障礙環境保障為殘疾人提供獨立生活的條件,是殘疾人參與社會和融入社會不可或缺的條件;文化與教育保障考慮殘疾人精神層面的權利實現,而司法保障則是前述具體途徑的制度兜底,為殘疾人各項權利實現提供司法渠道的支持。
3.1 社會保障支撐:健康支持與經濟幫扶
殘疾人社會保障一般包括殘疾人社會保險、殘疾人社會救助和殘疾人社會福利。然而,“殘疾人社會保障僅僅停留在一般法律制度安排遠遠不夠,必須通過專項法律制度給予特別扶助,才有可能減輕或消除歧視,維護實質公平和平等權利”(余向東,2002)。為了實現殘疾人群體的社會融合,這一“特別扶助”主要著力于身體層面的健康權利和財產層面的經濟權利兩方面。
就前者而言,殘疾人健康權利的保障是實現殘疾人發展權的“基礎硬件”。我國高度重視殘疾人健康權利保障,出臺《殘疾預防和殘疾人康復條例》以預防殘疾發生、減輕殘疾程度,幫助殘疾人恢復或者補償功能,并制定發布《國家殘疾預防行動計劃(2016—2020年)》以推進殘疾預防工作。此外,我國還積極建設康復機構,不斷提升康復條件。截至2020年底,全國有殘疾人康復機構10440個,其中殘聯系統康復機構2550個。(20)數據來自《2020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日本也將殘疾預防視為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重要工作。在《殘疾人對策基本法》(1983年修訂)中規定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必須促進關于殘疾發生原因及其預防的調查研究。為防止殘疾發生,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必須普及必要的知識、強化母子保健對策、推進對構成殘疾原因的傷病的早期發現及早期治療,并采取其他必要對策。(21)《障害者基本法》(昭和四十五年法律第八十四號)。
就后者而言,各國政府對殘疾人的經濟幫扶包括直接給予的資金支持和通過就業實現的經濟賦能兩個層面。在直接支持層面,各國以財政補貼、社會保險、社會保障基金等形式為殘疾人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以我國為例,截至2020年底,我國城鄉殘疾居民參加城鄉社會養老保險人數已達2699.2萬;680.1萬60歲以下參保重度殘疾人中,657.9萬人享受了參保個人繳費資助政策,占比96.7%。(22)數據來自《2020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英國,政府為殘疾人提供基礎收入保障和特殊需求津貼保障,包括殘疾人工作津貼(disability working allowance)、殘疾人生活津貼(disability living allo-wance)、傷殘醫療補助金(invalid care allowance)等。(23)參見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and Benefits Act 1992的規定,參見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2/4/contents/enacted,2021年5月31最后訪問。德國對于不同殘疾人群體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保障形式,比如說為老年殘疾人提供醫療服務、康復服務和護理保險待遇;對于需要配備輔助器械或者需要進行生活環境無障礙改造的群體,由政府或相應的社會保障基金(24)德國對殘疾人設置了“傷殘撫恤金”(Disability pension),參見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ssptw/2018-2019/europe/germany.html,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出資為其配備或改造(喬慶梅,2009)。美國的聯邦殘疾保險(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為足夠工齡并在工作期間繳納社會保障稅卻因為殘疾原因而無法正常工作的勞動者及其家屬提供保險津貼,直到他們身體恢復,重返工作崗位(馬盼盼,2012)。據美國社會保障局(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SA)統計,2021年共有800萬殘疾工人收益,平均每月給付近1300,000美元。(25)參見https://www.ssa.gov/oact/STATS/dibStat.html.,2021年7月26日最后訪問。
然而如果僅將經濟幫扶限制在直接資金支持的層面,那么殘疾問題似乎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資金問題,即政府、社會為殘疾人提供資金幫助,通過救助與“施舍”改善殘疾人生活狀況。盡管這一方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殘疾人發展權,但如果僅限于此,則將忽略社會環境以及社會期望與個人能力之間互動,使殘疾人難以擺脫“社會排斥”(李莉,鄧猛,2007)。因此,經濟幫扶的第二個層面,也就是通過就業實現經濟上的主動賦能,是保障殘疾人能夠自信主動地融入社會,獲得發展的基本方式(劉勇,2013)。在《殘疾人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006)中即表明殘疾人有權享受經濟和社會保障,有權按照其能力獲得并保有職業;有權接受職業培訓、職業康復和就業指導等服務,以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和技能并參與到社會生活。(26)參見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關于殘疾人的世界行動綱領》(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1982)也明確指出,“會員國應制定政策,設立各項服務的支助性機構,以保證殘疾人都能有平等的就業機會。”“應該為那些有特殊需要或有特別嚴重障礙而不能應付競爭性就業要求的殘疾人,提供受保護的職業”等。(27)參見https://www.cdpf.org.cn//zwgk/zcwj/gjwx/00044a3ddb554cc390f08ff4a2021616.htm.,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
美國在殘疾人就業權的保障方面更加偏重于發揮市場與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政府更多地擔當“守夜人”角色,通過培育融合文化并提供可靠機制保障、設立職業介紹所、就業政策辦公室等就業服務機構等,提供多樣化就業保障。此外,美國還在本世紀初興起了除庇護性就業和支持性就業之外的定制化就業政策,“因人設事”,更加充分地發揮殘疾人的“比較優勢”。(28)Office of Disability Employment Policy.Customized Employment Competency Model.https://www.dol.gov/odep/pdf/2011cecm.pdf.,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我國在《殘疾人保障法》和《就業促進法》中對各級政府提出了相應要求,規定政府需要采取優惠政策和扶持保護措施,實現殘疾人多渠道、多層次、多種形式就業,并對殘疾人勞動就業權的保障作了具體規定。《殘疾人就業條例》更是對保障殘疾人就業的基本方針和保障措施、保障殘疾人就業的政府職責和用人單位責任、提供給殘疾人的就業服務等作了詳細規定。同時,伴隨著我國“互聯網+”就業模式的興起,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自主就業創業等舉措和方式也在不斷拓寬殘疾人就業渠道,政府也在稅費減免、政府優先采購等提供相應的優惠政策和扶持保護措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日本、德國、英國等國在采用按比例安置殘疾人就業的同時,也建立了庇護工廠集中安置殘疾人就業,容納那些身體條件欠佳或患有較重殘疾,無法通過正常途徑獲得工作的人,并為他們提供職業培訓(路琪等,2017)。
總之,直接給予的資金幫助和通過就業實現的經濟賦能是殘疾人經濟幫扶的兩大重要因素,而完善的康復體系和積極的經濟幫扶又從社會層面保障了殘疾人發展權的實現。在我國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殘疾人發展權保障亦體現在殘疾人脫貧工作的方方面面。2020年助殘日主題為“助殘脫貧,決勝小康”,將殘疾人作為脫貧攻堅中需要特別關照和兜底保障服務的重點人群(張瓊文,2020)。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加速推進,我國扶貧事業惠及8000多萬殘疾人(石長毅,2016),在全國各地脫貧攻堅的實踐中,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政策實踐遍地開花,例如“開展農村殘疾人種養業大戶和基地扶持、實用技術培訓、康復扶貧貸款貼息、電子商務助殘、產業扶持助殘和手工制作等方式,促進貧困殘疾婦女就業脫貧,加大社會助殘力度,推動殘疾人精準脫貧增收。”等等(董銘勝,2018)。
3.2 無障礙環境支撐:獨立生活與充分參與
受生理條件的限制,公共設施包括信息設施的不健全會成為殘疾人社會參與過程中的嚴重阻礙。因此,殘疾人的發展權保障需要提供外部友好環境的支持,創造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環境是指“為便于殘疾人等社會成員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相關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獲得社區服務所進行的建設活動。”(29)《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22號)第二條。觀察各個國家無障礙環境建設的發展,可以發現其呈現出以下趨勢:第一,服務對象擴充,從“無障礙設計”向“通用設計”的發展,即把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服務對象從殘疾人擴充至所有人;第二,建設范圍擴充,信息無障礙越來越受到重視,障礙設施標準也越來越向智能化、網絡化方向發展;第三,立法科學性提高,無障礙設計研究機構在無障礙法律法規制定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四,設置專門機構實施建設和監督運行。
英國早在1970年的《慢性病與身體殘障者法案》(Chronically Sick and Disabled Persons Act)中就存在要求公共建筑物應設置無障礙設施的規定,(30)第4條“Access to,and facilities at,premises open to the public”;第五條“Provision of public sanitary conveniences.”但因法案中并未明確規定主管機關或執行單位,以及罰則等細節導致缺乏執行力等被經常詬病。之后在1995年頒布的《殘疾歧視法案》(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中作出了改進,實施方法以及社會場所和政府部門等多主體責任被明確。除了場所等實物方面的無障礙措施,英國也在推進信息無障礙的實施,例如英國政府對企業數字服務的無障礙化有明確的手冊要求,企業必須配備屏幕放大器、閱讀器、語音識別等功能,并要求用戶研究中必須有殘疾人參加。(31)https://www.gov.uk/service-manual/helping-people-to-use-your-service/making-your-service-accessible-an-introduction#what-to-do-about-accessibility-in-discovery.,2021年6月7日最新訪問。
德國在《殘疾人平等法》(2002)(32)Gesetz zur Gleichstellung behinderter Menschen(Behinder tengleichstellungsgesetz - BGG).當中明確了德國對無障礙環境的理解和判斷,也間接明確了德國無障礙建設的目標:殘疾人能夠以一般和通常的方式接觸和使用建筑及其他設施、交通工具、技術器具和公用設施、信息技術系統、口頭和視覺信息源、通信設備等,而沒有特定的困難(特萊莎·德格納,2007)。當中一并明確的還有聯邦政府在無障礙環境建設上的義務,包括建設無障礙建筑物、提供無障礙選舉環境及無障礙進入餐廳和交通工具等。德國通過法律與經濟手段實現雙重激勵,形成了以國家為主導、發揮政府部門示范作用的德國模式,無障礙環境建設實踐也取得了明顯效果(徐煥斌,2020)。
日本有關殘疾人無障礙的規定散見在不同群體的福利法中,如《兒童福利法》(1947)(33)由日本政府頒布,在第三章第四十二條、四十三條均規定了針對殘疾兒童的設施建設要求。參見沈重:“日本兒童福利法”,《國外法學》1980年第4期,第74頁。《身體障礙者福利法》(1949)《智力障礙者福利法》(2005)《精神保健及精神障礙者福利法》(1988)等。除此之外,日本也有專門的標準規范,如《無障礙化建筑設計標準》(1982)《長壽社會住房設計指南》(1995)等。
我國的無障礙制度建設則體現了從宏觀到微觀逐步細化的過程,《殘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條(34)《殘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國家和社會應當采取措施,逐步完善無障礙設施,推進信息交流無障礙,為殘疾人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創造無障礙環境。”在法律層面正式確立了建設無障礙環境和實現殘疾人信息交流無障礙的目標。《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和《“十三五”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規劃綱要》則從網站設計、公共服務場所建設和信息發布等方面進一步落實。在此基礎上,地方法規和規章相繼出臺,因地制宜對《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進行補充細化,使其更順利地落地于各省市。(35)目前,已有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出臺無障礙環境建設管理辦法的地方政府規章,例如上海市2021年發布并實施的《上海市無障礙環境建設與管理辦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5號)。特別值得一提的,海南省2020年出臺《海南省無障礙環境建設管理條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告第52號),將無障礙環境建設上升到地方性法規層面。中國殘聯、國家工信部、中宣部等部門還制定了多份其他規范性文件輔助無障礙建設的發展,進一步細化了無障礙建設過程中各項要求。(36)例如由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殘聯發布的《關于推進信息無障礙的指導意見》(工信部聯管函〔2020〕146號);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方案》(工信部信管〔2020〕200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開展無障礙環境市縣村鎮創建工作的通知》(建標〔2018〕114號)。此外,無障礙技術標準作為各類無障礙產品研發、使用的重要依據也越來越受到重視。(37)例如2009年出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無障礙設計規范》;2012年頒布的《無障礙設計規范(GB50763-2012)》等。2020年3月,我國首個信息無障礙國家標準《信息技術互聯網內容無障礙可訪問性技術要求與測試方法》正式實施,該標準將58項具體技術指標分等級進行細化規定,被譽為“在互聯網上鋪盲道”。
3.3 文化與教育保障:社會融合與權利實現
在完善法律制度,推進政治參與的基礎上,殘疾人發展權的實現還需要文化和教育的“軟實力”塑造,這關乎殘疾人發展權最終的權利實現,亦是促進殘疾人“社會融合”的重要途徑。
3.3.1 文化保障:形象塑造與文化參與
構建全面的文化保障體系、塑造積極正面的文化環境,對于促進殘疾人的社會融合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各國對于殘疾人的文化保障實踐跨越多種媒介,呈現出覆蓋范圍廣、表現形式靈活多樣的特征,不僅包括電影、紀錄片、電視連續劇、廣播等較為常見的類型,還包括新聞、廣告、真人秀、漫畫等新形式。跨越多種媒介形式的殘疾人相關媒體作品,有利于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式地展現殘疾人發展現狀,引起觀眾、讀者對殘疾人群體發展狀況的關注,同時有利于豐富殘疾人精神生活。
總的來說,殘疾人發展權的文化保障有兩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從社會公眾的角度來看,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媒介對殘疾人形象積極正面的宣傳能夠增進他們對殘疾人群體的理解,有利于消除對殘疾人群體的歧視。《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八條規定,“締約國應立即采取措施,發起和持續進行有效的宣傳運動以提高公眾認識。”按照公約的要求,各國都應該為促進殘疾人融入社會生活提供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例如在廣告方面,英美兩國以殘疾人為特色的廣告呈現日益增加的趨勢(Beth Haller & Sue Ralph,2006)。且播出的公益廣告中,對于殘疾人權利的關注更加深入,更關注殘疾人的“能力”而非其身體缺陷,更尊重殘疾人自我發展的多樣性(Arie Rimmerman,2014)。在日本,漫畫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通過漫畫作為媒介來表達殘疾人的文化訴求,具有其國家文化的獨特性,日本政府和教育系統將其用作社交文化和教學工具,漫畫文本在反映和塑造社會文化觀念、價值信仰方面起著重要作用(Andrea Wood,2013)。以著名漫畫家井上雄彥的《真實(Real)》(2000)為例,它聚焦于殘疾人籃球隊的現實情況,展現殘疾人在賽場內外的真實經歷,有利于使讀者對殘疾形成正確的理解和認知。德國曾連續舉行以殘疾為主題的電影節,并舉辦過關于殘疾人文化史的展覽。慕尼黑也成立了專門的殘疾人與媒體工作組,致力于向公眾宣傳和啟發關于殘疾的媒體描述。我國反映殘疾人生活處境的文藝作品也日益增多,涌現出了一批反映殘疾人生活、關注殘障人處境的藝術作品,例如電影《我的少女時代》(2011),歌曲《你是我的眼》(2002)及2014年的同名電視劇,2005年春晚的殘疾人藝術團舞蹈《千手觀音》等。總的來看,文化作品中的殘疾人角色數量呈現出增加趨勢,許多作品已經成功地創造了經典的殘疾人藝術形象,通過劇中人物的正確態度真實、積極地表現了殘疾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展現了殘疾人參與日常生活的能力,有助于在潛移默化中推動殘疾人群體在社會中的融入和自我發展,促進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互相理解與和諧交流。
第二,從殘疾人群體的角度來看,殘疾人發展權的文化保障和殘疾人的文化參與息息相關,后者直接影響到殘疾人文化權益乃至整個發展權益的實現。殘疾人的文化參與具體包括兩方面:殘疾人作為消費者享有公共文化產品以及殘疾人作為生產者參與社會文化生活。就殘疾人群體作為消費者享有公共文化產品而言,在新聞報道方面,許多著名的新聞媒體已經在官網中設置了一定比重的殘疾新聞專區。(38)例如《紐約時報》殘疾專欄,https://www.nytimes.com/topic/subject/disabilities,2021年5月19日最后訪問。截至2019年底,我國共有省級殘疾人專題廣播節目25個、電視手語欄目32個,地市級殘疾人專題廣播節目219個、電視手語欄目272個,基本實現大多數省市的覆蓋。(39)數據來源于《2019年中國殘疾人發展統計公報》(殘聯發〔2019〕18號)。就殘疾人群體作為生產者參與社會文化生活而言,隨著現代媒體、科學技術的發展,殘疾人能夠越來越便利地參與到文化生活和文化創作中,表達自己或群體聲音,為社會提供文化產品。根據自身特點、能力的不同,部分殘疾人能夠通過真人秀、紀錄片、影視創作等途徑參與文化生活和文化產品的創作,一些殘疾人也將獨立紀錄片、自傳式紀錄片作為自我表達的渠道。例如,我國2011年改編自張海迪的長篇小說《輪椅上的夢》(2005)的影片《我的少女時代》。此外,國內外越來越多的殘疾人參加了競爭形式的真人秀節目當中,例如我國的《中國達人秀》(40)2010年開播的系列電視節目,眾多殘疾人選手展示自己的風采。參見《電視綜藝節目從煽情轉勵志殘疾人表演震撼觀眾》,北京青年報2011年10月25日,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1/10-25/3413142.shtml.,2021年6月2日最后訪問。、英國的《X音素(X-factor)》(2004)和美國的《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2001)等,突破了殘疾人難與正常人同臺競技的傳統。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關于殘疾人的文化作品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殘疾人的負面刻板印象。例如1940年代到1980年代好萊塢電影中,精神殘疾人士通常被描述為危險、暴力的對象(Lisa Lopez Levers,2001)。影視作品對殘疾人的刻畫影響著社會公眾的態度,他們傾向于根據影視作品中的角色來理解殘疾人,具有負面刻板印象的影視作品不利于社會公眾對殘疾人群體的正確認知和包容接納。此外,在一些節目中,制作團隊仍然傾向于聚焦殘疾選手的殘疾經歷、突出其殘疾特征,從而引發觀眾的欽佩和憐憫,這將導致觀眾難以“平視”殘疾人,從而影響平等的競爭環境。
綜上所述,對于殘疾人發展權的文化保障在中國和部分主要發達國家呈現較為積極的發展態勢,對殘疾人社會融合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究其原因,在宏觀層面可以歸結于較為完備、與時俱進的文化媒體方面的法律法規規范,在具體層面也少不了社會共識的助力作用。各國政府及民間為展現殘疾人生活境況的各種媒介、關懷殘疾人的共識與一系列文化活動,在有效保障殘疾人基本生存權的基礎上,還為殘疾人行使文化類發展權利提供了保障。然而遺憾的是,各國仍不同程度地缺乏成體系的理論、實踐以及具體統一的保障行動。
3.3.2 教育保障:平等價值與融合理念
基于實質平等的要求,殘疾人的教育權應當予以傾斜保障。一方面,實質平等反對在教育過程中簡單將健全人和殘疾人混合的做法;另一方面,實質平等也反對沒有合理理由的“隔離但平等”(即使這種平等帶有某種實質平等的內容,比如提供便于殘疾人使用的特殊設施或教材)的做法。正如著名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41)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__ Topeka_ 347 U.S.483(1954).判決指出的一樣,教育方面沒有合理理由的隔離“會讓他們覺得自身在共同體中的地位低人一等,這種感覺會給他們的心智造成永遠難以抹去的傷痛”。(42)布朗案雖然不涉及殘疾學生的教育問題,但是推翻了“分離但平等”這一原則。這一原則亦是分離殘疾學生/學校與正常學生/學校的指向,因此這一推翻亦可論證殘疾學生與正常學生分離帶來了實質不平等。對此,起源于特殊教育的融合教育(全納教育)(43)本文中,融合教育和全納教育的概念是辯證統一的。從概念上看,“融合教育因其“全納”“公平”的理念和對弱勢群體教育權利的關注,受到各國教育者推崇,成為當前國際教育發展的主流方向。”可知融合教育的概念事實上涵蓋了“全納”的要求。參見彭興蓬:“融合與全納:新時代背景下隨班就讀功能轉化與生成”,《中國教育學刊》2021年第2期,第81-87頁;馮超、傅王倩、陳慧星:“國際融合教育政策演進路徑、特征及其啟示——基于聯合國組織的融合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中國特殊教育》2020年第11期,第14頁。關注到了特殊兒童被排斥在普通教育系統之外的這一普遍性的社會現實,“要認識到在普通教育體系里為殘疾兒童、青少年與成人提供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4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薩拉曼卡宣言》(1994),http://www.nwccw.gov.cn/2017-04/06/content_146937.htm.,2021年5月30日最后訪問。等融合教育的思潮的傳播和普及,也體現了對殘疾人人權保障的關切(黃志成,200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教育2030行動框架》(2015)將“確保全納公平的優質教育,使人人可以獲得終身學習的機會”作為明確目標。各國對殘疾人的教育政策也在此思潮的影響下,制定相應的全納教育政策。
在日本,傳統特殊教育理念認為“隔離”的、以“治療”為主的醫學模式能更好地滿足殘疾孩子的需求。因此,在發展初期,盲校、聾校、養護學校等特殊教育學校和普通學校特殊班級等教育形式開展“特殊教育”(賴晶玲,2017)。自融合教育理念提出以來,2005年日本發布《推進特別支援教育的制度改革》咨詢報告(45)中央教育審議會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共生社會の形成に向けたインクルーシフ?教育システム構築のための特別支援教育の推進(報告)》,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gijiro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2/07/24/1323733_8.pdf.,2021年6月3日最新訪問。,確立了“特別支援教育”的基本方針,并成為日本全納教育的綱領性文件,旨在建立一個不區分殘疾人,所有學生都能一起學習生活的“共生社會”(田輝,2011)。英國融合教育具有人本主義價值取向,其價值目標從“不欺”(NO Bully)演變為“全人”(Whole Person)。英國1976年頒布《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首次以立法形式打破了殘疾學生隔離教育的藩籬,逐步走向全納與融合。1978年出臺的《沃諾克報告》(The Warnock Report)突破了傳統殘疾特性的視域,以融合的視角對待殘疾個體,提出一體化教育原則,并強調“特殊教育需要”。德國簽署《殘疾人權利公約》后,政府更加積極地在各層面踐行融合教育,尤其關注殘疾人融入社會的能力提升,針對殘疾人的特殊需求,制定了完善的職業教育保障(王光凈,2016)。我國1996年施行的《職業教育法》亦對殘疾人在接受職業教育方面規定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同時在教育與就業銜接的方面,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財政補貼。(46)2021年3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此次修訂亦明確要“扶持殘疾人職業教育的發展”,以及“殘疾人職業教育除由殘疾人教育機構實施外,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接納殘疾學生。”強調殘疾人職業教育的“全納”,體現了殘疾人教育融合的理念。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8/content_5459462.htm.,2021年6月3日最新訪問。
我國《殘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殘疾人教育,實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以普及為重點的方針,保障義務教育,著重發展職業教育,積極開展學前教育,逐步發展高級中等以上教育。”系有針對性地對殘疾人不同的教育需求提供教育條件,開展教育政策。我國《殘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五條(47)我國《殘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普通教育機構對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殘疾人實施教育,并為其學習提供便利和幫助。”則為全納教育的“隨班就讀”提供了法律保障,要求普通教育機構中的普通班級需要接收殘疾學生入學,并為其提供必要幫助。教育部等七部門出臺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7—2020年)》(48)教基〔2017〕6號。正式確立了“以普通學校隨班就讀為主體、以特殊教育學校為骨干、以送教上門遠程教育為補充”的全面推進融合教育基本原則。2017年修訂的《殘疾人教育條例》同時指出應提高殘疾人教育質量,積極推進融合教育,體現了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殘疾人教育發展的新方向。各類實施細則、提升計劃等作為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法律法規的補充和延伸,更是共同支撐著我國特殊教育、融合教育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發揮著重要作用(石云鶴,龐文,2020)。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統計,1995年以來,融合教育招生數和在校生數一直多于特校招生數和在校生數,截至2018年底,融合教育招生數約是特校的1.20倍;融合教育在校生數約是特校的1.22倍。
3.4 司法保障:程序優化與實體支持
司法是法律生命之所系,加強與完善殘疾群體相關司法保障是推進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必然要求(董銘勝,2018)。(49)司法對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可以從程序性保障和實體性保障兩方面進行論述。程序性保障是指在一般訴訟程序中通過給予殘疾人特殊照顧或為其提供專門的訴訟程序來為殘疾人通過司法途徑維權創造無障礙的環境,為其參與訴訟活動提供便利。實體性保障是指司法機關在有關殘疾人的案件中通過判決在實體上細化法律對殘疾人權利的保障規則或在實體上創制尚未在立法中成型的殘疾人權利保障規則。
3.4.1 司法對殘疾人發展權的程序保障
根據《殘疾人藍皮書: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我國持續開展殘疾人法律宣傳教育,法律救助組織的建設也在持續推進,截至2017年,全國成立殘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協調機構1987個,建立殘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1746個。除此之外,我國也著力將互聯網技術運用與普及于殘障群體中,其對殘疾人的司法維權途徑亦有所影響,比方說殘疾人來信來訪服務數量下降,電話和網絡投訴服務增加,傳統信函反饋情況和直接到殘聯維權部門上訪的趨勢逐年下降。(50)2011-2016年全國各級殘聯維權部門每年處理殘疾人來信、接待殘疾人來訪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數據來自《殘疾人藍皮書: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
除此之外,在我國的訴訟實踐中,殘疾人的無障礙綠色通道不斷創新。在立案環節,對于殘疾人的案件做到優先立案,并對訴訟材料不齊全,主張不明確、不正確的情形進行一次性告知,同時安排專人指導殘疾人正確行使訴權;對于行動不便的,特設了電話預約立案的綠色通道。在庭審環節,盡可能地采取巡回審判,到殘疾當事人的住所地進行開庭。在執行環節,不僅優先為其執行,而且對生活困難的殘疾人,可依據其申請快速啟動司法救助審批程序,最大限度對其緩、減、免收訴訟費。(51)例如海南省高院和海南省殘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關于在審判執行工作中切實維護殘疾人合法權益的意見》所因地制宜做出的相關司法實踐。
在訴訟過程中,部分國家也設立了特殊獨立的法庭以更好地保護特殊殘疾人群體的訴訟權益。如英國開設有保護法庭(The Court of Protection)來監督《心智能力法令》(Mental Capacity Act)的實施,專門處理與缺乏自主決策精神能力的人有關的所有問題。由于精神能力缺乏者在某些情況下無法理性做出決定,行使其合法權利,故需要其在有行為能力的時候可以選擇他所信任的人作為他的代理人,或是由保護法庭根據缺乏精神能力者的具體情況與最大利益來指定代理人。再如印度在2016年修訂《殘疾人權利法案》(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ct,2016)時增設特別法庭,專門審判與殘疾人相關的,尤其是侵犯殘疾人的案件,并給予殘疾人參與司法活動以便利幫助。(52)“CHAPTER XIII SPECIAL COURT”,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ct,2016.
3.4.2 司法對殘疾人發展權的實體保障
司法對“合理便利”原則的運用和細化充分表明了司法層面的保障與法律規范一樣,在對殘疾人實體性的發展權利的實現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殘疾人權利公約》明確規定了將提供“合理便利”置于平等和反歧視的法律原則之中,作為義務主體提供義務時的參考因素,而更細致的判斷體系與標準則在司法實踐中逐漸形成。“適當”作為“合理”的關鍵要素之一,要求由合理便利的提供者與需要者雙方通過對話來溝通與協商,而其作為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在發生糾紛時法院需根據具體個案定奪。例如亨德里克·哈德森中心學區教育委員會訴羅利的案件(53)該案中,羅利.艾米(Amy Rowley)是一個只有微弱殘余聽力的聽力障礙學生,但讀唇辨意非常優秀。在一年級下學期學校為艾米設計了個別化教育方案,但不包含手語翻譯。這種翻譯服務在艾米上幼兒園期間曾進行過兩周的試驗,當時的翻譯者認為艾米并不需要這種服務。校方在與學區殘障委員會商議后認為,艾米在一年級時仍不需要翻譯服務,引發家長不滿。Se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Hendrick Hudson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v.Rowley,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2,458 U.S.176.,表明了美國最高院對“適當”這一法律概念的態度,促進了殘疾個體實質性教育權利保護制度的形成,切實保障了殘疾人發展權實現。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認定,判斷教育權是否得到保障的關注點應在于:殘疾兒童是否在公立教育系統中接受了實質性的特殊教育和相應的服務。努力使教育效果與殘疾兒童可能達到的發展水平相一致,并與同級普通學生的正常水平進行比較,而所有這一切都應當由公共教育資源來承擔。這一裁決對促進美國殘疾兒童的教育機會公平起到積極作用,使其能夠與普通兒童一樣接受公共、適宜和免費的教育(高杭,2010)。再例如在Terrell v.USAIR一案中,“便利措施的可行性”成為評價雇主是否履行合理便利義務的標準,(54)原告在工作中頻繁使用鼠標,導致其患有腕管綜合征,原告希望雇主把自己調到非全日制的工作崗位上,遭雇主拒絕。法院認為,被告無須承擔違反積極義務的責任。這是因為原告提出合理便利請求以前,雇主就已經解雇了所有非全日制工作的員工。所以,航空公司內部的所有崗位均為全職。雇主為原告安排非全日制的工作不具有可行性。See Terrell v.USAIR,132 F.3d 621(11th Cir.1998).轉引自韓旭:“論殘疾人就業中雇主提供合理便利的義務:美國經驗及其借鑒”,人權研究2020年第1期,第315頁。而在Vande Zande案中則明確了“便利措施的合理性”這一標準。(55)本案中雇主進行了工作時間的調整,但實施效果不佳,患有強迫癥的原告仍會缺勤,不能完成工作。后來原告又請求在家工作,雇主卻未批準。法院認為,雇主沒有完全履行積極義務。雇主在初次提供了一項便利措施,但被證明并不有效時,應當負有持續性義務,提供其他有效的合理便利。See Humphrey v.Memorial Hospitals Association,239 F.3d 1128(9th Cir.2001).轉引自前注,第322頁。
由此可見,“法院所宣布的結果——他們看待法律領域的方法和他們對法律領域的意見——將會反過來產生持續作用,以重新塑造法院起初著手審查材料的性質”(勞倫斯·H·卻伯,2005),通過這種“司法—立法—司法”的循環作用,實踐中的司法判決一方面按照法律規定保障殘疾人群體的訴訟利益與實體利益,另一方面反作用于法律制度本身,細化法規、制度、政策的標準,有助于將其落實到每個個體。
4 結語
保障殘疾人發展權需要國家、社會和殘疾人共同發力。其中,在法律基礎層面,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立法嚴格落實憲法精神和人類共同價值,確立殘疾人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位,將國家作為保障殘疾人發展權法律義務的主要承擔者。同時,各項保障殘疾人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與舉措為殘疾人的政治參與提供了規范依據,使殘疾人表達訴求、維護權益的途徑進一步拓寬。文化保障、教育保障和無障礙支撐一方面從殘疾人的角度強調要滿足殘疾人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強調為殘疾人積極主動參與社會生活、形成社會關系掃除障礙。司法保障則要求一方面從程序上疏通殘疾人通過司法獲得救濟的途徑,另一方面從實體上細化乃至創制對殘疾人發展權的制度規范,最終將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落到實處。
保障殘疾人發展權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姜素紅,2006)。習近平總書記曾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殘疾人一個也不能少。”(56)人民網:《習近平考察唐山》,人民網,http://pic.people.com.cn/n1/2016/0728/c1016-28593136-2.html,2021年5月31日最后訪問。“中國夢,是民族夢、國家夢,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也是每一個殘疾人朋友的夢。”(57)《習近平在會見第五次全國自強模范暨助殘先進集體和個人表彰大會受表彰代表時指出中國夢也是每一個殘疾人朋友的夢李克強劉云山參加會見張高麗參加會見并在大會上講話》,載《海南日報》2014年5月17日第1版。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必須將殘疾人的發展納入規劃藍圖,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決不能讓殘疾人掉隊。
總之,我國和國外有關保障殘疾人發展權的實踐表明了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目標不僅在于消除殘疾人生活中的不便利、滿足殘疾人生活中的物質需求,而且在于要更加注重殘疾人的社會融合,幫助殘疾人主動形成并維持一定的社會關系,致力于實現殘疾人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并融入社會。相信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升殘疾人的發展能力”的目標指引下,我國也將圍繞殘疾人發展權保障的關鍵方面,不斷提高殘疾人發展權的保障水平,最終實現殘疾人社會融合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