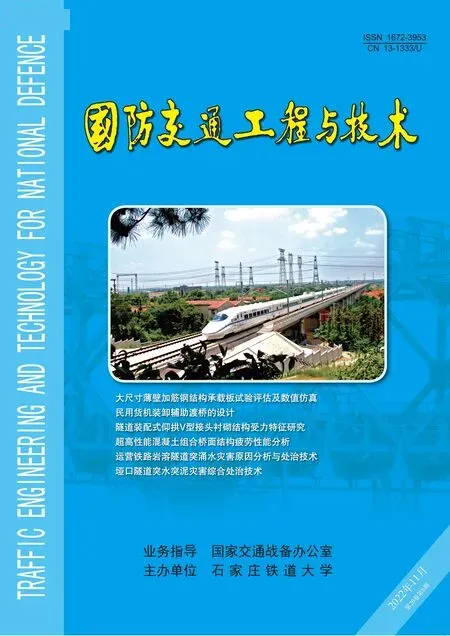美軍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機制研究及啟示
汪 欣, 王廣東
(陸軍軍事交通學院,天津 300161)
美軍戰時絕大部分裝備、補給、增援部隊都要通過海運到達戰區,海上運輸包括部隊人員、裝備、彈藥、油料和供應品的運輸,軍用物資的海上預置以及艦載物資向岸上轉運,這些海上運輸任務產生了大規模動員民船的需求。動員民船在戰時用于預置武器裝備、調運部隊及各種物資,同時部署后勤物資和清理戰后閑置物資,在美軍增強控制戰爭局勢的能力、實現戰略實施的機動性和兵力部署的靈活性方面發揮巨大作用,迅速、有效地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成為美軍高度關注的戰略問題。美軍在歷次戰爭中逐漸形成了成熟的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機制,為其軍事力量前沿化、快速化和形成全球威懾力提供重要支撐。研究美軍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機制,可為新形勢、新任務下加強我軍海上戰略投送能力建設提供現實借鑒啟示。
1 美軍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機制分析
1.1 戰時動員民船指揮機構
美軍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指揮機構包括軍事運輸司令部下屬的軍事海運司令部和國家運輸部下屬的海事管理局[1]。軍事海運司令部負責戰時動員民船的信息搜集、計劃提報、行動監督和協調服務,軍事海運司令部通過為美國軍事運輸司令部搜集動員民船能力的情報,提出相應的動員民船協議啟動計劃,監督整個行動過程中協議的執行情況;同時協調相關港務部門配合軍事運輸,確保動員民船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海事管理局負責根據政府命令對被動員的民船實施征用和管理,負責應急通信、港口應急運轉方面和協調海軍護航等工作,通過執行《志愿聯合海運協議》程序、《志愿油船協議》程序和軍事征用程序預備船和多種動員程序的啟用,為軍事運輸提供足夠的運力支持。軍事海運司令部與海事管理局協調配合,共同完成戰時動員民船的指揮控制與組織籌劃。
1.2 戰時動員民船方式方法
美軍發動的大部分戰爭都需要使用動員民船來滿足軍事運輸需求,動員民船資源是美軍海上建制運輸的輔助性力量。美軍戰時動員民船的來源渠道主要包括五大類[2]:一是懸掛美國國旗的民船,二是適用現行法律政策的外國民船,三是簽署了協議的動員民船,四是懸掛外國國旗的美國民船,五是具備軍事運輸能力的美國動員民船。這些動員民船資源類型可分為貨船、液貨船和客船三大類,貨船用來運輸作戰裝備和人員給養,液貨船用來運輸軍用油料,客船用來運輸戰斗人員、非戰斗人員以及戰場后送的傷員。無論是在美國注冊還是懸掛外國國旗的民船,戰時美軍都有權對大量的民船資源進行征用,這些民船資源共同構成了基數龐大、可滿足軍事運輸要求的動員來源。
1.3 戰時動員民船法規體系
戰時為有效地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形成了以《海商法》《海運戰備計劃》為骨干,以《志愿聯合海運協議》為主體,以《班輪協議》《志愿油船協議》等為補充的完整法規體系[3]。《海商法》《海運戰備計劃》從法律上規定了民船海上運輸的性質,保證民船平時正常營運,戰時則迅速轉入軍事運輸。《志愿聯合海運協議》以聯合運輸能力替代具體民船為導向,納入懸掛美國國旗的主要航運公司,確保聯合軍事運輸能力。《班輪協議》《志愿油船協議》則分別針對班輪、油船等民船的動員做出法律規定,解決應急或戰時的軍事運輸需求。戰時動員民船以法律為依據,以經濟為杠桿,一方面不斷完備法規體系和明確法律責任,提高動員民船執行軍事運輸任務的剛性要求;另一方面采用各種經濟手段提供補貼和優惠政策,提高民船戰時參與軍事運輸的積極性。
2 美軍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機制的特點
2.1 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模式多樣化
由于各種動員民船資源的來源不同,既有政府所有、也有私營航運公司所有,責任義務都不相同,因此會根據不同的民船資源采用不同的動員模式。美軍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模式分為征用、租約、現付交易和排他性購買權四種[4]:征用模式下,動員民船由美軍預選好,連同船員一并被征用,由政府按照規定給予民船固定費率。租約模式下,由相關管理部門與民船簽訂租約協議,采取資金租約的形式為海上軍事運輸服務。現付交易模式下,由相關管理部門對民船使用現付交易,這種模式下通常是單航程運輸。排他性購買權模式下,由相關管理部門購買民船未來運輸能力的獨占性授權,用于臨時海上軍事運輸。動員模式的多樣化保證了在節約總體經費開支的前提下,實現對各類動員民船資源保障軍事運輸能力的最大化運用。
2.2 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法規更新快
美軍從最初在海事立法中貫徹國防要求到專業動員法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1817年頒布的《海上運輸法》確保了航線上民船的保有量;1904年頒布的《軍事運輸法》促使美國私人航運企業參與到軍事運輸;1916年頒布的《海運法》、1920年頒布的《商船法》、1954年頒布的《貨物運輸優先法》以及 1978年至1986年之間先后頒布的《海事撥款法》《戈德沃特-尼科爾斯法案》等[5],都分別從法律層面確定了與軍事輸需求相配套的動員民船標準,提高了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執行剛度。美軍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后頒布的《海運戰備計劃》[5]等法規更是明確了相應的權利義務,規定了所有在美國建造或享受美國運營補貼的民船都必須在戰時承擔軍事運輸任務。進入21世紀后,動員法規隨著形勢不斷更新和變化,先后頒布的《海商法》《全國緊急狀態法》《國防法》等[5],提供了民船動員、民船補償等方面的法律依據,確保了動員民船在保障軍事運輸方面的針對性、有效性。
2.3 注重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適應性加改裝
自二戰后,美軍專門針對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持續進行大量研究試驗,形成了如《貨物專家手冊》等系列條令、標準和手冊,詳細規定了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流程、民船資源、組織指揮、職責分工、船舶布置、裝載加固、性能控制、安全管理等內容[6];同時,美軍在新船型利用和針對特殊任務的民船改裝方面,突出使用先進模擬分析工具開展研究,開展用于特殊行動的民用滾裝船改裝仿真研究,針對所擔負的海運、補給等任務,從船舶布置、船體結構、完整穩性、破損穩性、耐波性、操縱性、信號特征等方面進行了可行性研究。近年來,美軍聚焦于高速穿浪船用于戰場轉運、人員撤離等任務,在仿真設計研究基礎上完成了民船改裝技術研究試驗,動員民船的加改裝作業提升了動員民船的軍事運輸適應度。
3 對做好我軍保障軍事運輸機制的啟示
3.1 健全民船動員法規制度儲備軍事運輸能力
借鑒美軍《志愿聯合海運協議》等統一法規,以我國現有動員機制為基礎,發揮我軍平戰對接機制、國防教育宣傳機制、法規調控機制的優勢,進一步規范戰時動員民船征用的程序和方法,全面規范下達動員令、運力集結整備、交接點驗、復員等過程,形成一套實在管用的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案例范本,解決民船全要素動員實踐少、動員程序不規范等問題,切實提高動員民船效率。同時,建立主要戰略方向的民船動員潛力數據庫,對潛力統計指標架構進行優化論證,開發便于相關統計數據快速轉換的軟件,組織沿海省份的民船動員潛力普查,解決民船動員潛力變化快、更新難、統計不準的問題,切實摸清潛力底數,通過依法組建戰略運輸船隊等方式,扎實做好軍事運輸能力儲備。
3.2 加強民船動員指揮機構建設滿足新形勢要求
借鑒美軍在動員民船指揮機構建設的做法,加強我軍民船動員指揮機構的建設,建設軍地聯合指揮管理機構,有效暢通軍地協調通道,進一步規范民船動員組織流程、保障模式及技術標準。民船動員指揮機構下屬軍事指揮部門,主要負責提出動員民船需求,監督民船動員全過程;民船動員指揮機構下屬地方指揮部門則主要負責提供民船動員潛力數據,同時協調相關港務部門配合軍事運輸。由動員民船指揮機構統一組織開展常態化民船動員演練活動,開設裝卸載聯合指揮所、裝載上船、搭設棧橋碼頭、克服灘涂障礙和快速卸載等重點課目,組織滾裝船、半潛駁等動員征用,按實戰流程組織實兵裝卸載和航渡研訓演練,組織重裝備裝卸載問題研究,摸索民船輸送重裝備快速卸載的方法,為海上戰略投送積累實戰經驗。
3.3 規范民船加改裝設計適應軍事運輸特性
借鑒美軍在對民船加改裝設計方面的先進做法,考慮船舶損害管制、人員救助打撈、編隊及部隊通信等特殊問題,通過加改裝設計,使得動員民船在正常輸送部隊外,還具備傷病員后送、海岸卸載等多種功能,提高軍事運輸適應性。充分發揮動員民船的軍事運輸保障能力,提高動員民船的戰場環境適應性。由于我軍目前動員船舶種類和型號多,大多數船舶單件,加改裝技術、方案和工程設計只能針對單船,實船改裝驗證樣本少;下一步,需要針對具體動員民船型號形成多種多樣的加改裝設計,通過對眾多船型的加改裝設計進行深入研究,形成規范化的動員民船貫徹國防要求、裝載方案和保障方案等設計成果,實現戰時動員民船的快速加改裝,發揮其巨大的保障潛能。
4 結論
美軍戰時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機制成熟且完善,在動員模式、動員法規、加改裝設計方面獨具特色,為我軍提供了重要借鑒。我軍應進一步探索動員民船保障軍事運輸的內在組織和運行變化規律,優化動員民船指揮機構,擴展動員民船資源來源,完善動員民船法規體系,緊緊圍繞作戰任務需求,著眼海上投送能力生成的關鍵環節聚力攻關,為未來海上軍事行動提供堅強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