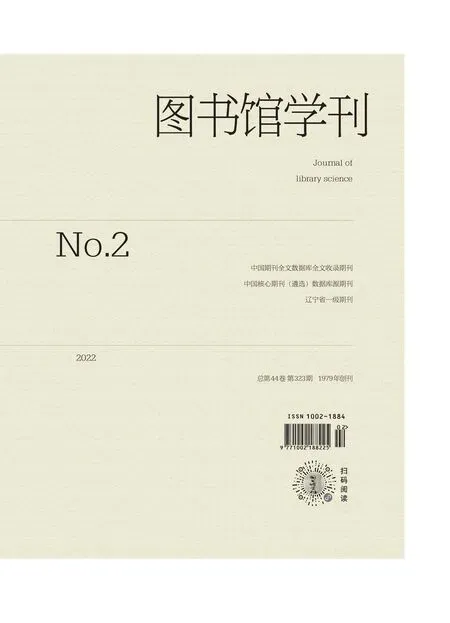阮元《兩浙金石志》訂補七則
陳 偉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阮元學問宏贍,在經史數算、版本校勘、天象堪輿等領域內都卓有成就,其在金石學領域成就則以《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為代表。其中《兩浙金石志》一書乃是阮元以一省行政長官之身份主持編纂,又積之前編纂《山左金石志》之經驗,因此收錄原則更為謹嚴,內容考訂甚是精詳。該書對于研究浙江地區之歷史沿革、人文地理等情況極具參考價值。阮元亦頗為自喜,在該書序言中稱:“使古金石自會稽秦刻以下迄于元末皆著于篇,好古者得有所稽,不亦善歟?[1]”有鑒于此,茲對《兩浙金石志》一書作簡要介紹,并對所見之七條訛脫逐一訂補。
1 《兩浙金石志》概述
《兩浙金石志》十八卷,乃是阮元任職浙江期間所編,收錄浙江地區自秦至元金銘石刻共計680種。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阮元調任浙江學政,嘉慶四年(1799)十一月又署浙江巡撫,直至嘉慶十四年(1809)八月因科場舞弊案牽涉而從巡撫任上去職。其間阮元也曾因任職京官和丁父憂而兩次離浙,但前后為官浙江仍逾十年之久。任職浙江期間阮元組織其幕僚趙魏、何元錫、許宗彥等人共同編著《兩浙金石志》。據王章濤先生《阮元年譜》記載,嘉慶元年(1796)十二月,阮元議輯《兩浙金石志》,并于次年九月前開始編撰,至嘉慶十年(1805)正月而成書。是年閏六月十五日阮父卒,阮元奏請解職,七月奉柩歸里,因而書成之后未能及時刊刻。直至道光四年(1824),粵中有抄本流傳,“校原稿又有所刪,鐘鼎錢印之不定屬浙物者亦多所刪,然亦簡明可喜[1]。”時阮元任湖廣總督,遂責成廣東按察使李沄“率浙人之官于粵者校刻之,不兩月而工畢”。是年秋,阮元子阮福又于揚州刻成《兩浙金石志補遺》一卷,收錄自藏金石及吳榮光所提供之石刻拓文共計9種。光緒十六年(1890),浙江書局又將《兩浙金石志》及《補遺》合刊,并廣為流傳。
王章濤先生《阮元年譜》又載:“(嘉慶九年)十月初一日,朱為弼為阮元序《兩浙金石志》[2]。”并于此條之下列出朱為弼的序文落款以為佐證,落款曰:“嘉慶九年龍集閼逢困敦陽月丙辰朔弟子朱為弼敬撰”,“閼逢困敦陽月丙辰朔”即甲子年(嘉慶九年)十月一日。筆者查檢知此條年譜訛誤,朱為弼未曾為《兩浙金石志》作序,所作乃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后敘》,上述落款乃敘文之落款,敘文見于《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之后。
2 《兩浙金石志》訂補
《兩浙金石志》的著錄體例是“先錄原文,偶附前代于是物之評介,后附按語說明金石碑刻文字、字體、地點、存世情況等[3]。”筆者在翻檢過程中發現該書所錄原文和考證皆有錯訛之處,茲以該書之初刻本即道光四年(1824)李沄刻本為底本,對其中的七處訛脫進行訂補。
2.1 石經歌序
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不愈游畋聲樂乎?”迨后□□□□□□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及□□□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大帝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
按:《兩浙金石志》卷八著錄宋太學石經,其中《周易》2石、《尚書》7石、《毛詩》10石、《中庸》1石、《春秋左傳》48石、《論語》7石、《孟子》11石。石經之后所錄乃是明宣德二年(1427)浙江監察御史吳訥所撰《石經歌》,上文摘錄內容乃《石經歌序》,有脫文14字,李沄刻本皆以“□”代替,今征以其他文獻,可以補足。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十、桂馥《歷代石經略》卷下皆完整收錄吳訥《石經歌序》。據此可知,“迨后□□□□□□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當作“迨后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4]”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十一所載《石經歌序》雖有缺文,而“曰寫字”三字尚存,可資參證。
“論□及□□□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依《經義考》《歷代石經略》《六藝之一錄》三書所載當作“《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此外,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十一亦載御書石經為“《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注:此在原書為雙行小字)《論語》《孟子》[5]。”另葉昌熾《語石》又載:“《南宋石經》,高宗御書,較嘉祐本無《周禮》《孝經》,而有《論》《孟》,《禮記》但有《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6]。”潛說友、葉昌熾之書所載正與朱彝尊、桂馥、倪濤之書相符,據此以補,當不誤也。
“親書扁曰光堯石經□□”當作“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除了朱彝尊、桂馥、倪濤三人之書“之閣”二字不脫之外,《咸淳臨安志》卷十一亦載:“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寘閣上[5]。”《咸淳臨安志》所載與朱彝尊、桂馥、倪濤之書亦可相互印證,可謂所補有據。
“取碑石壘□□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當作“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朱彝尊、桂馥之書“塔杭”二字不脫,倪濤《六藝之一錄》此處雖無脫文,然作“基杭”二字,郎瑛《七修類稿·杭石經并考》載:“元初西禿楊璉真伽造塔于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7]。”又《石經歌》后所收有孔繼涵之文,亦言:“元初西僧楊璉真伽欲取碑石壘塔,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1]。”可知此處脫文當以“塔杭”二字為是。
2.2 宋太學石經記
元末,肅政廉訪使徐炎改為西湖書院。明洪武十二年即書院為仁和學。殆末年復徙學于城隅之貢院。
按:此乃孔繼涵《宋太學石經記》,收錄于吳訥《石經歌》后,《兩浙金石志》未載篇名,此篇名筆者據孔繼涵《雜體文稿》所載而定。文中“徐炎”當作“徐琰”,《雜體文稿》所載不誤,“明洪武十二年”亦存疑。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六十一載:“西湖書院在杭州府治北,本宋太學故基,元至元末肅政廉訪使徐琰改為書院[8]。”又貢師泰《重修西湖書院記》曰:“容齋徐公琰始即舊殿改建書院。”由是,當以“琰”字為是。李賢《明一統志》卷三十八及沈朝宣(嘉靖)《仁和縣志》卷五均記載書院改縣學在洪武十一年(1378),而阮元《定香亭筆談》卷四及此處則俱作洪武十二年(1379),筆者未能決疑,故皆置于此。
2.3 元西湖書院增置田碑
西湖古無書院,自至元丙戌(注:“戌”,原文訛為“戍”),徐廉使改舊庠為之,創建之初,恒產缺然。
按:此碑收錄在《兩浙金石志》卷十五,又見于《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十一,其碑文乃元代湯炳龍所撰,其中“至元丙戌”之紀年當誤。依碑文之意,則是至元丙戌(1286)徐廉使(即徐琰)創立西湖書院,而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則稱:“德祐內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注:“元”,原文訛為“正”)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所西偏為書院[9]。”黃溍《西湖書院田記》亦曰:“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徐文貞公持部使者節蒞治于杭……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詳達于中書,界書院額,立山長員[10]。”又《兩浙金石志·元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碑》則曰:“(至元)三十一年,東平徐公琰為肅政廉訪使,乃即殿宇之舊改建書院[1]。”貢師泰《重修西湖書院記》亦有“(至元)三十一年,容齋徐公琰始即舊殿改建書院”之言,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以為“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浙行省長官徐琰謀改為書院,至元三十一年(1294)始得完成”[11]。至元二十八為辛卯年,至元三十一年為甲午年,而碑文作“丙戌”則誤也。
2.4 元西湖書院增置田碑
此田自瞿運使始,周廉使又為之勸率樂助,于是宏規具舉。山長陳屬炳龍記事焉。徐廉使者,東平子方也。瞿運使者,松江霆發也。周廉使者,饒州伯琦也。
按:《元西湖書院增置田碑》載:“延祐戊午,續置杭之仁和田……次年,周廉使特為勸率有高訾樂助者,并取補刊書板[1]。”因碑文未曾言及“周廉使”名號、籍貫等信息,故阮元等人于此有所考訂。上述摘句即是阮元等人所作的考訂文字,附于碑文之后。其中“周廉使者,饒州伯琦也”考訂有誤,此處周廉使絕非周伯琦(字伯溫),疑其當是周德元。另,摘句中“陳”當作“陳袤”,陳袤乃西湖書院山長,并撰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李沄刻本當是形近致訛。
據宋濂《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周府君墓銘》記載,明洪武二年(1369)六月,周伯琦卒于家,享年72歲,由此上推,周伯琦當生于元大德二年(1298)。《墓銘》又載:“(泰定二年1325)十二月,授將仕郎、廣州路南海縣主簿[12]。”是年周伯琦27歲,此為首次出仕,《元史·周伯琦傳》亦可佐證。由此可知,碑文所載之“次年”即延祐六年(1319),此時周伯琦方21歲,尚未出仕,何來“廉使”之稱。《元史·周伯琦傳》又載:“(至正)十四年(1354),起復為江東肅政廉訪使……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廉訪使[13]。”宋濂《墓銘》則記載周伯琦任浙西肅政廉訪使在至正十六年(1356)以后[12],二書所記雖有出入,但據此可知周伯琦任浙西肅政廉訪使至少是在至正十四年(1354)以后,因此延祐六年(1319)“勸率樂助”之周廉使絕非周伯琦。
西湖書院創立之后,在元仁宗、元惠宗兩朝又分別得到擴建,貢師泰《重修西湖書院記》于此有所記載,曰:“延祐三年(1316),周公德元徙尊經閣,建彝訓堂,創藏書庫,益增治之[14]。”據此推測,延祐六年(1319)周德元又勸高訾樂助者捐田于書院以“補刊書板”,當為合理,故疑周廉使當是周德元。
2.5 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
是用紀其實績,并見存書目,勤諸堅珉,以傳不朽。非獨為來者勸,抑亦斯文之幸也歟。
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見于《兩浙金石志》卷十五,為山長陳袤所撰,摘句中“勤諸堅珉”當作“勒諸堅珉”。至治三年(1323)夏,西湖書院曾對所藏書板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修復,山長黃裳、教導胡師安、司書王通等編成《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錄書籍共計122種,并被刻石留存,因此作“勒諸堅珉”方符合實際情況。民國六年(1917)吳昌綬《松鄰叢書》甲編所收之《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已改為“勒”字,可見“勤”字當是形近致訛。
2.6 元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碑
成化十二年,左布政使寗良即孤山舊萬壽寺故址重建西湖書院,見《成化舊志》。是元時院在城內后洋街,明時近孤山三賢祠,亦稱孤山書院。
按:《兩浙金石志》卷十六收錄《元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碑》,碑文為山長陳泌所撰,又見于《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十一,二者稍有異文。上述摘句乃阮元等人考訂之文,附于碑文之后,其中“后洋街”當作“前洋街”。
元代西湖書院即南宋國子監、太學舊址而建,其址本是宋代抗金名將岳飛之宅第。據《咸淳臨安志》卷八記載:“(紹興)十三年(1143),臨安守臣王請即錢塘縣西岳飛宅造國子監,從之[5]。”卷十一又載是年六月,王于岳飛宅建太學,可知國子監與太學皆在岳飛宅內,當相距不遠。且《咸淳臨安志》卷十一又提到太學在前洋街。此外,(嘉靖)《仁和縣志》卷五載:“宋太學在前洋街者,入元改為西湖書院[15]。”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十五亦有類似記載。(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十九亦載:“太學在前洋街,有大成殿、首善閣、光堯石經之閣、崇化堂[16]。”故阮元等人作“后洋街”誤也。
2.7 元周伯琦靈隱題名
至元戊戌二月廿三日,浙省參知政事鄱陽周伯琦伯溫將鎮中吳。
按:《元周伯琦靈隱題名》為摩崖石刻,見于《兩浙金石志》卷十八,摘句中“至元”當作“至正”。元代年號“至元”共使用過兩次,其一為元世祖忽必烈,共計三十一年,其二為元惠宗妥懽帖睦爾,共計六年,但兩次之中皆無戊戌年。宋濂《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周府君墓銘》稱:“(至正)十八年,丞相以漕粟事屬公,公分僚屬治姑蘇[12]。”至正十八年即戊戌年,《墓銘》所載“公分僚屬治姑蘇”與摘句中“將鎮中吳”亦合,故當以“至正”為是。
3 結語
筆者訂正《兩浙金石志》訛誤6條,另補足脫文1條,另對王章濤先生《阮元年譜》指瑕一處。《兩浙金石志》一書于浙江地區由秦至元之金石收羅詳備,其文獻價值自不必贅言,筆者限于能力在翻檢過程中僅指瑕七條,但窺斑見豹,可知在其他碑文、銘文或考訂文字中或亦有欠妥之處,因此在對該書之相關金銘石刻及考證結論進行利用的同時應當注意甄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