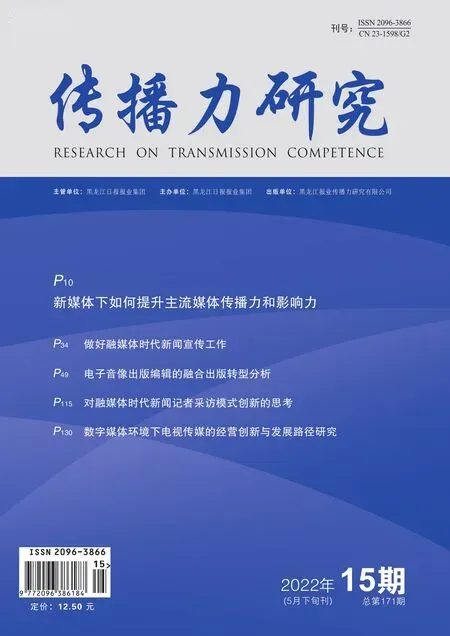試論垂直類綜藝節目的創新與發展
——以《我是特優聲》為例
◎宋佳寧
(吉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新媒體時代下,各個視頻平臺都在生產綜藝節目。雖然綜藝節目的數量不斷增長,但節目從內容、形式等多個方面趨于一致,走向“同質化”,難以讓人們 產生新鮮感。并且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人們不再滿足于接受同樣的信息,更傾向于差異化、個性化的“私人定制”。于是各大視頻平臺積極開發新題材,將注意力從大眾文化領域投向小眾文化領域,垂直類綜藝節目應運而生,進入了大眾視野。
一、垂直類綜藝節目概述
如今,物質生活領域和精神生活領域的產品日趨豐富,人類對物質和精神的要求也逐漸細化。針對這種現象,有學者提出了“垂直”的概念。垂直這個概念原用于電商領域,垂直電商是指專注售賣一個或者多個相關品類的電商。雖然在學界,垂直類綜藝節目并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垂直類綜藝中的“垂直”與垂直電商中“垂直”的概念基本相同,垂直類綜藝是指深耕某一領域,以特定專業化內容、面向特定的服務對象所生產出的綜藝節目。
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我們如今是把少數節目給極多的人看,將來是把極多的節目分給少數人看。”垂直綜藝順應了大眾文化的分眾趨勢,采用圈層化敘事手法,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圈層”原本屬于地理學概念,用來解釋地球內部的分層結構,后被引入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加以改造,應用于相關領域研究。如今隨著新技術革命和數碼領域的深入發展,移動互聯網走入千家萬戶,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互聯網為平臺,以趣緣關系為紐帶的新型人際圈層也隨之形成。“傳播圈層是一種由個體認同聯結為集體認同的社會交往”,個性化、差異化的人們因為相同的興趣愛好而形成一個集體,他們擁有相近的審美趣味、交流習慣,具有“共同體意識”,對圈層外部有一定的“排他性”。同時,“圈層傳播內容接入過程簡化,價值和觀念涵化,情緒感染加快和行動模仿傾向”,又加固了圈層關系。垂直類綜藝節目多采用圈層化敘事,提供符合圈層內審美的內容,以吸引具有高忠誠度的粉絲,是圈層文化的典型案例。
二、《我是特優聲》的節目創新點
“參與者、懸念、競爭、淘汰與選拔規則、時空規定、現場記錄、藝術加工”這是構成電視真人秀節目重要的其中元素。將從其中幾個方面挖掘《我是特優聲》的突出特點與創新之處。
(一)參與者——故事主體創新
真人秀在選擇節目參與者的時候,參與者與收視群體的相關性是必須首先考慮的。根據財報顯示,B站用戶中年輕群體占大多數,截至2020年年末,月活用戶年齡在35歲以下超過86.7%。針對這一特點,《我是特優聲》所選擇的33位參賽選手中90后占大多數,他們之中既有初入職場的配音新人,又有大四即將畢業的學生,他們的經歷和在配音方面的努力,更易激發年輕人的共鳴。《我是特優聲》將年輕的33位參賽選手構建成觀眾關注的對象,讓觀眾感到參與者的親和力和接近性。
其次,真人秀的人物之間的互動也必不可少。參與者需要構成一種網狀關系,這種網狀關系也是構成故事和主要看點的元素。《聲臨其境》的參與者主要是演員,如第三季第一期,邀請了何冰、胡軍、韓雪、俞灝明、秦俊杰、賈乃亮等,他們之間的關系主要是由節目賦予的,是因為節目安排才走到一起來,之間的互動難免顯得生硬,不利于故事的挖掘。而《我是特優聲》的參賽33位選手中,共有25名配音相關從業者,他們有些來自于同一個工作室或是在以往的工作中相互熟識,加之他們偏向于素人的身份,不用考慮對自身形象的維護。選手之間的互動就如同朋友之間的互動一樣,流露自然。
(二)懸念——敘事動力創新
能否制造出動力性目標是一檔綜藝節目能否從綜藝節目市場中脫穎而出成為爆款的關鍵,對于真人秀節目的參與者而言,這種動力性目標,如對優勝者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能夠驅使參與者去積極行動,參與者的積極性越高,對達成目標的渴望性越強,整個綜藝的敘事就越有吸引力,更能激發觀眾的觀看欲望。因此,故事的目標就作為一種懸念,推動參與者和觀眾與節目的進程捆綁在一起。在真人秀中,參與者和觀眾的目標是確定的,但是優勝者卻是不確定的,這正是真人秀的魅力之一。而在《我是特優聲》中懸念這一概念貫穿了節目始終,賽制隨機性非常強,如比賽一開始為選手提供八部作品共二十四位角色進行試音,每位選手有三次試音機會,選擇同一角色的參賽選手會進入封閉獨立的試音間,憑借一句臺詞讓導師評判能否拿到該角色。對于參賽選手來說,二十四個角色中是否有合適自己的角色,競爭對手的實力,這一句臺詞的發揮,都是未知的。
(三)競爭——網感化手段講競爭
《我是特優聲》作為一檔聲音演員競技類節目,節目中的“競爭”元素必不可少,但競爭在諸多綜藝節目中又屬于老生常談的問題,如何把“競爭”講得有新意?《我是特優聲》采用了網感化敘事。隨著互聯網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綜藝節目要想依托互聯網進行廣泛的傳播,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網感”必不可少。于是“網感”也成為國內影視研究中一個流行的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念是這樣解讀的:網感是指影視作品具有網絡文化的風格特點和傳播規律,具有碎片化、感官化、青春化的內容氣質,有一定的情節爆點和情感痛點,有較強的用戶參與性和體驗感,是網絡審美文化、價值取向、流行思潮的集中體現。有研究者從四個角度定義了“網感”,從內容上來看,網感要求節目制作者迎合年輕人的興趣,制造年輕人感興趣、能參與的話題;從形式上來說,拒絕起承轉合邏輯清晰的線性敘事,突出變化、新意與刺激;從人物上來看,需要表現對象有娛樂精神;從宗旨上來看,突出正能量、娛樂性。《我是特優聲》所選擇的配音作品中有大量年輕人喜愛的動漫橋段,如《霧山五行》《天寶伏妖錄》等,由于年輕群體對這些作品較為熟悉,他們能夠對選手配音的表現進行評判,提高參與感;從剪輯上來看,將更具有視覺、聽覺沖擊力的選手舞臺表現集中展示,既能讓選手們的表現形成對比,又能給觀眾帶來新意和刺激;從人物上來看,節目安排了許多環節去挖掘選手的娛樂價值,如《下一個是誰》,該環節會把相機交給選手,讓選手去拍他們之間的互動。又如,UP主企劃會安排選手圍坐在一起,對青春、情商、愛情觀等年輕人感興趣的話題進行討論;從宗旨上來看,既體現出了個人為了達成目標所做的努力,如演員高凱拿到《寶蓮燈》孫大圣的角色后,雖然該角色的配音難度較大,但經過他的反復練習與虛心請教,最終在舞臺上很好地呈現了這個角色;還體現出配音行業內的互幫互助,哪怕在比賽中是競爭對手的關系,更有經驗的配音前輩也會幫助新人去打磨角色。這些網感化的手段使《我是特優聲》獲得9.0的評分,這正是網感化敘事取得的成果。
(四)淘汰與選拔——增添戲劇化
在幾乎所有競爭性娛樂行為中,最具有戲劇性的變化就是勝利和失敗,《我是特優聲》將決定選手成敗的人多元化,四位導師中有兩位專業配音演員、一位老演員還有一位飛行嘉賓,四個人會從不同視角對選手的表現進行評判,加上現場觀眾的投票,增強了勝負的不確定因素。例如,選手趙乾景的晉級之旅,就體現出了故事的不可預知,他由于自身的異質性和個人魅力,在一登場就受到了較多的關注,被寄予較高的期望。但在第一個盲選試音環節沒有得到評委的認可,之后也沒有得到合適的角色,險些遭到淘汰。雖然開局不利,但在后期的比賽中表現不俗,最終取得總分第一的成績。
(五)時空性——奇觀化展現
真人秀是一種敘事性的節目形態,所有的敘事都必須有一個封閉的時間和空間,行動者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完成任務和達到目的,封閉創造了故事,或者說創造了故事的緊張、期待和節奏。《我是特優聲》就通過將比賽的空間奇觀化,來激發觀眾的觀看興趣。
“媒體奇觀”的概念來自道格拉斯·凱爾納,他將那些被媒體渲染到極致的事件稱為“奇觀”,指的是“那些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垂直類綜藝節目往往通過奇觀化的主題、人物、場景布置、故事布局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通過奇觀化敘事提供超越日常生活的奇特體驗。以《我是特優聲》為例,節目為了更直觀地展現配音的魅力,將配音演員請到臺前來,相較于在錄音棚為角色配音,臺前的配音給選手提供了表演的空間,如第二次公演中趙乾景和高其昌兩位選手將漫畫《鏢人》搬到了舞臺上,在配音的同時加上了表演。舞臺配合以燈光、舞美等技術手段來輔助展現,給觀眾帶來了視覺享受。
三、垂直類綜藝節目的發展與反思
(一)節目制作方:精準定位,力求“出圈”
從內容上來說,垂直類綜藝節目致力于深耕一個領域,注重展現一個領域的面貌,又有較強的專業性。這些特點對于某些觀眾來說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如《我是特優聲》能夠吸引配音愛好者,《舞蹈風暴》能夠吸引舞蹈愛好者,這些愛好者所形成的圈層,即為垂直類綜藝節目主要的受眾群體。但圈層具有排他性,圈層內部能從中獲得審美體驗的內容,可能不能引起圈層外部的共鳴。圈層外部缺乏進入圈層內的動力。一檔節目的好壞與觀眾的口碑是密不可分的。在獲得圈層內受眾的認可后,如何“出圈”,吸引更多圈層外的受眾去接觸節目并獲得他們的口碑成為了節目制作方需要思考的問題。因此,節目制作方要滲透破圈元素,讓更多人去了解該綜藝節目所垂直的領域,從而提升節目的社會價值。
(二)節目宣發方:細化渠道、打破“廣撒網”
綜藝節目內容不斷細化,受眾定位越發精準,這給節目宣發方帶來了挑戰,能否將垂直類節目的相關信息準確地投放到受眾所在的圈層,這影響了垂直類綜藝節目的宣發效率。但目前國內綜藝的宣發模式還是處于“廣撒網”的狀態,既依靠微博、自媒體炒作話題作為主要宣發手段,等待目標受眾自行撞進“網”,但在綜藝節目是滿足特定受眾的個性化、專業化需求時,這種“廣撒網”式宣傳所產生的效果相對淺顯,所以垂直類綜藝節目宣發時也要細化渠道,進行覆蓋式宣傳,深入與之相對應的圈層受眾所在的社交平臺,制作與節目內容相符合的短視頻、軟文等進行宣發,以此為主,并以在微博、自媒體等廣泛式平臺上做細化式宣傳為輔助,如選擇圈層受眾所在的微博超話進行宣發,以形成具有針對性的宣發矩陣。
(三)節目播出平臺:強化個性,提供“私人定制”
節目播出平臺為了迎合互聯網時代受眾個性化、差異化的需求,引入多樣化的內容進行播放。如騰訊視頻平臺上有電視劇、電影、綜藝、動漫、少兒、紀錄片等多個內容分區。未來,受眾對精神產品的審美要求不斷提高,節目平臺為了吸引受眾,將會承載更多樣化的節目,這樣的分區將不斷細化。而現行的會員免廣告、會員專區這種粗獷式的付費模式將會迎來挑戰,因為在會員制的付費模式下,付費用戶購買了大部分節目的觀看權限,而他們只看符合他們個性化需求的一小部分節目。如某一懸疑電影的受眾購買會員后,可能并不會觀看除懸疑電影外的內容。或許將來可以改變會員制這種簡單的付費模式,朝著定向付費發展,既用戶根據自己的需求為單一分區,甚至某一個節目、節目中的某一集進行付費購買,如貓耳FM等一些音頻APP上就實行著這種付費模式。《我是特優聲》在付費模式上也做過類似嘗試,它將舞臺純享版和花絮設置成會員專享,讓對該節目更有興趣的人進行付費,可以讓感興趣的受眾了解比賽的更多細節,而其余部分無需付費,這可以吸引對這個節目沒那么感興趣的普通受眾。在定向付費的模式下,受眾想看哪個買哪個,將自主選擇權交到受眾手里,這既給受眾帶來了一種節省付費的感覺,又會給制作方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