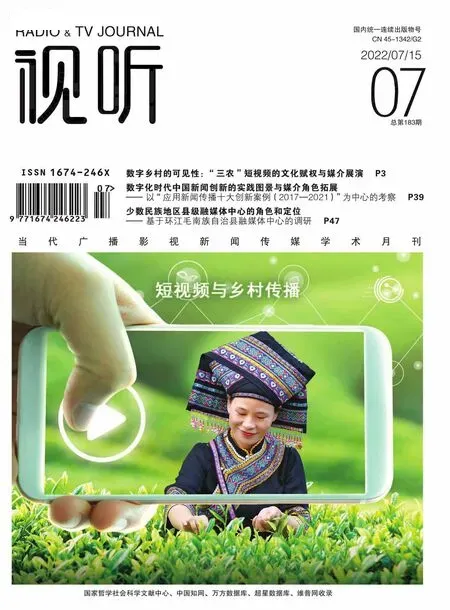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的角色和定位
——基于環江毛南族自治縣融媒體中心的調研
韋丹宇
近年來,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下文簡稱“環江縣”)頻頻獲得各級領導的關注和政策上的傾斜。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少數民族地區脫貧攻堅“絕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的重要指示下,環江縣開始不斷創新并大力推行“六聯一帶”、八大產業扶貧、就業幫扶等扶貧改革性舉措。2020年5月9日,環江縣正式退出貧困縣行列,毛南族實現整族脫貧。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視察時再次寄語少數民族地區和群眾:“擺脫貧困,接續奮斗,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在鄉村振興新征程上邁出堅實步伐。”①2021年7月2日,環江縣被確定為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自此邁上鄉村振興接續脫貧攻堅的新征程。
鄉村振興不是從無到有,而是在脫貧攻堅戰役取得決勝的基礎之上繼續盤活地區資源,重組物質資料和社會資料②,文化振興是提升鄉村“軟實力”和村民思想境界的保障。現實意義上,文化的發展能夠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鄉村基層整體的文化水平和素養;戰略意義上,文化的振興能夠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支撐;實踐意義上,鄉村文化振興能與其他基層戰略子系統同頻共振。因此,鄉村文化振興與縣級融媒體中心的發展存在著內在聯動性。高質量發展的文化產業能夠為縣級融媒體中心帶來可見的效益,反過來,縣級融媒體中心又能夠發揮自身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對內可興盛差異性、民族性的文化,對外則可形塑民族文化形象和品牌,反哺鄉村文化振興的發展。二者有機協同,有利于為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注入強大活力,為鞏固經濟成果、發展文化旅游經濟、實現民族文化品牌化打開新局面。
基于鄉村文化振興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這兩大政治任務能夠并行并舉、相輔相成的假設,本研究以鄉村文化振興為切入視角,以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為目標導向,對環江縣融媒體中心進行了實地調研,提出并試圖解決以下問題: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中應當或者能夠扮演怎樣的角色,將遇到怎樣的問題并如何解決。
一、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現實可行性
鄉村文化振興作為一項偉大的社會實踐,將受到場域、資本和慣習的綜合作用③。環江縣是地處我國西南邊陲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是全國唯一的毛南族自治縣,曾經是國家貧困縣和廣西深度貧困縣之一。同時,環江縣孕育著獨特的毛南族文化,花竹帽、儺面、肥套儀式、民歌等都是其引以為豪的文化象征。環江縣還擁有體量巨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截至2019年年底,環江縣登記入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達1442個。可見,環江縣以文化產品為符號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雄厚,是典型的豐厚的文化資本與貧瘠的經濟資本不相匹配的少數民族地區樣本。作為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之一,環江縣融媒體中心的建設與發展也具有代表性。環江縣融媒體中心雖然成立時間短、經驗不足、發展不成熟、受制于當地較為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但卻表現出了因地制宜謀發展的勁頭,形成了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環江樣本”。
(一)在地性優勢:民族文化傳播者
環江縣融媒體中心于2019年8月掛牌成立,其建設和發展是縣內“一把手”工程中的一部分。承載著“講好環縣故事、傳播環縣聲音”的職責和使命,環江縣融媒體中心發展成為當地涵蓋客戶端、微信公眾號、抖音號和微博號等傳播平臺的社會信息樞紐。在脫貧攻堅時期,縣級融媒體中心為扶貧主體提供的信息服務具有“嵌入式”的特征④,彰顯了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上的在地性優勢。而在鄉村文化振興的視野下,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在地性優勢則體現在能夠深入當地文化生活和文化實踐中,用真正的“源頭活水”塑造典型,打造少數民族地區獨特的文化立面。2021年2月,環江縣融媒體中心推出了一檔集平民化、娛樂服務性為一體的本土情景互動類欄目《毛南哆來咪——跟我學講毛南話》。每期視頻時長不超過3分鐘,在視頻內容上著重介紹了頗具毛南族特色的花竹帽、毛南族服飾、毛南族民風習俗等,在視頻制作上則與一般的網絡短視頻拉開了差距,畫質清晰,手法細膩,制作精良。2020年年底,“環江融媒”客戶端投入使用。環江縣融媒體中心在App的內容開發和界面設計上極其注重少數民族文化的視覺傳達。例如,App的logo是一頂花竹帽,欄目引導背景是一位身穿毛南族特色服飾的姑娘。此外,特辟《毛南文化》專欄,向讀者介紹毛南族語言、服飾、飲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該中心負責人說:“這也是我們盡力打造App的原因,就是要把我們的文化特色展現出來。”
(二)適應性優勢:基層社會記錄者
在全國范圍內建設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實踐中,我們發現,縣級融媒體中心能夠較好地適應獨特的鄉村社會體系,與基層縣域具有高度的適配性。鄉村縣域是費孝通筆下的“鄉土社會”⑤,縣級融媒體中心的文化傳播路徑遵循著熟人社會中特殊的人際傳播規律,重視人與人、人與地域之間的連接。環江縣融媒體中心設立了獨特的駐村通訊員制度,大大擴展了該中心對縣內輿情信息的掌握度和視野范圍。一方面,駐村記者大多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和民族語言,與民眾進行交流,村莊內發生的大事小事新奇事經過駐村記者的簡單采訪后,基本的新聞素材都能迅速到達縣級融媒體中心進行進一步加工。另一方面,各通訊員往往就是村支書和其他村干部,他們的社會關系也是縣級融媒體中心重要的軟資源。就算是不便進行溝通交流的采訪對象,對該采訪對象的生產生活情況頗為了解的村干部也能為新聞信息采集做出貢獻。同時,駐村記者在生活習慣上能完全融入當地,更懂風土人情,也更能挖掘當地的亮點和特色。目前,該中心官方抖音賬號“環江融媒”基本保持兩天更新一條短視頻的頻率,視頻內容涉及市縣重要會議、防疫政策宣傳和航拍形象宣傳片等,真正發揮了自身優勢,做到扎根基層、記錄基層。在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時期,該中心還發布了壯語和毛南語版的一次性口罩教學視頻,主持人身著民族服裝,仔細嚴謹地示范正確的口罩戴法。輕松的氛圍,有趣的方式,語言的親近,進一步增強了該視頻的傳播力,同時也塑造了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受眾心目中的親民形象。
(三)引導力優勢:產業發展路徑創新者
文化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戰略中文化振興和產業振興的交叉點,縣級融媒體中心作為地方社會力量的調動者和信息交互樞紐,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大量民族特色傳統文化未實現最大化開發的背景之下,必須加大力氣盤活好當地文化資源,并不斷探尋多種商業化變現可能⑥。分龍節是毛南族最為重要的節慶儀式,環江縣各媒體歷來十分重視對此節日的宣傳報道。在融媒體中心建成之前,宣傳報道主要以系列文字主題報道為主,縣級融媒體中心成立后,內容和形式更為豐富多樣,包括制作主題曲、音樂短片、縣域形象與節日活動宣傳片、網絡直播、電視直播、短視頻報道等。與網絡宣傳活動一齊開啟的是特色農產品的線上銷售渠道,各類商品悄然登上“小黃車”。對少數民族重大節慶活動的組合報道,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打造環江縣的文化形象,推動少數民族文化品牌的建設,吸引更多受眾前來體驗少數民族風情和民俗,發展文化旅游產業。除了少數民族文化節日,極具毛南族特色的花竹帽編織、儺面制作也具備“走出去”的潛質,但這些高度依賴手工技藝的民族文化藝術品由于缺少傳承者、市場需求量較小以及制作成本較高等特點難以實現量產,也難以走向更廣闊的受眾市場。在市縣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指導下,縣級融媒體中心應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上做好引導,下功夫挖掘民族手工藝品的藝術價值,同時創新傳播方式和手段,加大記錄和宣傳的力度。而更重要的則是路徑上的創新,需要縣級融媒體中心勇于嘗試,將目光投向數字化文化創意產品制作、數字化文化遺產保護、數字化文化旅游等領域也未嘗不可。
二、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困與變
(一)理念困局:民眾依賴心理的延續
民眾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形成的對政府主體的依賴心理是鄉村振興中的突出難題。勞倫斯·米德認為,貧困的代代相傳通常是由于貧困者在長期接受福利救濟的過程中,在思想和行為方面已經產生了依賴。在過去的扶貧實踐中,中央乃至地方政府針對少數民族地區脫貧均實現了多種政策上的照顧和傾斜,這有可能造成以往的扶貧對象、如今的振興主體對政府機構的“帶頭”“保障”和“兜底”作用產生依賴,從而導致“貧困的代際傳遞”。實際上,筆者在環江縣下南鄉南昌屯調研走訪時發現,在就如何利用電商直播平臺銷售農產品致富的問題上,大部分村干部和村民都認為這是個“自己單干不了”的活。他們更希望由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帶頭統一搭建起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平臺,輪流直播賣貨,實現盈利。然而,單一主體的方案并不利于毛南族特色農產品在網絡平臺上打開局面,而流量在當今儼然是一種可變現的“資產”。民眾的被動和過度依賴,將使其陷入“貧困——幫扶——返貧——幫扶”的“死循環”。
(二)現實困局:“內外交困”的營收境地
受自然資源、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長期處于經濟欠發達的狀態。目前,國家對于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基本規劃是前期財政撥款、人力支援與后期自負盈虧相結合。不同于我國部分經濟較發達地區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已實現自負盈虧的趨勢,環江縣融媒體中心由于成立時間較短,仍屬于依靠財政撥款的公益性媒體機構。整體上看,環江縣雖然剛剛擺脫了貧困,但是離“富起來”和“強起來”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一方面,有限的財政撥款使縣級融媒體中心難以放開手腳搞建設,中心內部僅27名編制人員和20名聘用制人員,待遇不太理想。“留不住人才”是環江縣融媒體中心主任著重提到的發展難題。另一方面,由于主要面向基層縣域傳播場,受眾基數小,與其他的社會化媒體、商業媒體及網紅自媒體之間存在競爭,靠內容輸出和作品打造實現流量變現并不現實。因此,環江縣融媒體中心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內外交困”的營收境地,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助推鄉村文化振興的腳步。
(三)主體困局:生產建設能力和傳播力不足
如前所述,環江縣融媒體中心并不缺乏優質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經過精心的包裝和宣傳,一旦在網絡平臺上打開局面,就能將其轉變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激發民眾在資本轉變上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但該中心在新聞內容主題分布上以政治信息為主,文化宣傳和報道次之,經濟服務信息較少,未能很好地承擔起“信息服務中心樞紐”的重任。例如,該中心的文化宣傳報道在時間上較為集中于每年的分龍節前后,其他時間則更多以時事新聞、民生新聞為主,在文化傳播上較為欠缺。雖然該中心開始具備了注重民族文化傳播的意識,但由于主體單一,內容生產受限,目前客戶端上對毛南族特色文化的宣傳文章數量較少。此外,制作精良、受到好評的《毛南新生活》欄目也無法做到定期更新,僅更新至第五期便停更了,時間停留在2021年4月。這進一步說明,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容易面臨內容生產難以為繼、信息生產能力不足、平臺運營持續性不強、總體傳播力不足的問題。
三、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助力鄉村振興的路徑優化
(一)豐富功能定位,強化鄉村振興的帶頭作用
德國學者馬萊茨克在對傳播模式的研究中提出,不論是信息的傳者還是受者,都將受到一定的“媒介壓力”。這種媒介壓力在現實中則體現在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特色農產品生產者身上。不論是個體還是商戶,都有使用互聯網進行盈利的需求,但由于受到文化教育水平、語言溝通障礙、設施設備不完善等限制,他們難以較好地利用媒介工具,還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媒介使用障礙。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完善縣級融媒體中心的教育引導、帶頭示范、平臺搭建的功能加以解決。縣級融媒體中心依靠自身搭建起的融媒體平臺開展助農直播,往往能獲得很好的收益。2020年3月25日,在“環江融媒”抖音號上,一場由環江縣副縣長現身主持的“助農”特產推介直播總共獲得了75萬點擊量,環江特色農產品沃柑、臘腸和“五香產品”都獲得了可觀的銷售量。駐村記者的作用也進一步體現出來。以地區為劃分的電商直播“幫扶+教育”模式,一方面使每村有電商直播賣貨需求的農戶都能用上先進的直播設備和布景,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不浪費,普通個體商戶也能排得上隊;另一方面,在專人專點、分點負責的管理下,也能更好地提高駐村記者和縣級融媒體中心的電子商務運作能力,實現縣級融媒體中心多個平臺的常態運營。
(二)完善信息樞紐功能,增強影響力和引導力
媒體天然是信息的傳播者,縣級融媒體中心必須擔任好本地信息資訊服務的提供者角色,否則,無法協同社會治理,也無法實現縣域象征資本和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轉變。縱觀環江縣融媒體中心的建設情況,整體而言,政務服務一體化的平臺還未完全建立,信息服務水平較低,說明該中心目前仍處于“組織融合”的階段,而未能完全匹配預期的“信息樞紐”和“服務窗口”戰略定位。考慮到少數民族地區在資源上的限制,縣級融媒體中心更應重視自己“信息服務樞紐”的角色和定位,起碼要在提供更優質的經濟信息服務、內強鄉村振興信心、外塑民族文化品牌上下功夫。為此,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融媒體中心應當積極探索跨部門協作的“信息+”服務,形成多域聯動的良好效應。當縣級融媒體中心與更多政府部門形成更好的協作關系時,其影響力和引導力必然也能得到提升。
(三)發展“民族+人才”的培養模式
基于環江縣融媒體中心優質內容生產難以為繼、財政資金緊張、技術人才欠缺、整體內容生產力較為薄弱的情況,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必須形成“民族+人才”的人才培養模式。在政策設計上,少數民族地區政府及相關部門要用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牽頭引進新聞專業技術人才,在縣級融媒體中心內部建立起正向的獎勵機制。要肯定成果、褒獎模范,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經濟回報,進一步鼓勵中心記者堅持文宣創作并創新內容和形式。同時,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融媒體中心還必須著重培養土生土長、了解當地民風民俗的新聞專業人才。這類人才一方面具備新聞傳播專業知識,具有較高的政治素養和理論素養,能夠勝任鄉村文化振興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們對自己的家鄉充滿了感情,作為“局內人”的文化優勢使其更能敏銳地洞察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振興特色,并調動起縣域內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打響民族文化品牌,以優質和差別化的文化內容生產和傳播,服務于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文化振興實踐。
四、結語
在縣級融媒體中心研究側重于描繪經濟發達地區成功案例的現狀下,“目光向下”地看到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小眾的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樣本是必要且迫切的,這是新聞傳播必須面向社會和大眾的規律的體現,同時也是重新發掘西部傳播的當代意義、反思和振興新時代新聞傳播學的需要⑦。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接續脫貧攻堅戰實踐和媒介融合戰略,在全國范圍內并行并舉、大力鋪展,少數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必須在承擔起縣級媒體原有職責的基礎之上,依據新時期的新政策、新目標扮演好新的角色,滿足國家、政府和人民對于縣級融媒體中心的新期待。這就意味著,縣級融媒體中心不僅要探索在“縣級媒體新機遇”“社會治理新樞紐”“政務服務新平臺”等方面的新成果,還應當努力開展興盛區域性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動員民眾參與文化傳播的實踐,在鄉村文化振興中做到有為、有位、有威,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注釋:
①權晟.信仰之光照亮百年征程[N].河池日報,2021-07-01.
②李澤璐.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文化建設路徑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20.
③石怡欣.民族地區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文化傳播現狀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20.
④王憶錦.信息扶貧視野下的縣級融媒體中心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20.
⑤耿曉夢,方可人,喻國明.從用戶資訊閱讀需求出發的縣級融媒體運營策略——以百度百家號 “用戶下沉”調研分析結論為啟示[J].中國出版,2020(10):3-7.
⑥吳重慶.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J].讀書,2011(01):19-25.
⑦沙垚.發掘西部傳播的當代意義[J].現代視聽,2019(07):85.